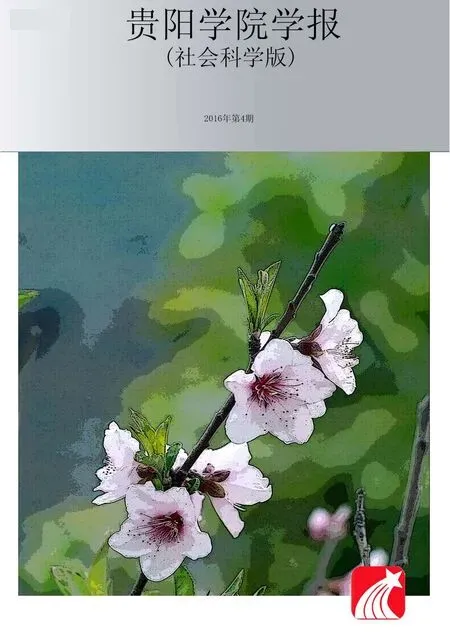民国初期舆论界清算用人瞻徇思想刍议
——基于《申报》和《盛京时报》的历史考察
2016-03-18赵炎才
赵炎才,蔡 伟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武汉市江汉区信访局 湖北 武汉 430000)
民国初期舆论界清算用人瞻徇思想刍议
——基于《申报》和《盛京时报》的历史考察
赵炎才1,蔡 伟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武汉市江汉区信访局 湖北 武汉 430000)
民国初期,针对传统与现实的官场表征,一些有识之士在报刊上猛烈批判用人瞻徇的弊端,认为如此势必导致所选之人多非贤才、私欲膨胀肆无忌惮与残害己身危害国家。根据其严重危害和传统血缘宗法思想等消极影响,他们围绕如何祛除用人瞻徇弊害,在思想、学理、原则、标准、操作、管理等方面作了一定探索,以期构建合乎近代民主共和精神的择人用人学说。
民国初期;舆论界;用人;瞻徇思想;清算
民国初期,伴随新旧政制鼎革,共和政府肇立,如何择人施政遂成新政府为政之道的首要议题,也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议题。古人云:“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1]2370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强调“为政之道虽经纬万端,要在得人而治”[2]68-465。他们认识到选贤任能之于共和的发展与完善极具价值,一再声言“选才任能,贤者当国,此古今不移之定理也。”然而,在具体施政过程中,用人瞻徇现象却颇为盛行,所谓“瞻徇私情,政界通病”[3]42-93直接道出其弊害。为促进中国近代择人施政渐入正轨,这些有识之士对此一弊害作了一定学理清算。笔者拟以他们在《申报》和《盛京时报》等报刊所发表的论说和时评为中心,尝试厘清其清算用人瞻徇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而揭示其所蕴含的积极文化价值。
一、“瞻徇”乃民初政治中“用人之大蠹”
1.“瞻徇二字,实吾国用人之大蠹。”
民国初期共和肇立后,如何进一步“肃官方而饬吏治”,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可谓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孙中山曾明确指出:“民国成立,万端更始,旧日城社,扫除略尽,肃整吏治,时不可失。然而法制未班〔颁〕,考试未行,干进者有〔存〕乘时窃取之心;用人者有高下随心之便,一或不慎,弊将有甚〈于〉满清之季者。”为消除传统吏治之弊害,他强调“该部总、次长等于用人之计,务当悉心考察,慎重铨选,勿使非才滥竽,贤能远引,是为至要。”[4]258-259后来孙一再明示民国临时政府相关部门尽快完善相关制度以做到铨选有程,官惟其才。事实上,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诸如《文官考试令草案》、《任官令草案》等文官法草案。后来以袁世凯等军阀主导的北京政府也曾颁布一系列相关法案,构建起中国近代文官制度。虽然如此,如何真正将其外化于政府施政过程之中,却面临诸多困难。
其时,政界中漠视共和真精神,用人瞻徇,吏治败坏等现象日趋严重。对此,有论者惊呼道:“嗟乎!光复以来,吏治之不饬也已久。”[5]27-269此一情形严重毒化人们的实际政治判断,仿佛此时之民国仍不脱清朝专制之巢穴。在一般民众看来,虽然专制确为弊政,但共和成立后,其所带来的危害更甚于专制,故“今日之中国,不得谓为共和真已成立也”[6]21-118。而如此名实相悖往往与共和政府官员政治道德堕落密切相关,所谓“国家政局之混乱分裂,社会情状之龌龊卑鄙,何莫非不道德阶之厉”[7]52-503。其中用人瞻徇可谓其中最主要、最突出的外在表现。有鉴于此,民初社会舆论界针砭之论可谓不绝于耳。如有论者直言不讳地指斥道:“瞻徇二字,实吾国用人之大蠹”[8]27-262。其言论可谓一针见血,触及一定问题实质。
2.用人瞻徇乃近代公私义利之错位
从语义学角度来看,所谓瞻徇即左右瞻顾屈意相从,至于用人瞻徇则具体表现为身居津要的官员罔顾既定法律法规,徇顾个人私情,援引、任用私人之谓。揆诸历史,不难发现,此乃中国传统官场的首要弊政之一,是导致吏治隳堕,政局紊乱的罪魁祸首。因此之故,历代官方对此颇为警惕,诘责之言可谓史不绝书,其中有清一代的表现颇为突出。如雍正帝批谕广东总督鄂文恭疏曰:“身膺封疆要任,当远大是务,不宜见识浅狭。公私界限,只在几微念虑之间,一涉瞻徇,即为负国溺职,重则贻累功名事业,轻亦难免物议于己,毫无裨益。”[9]364而光绪七年(1881年),礼部侍郎宝廷在其上疏中批评官场存在“瞻徇情面之弊”,力倡官员为政要能“破除情面”[10]213。清季袁世凯主持练兵时亦视用人瞻徇为行军之大忌,认为引用私人,“以瞻徇而成姑息”势必多行不义。此期梁启超亦重法律,强调裁判官厅独立可做到“守法而无所瞻徇”。这些论述虽主旨有别,但反对用人瞻徇的精神却无不相似。
迨至民初,针对政治领域徇私枉法之弊端,民国政界士人多有警示之语。如宋教仁就任农林总长后曾在报刊上刊登启事,明确表达了拒绝用人瞻徇的坚定立场。[11]464-5851913年,袁世凯论及政府用人问题时曾自责道:“夫用人实行政之本”。“本大总统,因循瞻徇,咎固难辞。”针对现实用人瞻徇的弊端,1915年,袁发布申令,告诫官吏应将“戒偷惰、戒瞻徇、戒奢靡、戒嬉游”奉为官箴[12]858。袁氏此举之动机与效果姑置不论,仅从其反省与训诫之言中不难窥见民初政治中用人瞻徇现象已非常严重。熊希龄就任总理后,对那种干辛之徒请托运动、包办推荐之举颇为反感,认为这只会将共和推向毁灭边缘。针对国事艰难,财源奇窘,民国财长周学熙亦反对用人瞻徇,指出“以一时瞻徇之故,致误要政而累大局”[13]558。可见,用人瞻徇实乃政治领域中公私义利错位的畸形表现,理所当然受到民初政界拒斥。
3.社会各界呼吁祛除用人瞻徇之害
与此相适应,在社会上,反对乃至要求祛除用人瞻徇的呼声也是此伏彼起,不绝于耳。如1918年,邵力子要求那些为政者具体施政应以国民人格和国家荣誉为重,不可瞻徇乡谊而因噎废食。1924年,邵氏又指斥教育领域中用人瞻徇实为中国教育界之病根,批评各地教育当局位置私人,各校长与教职员等勾结私党以扩张一己之势力。[14]934-935常寿祺也指出:从前许多办教育者存在根本性错误观念,视神圣事业的教育为一种差事,抱定利己主义,只知“为人谋事”,不去“为事择人”。究竟所聘请的教员是否懂教育,有无国家观念等概置之不问。[15]270教育领域的用人瞻徇现象实乃政治用人瞻徇的自然延伸,其危害性不言而喻。
针对民初用人瞻徇之陋习,这些有识之士痛加诘责,指出:“操用人柄者,其材识且不必言,即此瞻徇之念,已足摧毁一切而有余矣。”因此,“瞻徇之弊一日不铲除净尽,则所以败坏人才者盖至钜,以致后人将不勉为有用之才,而慕荣戈禄之恶根性,且深固而不易拔也。”“苟不铲除净尽,窃恐庶政之棼乱,有如昨日”[8]27-262。如此言辞颇为激进尖锐,深中肯綮。
二、现实社会用人瞻徇思想的突出表征
在民初政治中,这些有识之士认为用人瞻徇的具体表征甚多,其中最突出者有四:择人用人唯亲是尚、人才取舍一任私意、知法违法任免随意与选用人才标准不一等方面。
1.择人用人唯亲是尚
伴随新旧政治鼎革,个人主义盛行,固有人情观念影响,个人私欲恶性膨胀并泛化于大众广庭之下。由于追逐私利乃国人之大病,极端个人主义为具体表现,如私交重于国事,攘利加于公益,民初择人用人唯亲是尚遂大行其道。在这里,所谓任人唯亲即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亲疏远近,或以地域、团体的价值观、情感与好恶等为衡量取舍标准来择人用人。有论者指出:“古人以言不及私为美德,而今则无论为公团、为法定机关,均以各护其私为目的。且于大庭广众中,言之不怍”[16]26-144。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中任人唯亲是尚的突出表现为“为人择事”与“为人择地”两方面。对此,有论者指斥道:“惟瞻徇,乃不能为事择人,有时且为人而择事”[8]27-262。也有论者认为民国冗官之多实因“为人择地,非为地择人也”[3]42-93。这里的“为人择事”与“为人择地”显然不是尊重人性因才任事之积极义,而是当事者依据个人之好恶来择人用人的消极义。对其政治危害,宋教仁指出:“现用人行政,为人择事,并非为事择人,故各机关冗员异常众多”,政治日趋腐败。[11]464-585至于其严重践踏人才的恶果,有论者亦剖析道:“我国比年以来,内政不纲,中枢解纽,旁求英俊,久置缓图,英秀奇才,无由自见。”“为人设事,故无问其能不能,因爱授职,更不论其才不才”[2]68-465。在这些有识之士看来,此一现象如不更张“则求以底庶绩而贞百度,盖戛戛乎其难之矣”[8]27-262。
2.人才取舍一任私意
不仅如此,“考试有倖,保荐有冒荐,有冒滥”也是用人瞻徇任人唯亲的具体表象。对文官考试存在的瞻徇人情名实相悖现象,有论者批判道:“夫登庸人才之道,不外考试与推荐。”从理论上而言,凡“有入考之资格,一经考中,即可与分发人员一体任用。然名虽如斯,其有人情者仍可优先得有位置。其乏人请讬者,仍不受弃置闲散。”[2]68-465囿于人情与故旧,民初滥用职权保荐官员者可谓比比皆是。有论者描述道:今日之荐举搜罗仅及于官僚,荐举率为故旧。第见善夤缘者得官,不善钻营者向隅。以长官易员,而随以来者纷纷。“举凡弁兵走卒,婢妾近亲,一经有力者之提携,即可出任官吏”[17]67-417。不仅如此,排斥外省人的地方观念也日甚一日。囿于任人唯亲之故,主政者恣意妄为导致公举与委任弊害丛生。有论者指出:所谓公举与委任本来有利无弊。然而,由于厕乎其间者妄为主持,其利未见而弊乃相引于无穷。如各部各省官吏的任用既无确实标准又无一定手续,取舍之间,一任私意。由于未能如乎民意,以故民间之抗不承认亦多有所闻。至于以党见划线的现象也比较突出,植党营私党同伐异的现象层出不穷。如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尽驱民党诸督,而代以己派人物”。有论者深以为忧,指出:“救中国今日之大患,不在人材之缺乏,而在当势者之植党营私,有才者不能用。”[2]68-465其一针见血的评论是何等之深刻。
3.知法违法任免随意
民初用人瞻徇弊端还表现在那些当事者缺乏起码的近代政治道德,漠视法律精神,知法违法任免随意。对此,有论者指出:“民国成立后,政务官之任免随意,黜陟如奕棋无论矣。以言乎普通行政官吏,其任免更调,尤为繁数。”中国任用普通行政官吏也是如此,“惟凭吾之所好。及其免也,亦不以处分律为根据,惟凭吾之所恶。好恶所在,荣辱在之”[18]27-276。此一现象在军队中的表现更为突出。有论者指斥部分高官践踏法律,选任低级军官纯为一己之私,不经议会推荐,大半出于军人之拥戴。如此模式法律,用人瞻徇的危害甚大,侥悻登进者势必日众。[19]134-801即使是正常的民主选举亦无不如是。对此,有论者剖析道:“盖选举之初,本非出于人民之公意,各以其金钱势力,为个人谋位置,并无代表人民之思想,遑问其能监督行政,以造福于国家于社会。”中国“虽已共和十稔,犹不知选举为何事。”“吾中国选政之所以不良,国家政治之所以日趋于混乱者,实系于此。”[20]51-201
4.选用人才标准不一
由于择人用人唯亲是尚,人才取舍一任私意,知法违法任免随意,选用人才标准不一甚为流行。这主要体现在简单以功勋、声望、经验、资格、金钱、善言等作为选用人才标准。所谓以功择人虽沿袭了传统用人习惯,但其弊端不可小视。对此,有论者批评道:官不能作为赏功之具。比较而言,以声望择人之举也甚多。本来,国家因事而设此专官,必其人之才足以了此事。而“众论孚矣,而或仅震于其平昔之声望,而漫使之莅官而莅事”,不论其是否有无经验,“其害立见”[21]22-187。还有的只凭资格而无视实绩用人。此辈又彼此互相援引,布满中外。至于以金钱为中心,以货取才者更多。所谓自号为政治家者“不知施政之难,但为倚势结党,争入内阁。甚至同一职位,不顾大局,固辞其利权轻者而赀就其重。至于若者则不明为官之道,徒知纳财辇贿以獵其营私目的之一官。”[22]34-549甚至选举国会议员也以财,有富豪巨贾买得议员之头衔。至于以作大言善言词为用人取舍标准也时有所闻。如“聚义则发言盈庭,无不具有条理。及授之以事,则或以阻害之者之多。然废然思返,或好为捣乱。比其卒也,则利未见而弊已形。或同流合污于庸俗吏之所为,竟不知整理为何事?”[23]23-979如此选用人才资格不一,显然无助于共和宪政的次第推进。
三、用人瞻徇的现实危害及其生态环境
1.用人瞻徇的现实危害
事实上,民初用人瞻徇并非空穴来风,实乃那些身居津要者肆意追逐私利所使然。在这些有识之士看来,“利之所在,弊即丛生。此为我国之通病。”其现实社会危害甚多。详言之,这突出体现在所选之人多非贤才、夤缘奔竞仕途拥挤、私欲膨胀肆无忌惮、党争政争日趋激烈与残害己身贻害国家等方面。
所选之人,多非贤才。民初共和政府用人瞻徇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凸显为所选之人多非贤才。对此,有论者指出:“今日居官者之未必贤,尽人知之。”具体地说,此辈“主义之内更有主义,于是往往有主义在此而力行在彼,主义在彼而力行在此”[24]121-296。他们借爱国之名行争权夺利之实。至于朝野新旧人物唯利是尚,“求其操行不苟,稍稍自爱者,亦几如凤毛麟角。”求一朴诚任事者亦不可得。那些声称公仆者的思想纯为昔日专制之思想,其所为亦为昔日官僚之所为。其时许多当政者日言等庸人才,培育英俊,注重人才之论虽响彻云霄,但夷考其实,人才遭摒弃者为数不少,以致人才弃业,污滥弹冠。有论者剖析道:我国今日非不搜罗人才,企图弼成上治,然实际所用不得其法,“似才非才乃满坑满谷,误于任使”。那些留学生卒多置诸学习闲散之地,未见重用[19]134-801足可略见一斑。
夤缘奔竞仕途拥挤。受此影响,社会上夤缘奔竞之象日多导致仕途拥挤不堪。由于用人瞻徇,民初仕途政象异常恶劣,事无所能者悉聚而趋之为官。对此,有论者指出:“无论大小官吏,一经任命发表,夤缘奔进者,日踵于门,不有广夏千万,断不能容。不得已,则巧立名目,以位置之。”[3]因此之故,那些为政者几至穷于应付。而如此求过于用导致仕途拥挤,游民日多,祸乱愈甚。有的当政者为“各植私人势力,摒弃现有者而不用”。那些闲居官僚则“奔竞钻营,或至贿赂公行,以妄希一当”。其最终结果是“职位而滥芋,则耗国家有用之金钱,养吾民痛心疾首之蟊贼”[25]134-721。
私欲膨胀肆无忌惮。如此夤缘奔进者一旦获任即崇尚官僚专制陋习而肆行己意,私欲恶性膨胀,所行肆无忌惮。有论者指出:今日民国大小官吏,不能脱老官僚之习气,亡清之遗风,平生朘削民脂,无恶不作,与民为仇,以保全其生命位置。此辈斤斤于目前之权利,而不复计为其他,肆行官僚专制,不顾众人祸福,肆意恣为,奉行过力。这些人视政权为私物,假公济私,为所欲为,竞谋位置,先私后公,虚縻款项,以自封殖。他们不但为禄蠹,而且设法以侵蚀国财,敲吸民脂,以餍其欲望。又或凭借权势,肆行其不正当之行为,谋国事则偷,而骫法营私,则驾轻就熟,不假思索。[26]28-81
党争政争日趋激烈。由于用人瞻徇,政争党争日趋激烈,党同伐异大行其道。有论者指出:“若用人而为饭碗问题,则人孰无喫饭之能,孰非有用之才?孰当用孰不当用,此际将从何分别?纷争乃由是而起矣。”[27]141-267具体地说,今国家不爱惜人才,而才者亦不自爱惜,社会多戕贼人才,而才者亦还日戕贼。以至今日当道诸公意见是争,私心是用,不能和衷共济以维持此危局。有论者指出:“民国成立,首放异彩者,为党争耳。”然而,“以有党争之故,反结不共和之恶果”[28]21-119。以私见托诸国民公意,少数人士假全体名义,徒以纷乱国是而已。
残害己身贻害国家。民初用人瞻徇势必残害己身贻害国家。有论者认为它直接导致“统系不明,择政权鹿杂。资格不定,则任用纷歧,人人存一梯荣之捷径,怀一非分之希望,始则意见之竞争,继而笔舌之战斗,终且干戈相寻,以害于尔身凶于尔国者有之”[29]116-135。如日常行政食禄者有人,乘机肆应者无人,以致国事愈益阽危。而选人用人不严,共和基础必为之动摇,势必导致鄙夫或且倖进,縻帑误国。那些歆于微利者竟举恶赖市侩以为人民代表,不恤造成莠民之专制,使日日望治之诉求反为异日政治播下酿乱种子。
2.用人瞻徇现象滋生的生态环境
民初用人瞻徇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在一定程度上实乃历史与现实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详言之,这主要与传统血缘宗法思想、崇尚为官陋习、消极选官思想和现实社会党见党争肆虐、道德沦丧人格堕落等方面密切相关。
传统血缘宗法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以宗法血缘为社会基础,君主施政用人带有较大主观性,任意封赏爵位,随意设立官衔,而世家子弟多能超越等级限制得到迅速擢升。在等级性政治结构中,许多官吏秉承家长制遗风,将选人用人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结合起来,导致阿上卑下、攀附从众、惟命是从等畸形人格的出现,使冗官冗员充斥各处。对此,有论者指出:“吾国用人行政,昔皆权操于政府,地方行政之人由中央政府委任,中央行政之人,则由专制君主特简,人民不得参与也。”[30]117-889民初新旧政治鼎革后用人行政仍难摆脱其消极影响。
崇尚为官陋习的日渐勃兴。与此相吻合,崇尚为官乃中国历史上的固有传统,为官被视为最光荣之事,良家子弟无不以做官来报达父母的养育之恩。此一习俗在民初社会依然具有较强影响力,追求为官者,可谓络绎不绝。有论者指出:“我人以民国号召社会于世界者五年于兹矣。然返观举国各级社会中所充塞而无一刻忘者,殆惟此作官之一观念。是故中央各省之政争,已作官者之争夺地位也,政客权斗之奔走运动。未作官者之营谋计画以求获得相适之位置也。”[31]142-219另一论者亦认为:“今中国人以官为最重”,“以大官为致谀之阶”,优秀国民几尽趋于作官之一途,尽趋于官。因为为官可以用力少而得利多,为官可以营私舞弊。如此分析颇具理论深度。
消极选官思想大行其道。事实上,在中国传统选官思想中任人唯亲颇为流行,此与固有世卿世禄思想不无一定关系。从理论上而言,世卿世禄取代原始民主选举虽具一定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世袭意识甚为浓厚。它虽随社会发展进步自战国之后呈衰落之势,但作为选官方式并未真正销声匿迹,在不同时代仍有所表现。如所谓“荫任”“九品官人”“恩荫”“荫典”等贵以袭贵的选人用人模式无不说明这一点。即使是荐举制也不乏类似思想的遗存。由于举荐者的特殊地位客观上决定其能凭借个人意志取人,故“故吏”、“门生”多被纳入受举之列。受此影响,民初的人们“争羡而群趋之。”[25]134-721
称取原料20 g,加入10倍水研磨,按3.1.1的最佳结果按2%投料量将重组胰蛋白酶投入,按2.3.2.4的方法酶解,恒温40,45,50,55 ℃,反应时间为30 min,将pH调节到8.0的条件下进行酶解,结果见表2。
现实社会中党见党争肆虐。而在现实社会中,党见党争肆虐,道德沦丧人格堕落。对此,有论者批判道:“我国比年以来醉心欧化,国粹荡然,社会道德既已一落千丈,而政治道德之堕落又倍于明清末造之时。”清之亡既亡于专制更亡于腐败官僚。事实上,民国新造,创痍未苏。而私心滔滔,怪相满目,漠视民国真精神者甚多,“标既不正,影自不端,行见举国上下,凌轹叫嚣,争权夺利,暴乱相循,靡所底止。论者反谓政改共和,大局日危,党争实阶之厉。”那些“掌民政者,大都行不顾言,惟利是视,所谓交际无非花天酒地,虽一举而废中人之产,亦所不惜”[3]42-93。可见,民国现实的共和政治危机实坏于官僚之隳堕。
政府官员道德沦丧人格堕落。受此影响,所谓公举也严重扭曲变形。如谷钟秀批评北方各省“公举都督一层,政府若罔闻知。不但不照案施行,各省有援据该案进行者,政府亦峻拒之。”在他看来,政府“既失大信于天下,又蹂躏参议院议决之议案,民国前途,危险孰甚!”至于那些当事者挟众以自重,如改革政体“苟利于国而未必利于己,则且断断然争焉”,甚至以蹂躏一切为其天职。喜则通电各处,说都督既严且明,威望素孚。稍不惬意,便又数其罪恶,另举一人取而代之。“各省之民畏若辈如虎,又谁议其后者。此今日各省公举都督之现状也。”[32]22-209
可以说,这些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近代民主共和精神背道而驰。这说明在君主专制被推翻后,如何在共和政制下实现其内在用人行政的革故鼎新,以提高行政效率,尚存诸多有待跟进之处,客观上需要进一步深化。
四、祛除共和政府用人瞻徇弊害之要途
针对前述现存用人瞻徇的现实危害及其社会生态,这些有识之士围绕如何祛除共和政府用人瞻徇弊害的基本途径作了一定尝试性探索,努力构建合乎民主共和精神的择人用人学说,以利于民国政府选拔真正有用之才。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数端:
1.在思想上认清合理选用人才的重要价值
针对传统“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训示,有论者积极加以引申并赋以新义,指出:“人才者,国家之桢干,况在今日。乘机肆应,尤非有各种专门人才不可”[33]28-505。由于政府行政的良性运作与用人之道关系甚大,以清覆亡教训为民国之殷鉴成为共识。一位论者剖析道:满清之亡实亡于官。此辈不顾大局,不问国权,不恤民生疾苦,蝇营狗苟,竞争运动,攘夺权利,博取富贵。今者民国肇兴,荡涤睱秽,“而官治一途尤为群流所瞻仰,其关系民国之前途者实匪浅鲜。”事实上,“任官为行政上之要典。任官得其人,则百事具举,而庶绩咸熙。”“况新邦缔造之始,官治尤为扼要之点”[30]。在他们看来,由于今日中国已由帝制而改共和,牺牲至钜之价值,国人希望建设真正共和国,故“立国之道,用人与行政并重”,因为用人得失关乎一国之治乱兴亡,“以今日之官场,惟真心救国者,始可做之”[34]141-573。
在中国传统用人思想中,任人唯贤、举用贤才的思想颇为丰富。如重乡议、清议之法,实行荐举、考试、任官回避等法无不蕴涵诸多积极价值。前述时人肯定“选才任能,贤者当国”实乃对传统合理选人用人思想的继承与弘扬。对西方近代积极人事思想,他们也力图吸纳借鉴。如有的力主学习英德两国所注重的“适量教育”以避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至于党争之事,宜援世界先进诸国之法以无碍于国家进步而有助于国家发展,“凡为长官者皆能牺牲个人权利,以巩固国家之公安”[3]42-93。在选举方面,中国人尤需知晓西式选举实为法治之要义,不以握有政治实权为荣幸,应抛弃选举弊病,杜绝任情伪造民意无所顾忌之恶习。如美国求统领不问其贫富,不问其职业,但以贤不贤为断,适不适为归,与中国人之昏天黑地,置国政于不顾的情形迥然不同。鉴于中国实际,民初政治“宜尚选举,不宜尚委任。”唯有如此才能尽伸民权“以救吾病耳”。
3.在原则上严格遵循为事用人各取所长之道
这些有识之士认为“为人择事,不宜于专制时代,而尤不宜于共和时代也”[21]22-187。此言主要针对的是选人用人中的弊端而言,同那种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迥然有别。此与蔡元培所秉持的“为事择人,绝不为人择事”用人原则,徐世昌通令各省行政长官整饬官方注重“为地择人,勿为人择地”,财政部强调:“只能为事择人,不得为人择事”的表述颇为一致。具体选用人才应努力做到权限分而职任专。详言之,所谓“为事而用人者,则长于军事者,用之于军,长于政治者,用之于政,长于法律长于外交者,用之于法律外交。人有专长,世所共见。用人之标准既立,自无所用其纷争也。”[27]141-267如此一来权限分,职任专,斯民政亦得逐渐展布,而为国家立定长治久安之规模。
4.在标准上明确贤、才与适等具体尺度
民国初期,这些有识之士认为“新政府之组织,以用人为先决问题,而用人则以方针为先决问题”[35]140-700。在他们看来,共和为道德问题,而国民一人之精神关系全国政治之良恶。为此,广大国民尤其是志于从政者尤应具有完全国民之人格,自觉为主义而“做官”。做到信仰坚定真心爱国,守道义行忠信,讲信用乐守法,明公私惜名节,力行其言,勇于牺牲。政府用人当以尽心民事与否为标准,一以能否诚心为民为断,“择真爱国者用之。”当然,择人用人应贤与才并举,力求做到才、贤与适的统一。具体地说,“慎择需用之人,不偏新旧而惟才是取,不论亲疏而惟贤是用。”[22]34-549认真矫正袁世凯用人中“别党派,分新旧”的错误,既要“重经验”更要重学识。政府宜“专门行政须专门之人任之,并提倡尊重技能之士以为社会先。”当然,人地相宜,奉行适才适所原则亦不可忽视。此外,用人当尊重舆论,所选任官员应合乎民意,是“代表民意之人才”。
5.在操作上首推考试与选举,慎用荐举
从形式上而言,考试选人,人尽其才,可谓民初用人的主要模式,但实际推行却并非尽如人意。这些有识之士认为,鉴于政治衰颓,人才湮没,无术疏通,唯有“援民五旧例,举行文官考试。”同时,提倡选举择人,因为只有人民对国家用人有进贤退不肖之权,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才能日形密切,国有患难人民才能共同应对。在他们心目中,立宪之国重在选人,一国用人之权,除司法官外,皆应操诸国民。故慎选人才莫如选举。有论者指出:自民国成立,主张民权,一切用人之法皆以伸民权为主,“于中央行政员,则由参议院推举而总统特任之,于地方行政员,则由民选而都督委任之,是于选举之中,寓防弊之意,法至善也。”按之权利义务之说,“吾国任用行政者之法,亦宜尚选举也。”当然,委任也有其一定价值,但要慎用。那些主张委任者多以国民程度太低,选举势必导致流弊为辞。其实,由于现实社会中道德严重失范,委任多为官吏任情赠予之阶,甚至使贪使诈,因此,具体采用不可不慎。比较而言,选举胜于委任,虽然二者皆有弊,但应“取弊之易防者”[19]134-801。
6.在管理上应制度、舆论与剔汰三位一体
这些有识之士认为按照用人标准用人甄别宜严,在具体管理上应推行监察之法以强化监督。如长官考核属吏宜广采舆论,不能仅凭一己之好恶为取舍。要“揆诸共和国之好恶,一以舆论为从违”。简言之,用人“当视五族舆情之向背以为从违,不宜沾沾一二人之私而起用。同时,欲正本清源,及时淘汰剔除贪官污吏尤为当务之急。而裁汰那种以政治为生活却不负责任的政客则应首当其冲,因为国家将亡必有无数小人把持朝政,狼狈为奸。苟便私图,罔顾公益。为正本清源计,须以极严手段淘汰贪腐官吏,整饬官场风纪。[36]61-135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民国初期,面对共和政治理论与现实社会实践严重脱节之状,针对传统和现实中择人用人的弊害,这些有识之士努力批判继承传统用人文化的合理思想因子,积极借鉴西方近代用人行政有益经验。强调秉持近代法治精神,以平等公允形式广罗人才,努力建构合乎时代需要的近代用人之道以促进共和政治有序运作。这些思想虽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他们一定的“民主精神的自觉”。囿于具体时代,这些思想多停留于舆论层面,难为民初北京政府所采纳,遑论取得实质性成效。尽管如此,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民初孙中山等人的积极用人思想形成互动,也与南方护法军政府、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的相关价值诉求相吻合。这表明民初专制独裁思想与民主共和理念的较量甚为激烈,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中国化尚需时日。欲根除中国传统人治思想,摒弃任人唯亲用人陋习,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人事管理制度,自觉秉持民主法治精神推行共和政治的良性运作颇难一蹴而就,客观上需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和人们长期坚持不懈的积极努力!
[1]刘桒.旧唐书·窦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文官考试[N].盛京时报(影印本),1927.
[3]为持减政主义者进一解[N].盛京时报(影印本),1919.
[4]孙中山全集[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
[5]澄清吏治策[N].盛京时报(影印本),1914.
[6]论新民国之政弊[N].申报(影印本),1912.
[7]论道德救国[N].盛京时报(影印本),1922.
[8]用人赘议[N].盛京时报(影印本),1914.
[9]郑观应集[M].夏东元,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0]光绪朝东华录[M].朱寿明,编 .北京:中华书局,1958.
[11]宋教仁集[M].郭汉民,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2]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M]. 龚育之,等,主编.北京:线装书局,2002.
[13]周学熙集[M].虞和平,夏良才,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4]邵力子文集[M].傅学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庞守信,林浣芬.河南地方志资料丛编之三:五四运动在河南[MZ].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16]说私[N].盛京时报(影印本),1913.
[17]澄清吏治[N].盛京时报(影印本),1927.
[18]普通行政官吏任免问题[N].盛京时报(影印本),1914.
[19]生计与人才[N].申报(影印本),1915.
[20]说选举[N].盛京时报(影印本),1922.
[21]任官议[N].盛京时报(影印本),1912.
[22]救亡断在培植道德(二)[N].盛京时报(影印本),1916.
[23]时事泛论[N].盛京时报(影印本),1912.
[24]不可思议之人心[N].申报(影印本),1913.
[25]吾之所谓中国隐忧者[N].申报(影印本),1915.
[26]论裁减官吏[N].盛京时报(影印本),1914.
[27]用人问题[N].申报(影印本),1916.
[28]辟党迷[N].申报(影印本),1912.
[29]对于新政府之希望[N].申报(影印本),1911.
[30]中国用人制度宜从选举不宜从委任(续)[N].申报(影印本),1912.
[31]嗜官特性[N].申报(影印本),1916.
[32]推论今日公举都督及委任之弊害[N].盛京时报(影印本),1912.
[33]论今日保荐之滥[N].盛京时报(影印本),1914.
[34]议员与官[N].申报(影印本),1916.
[35]经验[N].申报(影印本),1916.
[36]俸禄[N].申报(影印本),1915.
责任编辑 何志玉
On the liquidation of the Practice Favoritism for Selecting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ShanghaiPostandShengjingTimes
ZHAO Yan-cai, CAI Wei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Hubei, China; 2. Wuhan Jianghan District Bureau of Letters and Visits, Wuhan 430000, Hubei, China)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some insights made fierce criticism upon the practice favoritism in the press in the light of the tradition and reality of officialdom evils. They thought that it would bring about some grave consequences, such as the most selected persons would not be the elites; some of them would be selfish in serving for their expansion and act recklessly and care for nobody; they would harm themselves and endanger the nation, etc. In view of such present situation, they had made a certain exploration around ideas, principles, principles, standards, operations, management so as to get rid of evils of practice favoritism during selecting talents and construct a new theory of selecting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modern democratic republic.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public opinion; select talents; the practice favoritism; liquidate
2016-05-20
赵炎才(1963-),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蔡 伟(1985-),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市江汉区信访局。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D693
A
1673-6133(2016)04-009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