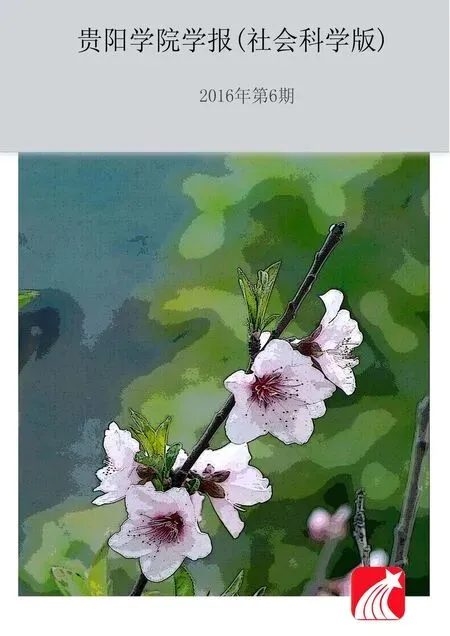小说《铁器时代》的创伤书写
2016-03-18吴晓群金怀梅
吴晓群, 金怀梅
(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小说《铁器时代》的创伤书写
吴晓群, 金怀梅
(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库切创作的小说《铁器时代》作为二十世纪创伤小说的代表之一,正面反映了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社会的内部矛盾与冲突。小说以卡伦太太的个体创伤贯穿始终,她经历和见证了家庭创伤、社会创伤和种族创伤,这三种创伤加剧了她个人的创伤之痛,导致她最终选择自杀来解脱创伤之痛。从创伤理论的视角解读小说的创伤书写,有助于揭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非暴力社会戕害不辜的事实,更好地理解库切对南非暴力社会的反感和无奈。
《铁器时代》;个体创伤;家庭创伤;社会创伤;种族创伤
创伤,原属于医学用语,随着弗洛伊德对心理创伤研究的逐渐深入,创伤研究从身体转向心理,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小说《铁器时代》从白人卡伦太太的视角描述了白人的殖民统治以及种族隔离制度给南非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与痛苦,创伤气息弥漫着整部小说。库切本人独特的成长经历及其作品关注的主题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对于库切的研究广泛,学者大多从后殖民角度进行研究,包括种族隔离、殖民话语、政治书写等方面,也有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该部小说的研究仅有几篇论文,视角多以后殖民角度为主。笔者认为,小说《铁器时代》整合了个人创伤、家庭创伤、社会创伤和种族创伤,从创伤理论视角阐释小说中的创伤书写,呈现了南非暴力社会的现状以及库切对现实社会的反感,为库切小说研究注入了新视角和新活力。
一、创伤理论
“创伤(Trauma)”一词来源于希腊语“traumatizo”,原始的意思为“伤”,是由某种外部力量造成的身体损伤,或是由某种强烈的情绪伤害造成的心理损伤。造成创伤的这种外部力量常被人们称之为生活事件,当然“生活事件并非都可以成为创伤性事件”[1]。凯西·卡鲁斯将创伤定义为“对某一突发事件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2]林庆新认为创伤是“由灾难性事件导致的、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造成持续和深远影响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失常的心理伤害[3]。”陶家俊则认为创伤来源于现代性暴力,指出:“人对自然灾难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4]显然,个体的心理创伤是由创伤性事件所引发的某种强烈的情感反应,对于个体的身体、智力、情绪及行为造成障碍性的影响和难以愈合的伤害。
二、《铁器时代》的创伤书写
“弗洛伊德对创伤的理解包含:童年早期经历的事件的记忆,青春期后经历的事件的记忆和后期经历事件触发的对早年事件的记忆。”[5]主人公卡伦太太的童年受母亲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后来关于死亡的梦魇与依恋母亲的记忆有关。她这一生也历经坎坷,与丈夫离异,女儿不堪忍受社会之伤而远走美国,到八十年代南非的种族矛盾空前激化,她所经历的家庭、社会以及种族等创伤性的事件给她的心理留下无法愈合的伤害。
1. 个体创伤
小说以卡伦太太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消息开篇,了解自己时日不多了,卡伦太太决定给女儿写封家书,这可能是她最后的机会,和女儿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想法。作为母亲,她的叙述流露出对女儿的思念,也映射了女儿的离开对她心理上造成的焦灼。作为南非社会种族矛盾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她表达了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控诉,对白人殖民统治的不满以及对黑人遭遇的同情。“当个体面临着某种威胁,威胁到身体或心理的完整性时,这种威胁就构成了创伤性的事件”[6]。目睹这些创伤性事件发生在他人身上也会产生创伤反应。
卡伦太太一开始对于黑人种族的非人遭遇并不知晓,当权白人殖民政府自然不会将自己的暴力公布于天下。随着女仆的儿子贝奇和他朋友的到来,残酷的社会现实才被一点点地揭示出来。她本来对贝奇等人抵制学校的行为感到不妥,认为他们不能因为种族隔离制度而不去上学。后来她亲眼目睹警察跟踪贝奇和他的朋友,并故意制造车祸导致他们意外受伤,卡伦太太既感到恐惧又震惊,她决定去指控那两名警察,结果被告知,“只接受‘直接受到侵害的当事人’的投诉”[7]87。为此,卡伦太太十分气愤,觉得警察的故意行为让人蒙羞,作为殖民统治者的同胞,她感到羞愧。“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我自己。你不受理我对此案的指控,就因为你说我不是直接受害者。可我是受害者,非常直接的受害者”[7]88。这股耻辱感深深影响到卡伦太太的身心,她认为从今往后只能生活在这种羞辱的状态中,这便是生命中的死亡。创伤性事件发生之后,受害者不能继续他们的正常生活,因为创伤的反复妨碍。[8]车祸之后不久,贝奇返回古古莱图,卡伦太太自愿驾车带着弗洛伦斯前往寻找,这一次她不仅看到了黑人的生活现状,还见证了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以及它对生命的严重威胁。卡伦太太内心的耻辱感随着她对黑人种族在南非社会受迫害现状的深入了解而与日俱增;空气中的硝烟,雨中的战栗,贝奇和其他四人的尸体、被焚毁的大厅,古古莱图的暴力与死亡场景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威胁着她的正常生活,这种创伤性的记忆不断出现在她的噩梦之中,可怕而又挥之不去,让她饱受煎熬。
创伤性事件之所以具有创伤性,是因为它“扰乱了时间的河流(the flow of time),打断前后的顺序,继而让受创主体难以按照逻辑或时间的序列来重组事实”[9]。古古莱图的经历让卡伦太太的心理濒临崩溃,感到绝望,她已不在乎自己是否可以活命,因为这些劣行让她觉得自己不配活着;她的身体、她的精神已经千疮百孔,痛苦不堪。弗洛伦斯的姐姐来替她收拾东西,卡伦太太签了一张支票给她转交给弗洛伦斯并代为转达她的抱歉,她的抱歉“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达”[7]119。“语言是治疗精神创伤的主要手段,无论口头或书写两种方式都有明显效果,而把创伤经历压抑在心底对健康有害无益。”[10]卡伦太太向范库尔先生倾诉自己内心的创伤、耻辱的深渊和无助,她渴望救赎,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她打算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范库尔先生,想通过牺牲自己来解救自己,她的心里无比纠结。周边的毁灭与堕落使她坠入噩梦深渊,苟延残喘,耻辱意识已经深深扎根。糟糕的事又发生了,贝奇的朋友约翰半夜来到卡伦太太的住处避难。他的到来再次唤起卡伦太太前期的记忆——自行车、车祸、流血;她渴望有人拯救自己,带着这种焦灼与痛苦开始做梦,关于死亡的梦境,出现幻象,“像是地狱的幽火”[7]144。贝奇的朋友最终死在身穿制服的白人警察手中,无论卡伦太太是多么地想保护他。事后,警察又来到她的住处盘问她。夜幕降临,她想象着约翰死前的抵抗,时间在那一刻盘旋着,没有回到时间的长河中。接着,卡伦太太陷入梦境之中,梦见弗洛伦斯化身为女神,带着面具,裸露右乳,疾步而去。“一个充满紧迫感的形象,她暗自饮泣,带着短促而尖厉的哭腔,身上沾着血和泥土”[7]187。白人的暴力统治早已碾压了她的价值观,创伤性事件的接连发生让卡伦太太身心疲惫,她对这个没有真理、没有真相的世界痛心疾首,她渴望被拯救却得不到救赎,她的创伤经历让她内心崩溃,无法承受,最终选择自杀来解脱自己。
2. 家庭创伤
卡伦太太是一个离异独居、罹患癌症的老太太。对于丈夫的描述很少,只提到她早年与丈夫离婚,后来丈夫去世。她内心孤独,身边没有能说话的人,女仆弗洛伦斯是一名黑人母亲,由于种族的关系,两人之间存有隔阂。在她得知身患癌症消息的那天,她注意到了家门口的流浪汉范库尔,或许是因为她不想被打扰,抑或是因为她渴望有人陪伴,她收留了他。正如她自己写道:“当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来敲你的家门时,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社会弃儿,一个酗酒者,一个失落的灵魂。可是现在,在我心里,我们渴望着我们这些平静的家庭,就像在那个故事里一样,在天使的圣歌中战栗。”[7]13范库尔手有残疾,冷漠、寡言,被动地接受卡伦太太的指示、倾听她的故事。卡伦太太时而叫上范库尔一同开车出去,她需要他的帮助,同时也需要他的倾听。她和他分享了她母亲、女儿、女仆和女仆的儿子等人的故事。卡伦太太唯一的女儿一九七六年去了美国,在美国结婚生子,永远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深处水深火热的国度,卡伦太太对女儿的离开颇感庆幸。她愿“独自拥抱死亡,自己来承担一切”[7]4。女儿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精神寄托,她对女儿的思念,时常会让她想象女儿的陪伴,像小时候一样,为她准备糖果,拥抱她,喊她起床。然后女儿离开之后她们的联系很少,十年都未曾见上一面,不完整的家庭给她带来的创伤使得她内心的孤独感与日俱增。作为这场战争中无法定义的他者,流浪汉范库尔先生是卡伦太太“表达忏悔的理想听众”[11]。
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的黑人母亲弗洛伦斯在卡伦太太家帮佣多年,尽管如此,她们两人之间因为种族不同而无法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在弗洛伦斯看来,卡伦太太是白人,种族隔离制度不断激化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自己女仆的身份并没有让弗洛伦斯完全听从于卡伦太太的指示,她内心深处对于白人的憎恨有时会溢于言表,无视卡伦太太的要求,任由自己的儿子带着他的朋友把卡伦太太的大宅子当成避难所、中转站。当卡伦太太指责弗洛伦斯不该让儿子贝奇带着陌生人回家时,弗洛伦斯回应,“他不是什么陌生人,他是客人”[7]46。同时她的儿子也向卡伦太太发起挑衅:“难道我们进来还要通行证?”[7]46当卡伦太太建议弗洛伦斯不该让孩子卷进这场纷争,否则会变成暴戾的孩子时,弗洛伦斯却瞪着她,厉声说道:“可究竟是谁让他们变得这么残暴?正是那些白人,是白人让他们变得这么残暴!没错!”[7]49可见,弗洛伦斯眼中的卡伦太太不是孱弱的老人,不是长辈或主人,而是一个白人。主仆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终究搭建不了信任的桥梁,这种紧张而不和谐的氛围让卡伦太太丝毫体会不到家的温暖。女儿的杳无音信、身边人的漠然使卡伦太太失去被爱感,这种家庭创伤让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卑微、渺小和不被需要,时常会出现幻觉和梦境。比如她在盥洗室里出现幻觉,看见已故母亲向自己走来,“笑靥如花,令人销魂,令人忘却一切,直抵天庭之阶”[7]55。显然,对卡伦太太来说,家早已不复存在,家庭创伤给她带来的伤害不只是身体疼痛的加剧,而且影响到她的幻觉、梦境和思想等,使她产生失望、抑郁等非常态情感。
3. 社会创伤
小说以八十年代的南非社会为载体,再现了当时种族隔离制度下的恐怖生活和暴力场景。从卡伦太太的视角观察社会的暴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伤性的体验,萦绕心头、难以抚平。卡伦太太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女性,她不满白人同胞对黑人的暴力统治,在古古莱图目睹的残暴场景让她感到震惊。凌晨时分,卡伦太太驾车带弗洛伦斯去寻找儿子贝奇,来到黑人的居住区(township),零距离地体验到恐怖、混乱和死亡。卡伦太太被塔巴拿先生从古古莱图带到棚屋区,看到“被蹂躏的景象:焚毁的棚屋还在冒着闷烧的烟雾,有些棚屋还在燃烧,冒出熊熊黑烟”[7]97。眼前的焚烧、抢劫、骚乱是她始料未及的,她心中的恐慌与不安让她不知所措,耳边响起的枪声拉近了她与死亡的距离。贝奇死了,连同其他四个同伴。暴力社会给人们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对卡伦太太的精神更是沉重一击,让她感到绝望;她眼前的一幕让她失语,让她精神上出现失常和幻想,“我的生命也是一种浪费。我们射杀那些人,好像他们都是垃圾,可是归根结底,是我们这些活人不配活着”[7]107。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7]108。
社会创伤使人们产生麻木不仁、歇斯底里甚至精神失常等非常态的情绪,贝奇的死让卡伦太太情绪失控,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在摇篮里就被掠走了,自己被布娃娃所取代,过着布娃娃的人生,“具有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概念”[7]113。她回忆起自己两岁时被妈妈压着肩膀和兄弟保罗拍照时的模样,照相机似乎夺走了她的灵魂,仿佛一直以来,自己徒有空壳,内里空空。这是一个疯狂的社会,人们过着不正常的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社会中,卡伦太太正一点一点地让自己溺毙。她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女仆弗洛伦斯心灵上的痛苦无人可以救济,她收留流浪汉范库尔,给予他很多却得不到他的仁爱,社会创伤留下的后遗症是持续性的。身处荒漠之中,卡伦太太将赌注压在范库尔身上,希望这个她不得不信任的人能在她死后将这封长信寄给美国的女儿。社会的冰冷漠然让范库尔先生变得麻木,他看透周遭,对卡伦太太的帮助来者不拒,生活随心所欲,他努力将自己置身于暴力社会之外,减少或无视社会创伤带来的影响。
社会创伤另一表现形式在于孩子童真的丧失。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孩子了,贝奇是这样的,他的朋友约翰也是,十几岁的孩子身上没有一点孩子气,却带有“某种麻木不仁的秉性,故意装傻充愣的麻木,拒人千里之外……没有幽默也没有仁慈和纯真”[7]80。孩子们成为了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卡伦太太看到并感受到他们对像她这样的普通白人的抵触。他们毫不避讳地加入这场战争,为反对白人的统治而抗争,最终没能逃脱死亡的魔爪。社会对孩子的戕害让卡伦太太感到痛心疾首,她渴望和平、渴望公正,她的诉求得不到任何回应,她想逃离这一切,裹着被子躺在通往比坦肯街的人行天桥下感受着大限已至的淡然。迷迷糊糊中看见三个小孩在她身边,最大的那个孩子顶多十岁、神色凶狠,伸手在她身上乱摸,企图能找到点值钱的东西,一无所获之后,竟然拿着棍子撬开她的嘴以便看看她是否戴着金牙,被卡伦太太推开之后,竟用光着的脚踢她。创伤的气息持续弥漫在身边,让卡伦太太感到窒息,感到在这片土地上的不自由,死亡不过是为了寻找自由而付出的代价。
4. 种族创伤
南非是库切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是非洲殖民主义权力机构持续时间最久、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漫长的种族隔离制度给黑人种族带来不堪回首的压迫和痛苦。白人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而黑人却只能生活在黑暗之中,种族隔离制度下矛盾和冲突不断。作为白人,卡伦太太试图和黑人构建和平共处的关系,但得到的却是黑人的无视和冷漠。
种族隔离让黑人的生活民不聊生,呈现在白人眼前却是另一番模样。卡伦太太在亲眼目睹种族冲突之前,对于黑人生活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政府的信息。古古莱图发生枪杀之后,弗洛伦斯把贝奇及他的朋友带回卡伦太太的住处,因此而被警察跟踪监视,老太太感到不满,要求弗洛伦斯让儿子的朋友回他自己家,弗洛伦斯拒绝了她并告知古古莱图发生的麻烦事,对于这一切,卡伦太太毫不知情,呈现在她面前的那片土地“是洋溢着邻里欢笑的和谐家园”[7]54。而这种和谐却被贝奇和他朋友的到来打破了,两人因为抵制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学校而被警察跟踪,他们骑着自行车越过斯昆德大街时,后面紧跟着先前在附近跟踪他们的警车。接着让卡伦太太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警车故意追到与男孩自行车并排的位置,开车门撞倒他们,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卡伦太太看到这一幕颇感震惊,尖叫起来。两个孩子受伤了,尤其是贝奇的朋友,前额的伤口不断涌出鲜血,卡伦太太急忙为他止血,凝视着这血,惊慑恐惧之情涌上心头,“难道这就是世界末日来临的情景?”[7]64她难以置信,内心深处恍惚无措,种族隔离让这个国家变得畸形扭曲,对于孩子们抵制学校的行为也是试图采取极端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贝奇的朋友被送进医院,卡伦太太费尽周折在医院找到他安慰他时,换来的是那孩子的面无表情和内心抵触。种族的矛盾与冲突让黑人甚至是孩子都变得麻木、冷酷,视一切白人为敌人。卡伦太太摸了一下那男孩没受伤的手,感觉到男孩的僵硬和“电流般的愤怒的反弹”[7]81。种族的创伤给男孩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随时会落地生根。
贝奇出事了,卡伦太太带着弗洛伦斯驾车来到古古莱图和C区,这次卡伦太太近距离地见证了黑人恶劣的居住环境和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棚屋区的房子“就像是胡乱长在沙丘北坡上的野草”[7]97,到处是被蹂躏的景象。种族暴力让人们失去理性,焚烧、抢劫,这个世界的喧嚣狂暴让卡伦太太感到恐惧害怕。贝奇在这场暴力中牺牲了,献身于塔巴拿先生口中所谓的“同志情谊”。身处聚集的黑人族群中,卡伦太太感到怨恨、憎厌和仇恨的情绪都冲她而来。种族创伤给黑人带来的伤痛已无法修复,同样给卡伦太太带来难以摆脱的创伤,她开始怀疑自己的生命,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活过。种族的战争并没有因为几条生命的离去而停止,死亡依旧在上演。贝奇的朋友约翰额头流血的记忆还在卡伦太太心头萦绕,尚未散去之时,卡伦太太又被迫体验约翰的死亡过程,这一切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她的住处。种族创伤给她的心理和精神都造成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创伤性的记忆时刻提醒着她的族群对黑人的迫害,而她作为普通白人群体中的一员却没有任何话语权,这种无能为力与边缘化让她内心倍感煎熬,难以解脱。“我们的时代是见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见证本身就是巨大的创伤”[12]。卡伦太太见证太多的创伤:家庭创伤、社会创伤、种族创伤等,而这些创伤给她的精神造成沉重的打击,犹如身上的癌细胞,侵入骨髓,慢慢地吞噬她的生命。
三、结语
二十世纪是一个创伤的世纪,一方面见证了太多的人类创伤事件,另一方面随着创伤研究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更深,揭示得也更多。小说《铁器时代》是一个力证,它整合了个体创伤、家庭创伤、社会创伤和种族创伤。小说以卡伦太太个人遭受的心理创伤贯穿始终,读者在她的自述中能充分体会到家庭创伤、社会创伤和种族创伤以及这三种创伤对她精神和心理上的打击,加剧了她个人的创伤之痛。卡伦太太不仅要独自承受心理创伤,而且还饱受家庭、社会和种族纷争之痛。她试图走出这些伤痛,用文字向女儿诉说,用语言向范库尔先生诉说,卡伦太太与他的对话让读者感受到她在家庭、社会及种族之伤中的蜕变。然而这些看不到尽头的创伤无法愈合,犹如百毒攻心,终究成为她无法承受之痛,唯有死亡才能解脱。卡伦太太的表述虽不能完全代言库切本人,却足以给读者一种难以名状的刺痛感。笔者从创伤理论的视角解读小说中的创伤书写,不仅呈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南非暴力社会戕害不辜,也反映了库切对南非暴力社会的反感和无奈。
[1]Herman J L , Schatzow E. Recovery and verification of memories of childhood sexual trauma[J].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1987(4):1-14.
[2]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P. 1996:11.
[3]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J]. 国外文学, 2008(4):23-31.
[4]陶家俊.创伤[J]. 外国文学, 2011(4):117-125.
[5]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6):93-97.
[6]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M].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18.
[7]J.M.库切.铁器时代[M].文敏,译.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
[8]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26.
[9]Anne-Laura Fortin-Tournes. From Traumatic Iteration to Healing Narrativisation in Shalimar the Clown by Salman Rushdie: The Therapeutic Role of Romance[A].Trauma and Romanc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C]. Ed. Jean-Michel Ganteau and Susana Onega 211-212.
[10]Pennebaker, J.W.Opening Up: The Healing Power of Expressing Emotion[M].New York: Guiford Press, 1997:2.
[11]Dominic Head. J.M.Coetze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30.
[12]Luckhusrt, Roger. The Trauma Question[M]. London: Routledge,2008:7.
[责任编辑 刘晓华]
Trauma Writing in the Novel Age of Iron
WU Xiao-qun,JIN Huai-m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230088, Anhui, China)
As one of the trauma literature masterpie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novelAgeofIronpositively reflects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under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Mrs.Curren's own trauma is a leading clue throughout the novel; she experiences and witnesses the family trauma, social and racial trauma, which co-accelerates her individual traumatic agony, leading eventually to her choice of committing suicide to get rid of traumatic suffering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uma writing in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uma theory contributes to disclosure of the slaughter of the innocent by the violent South Africa in the 1980s, and facilitat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etzee's sense of antipathy and helplessness to such a society.
AgeofIron; individual trauma; family trauma; social trauma; racial trauma
2016-09-19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创伤理论视域下的库切小说研究”(项目编号:SK2016A0447)阶段性成果。
吴晓群(1982-),女,安徽肥东人,安徽新华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教学法。 金怀梅(1981-),女,安徽六安人,安徽新华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教学法。
I106.4
A
1673-6133(2016)06-009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