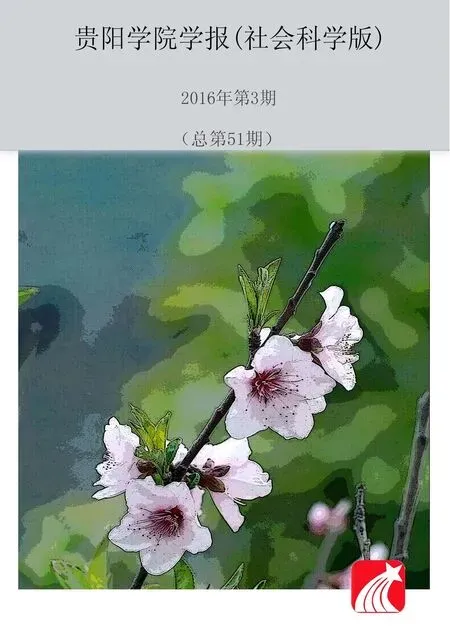罗近溪《大学》诠释之研究——从“三纲领”到“诚意”*
2016-03-18蔡家和
蔡家和
(东海大学 哲学系,台湾 台中 40704)
罗近溪《大学》诠释之研究
——从“三纲领”到“诚意”*
蔡家和
(东海大学 哲学系,台湾 台中 40704)
通过对罗近溪的《大学》诠释做一解说。其顺从阳明思维,宗主《大学》古本,不从朱子新本;定义《大学》为“大人之学”,系阳明“一体之仁”的引申发挥;又其近于泰州王艮“淮南格物”之说,而有自己的一套新义。关于《四书》之诠解,不取朱子之体系,而是遵于郑玄古义,以《中庸》在《大学》之前;并将“格物”的“格”解为“式”,取合格、格子、合于规范之义;亦强调“知”的重要性,认为《大学》的重点即在“知”字,顺此立论,从而自成一套思想体系。
合格;《中庸》;知本;大人;规矩
一、 前言
程、朱表彰《四书》,特别是朱子的《四书集注》,系以《大学》为首,用以诠释其他三书;《大学》
本是《礼记》的一篇,朱子却是重新诠释之以建构其理学体系①*①“朱子将其抽离礼的范畴,与《论语》,《孟子》,《中庸》结合后,重新赋予它理的内涵,作为进德修学的基础,从中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并且重新标彰《大学》目的,于是《大学》不再是《礼记》脉络里的《大学》,而变成心性理学诠释系统下的一部分。”高荻华:《从郑玄到朱熹:朱子〈四书〉诠释的转向》(台北:大安出版社,2015年,第23页)。。朱子诠释《大学》可谓用心良苦,甚至删动文字而为新本,与郑玄古本已是不同,更与原意大相径庭②*②朱子:“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闲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第2页)。朱子于《大学章句》序中谈到自己以己意补阙略,如《格致补传》。,以至影响后来的宋明理学,纷纷对
《大学》做出诠释。有人视为伪书,如杨慈湖①*①“慈湖不明反因正因之大因,故谓《大学》正心诚意、《孟子》存心养性、《易.翼》穷理尽性,皆非圣人之言,岂故矫言耶?实于事理硗甚。”明.方以智著,庞朴注:《东西均》(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2页)。、陈确、伊藤仁斋②*②徐复观:“其次为伊藤仁斋(1627-1705)。他开始是服膺宋学;后以宋儒体用理气之说,皆系佛、老之绪余,又以《大学》非圣人之遗着,遂走入古学一派。”徐复观:《日本德川时代之儒学与明治维新》,收黎汉基、李明辉编:《徐复观杂文补编》第1册(台北:中研究文哲所,2001年,第84页。等;有人重新评论、诠解,如阳明主张恢复古本③*③“《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止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轻叛孔已乎?”陈荣捷编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98年,第248-249页)。,然阳明所谓的回返,却还是套在其良知学体系中,非是真的回到古本④*④如阳明诠释格物:“格者正也,物者事也”,面对事以正吾人之心,即复其良知。这与朱子“格物”为“穷理”不同,但也不免于自家体系之说,亦与古本不合。。蕺山即曾说过,“格物”之解有七十二派之多⑤*⑤蕺山宗于淮南格物之说,其言:“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明儒学案.蕺山学案》选自明.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8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由此看出,《大学》相关诠解之繁复与重要性。
笔者讨论泰州学派罗近溪对《大学》的诠释,简言之,近溪一方面依于阳明以恢复古本,另一方面则近于王艮“淮南格物”之说⑥*⑥淮南格物者,乃王艮之说,此开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与近溪同属泰州学派,王艮传王东涯,传徐波石,传颜山农,传近溪。,而自成一套。此下文详述。在此,先对比心学与理学对《大学》的不同诠释,亦显出新本⑦*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暄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3-6。此乃朱子新本之顺序,然后接〈格致补传〉,再接〈诚意章〉。朱子新本的结构是经一章、传十章。与古本⑧*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暄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十三经注疏5.礼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页983-986。此乃郑氏本的顺序,此处未全举,只举到〈诚意章〉。与朱子的顺序相差甚多。郑氏的结构是,经一章,然后是六条目,其中传的“三纲领”在〈诚意章〉内,至于格致者,格乃是就物有本末言,致知乃知本,知之至也。的不同。
先举唐君毅先生对朱子新本之评论:
按朱子所编《章句》,移动古本之次序者三,改字一,删字四,新作《补传》,共百三十四字。此于原文之改动,不可谓不大,而使人不能无疑。[1]
例如:朱子对《大学》第四章(听讼)注云:“此章旧本误在止于信下”[2]6。然是否为误,此则尚待商榷;又改“亲民”为“新民”,并删“此谓知本”四字,谓是衍文,而加进他的《补传》一百三十四字。朱子之大幅更异,确实令人怀疑。
阳明已怀疑了*⑨“‘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民’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陈荣捷编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29页。,近溪亦不采朱子的新本说*⑩朱子视明德为“人之得于天而虚灵不昧者”,是把《大学》于礼、于政治下的脉络,转为心性论的脉络。,如朱子《四书》的阅读顺序为《大学》在先,《中庸》在后,而近溪则是置《中庸》于《大学》之前*①“问:‘中庸,比之大学,似更深奥?’罗子曰:‘先贤亦云:大学为入道之门。但以鄙见臆度,则义理勿论,而其次序则当先中庸而后大学。’时坐中有一习礼记者愕然曰:‘先生,岂常细观礼经篇目耶?盖二书,虽宋时选出,而现存篇次则果中庸先而大学后也。’问者曰:‘大学系曾子所作,中庸系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无序耶?’罗子曰:‘二书所作,果相传如是。但窃意孟子每谓愿学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学、庸,则此书信非孔圣亲作不能。而孔圣若非五十以后,或亦难着笔也,盖他分明自说五十而知天命。今观中庸首尾浑全是尽性至命,而大学则铺张命世规模,以毕大圣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诚、至圣结尾,而大学以至善起头,其脉络似彰彰甚明。自揣鄙见,或亦千虑一得,而非敢凿空杜撰也。试共思之。’”明.罗汝芳着,李庆龙汇集:《罗近溪先生语录汇集》(韩国首尔: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12-113页)。问者认为《中庸》深,应放《大学》之后。罗子却认为不然。习《礼记》者站在罗子方向,认为郑玄注《礼记》,《中庸》在前,《大学》在后。又有问者认为《大学》为曾子所做,《中庸》为子思,年代上应《大学》为先。但罗子认为《中庸》终于至圣,而《大学》始于至善,故可以《中庸》为先。,此同于《礼记》。
又如对“大学”的批注,朱子注为:“大,旧音泰,今读如字”[2]3。而在朱子之前(且在郑玄之前),“大学”则读为“太学”,意谓官学。朱子念为“大学”,目的在与“小学”相对②*②朱子认为十五岁入大学,而八岁入小学,先习洒扫应对进退之学。而这种讲法,伊藤仁斋是反对而质疑的。,别出“大学”所教乃是格物穷理之学。
依郑玄古本,对“大学”的批注则是:“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大,旧音泰”[3]983。即在郑玄以前,“大学”就读为“太学”,而郑氏不改其音,且顺古注诠解:是指作为博学广记者,有学问的人,可以作为人民的领导。
这是朱子与郑玄对“大学”诠释的不同处。朱子将“大学”解为“大人之学”,虽可与郑氏的“太学”相通,但朱子又在前面补上“小学”而与之相对,郑氏则无。至于阳明,则可接受“大人之学”,然此之“大人”,是指可与天地万物为一家、居于上位之人。
而王艮以“格物”为格本末先后之物(因原文谈道:物有本末);物者,事也,天下国家之事为末,身心性命之事为本;故格物者,以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即其所谓的安身说③*③“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之为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齐治平在于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身安者,则必爱身、敬身。爱身、敬身者,必不敢不爱人、不敬人。能爱人、敬人,则人必爱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爱我敬我,则家齐,一国爱我敬我,则国治,天下爱我敬我,则天下平。故人不爱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不敬可知矣。”见《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处士王心斋心先生艮》。包括刘蕺山、今人唐君毅皆采此解。。
近溪的诠解近于阳明、王艮,而远于朱子,此亦为古本与新本之不同。下文进入对近溪《大学》诠释的探讨。
二、近溪对《大学》的诠释
黄宗羲《明儒学案》列有近溪对《大学》的相关诠释,此置于近溪生平简介之后的评述中;黄宗羲以此为近溪学的重点,亦颇能显示近溪《大学》诠释之特色,文列如下:
尝苦格物之论不一,错综者久之,一日而释然,谓“《大学》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则尽。《大学》一书,无非是此物事。尽《大学》一书物事,无非是此本末始终。尽《大学》一书之本末始终,无非是古圣《六经》之嘉言善行。格之为义,是即所谓法程,而吾侪学为大人之妙术也”。夜趋其父锦卧榻陈之,父曰:“然则经传不分乎﹖”曰:“《大学》在《礼记》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则概而举之,继则详而实之,总是慎选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学术耳。”父深然之。[4]
这里约略记述近溪对“格物”之识解;以历来相关诠释甚多④*④以下略举诸家之说:(一)郑玄以“格物”为“来物”:“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十三经注疏5.礼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983页)。“格物”是引来外物:知善则引来善人,知恶则引恶人。(二)司马光谓「格物」为扞格外物,指不为物欲所诱。(三)朱子则以“格物”为穷理。(四)在阳明,“格物”是面对物以正吾人之心。以上看来,“格物”似乎只有形式义,不同学派皆能以自己学派义理来进行填充。,近溪初时亦陷入苦思,一日,悟到“格物”宗旨⑤*⑤近溪常有神秘体验,如早年的病心火而为颜山农所救,并拜山农为师,此亦曲折。,视为格物之本义,即《大学》在于“本于先知”。由于原文对《大学》“三纲领”谈完后,提到“知止而后有定”;《大学》“三纲领”为:明明德、亲民⑥*⑥近溪以古本《大学》为旨,故为“亲民”,非是朱子所改之“新民”。、止至善,而“知止”,在“知止于至善”;即要先知才能得——要从“知止”开始,最后才“能得”⑦*⑦“定、静、安、虑、得。”。
而所得、所知者,为事物之本末始终;需要能知所先后,方才近道。所言之“本末始终”,则指先要修身、齐家,而后治国等程序,即要明德于天下之前。如《大学》经常记述古书所载之嘉言善行,后辈学人之“格物”,即是依于古人之嘉言善行,以为格式而法效之,循序渐进,进学之以成大人之术,使居上位而为民服务。
但近溪父亲提出质疑,他认为“经”与“传”需分开①*①近溪父亲此言,系受到朱子影响;朱子言:“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4)但近溪是顺着阳明而回到古本,古本并未有经、传之区分;《大学》之经(既然无经,亦可称为“首一章”),若依古本,“首一章”结束后,加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矣”,之后进入〈诚意章〉;而朱子的〈传〉,经之后,接着是释“明德”;此系朱子自行改动顺序,因而不同于古本。又朱子改动之举,目的在于建构理气论,此从两个面向观察得知:(一)加入了〈格致补传〉;(二)将“格物”释为穷理。。对此,近溪的回答是:《大学》本只是一篇文字,并未有经、传的区分,“初则概而举之”:首先,系大要地谈“三纲领”、知本末;“继则详而实之”:即就先前之概言再做详论。因此只有初略、后详之别,而无有经、传,或是孔子、曾子之言的区分。因此古本《大学》总是慎选古人之嘉言,以令后辈学习而达于至善,成就大人之学。黄宗羲的此番概述,可谓点出了近溪《大学》诠释之宗旨。
以下,拟举近溪原文来进行解说,原文颇长,将分段进行,也因古本与新本内容殊异②*②〈诚意章〉以前,古本与新本相差较大,之后,即“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起到文末,二本则大致相同。,只举近溪的“三纲领”到“诚意”之诠释,共有两段,总开五小段,如下:
1.1问:“古本大学,其义何如?”
罗子曰:“大人者,以天下为一人者也。以天下为一人者,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也。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学大人以明明德以亲民者,其道必在止于至善焉。若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规矩者,方圆之至者也。学者于明、亲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则有定向而意诚,不妄动而心正,所处安而身修,由是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可虑之明而得其当矣。一知止,而大学之道得焉。是以明德、亲民者,必贵知止于至善,然至善之所当知者谓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为天下国家之本也;事有终始,是齐治平之始于诚正修也。是有物必有则,有事必有式,一定之格而为明德亲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后,即知止矣。道其不庶几乎!”[5]104
问者想知道近溪对古本《大学》的看法,以近溪顺于阳明,同样宗于古本,然此中所言却不见得同于阳明,反倒是较近于淮南格物之说,亦显示出对朱子新本的怀疑。
近溪解道:《大学》是学为大人之学!朱子虽也解做“大人之学”,但朱子的“大学”,是特定地与“小学”相对③*③“《集注》讥子游之不知有小学之叙,然游、夏同学于孔门,子夏独知有小学之叙,而子游不知之乎!观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诬也’,盖子游疑其有所隐而讥之也。”(日)伊藤仁斋:《论语古义》(东京:合资会社六盟馆,1910年,第377页)。伊藤怀疑朱子对大学、小学的区分,以子游、子夏既同学于孔子,而子夏知有小学,子游则不知,实属蹊跷。,近溪则无此意;而古本《大学》做“太学”解,指从政、为官之学;又近溪的“大人”特指上位者,上位者与百姓同其吉凶,故言“以天下为一人”。这种讲法源于阳明的“一体之仁”,最早则见于程子;阳明认为: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6]194-195
此即阳明的“拔本塞源论”④*④历来之学术研究,对阳明的“拔本塞源论”相当重视,可参见陈来:〈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学术界》2012 年第 11 期,第54-64页。苏子敬:〈王阳明“拔本塞源论”之诠释─文明的批判与理想〉,《揭谛》第9期(2005年7月),第153-186页。然依船山之见,此天下一体之说,非孔子本意,因为孔子谈人、禽之别,非是一体。,谈论重点在“一体之仁”,是从亲亲、仁民、爱物一脉而来,与墨家的“兼爱”⑤*⑤徐复观先生认为:“墨子的思想,是以兼爱为中心而展开的。‘兼’对别而言,在墨子为一专用名词,乃‘全体’或‘无差别’之意。”徐复观着:《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18页)。也有学者认为墨家非以兼爱为主,如蔡仁厚;而唐君毅则认为,至少早期墨家不是如此。并不全同。阳明认为此是有源之水,有其循序渐进,终以天下为一体。然人心有私,无此胸怀,因此主张复其良知。
而近溪之所以谈“一体之仁”,即在于“大学之道”⑥*⑥伊藤仁斋将“大学之道”之“道”字其中的训解之一为“方法”,即言:学做大人的方法。虽其不重视大学,但还是诠释之,“又有以方法言者,若大学之道,及生乎人今之世而反古之道是也。”(日)伊藤仁斋:《语孟字义》,选自《日本儒林丛书》第6册(东京:东洋图书刊行会,1929年,第12-13页)。是学做大人之学,此“大学”者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要明明德、亲民于天下,达于至善而后止⑦*⑦近溪视“三纲领”,层次不全同,系亲民、明德为一组,知止则自为一组,而止于至善与后文的“知止”、“知所先后”、“知本”、“知至”是相关一致的。;要达之于天下始可止,而且做到极致,犹如方圆之极、之至,合于标准才是至极。而“格物”者,谓“格之为式”,乃是法程于古人嘉言为其物则、为其范式,如同规与矩般,而达于其极。
故要知止于至善为先,才能近于大学之道。朱子把“三纲领”与“八条目”分开①*①虽不见得截然分开,但相较于近溪的诠释,朱子的分解性重,朱子言:“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3-4。,而近溪则是摄“八条目”于“三纲领”之中②*②在《大学》古本中,就已是八条目在于三纲领中,三纲领的至善要知止,至善始能止,而八条目要先格物致知,以知如何是至善,要依于格式、物则、规矩始能达至善。,也就是“三纲领”中的“止于至善”与后文的“知止”、“知所先后”、“知本”、“知至”是相关而一致的,即要达于至善,需先知止,才能有得,得于大学之道。至善如同方圆,以规矩为标准而为至极,即把明德、亲民做到至极。
而此至极之完成,有一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大学》在“知止”一段之后言道:“物有本末,事有先后,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里谈到物与知,近溪以为,系与格物③*③王艮的淮南格物即是如此,格本末先后的物,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致知有关,不需如朱子一般地增补〈格致补传〉。朱子因着《大学》之〈传〉,三纲领后马上接诚意,于是怀疑有错简,故自行补了《格致补传》;若依近溪,则格物已在“物有本末”、致知已在“知所先后、知本、知之至”之中。因此“八条目”并非一连贯的前、后相因,而是需将格物、致知与后六条目分开来看;格物、致知为虚说,格物是套在六条目之中,去“格”六者谁先谁后;致知则是知所先后,以至于至善。
因此近溪言:“物有本末,是意心身为天下国家之本也;事有终始,是齐治平之始于诚正修也。”物有本末,指的是意之为物、心之为物、身之为物;而事有终始,乃家国天下为终,诚正修为始。故物与事不同,例如以修身而言,修是事,身是物。这种解法近于王艮的淮南格物说,两者都以古本为准,而不采新本。
至于格物、致知如何诠释?近溪认为,物有则,事有式,格者,乃是法程、格式,依于规矩、范程而修,顺序而修,如以古人之嘉言善行作为准则,即能从本到末,从诚意到平天下,是依着知止于至善而为至极。知止则须以事物之进程、本末先后为准而做到治国、平天下,做到亲民、明明德于天下。一方面,要知止,知其至善之至极;另一方面,要知本末先后,即在至极之前要能踏实,要从基本的诚意、正心开始,达到治国、平天下,若不依此范程,则不可能至于至善之标的。
近溪依于古本,以诚意为起始点,至于诚意之前的格物、致知,近溪再做发挥如下:
1.2观夫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国齐家以明明德于民者,固必先修身正心诚意以明明德于己者焉;欲人己之间悉得其当者,又贵先明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在于诚意正心修身之如何而为本之始,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如何而为末之终。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于“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物皆当其则,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极焉耳。诚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止焉,则意可诚,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齐,国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天下国家之本。本乱则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所厚既薄,无所不薄矣。夫知乱本末者之非善,则知格本末者之为至善。故申之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5]104
近溪以为,欲明明德于民之前,必先明德于己,而己德内据于心,这与其宗良知学有关。除了明己心之德外,还要知所往,要知止于至善。故致知,乃要知所往,知所往为至善,然于达至善之前,有其范程,诚正修为本,而齐治平为末;从〈诚意章〉的「毋自欺」,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都是就其本末先后言;从诚意为本,先知“毋自欺”,以至于家国天下之末,亦知“国以义为利”,此知在知其本末。
至于格物,物有其则,事有其式,依此则式为准,循序渐进,以达于至善,即法程于大人之格式,天子以至庶人皆然,同此格式以进德修业。因此所言之格物与致知,皆有其秩序先后,致其本末先后以达至善之知,并依此法程而修学,则能至于大人之学。
近溪又举《大学》句:“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修身为本,身不修而能治国者,否矣。至于所该厚者薄,何以是“未之有也”?厚薄与本末、先后的对待性是一致的。身该厚而薄——自律该严,却责人以严,则是未能治国、平天下的。近溪引《论语》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篇》)相同地,该对自己要求多的,却少要求;该宽厚以待人的,却严以待人,此将招来怨尤;不只有怨,如此而能治平者,未之有之。此本末、先后、厚薄之阶序亦须知之。这是一种实践的智慧学,即《论语》既仁且智的意思。
而所谓格物、致知者,与本末、厚薄的关系为何呢?——知止者,知止至善,至善要循序而进,有其本末先后,若乱此秩序即为不善,顺此秩序而不逾越,循序则可达至,此则为善。此乃知所先后,亦与致知相关。至于格物,近溪言,吾人所要知者,为知“格本末者之为至善”,乃是指依于法程而循本,以至于善;以修身为本,天下为末,由本至末,顺此修进而为善,如此才是知本(意身心为本),才是知之至矣。在此看到近溪把止至善与知止相通,而知止又与知所先后、知本、知至相通。知本者,乃知修身为本,知至者,乃此为知止至善。
近溪又言:
1.3自大学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①*①近溪“知”之八处,标示如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后”,可见知所先后即知所止矣;次言“致知在格物”,又次言“物格而后知至”,末则复言“知本”则“知至”,然则至善之为本末,而本末之为格物也,又不彰彰着明也哉!所谓诚其意者以后,则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盖所谓诚其意者,即大学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历引淇澳诸诗、康诰诸书而及夫无讼之说者,皆求知夫诚意之所以为物之本、所以为事之始,而一一须合夫至善之格,如是则诚意为合格,否则为出格。[5]104-105
若把朱子修定的《经一章》,加上“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矣”②*②因为朱子把此段移到第四章。,则其中共有八处言“知”,包括:知本、知至、知所先后、知止、“及物格知至,知至意诚”、“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共有八处谈致知。而近溪把此八处致知统一起来,不用特别区别“三纲领”与“八条目”,且将格物、致知从“八条目”区分出来,只剩六条目。而格物与致知,不用如朱子所言,需加《补传》,因格物是顺物则之格式而为,致知是知此身为本,家国为末。格物、致知只是形式义,而意诚、身修、心正、家齐、国治、天下平,是内容义。两者层次不同,既不同,就不需如朱子的补充。且当近溪把此八处谈“知”统一起来,则知至,为知至善矣。至善却要有其本末之方法,故与“知所先后”相通,而本末先后则是物则,顺此物则以效法之,如此才合格,否则是在格外,是为出格。
近溪又言:“所谓诚其意者以后,则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要了解近溪此语,应先对《大学》古本顺序有一认识,笔者将此古本置于前文脚注处。近溪认为,格物、致知与其他六条目不是一例,不可做同一系列看;格物要有物的内容,内容则为诚意到平天下,而格物是形式义,诚意到平天下是内容义。格其本末先后之物,故近溪认为诚意以后,皆为法程物则之本末先后,而吾人之知止者以此,知所先后者以此。
而本末先后指的是什么呢?诚意为本,的确古本《大学》是先以诚意之“毋自欺”言之,明德者之内容,如“克明峻德”者甚至在其后③*③此乃朱子的新本与古本之不同处,新本先释克明峻德,后才有诚意。先释“三纲领”,才有“八条目”。。而近溪不取朱子作法;朱子分经一章,传十章,十章的传,先释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后自补《格致章》,之后是《诚意章》;近溪既不取,也就没有经、传的区别,至于《诚意章》,其言“毋自欺”,到淇澳之诗、康诰,以及孔子的无讼之说,都视为《诚意章》。孔子的无讼说后,又有一个“此谓知本”,乃知以诚意为本。
从这里看出,近溪版的《诚意章》范围太大,而所谓的“克明峻德”、“作新民”、“为人臣止于孝”等语,似乎是在诠释“三纲领”,那么朱子的讲法是否较合原意?但由于近溪不依“三纲领”、“八条目”的截然区分,其视《诚意章》重点在讲本、讲先④*④此即阳明意:“先生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陈荣捷编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129条。。此“本”与“先”乃为知所先后,从此先后做去,至于至善,故此与“三纲领”相通;“三纲领”者,以亲民、明德于天下,而依循先后到至善为极。先知,但后到⑤*⑤如同亚里士多德“目的因”,先有,但后达至。即先了解目标为止至善,而后依此目标做去。,在初学做大人之时,已知未来要做为大人的目的是亲民、明德,故诚意中已知将来事业:即为亲民、明德;故于《诚意章》中出现“三纲领”之文,在近溪言,亦是理所当然,以依此法程而去,则为合格,不依此,则不合格;此乃释格物,格物之物则,以诚意为本。
然近溪的讲法亦受到质疑与挑战,以其既要诚意,又要合格,此有重复之嫌:
2.1或曰:“人能诚意则善矣,何必复求合格也哉?”
罗子曰:“程子不云乎?‘用意恳切固是意诚,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则诚意而出格者也。例之修齐治平,节节为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诚意紧接着知本、知至说来,即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盖学大人者,只患不晓得通天下为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晓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则国家天下攒凑将来,虽狭小者,志意也着弘大;虽浮泛者,志意也着笃实;怠缓者,志意也着紧切,自然欺不过,自欺不过,便自然己不住,如好色恶臭,又自然满假不得,而谦虚受益。其凝聚一段精神于幽独之中者,又非其势之所必至也哉!幽独者,是未接国家之先,慎则是知得本立于此而敬谨严切,即前定其志意之谓也。此言君子之孳孳于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孳孳于不善者,亦惟日不足”。[5]105
问者的意思是:若格物、致知为虚说,始于诚意,而意若能诚则已善,何用再做合格工作。
这样的提问系站在阳明观点,阳明认为,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以良知自有天则,不用再谈合格与否,其诚意之说是以良知学为主,能致其良知则万事足矣。而近溪见解不全同于阳明,古本《大学》也未必以良知学为主,因此意诚之后尚有不足,还要法程于物则始可,这便是格物。
此处近溪引程子之言回辩,认为诚意者,岂知其出于私意?岂自知无所把持①*①如同朱子言,恻隐其所不当恻隐。恻隐是对的,但只依于主体,而无客观以定之,则有误。?因此要有一个外在的客观法则。如同谈阳明的良知是否具足,若是真良知,自然具足,但现实中能有真良知者毕竟不多,为避免将私意误作良知,故须多以他人的良知、经书为准则,这也是良知学后来的发展;如甘泉、高攀龙与蕺山等人,加进了朱子学的格物,以让心之发,常能合格。这也近于孟子所言:“徒善不足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尚需法效先王之道。
故近溪认为有意诚意,却成私意,这便需有一个外在标准以为规矩。在古本《大学》,诚意接于知本、知至之后,系与经文的“知止后有定”相通,故诚意乃是能定的意思。能定其为本、为先,而修齐治平为其秩序,节节做上去,以至天下国家,至善为止。虽然做到天下国家,然此家国天下与个人自我却是一体,若不知为一体,我为我,天下为天下,容易区分而有私心,不肯为国、为民;一旦知物我一体,天下一家,则心意狭小者,亦将广大恢宏;虚者将实,狭者将大,顽夫有廉,鄙夫能立志。
又诚意者,毋自欺也。朱子对诚意的解释是:“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2]3大人者,能实其心之所发,而真诚之,又知止至善,天下为一人,而依此进程而循序之,便自欺不过,而所发皆实,如好好色,如恶臭臭一般。而《诚意章》的本文谈到慎独,近溪认为,是前定其志意者,如此则诚,则为君子,不如此则为小人,小人见君子厌然揜其不善以着其善。
而古本《大学》与新本的不同,在于古本把新本《传》对“三纲领”的诠释,如“克明峻德”、“苟日新”、“为人臣止于孝”等文字,亦放在《诚意章》中,此乃近溪需面对者,答道:
2.2但其中既诚,则其外必形,如财富者必润其屋,涵养者必润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诚切,则自然明明德于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②*②淇澳詩:“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暄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烈文詩云:“於戲前王不忘。”此二詩近溪放在〈誠意章〉,而朱子則放在“三纲领”的止至善中。二诗,以见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则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贤可亲、可乐可利也,是非诚中形外之征也耶?所以康诰、太甲、帝典③*③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至於朱子新本则非放在《诚意章》,而是放在《明德章》。,皆自明其德不已,而及诸民又不已而通诸天。又明德亲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浃洽于父子君臣朋友间也,然总是从知止至善中来,知止至善从知所先后来,知所先后又是从知立本以及其末来也。故于意之能诚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也”。此段于明明德、亲民、止至善,详说备举,然却都是形容学大人者知本以后一段精神。如《易》谓:“拟而后言,议而后动”。拟议以将成乎身家国天下之变化者也。[5]105
诚于中、形于外是《诚意章》对于君子小人的形容,小人闲居为不善,表现于外,人见之,如见其肺肝然,此如同富润屋、德润身一般;诚于心中,则表现于外,富有之人,则屋亦华丽。君子先做到明德于己,明德之心若诚,则能推至于天下国家,明明德于天下。
至于古本《大学》难解之处,而与新本《大学》不同者,在于古本把新本的“三纲领”之《传》都放在《诚意章》,如朱子把淇澳之诗④*④“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暄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与烈文之诗⑤*⑤“於戲前王不忘。”置于传第三章,以此释止至善,而近溪则放在《诚意章》。“三纲领”之传文如何可与《诚意章》通合?近溪认为,民之所以不忘先王之德,即是诚意之征,人能诚意,以之为本,推而至极而平天下,则百姓不忘;此系诚于中,形于外之征。至于举康诰、太甲等例而及于“克明峻德”,此都是自明己德而施于百姓,从诚己意做起而通及于天⑥*⑥原文引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通及于民。
而关于知止至善一段,近溪认为,“三纲领”不是平列,是以亲民、明德为内容,而以知止为起点,把亲民、明德做到至善,施及百姓天下,此即止至善,因此近溪言:“明德、亲民之必得所止。”于是古本《诚意章》提到“为人臣止于忠”等等,系止于至善之征验。“止至善”是纲领,是从“知止至善”而来,因为大学之道乃是学做大人之学,要有目的、方向,故先知止,先有其方向,才可依此方向循序做去;而至善是目的,非是一蹴可即,需有本末先后的依从格式,诚意为先,平天下为末,此知所先后即能近于大学之道。
古本《大学》出现两次“此谓知本”,第一次是出现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意指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第二次是出现在《诚意章》之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这是指前文的《诚意章》,以诚意为本。然在朱子新本中却只出现一次,朱子引程子之说,视古本所出现的第二次“此为知本”为衍文。
然而两次“知本”意涵并不同,不应视第二次文为衍文,因为第一次“知本”,系知修身为本,第二次“知本”,系就诚意为本,都是从本达末,有其次序。《诚意章》之所以谈亲民、止至善,乃是从“知本”以后,能到天下国家,能到亲民,此乃学做大人之道的精神。在此近溪举《易经》文,用以比喻《大学》的本末先后,而必先知其方向,如《易传》言:“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易传系辞上》第八章此乃先前定学者的心志,拟议后才言动,如同《大学》,知其方向、目的之后,才有所言动。近溪把这三句文字的最后一句改为:“拟议以将成乎身家国天下之变化者也。”意谓拟议后才知从本到末的变化,从心身家国至于天下的进程。这与近溪所言的“先知”是一致的,知是形式义,知所先后,而内容中以诚意为先、为本。
三、结语与反思
笔者谈近溪的《大学》诠释,并只针对《诚意章》之前部分,原因是古本与新本的差异处即在此。近溪的《大学》诠释是依于古本,这也是依于心学阳明而来,然不以良知解《大学》,而是尽量依于古本脉络,而还其原貌。近溪之解甚至可说更近王艮的淮南格物,系是以身为本而家国为末的安身说。而近溪更进于淮南者,在于格物的“格”字以“式”字诠释之,故有合格、不合格的意思:若能依于本末先后,依于前人的嘉言美行而实践,则为合格!此乃近溪的贡献之处。又近溪的“大学”,以阳明学为本,又谈以孝、弟、慈为先,家家户户冀其能成就孝、弟、慈,此与他的《大学》诠释——修身为本、知所先后是相关的,盖孝、弟、慈为治国、平天下之本。
又文中之讨论,主要是以朱子的改本为对照;朱子的改本变动太大,以至于令人怀疑。依于前人研究,得知朱子新本已为理气论之精神,成一以内圣心性论为主的版本,虽也谈家国天下、政治之道,但毕竟是从心性开出,与郑玄本是有距离的①*①郑玄解《礼记.中庸》:“仁者,人也”,释之为相人偶,此亦近于许叔重的仁,以从二人的讲法,是放在人伦的脉络中,而朱子诠释是先从个人心性着手。。
至于朱子的《格致补传》,在近溪的诠释中,则是不必要的。格物与致知都是虚说的形式义,知者,知本末先后,诚意为先,平天下为末;格物者,则依于事物之则,而法程此《大学》之序,而成就大人之学。亦是说在《大学》原文“此谓知本”、“物有本末”,就已是在谈格物、致知,不必再补《传》,自然也就不用再分经与传,经、传之分是朱子做成,《礼记》之文亦未特分经、传者,则朱子的动作是可谓多余。而“三纲领”与“八条目”的区分,亦不具朱子所言的截然性,“诚意章”处都谈了明德与亲民,以此为“知”而达于至善。
故知近溪的诠释更顺于古本,而不用如朱子的删字、补字。然朱子的《大学》是用来设计其体用论、理气论。朱子的论述是一种创新建构,与近溪的企图回到原意,是两种不同的体系,而各有其优点。
[1]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M].台北:学生书局,1986:305.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阮元.十三经注疏 [M]// 礼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
[4]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罗汝芳.李庆龙汇集[M]//罗近溪先生语录汇集.首尔:新星出版社,2006.
[6]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M].台北:学生书局,1998:194-195.
[7][日]伊藤仁斋.论语古义[M].东京:合资会社六盟馆,1910:377.
[8]苏子敬.王阳明“拔本塞源论”之诠释─文明的批判与理想[J].揭谛,2005(9):153-186.
责任编辑 何志玉
The Research of Luo Jinxi's Interpretation ofTheGreatLearning:From the "Three Creeds" to "Sincerity"
CAI Jia-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unghai University, Taizhong, 40704, Taiwan)
The essay interpreted Luo Jinx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Luo Jinxi agreed with Yangming thought, and accepted principles of the Great Learning’s ancient texts, not the new version from Zhuzi; He defined the Great Learning as the cultivation of great person, which amplified and developed Yangming’s “The Entity of Benevolence”; His interpretation closed to Taizhou Wang Gen’s view of “investigating things in the south of Huai” but has his own neologism.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Four Books, he didn’t adopt the system of Zhuzi, but followed in Zheng Xuan's ancient meani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priors to the Great Learning. And he explained the “investigate” in “investigate things” as “pattern”, which means be qualified, check, and suit for standard; Moreover,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knowledge”, and he believed that the key point of the Great Learning is “knowledge”, and thus establishing the argu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he formed his own ideological system.
Qualifie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Knowledge-based; Great person; Standard
2016-03-17
蔡家和(1968-),男,福建惠安人,台湾东海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宋明理学。
B248.3
A
1673-6133(2016)03-00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