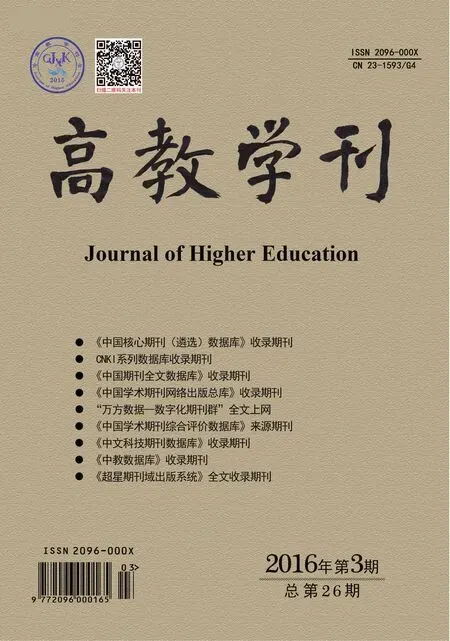论英语中的语用知识及其影响因素
2016-03-18龙湘明湘南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郴州423000
龙湘明(湘南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郴州 423000)
论英语中的语用知识及其影响因素
龙湘明
(湘南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郴州423000)
摘要:本文对语用知识的性质、内容和影响其使用的因素这三方面进行了研究。语用知识包括词汇信息、言语行为结构和语用策略的知识,它是一种语言知识。社会文化知识是影响语用知识使用的许多因素之一。语用知识的这种性质显示语用教学是可能的。现行的外语教材应该注重语用知识信息的输入,但与此同时也该意识到语用能力培养的艰巨性,毕竟有众多因素影响语用知识的使用,而且这些因素都非常复杂。
关键词:语用知识;影响因素;语用教学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finition, contents and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use of pragmatic knowledge. It is a kind of linguistic knowledge, involving lexical, speech act information and pragmatic strategies. Sociocultural knowledge however is only one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e of pragmatic knowledge.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pragmatic knowledge imply its teachability. The current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put of the information of pragmatic knowledge, but it should be reminded that pragmatic competence development is not easy, for there are so many complicate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e of pragmatic knowledge.
Keywords:pragmatic knowledge; influencing factors; pragmatic teaching
一、概述
Bachman认为语用能力是指:“在话语交际过程中根据语境情况实施和理解具有社交得体性的施为行为所运用的各种知识的能力”[1]。Bachman&Palmer(1996)对语用知识定义为功能知识(functional knowledge)和社会语言学知识(sociolinguis-tic knowledge)。然而,在实际运用中,我们发现语用知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很容易和其他的概念如言语行为、语用策略等混淆。因此,本文着重在语用知识的性质、内容和影响交际者使用语用知识的因素这三方面进行探讨。
二、语用知识的性质和分类
语用知识可以抽象地定义为关于语言运用的知识,但是这样模糊的定义在实际的研究中作用不大。本文认为,从广义上看,语用知识可以指任何准确理解语言意义和构成人们可以得体产出的知识。从狭义上看,语用知识指准确理解会话所表达的含意和构成得体传达的语言知识和语用策略知识。在此文中,我们在狭义的语用知识进行探讨。因为语言知识和语用策略知识构成了言语交际的内容,而文化知识只是影响语用知识使用的因素,是调节性内容,所以我们把语用知识限定在语言知识和语用策略知识的范围内。关于语用知识的分类,关于语用失误的分类,Thomas把语用知识分为语用语言知识和社交语用知识[2],关于语用能力的定义,Bachman把语用知识分为施为能力知识和社会语言知识[2],何自然则把语用知识分为语言表达知识和语言理解知识[4]。根据以上语用知识的狭义定义,我们把语用知识分为词汇语用知识、言语行为的语用知识和语用策略的语用知识。
(一)词汇语用知识
词汇存储于心理词库中,它们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以各种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如同义、反义和上下义的典型关系等)。例如,“家用电器”与“家庭电器”同义,与“电冰箱”、“洗衣机”、“电磁炉”、“微波炉”、“电饭煲”、“电吹风”等构成典型的上下义关系。根据认知语言学理论,这些下义词中有典型的中心范畴成员,有次要范畴成员,还有非典型的边缘范畴成员。在这些“家用电器”的下义词中,大概“电冰箱”、“洗衣机”是典型成员,“电磁炉”、“微波炉”、“电饭煲”是稍微次要的成员,“电吹风”则是边缘成员。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就很难理解以下对话最后一个话轮的隐含意义:
大妈:说出来都不怕大家笑话,他家穷的啥玩意儿都没有。
大叔:别巴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嘛。
主持人:还有家用电器呀?
大叔:手电筒呀![5]
现时今“手电筒”已经是“家用电器”非常边缘的下义范畴,十有八九的人大概不会认为“手电筒”属于“家用电器”。这位大叔这里仍然振振有词地说当时他家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产生了幽默的意义。这种偏离常规的词汇运用叫做离格使用法。可以说,很多话语含意的产生都和因为对词汇的离格使用有关。
(二)言语行为语用知识
在本文中,言语行为是指人们的交际意向(communicative intention),也就是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s)。也就是说,不同的结构构成不同的言语行为。比如请求言语行为可以由三种语体构成,它们分别为:醒示语、中心语和辅助语。醒示语的作用就是让对方注意自己说话的内容。请求醒示语有称呼语和提醒语。直接决定说话者交际意向的话语就是中心语。请求中心语有九种语义结构:祈使句、明示施为动词句、缓和的施为动词句、镶入式的祈使句、需求表达句、建议套语句、疑问句、强暗示句、弱暗示句,其中前三种为直接言语行为中心语,中间四种为规约性的言语行为中心语,后两种为非规约性的言语行为中心语。出现在言语行为中心语之前和/或之后的就是辅助语,它是表示原因、道歉、解释、结果、义务等附属性的语言,但又必不可少的一种结构。
(三)语用策略知识
语用策略是交际者使用特定话语去实现交际意向。根据各种分类标准,语用策略可以分为说话者语用策略、听话者语用策略,直接和间接的语用策略等等。按照言语行为中心语的界定,直接语用策略指说话者使用直接言语行为中心语,间接语用策略指说话者使用规约或非规约性的间接言语行为中心语。可是绝大部分交际意向的达成不仅仅只包括一个话语。故会话层面上的语用策略,包括言语行为辅助策略和话轮协商策略。前者有前辅助策略、后辅助策略和复合辅助策略。前辅助策略有时也称为预示策略,就是出现在言语行为中心语之前的话语,往往起到铺垫的作用;后辅助策略就是出现在言语行为中心语之后的话语,起到解释或者进一步说明的作用;复合辅助策略就是出现在言语行为中心语之前和之后的话语。言语行为辅助策略一般是使用在威胁面子程度高的言语行为中。
话轮协商策略就是交际双方通过三个以上话轮达成意向。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汉语中一般关系的交际者之间的邀请言语行为,即便邀请成功,也要经过多个话轮。邀请者使用的大多是直接语用策略,而受邀请者会根据会话进展情况,综合使用直接和间接语用策略。
三、语用知识使用的影响因素
从具体到抽象,影响语用知识使用的因素包括交际者(还蕴涵着交际者相互之间的关系)、交际场合、交际者的价值观念和交际者的个人推理能力。首先看交际者和交际者关系。言语交际中主要有说话者和听话者。他们的关系体现为相互之间的相对权力、距离和权利或义务。交际者双方的相对权力差异可能由于行政级别、专业知识、年龄、辈分、榜样参照等因素引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行政级别高者、专业知识更多者、年长者、辈分高者、有更大榜样力量者(例如明星和英雄相对于崇拜者)具有更多的实际和心理权力和地位。Spencer-Oatey[6]把权力分为法定权力(legitimate power,即某人因为社会角色、年龄或地位原因在法律上拥有对于另一方的心理和物质上的支配)、榜样权力(referent power,即某人因为成为偶像而拥有对崇拜者的支配)和专家权力(expert power,即某人因为在特定领域掌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而能够支配想掌握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特定个体)。一般情况下,权力地位不同的交际者会采取不同的语用策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高权力或地位者会相对直接的语用策略,而权力和地位低者则会采用相对间接的语用策略。
交际者双方的相对距离即他们的熟悉程度。一般说来,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最大,亲密朋友和家人之间距离最小,其他的如同事和普通熟人之间的距离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Wolf-son[7]的膨胀理论显示,对于关系处于两个极端的交际者来说,他们的语用策略往往是相对固定,而且可以预测的。而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交际者来说,他们的语用策略往往是相对复杂的。这是符合语言直觉的交际者在言语行为中还有相对的权利或义务。有强制性的权利或义务。比如,人们可以有自己行事自由的权利,但是这样的权利是以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为前提的。交际场合指交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事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但是大多局限在文体学和社会语言学领域,强调交际场合对人们言语表现的限制。但是语用学更强调说话者运用语用策略改变场合的性质。比如下例:
(F和M分别是J的父亲和母亲)
F: Our Jen done that.
M: How many coats did you put on it, Jen?
J: How many what?
J: Oh, quite a lot.
F: And'ow about the waistcoats and socks?
M: Oh, she didn't bother with those.
F: She'm lazy.[8:186]
这里,父亲选用了昵称(our Jen),而且还说了不合语法的话(Our Jen done that.)和不适当的省音('ow),他的目的是把严肃的场合气氛变得轻松些。可见语用上关于场合的知识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它需要说话者能选用合适的话语、语气甚至是副语言手段来改变场合的性质。
交际者的价值观念指人们关于事物、行为、想法重要与不重要、好与坏的判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言语行为、话题损益性质的知识;对交际修辞原则的知识;对社会实在物、社会现实和发展变化等方面的观念和知识。
言语行为、话题损益性质指特定言语行为的强加程度和特定话题的禁忌程度。强加程度高的言语行为和损害面子大的话题要求用间接语用策略,有时甚至要采取“退避”策略(off-record)。英语本族人认为大多数的言语行为都有一定的强加性质,这就是多数人发出邀请时用预示语列(prese-quence)的原因。他们一般不直接询问对方的年龄、身高、婚姻、收入状况、宗教信仰等,认为这些话题的面子损害程度很大。
最后,个人推理能力的不同也会影响到语用知识的使用。推理就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判断中推导出一个新判断的思维形式,包括论证推理和非论证推理。前者就是由给定的前提一定得到具体结论的推理过程,具体方法包括三段演绎法、联言分解法、选言推理法、假言推理法、连锁推导法、综合归纳法、归谬反驳法,等等。非论证性推理就是从一个前提可以推导出多个结论的思维方法。
另外,语用教学可以加快语用习得的进程,这已经得到实验研究的支持,比如,Koike & Pearson[9]、Alcón[10]等。他们的做法给外语语用教学带来一定启示。首先,他们都是以单个的言语行为作为实验教学内容(Koike & Pearson和Mart侏nez-Flor & Fukuya都是以建议言语行为作为教学内容,Alcón以请求言语行为作为教学内容)。其次是教学方法丰富多样,如教师讲授、学生-学生互动、学生-教室互动,等等。最后更重要的是有反馈,包括学生之间相互纠错和教师的反馈。总之,实际的语用教学也应该这样,结合知识输入和训练输出,结合学生的表现和教师的反馈,有效提高学习者的语用能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语用知识的性质、内容和语用知识运用的影响因素这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语用知识最重要的应该是语言知识,包括词汇信息、言语行为结构和语用策略的知识。社会文化知识是影响语用知识使用的许多因素之一。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语用知识的这种性质显示语用教学是可能的。现行的外语教材应该注重语用知识信息的输入,但与此同时也该意识到语用能力培养的艰巨性,毕竟有众多因素影响语用知识的使用,而且这些因素都非常复杂。
参考文献
[1]Bachman L F.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M]Oxford:OUP,1990.Bachman, L. & A. Palmer. 1996. Language Testing in Practice[M]. New York: OUP.
[2]Thomas , J.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3(4):91-122.
[3]Bachman, L.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 in Language Testing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Reprinted by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Shanghai, 1999.
[4]He, Ziran. Notes on Pragmatics [M]. Guangdo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1996.
[5]赵本山,等.昨天、今天、明天[EB/OL]. http://www.xici.net/ b157915/d24375129.htm [Retrieved on April 27th,2008.
[6]Spencer-Oatey, H. D. M. Conceptions social relations and pragmatic research[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2,20:27-47.
[7]Wolfson, N. The bulge: a theory of speech behavior and so-cial distance [A]. Fine, J. Second Language Discourse: A Text-book of Current Research [C]. Norwood, NJ: Ablex,1988.
[8]Thomas , J. Meaning in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1995.
[9]Koike, Dale April & Lynn Pearson. The effect of instruction and feedback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competence[J]. System,2005,33:481-501.
[10]Alcón, 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led versus learners' intera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s in the EFL classroom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2,37:359-377.
中图分类号:G623.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6)03-0263-03
作者简介:龙湘明(1981,9-),男,湖南望城人,英语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