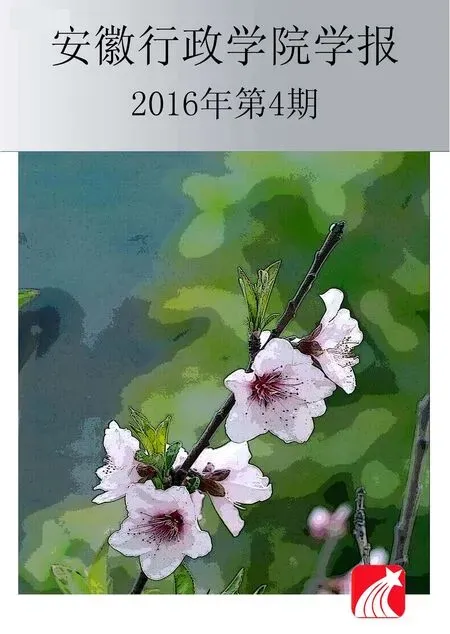公众参与平台:传统参与平台与新兴参与平台间关系研究
2016-03-18常凌
常凌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上海 200233)
公众参与平台:传统参与平台与新兴参与平台间关系研究
常凌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上海 200233)
公众参与的方式和途径可以划分为传统公众参与平台和新兴公众参与平台,二者在参与主体、客体以及方式上多有不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兴公众参与平台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显著,这将给传统公众参与平台带来深刻的影响。二者不仅有区别,也有联系,应形成有效的互补,共同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公众参与;传统参与平台;新兴参与平台;关系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途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所在[1]。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人们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从根本大法上明确了公众享有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各类规划编制以及其他国家大政方针的参与权利。从民主化发展进程来看,公众参与对于健全民主制度,拓宽民主形式,保障民主权利等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推动我国政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秩序和规范不断健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公民意识得到启蒙,对于自身权利的诉求更加强烈,因此,涉及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保障公众参与尤为重要,不仅能够确保决策和行政的民主性、科学性,也能够提升公众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传统公众参与的方式和途径较为单一,多为在国家机关主导下的公众参与,参与主体十分有限,多为各行各业的精英和代表性人物,其能否真正代表公众,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公众关切是有待商榷的;参与客体,即所要探讨的各项公共事务比较宏观,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事项仍多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参与方式单一,传统公众参与方式一般是开会,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将固定的参与人群召集起来开大会,通过讨论、发言、提案等渠道参与公共事务。可以看出,传统的公众参与方式的参与成本比较高,而且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难以充分保证,使得传统公众参与机制流于形式。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互联网+”已成为支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正逐步进入政府管理领域。依托互联网技术兴起的各类网站、社交软件、新媒体等改变了传统社会信息交流与传播模式,政府基于互联网技术搭建的公共服务平台得到推广和应用,这一新兴公众参与平台大大增强了公民与政府间的互动与交流,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渠道,促进了政府与公众间对话关系的形成。新兴公众参与平台出现之后,其与传统公众参与平台之间会产生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概念界定
(一)公众参与
公众通常是指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共同的兴趣或关注某些共同问题的社会大众或群体。公众参与就是指具有共同利益、兴趣的社会群体对政府涉及公共利益事务决策的介入,或者提出意见与建议的活动[2]。公众参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关于政治参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将其定义为: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政治参与是行动而不是主观的态度,参与的主体是平民而非官员、政治候选人和职业政治人员,政治参与的目标指向是政府决策的活动[3]。因此,公众参与是参与主体公民通过一定的参与方式和途径,对参与客体社会公共事务的知晓、影响。
(二)公众参与平台
宪法规定公民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公众参与的途径和方式一方面需要在制度和法律上予以保障,另一方面则需要相应渠道连接政府与公众,为参与创造可行条件。因此,公众参与平台可以界定为通过一定方式,连接政府和公众,使双方可以就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沟通、交流、协商、博弈和平衡的交互机制,具有公开性、平等性、广泛性和便利性等特征。
(三)传统公众参与平台
传统公众参与平台是由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衍生出来的,主要是党、人大、政府和政协等国家机关主导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及国家对公民权益救济的一系列制度平台。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①党委层面:党内民主生活会、各级党代会、与党外人士民主座谈会等;②人大层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③政协层面: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地方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内部各类专题调研会议;④政府层面:听证会、信访、政府信息公开等。在此之外,传统主流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公众参与平台的角色,由于其大多由党和政府控制管理,因此将其纳入传统公众参与平台范围。
(四)新兴公众参与平台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同时也推动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网络为公众和政府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自由对话、交流互动和表达意见的场域,并逐渐演化成为新兴公众参与平台。按照技术支持及互动交流方式,新兴公众参与平台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类:
(1)政府部门门户网站,是政府信息公开及向公众征求各项意见的网络平台,按照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总体上开通了政府门户网站,但是网站的功能及运营层次不一,一些政府网站流于形式。
(2)主流媒体网络平台,这主要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网等网络媒体平台,其一方面发布国家的大政方针,对政策进行解读,引导公众舆论,另一方面承担着舆情监测、收集民意的职能。这些网络平台经常组织网民就某一问题进行讨论,或设置评论区来观察民众的反应,通过传媒力量将公众意见传输给相关部门。
(3)网络论坛,这一网络社区平台集聚了大量网民,其中不乏一些具备一定知识背景和专业技能的人士,他们经常就政府和社会上存在的现象进行讨论,瞬间便可形成数万条讨论信息,尤其是一些意见领袖,其就某一问题进行描述之后,众多网民便会迅速跟帖,形成一股强大的网络力量,比如天涯论坛、强国论坛等较为有影响力的网络论坛。
(4)社交(媒体)平台,在我国主要是指微博、微信、QQ等社交平台,是人们日常用于沟通交流的技术软件,然而,原本简单的社交工具正逐渐演变成为公众表达诉求的平台。公众通过在社交平台上进行转发、评论、发起话题讨论以及点赞等手段表达自己对问题的关注和看法。依托社交平台诞生了许多新兴媒体,通过各类公众号进行媒体传播,而且随着技术的改进和网络影响力的发展,许多政府部门纷纷开通各类社交认证账号,用于发布信息、沟通交流及引导舆论。
(5)省市长电话热线,为缩短政府领导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为人民妥善办理好各项事宜,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许多省市开通了省市长电话热线,公众可以就任何政策及社会管理问题致电热线。
二、文献综述
(一)公众参与研究
目前对公众参与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和理论层面探讨公众参与同行政、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比如,王锡锌认为公众参与是实践民主的重要形式,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公众对公共行政过程形式多样的参与是“新公共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随着协商民主理论兴起,公众参与和讨论被认为是协商民主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而不仅仅是单纯地追求程序和投票,要通过“公众充权”和一系列制度框架来确保公众能够有效参与[4]。姜明安从行政法治的视角论述了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他认为民主同法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公众参与制民主是代表制民主的重要补充,是在进一步健全、完善代表制民主的前提下,扩大公民对公务的直接参与;公众参与有利于公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对行政决定和政策的理解,有利于保障社会公正,对公权力进行监督,进而加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推动公民社会向前发展,因此,公众参与具有重要的战术意义和战略价值[5]。彭宗超等以中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为例,对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进行了研究,指出当前价格听证的主要问题是目标定位不全面,具体建设制度滞后,导致透明度降低,实施过程缺乏制度和社会舆论的有效制约,并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认为应逐步扩大听证制度的应用范围,一方面将听证由政策规划阶段扩展至执行和评估阶段,另一方面,将听证制度扩大到其他领域的重大政策当中[6]。
还有一些学者则是对具体政策领域中的公众参与进行了研究,王树文等基于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关系的现实基础分析,剖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的演变及特征;根据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不同程度以及政府管制程度的强弱分别构建了公众诱导式参与模型、公众合作式参与模型和公众自主式参与模型[7]。莫文竞等认为参与主体的成熟度,即公众的参与能力和参与心理是有差别的,参与主体成熟度对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效果是有影响的,并就此阐述了通知型参与方式、协商型参与方式、合作型参与方式和授权型参与方式等几种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方式[8]。
(二)公众参与平台研究
近些年,学者对公众参与平台的研究多集中于互联网背景下公众参与平台的构建及产生的效果和影响。网络媒体作为公众参与的新平台已成为一种民主化力量,促进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9]。网络平台的差异使得公众实现政治参与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年龄和职业结构导致政治参与的内容多有不同,而仇官、仇富、同情弱势群体、关注公共事件以及爱国情怀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共同主题[10]。面对城市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新媒体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平台,通过平台管理机制、舆论监督机制、互动反馈机制和奖励机制来实现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制度外创新”[11]。网络平台不断拓宽公众参与的领域和范围,实现了在城市应急管理中的公众参与[12]。然而,目前我国公众参与还处于矫正型参与阶段,公民的参与层次依然比较低,公众诉求——公共部门回应——公众评价——公共部门反馈与矫正的完整互动交流机制还没有形成,网络参与平台下公众参与效果还有待提升[13]。因此,搭建信息收集系统、信息传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信息交互平台、培育公民组织则显得十分必要[14]。
综观以上文献,目前对公众参与和公众参与平台虽然已有一定研究,但是在新兴公众参与平台出现之后有没有对传统公众参与平台产生影响?传统公众参与平台和新兴公众参与平台分别承担的作用是什么?传统公众参与平台与新兴公众参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然而,作为公众参与的两条途径,传统公众参与平台与新兴公众参与平台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
三、案例导入
通过S市A街道在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和微博上女子怒斥医院号贩子这两个不同的案例来分析讨论传统公众参与平台与新兴公众参与平台的特征、意义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而从中剖析两者间的联系和区别。
(一)案例一
S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发展十分迅速,面对经济体制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急剧扩张和城市化日益加快等诸多变化,城市规划管理难度日益加大。城市社会关系开始建立在个人财产权利及由此形成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城市规划涉及城市中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及个人利益关系,因此,要让公众参与到城市规划当中来,才能达到和谐管理的目的。
A街道是S市的老城区,街道范围内分布有大量的旧式私家住宅,多为日式结构,具有极高的历史保护价值。“花园洋房”的安静、闲适也一直让小区居民引以为豪。但是随着城市规划的布局,小区周围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先是32层的高层建筑挡住了一部分旧式住宅的阳光,紧接着,施工队的噪音使得小区居民不能正常生活。随后,一个6幢的高层商业地产项目开工兴建,将这个旧式小区团团围住,变成了“水泥盆地”,一些原有的路口被开发商堵上,消防车、救护车等难以进入,给小区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自此,小区居民开始向区、市政府信访部门投诉,要通行权和采光权。在S市人大主任的一次执法检查中,发现A街道确如信访函件中所反映的那样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不良影响,为此,市人大启动相关程序,提出了整改要求,并对区规划局进行了包括暂停审批权在内的惩罚。
(二)案例二
2016年1月,一则女子怒斥医院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广为传播,视频当中女子痛斥号贩子高价倒卖专家号,无视病人的就医需求,一时间引发广大网民共鸣。视频最先是在微博上传播,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得到数千网民转发评论,随后一些大V和主流微博媒体也纷纷转发评论,在网上掀起关于医院号贩子的轩然大波,公众认为仅仅是号贩子是难以操纵医院的号源,肯定是医院内部与黄牛相互串通,进行利益输送。不久北京市卫计委官方微博便发表声明,宣布将介入调查。原本是屡禁不止的医院黄牛,因为微博上的一个视频便引发公众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并陆续采取措施打击倒卖号源的不法行为,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公众参与和微博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有效平台。
(三)案例分析
两则案例均为公众通过一定的参与平台对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事务施加影响,案例1中公众主要通过传统的信访渠道实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案例2则通过网络引起了全社会对号贩子事件的关注,两种不同的公众参与方式体现了传统公众参与平台与新兴公众参与平台的区别。
1.参与主体
传统公众参与平台的参与主体范围有限,无论是党内民主生活会,还是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类听证会议,其参与主体都是有限定的,甚至还需要对一部分参与主体进行资格审查,符合条件者才能行使参与权力,即使是信访平台的参与主体也是部分利益相关的群众,案例1中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居住在当地的居民。新兴公众参与平台的参与主体则是没有明确的界限和限制的,任何关心关注某一项社会公共事务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参与主体中既包括直接利益相关者,也有与自身毫无关系的公众,他们只要有参与意愿,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和意向参与进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案例2中参与号贩子事件讨论的群体非常广泛,既有当事人,也有经历者,而更多的是对这一不良社会现象的关注者。这与网络参与平台的特征有关,互联网具有即时性、匿名性和广泛性等特征,信息传播速度很快,凭借网络赋予的虚拟身份,公众可以自由参与评论公共事务,网络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距离,对某项事件的关注很快就会形成广泛的影响。
2.参与客体
参与客体,即公众参与关注的对象。通过传统公众参与平台表达的诉求主要有以下类型:①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这主要通过党委、人大和政协等渠道实现;②某项具体政策,比如水电价格等,这主要通过政府听证来得以实现;③区域性的利益诉求,比如拆迁、项目上马等损害了某一区域居民的利益,他们便会通过信访等平台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不满。
网络平台所关注的对象则具有一定的共性,可以归纳为:①国家公职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目前,网上对于国家官员和公共管理人员表现出不信任、讽刺和批评,在涉及公务人员与公众的冲突中,公众网络参与表现出一边倒的现象,尤其是在城市管理执法当中;②对“为富不仁”的反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富人的某些特权使得贫富阶层之间矛盾加剧,因此有关富人的不良行为和现象在网上也往往能引发热烈反响;③关注弱势群体,对社会中处于相对无权、无钱、对社会资源占有较少的群体的关注也是网络公众参与平台经常输出的信息内容,在这些事件的讨论中反映了公众对于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期待;④有关公共安全、环境事件和公共危机事件,从西藏、新疆等地打砸抢烧事件到全国各地PX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再到汶川、玉树地震,都是典型的公众通过网络平台对公共安全、环境事件和公共危机事件的参与;⑤爱国主义情怀,民族情感使得公众对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关注日益提升,2016年台湾大选结果公布之后,网民对于“台独”势力在网上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发生了“帝吧出征Face book”等网民自发事件。
3.参与方式
传统公众参与平台的参与方式主要是以开会的形式进行,程序繁琐,成本较大,而且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使得一些参与人员并不能够把自己真实想法表达出来。一些重要的会议召开频次很低,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公众参与相隔的周期很长,影响了参与的时效性。案例1中小区居民多次上访无果,楼盘建设已经完成之后才得到市领导的支持,利益诉求才最终获得了解决。新兴公众参与平台比较平民化,公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就所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不同的网络参与平台的公众参与方式也是不同的,比如门户网站主要是通过公开各类信息,以告知的形式实现公众参与;社区论坛则是以话题为中心,利用网贴进行讨论,通过用户回帖来表达意见进而产生舆论影响。这种网络参与模式不管发帖的主体是谁,重要的是所发的内容是否符合网民所关注的社会公共事务、是否符合社会需求。微博则是以个体为中心,一般情况下粉丝体量庞大的微博用户所发的内容才能得到公众的关注,特殊情况下典型的社会公共事件也会引发网民的转发评论,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力。无论是视频、话题还是长文论述,均可能在微博上造成热门,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案例2中女子的行为被拍成视频上传至微博,点燃了公众对号贩子事件的关注,成为影响广泛的事件。这类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网友经常将上海地铁中的不良现象拍成视频上传至微博,引发公众对不文明现象的声讨。
四、传统公众参与平台与新兴公众参与平台的关系
传统公众参与平台与新兴公众参与平台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在上一部分已经有所阐述,这一部分主要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
(一)新兴公众参与平台拓宽了传统公众参与平台的渠道
过去,信息传播手段单一,公众与政府所获知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公众很难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只能是一部分政治精英通过传统公众参与平台代表公众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政治精英能否收集到广大公民内心的真实诉求,清晰把握国情民意是很难衡量的。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兴公众参与平台改变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克服了通讯、交通、信息传播不畅等方面的困难。人们可以足不出户,通过计算机终端和网络就可以尽知天下事,并且可以随时将自己的意见建议上传至各类平台,参与政策制度的规划设计,行使自己的参与权。与此同时,传统公众参与平台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了解收集大众所关心的真实信息,以官方正式渠道反映至决策层。网络技术的实时互动与异步传输并举的功能打破了信息垄断,瓦解了统一舆论,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公共组织的界限和特征,使传统的各种意见模式、观念模式、舆论模式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15],拓宽了传统公众参与平台获取信息的渠道。
(二)传统公众参与平台为新兴公众参与平台将诉求转化为政策提供了手段
在我国目前政治参与的体制下,政治代表通过何种方式搜集并集中反映真实的社情民意、用什么样的方式问政是进行政治参与的基础,在当下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为此提供了更多选择。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16],面对如此规模的体量,网络问政似乎成为可能。根据人民网记者在2010年3月“两会”时的调查,97名受访的全国人大代表中,90%的受访代表认为新媒体在他们问政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或者较为重要的地位,7%的受访代表曾向人大会议提交过有关新兴媒体的议案,24.7%的受访代表每天上网,35.1%的受访代表经常上网[17],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开通了电子邮箱、微博和博客等来与公众交流互动。因此,公众通过新兴参与平台表达诉求,人大代表通过网络问政搜集民意,在结合实地调研之后,形成提案并上会讨论,将公众的声音传达至政策制定部门,进入议程设置阶段。
(三)新兴公众参与平台与传统公众参与平台在诉求内容上有效互补
前面对两种平台参与客体的区别已有所讨论,一方面,两种平台的诉求内容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两种平台的诉求内容存在着内在的互补关系。传统公众参与平台关注的多是大政方针、具体政策以及区域性利益,这些可以看作为制度内诉求,是制度范围之内的民意表达;而新兴公众参与平台关注的内容体现出个体性、社会性和道德伦理性杂糅的特征,有些是制度工具无法克服的,因此可以看作为制度外诉求。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既需要制度范围内的调整,同时也需要从制度外寻找创新,这样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否则,这个社会终将处于亚健康状态,并最终走向撕裂。两种平台的公众诉求在从不同层面对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弥补,从而形成有效的互补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公众参与”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新兴公众参与平台的作用会日益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公众参与平台将变成一个旧时代产物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由于技术限制使得网络民意难以代替真正民意,法律监管滞后在网络上容易形成无政府主义以及公民素质不高和缺乏道德形成的非真实民意等问题的存在,传统公众参与平台在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方面的作用不容替代,将同新兴公众参与平台一道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1]王锡锌.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一个理念和制度分析的框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1.
[2]张小罗.网络媒体:公众参与的新平台[J].太平洋学报,2009(7):76.
[3]萨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M].汪晓寿,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5-6.
[4]王锡锌.公众参与: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想象及制度实践[J].政治与法律,2008(6):8-15.
[5]姜明安.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J].中国法学,2004 (2):25-36.
[6]彭宗超,薛澜.政策制定中的公共参与——以中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为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5):30-37.
[7]王树文,文学娜,秦龙.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模型构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4):142-148.
[8]莫文竞,夏南凯.基于参与主体成熟度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方式选择[J].城市规划学刊,2012(4):79-85.
[9]张小罗.网络媒体:公众参与的新平台[J].太平洋学报,2009(7):76-81.
[10]周薇.网络平台影响下的公众网络政治参与演进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6):96-98.
[11]丁盛熔,唐礼勇.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有效途径及机制创新[J].理论导刊,2015(10):26-30.
[12]席广亮,甄峰,李晓雨,等.城市应急管理中的“微参与”:微时代城市管理的思考[J].规划师,2013(2):37-43.
[13]张廷君.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公众参与行为及效果[J].公共管理学报,2015(2):21-31.
[14]朱捷.北京市东城区公众参与机制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2010(1):125-131.
[15]刘京,陈旭玲.网络技术与公共领域的衍生问题[J].江汉论坛,2003(11):46-48.
[1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报告[EB/OL].(2016-01-22)[2016-3-5].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601/P020160122 469130059846.
[17]任珊珊.人大代表眼中的新兴媒体[EB/OL].(2010-03-02)[2016-03-05].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11052363.html.
[责任编辑:胡亭亭]
Public Participation Platform: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Participation Platform and the New Participating Platform
CHANG Ling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Party School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Shanghai 200233,China)
The ways and mean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traditional public participation platform and the new public participation platform,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the role and status of the emerg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platfor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and this will br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public participation platform.They are also linked,form an effective complementary,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public participation;traditional public participation platform;emerg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platform;relationship
D63-39
A
1674-8638(2016)04-0068-06
10.13454/j.issn.1674-8638.2016.04.012
2016-03-22
常凌(1992-),男,山西晋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众参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突发事件应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