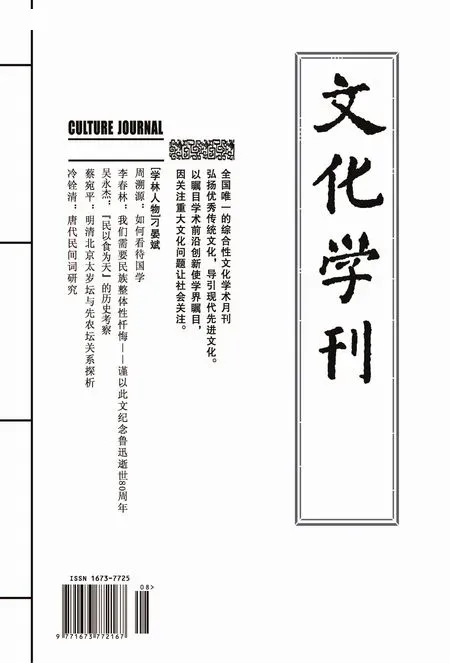《黄泥地》里的悲歌
2016-03-17盖伟
盖伟
(平顶山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文化艺术视野】
《黄泥地》里的悲歌
盖伟
(平顶山学院,河南平顶山467000)
刘庆邦的长篇新作《黄泥地》通过描绘底层知识分子房国春的悲剧人生,深刻地展现了当代乡村政治的复杂性与国民文化的劣根性,从文化性和人性的角度让我们感受到了国民劣根性中的泥泞感和纠缠性,也正是这种泥泞感和纠缠性演绎了黄泥地里的一曲曲悲歌,引发了我们对当代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及当今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现实语境并安置自身的思索。
刘庆邦;《黄泥地》;泥性;乡绅;悲歌
刘庆邦是一位用作品说话的诚实的劳动者,三十多年来他始终深切关注着中国的底层社会,挖掘着底层人物的灵魂与声音,为读者留下了沉甸甸的思索。诚如作家所说:“我不喜欢轻飘飘的东西。我们的历史是沉重的,现实是沉重的,作家的心也是沉重的。一个诚实的劳动者不知不觉就写出了沉重的东西,这没办法。”[1]“越写越痛”是作家的一种创作体验,他的长篇现实题材小说《黄泥地》便是一部让我们“越读越痛”的沉思之作。
一、“泥性”的悲歌
房户营村村民不满于房光民接替父亲担任新支书,却又都不想得罪具有一定势力的支书一家,于是就推举出村里德高望重的中学教师房国春出面反对,当村民们的愿望满足以后,房国春一家却遭到了房守本家族疯狂的打击报复,直至妻死子亡,而面对这一系列的遭遇,村民们却一改往日对房国春的尊重态度,而表现为漠不关心、冷嘲热讽,用人性中的恶唱响了一曲黄泥地上的悲歌。
国民文化的“泥性”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提到国民劣根性,首先想到的是文学先驱鲁迅先生,作为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圣手,鲁迅先生为我们塑造了“看客”这一形象,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国民的愚昧与人性的冷漠。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看客”是不觉悟的民众,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那么在《黄泥地》中,刘庆邦为我们展现的“看客”则是“有主名有意识的杀人团”,他们不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与导演者,在满足精神观看的同时,更看重争斗过后的利益,因为“他们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借助房国春的力量,把立足未稳的房光民拿下来。他们的手段也很明确,不用给房国春送礼,也不用请房国春喝酒,只动动嘴皮子,哄抬房国春就行了”[2],正所谓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因此,基于“谁为祥林嫂之死负责”这一疑问,笔者更想问“谁为房国春之死负责”。
刘庆邦在文本的开篇就向我们说明了答案:“这里的泥巴起来得可真快,看着地还是原来的地,路还是原来的路,可房国春的双脚一踏进去,觉得往下一陷,就陷落下去。稀泥自下而上漫上来,并包上来,先漫过鞋底,再漫过脚面,继而把他的整个脚都包住了”。这不仅是对房国春境遇的描写,更是作者对国民性中“泥性”的一种隐喻和思考。刘庆邦曾指出:“我给小说命名‘黄泥地’,有一种借喻:我们国民文化有一种‘泥性’,有一种‘构陷性’,人一旦陷进去很难自拔”。[3]这种“泥性”的力量使得房国春无法自拔,最终走上了家破人亡的悲剧道路。
二、乡绅的悲歌
中国文化在乡村,很大程度上由乡绅承载,房国春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乡绅文化的承载者。“曾几何时,房国春家作为房户营村的文化中心、话语中心,甚至是政治中心,是何等的吸引人,房国春是何等的受人推崇。”[4]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金钱和权力却慢慢替代了乡绅的地位和作用,成为现代乡村的主导。骨子里的自命不凡和缺乏对自身困境的反思造就了房国春的悲剧人生。
(一)封建士大夫的悲歌
作为当代乡土小说中少见的知识分子形象,房国春具有一种浓厚的封建士大夫情怀。他可以凭借自己几十年教书的威望和人脉关系,为村里修路,为因矿难死亡的乡亲争取最大额度的抚恤金,他宁可自己的饿着也会给去县城找他的乡亲一顿好吃的,即使自己穷到需转借同事的钱,他也也会帮助乡亲……从这些事情上看,房国春是一个舍己为人的人,是一个宁可自己吃亏也要维护自己在乡亲们心中良好形象的人。也正是这种心理,让他感觉在这个乡村处处高人一等,有一种优越感,他自认为就像古代兼济天下的士大夫一样可以为民立命、为民“代言”,这也是他一步步落入自己和村人集体为他挖的陷阱中的主要原因,但他仅仅是一名中学教师,并不是权力阶层的代表,在利益、权势之下,他所倚重的人情纽带在金钱的冲击下已断裂,他的学生杨才俊在收了房守本三百块钱的贿赂之后也不再理他,但他仍旧不能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由为民立命孤身挑战村支书一家演变为为个人诉求而上访,并且在上访的征途中又被其他上访户所鼓动。就这样,这个像古代斗士一般的知识分子就像他脚下的黄胶泥一般,陷入一张自己和众人集体编织的无形网中难以自拔,以致家破人亡。
(二)独裁者的悲剧
房国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高傲倔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面对妻子和孩子,他永远是高高在上的,他是家中的独裁者,妻子永远是作为他的附属品而存在,为他生儿育女、端茶倒水,而无个体所言,还要忍受因丈夫告状所带来的辱骂、羞打、断指。面对儿子,他采用的则是巴掌式的教育,因儿子房守良学习成绩太好,房国春经常抽儿子耳光,已伤及儿子的耳膜,致使儿子出现了耳聋的症状,这也为儿子日后的丧命留下了隐患。他的孙女小瑞也因为爷爷的告状,连在自己村里上学的权力也被剥夺,被迫每天跑十几里路到邻村学校上学……但这一系列的家庭悲剧并未引起这个独裁者的反思。
纵观房国春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位斗士式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与失语状态;看到了他固执背后对自身困境缺乏反思的执拗与孤傲;看到了现代意义上的现代性乡土社会传统知识分子阶层的衰落。房国春的悲剧人生是一曲乡绅的悲歌,同时这个悲剧的乡绅也导演了一曲女性的悲歌。
三、女性的悲歌
对底层乡村女性的执著书写是刘庆邦创作的一大特色,在他所建造的女性王国里,有魏月明式的坚强勇敢的母亲;有高妮、姑姑等执著追求的女性;有守明、喜如式的无奈的待嫁少女;也有宋家银、玉字式的掌握主动权或被迫引诱的失贞女性。《黄泥地》也不例外,对皇甫金兰、织女形象的塑造又一次丰富了他的女性王国,同时又一次奏响了一曲女性悲歌。
对于皇甫金兰,文中虽着墨不多,但却能感受到作者的匠心独运。皇甫金兰是一个完美的无可挑剔的中国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淳朴善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妻性美和母性美。她扮演好了人生中的每一个角色:女儿、妻子、母亲、嫂嫂、奶奶……但她的心中唯独没有自己。就是这样一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女性,一生却未得到丈夫的爱和自身独立性的认可。“丈夫用着她了,就在床上用一下。用完了,丈夫好像吃了亏似的,就不愿再理她,连话都不愿意和她多说一句。”[5]而她看到丈夫遭人辱骂、挨人羞打、被人掰断手指,只有在绝望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织女,虽不像皇甫金兰那样让读者同情和认可,也并非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形象,甚至是一个不守妇道、不贞洁的女性,但她并不同于刘庆邦笔下其他的失贞女性(在之前的论述中,笔者曾把刘庆邦笔下的失贞女性总结为掌握主动权的乡村失贞女性、被迫引诱的矿区失贞女性和忍辱反叛的失贞女性三类),因为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正义和勇敢的人性光辉,让我们不禁想要为这个勇敢的女性点赞,但她的一生仍旧是一曲悲歌,一曲为男权统治所利用的悲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可怜可悲甚至是不光彩的女性,却是一位敢于坚守信念的勇敢女性。在房国春遭遇宋建英的辱骂转而希望儿子房守良为自己助阵遭到拒绝时,房国春对自己的儿子大打出手,房户村的男女老少都在坐山观虎斗而没有一人制止。只有织女敢于上前与皇甫金兰把房国春从儿子身上拖开,并且很生气地说:“三叔,你这是干什么?打自己的孩子不算本事。”看似简单的动作和朴素的话语在一群有预谋、有意识的看客中尤显其珍贵。当皇甫金兰去世后,也只有她和房光东的母亲敢于去送葬,这些都足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不幸的乡村女性的善良和正义,而她的死也是带着遗憾而去的,临死前她希望房守现去看看她的愿望没有实现,她要求死后把她穿纺织服的照片放在棺材里,但是家人并没有放。
皇甫金兰、织女虽不是同等意义上的好女人的代表,但她们都同样处在一个男权文化的乡村秩序中,用她们的善良和执著为我们奏响了一曲乡村女性悲歌。
[1]刘庆邦.作家应该拿作品说话[N].中华读书报,2007-08-22.
[2][4][5]刘庆邦.黄泥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25.29.35.
[3]刘庆邦.从“黄泥地”中思考国民性[N].北京晚报,2015-02-02.
【责任编辑:王 崇】
I207.42
A
1673-7725(2016)08-0075-03
2016-06-05
盖伟(1982-),女,山东东营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