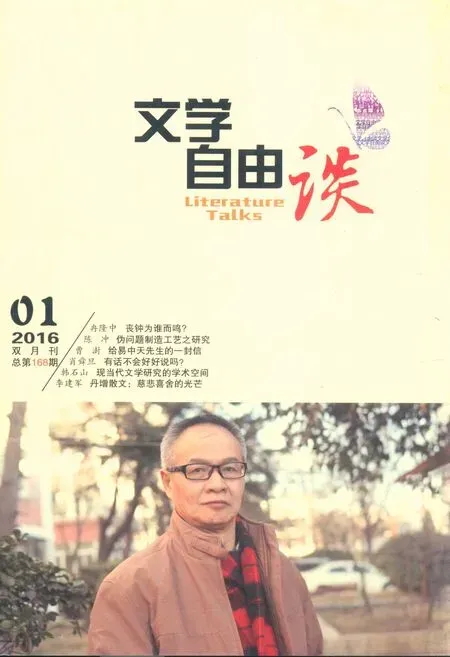我们眼里的“后现代”是什么
2016-03-16邵振国
邵振国
我们眼里的“后现代”是什么
邵振国
据说,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艺术潮流,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性,而又批判、摧毁或说“重建”着现代性。
但是如果我们要问一问“后现代”的概念体系亦即它的定义是什么,似乎谁也说不清楚。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在此课题中研究了四十余年,而今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最终会成为过去:“所有一切都不能阻止后现代主义从建筑、艺术、人文学科、社会中消失……它曾经不仅存在于学术领域,而且存在于商业、政治、媒体和娱乐工业的公共场所中;存在于私人生活的话语中。然而,至今对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并未获得一个共识。”
这段引文,笔者引自学者毛娟的《后现代性:独立的批判精神》一文。我们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到,这一“潮流”也曾在我们的各个领域的公共场所及私人生活话语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延续至今。但是它并不孕育于我们的现代性,因为我们的现实中之一切领域尚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性”性质,也就无从产生“现代之后”的东西,它仅仅产生于我们对于西方思想、文化、艺术潮流的理论“舶来”和艺术“模仿”。那么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它舶来之后针对我们的什么?它将批判、摧毁的是哪些东西?倘若是针对我们尚不具备而正在努力建构中的“现代性”,亦即针对我们“现代之前”的某些东西,这种“针对”是否有效且另当别论,起码是它自身的质性已不再是什么“后现代”了。它的种种质性表现方式,更谈不上“重建”什么现代性。
另一点非常重要,即它哪怕针对的是我们尚未到来的或即将建构的某种价值,而已经拥有提前量地做好批判、摧毁它的武器准备,亦未尝不好;而关键是这一“某种价值”该不该被批判、摧毁,特别是对于我们,对于我们中国国民?譬如,我们的主体性意识——窃以为现代性的首要之义就是对于人的自由本质的知性,它对于我们的国民尚在觉醒和建构之中;再譬如,我们的理性之中,究竟有多少人的价值关怀、人文关怀、终极关怀,有多少对于崇高、尊严、正义的担负,有多少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而产生“过剩”,需要某种解构和摧毁?——这些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在其萌生之初,是不是就需要后现代以其精神的无序状态、价值的虚无主义和“多元意识”、艺术的黑色幽默和自我游戏,来加以解构和摧毁,或说“重建”?尽管后现代是与现代性相对立而生的,它生来就以批判和解构现代性为己任,但我们还是要问,这些价值作为人该不该拥有,该不该被批判、摧毁?还要问摧毁后将“重建”什么?
事实上,仅凭“破坏”和“自我否定”的批判精神,而无一个明晰的“破坏”理由、“否定”理由,更无一个“重建”目标的行为或说理论范式,对于我们是不可思议的,对于我们任何一种现实之变更,亦是于事无补的。比方说,它以其精神的无序状态,试图摧毁人的理性,而不问这理性中的具体内容,亦不问“非理性”所要达到的目的;再比方说,它以其“虚无”否定人类既往的价值结构,而不管人之为人的本质,不管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及其前途与命运,更不关心人性和人生的终极问题,怎样才是于人和人性为幸运的、合目的性的。诸如此类。那么我们在此行为中怎能企盼得到一种更为合理的、美好的“现代性”呢?
前述毛娟的文章说:“后现代性具有独立的批判精神,它呈现出世界充满着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它质疑着宏大叙事或终极阐释。这个世界没有预设的蓝图,而是由许多彼此不相连的阐释系统构成。”
噢,我们不认为这就是人不需要“蓝图”的理由。恰如后现代不可能解构、摧毁人类既往的业已形成的文明一样,人和人的理性也不可能返回到无序、虚无,乃至空白;相反,人类既成的所有的文明、人类所走过的一切发展阶段,都只是为着一个目的——宏大叙事、终极的阐释,即人的“蓝图”!
这张“蓝图”的逐步绘制,与人的背景上的一切相联系着,不可能分离开来。包括物质世界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人的躯体感觉的、美学的和伦理的痛苦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哲学的、社会制度的,它们无一能够独立地得出什么“彼此不相连的阐释系统”。因为它们都在那张“蓝图”上作为绳墨和颜色,标示着人所获得的自由的尺度。除此,笔者看不到别的“阐释”了。黑格尔认为,一个纯粹的个别事物是不可能认识的,要认识必须是它联系着它的“全体”。恰如黑格尔给予人的定义:人即是“人的历史”。因此我们不可能是某一独立发展阶段上的人,同样也不可能有什么脱离了人的价值体系和自由尺度,而独立“阐释”的后现代。
我们知道,任何个别都含着一般。同样,任何偶然性之中也有着必然性。否则纯粹的偶然性,对于我们绝不可能产生意义。人,在其精神的寻觅中,或说在其“现代性”的建构之中,要那种纯粹的偶然性何用?诚然,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或叫做“多元的意识”,但这种存在绝不是以其个别来诋毁一般的理由。任何以个别诋毁一般的企图,在逻辑上、哲学上都是荒谬的,不可能实现的。更重要的是,人类对人之为人的探寻,不可能建立在那种“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上,人类势必要探寻自身经历的历史之各个阶段所积淀获取一定共识的必然性,即所谓普世价值,以绘制那张“蓝图”及作为自身的精神指向。
我们认为,后现代虽然具有批判、摧毁的精神,即具有“破坏意志”所激发的力量——即学者哈桑所谓的“后现代的冲动”,但它不具备我们上述所说的种种对于人的诉求和建设性。因为它的“冲动”没有明确的目的,也不想搞清楚其所“破坏”的该不该破坏,破坏后将以何代之,这全然是“不确定性”的。正如毛娟所说:“‘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它以‘不可界定性’来界定自我。”
那么到底什么是后现代?哈桑认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幽灵,“有一种无法压制的回归”。也许随着世界的改变、社会的进步,后现代主义已经改变了,“回归”到真正的“重建”现代性上来?即抛弃它非理性的“冲动”而审视自身行为的价值,也抛弃它的虚无和戏仿,抛弃它的“不确定性的本质特征”,而对人和人性之前途和命运,有了形而上层面的审视和担负,这一切才是可能的。这样,也就是说,它与我们尚未赢得的现代性将是无差异的。同时亦可谓之,后现代也有了一张关于人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