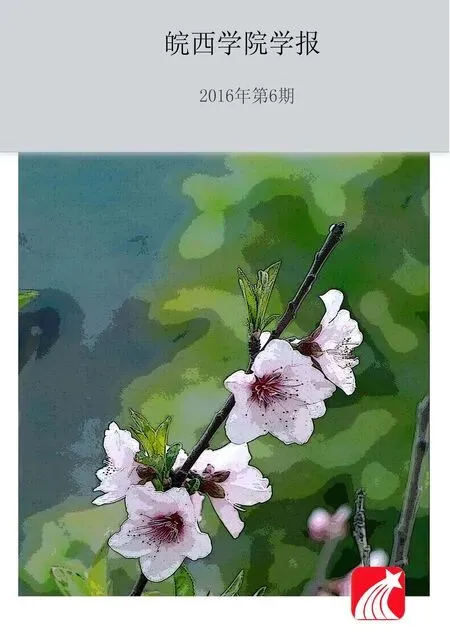皖西高校传承长征精神之“困”与“破”
2016-03-16张小姣
傅 敏,张小姣
(1.皖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2.皖西学院 法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皖西高校传承长征精神之“困”与“破”
傅 敏1,张小姣2
(1.皖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2.皖西学院 法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皖西高校面向大学生传承长征精神的教育正面临难以深入的困境,其症因在于:“传”的内容未能融入丰富具体的皖西地方历史素材,“传”的形式过于单调,而教师作为“传”的主体对于长征主体内容的把握和长征精神的亦存在理解不到位现象。唯有做到对学生的兴趣点、学生群体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以及学生喜爱的活动形式深入研究和把握,方能实现长征精神在皖西高校的有效传承。
皖西;长征精神;传承;大学生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长驱14省,实现战略大转移,胜利会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奇迹,被誉为“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1](P5)。在80年后的今天再度省思长征精神有否必要?习近平总书记近日的讲话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可见,今日对长征中革命先烈英勇事迹的纪念与缅怀,更多的意义实应落在“传承”二字上。所谓传承,是为传接继承之义,是对于一个民族、集体共同创造的精神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承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皖西地区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主力部队的发源地之一,皖西地方高校值此社会各界隆重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时,反思对长征精神的传承问题,必要且重要。然则,当下皖西地方高校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如何“传”,又如何“承”?在如何有效地“传”这一更具共性目标导向和路径的问题上面临何种困境,又当如何破解,时下颇具研讨意义,也期待就教于方家。
一、长征精神“传”之缺失
皖西本为红色故土,从这里走出的数万优秀儿女为红军的长征转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片土地养育的“娃娃兵”、女战士,在长征中谱写了数不胜数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事迹及其中凝练的精神义涵,本应为大学课堂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尤其对于皖西本地高校而言,更是如此。可惜事实远不能令人如意。
在围绕高校课堂宣讲长征精神的交流中,同仁们抱怨最多的内容是:现今是和平建设年代,跟学生讲革命、战争,根本没人听。现在的学生大多崇尚个人主义、个体价值,宣讲颂扬集体主义,为党、国牺牲的英雄事迹,学生觉得遥远,对于完全政治性的话语十分抵触,因此很难谈得上对学生产生心理的触动和精神的影响,不如不谈,说些长征路的花边事件、趣事乐闻,或许还能激发学生兴趣,长征部分的内容才能讲下去,学生才能听进去。事实上,这并非皖西高校革命传统教育的个例,2015年一项针对全国高校近千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当今的革命传统教育流于形式而实效性低,脱离学生日常生活而时效性弱,话语体系陈旧俗套亲和力差等问题[3]。深入反思,不难发现造成这一结果的症因首要在“传”的方面较为薄弱。
首先是“传”的内容问题。一是内容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存在照搬教材内容照本宣科的现象。目前高校通识必修课程在向大学生“传”递长征精神时,不能事先研究和把握学生所想所惑的问题,而教本内容是面向全国高校学生的,编撰时难免因线索化而相对骨感,仅仅依靠宣讲这些骨感的线索以期达到长征精神传承之目的,无疑是天方夜谭。事实上真正能够打动学生的恰恰是有着丰富具体内容的皖西地方性的历史素材,即贴近而生动,具体而有魅力的历史事实。可惜目前融入得太少。二是内容传达的话语系统不能体现时代性。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精神遗产的成功传承都不能脱离时代性,长征精神的纪念与传承自不例外。由于宣讲长征精神时未能因时制宜地剖析其时代内涵,呼应长征精神传承的时代性要求,高校学生在对这套话语系统的接收过程中,难免产生过时感,自然更无听下去的兴趣。
其次在于“传”的形式问题。长征精神的“传承”是双向互动过程,过度倚重对学生的单向宣讲教育,难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甚至可能会被学生视为说教而产生心理上的抵触,果若如此,这种传承方式将会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精力的低效耗费。因此,在肯定教师引导和讲授为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的基础上,必须尽可能避免单一的讲授形式,否则势必消解传承长征精神的正向效果。值得警惕的是,教师主体在思想意识层面部分存在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布置任务的被动想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积极参与构建立体评价机制的主动性,而若是在评价机制上不能纳入学生评价监督和回应的部分,那么纪念和传承长征精神的教育活动便难以真正触动大学生的灵魂深处。
最后是“传”的主体问题。高校“传”的主体是教师,目前影响长征精神传承教育效果的突出问题表现为:一是教师主体对于长征主体内容的把握和长征精神的理解存在不到位现象。“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师若不能对于红军长征的相关重要问题做到深入了解,对于长征内容的讲解便会出现科学性和系统性缺失的问题,诸如不能基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成长史的大背景厘清工农红军长征的原因,长征胜利之于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乃至中国共产党将士,尤其是皖西地区的参军儿女为实现长征胜利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时至今日仍不能忽视的精神价值追求等重要问题。二是存在片面迎合学生的猎奇需求,进而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现象。在进行长征精神教育的过程中,若是片面追求课堂的气氛与效果,便会冲淡教学主线内容,并易滋生不讲“正史”讲“野史”的乱象。学生群体中确实存在要求讲“花边”故事的吁求,若不能正确引导,便会助推其非理性要求,极大地消解党史、国情精神教育的效果,使得长征精神等一些本该为全民族,尤其是青年一代传承下去的优秀民族精神,逐渐为年轻人误解、疏远与淡忘。
二、长征精神“传”之困境的破解
关于长征精神的纪念与传承,无论是纪念日的仪式纪念抑或理论课堂的讲授纪念,皆为互通互补的重要的精神教育环节。纪念与传承长征精神的效果,首要在于对受众思想和心理状态的了解,在高校传承长征精神自然不能缺失对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状态的了解,这种了解必须实现几个方面的深度研究。
一是对学生兴趣点的深度研究。关注学生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发表的言论,梳理分析学生内心的情感诉求与思想动向,是对学生进行精神教育包括长征精神教育的首要环节。教育者可以利用各种渠道和碎片化时间,如QQ群的交流、课前课间休息的片断,关注学生情感日志等,倾听学生内心的声音,体察学生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追求。之所以强调倾听,是因为教育者主导谈话必定扼制学生表达自己观点的积极性,对学生兴趣点的了解便无从谈起,教师少说多听是此一环节的关键。细细揣摩,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学生的兴趣点,如皖西本科高校学生的兴趣点女生更多关注两性情感、美容美食、韩剧明星话题,而相较于女生,男生则更多侧重于网游、运动、人生事业起步等话题。这些兴趣点看似与长征精神的传承相距甚远,但它恰恰是传承长征精神的工作进程中需要琢磨契合点的第一站,如何寻找话题的切入和突破点,是直接决定传承长征精神成效的关键。
二是对学生群体话语深入研究。所谓“话语”有多层意义,口头话语或书面话语,均可归之为实体话语。而若对话语抽象分类,便产生“革命话语”“政治话语”“女性话语”“殖民话语”等类型话语,以及“学生话语”“农民话语”“公知话语”等群体性话语。面向任何一个具体群体的信息传播,都不能忽视目标群体的话语系统。虽然话语分析是国际社会科学中一门快速发展的前沿学科[4],而在中国针对青年学生群体话语的系统分析更是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在精神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中,这一问题理应首先提出关注并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逐步探索研究,更亟待另辟专文系统梳理。扼要而言,当今大学生主体为出生于1995年后的群体,在话语内容表达上倾向重视个体价值、个人感受,更感兴趣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等内容,革命史、政治史较难引起这一群体的兴趣,语式上则表现为短促式、萌点式等特点。从句式特点看,“95后”的大学生群体对于长句式、革命话语、官方政治话语较难产生共鸣,反而是标新立异式,卖萌耍宝式的陈述获得追捧。因此,对于承继者这一“95后”大学生群体的长征精神教育,必须在内容的形式包装、句式的表述,乃至短标题的运用上,下足工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征精神教育的话语系统应当突破传统革命话语的苑囿,更注重契合当今时代的精神,也即传承长征精神理应具有时代性。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时代性的话语如创新、创业、就业、生活困境等,应当成为长征精神教育的重要关注点,一旦将长征精神教育的话语系统提炼融入时代性的话题和问题,那么长征精神的传承便有了实实在在的灵魂。当今学生的创业、创新、求职、就业,无一不需要突破重重困难、勇往直前的大无畏长征精神,唯有将长征精神传承教育与学生关注的现实问题联结起来,寻找契合点,才能使得长征精神教育话语具有时代性。其成效恰如雷蒙德·鲍尔在《顽固的接受者》中所言:“在可以获得的大量(传播)内容中,受传者中的每个成员特别注重选择那些再他的兴趣有关,同他的立场一致,同他的信仰吻合,并支持他的价值观念的信息。”[5](P142)
三是对学生自发性活动的常用形式深入研究。虽然对学生自发活动的形式运用,并不能够完全取代教育者对精神教育活动形式创新的不懈追求,但是借鉴学生自发组织的主动参与意愿高的活动形式,对于长征精神的传承教育无疑是有益而重要的。只要平时关注学生自发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便不难发现能为学生广泛接受的活动形式。从目前学生自发性活动开展的情况看,颇受学生好评的活动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体验感强、学生个体的参与度高、学生个体的创造力和想法能得到充分表现与表达、学生某方面能力能得到锻炼提升等。长征精神传承教育活动虽然难以实现这些受学生好评活动的全部特点,但是有意识地在教育活动中创造这样的环境,尽可能满足学生的上述心理需求,却是必须努力且可以努力的。
当然,长征精神的传承教育虽强调对学生群体的了解,却并不意味着教育传播者丧失对整个长征精神教育方向的主导性,盲从学生的非理性要求,而理应是用更能为学生接受的语体、内容、形式达到长征精神更深入的传播,对长征精神更精准的理解与把握。同时,长征精神的传承纪念也不能片面强调形式,而忽视对长征史实和精神内涵的不断挖掘这一核心。
三、皖西地方长征史实的挖掘宣讲与精神凝练
皖西红色历史资源十分丰富,仅在金寨这片红色故土就曾走出过59位开国将军,10万金寨儿女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国捐躯,是为11支整建制红军部队的诞生地和重组地,在红军长征史上曾留下鲜明的印记。其中,从这里走出的红25军是长征中人数最少的一支队伍,却在此后的革命洪流中培育了共和国近百位将军。学界关于红25军的研究却相对薄弱与不足。因此,结合“95后”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时代语境,当下皖西地方高校的理论工作者应着力挖掘研究如下史实。
其一,“娃娃兵”的史迹亟待在高校学生群体中传颂。红25军被百姓称之为“娃娃兵”或“童子军”,诞生于金寨县麻埠镇。1934年秋,由于国民党军的残酷围剿,鄂豫皖苏区根据地面临生存困境,被迫实施战略转移。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近3000名指战员,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告别大别山区,开始长征。这支军队的年龄很小,军队最高领导军长程子华仅29岁,军政委吴焕先仅27岁,营团级别的干部大多20岁出头,连排级干部大多不满20岁。在这批队伍中,竟有不少十二、三岁的少年儿童。对于如此年少的孩童为何积极参军,目前党史研究工作者大抵基于《共产国际》中的论述,其中言及:“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些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25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部队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都是从13岁到18岁。”[6](P113-114)此中至少透露出两点少年参军的原因,一是少年参军者的家庭状况较为困苦,“寻找父亲”说明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缺失,而主要劳动力在一个农业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之重要是可想而知的。二是国民党在鄂豫皖边界实施的白色恐怖非常残酷,残酷的斗争现实教育和锻炼了山区的孩童,使得他们在军事政治上“早熟”。虽然此处史料中仅提及“崇山峻岭”,未述及乡风乡情,但皖西大别山区民风相对彪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此地确有一定的群众斗争之基础。惜而目前披露的信息是总体概略性的,关于这些十二、三岁少年的具体身份资料信息甚是有限,尤其是他们如何走上参军之路,参军前后在思想上、生活上发生了哪些具体变化,均需着力发掘与研究。红25军“娃娃兵”这一群体性的事迹传达给后世十分重要的信息,诸如国民党统治时期底层民众生活的困苦程度,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竟然被迫走上革命道路,这批少年又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革命集体的思想熔炉中和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历练,思想上逐步成长、成熟的发展轨迹等。这批“童子军”的事迹,不仅是总结凝练长征精神的重要史实基础,且对于触动高校学生群体的灵魂,十分有益而必要,无疑是吸引高校学生纪念与传承长征精神的重要突破口。
其二,妇女独立师的精神亟须在高校学生群体中传扬。红四军长征前,于1934年11月,在川陕根据地动员各县组织女侦察队,“侦察敌情,破坏敌人后方”,并做后勤、医护保障等工作[7]。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进一步组建妇女独立师,这也是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支完全由妇女组成的部队。这支柔弱的女性群体,不断超越自我,冲破生理与心理上的重重难关,随红四方面军翻雪山过草地,跋涉征战,在西征最后关头,以大无畏牺牲精神引开敌人,掩护了主力部队撤退,最后在与马匪的抗争中,九死一生,幸存者仍不忘寻觅红军部队。如吴富莲1936年7月被任命为妇女先锋团政治委员,12月率领妇女先锋团在甘肃境内顽强抵抗国民党地方军阀马步青等部队,进行了3个多月的殊死血战,突出重围。随后转战到祁连山犁园堡一带,在茫茫戈壁与敌人孤军奋战、浴血厮杀3天3夜,最终弹尽粮绝,先锋团大部牺牲,25岁的吴富莲被俘吞针牺牲[8](P93)。这支妇女独立师的命运较之西路军一般男战士更加苦难,对于倡导尊重女性、同情个体不幸遭遇的青年学生,妇女独立师英勇悲壮的事迹,恰恰是唤醒今天的青年学生对长征阵亡红军将士祭奠的最深刻的史实,也会鼓舞高校学生主动地传承长征精神,传承这种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拼搏和牺牲精神,激励他们感恩现今的生活,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奋斗。
其三,红军长征中对沿途群众的动员必须重点讲解。红军长征途中的艰苦战役、经典战例固然是传统的长征史宣讲中的“重头戏”,但是对于生长于和平年代的青年学生而言,红军在艰苦作战环境下,影响和动员群众的具体史实更易感染他们。诞生于金寨的红25军切实联系群众,成为长征途中唯一增员的部队。红25军从1934年11月河南省罗家县何家冲长征出发时的2980余人[9],发展到1935年9月行至陕西延川完成长征时的3400余人[10],开创了诸多神奇的特例,如红军长征史上唯一在征战途中建立了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红25军如何做到转战至陌生之地迅速建立起群众对军队的信任,并愿意加入军队;又是如何在作战之余,建立起地方武装和建设基层政权;如何以艺术的活动与形式吸引了群众和鼓舞士气;女战士们在动员群众中的活动与作用等等,这些史实的梳理和问题的阐明,对于青年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血脉关系,理解中国人民为何选择支持中国共产党皆有重要的意义,更是纪念与传承长征精神的旨归。
对于长征的纪念和长征精神的传承,必须结合不同时代的特点,不同群体的特点,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和青年学生群体的思想脉动,变被动式的宣讲接受为主动的参与理解与纪念,方可更好地实现对长征精神纪念与传承之鹄的。
[1](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过家鼎,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2]李建华.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长征路[N].人民日报,2016-09-12(7).
[3]檀江林,王帅.自媒体时代大学生革命传统教育现状与对策探析——基于全国62所高校的抽样调查[J].当代教育科学,2016(15):60-64.
[4]施旭.构建话语研究的中国体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1-05(A08).
[5]洪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6]芦振国,姜为民.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7]罗晓平,伊国华.硝烟红花——记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J].环球军事,2005(18):14-15.
[8]中共中央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福建省[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1.
[9]徐占权,徐婧.北上先锋——红25军的长征[J].党史博采(纪实),2016(7):4-8.
[10]红25军长征大事记(1934.10-1935.9)[J].军事历史,2006(10):3.
The Long March spirit inheritance’s Predicament and Crack in Western Anhui Colleges
FU Min1, ZHANG Xiaojiao2
(1.School of Marxism,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an 237012, China;2.LawSchool,WestAnhuiUniversity,Lu’an237012,China)
The Long March spirit inheritance is now facing difficulties in local colleges in Western Anhui. The reason for it is that the rich lo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Western Anhui isn’t 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 that the teaching form is too monotonous and that teachers, as the tutor, don’t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n the main content and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 Only if an intensive study of the three aspects are made, that is students’ interest points, the discourse system students willing to accept and students’ spontaneous activity form, the effective succession of the Long March spirit in Western Anhui Colleges can be true.
Western Anhui;the Long March spirit;inheritance;college students
2016-09-12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3SQRW058ZD);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SK2015A155)。
傅敏(1980-),女,安徽南陵人,副教授,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张小姣(1981-),女,安徽六安人,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G641
A
1009-9735(2016)06-0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