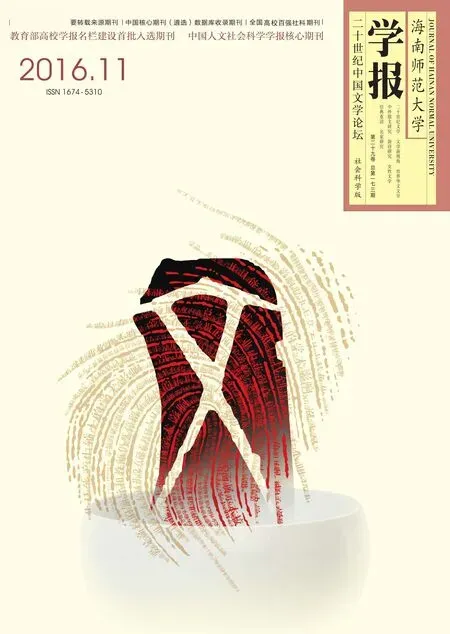海南五指山杞黎的亲属制度研究
2016-03-16王晓慧
王晓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海南五指山杞黎的亲属制度研究
王晓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前辈学者对海南省五指山地区杞黎的亲属制度研究多从进化论的视角进行探讨与分析,并认为杞黎社会中存在母系社会的残余。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以蔡华教授提出的亲属制度研究理论为视角,对杞黎的亲属制度作出总体性概括和系统的描述,从而得出五指山地区的杞黎的亲属制度是一个双边不对称制度。
杞黎;母系社会;亲属制度;双边不对称制度
杞黎作为海南岛黎族五大支系中的一支,主要分布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五指山市三个县市。其中,五指山的杞黎自称“ei51”,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该地区的杞黎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保持着传统的风俗习惯和信仰。2010年至2011年笔者在五指山市冲山镇报龙村进行了为期十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综合考察了杞黎的亲属制度,得出了与以往学者不同的观点。
一、概况
五指山市冲山镇位于五指山市区,区域总面积325平方公里,总人口51,783人,有汉族、黎族、苗族等民族,其中,黎族人口占80%以上。①根据2008年的数据统计,数据来自于五指山市冲山镇(现通什镇)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报龙村委会位于五指山市区西北部,距离五指山市区约10公里,是五指山市冲山镇辖属最偏僻、人口最少的村委会,辖有报龙村、小明形村和格什村三个自然村。由两条道路可从市区到达报龙村委会,均为2008年以后开通,之前为土路,遇到雨季时交通出行极为不便。报龙村委会位于深山密林中,森林覆盖较密集,2009年林改之后,公益林受国家保护,不许开垦及砍伐,主要经济作物除去水稻种植之外,大多数的家庭种植橡胶、芭蕉、生姜、花椒和花生等经济作物。
笔者在田野期间,整个村委会只有五六户人家的橡胶成熟到可以收割,主要集中在小明形村和格什村,大多数人家的橡胶已种植六七年,但生长缓慢。直到近些年,村民们才开始接受使用农药等方法给稻谷、橡胶和其他集中种植的经济作物消除病虫害,但是芭蕉和各种时令蔬菜等仍让其自然生长,坚持“不打农药”,而且村民们把这当成他们优于城里人的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
除去橡胶和稻谷,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还包括养猪、鸡、鸭和牛等。其中,猪、鸡、鸭均为散养,没有圈养习惯。黄牛和水牛等在山上放养,主要用于婚礼、丧葬等大型群众集会时享用,或者卖与他人。稻米一年两季造,米饭为主食,喜爱饮酒,每家每户有小块菜地,供自给自足食用。笔者在田野期间,三个村95%以上的房屋为茅草房,仅有几户平房。茅草房形似船型,房顶为茅草编制,墙壁则由茅草与泥土和在绑定的竹片上晒干而成,有存贮稻谷的谷仓,由茅草与竹片搭建。总之,本地经济收入的来源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辅以家禽饲养等手段,遇到闲暇时,有的也卖自家种植的蔬菜、上山挖野菜、找草药等去市里卖。
二、身体表征系统
身体表征系统亦作身体再现系统,指称每个民族对人身体的认知结果构成的概念体系。*蔡华:《人思之人——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蔡华教授将身体表征系统纳入亲属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这对于亲属制度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杞黎的身体表征系统,旨在表达该民族的身体来源和所属的地方性观念,意在描述杞黎的社会血缘观念,包括对人体器官和体液的认识、男女双方在孩子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性别的成因等。
关于“孩子是怎么来的”或者“人类是怎么来的”,杞黎有如下神话传说:
人类从男人小腿的地方生出来的,男孩子一边,女孩子一边,生出来是龙凤胎。但是不知道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女的话,就放在山猪经常跑的那条路上,用黄金(山猪的一种,据说与鹿差不多大,但是头上没有角)踩在女人的阴部,如果能踩下,就是女人。男的话,看看能不能插在山竹的竹筒状枝杈上,如果能插上,就是男的。
从该神话传说可以发现,在有男女之分前,男人生出了男人和女人,也就是说,原初的新生命是寄托在男人身上的。当他人在询问妇女所生的孩子时,通常会问:“pai55zhao51v55m51hai51m51?”(是不是男的?)杞黎的一句谚语为“wei55lu55pa55, wei55lu55bi35,wei55lu55ao51”(没有爸,没有母,就没有人),即男人和女人必须“一起睡”,才会有孩子。但是,这个新生命是如何寄居在男人身上,又是如何通过男女之间的性行为转移到女人身上的,则不得而知。
那么,在杞黎的观念中,男性与女性分别在新生命的诞生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杞黎认为,男人与女人分泌的体液是一样的,认为“如果生下的孩子像爸爸多,那么就说明爸爸的血液多;反之,如果更像妈妈,则是妈妈的血液多”,这里的“血液”是血缘的涵义。因此,杞黎是按照“体液”在计算,即新生命的性别由其占有父母体液的多寡来决定。
很遗憾的是,笔者再也找不到其他更为详细的杞黎对生命起源的解释。因此想要详细阐述杞黎的血缘观念只能到这一步。但是综合上述可以得出,在新生命的诞生过程中,男性与女性对新生命的产生均发生了作用,同时,虽然女性不可或缺,但是显然男性对生命的诞生所起的作用要比女性更为重要。
三、乱伦禁忌与社会血亲
杞黎社会中,主要有两个词汇用以指称亲属群体或亲属集团。“lin55wan24”专指男方的血亲,杞黎自译为“亲戚”;“tu55”专指外家,是相对于亲戚而言,嫁入的女方的父母兄弟姐妹那一类亲属群体。杞黎传统观念中,同一祖公的后代严格禁止结婚,这是杞黎最基本的禁忌规则,这也是唯一的一条制度性的性禁忌规则。祖公,杞黎语“b’ u33”,海南汉语为祖公的意思。也就是说,杞黎的性禁忌规则为不论男性多少代计算,同一个男性的异性后代之间严格禁止婚配。在调研中,报龙村、小明形村和格什村分别由一个男性祖先的后代们形成,村内男性后代中同辈男女均为血亲,为堂兄弟姐妹的关系,他们之间严格禁止婚配。
按照杞黎的传统说法,不论是堂兄弟姐妹还是表兄弟姐妹,如果不顾禁忌非要在一起结婚,违背禁忌规律的话,要么生育的孩子有问题,与正常婴儿不同,要么夫妻二人会发生问题,有性命之忧或者身体发生病变。总之,会对自己和孩子不利。
那么,延展来看,在杞黎的生活实践中,与乱伦禁忌相关的规则有如下几条:第一,同胞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性禁忌。第二,理论上无限延伸的双系平行旁系亲属和交叉旁系亲属禁忌。即一个男子不能与他父亲兄弟的女儿,以及母亲姐妹的女儿结婚。女性亦然。在这里,理论上的无限延伸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根据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并不是如报道人所说的比较含糊的女方超过十代之后就可以结婚了,而是超过两代就可以婚配。以阿杨(成年未婚男性)为例,他不可以娶舅舅和姨妈的女儿,姑姑的女儿,但是与姑姑的丈夫同属一个祖公的兄弟的女儿可以娶,也可以娶与姨夫同属于一个祖公的兄弟的女儿。
根据蔡华教授提出的社会血亲性排斥定律,即社会血亲性排斥定律决定乱伦禁忌,在乱伦禁忌中起作用的是社会血亲,而不是生物血亲。在一个社会文化中,禁止发生性关系的人,是这个社会的文化认为是血亲的那些人,这里的血亲,不是生物性血亲,而是社会性血亲。对于杞黎来说,就包括上述的血亲群体。因此,在调研中发现了报龙村与格什村这两个村子大量交换妇女的案例,并没有触及杞黎的乱伦禁忌。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即婚前两人的亲属关系和辈分关系,有固定的称谓指称,但是在婚后就发生改变,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在现代社会里,随着人员流动的加强,外来打工者的增多,以及村庄人数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同祖公的概念外延也愈加模糊和扩大,大多数年轻人只是知道这个村子是哥哥,“我们”村子是弟弟,至于村子里的人和自己具体是什么亲属关系,已经不是很清楚了。同时,受汉族观念的影响和现代婚姻法的普及,与亲属关系密切的村子结姻的现象逐渐减少,大多数年青人外出打工,自由恋爱越来越兴盛,大多数青年多以远离本村的适龄对象作为伴侣的首选。
四、性生活模式
杞黎的青少年在成长之后,没有成年礼或者其他纪念青春期的礼仪。约到十二三岁时,离开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房屋,自己或者跟村内其他年龄相仿的同性青少年住在“b55ɡuei55”之中。“b55ɡuei55”,杞黎中专指“没有灶台的、不能烧火做饭的房子”,汉译为“布隆闺”,一般在父母房屋的一边墙外直接盖一间,或者单独一间小屋子,屋内仅放一张床,可供1-2人睡觉使用;有的地方亦见一间大屋子,床铺可供多人同时睡觉使用。独立之后,青少年的生活就相对较自由,在恋爱期间,异性可以自由在布隆闺里过夜。
传统上,一般父母包办的婚姻比较常见,女孩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如两三岁时就已定亲,到了成家的年纪或怀有身孕后,再结婚并且到男方所在的村子去居住。如今,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自由恋爱在杞黎中较盛行,但女孩在婚前到男孩家生活几天,看看男孩家经济水平如何,不满意就放弃的情况也很常见。现代的婚恋模式中依然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习俗与规定。
与纳人*参见Cai hua, A Society Without Father or Husbands: the Na of China,New York: Zone Books, 2001.不同,杞黎的制度性生活模式只有一种,即婚姻。杞黎的婚姻过程主要分为如下四个过程。
(一)碰头——ao51n55
由介绍人介绍,或者通过其他人、其他渠道得知哪户人家有女孩降生,男方父母就会带着酒和菜到女方家去,由男女双方父母四个人“碰头”,中心议题是“你的女儿要嫁给我”,四个人一起喝酒吃饭,商议婚事。
父母敲定之后,择日再一次到女方家里。这次,男方的母亲要带给女孩一块黑布,黑布约莫普通毛巾大小,黑布内不含有任何物品,倘若女孩接受了,表明本人接受婚姻。女孩是否接受以双方对歌为定,但通常都是男方的父母赢得胜利。本次商定好了正式订婚的具体时间,不需要支付任何彩礼。
(二)订婚——cao51n55
订婚之日,选取良辰,男方父母带男孩一同过来,男女双方第一次正式见面。男方母亲要再给女孩一块黑布,黑布里面要包着钱,是彩礼费用。一般情况下,女孩应接受,因为如果女孩不喜欢的话,会在订婚之前与父母商量,在“碰头”的时候就已经拒绝,从而阻止订婚的发生。但也有在订婚当日拒绝的情况,比较少见。钱的数目,一般为几块光元,或者最多十元。陪同男方一起来女方村子的还有男方村里的几个人,为男方父亲的兄弟及配偶,一般为四人者六人,均已生育并有后代。有一种说法,认为来的人越多越好,因为人越多,女孩子就会很快同意。
定好日子之后,男方开始准备牛只和猪,为婚礼当天宴请宾客之用。一般为四头牛和四头猪,也为双数。如果没有猪和牛的话,要么去买,要么去借,一些家庭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娶妻在杞黎人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任何一户普通人家都是倾其所有,即使花掉所有财产也在所不惜。因此,订好日子、准备好猪和牛之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要迎娶新娘。
订婚后何时正式结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女孩儿如果年纪尚小,只有两三岁那么大,就要在女孩长大之后再择日正式结婚。第二种,男孩女孩年龄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那么双方父母就直接商讨具体的结婚时间,一般半年或一年内就正式结婚。
结婚一般分四个步骤:第一步,迎亲。男方派人到女方村子迎接新娘。迎亲队伍由一个成年男性带领,此人被称为“pa55kai51”,杞黎语为“大公鸡头”之意,一般由村里最会讲话、最会唱歌的男性担任,已婚或者未婚均可,但优先考虑未婚男性。此人需要性格开朗,活泼好动,能够带动气氛,会说笑话,会说也敢说表达爱情的语言。陪同他一起来的一般为四人或者六人,均为成年已婚已育女性,每人在腰间缠一个“f’51”,里面装有自家种的稻米。*串门或看望亲戚朋友时,杞黎妇女经常自带一f’ 51米,这已成为杞黎之间人情交往的普遍方式。杞黎男性则不必带。
男方迎亲队伍离开的时,新娘的父亲会将牛的一条左腿和猪的一半切下作为礼物让他们带回。一般新娘会有两名伴娘,一个是未婚年轻女孩,一般为新郎的妹妹,*新郎的亲妹妹、同村的堂妹也可以,或者是与新娘同村的好姐妹。另一个是新娘血亲中最近的人,可以是其堂姐或婶母,一般要比新娘年长。迎亲队伍是从男方村过来的,那么相应的,女方村会有送亲队伍。杞黎送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送新娘的人均为女性,包括新娘的母亲、婶母和伯母,新娘的奶奶等。男性严令禁止跟随,新娘的父亲和亲兄弟也不例外。
第二步进村。杞黎新娘离村时身穿黑色服装,临近新郎村口附近时,需要更换传统民族服饰。新娘在进村之前,需要“bi35ja214”*bi35 ja214,有学者翻译为“娘母”,认为娘母是杞黎传统法师的黎语称呼,但根据笔者调查,专门做传统驱鬼仪式的杞黎法师为“tn55”,“bbi35 ja214”和“tn55”是两种不同的称呼,前者类似汉族的“长老”,后者则属于专门的宗教方面的法师。二者性质职能均不同,但经常为一个人,一般由男性担任,所以才会发生混淆。做一个被称为“t’ai51n51v55dai55”*汉译为“驱除恶鬼”的意思,是举行婚礼时的特定仪式。的仪式。这个仪式必须由新郎或新娘村内的“bi35ja214”来做,一般为新娘或者新郎的阿公或外公,因为“怕外人搞鬼,搞破坏”,必须是“最亲近的人做才行”。“t’ai51n51v55dai55”仪式的目的是对新人的祝福,希望新娘进门之后能够平平安安,幸福生活。
仪式结束之后,到了婚姻过程的第三步,正式宴席。杞黎婚姻宴席有一定的规则。例如,宴席之前的准备工作主要由男方村里的青年男性负责,端菜、上菜的也都是他们,已婚未婚的均可,人手不够的时候,还可以叫上邻村的或关系好的青年男子来帮忙。如果新郎有哥哥但未婚,弟弟需要将一条白毛巾蒙在哥哥的脸上,寓意为哥哥是大辈,弟弟是小辈,给哥哥洗过脸后,弟弟就可以落座。每个人的座位要遵循一定的次序,男女双方分坐桌子两边。等新郎的母亲把剩余的聘金给新娘的母亲之后,新娘要到新郎旁边坐下,这才意味着嫁给了新郎,进了新郎的家门,成为新郎的一家人。女方送亲队伍在享用食物之前,新郎的母亲还需要给每人一点费用,感谢她们对新娘的陪同。
宴席结束之后,结婚完成,最后一步程序是送亲的人回村。出发之前,她们会用木炭灰将脸摸黑,新郎一方会将牛的一条腿和猪的一半等作为礼物让新娘的母亲带回。
(四)回娘家
一般结婚三天后,新娘在其婶母的陪伴下回娘家。吃完饭之后就返回,当日不能住下。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在两三岁的时候结婚,在办完婚礼后,由女方母亲领回家,等长大后到了结婚年纪之后再回男方家居住。通常在青少年期间,住在布隆闺之中,等有了第一胎*有时候,女孩怀有第一胎孩子的生物性父亲不是她的丈夫,这在杞黎的观念中对此并不特殊规定。之后,便正式回到男方家居住,杞黎的这种结婚模式叫做“不落夫家”。
笔者在调查中没有发现不落夫家的案例,但是据报道人讲述曾经存在有放竂的现象,“以前不论男人女人都去布隆闺,不论结婚还是未婚的都会去”。这说明杞黎在婚前婚后性行为还是较自由的。在一些资料中对放竂的现象也有提及:
解放后夫或妻参加政府工作,对方有干涉的现象,尤其妇女参加工作,男子多表示不满,主要原因是当地仍盛行“放寮”习惯,怕自己爱人在外“放寮”,今后应加强教育,逐步革除“放寮”陋习。*《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调查报告暨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1982年,第58-59页。
放竂的习惯与传统上两三岁结婚但至长大生育有第一胎才正式从夫居的习俗相关联,不落夫家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不落夫家和放竂等现象消失的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宣传教育。这种传统“落后”的习俗退出历史舞台后,杞黎在婚龄上发生了深刻改变,从而整个婚姻制度相应地发生变化。
五、亲属称谓与承继规则
杞黎的亲属称谓是类分式的。*[美]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杞黎把亲属大致分为亲戚和外家,外家指妻方亲属群体,一般仅限于同村亲属;亲戚范围比较广,狭义上指一个村子内所有家族,广义上包括与其关系为兄弟的、生活在其他村子的家族。杞黎的亲属称谓十分有特色,从亲属称谓和称呼中能够看出个体的身份辈分,以及与他相关的核心家庭成员目前的状况,十分精细。杞黎的亲属称谓基本上是根据辈分进行指称,不论年龄大小,长辈对晚辈的称呼,因长幼(指父辈辈分)序列和男女性别差异也不尽完全相同,这杞黎亲属称谓中最为显著的特点。
杞黎的身份发生改变之后,其亲属称谓也相应的发生改变,这是杞黎亲属称谓系统中另一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日常中提及过世之人的名字是忌讳,如果有亲属去世了,则亲属称谓就要相应发生变化,称谓变更后,便于第三人或对话的双方通过亲属二人之间的称呼,能够明晰双方的基本身份。例如,称呼父母双全的男性为lu22+名,称呼父母双全的女性为ɑu51+名;称呼没有父亲的男性为lu22kai55+名,称呼没有父亲的女性为ɑu51kai55+名。
第二,婚后亲属称谓发生变化,尤其是生育孩子之后及相关的他称要发生改变。例如,“li t55pa55”与“li t55kɑu51”分别表示年龄段在出生后至青少年之间的男孩与女孩,等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相应的改为“t’an55mn55ja51”和“bi35mn55ja51”,以区分是否到了成婚的年龄。父母称呼自己的子女也可按此规则。再如,女性无论在婚前婚后(未生育前),女性的部分同辈或长辈血亲对其称呼不曾改变,为ɑu51+名,而刚刚嫁入、未生育的女人,被男方亲属及村子里的人称呼“niou55nɑu51”,译为“新媳妇”,女方亲属称呼刚刚结婚、娶该女性的新郎为“li55tsie5”,译为“女婿”,意思是外家的小孩来娶他的女儿;基本上,在婚前和婚后未生育前,双方亲属称呼一对夫妇均以其名字为主,即lu22+名与ɑu51+名。
第三,如果一个核心家庭中有第三代或第四代出生,在指称上辈分与称谓要分开,采取按照最低辈分统一称谓、指称与辈分相分离的原则。例如阿杨叫笔者阿姐,则阿杨全家成员,包括阿杨的阿爸、阿妈、阿姐、阿哥、阿叔、阿婶、阿公和阿婆等等均指称为笔者为阿姐。同样,阿杨叫阿公为“b’ɑu55”、阿婆为“te55”,则阿杨的父亲指称其父亲也即阿杨的阿公亦为“b’ɑu55”,指称阿杨的阿婆即其父亲的母亲亦为“te55”。即在日常生活中,家中最低辈分的人指称为何,其家中所有成员也指称为何。
第四,小孩指称其父亲的姐姐时,除了叫“kin51”之外,指称其为bi35+在世长子名,二种称呼等同,没有尊卑的差异且无不敬的意思。这点与汉族不甚相同,在汉语亲属称谓和称呼中,指称爸爸的姐姐为伯母,有且仅有这唯一的指称,不可能称其为某某的妈妈。
因此,属于类分式的杞黎亲属称谓体系更侧重于辈分之间的区分,尤其是长辈、同辈和晚辈之间的区别,不考虑实际年龄的大小;比较注重对现世的人、尤其是孩子身份的凸显,避免提及过世之人的名字,存在因家人过世而改称称谓的现象,在家庭中有了孩子之后,称谓指称上完全以孩子的称呼指称其他亲属成员;“兄弟姐妹”的社会血亲关系不仅限于一个村内同一祖公的同辈人之间,也可指称拥有同一男性祖公的两个村之间,即为“哥哥”与“弟弟”关系的两个村之间。
杞黎家庭的分裂最典型的模式是在一代人中多兄弟姐妹的情况下,姐妹相继嫁出,兄弟娶妻生子。青年男女结婚之前,与其父母共同生活,由父母支配家庭财产。在生育有第一个孩子,且孩子平安度过一周岁之后,通常就会分家。
杞黎聚集的五指山属于是合亩*有学者认为“合亩”二字不甚妥帖,但没有找到黎族更古的语源及更妥善的汉译以前,暂时沿用合亩这个名词(见岑家梧:《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收录于詹慈编:《黎族合亩制论文集》,广东省民族研究所1983年编印)。本文沿用学术界的统一用法,于词汇上不拟予以赘述。制地区,合亩内的田地归全体合亩成员所有,合亩内所有的农业收入归合亩成员共同所有,收获的粮食由亩头和妻子按照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因此,属于核心家庭的财产包括分配得到的粮食和牛只,其他的如农业用具,茅草房和房屋内的生活用具,小块自给自足的菜地,以及种植的芭蕉、槟榔等农作物归属个人所有。那么,一个已婚男性分家后,获得拥有自己的农具,自己开辟的新的菜地、槟榔或芭蕉等,以及可能分到的牛,并且以自己的核心家庭为单位参与合亩的劳动。
在现代社会中,分家与合亩制时期分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财产的类型和数量上。首先,田地的归属性质发生了变化,合亩制时期田地属于合亩集体所有,现在所有权归属于村集体,并由村民家庭承包经营。分家的时候,一般由家长主持,家庭所有成员都参与,谁先结婚,就分给兄弟数目的几分之一。其次,芭蕉树等其他农作物的种植,如果属于男青年婚前个人种植所得,分家后归属个人。即使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听到“这是某某的芭蕉”、“这是某某的小狗”等说法,这多少揭示了杞黎的观念中对个人所有物的重视,从另一个侧面来讲,也是合亩时期对个人私有财产称呼的延续,反映了当时个人私有物品的稀少。因此,传统上杞黎分家关键在于单独开灶,更多是从象征层面上阐释的,而现代社会的分家是原先家庭财产的再分配,包括土地和其他财产,二者有着根本不同。
实际上,如果最小的儿子成家后因为各种原因,拒绝赡养父母,也是可以的。根据报道人的说法,“如果有兄弟,就给兄弟,谁埋给谁,谁养给谁,要‘有头有尾’”。即按照“谁照顾老人,(财产)就给谁”的变通原则,经商量后,可以由大儿子一家照顾,也可以由二儿子、三儿子等一家来照顾。
然而,并不是每一对夫妇都能够生育有儿子,如果一对夫妇只是生育有女儿,等到女儿嫁出之后,当年老体衰、没有活动能力之际,必须由人照顾,这种情况下,老年男性的兄弟或兄弟的儿子就担负起赡养的义务与责任,那么夫妇的财产也就要赠给赡养他们的这位血亲。
在杞黎词汇中,不存在“收养”或“过继”的明显区分,均使用“li55bɑu51”这一词汇,字面意思为“认兄弟做干儿子,鬼入你这里”,意思为抚养同一族的男孩子*传统上一般抚养男孩,不会选择女孩,但是近年来,也有抚养女孩的情况出现。。夫妻离异之后,子女原则上归属丈夫的家族,如果孩子尚年幼,先由母亲带回,待长大后再回父亲家。尤其是男孩子,通常都会被父亲要回,如果父亲去世,其父亲的血亲有抚养的义务,并且共同帮忙直到成家为止。
现在社会中,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和受汉族观念的影响,对男孩的限制要少一些,对男孩长大后是否回到父亲村子也有了其他的看法,因此,男孩本身自己的意愿和选择也越来越重要。如今,已经出现男孩随母亲改嫁且在继父的村子娶亲生活的现象。
六、结论及讨论
岑家梧、曾昭璇和陈凤贤等学者对杞黎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和风俗习惯进行了分析,发现杞黎亲属关系的一些特征,如放竂的习俗、死后埋葬回娘家等习俗,认为这些习俗体现出母系氏族制的遗迹,因此,杞黎留着母系氏族制的残存。或者认为,由于杞黎合亩内男子在生产上、经济上渐占优势,成为主要劳动力和领导者,从而确立了按照父系计算世系和血缘及男子继承的规则,体现了男子的主导型地位,因此,合亩体现了从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的过渡。*参见岑家梧:《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史学月刊》1957 年第9 期;持有相同意见的还有曾昭璇、张永钊、曾宪珊:《海南黎族人类学考察》,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2004年,第20页;陈凤贤:《从文化遗存试探黎族母系氏族制及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在杞黎的血缘观念中,人是从男性小腿的位置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男性的血液多,那么生下的孩子像父亲,如果女性的血液多,生下的孩子更像母亲,血液的多寡是决定性别的关键因素。可以发现,血液作为人体的重要内在特质,分别是从父亲和母亲两边独立传递。
杞黎社会中,由同一个真实的男性祖先传下的后代具有相同的血缘,属于同一个亲戚集团,也就是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我们都是兄弟”。一个亲戚集团是一个社会血亲单位,其成员之间互为社会血亲,该集团内部严格禁止内部通婚,这是杞黎最基本的性禁忌规则。亲戚集团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集中居住等外在表现形式,即使现在外来人口的混杂较多,人们也能较为容易认清谁是亲戚,谁是兄弟。因此,杞黎社会表现出了父系的特征。第一,在婚姻过程中,男性是婚仪和婚宴的主要承担者,需要支付聘礼,承担大量费用,如果发生离婚等情况,对于女性的惩罚要比男性重的多,婚礼仪式中以男性为中心;第二,婚后实行从夫居的生活模式;第三,在分家、财产承继和继承人的认定方面,男性是最主要的接受者和接收者,女性没有权利分得任何家产;第四,互为亲戚或者兄弟的青年男女严格禁止婚配等。
然而,杞黎并非是一个纯父系的社会。与亲戚集团概念相对,男性的配偶组成的集团被成为外家集团,属于另外一个社会血亲范围。在该血亲集团范围内,内部也实行禁止通婚原则。
亲戚集团与外家集团都属于杞黎的亲属群体,二者既有区分又有联系,这在亲属称谓的指称上可以明显的体现出来,例如,对于夫方和妻方的称谓上有着不同指称,但对于双方的兄姐及其配偶的称谓则基本保持一致。亲戚集团内部无论相隔多少代均不能通婚,外家集团实行在第三代(含第三代)之后,就可以继续与已经形成的亲戚集团再次通婚,同时解除性禁忌,也就是说,杞黎人的身份认定制度由三项规则构成:血缘规则,父系血缘计算无限代的规则,以及母系血缘三代(含第三代)之后消逝的规则。该规则基本上与布几纳法索的萨莫人的身份认定规则相一致。*蔡华:《人思之人——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第32-34页。
由此可见,在杞黎社会中,亲戚集团和外家集团均属于社会血亲范畴,在日常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亲戚集团比外家集团的范围更为明确和更为重要,对其的约束力和限制条件也更多。所以,可以认定杞黎的社会血缘制度属于双边不对称制度,或者称之为奥马哈制度。*蔡华:《人思之人——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第25页。这也有力证明了身体表征系统这一反映民族的血缘观念在该民族的文化身份决定血缘规则中的绝对解释力。*蔡华:《人思之人——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第139-141页。
(责任编辑:晏 洁)
On the Kinship System of Qi Li People around the Five-finger Mountain in Hainan
WANG Xiao-hui
(InstituteofContemporaryChinaStudies,AcademyofChineseSocialSciences,Beijing100009,China)
Previous scholars tended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kinship system of Qi Li people around the Five-finger Mountain in Hai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ism, and believed that there were remnants of matriarchal society in the tribal system of the Qi Li people. Through some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n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kinship system research theory advanced by Prof. Cai Hua, an overall summary and systematic description has been made of the kinship system of the Qi Li people,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kinship system of Qi Li people around Five-finger Mountain is an asymmetric bilateral one.
Qi Li people;matriarchal society;the kinship system;the asymmetric bilateral system
2016-07-20
C951
A
1674-5310(2016)-11-009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