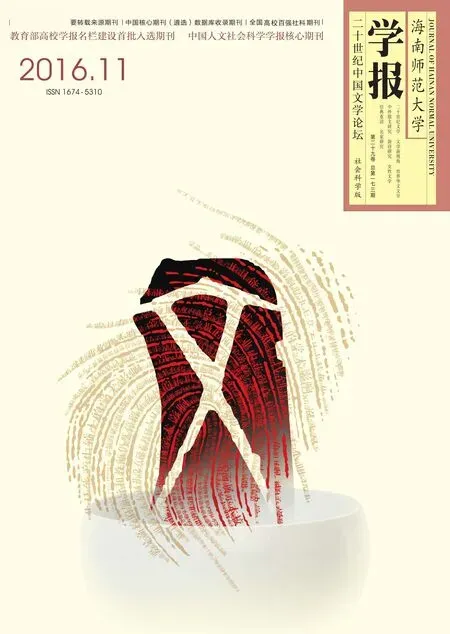试论历史上东亚国际秩序与中琉边界问题
2016-03-16刘玉山
刘玉山
(龙岩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福建 龙岩 364000)
试论历史上东亚国际秩序与中琉边界问题
刘玉山
(龙岩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福建 龙岩 364000)
东亚地区自古以来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我们称之为“东亚国际秩序”,在此秩序下,中琉关系最为和谐。中琉边界也一向清楚,没有发生任何的领土纠纷,两国睦邻友好,书写了一段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佳话。
东亚国际秩序; 中琉边界; 黑水沟
一、明清两代对钓鱼岛主权管辖的制度支撑——东亚国际秩序
在谈论古代东亚是否存在一个区域性质的国际秩序之前,我们有必要注意一下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体系”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服膺于其理论下的中国学者有王正毅等。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体系理论探讨的内容有十个方面:(1)周期和趋势;(2)商品链;(3)霸权和竞争;(4)地区性和半边缘性;(5)融入和边缘化;(6)反体系运动;(7)家庭;(8)种族主义和性;(9)科学和知识;(10)地缘文化和文明。概括起来,其讨论主要集中在世界经济体系、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文明三个层面。①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1页。他认为大致的世界体系形成于16世纪。可以发现,沃氏的研究多以西欧商品经济发展为视角,认为16乃至17世纪后,伴随工业革命的兴起,由于商品输出的需要,世界有连为一个“体系”的倾向。学术界对世界体系形成时间和地点的看法有分歧,如弗兰克认为世界体系形成于1492年的西欧,莫德尔斯基认为形成于1494年的西欧,阿布古德认为形成于1250年的东方。在笔者看来,随着17世纪以后欧洲民族国家、主权排他性等观念的形成和日益根深蒂固,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逐步地融合,但是也会出现拒不融合的情况,有些地区还会成为强权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商品倾销地,直到今天,各个地区因部落、种族、传统、习俗、文化等不同而很难具为一体说形成了“世界体系”,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unit),除非出现“地球村”(global village) ,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跨越了种族、国家与习俗的界限而“各亲其亲”,类似于中国儒家“大同”社会的设想,但至少目前是不可能的。针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如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她认为早在13世纪世界体系已经形成,但从她的著作《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来看,其所论述的也无非是区域性的欧洲布鲁日、佛兰德斯、热那亚、威尼斯乃至中国杭州的经济繁荣,笔者也读不出那个世纪有形成世界体系的事实。
那么,古老的东方是否具备形成区域性体系的条件呢?我们看到,喜马拉雅山以东至大海,蒙古高原以南到中南半岛,这块大的区域内从夏朝开始即以华夏族(汉族)为核心,其他民族(包括建立的政权)为外围,形成同心圆似的统治秩序。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天然的地理环境。在这一几近封闭的区域内,中原王朝军事上的主要对手是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突厥语族等部落,经过秦汉唐强盛的封建王朝的军事打击,这些部落民族遁去中亚直至欧洲,即使在两晋南北朝中原板荡的情势下,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如以鲜卑为首的“五胡”也是主动融入汉文化这一主流,魏孝文帝的改革堪为代表。即使宋以后,中原王朝国力孱弱,蒙古人与满洲人相继入主中原并建立王朝,但所遵循的路子还是与唐以前一样——融合。
被中原王朝赶至中亚以西的游牧部落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欧洲帝国与中原王朝的“挡箭牌”,一方面这些部落虽然在与中原王朝的角力中拜于下风,但却可以横扫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造成欧洲人口民族的流动变迁,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结构。古代的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等虽然与中国的封建王朝有某些联系,如贸易往来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但也曾经发生一定烈度的战争,如公元751年唐安西藩镇与阿拉伯帝国中亚怛罗斯之战,更多的是在远离中国封建王朝以西的地中海角力,本质上这其实也是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劣势,欧洲不具备东亚特有的天然地理优势。东亚这种独特的区域性的“体系”,何芳川教授称之为“华夷秩序”,而且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完整的一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在内,没有一个有如‘华夷’秩序那样源远流长,一以贯之”,*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第30页。评价不可谓不高。
对古代一直存在的东亚国际秩序的解读,学界最著名的要数汉学家费正清提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一说。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一书中,费氏提出“中国的世界秩序”,但在这本书所摘选的数十篇论文中却又提到“朝贡体制”,或者说这二者在费氏看来本就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学者比较多采用“朝贡体制”、“朝贡体系”、“封贡制度”、“册封体系”、“宗藩体系”等称谓,如李云泉、孙宏年、陈志刚、修斌等。香港学者黄枝连则立论新颖,用“天朝礼治体系”来称谓,在他看来:“19世纪以前,远东地区有一个突出的区域秩序,是以中国封建王朝(所谓‘朝’)为中心而以礼仪、礼义、礼治及礼治主义为其运作形式;对中国和它的周边国家(地区)之间、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起着维系与德定的作用,故称之为‘天朝礼治体系’。”*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也就是说“朝贡体制”看到了朝贡一方的“称臣纳贡”和宗主一方的“册封赏赐”双重内容,*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1页。而“礼治体系”则突出了儒家教义之仪礼体系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的作用,当然前者是互惠关系,后者有天朝自我道德规范下向周边国家外铄的意味在里面。根据上文所列,尽管称谓不同,所观察的视角也殊有差别,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确实存在一个区域性的国际体系则是学界较为一致的意见。 古老中国的夷狄观念肇始于先秦时期,如《尚书·禹贡》提出“五服说”(每隔五百里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提出“九服说”(每隔五百里依次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这里的“五服”或“九服”很显然越靠前则与天子的血缘关系越密切,如果到“荒服”、“藩服”,则涉及到古代中国数千年的“华夷之辨”。春秋时期楚将沈尹戌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郭丹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020页。,言下之意四夷应为天子守土。东汉班固在谈到困扰汉朝边疆的匈奴时说:“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东汉]班固:《汉书·匈奴传》卷94,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31页。也就是说天子对夷狄采用羁縻政策乃是常例。稍后西晋的江统在看到大量胡人内迁而阐发的《徙戎论》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我们或可用“守中治边”和“守在四夷”来大致概括中国古代处理夷狄的政策。即使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因大规模人口迁徙而有“五胡”称王中原,相比之,元朝和清朝以“夷狄之身”不仅入主中原,而且开拓了远比汉唐更为辽阔的疆土,康熙和雍正也可以如唐太宗一般喊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可以看出,从古至今,在东亚存在的这种秩序观是建立在自我想象与实力验证的双重基础之上的,突出反映了“华夏中心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也会因一些先前目为“夷狄”的加入而增添新的元素,但核心思想不变。这不奇怪,当明代官员为利玛窦没有将中国标示于世界地图中心位置而耿耿于怀时,欧洲人实际上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一幅地图反映了中世纪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眼中的地球北半球和南半球从东边的印度一直延伸到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和英伦诸岛,地图中心是耶路撒冷。*Jerry Brott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London: Penguin Books,2013,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10页。综上,在笔者看来,用“东亚国际秩序”来称呼古老东方存在数千年的秩序会更周延,更能体现出中国对外关系的本质即中国主导下的区域性地方秩序。
二、明清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运作
这一秩序对周边国家有一定约束力,如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及东南亚部分地区,故而出现了周边国家争相朝贡的局面,到了明清尤甚。但与中亚以西国家的关系则就不那么亲密,正如上文所展示的,一方面缘于东亚没有综合国力超越中国的国家,能够对中国的秩序发起挑战,另一方面西方帝国忙于经略环地中海沿岸,对中国尚不构成实质威胁,史书中虽然也有中西交通的记载,但这种看似对中国的“朝贡”,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的亲密程度。所以按照朝贡的亲密程度,有清一代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典型的朝贡关系,主要表现形式是朝贡国向清朝称臣,如朝鲜、琉球、安南。二是一般性的朝贡关系,其国王虽受清廷册封、赏赐,但与清王朝政治关系较为松散,表现的经济属性更为明显,如南掌、暹罗、苏禄、缅甸。三是名义上的朝贡关系,如清初厉行海禁,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出于贸易需要,偶有遣使清廷之举。*李云泉:《再论清代朝贡体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95-96页。
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对周边国家的政治意识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以致于有些国家也会建立小范围的“秩序圈”,如日本自丰臣秀吉始至德川家康时期对琉球用兵,并希望“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宾”。*京都史迹会:《林罗山文集》,大阪:弘文社,1930年,第130页。转引自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第8页。越南王朝也曾对外宣称:“缅甸附边则却之,万象有难则救之,多汉、南掌、火舍,慕爱义来臣,勉之以保境安民。至于洋外诸夷,如英吉利、富浪沙,于清、逞罗所傲视者,亦皆闻风而臣服。”*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2页。
在东亚国际秩序下,明清两代与秩序内诸国形成了一定的运行机制,如明朝捕获沿海盗匪后,还会请琉球贡使团进行辨别,并将整个过程通报琉球国王。清朝与朝鲜遇事会互通咨文。在诸国遇到军事威胁时,中国则有义务进行帮助。如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朝即派大军协助平倭,战争胜利后即使撤军也“庶不负抚危字小之仁矣”*《明太祖实录》卷329,《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日庚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686页。。而1875年日本侵占琉球,清廷也派何如璋进行交涉,并请美国总统格兰特进行调停斡旋。可以发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尚能正常运转,但到了清朝后期,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崛起,一个足以挑战古老东方文明古国的政体开始对此秩序发起了挑战。清政府请“洋人”调停,反映了这一秩序力有不逮与濒于土崩瓦解。
总之,古代以来一直存在的中国主导下的东亚国际秩序与近代西方学者所言附属国或宗主国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近代以来欧美列强通过对亚非拉弱小国家进行资本扩张、武力侵略和政治威慑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极端不平等的国家联盟关系的产物。*陈志刚:《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的本质属性:中原王朝陆基性国土防御体系——以封贡体系的理论框架与内部组成、运作规律为中心》,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受到儒家与佛教深度浸染的中国一向奉行和平主义,我们甚至在史籍中能够发现很多“天朝”对朝贡国“无礼”之举的容忍,中国与其主导下国际秩序的成员国平等、互相尊重,我们在下文所谈及的中琉关系即是一明证。
三、东亚国际秩序下的中琉边界
日本学者菅沼云龙在谈到中日钓鱼岛争端时特别看重历史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历史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中日关系中更是如此。”*[日]Unryu Suganuma:《中日关系与领土主权》,东京:株式会社日本侨报社,2007年,第6页。诚然,中琉关系一样不容忽视的是历史,我们看到,自从明初洪武五年(1372)琉球官方与中国交通以来,有明267年的时间里,琉球对中国朝贡达182次,继明而起的清代,从1644年到1867年,琉球朝贡又多达100次以上。*黄枝连:《天朝礼治系研究》上卷,第192页。从1372年至1879年日本灭琉球王国止,中国派往琉球的册封使共24次,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为方便贡使往来,更是赐闽人36姓给琉球,化俗成琉,中琉关系之友好、亲密,在世界邦交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本节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中琉之间没有出现任何的领土争议,其内在本质是什么?
我们先从中琉两国的历史文献中找寻对于钓鱼岛的相关记载,先说中国方面。现存最早有关钓鱼岛的中方文献记载是目前珍藏于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成书于明永乐元年(1403)前后的《顺风相送》,该书系誊写本,每页9行,每行24字,封底有拉丁文题记,里面有“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这是所见最早有关钓鱼岛的中方文献记载。陈侃《使琉球录》记载:“五月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台湾文献丛刊·使琉球录三种》(第三辑,55)第287种,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第11页。郭汝霖《使琉球录》记载:“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见姑米山矣。”*严从简辑:《殊域周咨录》卷四《琉球》,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第23页。谢杰《虔台倭纂》之界说:“如所云小琉球、鸡笼屿、彭嘉山、钓鱼屿,并来之睹,惟古米山见熹微,而琉球至矣。”杜三策从客胡靖撰《杜天使册封琉球真记奇观》写道:“薄暮过姑米山……深夜,镇守姑米山夷官远望封船,即举火闻之马齿山,马齿山闻之中山。”这是琉球国边防官员用火为信号向国内报告中国册使入境消息。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所载“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台北:大通书局,1987,第24页。汪楫《使琉球杂录》记载:“薄暮过郊(沟、郊福建方言同音)……问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引自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清抄本。生活于清朝乾嘉年间的一个文人叫沈复,他创作的自传体随笔《浮生六记》,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卷五《海国记》(又称《册封琉球国记略》)记录了他1808年随同清朝正副使齐鲲、费锡章出使琉球时的见闻:“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张百新:《钓鱼岛是中国的》,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55页。这些史料清楚记载了中、琉的分界线,从中国方面看是赤尾屿,从琉球方面看是姑米山(久米岛),中间的海沟就是最深达2,717米的琉球海沟。
有关这个海沟的记载在中国方面也是不绝于书。张学礼《使琉球记》云:“顷之有白水一线,横亘南北。舟子曰:‘过分水洋矣。此天之所以界中外者’。”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记载:“去由沧水入黑水,归由黑水入沧水。”这里沧水为福建海域,黑水为琉球海域。夏子阳、王士祯《使琉球录》记载:“且水离黑入沧,必是中国界”,*《会稽夏氏宗谱使琉球录》,黄润华:《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33页。明确指出沧水为中国海域。周煌《琉球国志略》:“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黄润华:《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中)》,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899页。李鼎元《使琉球记》:“ 十月六日,随行者问:‘海面西方黑水沟与闽海界,古称沧溟,亦曰东溟,球人不知,此行亦未之过,何也?’”*鞠德源:《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探源》,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25-27页。
明代海防图连续详载中国固有的主权领土钓鱼台列屿。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郑舜功绘《小东岛(即台湾岛,亦称小琉球)暨诸海山图》;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郑若曾绘《万里海防图》、《福建沿海山沙图》;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徐必达、董可威仿照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摹绘成《乾坤一统海防全图》,明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绘《福建沿海山沙图》,施永图绘《福建防海图》;嘉靖四十年(1561)郑若曾还绘制了《琉球国图》;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王圻再绘了《琉球国图》。这些海防地图均根据“详外而略内”的原则,将台湾岛附属岛屿钓鱼屿(又作钓鱼山)、橄榄山(又作黄茅屿、薛坡兰)、黄尾屿(又作黄麻屿、黄毛屿、黄尾山)、赤屿(又作赤尾屿、赤坎屿、赤尾山)等岛屿凸显地绘载于图内,郑若曾和王圻先后所绘的《琉球国图》,又充分显现了明人所运用的地理密集编绘之法,其中所绘载的澎湖岛、小琉球(即台湾岛)、鸡笼屿、瓶架山、花瓶屿、彭家山(即彭住屿)、钓鱼屿,不仅简明地揭示了福建驶往琉球航路上所通过的中国岛屿,而且集缩于琉球国海域之近旁,则更加凸显出宗藩之间的地缘环境,而在地理上却与琉球国绝无任何领属关系。*鞠德源:《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探源》,第42-45页。
那么从琉球出版的文献来看有没有钓鱼岛的相关记载呢?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曾编辑出版《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丛书32册,编委之一的韩结根教授经过详细比对,查找了《中山世谱》、《琉球国旧记》、《琉球小志并补遗》、《中山世鉴》、《指南广义》等文献,均未发现钓鱼岛属于琉球的记载。甚至琉球国第一部正史引用了陈侃《使琉球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这样的话语,《指南广义》沿袭了中国对钓鱼岛列岛命名的习惯,如鸟屿、黄尾屿、赤屿等,甚至在《指南广义》作者程顺则的诗集《雪堂燕游草》卷末附录一篇《琉球考》,文章中有“望见古米山,即其境”之语。*韩结根:《钓鱼岛——历史的真相与故事》,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第152页。
综上,琉球国历史文献不见钓鱼岛属于琉球的任何记录,而中国方面的历史典籍对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记载却比比皆是,这说明了什么?这里可以回答上文提出的为什么中琉之间没有出现任何的领土争议,其本质原因就在于有一个看不见却切切实实存在的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在这一秩序下,琉球遵守该秩序。中琉关系一向和睦,边界清晰,兹作如下几点说明:
其一,那个时代不适用于欧洲自格劳秀斯开创的“国际规则”,格老秀斯的理论是欧洲资产阶级掠夺亚非拉国家的产物。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极力挞伐的与明清同一时代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对美洲大陆的“占有”,却恰恰反证了那个时代对于“占有”的认识。我们看看卢梭怎么说的:
当努涅兹·巴尔波在海边上以卡斯提王冕的名义宣布占领南太平洋和整个南美洲的时候,难道这就足以剥夺那里全体居民的土地并把全世界的君主都排斥在外了吗?然而就在这个立足点上,这种仪式却枉然无益地一再为人们所效颦;而那位天主教的国王,在他的暖阁里只消一举就占有了全世界,只要随后把别的君主已经占有的地方划入他自己的帝国版图就行了。*[法]卢梭:《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8页。
也就是说“时效原则”、“关键日期”、“无主地先占”等现代国际法理念不应强加于那个时代的国际领土观念,那个时代就是“谁发现谁拥有”。因钓鱼岛列岛与琉球姑米山之间隔着深深的黑水沟,从地理洋流的角度,中国的渔民可以顺利到达,但琉球方面却逆流而上,所以钓鱼岛列岛最早由中国人发现、命名和利用,琉球之间的“黑水沟”成为东亚国际秩序下中琉两国的天然分界线,约定俗成,双方都默认“黑水沟”是分界线,这在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下是受到双方官方承认、民间履行的,上文列举的一系列文献记载就是这一反映。
其二,有历史可考的中方对钓鱼岛的记载是明初的《顺风相送》,那么明以前中琉之间肯定也是本着“黑水沟”为分界线的原则,目前没有发现明代以前的历史记载不代表不存在上述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先有中琉边界早已约定俗成这一社会存在,才有后来《使琉球录》中大量的中国与琉球双边人士对两国边界的详细而传神的记载。中琉之间边界的定论肯定在明代以前,甚至可以上溯到宋元,因为“集体记忆”需要时间的沉淀,这个时间肯定不是三五年,应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其三,在东亚国际秩序下,琉球安守本分,谨事中国,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中国皇帝甚至可以赐予自己的臣民给予对方,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看来几无可能,但却在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下已然运转良好。这证明东亚国际秩序历经两千多年的时间考验与实践检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一体系下的中琉关系为国与国之间树立了良好的相处典范,如何在当下挖掘和唤起东亚国际秩序是一项较有意义的课题,当然,这脱离了本文主题,当另文专论。
其四,中琉两国的人口、土地面积、综合国力及文化影响力不仅仅是不在一个等量级的问题,用通俗的话来说,这根本就是大象与螳螂之间的关系。所以,本就“华夏中心主义”的“天朝上国”根本无需对琉球官方发布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的声明,因为对方太过弱小,中国官方也没有必要在边界问题上刻意澄清。
其五,即使中琉实力完全不对等,中方无需就中琉边界发布正式声明,但明清几十位册封使使命完成后回来据实以录的《使琉球录》,是经皇帝批准以官方文书的形式颁行于天下的,琉球同样没有持任何异议,这就等于是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了中琉之间的边界。换句话说,若不是日本这一“恶邻”对琉球历史的介入,钓鱼岛列岛在中琉之间根本就不是问题,中琉边界在东亚国际秩序下一向清楚。
四、结语
在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下中琉边界一向清楚,其边界就是根据自然形成的“黑水沟”,中方一侧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琉方一侧是姑米山,这在当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使琉球录》里都有详细而传神的记载,白纸黑字,非常清楚。中琉两国在东亚国际秩序下和睦相处,平等交往,书写了一段国与国之间邦交的佳话,如何在今天进一步挖掘东亚国际秩序的成功价值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胡素萍)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China and Ryukyu
LIU Yu-san
(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LongyanUniversity,Longyan364000,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there has been a China-dominat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known as the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order”, under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Ryukyu has long been harmonious, because the boundary between two countries has always been clear without any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a good neighborly friendship has been established between them, thus having set an example for nation-to-nation exchanges.
internat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Ryukyu; the black ditch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民间‘保钓’运动史研究(1970-2014)”(项目编号:14CZSD20)
D829.13
A
1674-5310(2016)-11-01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