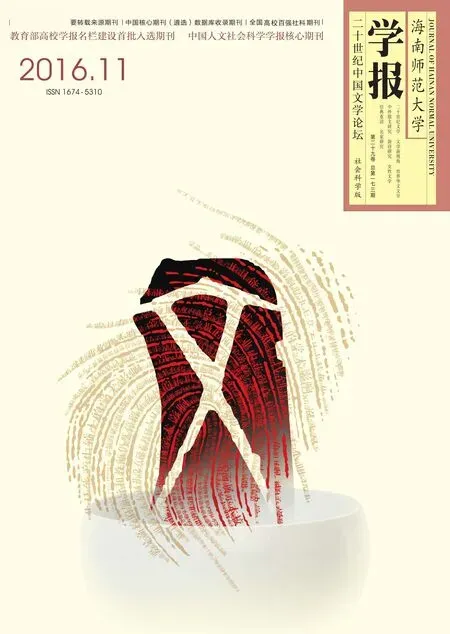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新女权运动及其反思
2016-03-16孙继静
孙继静
(湖南女子学院 教育与法学系, 湖南 长沙 410004)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新女权运动及其反思
孙继静
(湖南女子学院 教育与法学系, 湖南 长沙 410004)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出现的新女权运动,将妇女解放的阵地转向私人领域。在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女权主义者就堕胎、家务劳动、性骚扰等个人问题发表了相关看法,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活动。这次运动虽不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给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巨大改变和冲击。之后,人们开始对女权主义理论及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容和方式进行理性的反思。
法国;新女权运动;反思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女权主义的复兴,掀起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新一轮女权运动的高潮。这次女权运动的目标和范围涉及妇女权益的方方面面,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第一次女权运动。这次女权运动针对现代社会的父权制文化和制度,向整个社会发起全面挑战,要求获得更广泛的男女平等:政治上,号召妇女积极参与政治,影响政治权力;经济上,号召妇女争取工作权力,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争取工资地位等方面与男性平等;文化上,争取把女性从男性中心的传统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中彻底解放出来;历史上,争取社会承认女性同等的贡献。这次女权运动不仅关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也开始关注私人领域内的不平等。
保守势力强大的法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一热潮,法国这次的女权运动相对而言兴起较晚,但也更为激进,其成果也十分显著。在妇女们的努力下,法国社会开始关注妇女问题,逐步改善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法国政界为了争取妇女选票,也将妇女问题提上日程,妇女地位日益得到改善,取得令人欣喜的成绩。
一、法国新女权运动兴起的背景
(一)“五月风暴”的洗礼
1968年爆发了震撼西方的“五月风暴”运动,这场运动主要以学潮和工人运动的形式展开,虽然仅仅持续一个多月,但却引起了人们无尽的反思。运动的主角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当时的生存状态是“自在中感到不自在,在舒适中感到精神上的不舒适,在富足中感到情感上的贫乏,在合理中感到根本的不合理”①[法]米歇尔·威诺克:《60年代:青年人的冲击》,《有关1939年至今的法国研究》,巴黎:巴黎瑟伊出版社,1985年,第307页。。该运动以“改变生活”为口号,反对现存的一切生活模式,对几百年来形成的对权威、习俗、父辈的顺从和隐忍不满,期待建立自由自主的新生活。实际上,这场思潮中年轻一代和前辈师长的关系与父权制社会中男女两性关系一样,都是前者对后者权威的绝对服从。这样一来,许多参加了五月风暴的女青年们,在这场运动的洗礼下锻炼了自身,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认为有必要再次唤醒社会对女性命运真实性的关注。她们清醒地看到法律上的平等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平等,要求实行一系列社会立法改革,对传统制度文化和传统的性别角色提出质疑。
(二)女权主义思想理论
新女权运动的出现不同于以往的女权运动,这个时期是女权运动最具影响力也是最有成就的时期,不得不说这一局面的出现得益于一种新的女权主义理论。法国著名女作家女哲学家西蒙·波伏娃里程碑式的作品《第二性》的出版,为该时期的女权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成为法国新女权运动有力的思想武器。书中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9年,第13页。这句话像一座灯塔,指引了法国新女权运动不再如以往只停留在不触动现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法律层面的改良,而是将矛头直接指向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
二、法国新女权运动的内容
新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口号是“私事即政治”*[法]弗朗索瓦滋·皮克:《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社会效果》,巴黎:巴黎第七大学,1987年,第135页。,她们认为私人领域是妇女受压迫受剥削最深重的地方。因此这次新女权运动与历史上前几回女权运动有所不同,参加者不带明显的政治色彩,常常围绕孩子、家务、性等问题展开行动,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斗争。同时,她们也一改之前说教性的风格,采取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轻松诙谐的格调。
(一)争取堕胎自由权
60年代末的法国社会,由于堕胎的不合法,导致妇女在做不做母亲这一问题上没有自由选择权利,她们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自由支配权。于是,很多女性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选择秘密堕胎,而这种方式给女性带来的往往是无尽的痛苦、耻辱、对生命与健康的威胁。同时,当时人们还固执地认为,上帝赋予女性生育的功能就意味着抚育孩子也是女性的唯一天职,这种思想有碍于妇女进入社会从事公共劳动。
1970年10月,“妇女解放运动”和“争取流产自由化运动”举行了第一次示威游行,要求全面实行流产自由。1971年初,《新观察家》杂志发表《流产宣言》,宣言中签名的包括西蒙·波伏娃在内的343名妇女宣称自己曾有过堕胎的经历。这一宣言显然是对法律的一种对抗,主要目的是将这个隐匿在法律之下的巨大事实摆在公众面前,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1972年10月,一位17岁少女遭强奸怀孕后,因非法堕胎,致其本人母亲及帮助过她的3人一同受审。这一案件引起了全国性的剧烈反响,包括工会和许多政党在内的组织都纷纷表示支持堕胎自由。最终,在女权主义者多次示威游行和反复辩论及新闻报刊的舆论攻势下,法国政府于1975年通过了决定废除1920年颁布的刑法第317条中禁止人工流产的规定。70年代的最后一年议会正式通过了《自愿堕胎法》,给予了妇女自由堕胎的权利。
(二)家务劳动及解决办法
新女权主义者认为,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其中最根本最深重的压迫,而最典型的则是私人领域。她们认为女性之所以从属于男性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妇女的家务劳动被无偿占有,这部分只有价值没有交换价值的“无形劳动”是妇女参与公共劳动获得解放的最大障碍。由于女性的性别身份,导致人们固有观念中将这部分劳动视为理所当然,不能享有报酬,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因男人们挣钱养家而已经得到了实际的报偿。新女权主义者驳斥了这些说法,她们提出如果将这些如洗衣做饭抚育孩子的劳动放到社会市场中去,作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它们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同时,男人养活妻子的花费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换成社会公共劳动的价值是相差甚远的。据当时法国的一项统计显示,“法国的雇佣劳动者每年干活430亿工时,而妇女每年做的无偿家务劳动则为450亿工时”*[法]雅克·J·赛菲尔:《西蒙·波伏娃的新女权思想》,巴黎:德诺埃尔出版社,1982年,第123页。。因此,妇女的家务劳动实质上是被男性所剥削的。
新女权主义者在看到了家务劳动的本质之后,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当时有人提出由国家给予女性家务劳动以报酬的办法,但以德博瓦为首的清醒的女权主义者们并未落入此阴谋论中,她们对这种做法持否定态度。首先,这种做法缺乏可操作性。家务劳动不同于公共劳动,属于私人领域,无法公平量化和监督,涉及到每个具体家庭的具体问题,绝不是她们可以在各自家中彻底解决的。其次,女权主义者看到这种做法最终将导致女性完全束缚在家庭中,更加强化现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使得女性与社会脱节,更加弱化其作为社会人的身份,而对男性产生更深的依附关系。因此,这样做不但不能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反而会将一套更严密的枷锁加于女性身上。于是,法国新女权主义者提出“婚姻是最大的陷阱”*[法]阿利丝·施瓦采:《今天的西蒙·波伏娃》,巴黎:梅库尔出版社,1984年,第77页。,倡导妇女选择不结婚或者不生育等极端方式来摆脱这种剥削。虽然这带有明显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特点,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毕竟法国新女权运动者们看到了女性在家务劳动这一问题上所受的不公平的待遇。
(三)性骚扰、家庭暴力、避孕等其他问题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法国妇女仍然继续着前人的步伐,为改变自身命运做着不懈地努力。受到“五月风暴”运动中反传统、反等级、反权威宗旨的影响,妇女们摒弃一切形式主义的做法,拒绝成立严密的组织,没有政党,越来越强调妇女组织的独立性,更多地致力于改善妇女地位和处境的斗争。
考虑到当时法国可能有1/5的妇女曾是性骚扰的受害者,女权主义者便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有关制止工作中性骚扰女性的法律草案;注意到可能有1/6的女性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女权主义者专门为这些妇女设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电话咨询台;了解到许多女性因为性知识的缺乏导致未婚先孕,女权主义者召集媒体开展了一场关于14-20岁年轻女子的全国性避孕知识宣传活动。除此之外,新女权主义者还对妓女、卖淫以及同性恋等问题给予关注,并采取了一定的行动。
三、法国新女权运动对法国社会的冲击
经过六七十年代的新女权运动,法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政府在许多领域尤其是私人领域等事务上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女性的法律;另一方面,由于过于激进,新女权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多地方脱离了现实,妇女们在享受这场运动所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饱尝苦果,开始逐渐对女权主义产生了种种质疑。
(一)形式多样的家庭结构
当女权运动者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私人领域时,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之一——家庭就注定要发生改变了。
第一,传统的核心家庭日趋衰落。所谓核心家庭,即一对夫妇共同抚养其子女。在这种传统型家庭中,丈夫是一家之主,出外工作;妻子则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子女,辅助再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来补贴家用。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女权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职业妇女人数日益增多,逐渐想要摆脱对家庭和男性的经济依赖。这些必然导致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日益受到挑战,趋向衰落。一方面,结婚的人越来越少。四五十年代的时候,绝大部分少女仍以结婚生子为人生既定目标;但七十年代以后,年轻人尤其是女青年对于婚姻不再感兴趣。尽管政府所规定的结婚年龄低,但实际结婚的平均年龄却推迟了:女性为26.3岁;男性为28.3岁。同时,结婚率不断降低:六十到七十年代,全法国每年有35万对到40万对男女结婚;到1992年,减少到27.2万对。*徐鹤森:《法国妇女现状一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2期。另一方面,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今天的法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夫妻因种种原因而离婚”*徐鹤森:《法国妇女现状一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2期。,而其中有70%都是由女性提出来的。当女性有了一定的经济独立地位,参与社会劳动又开阔了她们的视野,各种平权运动的经验促进了其权利意识的觉醒,参与公共劳动活动的妇女对丈夫和家庭的依赖不再如之前那么强烈,她们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和婚姻中的情感联系。当发现婚姻生活并不如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时,她们也能无所顾忌地提出离婚。同时,居高不下的离婚率,离婚时繁杂的手续,为了自身利益而在法庭上针锋相对所带来的情感伤害和纠葛,使得年轻人对婚姻更是望而却步,这进一步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第二,新式家庭的出现。伴随着传统家庭的衰落,新式家庭在法国日益增加,例如单亲家庭(独身的父亲或母亲独立抚养子女)、混合家庭(离婚的男女带着婚前或前婚中的孩子共同生活)、同居家庭(未婚同居男女及其子女所组成的家庭)、丁克家庭(不要孩子的夫妻俩所组成的家庭)、同性家庭(同性恋者组成的家庭)、独居家庭(一人独居的家庭)等。
当今法国社会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未婚同居十分普遍,同居风潮的出现展现出法国女性的独立和自我,向往自由生活,不希望被传统的婚姻家庭束缚。人们普遍认为没有经过婚前的同居生活,就不会有婚后的幸福,未婚同居成为婚姻的必经阶段。而现在甚至有更多的人完全放弃了婚姻,即使他们有了好几个孩子也不愿结婚。法国著名的女政客罗雅尔与男友共同生活了25年,育有四个孩子,但至今也没有步入婚姻的殿堂。另外,这种婚姻形式不仅得到了普通群众的认同,更是得到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和鼓励。国家不仅发给证书,而且在税收制度上还采取了更有利于同居者的措施。1968年至1969年,同居“婚姻”仅占婚姻关系的17%;1976至1977年上升至44%。*沈炼之:《法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32页。这样一来,婚前同居在法国青年人中全面流行开来,且得到公共意识的认可,无论是以公开的方式,还是保密的方式。
由于婚姻关系的不稳定,尤其是同居“婚姻”的不稳定性,单亲家庭、混合家庭增多。此外,受到激进主义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对婚姻家庭的恐惧与排斥,对个人自由生活的追求等使得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女性选择独身,或组成丁克家庭、同性家庭和独居家庭。传统的家庭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家庭结构形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然而这些新式的家庭结构形式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人类在婚姻家庭中所遇到的问题,反而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上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出现。
(二)走向泛滥的性解放
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针对传统性观念中对男女所提出的不同要求,认为传统的性关系是男性对女性的严重束缚,女性在这种关系中是压抑的、被动的,女性自身的意愿和情感得不到根本的体现。她们要求将妇女从传统的性关系中解脱出来,提出了性解放。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六七十年代整个西方社会陷入性解放甚至性泛滥的狂潮中,天性浪漫的法国人自然也不例外。“70年代初,法国妇女在21岁时还是处女的占一半以上,80年代,90%以上的未足18岁的年轻姑娘已尝过‘禁果’。……60%的法国已婚男人面临着妻子不忠的威胁。”*姚培锋:《论女权运动及其对西方国家婚姻家庭的影响》,《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2期。然而,迅速卷入性解放浪潮的法国人不得不面对自己种的苦果。走向泛滥的性解放不仅威胁到婚姻家庭的稳定性,也威胁到青少年的生活,更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导致如未婚妈妈、少女妈妈、问题儿童、艾滋病的流行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性解放带来的同居风潮造成未婚女子增多,未婚产子的情况也随之增多。据统计,当时法国未婚女子每年生下的私生子达9.2万,但即便如此,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法国妇女独身或不愿生育的强烈欲望导致新生儿出生率一直低迷。同时,年轻的未婚妈妈缺乏自理能力,为了孩子又不得不放弃学业,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难免处于劣势,生活贫困,有些少女甚至因此走上犯罪的道路,而那些缺乏照顾甚至被母亲抛弃的儿童又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另外,性解放带来的艾滋病的流行也一度令西方国家感到恐慌。
四、对法国新女权运动的反思
法国新女权运动由于过于激进超前,出现了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落差,其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的一些误导致使女权运动的负面效应严重。因此,运动的一开始就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她们将这些归结于女权主义的错误。那么作为行动者、倡导者的女权运动者是否该为此负上全责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激烈的思潮退去之后,女权主义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女权主义的误区
作为女权运动的指导思想,女权主义对女权运动所带来的副产品也难辞其咎。女权主义者在追求男女平等的目标上一味地将男女两性完全对立起来,难免有失偏颇。
一方面,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在强调男女平等的同时,却走向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注重强调男女两性的完全平等,极力淡化甚至贬低女性特质,严禁一切女性化行为,倡导将如高跟鞋、化妆品、假发等有女性特色的物品扔进历史的垃圾桶。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为了表示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常常以一身男装示人。即使在今天,进入男性占主导工作领域的女强人也常常是一身利落的男性化十足的职业装。对六七十年的女权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也极力贬低女性气质,她认为女性所独有的气质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而正是这种男权社会中所造就的女性气质成为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在职业领域,这种女性气质也妨碍了女性的工作,成为女性追求个人价值的绊脚石。实际上,这种形式上的男女平等是在肯定男性特质优于女性特质基础上的一种所谓的平等,从根本上否定了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存在的价值。
另一方面,一些女权主义者坚持女性比男性优越,极力贬低男性地位,拒绝男性价值,迷恋女性的道德优越感,建立一套“解放女性”的守则,想另辟蹊径发展女性自身的主体空间,却逐渐走向大女子主义。她们对男性极其失望甚至将他们当作“敌人”, 认为男人对女人的压迫是社会中最根本最深重的压迫,妇女的解放斗争必须直接针对男人的统治,将男女两性完全对立起来。同时,新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对女人的家长制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权利关系,而这尤其存在于私人领域中,因此女性自己的使命就是要消灭家庭、婚姻、爱情、母亲责任、异型性关系等这些包括性别角色的传统习俗制度。这使得一部分女性放弃对异性恋和婚姻家庭的追求,把女同性恋、性别分离主义做为唯一可行的女权主义选择。她们为了得到解放,就要摆脱婚姻家庭的束缚,妇女必须跳出异性欲恋的限制,通过独身、自娱或女同性恋创造出独到的性欲。波伏娃就认为婚姻只对男性有利,而对广大的妇女而言则完全是一种束缚,然而在男权社会中所塑造出来的女性只能选择婚姻。“她以牺牲来获取,她以放弃自由来取得自由,她以放弃世界来争取世界。”*[法]西蒙·波伏娃:.《女人是什么》,王友琴等译:《〈第二性〉选译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229页。这样的婚姻又怎么能让女性尤其是追求个人自由的女性走进去呢?在女权主义者提倡的只有女性之间的爱才是平等无害的理论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了不婚和独居等生活方式。一些女性走向极端,女同性恋现象普遍。
(二)理想与现实的反差
近代以来,妇女的群体意识逐渐觉醒,开始关注自身权益。作为女权运动的倡导者和直接受益人,妇女大多对女权运动予以同情和支持,她们也深受女权运动的影响。然而在她们接受女权主义的同时,男性占主导的社会并没有接受这些激进的观点。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她们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对于传统婚姻家庭生活备感失望。比如传统的观念中女性应该负担起家务劳动,而男性要在外工作。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男性愿意从事一些家务劳动,但家务活的重担主要仍是由妻子来承担。据调查,法国职业妇女每天从事家务平均5.24小时,而男子近2.4小时。*端木美、周以广、张丽等:《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44页。这些职业妇女一方面要在职场中与男性一起拼杀,承受起外出工作的压力;另一方面沉重的家务劳动又要占据她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女权运动使她们获得了与男性同等工作的权利,却也使她们疲惫不堪。在事业与家庭中试图找到平衡点的女性大多只能以失望告终,即使找到了那个平衡点也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忍耐和毅力。更何况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社会依然期望妇女在事业与家庭的冲突中选择放弃个人事业。这都使一部分女性对婚姻望而却步,情愿选择独身,甚至独自抚养孩子也不愿步入婚姻的殿堂。
(三)个人主义的影响
个人主义作为西方社会一种十分重要的价值观念,对整个西方世界影响深远。它以个人利益和自身享受为出发点,追求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这一人生观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成功而成为统治社会的意识,并且随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完成而普及。德国近代哲学家费尔巴哈说:“你的第一个责任便是使自己幸福。你自己幸福,你也就能使别人幸福。幸福的人但愿在自己周围只能看到幸福的人。”*安徽劳动大学《西欧近代哲学史》编写组:《西欧近代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89页。以自身的享受为主体的人生观是纵欲的,多欲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标志,用合法的手段去追求幸福是符合人权与基本道德的。女权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就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60年代以来,这种个人主义更是在各国盛行,导致年轻一代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她们只愿享受生活,不愿为他人负责。而婚姻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责任感,对孩子的照顾更需要耐心和责任,同时社会要求女性在这一方面付出得更多。这样一来,拒绝责任的年轻人尤其是女青年又如何愿意去接受婚姻呢?另外,弗洛伊德等人的性学说在西方世界传播开来,使得人们对性生活上的神秘感大大降低。这种学说认为严格的性限制干扰了人们享受乐趣,制造了一大批心理症患者,使得违法犯罪率激增,泯灭了人性与自我。人们为这种性限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得到的东西却少得可怜。因此他们呼吁提高人道,取消不必要的性限制。同时,医学界研究出来的避孕药、安全套、人工流产等满足了享受性自由的需要,为性解放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都导致婚前同居行为成为一种大众习以为常的风俗。
总之,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新女权运动使得妇女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妇女处境得到改善,整个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转变,法国女性个性独立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这次激进色彩浓厚的女权运动也对法国社会尤其是婚姻家庭造成巨大冲击,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我们享受女权运动所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要对其负面效应进行反思,从而构建一个男女两性真正平等的和谐社会。
(责任编辑:晏 洁)
The New Feminist Movement in France from 1960’s to 1970’s and Its Reflection
SUN Ji-jing
(DepartmentofEducationandLaw,HunanWomen’sUniversity,Changsha410004,China)
The new feminist movement which happened in France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urned the front of women’s emancipation to the private sect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que social background and ideological theory, feminists aired some views on such personal issues as abortion, housework, sexual harassment, etc. and conducted a series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Although without its obvious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movement has caused great changes and impacts in many social aspects in France. Later on, people began to reflect rationally on the feminist theory as well as the content and the pattern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France; the new feminist movement; reflection
2016-07-12
D440
A
1674-5310(2016)-11-008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