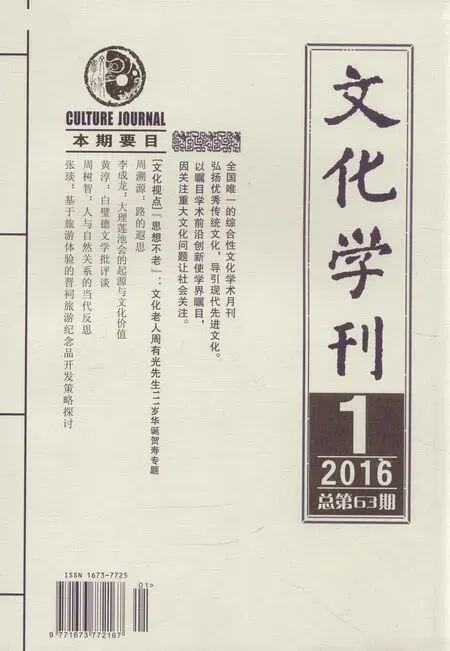英汉诗歌翻译中的意境美
2016-03-16廖锦凤
廖锦凤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系,广东 广州 510510)
【语言与文化】
英汉诗歌翻译中的意境美
廖锦凤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系,广东 广州 510510)
意境美是诗歌的灵魂和精神所在。诗歌的翻译,不但要求译者准确理解原文,更需要追求深邃的意境,才能产生浓厚的感染力和强烈的艺术效果,从而使诗歌翻译本身具有的特点得到体现。本文从诗歌翻译的主要特征出发,例举了两首名作的翻译,以解释诗歌意境的再现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意境美;诗歌;音译
翻译是一门艺术,在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的过程中,[1]译者需要对审美和情感形式进行再创造,同时把原作的内容和艺术意境传达出来,才能达到翻译的效果。要译好一首古诗,首先要译出那深沉而朦胧的意境美。近代学者殚精竭虑,从严复的“信、达、雅”到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从傅雷“神似”到钱钟书的“化境”等,均为诗歌翻译提供了有益启示。尤其是许渊冲教授,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理论,其中意美最为重要。诗歌的英汉翻译,不但要传达原文的风格,还必须能驾驭和运用与原著同样精炼的语言,才能使译作达到艺术性的水平,在阅读中得到美的享受。诗歌的翻译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一、再现原作的意境和艺术美
诗歌的翻译不但需要忠于原文的内容和思想感情,还要求译者能运用特殊的语言和艺术手法创造性地再现原文的意境,体现译者独特的艺术风格。如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孤鸟》中的前半段译文。
A widow bird state morning for her love,
Upon a wintry bough;[2]
孤鸟栖寒枝,悲鸣为其曹;
The frozen wind crept on above,
The freezing stream blow;
河水初结冰,冷风何萧萧;
There was no leaf upon the forest bare,
No flower upon theground,
荒林无宿叶,瘠土无卉苗,
And little motion in the air,
Except the mill-wheel's sound.
万籁尽寥寂,惟闻喧桔槔。
原诗表达的是一种悲凉的意境,译者紧扣诗篇的感情色彩,通过“寒枝、悲鸣、冷风”几个译词清晰地勾画出一幅冬日荒凉凄惨的景象:寒风呼啸的冬日,滴水成冰,一只小鸟孤独地站在枝头为自己失去的伴侣啼叫哀鸣,创造性地传达出原作的艺术境界,且译文较原作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读罢,对那只孤苦伶仃的鸟儿顿生怜惜之意,从心底泛起一股悲怆之情。又如苏格兰著名诗人罗伯特彭斯的情诗《吉恩》后半段的译文。
I see her in the dewy flowers,
I see her sweet and fair.
露滴芳蕊开,见伊容色鲜。
I hear her in the tunefu’birds,
I hear her charm the air.
春禽婉转啼,闻伊歌缠绵。
There’s not a bonnie flower that springs,
But by fountain, shaw, or green.
清泉流汩汩,树丛草芊芊。
There’s not a bonnie bird that sings,
But minds me o’my Jean.
花香鸟语处,总念吉恩妍。
彭斯的情诗《吉恩》韵致缠绵,语简而意长,感情强烈。译者翻译时亦用词不多,韵脚工整,清晰地勾画出了花丛深处、花香鸟语中吉恩的芳容倩影,充分表达了原作中诗人对吉恩的深深眷恋和爱慕。一首好诗,往往让人读后感觉意中有境,境中寓言,耐人寻味。因此,在诗歌翻译时,不但要求译者对原作心领神会,移情于自身,充分发挥想象力,还要求译者有较强的文学功底,才能把把原作的艺术美和意境美再现出来。
二、使用音译
音译是一种创造性的美,这种创造性关键在于抓住蕴含在原作中作者的思想感情,甩开原文形式,按原文词汇中的音韵找到绝佳的词句、表现手法,创造性地再现原作的内容、情感、意境、韵味和风格。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 Gerald)翻译的译作《鲁拜集》(The Rubaiyat),不但传达了原诗的意境,还具有英国诗的音韵之美,是吸取灵感的再创作,在诗坛上堪称一绝。
徐志摩的《哀曼殊斐儿》,诗中的爱尔兰女作家Katherine Mansfield被音译为曼殊斐儿,这四个字用来形容其冰清玉洁的美好气质再贴切不过。在志摩笔下再现出令人震撼的美,而按直接音译成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就完全失去了应有的诗意。又如Cambridge在翻译中译作剑桥,而徐志摩独创性地在诗作中将其译成康桥,更多了象征的意蕴。Violin在英文中是小提琴的意思,而《荷塘月色》中的名句“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铃上奏着的名曲”,将“Violin”音译为“梵婀铃”便多了一种婉约清丽的和谐。
三、结语
汉语的语言文字之美是特有的,无可替代。西方的文学变成声音,透过想象才能感到绘画的美,而中国的象形文字可以直接表现绘画的美。汉字含有物象的基因,有一种模糊的图画美,具有某种空间性和可视性,比如看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诗,立刻就可饱览绘画之美。诗歌的英汉翻译通过语言文字之美,译后可使读者看到“既有意思,又有响声,还有光彩”的创作。[3]一件好的译品不但要文字流畅,忠实通顺,更重要的是有思想之美,意境之美,感情之美,并且能做到音、形、义兼美。
[1]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115.
[2]《中国翻译》编辑部.诗词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206.
[3]《中国翻译》编辑部.论英汉翻译技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88.
【责任编辑:刘亚男】
H059
A
1673-7725(2016)01-0169-02
2015-10-05
廖锦凤(1973-),女,广东大埔人,讲师,主要从事翻译与外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