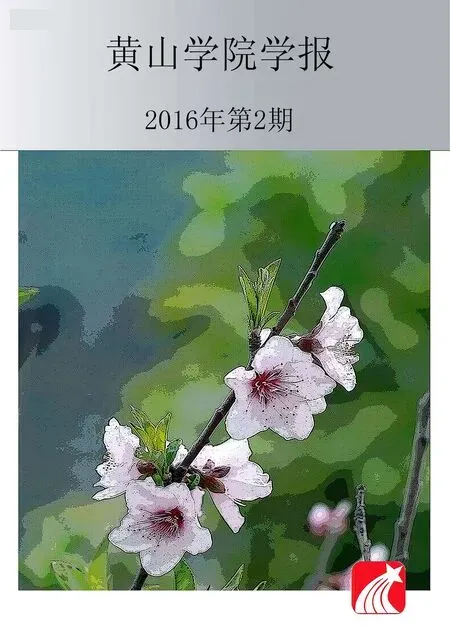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寿州锣鼓研究
2016-03-16孙四化
孙四化
(安徽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230011)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寿州锣鼓研究
孙四化
(安徽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230011)
锣鼓是我国民间打击乐器中的主奏乐器,又是中国古代冷兵器时期战场上的助威武器。和平时期锣鼓是我国民间艺术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打击乐器。锣鼓的使用一直以来与地方民俗相联系。作为历史古城的安徽寿州,锣鼓音乐由来已久,是寿州历史文化发展的象征。基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将寿州锣鼓的历史、发展和艺术特征置于寿州古老文化中予以阐释,为寿州锣鼓现阶段的发展和传承提供参考。
文化人类学;寿州;寿州文化;寿州锣鼓
一、文化人类学的视野
文化人类学从文化视角来研究人类的一切活动,或者探讨文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在文化嬗变和发展中的作用。从文化人类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它与民族学、社会人类学在研究视野和研究对象上有着相通的地方。林耀华在其主编的《民族学通论》的导言中指出:“‘民族学’作为一个名词,起源于古希腊文,是一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学问。英国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美国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和当前合称的 ‘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无论从研究对象和范围来说,都基本上等同于民族学,彼此间也经常互相通用。”[1]1社区、族群的研究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范畴,包括其起源、发展和灭亡,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该族群(社区)的物质生产、人类活动、宗教和文化。对于族群(社区)艺术活动的研究,可以考察其宗教,也可以考察其独有的文化。本文所要关注的是沿淮地域内的艺术活动之一,春秋时期楚国都城寿县民间的一种民俗活动——寿州锣鼓。寿州锣鼓流行于以寿县为中心的沿淮河一带,它既是得胜锣鼓,也是扬威锣鼓。将它作为研究的焦点,必然要探讨寿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寿县为中心的沿淮百姓的生产生活以及民间习俗。也就是说,本文是以古老的楚地文化为背景来研究当地民间锣鼓艺术的形态和文化内涵,并以此作为实例来探讨当前现代化进程高度深入的大背景下,古老民间艺术传承及发展的路径。
二、锣鼓音乐艺术研究的概况
当前学术界对地域文化的研究逐渐升级,关注地域的民俗、地域的艺术形式,追溯其起源与流变,思考其在当下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以民间艺术活动中的打击乐形式——锣鼓为例,研究者大都聚焦藏族、佤族和傣族等少数民族的鼓文化,以及汉族族群中的中原鼓韵、江浙一带“十番锣鼓”等。纵观前人的研究成果,具体涉猎的研究领域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锣鼓音乐形态的研究
锣鼓是打击乐器,纷繁复杂的节奏类型、迷幻般的音乐调式体系是锣鼓敲击时的音乐表述。速度的快慢、调式的变换表达了不同场合的不同情绪。傅利民、何顺清的论文《丰城花钗锣鼓音乐形态分析》选取江西丰城县的花钗锣鼓为研究对象,从其音阶、调式、结构、配器、演奏方式等诸多方面加以分析,目的在于揭示丰城花钗锣鼓的地域特色和音乐个性,并在文末点明丰城花钗锣鼓音乐的不断发展与当地丰富的民俗文化分不开。
(二)从仪式中考察锣鼓音乐的艺术特性
民间的仪式活动从全国来看虽各有特色,但相同之处在于仪式活动大都离不开打击乐的参与。也就是说,锣鼓艺术与民间的仪式活动密不可分。各地的民俗节日、祭祀仪式、婚嫁仪式、丧葬仪式等民间礼仪或宗教活动需要有锣鼓音乐来营造氛围。商文娇的论文《青海民和土族纳顿节锣鼓音乐艺术研究》在青海民和土族纳顿节这一民间节日活动的场域内考察锣鼓音乐艺术,指出青海民和土族纳顿节仪式中的锣鼓音乐始终贯穿其中,对仪式进展起到引领作用。此时的锣鼓音乐不仅是舞蹈和民俗表演的伴奏,更是青海民和土族纳顿节民俗文化内涵的象征。
(三)借考察锣鼓音乐研究地域传统音乐文化
锣鼓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不同,锣鼓音乐的外在表现也不同。此时的锣鼓音乐既体现着地方原生态音乐的特点,又是地域民间文化的外在表征。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在他的著作《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一书的自序中指出:“音符是记录音乐的符号,曲式调性是建构音乐的手段,声音也只是音乐的载体,而音乐的真正源泉是人和他的文化。”[2]1因而学术界一直以来就有以音乐载体为“点”来考察地方文化这一“面”的研究思路和视角。杨永兵的论文《晋南丧葬锣鼓考述》基于陕西锣鼓音乐传统文化这一大视野,选取晋南丧葬仪式中的锣鼓音乐为考察点,用乐种学和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解析,阐释晋南农村传统的丧葬仪式音乐文化。
(四)地方性锣鼓音乐的民族志调查和研究
民族志调研是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强调人类学研究的实证性。他在特罗布里恩岛滞留长达两年多,期间对岛上土著居民进行田野调查,《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是他此次人类学研究的实践成果。马氏这一方法论对后世人类学研究有深远的影响。当前音乐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强调实地调研和民族志阐释。河北师范大学田超超的硕士毕业论文《近代耍锣鼓音乐调查与研究——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耍锣鼓为例》对重庆石柱地区土家族耍锣鼓音乐进行文献调查和实地探访,考察了耍锣鼓音乐的乐器组成、曲牌、曲式调性、演奏团体、音乐功能,阐述了耍锣鼓音乐与重庆“打溜子”音乐的共性和其自身的特性,并为耍锣鼓音乐的传承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文为研究少数民族地区锣鼓音乐提供了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锣鼓音乐艺术的研究理论丰厚、视角多样、成果丰硕。但也不难发现,目前对锣鼓音乐的研究主要关注的地域有中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江浙、珠江长三角地区等,作为淮河流域的安徽,对其境内的锣鼓音乐研究成果很少。从历史上看,安徽文化底蕴深厚,民俗活动众多,民间艺术形式丰富多彩。以寿州锣鼓艺术为例,其发展已有千余年历史,是春秋时期楚文化的遗存。寿州锣鼓艺术值得学术界关注和研究。
三、寿州锣鼓艺术的发展历史
(一)寿州城的历史地理
寿州现称寿县,隶属淮南市辖区。古时寿春在此地域内,但非现在寿县的全部地界。寿春是春秋时候楚国的郢都。《史记·楚世家》载:“(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241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王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秦将王剪、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据此可知楚国在寿春共建都19年。[3]26从历年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中发现,寿州城的文物古迹丰富,地域文化深厚。
寿州位于安徽的中部、淮河的南岸,处在江淮腹地、亚热带季风气候带的北缘。大豆、稻谷和棉花是寿州的主要农作物,尤其是大豆,年产量丰厚,因而与大豆相关的衍生品——豆腐成为寿州有名的土特产,寿州也成为豆腐的发源地。寿州便利的交通、丰富的农作物和优良的地理条件使其自古以来是养兵秣马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清光绪年间编写的《寿州志》描绘寿春镇“控扼淮颍,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东连三吴之富,南引荆汝之利,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许,水路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有淮肥之固,龙泉之陂,粮田万顷。”[4]103寿州在军事意义上的重要性使寿州古城建筑颇具规模,从而身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安徽省三大古城之例。
(二)寿州的文化
作为楚国的都城,寿州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是中国古代楚人所创造的一种有自身特征的文化遗存,具有一定的时间范围、空间范围、族属范围的文化特征内涵,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161寿州处淮河流域腹地,这使得寿州地域文化融合了中国南北方的文化特点,主要表现为崇礼重教、爱国忠君、豁达明朗、包容万象、勇于开拓。从历年考古的成果来看,楚国铸造工艺的精湛和文字艺术的精美足可以印证楚文化的繁荣和它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的地位。
(三)寿州的民间艺术
寿州的地域文化受到南北方文化交流的影响,既有北方直爽、重义气、好争斗的民风,又有南方崇文尚礼、文质彬彬的风格。这种刚柔并畜的复合型地域人文特征是寿州独有的地域文化特点。尤其是寿州彪悍的民风在民间艺术中多有体现。例如寿州的锣鼓艺术,铿锵有力的敲打配合一定的武术表演,展现了寿州人自古以来习武尚健的习俗。
四、寿州锣鼓的艺术特征
寿州地域文化融汇了南北方地域文化的精华,且杂糅了淮河腹地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寿州锣鼓音乐的艺术特征上多有表现。寿州锣鼓音乐的曲牌、调式、旋法等保留了淮河一带锣鼓音乐 “十八番”“凤凰三点头”的优秀谱法,且受到中原和河北一带锣鼓音乐的影响,铿锵有力,气势宏大,又有江浙一带“十番锣鼓”音乐细腻和婉转的特点。现存寿州锣鼓音乐的主要代表曲目有 《长流水》《十八番锣鼓》《拾玉镯》《兔子趴窝》《雁落沙滩》等,主要的演奏乐器有鼓、手鼓、钢锣、钹等。当前寿州锣鼓已经成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曹玉海是其代表性传承人。
(一)寿州锣鼓音乐的织体与旋法
寿州锣鼓具有织体丰富、旋法跌宕起伏的特点。乐句之间环环相扣,强弱对比明显。代表性乐句多次穿插、不断反复,给予整首锣鼓音乐气势磅礴、翻江倒海之势。以《十八番锣鼓》音乐为例,其代表性织体分布如下。
一咚一咚哐|一咚一咚哐个叮哐一叮哐|咚|哐咚哐咚哐一咚哐|(敲3遍接绞丝);
咚|咚|哐咚哐|一咚一咚哐|一咚一咚哐|一咚一咚哐个叮哐一咚哐|咚(敲3遍接绞丝);
咚咚咚|哐哐咚咚哐|咚咚|哐咚哐|一咚一咚哐个叮哐一咚哐|咚|哐咚哐|咚哐一咚哐|(敲3遍接绞丝);
咚咚一咚一咚哐|咚咚一咚一咚哐|咚咚一咚一咚哐|咚咚哐|咚咚哐|咚咚哐|(停半拍),哐咚哐咚咚一咚|。
织体分布中的“绞丝”原指缫丝厂将丝片绞成丝束,这里指锣鼓环环相扣、连接有序的打法,它使各鼓点错落有致地排列、顺接,鼓声和锣声相互交织。从《十八番锣鼓》的织体分布来看,该锣鼓音乐织体较为复杂,具有代表性的织体样式不断反复,锣鼓演奏一起一伏,节奏强烈,气氛热闹。
(二)寿州锣鼓的演奏样式
寿州锣鼓是安徽民间打击乐的传统形式,往往与花鼓灯音乐相得益彰。寿州锣鼓演奏形式的基本样式较为单一,主要是一领众合。领者可以击鼓也可以敲钹,一般居于演奏阵式的中间,其他演奏员或击手鼓,或击大鼓,或敲手钹,围住领者演奏,期间众人还穿插各自武术类动作,增添演奏的氛围,表现出淮河腹地百姓强健的体魄和浓郁的皖北文化氛围。
寿州锣鼓在演奏过程中的起承转合也有讲究。为了突出锣鼓音乐的文化意蕴和寿州地域的人文特征,寿州锣鼓多为慢敲鼓起、击钹加速、锣鼓相间、快慢得当。如代表曲目《长流水》,总体音乐气氛是欢快、节奏感强。但是在演奏过程中,该曲的两节演奏速度截然相反。第一节较慢,且慢起音;第二节明显比第一节速度快,气氛热烈。代表性织体分布如下。
鼓起(慢):一咚一咚一咚咚|哐哐咚匡一咚哐|哐哐咚哐一咚哐|(慢)哐个咚咚|一咚一咚哐咚咚|一咚一咚哐咚咚|哐个咚咚|哐个咚咚|哐哐|咚咚|咚咚|哐哐咚哐|咚哐|。
结语
寿州锣鼓有其自身的艺术特点,它体现了淮河腹地地域文化的特性。寿州锣鼓与皖北民俗活动密不可分,是沿淮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当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文化的不断繁荣,寿州锣鼓的艺术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但是它的文化精髓没有丧失,等待寿州锣鼓的是新的、光明的发展前景。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洛秦.音乐中的文化和文化中的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
[3]丁邦钧.楚都寿春城考古调查综述[J].东南文化,1987(2).
[4]郭福亮.从《寿州志》记载论寿春镇居民的观念[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4).
[5]丁继龙.试论寿春楚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J].今日中国论坛,2013(12).
责任编辑:吴 夜
A Study of Shouzhou Drums and G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Sun Sihua
(School of Arts and Media,Anhui University,Hefei230011,China)
The drum and the gong are not only the main accompanied musical instruments among China’s folk percussion instruments,but also the cheering weapons in the period of cold arms in ancient China.In peace time,they are indispensable to folk art activities in China.The use of drums and gongs has been linked to local customs.There’s a long history of beating drums and striking gongs in Shouzhou, a historic city of Anhui. They are symbol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This artic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culturalanthropology,discussesthe history,development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houzhou drums and gongs in the scope of ancient Shouzhou culture to offer references for their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at the present stage.
cultural anthropology;Shouzhou;the culture of Shouzhou;Shouzhou drums
J632.7
A
1672-447X(2016)02-0020-04
2015-12-15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Q2015D92);安徽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378);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SK2015A261)
孙四化(1980-),安徽寿县人,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作曲及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