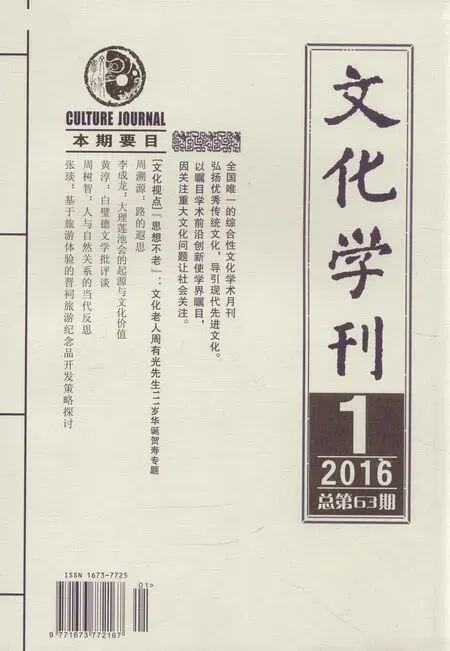《长恨歌》历史叙事中的个体意识
2016-03-16丁晓莹
丁晓莹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文学评论】
《长恨歌》历史叙事中的个体意识
丁晓莹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长恨歌》塑造了王琦瑶这一具有个体意识的人物形象,并将其形象模糊与符号化,通过叙述其日常生活解构以往宏大历史叙事模式。在个体意识与社会历史关系的内在缠绕中,个体意识在历史中深化成长,看似边缘化的个体生命与意识,始终存在于社会历史体系中,在王琦瑶的个体意识发展演变中,可以窥见其潜在的现代性特质。
历史叙事;个体意识;符号化;现代化
《长恨歌》是王安忆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当代文学史上典型的历史叙事文本。小说体现了历史洪流中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深化。作者从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个体出发,通过描写人物在历史潮流中的个体意识来反思个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王琦瑶是作者创造的具有个体意识的人物符号,其个体意识通过琐碎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来。宏大的主流历史叙事在这篇小说里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弄堂、公寓和里巷里,小家碧玉似的生活气息,以及江南水乡浓厚的地域气息。这是王安忆对传统历史叙事的一次彻底解构与颠覆。在这种日常化的边缘叙事背后,还潜藏着作者对上海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思考与反思。
一、王琦瑶—是女性,更是个体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一位女性,作者却始终都没有具体描述过其外貌与神态,其形象始终是模糊的。读者只知道她是一位上海小姐,像普通人一样,经历过人世的沧桑,最终被人杀害而死。她是一位深藏在上海闺房中的小姐,正如文中所说的“王琦瑶是上海典型的弄堂的女儿”,[1]上海的每个角落都是“王琦瑶”,王琦瑶就是上海。王安忆自己也曾说过:“王琦瑶的形象就是我心目中的上海,在我眼中,上海就是一个女性形象。”[2]在王安忆看来,王琦瑶就是上海,而上海是一位女性,所以王琦瑶这个人物设定也必须是一位女性。笔者认为,王琦瑶是一个符号化、模糊化的人物形象,并没有一个确定形象,但却也是一个生命个体,而这样一个生命个体却可以代表整个上海,王琦瑶的一生便是上海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显然,这样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形象,几乎没有什么女性意识可言。在王琦瑶与其一生中几个男人的感情纠葛中,她始终没有站在与男性的对立面上,大部分时候都顺从命运的安排。在与李主任的交往中,她始终逆来顺受,甚至认为像李主任这样的风云人物就该由他决定一切,王琦瑶只需要顺从一切安排。在王琦瑶看来,程先生虽然一心一意地爱着自己,可是却“太女人气”,程先生对自己的温存是一种女性化的表现。她所崇拜的是像李主任一样的大人物,她渴望李主任对自己负责,甘愿臣服于男权之下,因而她心甘情愿地接受李主任给她的爱丽丝公寓。由此可见,王琦瑶是一个典型的小女人,渴望被呵护与保护,而《长恨歌》里的男性人物几乎都是比较柔和,有女性化的气质。这些都不能构成女权主义中女性与男权之间的对立关系。[3]
王安忆在谈到妇女文学问题时曾表示自己并不是女权主义作家。在她看来,中国的男人很不容易,中国女性与社会对男性的要求太高:男性既要有男子汉气概,又要温和。王安忆本身并没有女权意识,她认同男权社会的合法与合理性,因而其笔下的王琦瑶,不会是一个有女性意识,或是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缺乏女性觉醒意识的女人。
笔者认为,王琦瑶始终是个体生命的典型代表,王安忆在《长恨歌》里要探讨的是作为生命个体的王琦瑶与风云变幻的大上海之间的纠葛,而不是女性意识与男权社会的二元对立。
二、历史解构中的个体意识
把王琦瑶符号化,运用人物的模糊性来解构国家叙事模式,是《长恨歌》的重要叙事手法。在《长恨歌》里,上海的每个角落里都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电影的是一群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4]王琦瑶也可以不叫王琦瑶,可以叫其他任意一个名字,王琦瑶只是一个符号的指称而已。作者通过将王琦瑶这一人物符号化来解构宏大叙事的典型人物塑造。王琦瑶是上海的典型代表,也是历史叙事中的核心人物,而她的形象不再是高尚或是有牺牲精神的高大全人物,而是处于历史边缘的小人物。
看似与历史无关的王琦瑶却又与历史紧密相连。王琦瑶的个人意识带有浓郁的都市小市民色彩。在平安里的那段漫长岁月里,每天除了给人打针以外,几乎就是跟严家师母,毛毛娘舅等打牌,或是小聚。这些充满琐碎生活化气息的场景表明作者刻意追求解构宏大叙事。在这种散文化的叙述与流言式的表达方式背后,是作者对个体生命意识与社会历史关系的深刻思考。细读文本发现,王琦瑶的个人历史与当时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可以说王琦瑶的悲剧是从李主任离去后便杳无音信开始的,然而,李主任的消失又与时代相紧密关联。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李主任死于非命,他的死也改变了王琦瑶的人生轨迹。表面上看,王琦瑶个人生命的意识流动似乎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毫无关联,可实际却是王琦瑶的个人命运与生命意识始终受到社会时代和环境的影响。王琦瑶这个看似独立的个体生命,其实也被包含在巨大历史洪流中。个体生命和意识始终摆脱不了社会历史的年轮。正如王安忆自己所说:“王琦瑶就是上海”。[5]她代表的是上海的形象,因而在作者那里,王琦瑶所具有的个体意识便是上海的历史沉淀和意识,这是其个体意识产生的根本所在。
三、个体意识中的现代性反思
《长恨歌》中王琦瑶所表现的个体意识十分隐秘与私人化,就像私人的秘史一样,其日常化的历史叙事中暗含着许多现代性因素。笔者认为,其中夹杂着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反思与思考。在王琦瑶进行“空间移动”的人生中,从闺阁到爱丽丝公寓,再到邬桥,再到平安里,王琦瑶已无形中被卷入现代化的浪潮中。到邬桥外婆家的暂时躲避是安逸而又和谐的,可以说像邬桥这种从未被西方殖民主义污染过的地方,“才是人们真正的母体”,[6]在这未被污染的净土上,王琦瑶看到连阿二都要去上海追逐自己的理想,她便也鼓起勇气回来了。在现代化进程中,邬桥象征的是未必洗染过的原始净土,而王琦瑶始终要回到上海,则是王琦瑶作为生命个体的自然选择,同时也是现代化发展中个体意识的必然选择。[7]王琦瑶看惯了大起大落的上海魔都,也习惯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她最终选择回到里弄,继续她的闺院生活。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上海造就了王琦瑶,上海使王琦瑶成为“三小姐”,同时也使她最后因长脚的杀害而香消陨落。旧上海的时代过去了,王琦瑶的个体生命也结束了,她的个体生命与意识,始终受制于上海的世事变迁。王安忆认为,她对于王琦瑶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比较成功的,她所塑造的王琦瑶是勇敢的,面对旧上海的灭亡,新上海的到来,她选择了死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正如上海一样,勇敢接受现代性的挑战与洗礼。[8]笔者认为,作者所表达的并不是有些学者认为的对现实历史的逃避与隐逸,而是认为西方现代化对于上海、对于中国的冲击是一种必然,正如小说开头预示着王琦瑶的死亡一样,而面对这种挑战与危机,需要的是反思我们当前的社会体制,并从容地迎接挑战。
四、结语
《长恨歌》重在强调历史潮流中个人的生活与发展,探索的是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王安忆所塑造的灵魂人物王琦瑶,是一个已被符号化与模糊化的人物,虽不像先锋作家笔下人物一样具有抽象性,然而,王琦瑶的形象是具有模糊化的象征性的。这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一种颠覆与解构,通过对王琦瑶进行个体意识的描写和塑造,在平和冲淡的表层叙事中还暗含着作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考。笔者认为,王安忆在《长恨歌》里想要表达的是,王琦瑶的辉煌时代已过去,薇薇的时代已来临。然而,上海的历史中会有无数个“王琦瑶”,也会有无数个“薇薇”。[9]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化进程,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历史发展潮流,而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历史洪流中个人的生存状态与个体意识的发展。
《长恨歌》是王琦瑶这位上海小姐个人的私密史,同时也是窥探上海历史进程的一个隐秘窗口,只有透过这个窗口的表层事物,抓住其核心本质,才能真正窥探魔都上海的“芯子”。
[1][4][6]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7.38.134.
[2][5]王安忆.重建象牙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207.207.
[3]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78.
[7]王金胜.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23.
[8]艾科.符号学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420.
[9]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56.
【责任编辑:王 崇】
I207.42
A
1673-7725(2016)01-0076-03
2015-10-05
丁晓莹(1990-),女,山东淄博人,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