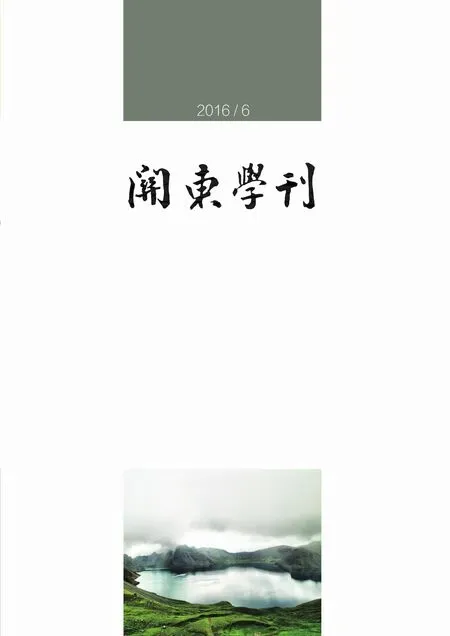阎连科小说的狂欢化文学叙事研究
2016-03-16李缙英
李缙英
阎连科小说的狂欢化文学叙事研究
李缙英
本文从仪式与庆典、复调与杂语、降格和戏仿等方面,分析阎连科创作中内蕴的狂欢化理论和酒神精神内质。狂欢化的文学叙事,具有“民间”和酒神非理性精神的消解、解构精神,可以颠覆正统、主流,消除意识形态的遮蔽,在话语/文学中寻觅政治历史文化的“真实”。
阎连科;狂欢;酒神;复调;极致化
阎连科小说的创作中存在着“仪式”“庆典”、复调、降格等狂欢化形式,狂欢化的叙事形式体现了他的怪诞现实主义风格①巴赫金认为,“怪诞现实主义”是民间诙谐文化所固有的特殊形象观念,其审美特征:一是夸张主义和过度性;二是降格,即贬低化和世俗化;三是深刻、本质的双重性。参见\[苏\]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钱中文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页。,而且体现了人性的非理性精神和“民狂”文化的特质,以及以民间话语消解正统、权威的颠覆力量。
一、“仪式”与“庆典”
阎连科小说中的许多场景与“仪式”“庆典”的象征化、狂欢化具有相通之处。巴赫金认为,狂欢节庆典是凝聚着文化积淀的民俗,不仅具有独特的外在特征,如全民性、仪式性(笑谑地给狂欢节国王加冕随后脱冕,还具有换装仪式)、颠覆等级、插科打诨(表现在语言上为模拟讽刺、嬉笑怒骂、滑稽改编)等特点,还具有意蕴深厚的内在特征,如狂欢化的世界感受、狂欢的双重性和欢快的相对性等。②夏忠宪:《内容提要》,载《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页。而庆典时刻以欢乐高潮的顶点是悲剧的突然呈现为基本模式,庆典正是通过仪式化、游戏化的方式把象征强调出来,是小说重要的隐喻和象征途径。
“庆典”和“高潮”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承载了内结构的作用,与外在的形式相比更含蓄隐秘也更具有美学意义。其中《受活》中的“受活庆”、柳鹰雀的“加冕——脱冕”等,是最典型的仪式、庆典的运用。受活庆是欢庆丰收的盛大仪式,往年丰收才办的受活庆,在受灾之年被柳鹰雀主持操办起来。狂欢节是人民大众的节庆生活,是诙谐因素构成的另一种生活;但官方节日跟民间节日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它违反、歪曲了节庆的真正本性。①[苏]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狂欢节是民间的诙谐文化,具有非官方性、全民性、双重性、原初性和乌托邦性等,能够发挥解放作用、反乌托邦的乌托邦效果和对话的功能。但由于狂欢节本身(包括其他民间诙谐文化)的非组织性和自发性,很容易成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
在《受活》中,受活庆借助了各种民间诙谐文化和文艺形式,在类似酒神的民狂魔力下,人与人暂时搁置分歧团结一致,人与自然和解,连奴隶也成为自由之人。每个人在超自然的魔力下欣喜若狂、居高临下,在这种状态中,艺术作为放纵之力支配着人,以群体性的否定个体的方式实现众生狂欢。在受活庆上首先上演的是名角草儿的哭戏,以残疾媳妇的身份边哭边唱,引得一众受活人忘我地边哭边笑。受活人自己的表演更能体现狂欢化的酒神精神,他们以“绝术”掩盖或忽略自己的残缺,以舞台上的群体表演解除个体苦痛,在痛、乐、狂的癫狂状态中寻求慰藉。在此,民间艺术形式和诙谐文化创造出一种痛苦与狂欢交织的癫狂状态,展现出人们内心的非理性精神,个体通过自我否定而复归世界的本体,体会前所未有的归属感。这些都是对自身残缺和荒诞处境的另类反抗方式。
《受活》不仅是黑色幽默又是红色荒诞,其主要的文本策略是把荒诞推向极致。②刘再复:《中国出了部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在受活村,夏天下热雪,冬天晒酷日,桃树上结红枣,残疾人有比圆全人更厉害的绝活,这些鬼话连篇的描绘在受活庄都成了事实。只要是跟受活、受活人有关的,都具有了民间荒诞不羁、魔幻、鬼魅和另类的色彩,时间和精神都错乱了。受活庄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使“历史”在轮回中消解,农历纪年与西元纪年的错位,使历史事件祛除意识形态的遮蔽,显现出陌生化、个人化的特点。而那些“宏大叙事”的“历史”,其实都只是被赋魅的、被利用的标志性话语事件而已,对于受活庄人或边缘化的农民来说,历史和政治只是生活和生活的变动而已。
通过菊梅生四胞胎女儿、建国、女儿们的年龄等民间记忆,可以大体推算出中国当代历史的“大纪年”事件和民间历史所处阶段的官方命名。受活闹剧的开端,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对人们的影响,而柳县长带领受活绝术团去赚“购列款”大约在世纪末或新世纪初……日常化、陌生化的他者化关照,使历史、政治的荒谬、虚伪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和象征中显露出来,逐渐明朗清晰。
这场发生于世纪末或新世纪初的“世纪闹剧”,由政治权力操纵农民残缺的身体,以市场经济的形式,把人的恶魔性欲望都释放出来,民狂精神肆意狂欢。这场大型的“庆典”,由于政治权力和金钱的染指而成为变质的庆典。
权力把茅枝婆的“政治乌托邦”消解掉,柳县长作为政治权力的代表接管受活。他用枪打散云雾,接着主持受活庆,发表了封建主义父母官式的讲话,为人们发赈灾救助款并接受受活人的磕头跪拜。这一系列行为,其实正是他凭借权力代表的身份,统治受活村及全部残疾人的“加冕”仪式。
而柳县长的农民思想和封建帝王意识,现代革命思想和癫狂权欲,以及阴险歹毒的计谋手段——强奸菊梅、抢劫虐待受活人、让人强奸四个儒妮子,这些思想行为的两面性、反复性,使他之前高傲、正统、权威的形象通通崩落,他亲手为自己“脱冕”,走下了神坛。在巴赫金看来,国王加冕脱冕仪式的基础,是交替和变更的精神、死亡和新生的精神,这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狂欢节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由此可以说它表达了狂欢式的思想。①曾军:《民间诙谐文化视角下的莫言的民间写作》,《语文教育》2012年第12期。柳县长和其他圆全人在残疾人面前的对比愈发明显,仪式上表演“加冕—脱冕”的狂欢就更为隐秘而恶劣,这不仅是人性的虚伪,还是权力、体制异化人的表现,意识形态和政治被嘲讽、解构。
金钱和欲望的狂欢也并未放过受活,使人们幻想出“市场经济/金钱的乌托邦”,而金钱、权力驱使人性的罪恶本性,又把它转变为人性屠戮的大刑罚。个人的政治狂想引发的大悲剧,以狂欢庆典后的悲剧骤然收场,最终侵蚀全国的社会现象转嫁到了受活人(农民的代表)身上,化为乌有——农民永远都是政治错误、历史灾难的实际承受者,而灾难的发起者就以历史、政治失败者的身份,消失在历史和人民群体中。
二、“复调”“杂语”
在《受活》《坚硬如水》《乡间故事》和《四书》等小说中,存在着不同话语、不同声音的杂语共生现象。巴赫金认为,小说只有利用社会性的杂语和个人性的多声现象,表现所关注的题材和整个实物、文意世界,才能更好地显现作者的创作意图。②\[苏\]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钱中文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41页。杂语就是多种话语类型的集合,一部杂语小说就是一个杂语现象的文本表现。
多种语言、话语代表了不同的身份、立场和权力,方言土语、官方普通话、意识形态的“毛文体”、欧式白话的“翻译体”等语言,以及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等,这些不同的语言、话语的众声喧哗也就是话语权的争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杂语”和“复调”,就是反抗具有政治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具有言说资格的精英知识分子话语的最有效方式。
实际上,“话语”不仅表现在人物、文体的语言方式上,有时人物身份、命运本身就隐喻了不同的话语。在《炸裂志》中,孔东德的四个儿子在“走梦”占卜人生时,分别走向了四种人生方向,他们的不同身份、立场和命运,分别代表了知识分子话语、发展主义话语、国家主义话语,以及人性话语撤退到宿命论的变化。③陈国战:《〈炸裂志〉:碎裂的历史主体及其当代境遇》,《文艺研究》2015年第2期。在小说中,不同话语的“杂语”,引进了各种各样的语言,也就引进了不同的身份、社会阶层的视角。而这些视角虽然都是作者的意向投射,但在投射过程中会产生变形,这就意味着文本的呈现方式存在着隐喻。
除了杂语,还有复调的运用。阎连科擅长借助民间想象并发挥个人想象进行创作,有关生死、轮回、阴阳和人鬼的想象,体现在叙事上就出现了“人鬼对话”和“死人言说”,这也是复调狂欢形式的重要表现。叙述对象或叙述者的非理性、超现实化和魔幻化,使人与鬼、理性与非理性、现象与本质、真实与虚构共时性呈现,共同发声,展现出世界的原初、本真状态。
民间想象的其中一种,就是经验与虚构的融合,如人、鬼、神互相转化,天堂、阴间、人世互相沟通,并且各种鬼神形象都具有人性化的特点。阎连科借鉴了鲁尔夫的《佩德罗·巴拉莫》,解决了人和鬼的界限问题,使得人鬼混杂。阎连科开始有意识地借助鬼魂、魂灵穿梭于阴阳两界的言说,是在写中篇《寻找土地》时,之后开始广泛地运用复调化的“死人言说”和“人鬼对话”。以死亡视角叙事的有《自由落体祭》《鸟孩诞生》《乡难》《生死老小》等。由于鬼魂的言说和叙述,在结构上顺序、倒叙、插叙随意倒转,小说不受传统情节结构的束缚,尽量呈现生活断片式的混乱、无序状态,使梦呓、梦魇、回忆、迷乱和潜意识想象等也能够发声,作为人物形象或描写对象平等地言说。
除了这些,阎连科还将人鬼对话、死人言说等语言的复调化狂欢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形成真正贯穿小说整体结构的“死人言说体”。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讲述的是马光死后的灵魂来向“我”讲述他与阿琴的爱情悲剧故事。这部中篇小说,是以马光亡灵的第一人称叙事、人物“我”的第一人称叙事和叙事者的第三人称叙事三种叙事交替使用的,亡灵叙事更为叙事带来诡异的效果。第一人称叙事本身就具有“回忆”的似真如幻的特点,而马光这个叙述者的鬼魂身份和特点,更使小说的复调化带有超现实主义的魔幻意味。这种叙述方式上的真实感与死人讲故事的虚构、荒诞结合在一起,是一种阎连科所谓的半因果、半逻辑的叙述,小说以众声喧哗的现实与虚构呈现别样的真实。
《耙耧天歌》因为尤石头这个鬼魂及鬼魂叙述,而变成了众鬼狂欢的叙述。尤石头隔代遗传给孩子们的遗传病,像“宿命”一般以血的稳固笼罩着无法逃脱的子女。尤四婆为满足孩子的食欲、性欲和生命,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重担,这种单方面的付出,在贫穷、饥饿、疾病和残缺以及父权缺失的情况下达到极端,而孩子的饥饿、性欲、结婚生子繁衍后代的强大非理性欲求,却时时刻刻催逼着她。
尤石头在得知孩子们患的是隔代遗传的羊角风那天,就因内疚与恐惧“被未来的日子吓死了”。可见男女对抗压力的能力是不同的,母性在承受苦难方面具有惊人的天赋和本能,而这种母性具有圣母救赎的性质;而男人作为罪愆的根源却用死亡逃避了应有的责任。他们的生死观就是生而受罪,死而享福,活着就是一场“罪与罚”“受难与救赎”为主题的生命之旅。
尤石头作为“缺席的存在”,在这个充满痴言怨语、极端非理性和人鬼混杂的小说中以鬼魂的身份出现。
尤石头鬼魂出没,尤其在尤四婆抚养照顾孩子,为他们寻找配偶的生活中经常出现。尤四婆在幻想中与死去的男人对话,三妞指出:“没人你跟谁说话呀”,老人也说她自言自语,但全人女婿却说他见了鬼,还跟他说过话。尤四婆子与死人对话可以解释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现实与理想化的对话,从科学角度也可以解释为尤四婆精神分裂的双重人格之间的论争。但当孩子们喝了婆子的脑汁、头骨熬的汤之后全都成了全人,替婆子守孝哭丧时,婆子又亡灵出没,告诫他们这痴傻病还会遗传下去,只有至亲的骨血才能拯救,这又将逃脱出残病的孩子们坠入新一轮还债的命运循环。这种人鬼对话的多声部复调,以狂欢、夸张、荒诞的手法和形式,以非理性的声音、视角、形象和逻辑,展现荒诞的真实,能够超越表面化的真实而达到情感的真实和逻辑的真实。
阎连科注重阴间天宫、鬼魂亡灵等阴阳之物,是由于他对生命存在的探问。人们对死亡有不同的想象和态度,最普通又最理想化的是否定死亡的终极性,想象死亡之外另有一种状态存在——复活、轮回或超生,以及通常所说的从现世超渡到死亡的空间:阴曹、天国和地府。面对死亡,中国人乐意相信生死轮回和善恶有报的观念。阎连科正是通过民间鬼神和佛道信仰、观念的演绎,来实现本土化、个人化的生死的魔幻表达。另外,把魔鬼泛化是中国恶魔性小说的一个艺术手法,①陈思和:《“文革”书写与恶魔性因素:〈坚硬如水〉》,载《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2-425页。也是阎连科借用鬼魂言说、亡灵叙事表达阴阳沟通、人鬼对峙效果的民间文化基础。死人言说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窠臼,使叙事拥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叙述自由,而陌生化、魔幻化的叙事策略使作品产生出审美意义上的震惊。
总之,阎连科小说的“杂语”体、人性分裂和人鬼对话、死人言说等都是复调化狂欢的形式,正是在不同的语言、言语的喧哗中,在人物的精神人格分裂、阴阳转换、人鬼沟通中,达到复调的狂欢化效果,在非理性与理性声音的对峙、辩驳中,获得对抗现实的审美化人生,呈现世界的碎片化、荒诞无稽的真实状态。
三、“降格”化
阎连科的小说中充满形而下的肉体、物质层面的形象和物象,还有丑陋卑琐的人体和高高在上的正统者、掌权者的崩落,这种肉体化的“丑陋”和类似于脱冕的“崩落”就与降格化有关,即把一切精神性的、抽象化的、理想化的和高级的东西转化为物质——肉体层面。②\[苏\]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钱中文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第24页。在阎连科的小说中,降格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怪诞人体(形象)和“弱智化”。
怪诞形象以新和旧、垂死和新生、变形的始末等对立两极同时出现的形式显示,③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8-110页。阎连科作品中的怪诞形象,不是只有受活庄的聋哑瘸残们,他对怪诞形象的展示不胜枚举:耙耧山脉上性欲萌动的三傻妞、四呆儿的丑态百出,是一种丑陋展示,尤四婆开脑分骨、死不得全尸,更是诡异震惊的尸骨陈列;先爷瘦骨嶙峋的身体,在玉米根须魔爪的吸噬、腐蚀下,在日月风土的侵蚀下,成为一具残损的骷髅,骨殖上暄草包一样的瞎狗是他坟头上招摇的草;在三姓村,要么是卖腿皮得溃烂脓疮,要么是卖肉得性病、妇科病的霉臭腐烂,就连灵隐渠的水都是恶臭漫天的污水。“残缺之躯”一直是阎连科小说的重要形象,也是“怪诞人体”形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怪诞的元素狂欢化地充斥在阎连科的作品中。这种极端地处理身体的方式,唤起了当代人对“身体”,尤其是对农民身体的感知和强烈的残酷感、恐惧感。除了肉体上的丑陋不堪,还有人性的毒恶:在育新区人们为了自由背叛、出卖他人,为了食物糟践尊严、蹂躏身体,为了活下去可以同类相食,堕为兽类。人被降格为肉体——物质层面,以外在丑陋、残缺,内在恶魔、疯狂的形象呈现狂欢化的解构和讽刺。
怪诞人体形象确实是夸张、讽刺的,但却不是以讽刺为目的的否定性夸张。这种以极端方式自我否定的存在方式,其实是对世界病态的变相鞭挞,只有世界荒诞不羁,生存无可留恋让人生不如死时,人类的恶魔性才会对自己、他人的肉体残酷蹂躏。这种肉体的降格化就是人类身体和人性的狂欢,当群体性、集体化的丑陋、怪诞、自虐的肉体出现时,就以疯子似的非理性方式宣扬肉体的形而上哲理,进行无声的狂欢化的喧哗,并对“失语”进行形而下的反抗!
除了怪诞形象,人物形象的“弱智化”倾向,也是一种“降格”,也是狂欢化的形式。例如《黄金洞》的傻子视角是对因果逻辑关系、理性思维的解构,二憨的第一人称叙述了爹、大哥、桃和他自己关于食色与黄金欲望的诡谲故事。这一叙述者的身份和特质,使人性的欲望散发出与其本性相似的神秘性和宿命性,使观察视角和叙述话语下的全部人物,蒙上了非理性的癫狂和欲望压抑的轰鸣骚动,人性的动物性成了压倒性的神秘力量操纵着整个世界的人类;《丁庄梦》的儿童式的视角,导致个人记忆与历史时序的错乱,以及现实生活的如梦如幻状态,并借助梦、回忆、狂言、幻想等非理性方式把真实的人性表现出来。
在狂欢化小说中,通常是利用疯子、傻瓜、孩童、局外人等形象作为主人公、叙述者或关键人物。阎连科小说的傻子叙事、婴童叙事、亡灵叙事里,承担叙述者角色的人物具有“弱智”或“非理性”的特征,这使整个小说的叙述视角变得生物学化了。以降格的方式,把弱智化视角内的人物同样降低到欲望层面,也即人性层面,以此考察人类原始欲望作为历史之前进动力的实质①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5页。。小说人物形象、叙事者的“降格”,为小说营造了返璞归真的、充满反讽意味和喜剧意味的、犹如假面舞会式的狂欢化叙事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物的怪诞化、残缺化和弱智化的“降格”,不但没有降低作品的思想含量,反而增加了。降格以极端的拉低方式,祛除意识形态或所谓文明的遮蔽,彰显人的狂欢和恶魔性的肆无忌惮。
四、“戏仿”化
阎连科的创作中有许多看似模仿既有文体、典型形象、情节模式等的作品,如“东京九流人物系列”,是在一系列洛阳民间人物传记、传说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半文人化半民间化的再创造产物;《潘金莲逃走西门镇》,是对古典章回小说《水浒传》《金瓶梅》中潘金莲故事的“现代乡土版”改写;《受活》具有明显的“桃花源”或“乌托邦”的意味,但却是“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述;而《为人民服务》的书名本身就是对革命伟人话语的挪用;《四书》也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经典”的借用……而这些模仿却具有明显的嘲讽、解构的意味,这就是“戏仿”。
戏仿又称滑稽模仿,是对严肃事物或严肃文体进行模仿,强化内容与形式的不协调,②曾军:《民间诙谐文化视角下的莫言的民间写作》,《语文教育》2012年第12期。既可以指对体裁的戏仿,也指对情节内容、话语语言或人物、仪式的戏仿等。在狂欢化叙事中这几种戏仿形式和戏仿因素都存在,阎连科运用戏仿的目的就在于嘲笑和讽刺。
在《坚硬如水》中,不仅有“文革体”在文体体裁方面的戏仿,也有对“毛文体”戏仿化、复调化形成的话语狂欢,还有内容上对传统性爱故事的戏仿,而最核心的是对“革命”和“历史”宏大叙事的戏仿和消解。高爱军和宋红梅之间不仅是两情相悦、性欲驱使的情爱故事,其中还掺杂了革命造反、政治癫狂和性压抑变态等异质成分,是潜意识支配非理性欲狂的表现。他们一面痴狂地互相造神,一面拿性爱、屎尿粪便、污言秽语来亵渎他们的“革命对象”——程寺、牌坊和原来的权力拥有者,甚至能以强烈的欲望和怨恨激发起革命和性爱的热情。“革命”是由于他们称王封帝的封建残余思想和狭隘的私人恩怨而上演的“造反”,他们拿“文革”语言改造成嬉笑怒骂的语言漩涡,以狂欢化的“降格”、颠覆等级、插科打诨等方式,显现出历史与人性欲望的本质。
宋高二人将革命与性爱媾和在了一起。当他们选在旧坟窟意欲第一次结合时,高爱军恰巧被一节腐烂的尸骨头扎到。这一情节十分富有象征和预言意味,象征性的封建“遗骨”泼冷他们的性欲和热情,暗示了传统力量的破坏以及他们的结局。
高爱军是一个十足的“弑父者”,对长辈、权贵、正统人士具有强烈的反叛与忤逆心理。高爱军不仅假借革命和政治,将政治生活化或将生活政治化,把生活的鸡毛蒜皮都上纲上线,以此对抗他的敌人,还掩盖了与他有关的两宗杀人案。他担心妻子程桂枝因他自杀,会带给他带来道德舆论压力,借助桂枝砸毛像、撕语录的事实,而将她的死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自杀案”,桂枝的爹老村长为了替女儿伸冤叫屈也得了疯魔症。政治压倒道德伦理成为生活的显性准则,政治逻辑战胜一切,成为解释一切的“真理”,但“政治”打着理性、现代化的旗号,却是在人的非理性欲望的驱使操控下产生的。高爱军在模仿“政治”和“革命”的行为中,泄露了它们的欲望缘起和本质。革命在家庭矛盾、私人恩怨的形式下取得成功,却彻底消解了意识形态下所谓的革命和历史。
在铲除敌人王镇长时,我们发现,分产到户、为民着想的镇长成了“反革命”,而为私欲和个人恩怨才革命的宋高二人却立了功。“革命”和“反革命”,成了一对在荒诞逻辑中互相颠覆既定内涵和外延的意识形态术语。
高爱军和宋红梅以性爱庆贺他们的每一次革命成功,这非常类似于罗马、巴比伦的酒神节日,其核心就是癫狂的性放纵,天性中最凶猛的野兽径直脱开缰绳,乃至肉欲与暴行令人憎恶地混合在一起。高爱军以“革命离不开暴力”为理由,把撞见二人奸情并欲揭发的红梅丈夫杀死,把他的尸体埋在地道里的标语下,“地道”成为真正的隐藏秘密之所。而红梅丈夫之死却恰巧被一场暴乱掩饰过去——暴力是一切神圣事物的核心及秘密灵魂,耙楼山脉的暴力成为文明的暴力性象征,以极端的演绎表现出核心实质。①梁鸿:《神话、庆典、暴力及其他》,《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如果说高爱军是性欲的奴仆、权欲的工具,那宋红梅就是虚伪的物化女奴,性欲(性压抑、性变态)驾驭政治癫狂,使他们由受虐的一方变为施虐的一方,“受虐—施虐”不仅表现在二人的性爱关系上,还表现在他们对程岗镇人的施虐报复上。革命也显现出荒诞、暴力的本质,“革命+人性”的狂欢以病理化的形式呈现在人物身上,借助“文革”的癫狂历史时机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体现出民狂的精神气质。这两处非理性区域,使整个世界都癫狂、荒诞起来,而这革命故事再经由“厉鬼”讲述,更是人鬼不分、诡谲不羁。阎连科以戏仿的“革命+恋/性爱”叙事,瓦解了经典革命的叙事美学及其象征符号体系,使革命背后沉重而暖昧的灰色阴影显现了出来。②梁鸿:《阎连科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与美学策略》,《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革命被性欲解构了,而所谓的“革命”难道就是崇高的、为人民服务的和理性的吗?真的就如宣称所言是大势所趋和历史必然吗?还是“革命”本身就是人性私欲无限膨胀而导致的一系列“弑父”、“造反”浪潮……对此我们难以定论,但至少可以肯定,革命与人性都具有非理性、恶性膨胀,以及类似恶魔性的毁灭与新生的两面性特质,并且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二者的结合、转换也是被无数次印证的历史事实。
除了戏仿革命话语和“革命加恋爱”的叙事,《炸裂志》也是全篇充满解构意味的戏仿之作。全书包括十九章,除第一章和第十九章的“附篇”和“主笔导言(尾声)”,是以作家“阎连科”的身份来讲述志书的编纂和具体事宜外,其他十七章讲述的是一个二百人的小村庄“炸裂”村,在三位“开拓者”(分别代表权力、美色、暴力的孔明亮、朱颖和孔明耀)带领的畸形、神速发展方式下,成为一个超级大都市的发展历程。小村庄的炸裂,也是人性欲望的狂欢和酒神精神的炸裂。
《炸裂志》模仿了地方志书的文体形式和篇章结构,根据地理、历史、人物、地舆改革等方面来结撰全文,但这只是在编排和书名上的模仿,从内在来看其实是一种解构和颠覆的戏仿之作。这是一部文学性的超现实主义文本,其中充满象征性、夸诞性、魔幻化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风格,尤其是对孔明光的权力、孔明耀的狂暴武力的展示部分,更是荒诞至极。明光的话、印章、通知等能让天气气候、花鸟百兽都听从他的任意调遣;而孔明耀的军人口号、军乐、武器等,能让建筑飞速建成竣工……这些描写具有超现实、非理性、无逻辑的特点,也是对权力、武力、美色(性欲)的艺术化、夸诞化展现,与传统志书写实手法为主的创作特点形成强烈对比。《炸裂志》中植物开错花、结错果,父亲孔东德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梦境和未卜先知的能力,以及与人们生死相关的钟表,明辉捡到的能够预示人们命运的万年历等直接的神秘物象——这些预言和隐喻,在小说中成为宿命式的象征性存在,使小说超脱志书、历史教科书的理性束缚,呈现怪诞、神秘的色彩,使小说具有寓言、象征和讽喻、嘲解的意味。
“走梦”所具有的仪式化意味和炸裂的“炸裂”式发展方式,都使小说具有巴赫金的狂欢化特征。炸裂的发展史、炸裂人的人性欲望膨胀,都将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引向极端,人物肆无忌惮的狂欢化分裂并走向极端癫狂,以自我屠戮的方式毁灭自我、伤害他人、摧毁世界。这种类似酒神精神的风格在整部炸裂“志书”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可以克制非理性欲望的道德伦理、哲学艺术等力量,则体现在猫一样的明辉身上,微弱、无力而迷蒙,只是命运随波逐流的潮汐中试图清醒而不能的暧昧光辉。戏仿在经典与戏说、预期与突变、正统与边缘之间的缝隙中,将前者抹杀在崩落、降格和消解之中。
总之,阎连科创作中的“仪式”、“狂欢”、“复调”化、“降格”化和“戏仿”,不仅源于民间文化仪式,更是文学的狂欢化,都是一种狂欢化的创作形式。文学的狂欢化,是一种由诙谐因素架构的语言或符号系统,具有双重的指向性和巨大的象征概括性。①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第177页。阎连科以狂欢化的叙事形式和陌生化、狂欢化的眼光关照世界人生;以杂交、杂糅的方式混淆高贵与卑劣、正统与边缘,动摇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的权威性、优越感;以“加冕—脱冕”结构,让高贵、正统的因素降格,自我解构;发挥被官方文化贬低的人物形象所具有的形式—体裁的功能;将深邃高远的象征寓意赋予粗鄙、怪诞的意象和物象,发挥诡谲怪诞的美学特点……这些内容和叙事手段创造出一种狂欢化的诗学。
五、狂欢化酒神精神特质
阎连科的酷烈、怪诞风格是以狂欢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其内在精神则是狄俄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正是这种非理性、敏感放纵、充满艺术气质的酒神精神,贯穿并张扬于阎连科创作的始终,只是与莫言作品张扬原始生命强力的酒神精神相比,阎连科作品的狂欢、迷醉成分是掩盖在压抑、怪诞的表象之下的,就像“受活”这个方言词本身的内涵一样,是一种扭曲痛苦并伴有享受的、带有性欲的隐秘色彩的精神状态。
狂欢精神作为一种发源于民间的精神,与民间的艺术形式和诙谐文化相结合,就呈现出一种类似于酒神精神的“民狂”,民狂是非理性的、痛苦与享乐相伴的、充满艺术性质的,同时也具有民间藏污纳垢的特点和嘲讽、“降格”的解构作用。民狂与狂欢都是一种源于人性之初的、隐蔽深层的感性传统,但又不是肤浅的感性游戏,虽然保留着游戏的消遣与娱乐性能,然而又充溢着揭示、揭露乃至抨击当下生存景况的历史功能。狂欢的精神渴望可谓根植于人性的深处,是充满了生命冲动和创造力量的本源。狂欢形式的非理性精神内质就是酒神精神,在酒神世界里,放纵、狂肆、非理性对理性取得了胜利,挥霍浪费、快感狂喜、喜极而泣等极限体验,是生命力量的另类挥洒。
狂欢化思维,作为颠覆权威化、理想化、终极真理、专横话语、极权政治等的代名词,在许多方面与解构主义与异曲同工之妙,但狂欢化思维强调“颠覆”是为了重新建构,而且是积极的、创建性的建设,与解构主义有明显差异。这些狂欢化小说深深植根于民间诙谐文化中,民间广场语言的喧哗、节日庆典的欢快和狂欢的双重性的诙谐,为小说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①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第5-6页。
阎连科作品中这些表现狂欢、民狂精神的形式和内容,以“民间”的诙谐性、草根性、真实性和消解性,在民间或“伪民间”的仪式典礼上不断实现暂时的平等、发泄和狂欢,不断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精英知识分子话语言说的空隙中发声和表意,不断模仿正统的“封神”、“加冕”却以诙谐、狂笑瓦解他们的赋魅言行……这些都是阎连科消解正统、消除“赋魅”、瓦解既有体系的手段,也是他追求真实的方法。
李缙英(1989-),女,上海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