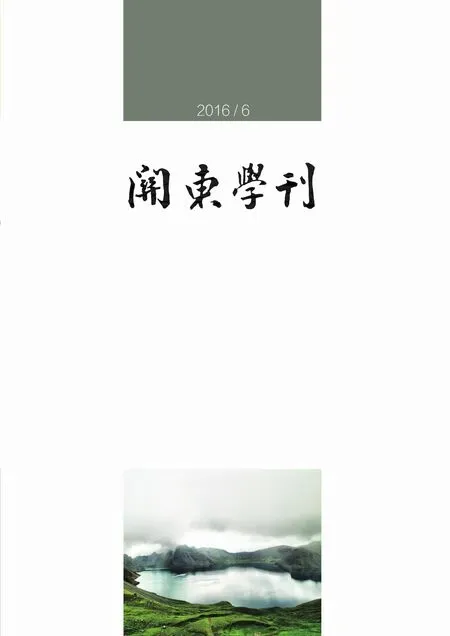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相互性
2016-03-16李海峰
李海峰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相互性
李海峰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相互性原则,可以从儒道释的相互交融,以及儒家中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邦国关系三个层次来探讨,特别集中体现在《中庸》中的五达道(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三达德(智、仁、勇)、九经(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在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传统中重视伦理关系的特质,物我一体、民胞物与的情怀更应该引起人类的重视,发挥独到的作用,可以从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进入的角度提供探讨共享性的特殊路径,也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
传统文化;相互性;中庸
相互性(reciprocity)意味着人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当人或人类群体将某样东西给予其他的人或群体时,他们之间就发生了某种形式的交换。没有任何人能够孤立地成为一个真正拥有理性的人;没有与他人共时或历时的相互作用,甚至没有谁能够作为人进行思考。作为一种人类价值,相互性的重要意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日益突出。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种种问题与挑战,需要在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神学及宗教学等领域中进行多角度深入探讨,从不同民族文化中寻找智慧的资源。当今时代,信息化、互联网成为时代的主流,信息与物质、能量不同,信息的主要特征就是“共享性”。信息不仅是可共享的,且信息共享具有不同于其他共享的性质,信息共享决不会如同物质或能量共享那样减少,反而,人们作为能动者参与信息共享时,参与共享的人越多,参与者在共享中得到的信息就越多。共享是人类相互性的主要特征之一。
相互性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而出现,全球化是当下的时代特征,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被席卷到全球化浪潮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对弱势的文化需要警惕。全球化浪潮下,强势文化的席卷有可能湮没每个国家本身文化的特点,最终导致同一性、单调性。因此,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中相互性的体现,保存中国的儒家道德,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相互性与共享成为时代主题之时,以中国文化的特色为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和提升贡献一份独特的智慧,会对当代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传统文化中相互性的体现
“全球化,就是全球范围内联系的普遍化和密切化。具体而言,是指人类跨越地域空间距离,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社会差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广泛关联并受这种关联影响和制约的过程。”①李道湘、于铭松主编:《中华文化与民族凝聚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在这样相互关联影响和制约的过程中,相互性体现得十分突出,它意味着人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不断地发生相互的作用,彼此在交换着信息与能量。中国的孔子学院开到了世界各地,而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也出现在中国的城市之中,文化在彼此的渗透与相互影响中,并没有泯灭各自的特色,而是在与他者的对比中更加凸显出彰显自身文化特色的需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有自身特质的文化现象越是能吸引世界的关注。可以说,“民族性是文化全球化的核心特征。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民族性,这是这一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②王媛媛:《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全球化与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在相互性的作用中,中国人应当树立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文化自觉角度去思考中国文化能够为世界提供的优秀的价值与思想资源。
中华传统文化的相互性首先表现在构成文化主体的儒道释三家和平相处、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最终形成儒、释、道三教互补互融,三元一体的稳定文化结构。南宋孝宗《原道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就好比一个吸纳器,它能将历史中各种异质文化吸纳、包容在一起,并最终抟聚铸就成一个文化统一体,作用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身心修养和人格塑造上。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无论是儒家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从、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仁”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仁者,爱人也”。仁,从说文解字来讲,仁乃“人”+“二”,可以理解为二人相处之道。在易经里面,“一”代表道,“二”暨由两条大道组成,暨天道与地道,人必须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不断地遵循天道地道这些自然大道来立于世,如此能修成“仁”。
仁的内涵就是爱他人,这就涉及了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孔子的思想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仁”价值主要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就是人们之间相互用友爱友善的态度对待对方。仁字同时蕴含了丰富的生生之德,植物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是果仁,它蕴含着的能量是巨大的,而仁包含着强大的生命力,是一种成长的能量,对于他人成长的伤害就是不仁,比如严厉的批评有失仁和,伤害别人的肉体和心灵是一种不仁之举,体贴他人的处境与需求是仁爱之心的体现。达到仁的境界对于个人修养有很高要求,需要自我的关注度很低,对他人的苦乐冷暖生命状态能够及时体察和觉知到,这是一种灵敏和虚灵若谷的状态。普通人执着在自我的情绪、愤怒与标准的时候,很难察觉到他人的生命状态,就会比较容易伤到他人,只有按照儒家的标准修养到仁者的程度,才可能虚怀若谷,中正平和,寂而不动,感而遂通。
儒家调节人际关系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达德:智、仁、勇。“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这是用来调节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中庸》第二十章阐明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从这段话可以看到,儒家的修身、治人几乎为一体般紧密,必须先修身然后再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由近及远的有差等的处理人与自己、家庭、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
在儒家的传统中,存在着相互性的明确体现,而且可以由小到大,分出清晰的三个层次。
第一是家庭关系中,儒家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儒家的思想观念中强调人伦首位,而且一切事情反求诸己,先问自己尽道与否,再问他人。对自己:克己复礼为仁,在家庭中提倡孝悌是仁的基础。“仁”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
第二是在社会关系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朋友讲究信用,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运》所言:“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中国人之所以能够特别注重集体,就因为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万物本为一体,大家本为一人,并不特别看重个体的价值,反而侧重群体的价值,因此中国人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将君臣关系视为上下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中庸》第十二章详细论述了夫妇的人际关系,将夫妇关系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其文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十三章论述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达道。综观斯两章,五达道备焉。五达道就是天下通行的五种人际关系。通过正确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达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诚如《礼运》所言:“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孔子的最高境界是仁,“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但这不只是个人的匹夫之仁,而是治理有方为民造福的大仁大义,更是指有权势在手的统治者的仁,要这些人克服自己的私心欲望,遵守秩序,有步骤地管理国家。
儒家重视民生,主张满足人们求生存的基本物质欲求,并提倡富民思想,强调先富后教,使民从善,然后政权得以稳固。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儒家认为,民生是治国之本,民以食为天,衣食足,有恒产才有恒心,满足了百姓的衣食需求,国家才能稳固而得到治理。儒家从重视民生出发,倡富民思想。儒家经典《周礼》提出“保息养民”的六项措施,即“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富而安之,体现了儒家早期的富民思想。孔子提出富而教之的思想,“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使众多的人民生活得到满足而富裕,然后施之以教,使人民有道德。把富民作为施教的前提和基础,可见对富民的重视。孔子还把富民与利民、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利益联系起来。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利民、富民、保民、爱民,体察和顺应民心的向背,这是儒家富民思想的特征。满足了百姓的生活需求,使之富足,就会使民众达到仁的境界而国安。而民穷则争,争则起暴乱,国难以治。可见民富才能国安,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民富而国富,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点。
孟子提出著名的仁政说,要求把仁的学说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治理中,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孟子提出一些切于实际的主张,重点在于改善民生,加强教化。其首要之点是“制民之产”,要求实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把仁政说与王道政治联系起来。认为人皆有仁爱之同情心,即不忍人之心,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行仁政,天下可得到治理;不行仁政,则天下难以治理。孟子认为,即使是百里小国,只要行仁政,天下百姓也会归之而王。行仁政须落实到“省刑罚,薄税敛”,发展农业生产等要事上来,在巩固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基础上,修德行教,使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即使是坚甲利兵也能战而胜之。儒家学说一贯强调以仁政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批评暴力,反对战争。这是儒家仁政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第三是在国邦关系中,崇尚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讲“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感。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体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九经就是以中庸之道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修养自身,就能够达到美好的人格;尊重人,就不至于迷惑;爱护亲族,叔伯兄弟之间就不会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于糊涂;体恤群臣,士就会尽力予以报答;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受到勉励;劝勉各种工匠,财货就能充足;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四方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就会敬服。这段话讲到儒家学说治理国家的要素,要做好这九项工作,就必须用至诚、至仁、至善的爱心去充分体现美好人格。做好这九项工作,事实上也就处理调节好了九种人际关系。调节这九种人际关系是使天下国家达到太平和合理想的重要保证。“九经”的提出,是对《尚书.尧典》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国家安定的理想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修身理想的继承和发展。
国邦关系中的要点在于不是以武力、战争去征服,而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通过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来让其他国家归附和作为价值模板,“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中国一直就是一个非常注重人文性的国家,不去崇拜神,也不迷恋物,把人的主体位置放大,在天地之间与天地并成为三才之一。
习近平在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中华文化爱好和平的特质,这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相互性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
第一,一体不二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深层的潜意识在时空纬度上可以用“一”来表示:其一,空间上,中国人认为人与大自然是一体的,即我们说的天人合一,人类是自然的儿女,天生之,地养之,物成之;其二,万物也与我是同一的,即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石头会说话,景物可以传情,春风可以思春,万里长城会因孟姜女的痛苦而倒塌;其三,家与国是一体,孝子可以为忠臣,齐家之后可以治国、平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四,文化思想上儒释道可以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中华民族也曾经被其他民族在武力上征服,但是却从文化上包容、同化、影响到入主中原的民族。
时间上,分为两重涵义:其一,生命是一个序列的链条,祖宗、儿女皆是与我在同一条生命的链条上,是一体不二的,因此有了族谱,祭祖仪式,宗庙祠堂等。其二,因果同担:人们积德行善,以荫子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们生活中也会以儿女的出息与否来看待父母是否德行深厚,咒骂作恶的人断子绝孙,如果有什么祸事躲避之后也会认为是老祖宗有护佑。这种天人合一、祖宗子孙合一的思想深深贯穿在中华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就会用到上述这些观念,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价值共识”“命运共同体”等思想都是缘于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潜意识。以时空维度的合一作为主线,再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串在一起。在最深层次的潜意识之上,许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就可以被推导出来。生活目标的追求上,是追求内圣外王,追求人与道的合一,圣人即已经对道有体悟的人,并且把这种道与德广布于天下;行为方式上,理想的境界是知行合一,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第二,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本指歌唱的相互应和。说文“和,相应也”引申而指不同事物相互一致的关系。《国语·祁语》记载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指不同事物相互聚合而得其平衡,故能产生新事物;如果只是相同事物重复相加,那就还是原来的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论语》中也提到了“和”的价值理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篇)“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篇)”君子人格的包容性和差异性是不同事物都能融合的多样性统一,而古代礼的作用本来是区分尊卑等级的,但是《论语》中又指出在以礼区别等级的过程中,最为珍贵的仍然是融合与协调,这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人与人的关系中渗透着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第三,和平解决争端的行为方式。相互性以承认事物的差别,尊重事物的多样性为前提。古代中国人对自然万物与人的存在之和的根本把握往往追寻一种转换及“化与合”的境界,而非对立消灭其中一方。这充分体现在西医与中医对治疗方式的不同选择上,中医用调养、温补等柔和的手段,西医用手术、杀菌等对抗性治疗。生命并不只是人自身的存在,而必须是在与自然万物的生态有机一体中互惠、共生、共荣的和。《淮南子·本经训》曰:“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淮南子·天文训》还曰:“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和合而万物生。”这说明“和”之存在不在于同一性,而在于多样性。《道德经》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哲学意义上说,“和”与“同”是不一样的。“和”作为多样性的统一,其中各种要素以多样性的“化与合”共同参与“和”的运行,各种元素不断地进行相互作用,生生灭灭,相交相融,不断地生成新的个体。“同”的基础不同于多样性,只是单个元素,或单个种群、生命个体的单一性的重复,混合起来无法产生新的事物。“和”与“同”更重要的区别还在于:宇宙系统运行的逻辑起点与终点都是“和”,不过在终点上的和,既是对起点及过程之和的超越,同时又是新的运动过程的起点。因此,“和”的动态性就在这种转换、循环过程中呈现着创造性。“同”则不可能具备这些特性,没有创造性,甚至会阻碍万物的生存,导致万物的衰竭。“和”的这种对于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包容和尊重,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生态多样性和创造性的智慧把握。这种尊重多样性的思维模式体现在中国对待种种事物的态度上,天下大同,民胞物与,总是以和平统一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而不是以冲突和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和争端。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相互性的当代价值
中国文化主体性背景下,以民族性的内涵来结合现代性的内容,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张力与融合中,可以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互性在中国和世界的当代价值。只有真正民族性的东西才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中国思想中的儒家重视人伦关系的推己及人、反躬自省,由个人修身再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一种个人安顿自己身心和人在世界关系的心灵地图。中国文化侧重人文的民族精神内涵是对现代性弊端的纠正,中国的人文精神强调“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其中的理性精神蕴含着人的主体性的发扬,人不会变成上帝的仆人,也不会成为物质的奴隶,而是靠自己掌握命运,福由己做,命自己求,这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在不同的时代都焕发着光彩。源于西方启蒙时代的现代性理念主张民权取代王权,理性取代信仰,发达的工具理性使得人们逐渐迷失自我,在物质与科技的狂欢中迷茫;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社会结构调整与变迁,都市的繁华与放纵的欲望导致现代性危机逐渐显现,只有重新回到民族文化的根源汲取营养,从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中寻觅一条安顿身心之道,才算是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张力中找到了平衡与位置。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治天下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大同”世。“大同”一词出自《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东方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其中蕴藏着克服国家界限、民族界限的美好社会理想,勾勒了一幅由修身到世界和平的美好图景,是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贡献。
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就在于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世界是一个整体,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思维方式提供了维持世界长久和平的思想资源,对于解决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之下的冲突提供一种思维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不同国家利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制度的分歧甚至对立,但基于整体关联思维方式的“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使得不同信仰、制度和民族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有序竞争,让共同利益压倒分歧对立,让人类理性选择世界的未来。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文化整体关联思维应用到政治、外交的成功案例,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与关注,符合全球化时代特征的需求,是用中国智慧解决世界难题的成功范例。互联网把人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跨国大公司的商业流通使得人们可以享受世界上所有地方的商品与食物,全球一体化带来生活与物质上的便捷;而只有一个地球的生态环境更使得人们命运相连,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每个国家甚至是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日本福岛核泄漏,沿海的区域以及周边的国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球化时代的各种事件都证明了每个个体都不能脱离整体而独立生存,人类的利益、命运都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都验证了古老中国文化中整体关联思维的前瞻性与科学性。
中国大乘佛教华严宗提供的事事无碍法界对于相互性进行深度诠释,不仅用一体的方式来看待人和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能看到人类与自然万物、宇宙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事事无碍、相即相入的不可思议境界,提供了探讨共享性的特殊路径,能够为更好地解决人类和自然的矛盾提供思路。华严宗是佛教进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结合而产生的佛教流派,兴盛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提出事事无碍法界的理论,核心是圆融无碍,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包含、相互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华严宗三祖法藏为武则天讲述的《金狮子章》中,指出一一毛中皆有一个金狮子,部分里包含了整体的金狮子的信息,毛不是孤立的,而是金狮子的构成部分,每个毛体现的都是整个金狮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每个生命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人与各种动物、植物都蕴含着世界整体的信息,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状态,当人类活动超越了自然承载时,就对其他物种的生存造成了负面影响,只有人类真正意识到万物之间都是相互含摄、相互作用的状态时,才能尊重地球上每一类生命的生存权,达到人类与地球万物、宇宙的和谐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相互性有诸多宝藏,需要挖掘与转化,通过世界能够接受、产生共鸣的观念和思想弘扬出去,才能有益于人类与世界的总体和谐,才会拥有被世界认可的独特地位。
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资助。
李海峰(1975-),女,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北京10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