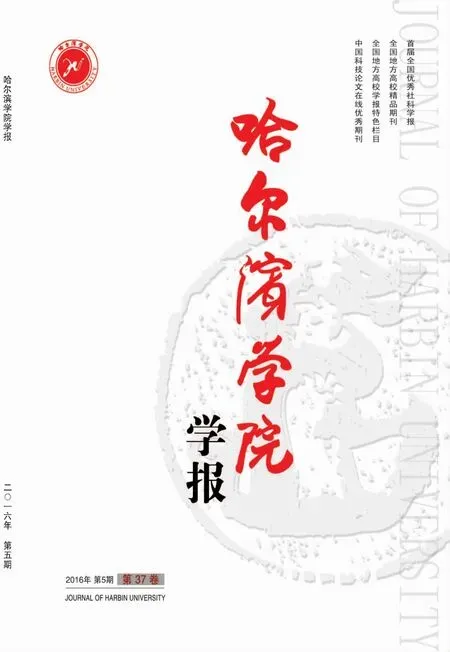春秋诸侯决策监督考论
2016-03-16张凯
张 凯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90)
春秋诸侯决策监督考论
张凯
(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150090)
[摘要]春秋时期贵族政治中所包含的原始民主成分,促成了对最高决策者决策行为的一系列监督。春秋时期的诸侯决策监督,应属后世中央监察制度前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决策监督的形式以舆论监督为主。
[关键词]监察制度;决策监督;思想基础;舆论监督
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而设立的一项政治制度。它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发挥着调节、制衡作用。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监察因素和活动的某些萌芽。
春秋时期贵族政治中所包含的原始民主成分促成了对最高决策者决策行为的一系列监督制度。春秋时期诸侯决策监督制度与后世的中央监察制度在本质上有着密切联系,应该属于后世中央监察制度前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出现的时代,学界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其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张序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始创于春秋战国时期。”[1]白钢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从有国家时起就已存在着国君对臣下的监察活动,同时也存在着以贵族为主的国人对君主实行着监督。在春秋中期以至战国,国君监察臣下之职主要委之于御史。同时又设立谏官以匡正国君的过失,我国的监察制度即滥觞于斯时。”[2]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中央监察制度由谏官制度、御史制度及封驳制度三大体系组成。这三大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个体系制度产生、确立的时间与发展状况也不一样,从中央监察制度的整体发展线索来看,御史制度是三大体系的核心”,并认为中国古代中央监察制度产生、确立于东汉时期。[3]笔者赞同此说法,在春秋时期,还没有设置专门的监察机构,也没有普遍设置专职的监察官员,更没有专门的监察法规,监察活动相对后世而言比较简单,严格说来,春秋时期还未形成一种监察制度。因此,春秋时期不宜冠之以监察制度之名,于决策而言,可称之为决策监督制度。
一、春秋决策监督的社会思想基础
春秋时期内政、邦交形势复杂多变,尽管各诸侯国大小强弱有别,但其决策者都认识到,提高决策水平,避免决策失误,需借助一定的手段。因此,政治家、思想家认为决策者能否任用谏臣、虚心纳谏制约着决策水平的高低,即决策的制定需要监督发挥作用,并将对决策监督的议论集中于以言谏为主的舆论监督。
期望中的决策者是聪明睿智、事无不通、超越常人的。但现实并非如此,与之映照的客观事实是:“孤家”“寡人”的处境带来的孤陋寡闻,何况各诸侯国君、最高执政等决策者在个人能力、素质上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可见,决策水平的高低必然受个人能力的掣肘。因此,作为各诸侯国的决策者,要提高决策水平,巩固统治,就应当任谏臣纳谏言,重视和利用朝臣、国人等各阶层的人员在谏言中表达的建议、意见来弥补不足。《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韦昭注:“和,谓可否相济。同,谓同欲。”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杨伯峻先生解释为:“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4]“和”“同”之论为纳谏与进谏这一对事物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齐大夫晏婴向齐景公批评梁丘据时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上述思想说明决策者绝非事事皆能正确无误,其决策本身有“可”有“否”,准确与失误并存。因此,为人臣者对于为君者决策制定上的乖谬与失误之处应及时纠偏,设法匡正。
尽管“国、君一体”思想尚存,但将君主与社稷分离、区别对待的主张已经出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晏婴曰:“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杜预注:“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禄,皆为社稷。”晏婴之说已鲜明的表达出社稷即国家是统治集团或曰一国贵族全体利益的象征,即使作为贵族最高代表的国君也应服从社稷——贵族的整体利益,当君主的决策与贵族的整体利益不符甚至危及整体利益时,为臣者的取向应以整体利益为准。《荀子·臣道》中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
二、春秋决策监督的形式
春秋时期的决策监督形式,考之史实,以舆论监督为主,“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国语·周语上》),舆论监督于此可见一斑,简言之,其中包括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的言谏,国人的舆论监督,议谥等。其中,贵族的言谏是直接面对国君或执政等决策者表达意见,为直接舆论监督;国人的舆论监督,议谥则无法面对决策者本人,为间接舆论监督。
(一)直接舆论监督
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即朝臣言谏是舆论监督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从言谏人员的身份来看,有卿,如齐国管仲,晋国魏绛,楚国子囊、薳子冯、子木、子西,郑国子大叔、子羽,齐国晏婴,宋国乐豫,晋国士季、赵盾,卫国宁庄子,鲁国叔孙穆子,共14人次;大夫数量最多,如郑国五父、孔叔,富子、叔詹,鲁国臧哀伯、御孙、臧武仲、穆叔、冶区夫、臧僖伯、荣驾鹅(荣成伯),晋国里克、士贞子、伯宗、苗贲皇、韩厥、叔向、士蒍、庆郑、司马侯、士弥牟、阎没、女宽,楚国申公巫臣、椒举、薳启强、太宰犯、叶公、白公子张,齐国崔杼、诸御鞅,莒国苑羊牧之,卫国石碏、公叔文子、曹负羁,吴国伍子胥,越国范蠡;亦有地位甚低下、书名或未书名的“微者”,如郑僖公之侍者,晋平公时膳宰屠蒯,齐庄公之侍者。由上可见,春秋时期言谏人员即对决策者进行直接舆论监督的人员身份呈现多元化,上至地位显赫的一国正卿,下至地位低微的“侍者”,虽然“侍者”也有向一国之君或执政等决策者当面进言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人、庶民也可以向决策者直陈谏言。作为“侍者”与“膳宰”等微者具备这种可能,也不过是缘于他们接近一国的权力中心或曰决策中心,与决策者的近距离接触而创造的这种可能。
舆论监督行为可以追溯至氏族时代。氏族时代“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5]以言语规谏决策者的较早事例如《国语·楚语上》载傅说规谏武丁。
文献中最早提出“谏”这个概念的是《诗经·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谏”字亦已出现。著名的铜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文中有“朝夕入讕”一语,唐兰先生指出:“讕字从言闌声,即谏字。”并释此句为:“早晚来规谏。”[6]另外,懿王时有铜器名曰“谏簋”。[6]《说文解字》曰:“谏,证也。从言柬声。”《广雅·释诂一》亦曰:“谏,正也。”综上所述,“谏”的含义是以正直之言规劝别人,以使其有所领悟,以达到补阙的目的。①如有学者认为:“谏是规劝,诤是直言,谏诤也就是对君主或上司提出规劝性的意见。”[7]臣属言谏有其特定的对象,即是诸侯国的决策者。
周王室设有“保氏”一职。《周礼·地官》:“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周礼·地官·保氏》郑玄注:“谏者,以礼义正之。”贾公彦疏:“王有恶则谏之,故云掌谏王恶。”“保者是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保氏”的职责中有规谏王者过错一项,但依其另有“养国子以道”的职责可知“保氏”并非专职谏官。
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设立专职谏官。《管子·小匡》云:“使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宁戚为田,隰朋为行。”“管仲曰:……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韩非子》《吕氏春秋》中也有齐国设立谏官的类似记载。②楚国也有设立谏官“箴尹”的记载。《左传》宣公四年:“箴尹克黄使于齐”,杜预注:“箴尹,官名。”《左传》襄公十五年:“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吕氏春秋·勿躬》高诱注云:“楚有箴尹之官,亦谏臣。”可以确定的是,“箴尹”一职位在莫敖之下、连尹之上,为大夫一级职官。《左传》定公四年:“鍼尹固与王同舟”,杨伯峻先生注曰:“鍼尹亦作箴尹。”[8]“箴”,《说文解字》释曰:“缀衣箴也。”段玉裁注曰:“缀衣、联缀之也。谓签之使不散。若用以缝则从金之鍼也。《尚书》‘赘衣’即缀衣也。引申之义为箴规。古箴、鍼通用。”可见,“箴尹”确为负责规劝之官。除齐、楚外,有学者认为郑国也设立了谏官。③从现有史料来看,春秋时期少数几个诸侯国设置了专职谏官,谏官的设置尚不普遍。从内容来看,朝臣的进谏涉及到多种决策问题。
有谏国君立卿之嗣者,如: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
有谏邦交决策者,如:(重耳)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弗听。”(《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小邾穆公来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季孙从之。(《左传》昭公三年)
吴子使徐人执掩馀,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子西谏曰:“……吾又强其仇,以重怒之,无乃不可乎!……”王弗听。(《左传》昭公三十年)
有谏刑罚者,如:晋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晋侯使复其位。(《左传》宣公十二年)
楚子以诸侯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将戮庆封,椒举曰:“臣闻无瑕者可以戮人。庆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从于戮乎?播于诸侯,焉用之?”王弗听。(《左传》昭公四年)
有谏征伐战事的,如:晋侯将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乃止。(《左传》宣公十五年)
齐侯伐卫。……自卫将遂伐晋。……崔杼谏曰:“不可。臣闻之:‘小国间大国之败而毁焉,必受其咎。’君其图之。弗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兴师伐吴,至于五湖。吴人闻之,出而挑战,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许之,范蠡进谏曰:“夫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许也。……”王曰:“诺。”弗许。(《国语·越语下》)
有谏用人决策的,如: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臯落氏。里克谏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不对而退。(《左传》闵公二年)
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陈成子惮之,骤顾诸朝。
诸御鞅言于公曰:“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左传》哀公十四年)
朝臣进谏围绕诸侯国决策还涉及很多方面,此不赘述。总而言之,“君有过则谏”(《孟子·万章下》),“臣之事君,……执其是而谏其非”。[9]即对于诸侯国的决策者在决策中发生的偏差、失误,都是为人臣者进谏的对象。
(二)间接舆论监督
公众舆论监督可以上溯至氏族社会,赫胥黎说:“只要观察一下我们的周围,就可以看出,对人的反社会倾向最大的约束力并不是人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对他的同伴的舆论的畏惧。传统的荣誉感约束着一些破坏法律、道德和宗教束缚的人们。人们宁可忍受肉体上的极大痛苦,也不愿与生命告别,而羞耻心却驱使最懦弱者去自杀。”[10]氏族社会中,即有公众通过舆论监督氏族首领的事例,据《管子·桓公问》记载:“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由此可见,国人对决策者的舆论监督是原始民主制的一种遗留。古有批评统治者过失的制度,统治者也注意到国人的舆论,如《尚书·酒诰》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11]国人对诸侯国决策制定的舆论监督,因无缘与决策者面折廷诤,所以是通过间接方式,即“以诗歌创作和传诵来表达对国家政治的意见,对时弊的针砭。”[10]西周时期即有以诗赋为媒介进行舆论监督的记载,《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春秋时期,国人对决策的舆论监督多以诗赋为媒介,于史实可证。典型事例如《诗经》中《黄鸟》篇即为秦之国人哀伤殉葬的三良、批评秦穆公而作。《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史记·秦本纪》:“武公卒,……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缪(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诗经·秦风·黄鸟》序云:“《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12]国人对秦穆公的不当决策——殉三良的舆论监督以诗赋的形式保存在《诗经》中,诗赋形式的舆论监督多称为“诵”④“讴”等,如:“从政一年,舆人⑤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左传》襄公四年)
“宋皇国父为大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收。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左传》襄公十七年)
除诗赋形式外,谤议也是国人舆论监督的常用形式。西周时即有国人诽谤国君的事例,如为人熟知的“厉王虐,国人谤王”。⑥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丘赋”,杨伯峻先生注曰:“谓一丘之人出军赋若干。”[8]现代决策理论认为:任何一项公共决策,其实施的结果必然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利益。但这种利益对具体的个人或团体来说则是不同的,有的个人或团体可以从决策中得到较多的利益;有的个人或团体则从决策中得到较少的利益,甚至得不到利益或许还会失去原来的某些利益。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决策中对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节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超越了一定的限度,那些得益较少或失益较多的个人或团体就有可能对决策的实施进行抵制或减少对决策的支持程度。子产“作丘赋”这一决策,显然影响到了国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一度遭到了国人的非议、批评。又如:
宋襄公败于泓之战,“国人皆咎公”,(《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楚郤宛之难,国言未已,进胙者莫不谤令尹。”(《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令尹子常听信谗言,杀害郤宛。国人对其错误决策予以谴责。
春秋时期,国人又有通过集中议论表达舆情、监督决策的地点——乡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童书业先生指出:“古学校在平时盖又可为‘国人’论政之所,故‘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13]
议谥制度是间接舆论监督的又一形式。春秋时期臣属集体评议已故国君一生功过的议谥制度始于西周的谥法制度。《逸周书·谥法解》云:“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谥号是对死者一生的评价,正所谓盖棺论定,反映了统治集团舆论对死者的褒贬、扬抑态度。尽管谥号对已死者无法发生作用,但对于后继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警策。《左传》襄公十三年载楚共王临终前告大夫定其谥为“灵”或“厉”,依《逸周书·谥法解》,“灵”与“厉”皆为恶谥,故杜预注:“欲受恶谥以归先君也。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楚令尹子囊因楚王“知其过”,与大夫最终议谥为“共”,即《逸周书·谥法解》之意:“既过能改曰恭(共)。”
为死去的国君、最高执政等决策者⑦立谥号,一定程度上会对后继者起到舆论监督作用。
三、春秋决策监督的特点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决策监督制度与西周时期相比有着深刻的变化。简言之,就决策监督机制的产生因素来说,因周王室已丧失了对诸侯各国决策予以监督的能力,使诸侯各国的决策监督因素减少主要来源于各国自身。
春秋诸侯各国,大多是周初“封藩建卫”的产物。周初,周王室实行的命卿制度、监国制度、巡狩制度和述职制度等都对诸侯各国的决策形成了事实上的监督。《礼记·王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郑玄注:“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误脱耳。”孔颖达正义曰:“郑何以得知应三卿?按:前云小国又有上、中、下三卿,位当大国之下大夫。若无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在命卿制度之下,作为各国诸侯股肱之臣的卿佐,三人中至少有一人为周天子任命,周王室对诸侯决策的控制可以想见了。周王室还通过监国制度对各国诸侯进行监视。《周礼·天官·大宰》:“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礼记·王制》:“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毫无疑问,周王室通过监国制度将各诸侯的决策纳入其监督范围。巡狩制度和述职制度相对,是周王室监督各诸侯决策的又一方式。《孟子·梁惠王下》有:“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礼记·王制》:“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五年一朝。”“聘”是指诸侯派员前往王室汇报;“朝”则指诸侯亲自赴王室朝觐、汇报。周天子通过亲自巡行各诸侯国和诸侯定期和不定期向天子汇报以及临时的会、同,⑧对各诸侯的决策予以定期和不定期监督。
周室东迁,共主衰微,王命不行。进入春秋时期,衰微的周王室再也无力对独立性日益增强的诸侯国的决策实行有效的监督了,诸侯们只是在观念上认为自己是周天子的下属,周天子是各国诸侯精神上的宗主,[14]所谓“春秋时共主悉臣之义犹在人心”。[15]昔日体现周王室对诸侯决策实行有效监督的“赐命”“请命”之举,已沦为具文故事。
春秋时期,对决策制定的监督,以舆论监督形式为主,类似鬻拳“兵谏”楚文王的例子颇为少见。贵族、国人对国君或执政的舆论监督是否被听取,完全取决于决策者个人的意志,即其对决策者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因而使规谏与诽谤往往流于空洞的道德说教。桓公二年,宋赂鲁桓公大鼎,桓公置于太庙,《左传》作者斥桓公此举为“非礼也”,大夫臧哀伯因此劝谏此“非礼”之举。周内史称赞臧哀伯:“君违,不忘谏之以德。”又如庄公“丹桓公之楹”(《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刻其桷”,鲁大夫御孙谏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国人对决策制定的意见无缘直接面陈决策者,只能通过诽谤等间接舆论监督方式上达决策者,毋庸质疑,这种间接的口耳相传式的传播途径在舆论向上层传递的过程中难免造成信息的流失或失真;从时效性来说,速度也不及直接奏闻决策者的方式快。
朝臣、国人的舆论监督没有法律保障,意见是否被听取取决于决策者的个人意志。春秋时期频繁见诸文献中的“不听”“弗听”等记载均是国君或执政等决策者对待谏者的答复。决策者拒谏——拒绝接受舆论监督的事例不胜枚举,轻则“愎谏”,⑨重则动用极端手段,“谏者有刑”(《左传》桓公十三年),“有敢谏者死无赦”(《史记·楚世家》)等言辞则足以表明有些决策者公然扬言拒谏,甚至出现多起杀戮进谏之人的流血事件。此类行径古已有之。周厉王杀戮国人以“弭谤”即为众所周知的事例(《国语·周语上》)。宣公九年,陈大夫洩冶谏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宣淫于朝被杀;襄公七年,郑僖公杀进谏的侍者;晋灵公因赵盾屡次进谏,竟挖空心思的多次设计必欲除掉此正卿而后快的事例更为人熟知(《左传》宣公二年)。此种行径的实质是对臣民舆论监督权利的侵犯,是对舆论监督机制的践踏,是渺视舆论监督的极端行为。反之,奖掖、提拔谏者的事例则罕见,[16]如:晋平公提升屠蒯。《左传》昭公十七年云:“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屠蒯本仅为“膳宰”,职位低微。晋平公此次使其担任赴王室之使节,可见屠蒯已被提升。故杜预注曰:“屠蒯,晋侯之膳宰也,以忠谏见进。”见于《左传》的拔擢谏者的事例可谓绝无仅有。
春秋时人已得出的“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的观点(《国语·晋语六》),确能在一定程度说明时人已认识到能否任谏臣、纳谏言反映出决策制定的水平,是决策者执政优劣状况的一种标志。同时,相对而言,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身为人臣,食君之禄,君有过失而不劝谏、曲意媚君,难免自食其咎。即《国语·周语上》载:“大臣享其禄,弗谏而阿之,亦必及焉。”综合决策者与进谏者两方面的因素,一国进谏之言路通畅与否,是判断其决策水平高低,政治清明抑或昏乱的重要标准。如晋大夫郤叔虎根据翟柤“有纵君而无谏臣”的政治状况,判断翟柤国力虚弱,将无力抵御外来进攻,因此使人劝献公攻克了翟柤。(《国语·晋语一》)春秋时期谥法能比较真实的反映决策者生前执政状况或生平。童书业先生在《周代谥法》一文中指出:“所谓令主身后,固按其行事奉以美谥,若不得其死或失国之主,自易以恶谥谥之,与后来中央集权专制之世臣下不敢议其君上者有异。”[13]
注释:
①“补阙”一词源于《诗经·大雅·烝民》:“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为君主弥补过失之意。
②《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云:“桓公问置吏于管仲,(管仲)曰:‘……犯颜极谏,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谏臣。’”;(《韩非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吕氏春秋·勿躬》载管仲对齐桓公说:“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贵贵,臣不若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③如左言东据《诗经·郑风·羔裘》“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认为“司直”为郑国掌谏国君之官。见于左言东《先秦职官表》,商务印书馆,1994年。
④《周礼·春官·大司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曰:“以声节之曰诵。”《国语·晋语三》:“舆人诵之”,韦昭注:“不歌曰诵。”
⑤童书业先生指出:“‘舆人’必非奴隶或贱民,而为国都中甲士一类人物也。”“‘舆人’盖‘国人’中之从征从役者耳。”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⑥《国语·周语》,韦昭注:“谤,诽也。”
⑦卿大夫自春秋始有用谥法之礼者,杨伯峻先生对此有详细解说,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
⑧《周礼·春官·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
⑨《左传》昭公四年。《逸周书·谥法解》注云:“去谏曰愎”。
[参考文献]
[1]张序.我国古代官员监察弹劾制度之演变[J].政治学研究,1987,(3).
[2]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贾玉英,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9]杜预.春秋释例[A].丛书集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0]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1]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4]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5]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刘世敏.政府德性行政的构建路径探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11).
责任编辑:魏乐娇
Feudal Princes’ Decision-Making Supervision System at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ZHANG Kai
(Center for Sports Lotteri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Harbin 150090,China)
Abstract:At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 aristocracy politics included primitive democracy,which developed a series of supervision practice to the top decision-makers. The feudal princes’ decision-making supervision practice was important pa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ter central government supervision system. The form of this supervision system mainly depends on public opinions.
Key words:supervision system;decision-making supervision;ideological basis;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收稿日期]2015-12-08
[作者简介]张凯(1978-),男,长春人,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决策与战略发展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5—0079—06
[中图分类号]K2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5.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