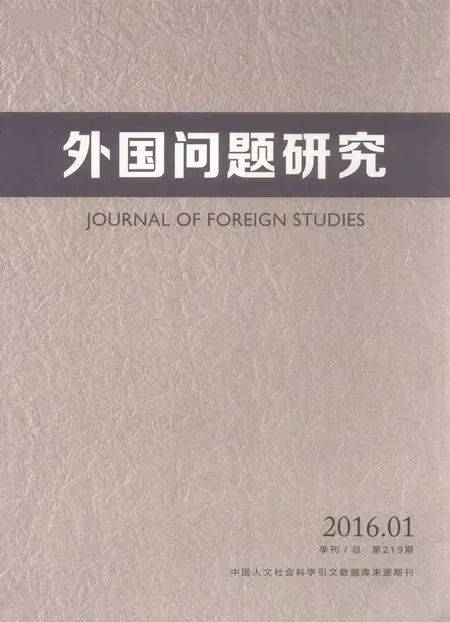禁倭与申交:明太祖对日交涉目的探析
——以洪武初年的对外诏书为中心
2016-03-16刘晓东
刘晓东 年 旭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禁倭与申交:明太祖对日交涉目的探析
——以洪武初年的对外诏书为中心
刘晓东年旭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内容摘要]目前研究多将明太祖对日交涉核心目的归结为禁倭,但以洪武初年对外诏书的对比来看,禁倭很可能只是次要目的,申交方是明太祖对日交涉的核心目的。明太祖试图通过万国来朝局面的营造,进一步彰显自身较元朝更为有效的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在这一层面上,被塑造成为维护中华正统而不向元朝朝贡的日本,其象征意义就显得较为重要了。《明实录》洪武四年日本国王入贡条目中,对赵秩与日本国王对话的记述,某种程度上或是为满足这一需求的刻意夸张。围绕“禁倭”与“申交”而展开的洪武初叶的对日交涉,也是洪武君臣践行以“王道政治”为基础的新型东亚区域秩序的一个微观侧面。
[关键词]明太祖;日本;倭寇;洪武;朝贡
学界受传统倭寇观影响,且依据洪武初年对日诏书中明太祖所言“不在意日本称臣与否”*《明太祖实录》卷39,洪武二年二月辛未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787页。及关于倭寇问题的论述,多将明太祖对日交涉之核心目的归结为禁倭。但详考《明实录》中洪武初年的倭寇侵扰记录:从建国至洪武二年杨载使日前,只有一次;*《明太祖实录》卷38,洪武二年春正月乙丑条,第781页。从杨载使日至次年赵秩使日期间,只有两次。*《明太祖实录》卷41,洪武二年夏四月戊子条,第824页;卷44,洪武二年八月乙亥条,第866页。如此稀疏的倭寇问题,却催生出明廷极为强烈的“禁倭要求”,这不能不令人略生疑惑。同时,以往的解读多仅限于明朝与日本之间,而忽略了明、日关系仅是朱元璋构建东亚区域秩序体系中的一环。因此,对于洪武时期尤其是初叶明、日关系的解读,既要考虑两者本身的特殊性,也要顾及日本在“天下”关系再确立背景中所处的一般性。本文即希冀通过对洪武初叶对日诏书与同期其他对外诏书的比较,进一步解读洪武初叶明朝对日交往的深层目的与意义所在。
一、洪武建元的海外宣谕与对日诏书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便遣使四处,诏谕诸国,其中蕴含了明朝廷海外交往的何种基本理念?我们不妨将洪武帝颁谕诸国的初次对外诏书之内容,略作比较与分析:
1.高丽:“自有宋失御,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华夷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暴兵忽至,误入其中,见其无成,忧惧弗宁。荷天地眷祐,授以文武,东渡江左,习养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报,故遣使报王知之。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朕虽不德,不及我中国古先哲王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余不多及。”*《明太祖实录》卷37,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第749页。
2.安南:“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远,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扫群雄,定华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国,建国号曰大明,改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远未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明太祖实录》卷37,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第750页。
3.占城:“朕之遣使正欲报王知之,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王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于生业,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孙,上帝寔鉴临之。”*《明太祖实录》卷39,洪武二年二月辛未条,第785页。
4.爪哇:“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国,恐遐迩未闻,故专使报王知之……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于生理,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孙。”*《明太祖实录》卷39,洪武二年二月辛未条,第786页。
5.日本:“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羶中土,华风不兢,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惟四夷未报。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图,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明太祖实录》卷39,洪武二年二月辛未条,第787页。此次诏书并非明太祖第一次对日诏书,明太祖第一次对日诏书并未抵达日本,而是于途中毁溺,即《明使仲猷无逸尺牘》所言:“首命使适日本通好,舟至境内,遇贼杀杀害来使,诏书毁溺。”(载《大日本史料》第6編37冊,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第349頁)此次诏书是毁溺后的重发诏书。因之前诏书日本并未收到,此次诏书仍可算作初次对日诏书。
归纳这些诏书之内容,不难发现:诏书前半段的叙述理路,各国几乎完全相同,即元朝作为夷狄窃据中华所导致的“华夷失序”,及朱元璋不满华夷易位,荼毒天下生灵,已奉天命恢复中华正统。后半段的叙述理路,则针对各国略有不同,对高丽、安南、占城“非有意于臣服”,只为告建国之事;对爪哇认为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对日本除“报正统之事”外,还“兼谕倭兵越海之由”,并做出了只要不为“寇盗”之行,“臣”与“不臣”皆可的姿态。
从诏书前半段的叙述来看,以大量篇幅描述元朝的以夷乱华,无非是要强调元朝统治的非法性,及明朝对中华正统的恢复之功,实际上是要表明自身的正统性所在,这也是塑造新朝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诏书的后半段叙述中,都表达了对其是否加入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似乎并不太在意。但事实上,所谓“非有意于臣服”只是一种谦逊的表示,明太祖在后来颁赐给占城的诏书中曾云:
海外诸国入贡者,安南最先,高丽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称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尔彼此世传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国,尔前王必有遗训,不待谕而知者。*《明太祖实录》卷47,洪武二年十二月壬戌条,第934页。
对诸国来朝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而在命中书省给安南的回文中,又说:“安南僻在西南,本非华夏,风殊俗异,未免有之,若全以为夷,则夷难同比,终是文章之国,可以礼导,若不明定仪式使知遵守,难便责人,中国外夷,若互有道,彼此欢心,民之幸也。”*朱元璋:《明太祖文集》卷8《命中书回安南公文》,《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223册,第75页。
可见,明太祖所谓的“非有意于臣服”,并非真的不欲诸国来朝,毕竟就前近代的东亚区域秩序而言,这显然是一种重要而有序的国家交往方式与途径。不过,在洪武君臣的心中,似乎更倾向于追求一种“合于古制”的奉表称臣,即中国不以武力相胁而使诸国感文德之化,尊奉天朝,宾至来归。这较之武力征讨,显然更能彰显新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因此,这次对日诏书中所谓“不臣则修兵自图,永安境土,以应天休”的表述,实际上也并非洪武君臣的真实意愿。
由此而论,洪武二年的对日诏书中,虽然表达了这样两种目的:1.“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即申交朝贡;2.“谕倭兵越海之由”,即禁倭。但结合洪武二年的其他对外诏书来看,其真正的核心显然还是前者,“禁倭”只是一种次要目的与辅助性手段,正如诏书中所云只是“兼谕”而已。这在洪武三年的对日诏书,表现得更为明显了。
二、洪武三年对日诏书的叙述理路
洪武三年三月,明太祖遣莱州府同知赵秩携诏书再次使日,书云:
朕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粤自古昔,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历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窃主中国,今已百年,汙坏彝伦、纲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与胡相较几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効灵,诸将用命,收海内之群雄,复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尝遣使持书飞谕四夷,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琐里即能顺天奉命,称臣入贡。既而西域诸种番王各献良马来朝,俯伏听命。北夷远遁沙漠将及万里,特遣征虏大将军率马步八十万,出塞追获,歼厥渠魁,大统已定。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己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致罚于尔邦,俄闻被寇者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尔嗣。*《明太祖实录》卷50,洪武三年三月戊午条,第987页。
此次对日诏书内容,大体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同初次诏书叙述理路相同,言元朝以夷狄窃中华,非中国正统,新朝已承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第二部分叙述明朝近期对内对外之政治、军事成果,及大统已定的基本格局;第三部分言及倭寇问题;第四部分则希望日本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与前次对日诏书相较,第二、三、四部分是新增内容,显然也是需要我们进行重点分析的。
不过,像日本这样“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需要进行二次遣使招谕的地方并非只有日本,还有八番、西域、西洋、琐里、爪哇、畏吾儿等地。因此,我们也不妨将这些地方的第二次招谕诏书与第二次对日诏书略作比较,或许能另有一番启示。《明实录》中对洪武三年颁敕西洋、琐里、爪哇等地的诏书内容,也有着十分详细的记载:
洪武三年六月,遣使持诏谕云南、八番、西域、西洋、琐里、爪哇、畏吾儿等国曰: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不欲其安土而乐主。然必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近者元君妥欢帖木儿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四方豪杰割据郡县,十去八九。朕悯生民之涂炭,兴举义兵,攘除乱略,天下兵民尊朕居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丽诸国俱已朝贡,今年遣将巡行北边,始知元君已殁,获其孙买的里八剌,封为崇礼侯。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咸乐其所,又虑汝等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闻知。*《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戊寅条,第1049页。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对日诏书中的第二部分,即对明朝近期政治、军事成果的展示,并非其独有内容,而是洪武三年招谕诏书中的通用内容。这实际上是意欲通过对自身军事实力及已朝贡诸国政治成果的展现,施加压力以敦促其仿效来朝。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日诏书的新增内容不仅较其他诏书为多,而且其中所谓爪哇、西洋、琐里等地已“顺天奉命,称臣入贡”的信息实际上是虚假的。如前所述,赵秩使日日期为洪武三年三月,而遣使诏谕云南、八番、西域、西洋、琐里、爪哇等地,却是在这年的六月,《明实录》中所载爪哇的首次朝贡则是在九月。*《明太祖实录》卷56,洪武三年九月壬寅条,第1092页。西洋也是如此,据洪武时人龚敩《赠刘叔勉奉使西洋回序》记载,明太祖曾于洪武二年春令刘叔勉往谕西洋,至三年夏始才到达。*龚敩:《鹅湖集》卷5《赠刘叔勉奉使西洋回序》,《四库全书》第1233册,第669页。原文为:“洪武二年春……其令刘叔勉持节往宣朕意,承命喜跃,即日就道,海舶间关,风涛万里,三年夏才至西洋”。因久无信息,洪武三年六月又二次遣使,九月西洋方才首次朝贡。*《明太祖实录》卷56,洪武三年九月乙卯条,第1100页。而琐里的首次朝贡时间,则更晚些,是在洪武五年正月。*《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春正月壬子条,第1313页。此入贡顺序亦如宋濂所述:“其称臣者,高句丽最先,交趾次之,琉球、琐里又次之。”*宋濂:《宋学士全集》补遗卷2《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丛书集成新编》第6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1277页。之所以虚造,显然是想营造一种“万国皆朝、独缺尔国”的假象,以敦促日本尽快效仿。这种在诏书中虚造史实敦促朝贡的情况,在洪武朝的对外诏书中,极为少见。由此可知,相较于其他海外诸国,明太祖似乎对日本的朝贡显得更为重视与迫切。
第三部分的“倭寇”问题是对日诏书的独有内容,也是学界将明太祖对日交涉核心目的定位为“禁倭”的主要依据。不过,细加分析却不难发现其隐含的深意所在。首先,诏书中云“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简单。这次遣使,使臣至日被杀5人,杨载、吴文华被拘三月方才放还,已远远超出了所谓“不答”的程度。*《明使仲猷无逸尺牘》,载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6編37冊,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第349頁。此篇原文虽然名言杀使之事,但其后则以“開諭一節略無見畣”予以淡化。但对这次“杀使”事件,朱元璋却并未过多强调,反而主动以“不答”为由,巧妙避开。其次,据诏书所云,明廷似乎曾一度欲兴兵讨伐,但因被寇者来归,方知“倭寇”侵扰并非日本国王指使,故才停止造舟之役。表面看似为彰显明朝武力,但实际上却将“倭寇”与日本国王分别开来,从而为明、日封贡关系的缔结创设可能。
在将“倭寇”问题缓和后,明太祖在第四部分内容中通过对“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理念的宣扬,充分表明了希望日本“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的真实目的所在。除非日本“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否则不会如元朝般妄兴征伐。所谓“革心顺命”,就是要如爪哇、占城那样“知正朔所在”,*《明太祖实录》卷39,洪武二年二月辛未条,第785页。能“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国……不待谕而知者。”*《明太祖实录》卷47,洪武二年十二月壬戌条,第934页。
由此来看,明太祖最初对日交涉的核心目的是想通过“申交”确立起与日本的封贡关系,将其拉入到新的东亚区域秩序中来,“禁倭”只是次要要求。事实上,《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中的一段记述,就颇值得玩味:
故首命使适日本通好,舟至境内,遇贼杀杀害来使,诏书毁溺。寻有岛民踰海作寇,数犯边卤,多略子女,皇帝一欲通两家之好,悉置之而不问,但令自禁之。*《明使仲猷无逸尺牘》,《大日本史料》第6編37冊,第349頁。
当“禁倭”与“申交”相抵牾时,明太祖显然更倾向于后者。
与洪武二年的其他对外诏书相较,对日诏书特别强调了“修书特报正统之事”问题,这与申交有着何种关联?而从洪武三年对日诏书来看,较其他各地而言,也表现出了对日本申交的重视之意与迫切之情,甚至不惜虚造史实、搁置倭寇问题、淡化杀使事件,这背后又隐含了明朝廷怎样的深意?
“四夷宾服”历来是中原王朝彰显其正统性与合法性的一种必要手段,明代亦然。早在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就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诸地,宣扬“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冬十月丙寅条,第401页。因此,建国伊始朱元璋便遣使四处、播告正统,“皇帝廓清四海,遂登大宝,遣使者播告诸蛮夷,俾知元运已革,而中夏归于正统。”*宋濂:《宋学士全集》补遗卷2《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第1277页。力图营造出比元朝更为盛大的“万国来朝”局面。因此,除元朝传统朝贡国外,朱元璋还多向未曾朝贡于元朝的区域派遣使臣,诏谕往来,“洪武二年春,皇帝若曰:海外之地不内附之日久矣,盖自中唐以来,五六百年于兹。然亦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临,朕岂忍弃之,不使沾中州文明之化哉。”*龚斆:《鹅湖集》卷5《赠刘叔勉奉使西洋回序》,第669页。之后赵秩出使毛人地,*春屋妙葩:《雲門一曲》,载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6編40冊,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第322頁。沈秩往渤泥国,*宋濂:《文宪集》卷4《渤泥入贡记》,《四库全书》第1223册,第347页。杨载往琉球,*胡翰:《胡仲子集》卷5《赠杨载序》,《四库全书》第1229册,第58页。佛麻国故民捏古伦往佛麻国*宋濂:《圣政记》卷2,《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4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610页。等,即是这种理念下的招徕之举,而日本更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环节。
元朝与日本虽未建立正式的国家交往,但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却始终未断,这为明朝廷寻求与日本国交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必要基础。朱元璋在《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一文中就云:“往者我朝初复中土,彼日本僧俗多至,间云使则加礼礼之,或云商则听其去来,斯我至尊将以为美矣,必欲深交日本,是有克勤、仲猷二僧之行。”*朱元璋:《明太祖文集》卷16《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四库全书》第1223册,第195页。而克勤在《致延庆寺座主书》一文中则言:
向蒙古僭入华夏,灭宋自立,日本怒胡人有犬豕之行,即与之为仇,自是学教之徒绝迹于中国矣……今以大国之有节义,尝慕宋而仇胡,又能奉佛敬僧,故特以我取信而来。*《致延暦寺座主書並別幅》,载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6編36冊,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第156頁。
据其所言,明太祖遣使日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认为日本“有节义,尝慕宋而仇胡”,即曾为维护中华正统,否认夷狄占据中华的合法性,而拒绝向元朝朝贡。这与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新朝合法性的塑造,无形中有了某些暗合之处。
事实上,作为与元朝曾有过激烈对抗的“不臣”之国日本,若能“深交”于新朝,其象征意义无疑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为如此,明太祖对日本的朝贡与否便显得尤为重视与迫切了。这点也不难从洪武四年日本怀良亲王遣使入贡后,明朝内外招服诏书中言辞语意的变化,略窥一斑。我们不妨将上述诏书之外,其他诏书中的相关内容,略作排比分析:
1.洪武三年五月,诏谕纳哈出曰:“破竹之势直指川蜀,云南六诏使者相望。交趾、占城万里修贡,高丽称藩,航海来庭。”*《明太祖实录》卷52,洪武三年五月丁巳条,第1030页。
2.洪武三年六月,诏谕元宗室、部落、臣民曰:“朕即位之初,遣使往谕交阯、占城、高丽诸国,咸来朝贡,奉表、称臣,唯西北阻命遏师。”*《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条,第1046页。
3.同月诏谕云南、八番、西域、西洋、琐里、爪哇、畏吾儿等国曰:“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丽诸国俱已朝贡。”*《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戊寅条,第1049页。
4.洪武三年九月诏谕辽阳等处官民书:“近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锁里海外诸国皆称臣入贡,是盖知天命之有归,顺人事之当然者也。岂汝之智反不及耶?”*《明太祖实录》卷56,洪武三年九月乙卯条,第1100页。
通过梳理,不难看出每当有海外新国朝贡后,朱元璋都会很快将其名列入对其他区域的诏书中,进而彰显新朝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同时也是一种敦促来朝的手段。但在洪武四年十月,所谓“日本国王称臣入贡”后,其内外招服诏书中的言辞却发生了一定改变,如在洪武五年正月诏谕云南的诏书中就不再罗列诸国名称,而是用“蛮夷酋长”一言概之,“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莫不称臣入贡。”*《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春正月癸丑条,第1314页。同月,遣使诏谕琉球国的诏书也是如此,“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春正月甲子条,第1317页。可见,日本的朝贡与否,对洪武初叶新的东亚区域秩序的建构,显然具有与他国不同的特殊意义所在。
三、“日本国王称臣入贡”叙事与“良怀”问题
《明太祖实录》关于洪武四年十月的记载中,首次出现了“日本国王称臣入贡”的记录,即日本南朝怀良亲王的遣使入贡。*《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冬十月癸巳条,第1280页。对于此段记录,因言辞略显夸张,日本学界对其真实性长期以来一直存有疑虑。围绕其中的“怀良亲王称臣与否”问题,产生了藤田明的伪作说、佐久间重男的误解说等一系列观点。*蔭木原洋:《洪武帝期日中関係の研究動向と課題》,《東洋史訪》,1996年3月。直至村井章介以佐藤进一关于日本南北朝时期的一系列史实考证为依托,所揭示出的当时征西将军府表现出的南朝内部自立性、分离性倾向,并根据当时南朝所面临的严峻政治、军事形势,指出怀良亲王有想法也有力量完成对明的称臣入贡。*村井章介:《征西府権力の性格》,载《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第282—293頁。中国台湾学者郑樑生也推测怀良亲王很可能是想通过向明的称臣入贡以换取明朝支持,进而挽回颓势。*郑樑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以明史日本传所见几个问题为中心—》第3章《明与征西将军府的交通》,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第146页。这两种说法,目前虽已得到学界的大致认同,不过其中却仍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解明,即《明实录》中为何要对“日本国王良怀称臣入贡”一事进行如此详细而夸张的描述?虽然石原道博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并无过多深意,只是一种“润笔”而已。*石原道博:《日明交渉の開始と不征国日本の成立》,《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紀要》人文学科,1954年第4期。但如果我们详细解读这段记录,却会感到似乎并非全然如此。
在这段记述的前面,描述了洪武三年赵秩出使的情形:
先是赵秩等往其国宣谕,秩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关者拒勿纳,秩以书达其王,王乃延秩入,秩谕以中国威德,而诏旨有责让其不臣中国语。*《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冬十月癸巳条,第1280页。
根据赵秩所述,洪武三年诏书中首先着重指责了日本的“不臣”,这与我们前文的分析颇为契合,也印证了明太祖对日“申交”的核心目的。其后围绕“称臣”问题,日本国王作了如下陈述:
吾国虽夷,僻在扶桑,未尝不慕中国之化而通贡奉。惟蒙古以戎狄莅华夏,而以小国视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赵姓者讠术我以好语,初不知其觇国也。既而使者所领水犀数十艘已环列于海岸,赖天地之灵,一时雷霆风波,漂覆几无遗类。自是不与通者数十年。今新天子帝华夏,天使亦姓赵,岂昔蒙古使者之云仍乎?亦将讠术以好语而袭我也?*《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冬十月癸巳条,第1280页。
这段描述展现出了这样两层含义:1.日本不愿臣服元朝的根本原因,乃在于蒙古是以戎狄莅华夏,非中华正统,作为仰慕“中国之化”的日本,自然不会向夷狄臣服;2.对于华夏元灭明兴的王朝更替,日本一无所知,仍处于“蒙古来袭”的戒备之中。
前者借日本国王之口对元朝统治正统性的否定,实际上潜在地彰显了新朝统治的合法性。而后者则通过“不知王朝兴替”的方式,为明朝故意淡化杀使事件及日本的未能及时来朝,作出了隐性的合理解释。记述的最后,则用尽笔墨,生动地刻画了赵秩临危不惧、慷慨陈词,终使日本国王幡然醒悟、自悔不及,决意尊奉新朝、遣使朝贡的悲壮场面:
今圣天子神圣文武,明烛八表,生于华夏而帝华夏,非蒙古比。我为使者非蒙古使者后,尔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杀我,则尔之祸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无不一当百,我朝之战舰,虽蒙古戈船,百不当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违?岂以我朝之以礼怀尔者,与蒙古之袭尔者比耶?于是其王气沮,下堂延(赵)秩,礼遇有加,至是奉表笺称臣,遣祖来随秩入贡。*《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冬十月癸巳条,第1280页。
怀良亲王的称臣入贡,应该确有其事,但是否真如《明实录》中所记载的那样详细与夸张,则很难确实。不过,这番逻辑性极强的精心描述,使明、日交涉中原本存在的一些龃龉,不仅得到了有效消解还被给予了相对合理的解释,这恐怕也是符合明太祖对日交涉之核心目的的一种刻意之举吧。
在明朝的官方文书中,一直将“怀良亲王”误写为“日本国王良怀”。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日本学者粟林宣夫认为,怀良亲王为挽回颓势,委派九州的中小豪族押送被掳民入明,以换取赏赐品并探取明朝情报。这些豪族在赵秩教唆下,依据上表朝贡形式,将怀良亲王拟作日本国王,但又担忧怀良亲王责难,故而将“怀良”写作“良怀”。*栗林宣夫:《日本国王良懐の遣使について》,《文教大学教育学部紀要》,1979年第13期。这一解说显然是难以成立的,事实上在日本相关史籍的记述中,都明确写明为“怀良”而非“良怀”。如《桜雲記》中就记载:
(建德二年二月)……南朝ノ宫征西将军式部卿怀良亲王ヲ取立是ヲ仰テ、近国ノ诸将附属ス。项日、使者ヲ调ヘ、舩ヲ设ケ大明ヘ遣之。其状ニ曰:日本国王怀良ト书セリ、大明ヨリ日本国王ヘ来ル使者、筑紫ニテ菊池畄テ、其返古又ヲ怀良ヨリ遣ス。*《桜雲記》下,東京:早稲田大学蔵本,第4頁。此书作者不详,但记录较为翔实,据考证可能是江户初期书物奉行浅羽成儀的著作(参见勢田道生:《“南方紀伝”·“桜雲記”の成立時期の再検討》,《語文》2008年第91輯)。译文:“应安二年二月……为寻求南朝征西将军宫式部卿怀良亲王的庇护,临近诸国的诸将纷纷归附。今日怀良亲王安排使者、制造海船,往大明遣使。其书状有云:日本国王怀良作书,大明派往日本国王使者,已经由筑紫的菊池留奉怀良命令护送返回”。
而与事件有关的豪族之一菊池家族的文书《菊池家代々記録》中,也是如此,“武光の嫡子、隈府に城を筑住居す、武威父に劣らず、亲王の命を奉し、応安四年如瑶蔵主を大明に遣ける、赵秩と云ものを日本に遣ぬれハ、是をとどめ、懐良亲王に谒せしめて帰す。”*《菊池家代々記録》,载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史料》第6編40冊,第573頁。译文:“在隈府筑城居住的菊池武光的嫡子,有着不逊于其父的武威,受亲王的命令,于应安四年,护送如瑶藏主前往大明。大明以叫做赵秩的人往日本遣使的事也在此终止,赵秩谒见怀良亲王后便归还了”。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则是由于明朝对日本状况不了解而出现的误书现象。的确,自元代以来中国与日本便无正式通交关系,但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交流的断绝与洪武君臣对日本情况的一无所知。村井章介在《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一书就曾指出,元末明初的众多入明僧应该为朱元璋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对日认知。*村井章介:《日明交渉史の序幕-幕府最初の遣使にいたるまで—》,载《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第246頁。事实上,洪武君臣与日本入明僧是有着诸多联系的,其中著名者如绝海中津、汝霖妙佐、椿庭海寿、权中中巽等。尤其是绝海中津,他于“大明洪武元年二月,航溟南游,寓杭之中竺,依全室禅师,禅师甚器重之,命俾作烧香侍者,后复又转藏主。”*《翊聖国師年譜》,塙保己一編:《続群書類従》第9輯下,東京:群書類従完成会,1925年,第670頁。这里的“全室禅师”就是明朝著名高僧中竺寺住持季潭宗泐,他与朱元璋相当熟稔且往来颇多。据《泐季泐传》记载,朱元璋“建广荐法会于蒋山太平兴国寺……命师升座说法,上临幸,赐膳无虚日,每和其诗,称为泐翁。”*明河:《泐季泐传》,《补续高僧传》卷14,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史部29,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533页。洪武四年,祖阐、克勤受命出使日本前,季潭宗泐与朱元璋还先后赋诗饯行:
天宁禅师祖阐、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会朝廷将遣使日本,诏祖阐与克勤俱。祖阐不惮鲸波之险,毅然请行,上壮之,赐以法器、禅衣之属,令太官进馔,享于武楼下,且谕其国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时天界禅师宗泐尝赋诗饯之,其诗上彻预览,遂俯赐和答。*宋濂:《宋学士全集》补遗卷3《恭跋御制诗后》,第1285页。
当明太祖、祖阐、克勤、季潭宗泐与日本之间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关联的时候,对于急需了解日本情况的洪武君臣来说,真的可以忽视绝海中津等入明僧的存在而不闻不问吗?虽然目前还没发现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入明僧对朱元璋日本认知的影响,但若由此而认为朱元璋对日本情势毫无所知,显然也是不合情理的。
除却“良怀”之外,“日本国王”的称号实际也是错误的。当两种错误同时集中于一人身上的时候,简单以“误写”予以解释恐怕也是难以令人全然置信的。如果说洪武君臣对怀良亲王“日本国王”的最初认识,是由于对日本内情的不了解所致。那么,随着交往的进一步加深,洪武君臣显然已经认识到了这种错误的存在。宋濂在《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中就说,“先是日本王统州六十有六,良怀以其近属窃据其九,都于太宰府”。*宋濂:《宋学士全集》补遗卷2《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第1277页。朱元璋也云,“朕惟日本僻居海东,稽诸古典,立国亦有年矣。向者国王良怀奉表来贡,朕以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明太祖实录》卷90,洪武七年六月乙未条,第1581页。
可见,对于南朝怀良亲王的奉表入贡,洪武君臣并非十分满意。其虽在形式上满足了明朝“四夷宾服”的需求,但在实质上却并未达到朱元璋意欲“深交”于日本的政治目的。因此,在与日本北朝方面尚未取得联系,及其正式奉表入贡之前,朱元璋虽然还是坚持赋予了怀良亲王“日本国王”的正统性称号,但也进一步强化了“表贡允合”的礼仪原则并多次对违礼者却而不受。可以说,在怀良亲王“日本国王”错误称号的背后,也隐含了朱元璋对日本北朝申交入贡的期待。那么,“怀良”误写为“良怀”是否也是一种刻意的笔注呢?
虽然终洪武之世,朱元璋君臣也未能实现对日本的这种政治期待,但明朝从建立伊始便将“王道政治”作为其构建新型东亚区域秩序的重要基础与理念,“十五不征国”的出台便是这一理念、政策的产物,并对以后中国及东亚区域秩序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围绕“禁倭”与“申交”而展开的洪武初叶的对日交涉,正是洪武君臣践行以“王道政治”为基础的新型东亚区域秩序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微观侧面。
(责任编辑:王来特)
[收稿日期]2015-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史上的‘落差—稳定’结构与区域走向分析”(编号:15ZDB06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十六世纪前后的倭寇与东亚区域秩序研究”(编号:10BSS009)。
[作者简介]刘晓东(1972-),男,辽宁凤城人,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年旭(1987-),男,吉林省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日本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6)01-005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