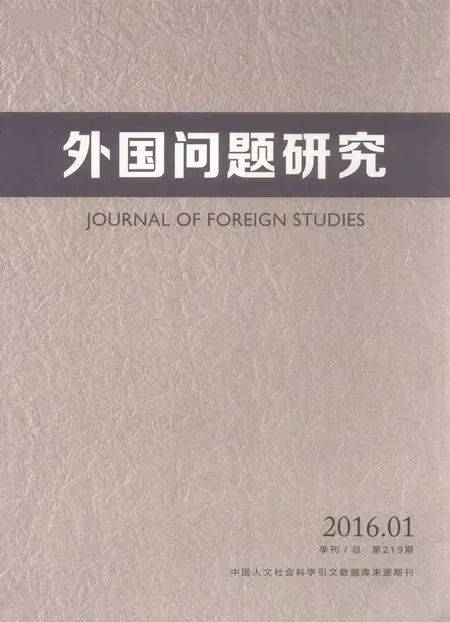松永尺五伦理思想之形成及其儒教实践
2016-03-16王明兵
王 明 兵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松永尺五伦理思想之形成及其儒教实践
王 明 兵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内容摘要]松永尺五思想的形成,既拜其师藤原惺窝的授业所赐,又受到南宋儒者陈淳的深刻影响。从文献对接的角度察之,松永尺五在《彝伦抄》中对“命、性、心、情、意、诚、敬”概念的阐释明显来自陈淳《北溪字义》的解释。松永尺五所主张的儒释道三教调和与儒教“三纲五常”之伦理,贯穿于他践履儒者之“传道授业”的教书讲学的生命历程中。从开设春秋馆、招徒讲学、培养弟子,尤其是江户大批知识人都出自松永门下之史实观之,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儒者形象,才是松永尺五的历史本色。
[关键词]松永尺五;藤原惺窝;陈淳;儒学;教育
一、引言
松永尺五(1592—1657),字遐年,名昌三,又称昌三德,京都府人。在日本儒学史上,多有留名。然而,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对于相关问题均又语焉不详,大都是一笔带过。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1.松永作为日本近世歌学贞门派缔造者松永贞德的次子,在贞德传略中,屡被提及,诚属正常;2.他作为当时儒学大师藤原惺窝的高足,诉诸各史家之笔端,也为自然之事;3.尽管其遗留文字有《尺五堂先生全集》和《彝伦抄》,但是大部分为诗文之作,所以很难从中概括和提炼出能反映他系统学术思想和代表性观点的学说来;4.虽然他不曾有过出仕为官的经历,但他一生以私塾为基、传道授业,门徒逾五千,尤其是弟子及再传弟子木下顺庵、贝原益轩、安东省庵、夜间敬轩、泷川昌乐、冷泉为景、平岩仙门、泽田昌庵、新井白石、室鸠巢、雨森芳洲等均为执江户中期儒学之牛耳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勾勒江户儒学系谱图,松永尺五确乎还是一位无法绕行的重要人物。
《尺五堂先生全集》,作为松永尺五的主要著作汇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曾留传于世。与其师藤原惺窝之著作在日本主要图书馆与文库都有收藏*藤原惺窝著作的一些善本和刻本,在日本著名大学的图书馆都有或多或少的收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著述的流布面和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科系文学研究部收藏有享保二(1717)年藤原未经编录的《惺窝先生文集》12卷;大阪市立大学学术情报综合中心藏有天明八(1788)年的《千代茂登草》;筑波大学中央图书馆所收藏的藤原惺窝文稿为数最多:承应三(1654)年的《惺窝文集》(林罗山、菅玄同编汇)、宽永五(1628)年藤原惺窝训注的《春秋经》、《书经》、《礼记》、《周易》、《诗经》等儒家经典。适成对比的是,迄今为止,松永尺五的著书,仅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和无穷会图书馆四处有其残本收藏,而且都残缺不全:日本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尺五先生全书》,十二卷十册,缺内卷、十一卷与十二卷;京都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尺五堂先生全集》,共有八卷三册,缺卷二、卷十一和卷十二;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尺五堂集》,二卷二册,缺《坤》卷;无穷会图书馆收藏有《彝伦抄》。经德田武对前三地残本的分类汇总与校对稽考,以《尺五堂先生全集》为名,于2000年由唐鹅社(ぺりかん)出版发行。尽管该文集还有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之缺,但它作为人们了解松永尺五学术和思想情形的基本资料,意义诚不可谓小。
就松永尺五的研究而论,学界对其关注者却相对较少。大江文成之《松门之祖尺五及其子孙》当属对松永尺五最早有所关注的论作之一,*大江文城:《鬆門の祖尺五とその子孫》,《本邦儒学史論攷》第三章,東京:全国書房,1944年,第135—154頁。该文对松永尺五家世谱系、学风流脉等问题,均一一揭橥,但其略有余,其详不足。其后,玉悬博之对《彝伦抄》进行了读解,以为松永尺五的不少说法都是陈北溪《性理字义》的翻版,很多地方无异于剽窃;*玉懸博之:《松永尺五の思想と小瀬戸甫庵の思想》,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解說,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505—512頁。今中宽司承此,指出尽管松永尺五《彝伦抄》有陈北溪《性理字义》的鲜明影响,但在日本近世《春鉴抄》、《三德抄》与《彝伦抄》之三大抄本谱系中,自有其思想史的重要意义在。*今中寛司:《江戸时代初头に于ける教训仮名抄について――春鉴抄·三徳抄·彛伦抄の思想史的系谱》,《史林》40—3,1957年。近来,木村昌文在对日本近世生死观的研究中,着力探讨了松永尺五对生死及生命的一些看法。*本村昌文:《松永尺五の死生観》,《日本思想史研究(37)》,2005年,第22—38頁。事实上,倘若综合留存于世的关乎松永尺五的《尺五堂先生全集》和《彝伦抄》来看,松永尺五的思想面貌及其特色,还有对其进一步深探的必要性。
由于本文还试图寻找朱子门人陈淳与松永尺五思想之关联,所以对二者思想之关联的把握也就未尝不是对儒学思想在日本之传播、影响日本的一种探索。仅就陈淳之个案研究而论,目前学界对他的研究也还仅限于一国一域之内,尚未注意到陈淳对松永尺五的影响及其思想在海外的传播。故而,本文也借此突破民族国家之地域限制,在大的东亚视域内以窥中日思想之内在关联。
二、松永尺五与藤原惺窝
松永尺五乃藤原惺窝之高徒,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与林罗山在藤原惺窝笔下处处留迹适成反差的是,松永尺五在其师的著述中,却是鲜有被提及。其中所记载的藤原惺窝与松永尺五的唯一一次诗唱之作,还是得益于林罗山的从中运作。该诗为:
因林道春请和遐年诗
林忠访我叩幽深,袖里遐年诗记游。今日诗文期德业,花之春与秋之实。*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編:《藤原惺窩集》巻上,東京:思文閣出版,1941年,第79頁。
此诗写作之时间,并无明确记载。不过,根据龙川昌乐为松永尺五所做的《尺五堂恭俭先生行状》的记载,大致还是可以考证得出来的。其记曰:“昔日林道春、堀正意、林永喜、菅田德庵于堀正意杏庵亭为诗赋之,曾吟游。时当中秋赏月,昌三先生亦在其席。林罗山子截‘秋月扬明辉’之句,拈出于诗题,各阄之先生,得‘秋’字,则赋之,立成矣。其三四句曰:‘清谈尤胜十年学,风落林间黄落秋’是也。先生惟时,十一岁。林罗山以此诗,献惺窝师。惺窝师见之,惊异,爱其妙龄奇才,祝其远大,谓‘喜!我亲族繁荣’,和之曰‘林忠访我,扣神衣袖里,遐年诗记游。今日斯文期德业,花其春兮实其秋。’是载而在惺窝文集。”*松永尺五:《尺五堂先生全集》,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年,第240頁。松永尺五十一岁时,应是庆长七年(1602)。从所记可知,藤原惺窝对松永尺五之道德文章是欣喜有加,对其才学成就亦抱有相当大的祈望。由此,德田武推断,其或为松永尺五入藤原惺窝之门时所为。*德田武:《尺五堂先生全集解題·解説》,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年,第12頁。如果从诗情来看,这种推断是可能的。
在松永尺五之孙昌琳为其所作的《尺五堂恭俭先生行状》中,曾有藤原惺窝惊叹松永尺五诗作之伟、且收受松永尺五为徒的记载:“元年壬辰诞先生于洛阳教业坊之宅。先生生(性)安静,幼不好弄戏。六岁丧母。自八岁读书精勤甚笃、日夜不倦,出父之歌海,入师之儒林,从事妙寿院惺窝公。惺窝公知其少年诚实简默,必成儒者之名而授与先生,以自所著深衣,十一能诗,佳句惊人。”*松永尺五:《尺五堂先生全集》,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年,第6頁。从松永尺五所遗留的大部分文字皆为五律七绝与杂诗来看,其绝对可称得上是“佳句惊人”。事实上,如果从修辞、用典、遣词、意旨与审美等诸多方面做一个综合衡量和评判的话,松永尺五的诗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超越其师藤原惺窝甚远。从其家学渊源来讲,这是应该的,似乎也是必然的——作为一代歌学大师松永贞德之子,作诗作歌,乃家统使然。
龙川昌乐为松永尺五所作的行状,与松永尺五之孙昌琳所作的行状,就其内容而言,两者并无二致,只不过龙川昌乐的记载对松永五尺受教藤原惺窝之学更为详备。松永五尺“自八岁读书,甚笃日夜不倦,出父之歌海,入师之儒林,从事妙寿院惺窝公。惺窝公知其少年诚实简默,必成儒者之名显父母,以自所著深衣幅巾。是继道统之传,此其证也,云云。”又:“三十而请惺窝公,传周易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卜筮九图太极图,及书洪范九畴春秋奥义。是有一子相传之誓盟,不漏他子矣。云云。”*松永尺五:《尺五堂先生全集》,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年,第240頁。从此可以确知,松永五尺侍师藤原惺窝所习,主要是儒学之业。而且,其所修习的《周易》、《河图洛书》、《太极图》、《尚书》、《春秋》等中国先秦典籍,从知识难度系数来讲,绝对是难于论孟之儒书。而《周易》、《河图洛书》、《太极图说》则正是宋明理学的哲学基础和形而上源头。或许正是通过此般入朱学之堂奥而非只止于宋学之虚表的学习,才将其与一般只知三纲五常的浅弊之儒区别了开来。这也正是世人皆谓松永五尺乃藤原惺窝真正弟子的真正缘由。*玉懸博之:《松永尺五の思想と小瀬戸甫庵の思想》,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解說,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505—512頁。
然而,在藤原惺窝的文集中,却鲜有其高足松永尺五之名之事的详细记载。当然,在松永尺五文集中,也少有藤原惺窝之显现。不过,这不能说明师徒关系徒具虚名或有名无实。相反,松永尺五对藤原惺窝的师恩之情,他是时刻所不敢忘却的。通过其追悼藤原惺窝之挽词可略窥一斑:
悼惺窝师挽词七绝
千载真儒道学存,天乎丧轮泣招魂。何看霁月濂溪水,难遇深衣独乐园。*松永尺五:《尺五堂先生全集》,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年,第77頁。
显然,松永尺五对于其师之逝,悲怆有加,以至于发出了“千载”、“难遇”之叹。确乎,松永尺五的儒学修为,应该说完全来自于其师的传授,其留名于史,也离不开藤原惺窝的着力栽培。正惟如此,才有松永尺五在藤原惺窝逝世之三十三回忌日之时,才能写下如此怀念、感恩其师的悲壮诗篇:
惺窝先生三十三回忌日拈香并叙
庆安弟四重光单于无射旬有两日,惺窝先师之三十三回讳辰也。令嗣为景朝臣究礼奠之敬,尽祭享自诚。夫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惟孝子仁人之至情也。先师者,本朝太辅道长公之世家,而定家乡之云孙也。自幼薙染入淄徒居万年山,禅窟有年于兹,天质英挺夙智朋哲应奉五行蘓颋,一览二妙备四德,并且眼界高明,胸宇开豁,闻往知来,即始见终,触排汉唐记诵之俗儒,尊崇宋元性命之道学,遂脱却嵩山少林之禅机,接得濂溪伊洛之道脉,解法衣,着司马之深衣,抛贝叶,讲晦庵之集注,始点和训于六籍,新极工夫于圣言。昔在延天之诞,膺图宏之才硕学之鸿儒,强记博识之词人,满上列下莫盛于斯。时寔文明之治世,学业之嘉运也。虽然夸佑僤鈆椠之挟夹,耽斗靡争妍之雕虫,刊陈落腐好文藻之绚糜回声,揣病恍诗章之精致,自厥以降,巨魁猾夏兵燹胁国文道学术业如玉,世乏人而不绝如缕,近代海内安泰奸贼绝迹。先师崛起,百世之下超迈千载,之上怀宝韬光。开三经于北肉,想元亮之隐栖存心,尊性养天下之广居,养孟子之浩然,谢绝世,故景师李愿中不足,越阃忙杀杜五郎,世无古今,地无远近,其心同,其理同,则圣圣一揆,何有异论乎?我国真儒之鼻祖,道学之滥觞,舍公其谁欤?伟哉!开来学之功,岂谫谫哉。……惟是孝思迫切之情无所不至乎哉。同制无言以备办香云:
追远曾纯孝,敬同岁月加。深衣温表德,道洗颢无邪。
文澜尊东海,官门联北家。儒林根底同,生宝又生花。*松永尺五:《尺五堂先生全集》,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年,第21—22頁。
全文读下来,一个感知是,与其说松永尺五是在尽弟子之孝,还不如说他在为恩师藤原惺窝谋求其在日本儒林、学界的历史地位。如果说藤原惺窝乃“我国真儒之鼻祖,道学之滥觞”与“开来学之功”勉强还算说得通的话,那么说他“百世之下超迈千载,之上怀宝韬光”就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了。当然,作为弟子,敬奉师尊,铭记其恩,是应该的,亦是必然的。从中亦可确知的是,松永尺五作为藤原惺窝的弟子,已继其师之志,续道统之绪,袭“深衣温表”之德,竭心尽力于儒门大业,藉而以期不负于恩师之厚望。
三、《彝伦抄》的主要思想与陈淳的《北溪字义》
由于《尺五堂先生全集》所收集的主要是松永尺五的五言和七言诗作,而这些诗作大为吟花弄月、游山玩水、饮酒把盏、送朋访友之作,这对于解读松永尺五学术体系、尤其是对于其儒学思想的了解,意义着实不大,故而在对松永尺五学术思想的把握中,《彝伦抄》就成了揭橥其思想观念的主要史料依据。而事实上,松永尺五的遗留著作,除了《尺五堂先生全集》,也就剩《彝伦抄》了。
彝伦,即常理,最早出自《尚书·洪范》:“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顾炎武《日知录·彝伦》曰:“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孟子之言人伦而已,能尽其性,以至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彝伦叙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彝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1页。而松永五尺以为彝伦乃天道、天理,作《彝伦抄》之旨亦是为匡正世俗、拯救世道人心:“天理者,人心之固有也。道者,不待求之日用彝伦之外,舍此何求他哉?弗思之甚也,以兹以易悟之俚语说、纲常之大,尤使向之所谓童蒙书生。迷异教、陷妖术者,粗知君臣父子之道,仁义礼智行若千万人之中,纵令百之十、十之一,也可奋然兴起而抵排异教攘斥妖术,钦崇正道,发挥儒风,则后世苒苒或有洋溢数列、施及万民,岂非世教之幸也乎。”*松永尺五:《尺五堂先生全集》,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年,第221—222頁。由此可知,松永尺五所谓《彝伦抄》,也即是他关于社会基本伦理的相关思考。如果对其思想内容作一总结的话,他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一)儒、释、道三教之平视与调和
松永尺五开篇即言三教问题。他指出:“天地之间,大道有三:儒、释、道也。儒为孔子之道,释为释迦之道,道为老子之道也。我朝释迦之道繁昌,上下仅皈依。儒道虽有,成文字言句之沙汰也。或以读书作诗思为儒道。理学示人、阔人,以此行三纲五常,法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松永尺五:《彝伦抄》,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04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松永尺五认为儒释道之“道”乃老子之道,但他有时也将其混为日本的神道。即便如此,他也往往是站在儒家的角度对神道进行儒学化的解读。他指出,士农工商之四民阶层划分,完全是日本自古作为神道国的产物。显然,这无疑是一种自民族中心主义的认识方式。不过,他在对待儒释道三教问题上,基本倾向还是积极支持“儒道”的:“今此国,可能会佛法繁昌,就佛法之教而言,也应该申行儒道之义也。”*松永尺五:《彝伦抄》,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05頁。
如果结合江户幕府对基督教的禁压政策来看,松永尺五对三教兼收并蓄的宽容态度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江户幕府最初对基督教的禁压,是庆长十六年(1611),而松永尺五著述《彝伦抄》是在宽永十七年(1641),前后相差三十年,从此意义上而言,我们不能不对松永尺五的学术勇气和学术宽容给予积极的肯定。
(二)力倡儒教之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乃儒道之精要,是松永尺五对儒学的一个基本态度。由于松永尺五对儒释道三教一致观念的执著固守,所以其对三纲的阐扬,就难免不有对儒佛之强行拉郎配的现象出现:“三纲,君臣、父子、夫妇所身行之道也。释尊育净饭王之御子,君臣之道也;罗护罗,父子之道;耶轮陀罗女,夫妇之道也。”*松永尺五:《彝伦抄》,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05頁。显然,松永尺五的这种作法,与其师藤原惺窝以及朱学之祖朱熹对佛教灭绝人伦的批判,大相径庭。究其究竟,松永尺五的这种肆意附会,无论在事实上,还是逻辑上,都是不可通约的,所以其意义也自然有限。
就松永尺五的“五常”论述而言,其中亦不乏佛教禅语的鲜明痕迹。他将“仁”解为“心之德、爱之理”,以为儒家之“仁”与佛法“人人具足、个个圆成、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慈悲为利”、“戒杀生”等名异实同,均是在实行“仁道”。*松永尺五:《彝伦抄》,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05—306頁。将“仁”解为“心之德、爱之理”的做法,完全是袭自朱熹“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的解释,而且他接着将“义”解为“心之制、事之宜”也同样是来自朱熹“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1页。同样,他对“仁义礼智信”之五常的理解,也几乎完全是来自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说法。比如他解“礼”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智”是“智之理、心之别,知是非邪正”、“信”为“无一不实”。*松永尺五:《彝伦抄》,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06頁。当然,他也试图从佛法中为“仁义礼信”找出相当的对等戒律来,认为“仁”对应“慈悲”、“义”为“戒偷盗”、“礼”乃“戒邪淫”、“信”是“无妄语、绮语、恶口两舌”。难以思量的是,他并没有为“智”在佛法中找出对等的戒条来。小乘有五戒、八戒、二百五十戒,大乘有三聚净戒、十重四十八轻戒等,而他却不能从中择列出与“仁义礼智信”一一相对应的佛法戒律来。倘若从“三教合一”论的视域观之,他的这种作法也是有理论渊源的。*参阅:晁迥:“儒家之言率性,道家之言养神,禅家之言修心,其理一也,何烦诤论?”又指出尽管“理”同,但佛教之理是高于儒、道之理的,故佛可涵容儒、道:“孔氏之教,在乎名器,如释氏之相宗也。老氏之教,在乎虚无,如释氏之空宗也。唯释氏之教,本乎性理,而兼该二教之事,方为臻极。”张商英拿用药疗疾做譬喻,认为三教虽同在救治众生迷失本性之病,但其方法和疗效皆不同:“三教之语以驱其惑者,药也。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内;儒者赅博,而佛者简易。儒者使之求为君子者,治皮肤之疾也;道书使之日损、损之又损者,治血脉之疾也;释氏直指本根、不存枝叶者,治骨髓之疾也。……三教之书,各以其道善世砺俗,犹鼎足之不可缺一也”(晁迥:《法藏碎金录》卷九,《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第10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79页);张伯端:“老氏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修种,以逃生死。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其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如得其要枢,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论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又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岂非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缁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一而同归矣!”(张伯端著、王沐浅解:《悟真篇浅解·自序》,中华书局,1990年,第1—2页。)
(三)心性论与陈北溪的《北溪字义》
在松永尺五看来,对“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社会基本伦常规范的恪守,乃是社会正常运作的前提。如果从“成人”——人之所以为人的形而上诉求来看,除了对三纲五常的恪守外,对“命、性、心、情、意”等关乎人心性命理的彼岸世界的关注,也应该是人关注其自身存在的根本要求。这种思考,也即是朱子学对宇宙人生的基本关注点。在朱子学体系中,关乎心性命理的哲学概念,数目众多。松永尺五对其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命、性、心、情、意、诚、敬”这七大核心概念上。
比如他对“命”的解释:“命,所受天也。有理有气,生成者谓之气,气之主谓之理,且理气不分也。万物受此理而谓之天道;万物受理之所谓之天命。人受此气,或富贵,或贫贱、或长寿,或短命,或恶运,或幸福,皆有之。其由气之长短厚薄所致也。此受之气或有变,又气有清浊之分,受清之气,成智者贤人;受浊之气,成弱者不肖者。受气之后又成气之所也。故学文,成贤人智者,此即学文之重要之所在也。”*松永尺五:《彝伦抄》,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08頁。显然,松永尺五的这种“气质之性”说,有着朱熹思想的鲜明色彩。不妨一观朱熹之言:“人所禀之气,虽皆是天地之正气,但衮来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异。盖气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恶也。”“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8页。两相对照,不难发现松永尺五的言论只不过是对朱熹发言的一个翻版或改写,就其思想深度而论,着实无甚新意。
关于“性”,松永尺五言道:“理与气之受谓之性。有性即有理,理出不离气。天地受之,谓之理,人受之谓之气。……此性,荀子见之恶、杨子见之善恶混、韩退之有上中下三品说、近代东坡云未有善恶。……此与佛法云作用是性相似也。儒者之言性善,自孟子而至周茂叔、程子,愈盛也。此性之外,有气质之性。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理一而分殊也。最前有清浊之气。本分之性,尽善成恶;气质之性,有善恶。”*松永尺五:《彝伦抄》,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08—309頁。在此,除了其所比附于佛法中的“作用是性”之论述外,实在很难再找寻得出属于松永尺五自己真正的思考,因为“天理之性”、“气质之性”、“理一分殊”均来自于朱熹的发言。
值得注意的是,松永尺五接下来对“心”、“情”、“意、诚”的阐述,则主要是袭自朱熹弟子陈北溪对理学核心概念的总结。
对于“心”,松永尺五道:“心为身之主,性动之所谓之心,如石中有火就是性,由内而出,火之形之明即心也。性和知觉,心之名也。心从气来而不离理也。物体六根之作,食物饮水,知热知冷,是心也。此皆适理而心正;邪气存而心不正。心有体用,具众理之所谓之体;应万事,感而随通之所,谓之用。”*松永尺五:《彝伦抄》,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09頁。陈北溪言:“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运动,手持足履,与夫饥思食、渴思饮、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为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为邪气所乘,内无主宰,所以日用间饮食动作,皆失其常度,与平人异。理义都丧了,只空有个气,仅往来于脉息之间未绝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为性,得天地之气为体。理与气合,方成个心。”“心有体有用,具众理者其体,应万事者其用。寂然不动者其体,感而遂通者其用。体即所谓性,以其静者言也。用即所谓情,以其动者言也。”*陈淳:《北溪字义》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总0709册·子部00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11页。
对于情,松永尺五道:“情,性之所动也,而有七:喜怒哀乐好恶欲。此七者,存于心而无过不及谓之情。有过不及者,谓之私欲。情本来好物。此七者之情,与人所生,不可缺也。”*松永尺五:《彝伦抄》,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09頁。陈北溪解释为:“情者,性之动也。在心里面未发动底是性,事物触着便发动出来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这动底只是就性中发出来,不是别物,其大目则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情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无,不是个不好底物。”*陈淳:《北溪字义》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总0709册·子部00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对于“意”,松永尺五指出:“意,心之所发也。思而心,性动而情,心动而发谓之意,由心而直出。”*松永尺五:《彝伦抄》,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09頁。陈北溪认为:“意者,心之所发也,有思量运用之义。大抵情者性之动,意者心之发,情是就心里面自然发动。”*陈淳:《北溪字义》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总0709册·子部00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页。
对于“诚”,松永尺五解释道:“诚,真实无妄。从天地自然之理中出谓之诚。知诚之一字,而叫忠之一字。忠乃人之工夫上而言。天地之诚,夏热、冬冷,天道之诚。”*松永尺五:《彝伦抄》,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10頁。陈淳的阐释是:“诚字与忠信字极相近,须有分别。诚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出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说。诚字后世都说差了,到伊川方云‘无妄之谓诚’,字义始明。至晦翁又增两字,曰‘真实无妄之谓诚’,道理尤见分晓。……诚字本就天道论,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只是一个诚。天道流行,自古及今,无一毫之妄。暑往则寒来,日往则月来,春生了便夏长……*陈淳:《北溪字义》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总0709册·子部00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对于“敬”,松永五尺道:“敬,心之明也。静而无事之时,常内明,动之时,心如其事之动,凡可谓心之不移。有‘一无适’之注也。敬,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本。”*松永尺五:《彝伦抄》,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11頁。陈北溪的阐述是:“程子谓‘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无适之谓敬’,尤分晓。……敬所以主宰统摄。若无个敬,便都不见了。惟敬,便存在这里。所谓敬者无他,只是此心常存在这里,不走作,不散慢,常恁地惺惺,便是敬。……无事时,心常在这里,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时,心应这事,更不将第二第三事来插,也是主一。……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本。”*陈淳:《北溪字义》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总0709册·子部00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29页。
通过上述对松永尺五“命、性、心、情、意、诚、敬”这七大核心概念的阐释和发挥与朱熹及其弟子陈北溪的发言之间的文献性对接,我们可以断言,松永五尺的确是站在了朱子学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延长线上。当然,对此松永五尺自身也有着清晰的认识,以为:“性命之书,奠切焉;道德之学,莫详焉。”*松永尺五:《尺五堂先生全集》,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年,第223頁。
尽管松永五尺对其师藤原惺窝以及朱子学崇拜有加、且誓志以弘扬性命道理之学为安身立命之所,一生锲而不舍,躬身实践。然而,其思想体系中蕴含着的佛教因素,也是异常明显的。他在其理学思想的理解和阐发过程中,不时拿佛法予以参比。比如他在对“心”的阐发中,指出朱子学之“心”与《法华经》中所谓的“三界惟一心、心外无别法”、“地域天道皆我心、是仏非所知”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松永尺五:《彝伦抄》,日本思想大系28《藤原惺窩·林羅山》,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12頁。从学理的角度而言,松永五尺的这种比附或拟比并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朱子学的不少概念体系、论证逻辑和思想意旨都受过佛教哲学的重大影响,这已经被学界所证明。*参阅:高建立:《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从其思想主要倾向来看,其儒学者的身份和角色定位,则是毫无疑问的。
四、结语:松永尺五的儒教实践认知
与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的思想倾向相较,松永五尺的思想几乎可以说是毫无特色。从思想体系建构来说,它既没有藤原惺窝儒教、道家、佛法乃至神道教相容并包的庞大规模,也没有林罗山以朱学为体而以神道为用所构建起来的一派“理当心地神道”喧人耳目;从思想特色来说,既无法与藤原惺窝思想的“折衷综合性”相提并论,又难望林罗山凌厉的“排佛释耶(基督教)”锋芒之项背。总而言之,就学术成就与思想贡献而言,松永五尺既无法超越其师藤原惺窝,亦难匹敌同门师兄林罗山。
然而,如果从学术实践的角度来衡量,作为一个教育实践家的松永五尺,才是他学术人生价值的实现形式,也是他历史存在的本真面貌。而这也是我们对其学术功绩予以定评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这主要体现在春秋馆的开设与以此为据点而穷其一生尽力于江户教育和人才培养。
春秋馆,乃松永尺五一生心血寄托之所。它由松永尺五于宽永五年(1628)开设,至第十代松永信藏于明治二十二年(1880)废校而终,前后存续达二百五十年之久。其经营维持,自始至终,皆由松永家族担当。龙川昌乐对松永尺五开坛讲学的轰动场面有过这样的描绘:“开讲筵,门人倍多,官门槐宫得接孟邻,而访问不绝,冠冕佩剑满座上,车驾奴隶盈门巷。”*松永尺五:《尺五堂先生全集》,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年,第240頁。这种盛况,衡之于江户讲堂、学寮之私塾,委实并不多见。而据大江文城的推算,至少有五千弟子曾受教于此校。*大江文城:《本邦儒学史論攷》,東京:全国書房,1944年,第147頁。松永尺五门下,人才辈出,诚为实情。如果从以下江户时代颇为著名的众多学者皆出自松永之门这么一个事实进行考虑的话,就不能不将“教育巨匠”的桂冠置于松永尺五的头顶。他们分别是:木下顺庵、平岩仙山、冷泉玄谭子、安东省蓭、贝原益轩、宇都宫遁蓭、龙川昌乐、夜间静轩、伊藤万年、三宅玄三、林厚蓭、田生蓭可敬、柴田良蓭、杜宗之、田渊三轴、田代宗的……等知识人。而其中顺庵门下,又出现了新井白石、室鸠巢、雨森芳洲等江户中后期的儒者。如果没有这些儒者,江户儒学势必会失去半壁江山。
对于松永尺五及其高徒木下顺庵培养弟子的教育功绩,柴野栗山曾道:“参谋大政,则源君美在中,室直清师礼,应对外国则雨森东伯阳、松浦仪祯卿,文章则袛园瑜伯玉、西山顺泰健甫、南部景衡思聪,博该则柛原玄辅希翊,皆瑰奇绝伦之材也。其冈岛达之至性、冈田文之谨厚、堀山甫之志操、向井三只气节、石原学鲁之静退、亦不易得者。而师礼之经术,在中之典型,实旷古之伟器,一代之通儒也。”*柴野栗山:《錦裏先生文集序》,转引自大江文城:《本邦儒学史論攷》,東京:全国書房,1944年,第150頁。所褒扬的这些人物,皆为执江户学艺之牛耳者。
尽管松永五尺并没有留下有关教育问题的思考,其残缺不全的遗留文集中除了吟风弄月的满篇诗歌外,能够揭橥其思想面貌的相关数据也没有多少,但是,从开设春秋馆、招徒讲学、培养弟子,尤其是江户大批知识人都出自松永门下之史实观之,松永五尺绝对是一个难得的务实教育家。这,应该才是松永五尺本来的历史面貌。
从松永家族史的角度观之,自中世始,作为日本俳句和歌学家的松永家族就有着家族性的佛教法华信仰,以日莲宗为信奉对象,忠贞不二。而松永尺五却一改松永家族之佛教信仰,转而改投儒门,开设儒教私塾教育,招徒讲学,宣传宋明理学。松永的这一“改换门庭”行为,无疑是对家族佛教信仰的背弃。不过,倘若将他的这一“脱佛入儒”行为置于日本佛儒互争的思想背景下来观察,其“倒行逆施”倒也反映出了宋明理学传至日本、在江户时代所具有的思想魅力和理论革新意义。
松永尺五以春秋馆为志业,开日本江户时代儒者创办教育私塾之先河。稍后的不少的儒者都以松永尺五为楷模投身儒学教育事业,兴办私塾与书院,一时蔚然成风,如伊藤仁斋所创办的古义堂、中江藤树建立的藤树书院等。江户社会私塾教育的兴起,一方面打破了日本中世知识权力和思想教育由贵族与僧侣阶层所垄断的社会控制体系,另一方面,“学在民间”之私塾教育的下行实践,使得社会风貌为之大变;思想与教育的自由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和扩大了社会的自由化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江户儒者的教育实践活动乃是促使日本近世社会解放甚至是“近代化”启蒙的动力要因之一。
(责任编辑:王来特)
[收稿日期]2015-09-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日本禅僧‘脱佛入儒’历史过程研究”(编号:12CSS004)。
[作者简介]王明兵(1982-),男,甘肃酒泉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6)01-0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