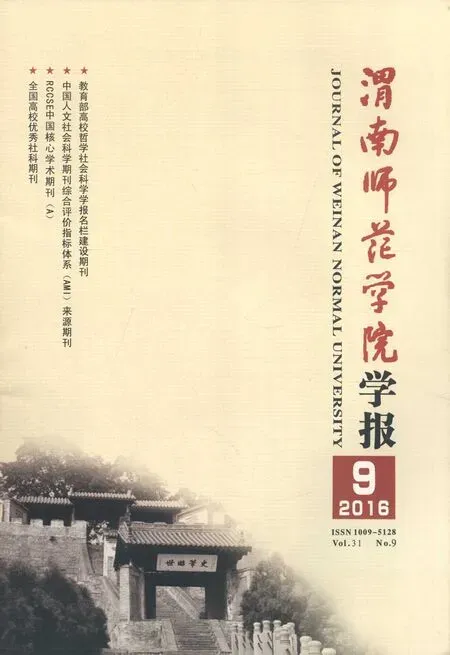论《史记》的音乐隐喻价值
2016-03-16王炳社
王 炳 社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论《史记》的音乐隐喻价值
王 炳 社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摘要:《史记》是一部具有很高隐喻价值的著作。艺术隐喻就是采用替代、暗示、借用、讽喻等方式而使客体非直接表现化,也就是以非直接表达的方式,从而使对象意象化的过程。所以,从艺术思维的角度来看,《史记》是被意象化了的,是一种隐喻的存在。因此,《史记》中关于音乐的记述具有隐喻价值。其主要表现于:可以观风俗、知民情,可以传达社会声音,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摇荡人情感、启发人心智、感化人灵魂,可以表现人的内心情感,可以以音观世,其声调、乐器、演员的具体动作、人们的喜好等也具有隐喻价值。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音乐隐喻;价值
著名《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先生说,《史记》中存在着大量隐喻问题。这也就是说,《史记》是一部具有很高隐喻价值的著作。但此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如今,隐喻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关于《史记》中的有关隐喻问题,不管是史学界还是文学界,至今关注者寥寥,而对《史记》音乐隐喻价值的探讨更是空白,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史记》的音乐隐喻价值作为该著作隐喻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展开研究,无疑对我们研究司马迁和《史记》都很有意义。
隐喻,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人类普遍的一种思维方式,是超越本体而创造出新意义的思维活动”[1]60。而从艺术思维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已知的某一对象的个别属性来暗示或者隐含另一对象相似属性的对材料的特殊加工处理及整合过程”[1]76。以此而言,对象意义实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隐喻艺术,一种隐喻艺术思维的过程。因为创造主体“意向”的缘故,对象被思维所运作,从而具有了某种价值。所以简单地说,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2]79。具体来说,“‘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2]79。从艺术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隐喻就是采用替代、暗示、借用、讽喻等方法而使客体非直接表现化,也就是以非直接表达的方式,从而使对象意象化的过程。所以,从艺术思维的角度来看,《史记》是被意象化了的,是一种隐喻的存在。因此,《史记》中关于音乐的记述具有隐喻价值。
一
音乐具有观风俗、知民情的隐喻价值。
关于《史记》中的音乐隐喻问题,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线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3]2702司马迁此言是说自己一不能凭忠诚取得皇上信任,二不能为国家招贤纳才让那些奇才为国家效力,三不能对敌作战建立奇功,四不能获得高官厚禄光宗耀祖。这四点可以说全是隐喻,从中我们能够看出当时朝廷存在一定问题。其言外之意就是自己最多也只能尽一个史官的职责罢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曾一度奸佞当道,忠贞之言往往被遏制,真正的人才得不到重用,有功之臣得不到肯定和重用,愿意为国家贡献力量的人才常常被误解和屈辱。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为忠臣也只能在一种郁闷中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罢了。怀着更大的抱负想干更多的事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在遭受腐刑之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司马迁也只能以隐喻的方式来撰写历史了,所以他笔下的历史我们也只能以隐喻的方式来解读,其中对音乐的记述也常常是采用某种隐喻的方式。
《史记》中关于音乐的记述,主要集中于《五帝本纪》《夏本纪》《乐书》《殷本纪》《田敬仲完世家》《刺客列传》等篇章中,当然其最基本的观点则集中表现于《乐书》中。据《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迁记载音乐,是因为自秦焚书坑儒以来“礼乐损益”[4]3319。由此看来,司马迁是本着“补损”的理念来整理音乐史料的。也就是说,他更多的是要“继五帝末流”[4]3319,重立“周道”[4]3319。因而《史记》对音乐的记述,更多是隐喻正统的价值观,是要弘扬“周道”。在上古时期,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也是某种权力的象征,只有身份高贵的人才可以拥有音乐。因此,在尧舜时代,当尧帝年迈的时候,他经过反复考验和思考,觉得舜可信,遂让帝位于舜,“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4]34。其中的赐予就有乐器“琴”,这是很高的礼遇,由此确立了舜的帝位。这也说明,早在上古时期,自尧舜开始,就已经十分重视音乐了。他们之所以重视音乐,就是因为音乐具有重要的隐喻价值。对此,《史记·五帝本纪》有记载:舜帝在天下太平之时要对大臣们进行分工,众人推荐伯夷典三礼,伯夷则推荐夔、龙,于是舜命夔典三礼。
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4]39
据传,夔是舜帝时期很有才能的人。舜帝之所以任命夔掌管音乐,其目的就是要达到人与神和的境界。而夔不仅能够做到“神人以和”,而且能够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可见,当时音乐的隐喻价值就是促使人与人、人与天地和谐的。由此看来,音乐确实具有“和”的隐喻价值。因此,当禹登基以后,“乃兴《九招》之乐”[4]43,他也主要是看重音乐的亲和价值。由此也不难看出,司马迁是很重视音乐“和”的隐喻价值的。当然,依靠音乐,也可以观风俗、知民情,这是音乐的隐喻价值之一。因此禹说:“余予闻六律五声八音,来始滑,以出入五言。”[4]79-80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都看重音乐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历代帝王们还常常参与修乐、作乐,如《夏本纪》记载:
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钦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4]43
夔行乐,已经让舜帝感受到了音乐巨大的隐喻价值,于是为了让天下和谐,百官百姓都能够守礼守规,舜帝也即兴创作了两首歌,其内容都是教育大臣们要和谐共事的。后来于禹帝时期兴起的《九韶》,就成为祭祀山川神主的乐章,可见《九韶》就是隐喻祈神保佑、天下和谐的音乐,其隐喻所在不言而喻。
二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音乐的产生原本就是人们表达、交流情感的一种手段,它本身就是一种隐喻的存在。因此司马迁认为,作为统治者,正常的音乐活动并没有错,关键是要把握好度,不能过分,不能沉溺,如果整天沉溺于音乐,那就不应该了,甚至是很危险的,因为音乐对人的情感影响太大太深刻了。
随着氏族公社的诞生,音乐便成为氏族首领特享权力的某种隐喻。后来,阶级出现了,音乐也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什么人享受什么音乐,便有了严格的等级限制,所以音乐的隐喻内涵更加明晰。这如同《诗经》中的风、雅、颂一样,对各路神仙或逝去的统治者首领,就用歌颂的音乐,即所谓“诗人歌乐思其德”[4]112。而宫廷的音乐都是很正统的,不能乱来。只有乱世,才会有淫乱的音乐。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殷纣王“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4]121。所以,社会怎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去观察社会,如果光听一听音乐,就能够知道社会的“正”与“乱”了。因此,音乐的隐喻价值之一,就是它是“社会的声音”。
在古代,宫廷中的宴飨会有音乐演奏,但也是因情因景而乐。如周惠王时期,因夺大臣园圃而生乱,大夫边伯等五人不满,计划招来南燕、卫国的军队攻打惠王,惠王逃奔到温,而后留在郑国一个叫栎的地方。燕、卫等立周釐王的弟弟穨为王,但穨却整日沉迷酒色,即所谓“乐及徧舞”[4]151,就是整日沉迷于六朝的舞乐(包括杂舞),最后招来杀身之祸。按说六朝的音乐是华夏正统的音乐,它上承九代之文化传统,是在旧有的相和歌和由南方民歌发展起来的“吴声”“西曲”相融合而发展起来的音乐,穨王享用这样的音乐应该是没有什么过错的,其主要问题就在于“沉溺”。他整天沉溺于舞乐,荒废朝政,这当然会引起众人的不满,因而才有“郑、虢君怒”[4]151。于是惠王四年,“郑与虢君伐杀王穨”[4]151。这里,《史记》关于音乐的记述,其隐喻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说明司马迁在文化上是趋于保守的,他对南方的所谓“蛮夷文化”是持保留意见或排斥的;二是音乐的专属和等级制度是应该遵守的,不可妄为;三是表明司马迁的音乐隐喻观,“乐可乱政”,“乐可荒政”,所以作为国君,对音乐应该持审慎态度;四是因穨王“乐及徧舞”而被伐杀,也说明司马迁心目中的“正统”乃是自周朝传承下来的文化。
三
司马迁认为,礼乐具有规范人们行为的隐喻价值。他继承了前人“治定功成,礼乐乃兴”[4]1175的观念,认为音乐实际上是政治安定、事功完成的隐喻。统治者修订音乐的隐喻所在不言而喻,就是为了提升人们的品德修养,为了“节乐”[4]1175,为了对人们的言谈举止予以规范,“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4]1175。社会安定了,人们在道德修养、做人处事方面对自己要求也高了,即所谓“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4]1175。司马迁认为,音乐作为社会的隐喻,它能够准确反映出社会的正邪面貌和内在本质。当年郑国淫声四起,未能得到很好的遏制,最后郑国灭亡,“并国于秦”[4]1176;到了秦朝,秦二世被赵高等太监左右,不听李斯言,“秦二世尤以为娱”[4]1177,纵情声色,抛弃传统,最后国家也灭亡了。在司马迁看来,音乐无小事,这是很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尤其是皇上制作音乐,就必须“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4]1178,关注音乐的隐喻价值,这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注意的。
所以司马迁肯定,音乐的确是隐喻的,这是因为: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4]1179
司马迁认为,音乐的产生本身就是隐喻的,它是因“人心感于物”而产生的,这是天然的形态,因而就需要对诸如“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等心情下产生的不同的音乐进行引导规范,不能任其发展。这里,司马迁把音乐和礼、刑、政并列,认为“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它们的方法形式不一,但其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让人心为一。
因此,司马迁进一步指出,音乐作为一种隐喻的存在,在规范音乐的同时,作为统治阶级,也应该认真听一听真正代表人民心声的音乐,这对于了解民情,及时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很有好处,也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惉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共君骄;商乱则搥,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4]1181-1182由此看来,音乐作为意识形态的隐喻,政之“和”与“乖”,君是否“骄”,臣是否“坏”,民是否“怨”,事是否“勤”,财是否“匮”,都可以从音乐中体现出来,音乐及其宫、商、角、羽、徵其实就成了社会的隐喻,因为“隐喻是人们选择的一种看待事物、感知现实的方法”[5]132,这是千真万确的,司马迁深知这一点。其实,司马迁是有自己鲜明政治观点的,但出于种种考虑,他还是隐喻地用音乐来说明他的政治观点,这样更为巧妙,也更容易让统治者明白和接受,因为“隐喻使复杂的政治问题为大众所了解和理解,因为‘隐喻不仅简化了复杂的政治,更重要的是包装了无形的政治,给予抽象问题以生命力’”,且“‘就政治家的交流而言,隐喻能使他们避免直接提及而伤及脸面’”[5]99。
音乐的确具有规范人们的行为、制约人们的欲望、和悦宣导人民心声的作用,所以先王就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礼乐,而且用法律保障其施行,即司马迁所言“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4]1186。所以对礼乐要很好地规划,充分挖掘礼乐的隐喻价值,发挥礼乐的隐喻作用,做到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因而解决社会问题首先要靠礼、乐,其次才是刑、政。而且,礼乐对老百姓的教化功能和作用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4]1189。也就是说,礼是对人与人之间的等差进行精密的区分,由此以启发引导人们了解因等差而必须彼此敬重的道理;乐则是综合各种不同的声音,予以有机调节组织,使其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启发引导人们了解群体生活互亲互爱互敬、团结友好的道理,即所谓“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4]1188。所以,礼因等差而形成隐喻,乐因声音的不同而形成隐喻。因此,声音符合乐理的高低快慢就是音乐的隐喻。由此看来,司马迁是赞成社会等差观念的,他对音乐隐喻价值的发掘也是颇有新意的。
四
司马迁认为,音乐是“德”的隐喻,音乐创作应该充分挖掘其隐喻价值,使其对人们的心智启发、思想教化达到最大化,这和汉代强调艺术政治伦理价值的观念是一致的。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容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4]1191-1192
由于音乐本身代表着天地万物间最和畅的情态,所以和历代统治者的观点一样,司马迁也特别看重音乐对社会发展的隐喻价值。因此,他认为音乐创作一定要讲究原则,不能随性,否则的话,便会“过作则暴”[4]1191。这个原则就在音乐本身,也就是一定要按照音乐本身“和畅”的要求,遵循音乐本身的规律,如此,音乐摇荡人情感、启发人心智、感化人灵魂的隐喻价值才能够体现和发挥出来。
司马迁认为,音乐的本质就是追求天地之间和畅的,这也是音乐最根本的隐喻价值之所在。所以音乐创作就是要贯彻天地和畅的精神,要把天尊地卑、君臣上下、人物等差等理念贯穿其中,音乐的旋律(隐喻因素之一)就应该像“地气上隮,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兴焉”[4]1194-1195一样,精准把握天地人间的一切规律,有起有伏,有张有弛,有升有落,只有一切相和畅达,也就是做到“天地之和”[4]1191,那才是真正懂得了音乐创作的奥妙,如此创作出来的音乐才具有较高的隐喻价值。因此司马迁进一步认为,音乐是无所不能的,它能够“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4]1196,所以不能小看音乐,只有很好地挖掘礼乐“天地之情”[4]1196之隐喻价值,天下才会和畅无比了。
司马迁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音乐就是“德”的隐喻,即所谓“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4]1197。在司马迁看来,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配拥有和欣赏音乐。从艺术隐喻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音乐实际上是“德”的替代。所以在舜帝时代,像《南风》(相传舜帝作诗,夔作曲)那样的音乐,就是赏赐给有德的诸侯的最高礼遇。可见作乐和赏乐都是有讲究的,那就是首先要考虑音乐的隐喻价值,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情绪宣泄。因此司马迁认为,音乐是一种隐喻的表现,是很高雅高尚的艺术,是不能随意亵渎的。所以万事都要有所节制,而不能任性妄为,有如“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4]1199,创作音乐一定要注意其隐喻价值和功能,要以陶冶人的性情和教化人民为主,一定要适时和合乎常态。可见司马迁对音乐这种时间的艺术之真谛和音乐陶冶人性情的功能的了解是颇深的,所以他说“乐者,所以象德也”[4]1200。
五
司马迁认为,音乐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这也是音乐的隐喻价值之一。司马迁充分认识到了音乐艺术的特殊性,认为“乐其所自生”[4]1201,也就是说,音乐是人内在情感的流露,是情感的隐喻,这和现代西方表现理论的认识有某种相似之处。现代西方表现理论认为:“音乐作品中表现的情感,是在创作它的时候倾泻或涌入到作品中的,而不是作曲家在平静专心的时候有意识地冷静地涉及到音乐中的。”[6]150也就是说,音乐创作靠的不是无序的情绪,而是激情,一种“思”之下的激情。艺术是苦闷的象征,是表现欲望下的苦闷促使艺术家走向创作,使他们感到不吐不快,因而,“有如铁和石相击的地方就迸出火花,奔流给磐石挡住了的地方那飞沫就现出虹采一样,两种的力一冲突,于是美丽的绚烂的人生的万花镜,生活的种种相就展开来了”[7]3。当然,司马迁所认为的音乐激情,并不是失控状态的情绪,因为他深知,人在特别激动的时候是不宜进行创作的,因为那不利于艺术隐喻的挖掘。况且就音乐而言,它要求表达统一共通的情感,即所谓“乐统同”[4]1202,“礼乐顺天地之诚”[4]1202,因而绝对个人的情绪化的东西当然是不符合音乐的本性的。司马迁的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切中了音乐隐喻的实质。
司马迁认为,音乐就应该表现社会生活的主流,艺术家就应该表现万事万物安详和泰、繁荣茂盛的情景,而不应该违背事物的自然规律,这是音乐的基本要求,也是汉代音乐隐喻的基本出发点和常态。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翮奋,角觡生,蛰虫昭稣,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4]1203
由此看来,音乐内在的隐喻是很深刻的,并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只有那些谙熟社会上下前后秩序的人才能够真正把握音乐隐喻的本质,即所谓“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4]1206。也就是说,音乐的隐喻价值就在于其移风易俗、感化人心、趋善向美的力量。因此,依音乐的本性来看,它是最容易使人情感激荡的艺术,也最能反映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以说“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啴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经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4]1206。简言之,音乐就是社会现实生活的隐喻。因此司马迁认为,创制音乐首先要考虑音乐的隐喻价值,即要做到“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4]1208,要“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4]1208。
司马迁认为,要通过对音乐的创作和欣赏,让接受者对人生获得深刻的体认,这可以说是司马迁对音乐隐喻的社会学认识,对我们今天的音乐创作不无启发意义。司马迁准确把握住了中国人思维系统当中具有“正义感觉”灵魂的一面,他所看重和强调的正是音乐中正平和、阴阳刚柔和畅的隐喻价值。同时,他也指出,乐可观世,如果出现“乐淫”的现象,那正好可以说明“世乱”,因而淫乐便是乱世的隐喻。因此,就社会发展来说,音乐具有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对音乐创作一定要加以引导,而不能“放任自流”,音乐创作一定要和一定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合拍。也就是说,音乐是人的真情的表现,不可虚伪做作,因此对诗、歌、舞的创作必须依本于人内在的心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音乐的隐喻价值,即所谓“是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4]1215。
六
以音观世,是《史记》隐喻价值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音乐的隐喻价值进行了辩证分析。在谈及音乐隐喻价值的时候,司马迁常常把乐和礼相提并论,因为这二者一放一收,恰好是人性的两个方面,即所谓“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4]1218。而一个人只有达到“内和而外顺”[4]1218之时,就达到了很高的修行,一般人自然不敢和他争论是非,也不敢对他有丝毫的怠慢情绪,可见礼乐对培养人的精神境界是多么重要。这虽然可以被看作是正统的思想,但对我们今天的人才培养仍不无启发意义。
司马迁认为,只有礼乐二者相互配合,其隐喻价值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因此他说:
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谦,乐主其盈。礼谦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谦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4]1219
在司马迁看来,音乐虽然要求充分的喜悦满足,但也不是一味的放纵,而应该是极限之下要有一定的自我抑制;礼仪虽然讲谦退,但也不是说一味的谦退,而是在谦退中提升人的涵养,从而获得奋勉求进的精神,这才是礼乐的真正隐喻价值所在。因此,对音乐的喜悦和礼仪的谦退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定要辩证地去看待这二者。
司马迁认为,音乐作为人情感的隐喻,通过人的嗟叹吟咏、手舞足蹈等,就能够体察到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好的音乐能够感化人、引导人,因而音乐创制者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多创作一些“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纶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4]1220的符合真善美的音乐,做到“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4]1220,这样,音乐的隐喻价值才算得到了真正体现,古代先王也深知这一点。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齐矣。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4]1221
所以,司马迁认为,观察一个社会,了解一个人,也许光听一听其音声,就可以判断出这个社会或某个人的喜怒哀乐了。音乐作为人的情感的隐喻,作为社会的隐喻,它自然可以作为我们观察社会的一面镜子。所以音乐也是人的内在情感的隐喻,它与人的内在情感是相通相协的,即所谓“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4]1235。音乐不仅隐喻社会人生,而且往往昭示社会人生的变迁趋势,“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4]1235。也就是说,音乐不仅是隐喻,而且其隐喻价值是其他艺术所无法比拟的。只有充分挖掘音乐的隐喻价值,提倡畅和、美德之音,人们的灵魂才能够得到净化,社会才能进步,这对我们今天实现强国梦不无启发意义。
七
司马迁认为,声调、乐器、演员的具体动作、人们的喜好等也具有隐喻价值。在《史记·乐书》中有一段魏文侯和子夏的对话,子夏说:
今夫古乐,进旅而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4]1222
可见,子夏很重视音乐的隐喻价值。他认为郑、卫之淫声,使得魏文侯不能自拔,并告诉他作为君主,一定要有君主的样儿,一定要顺承传统,要切记戒掉放浪奢靡、柔细娇弱、急促疾速、高傲粗犷的音乐,因为这四种音乐有害人的情感德行健康,即所谓“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4]1224。其实这是《史记》另外一种隐喻方式,也就是假借历史人物来传达自己的历史价值观。所以子夏认为,音乐的主流就应该是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的“德音”,而不应该是“新乐”那样的淫溺之声。而“德音”不仅取决于声调,也与乐器有很大关系。子夏认为,以能够演奏出“德音”的鞉、鼓、椌、楬、埙、篪等基本乐器演奏,用钟、磬、竽、瑟作为调和,再用干盾、大斧、旄旗、翟羽等来配合舞蹈,就可以很好地实现音乐的隐喻目的,即“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硜,硜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4]1224-1225,难怪亚里斯多德说“最巧妙的话来自隐喻”[8]183。
其实,音乐本身与接受者或演奏者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隐喻关系。什么性格的人,就有什么样的音乐爱好。所以从艺术隐喻学的角度来说,音乐不仅能够陶冶人的性情,而且能培养和造就人的气质、性格。对此,司马迁在《乐书》中借用师乙的话解释得很清楚:
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4]1233
当然,只有真正懂得音乐,能解诸如《颂》《大雅》《小雅》《风》《商》《齐》等隐喻价值的,且受其长期的耳濡目染,接受者的性格就会如音乐本身所表现的一样,“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4]123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良好的性格是因为美好音乐的熏陶而形成的,这就是音乐的魅力,这就是音乐的隐喻价值。所以,人的内在情感往往就是通过音乐得以表达的,人的基本情绪就是靠音乐得以宣泄的,即“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殷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4]1234。
同时,司马迁认为,音乐作为人的情感的隐喻,它不仅以意象的方式表现社会生活,表现人的内在情感,而且它本身也隐喻着人的善良或邪恶,往往能够揭示人的本性,所以喜好什么样的音乐,往往也就昭示着人的最终结局,即所谓“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4]1235。言为心声,声本乎情,声隐祸福。因此司马迁说:“夫乐不可妄兴也。”[4]1235在司马迁看来,上古时期的圣王明君,他们提倡音乐,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感官刺激需要和嗜好的,而是看中了音乐的隐喻价值,所以他们才特别重视音乐,司马迁也非常赞同这一点。因此他说:“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4]1236这就是音乐,这就是音乐的隐喻。
参考文献:
[1] 王炳社.艺术隐喻学[M].西安: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2] 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林宝珠.隐喻的意识形态力[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6] [美]斯蒂芬·戴维斯.音乐的意义与表现[M].宋瑾,柯杨,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
[7] [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M].鲁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8]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责任编辑朱正平】
Values of Musical Metaphor in Historical Records
WANG Bing-she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more metaphors in Historical Records, so Historical Records is a valuable metaphorical masterpiece. Metaphor is the means of using substitution, indication, borrowing and allegory to make the object metaphorized, that is, it uses the indirect ways to process the object imagerized. H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s, Historical Records is imagerized, being metaphorized. Therefore, the narration about music in Historical Records is endowed with the value of metaphor. The reflection of musical metaphor is to experience folklore, to understand the feelings of the people, to express the society’s voice, to normalize the people, to inspire the people’s feelings, to enlighten the people’s mind, to purify the souls, to reflect the people’s insights, to standardize the outlook through music. The tones, the instruments and the actions of actors are all endowed with the metaphorical values.
Key words: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music metaphor; emotion
作者简介:王炳社(1960— ),男,陕西大荔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渭华学者,渭南师范学院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副院长,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得者,主要从事艺术隐喻研究。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音乐隐喻史研究(2015J025);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类重点科学研究项目:《史记》隐喻艺术思维研究(16SKZD01)
收稿日期:2016-04-07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9-0019-07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