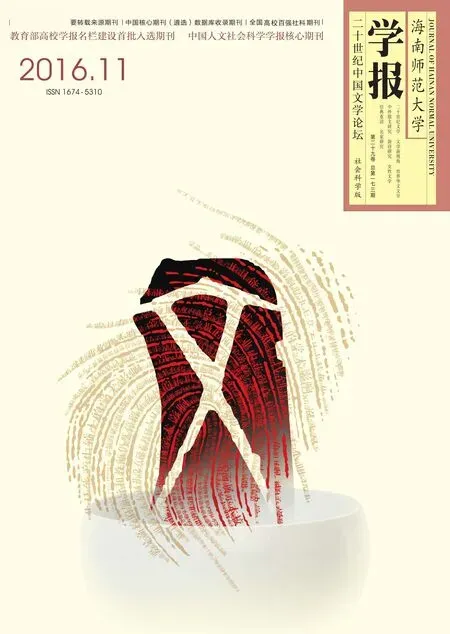身体·革命·理想——评张炜新作《独药师》
2016-03-16姚亮
姚 亮
(贵州大学 中文系, 贵州 贵阳 550025)
身体·革命·理想
——评张炜新作《独药师》
姚 亮
(贵州大学 中文系, 贵州 贵阳 550025)
《独药师》蕴含了三种身体观:以徐竟为代表将身体视为机器的笛卡尔型身体观,以季昨非为代表将身体当做本体的尼采型身体观,以邱琪芝为代表将身体看做身心合一且朝向世界的梅洛-庞蒂型身体观。主人公在身体观上的摆荡和犹疑折射出他在道德理想和终极理想之间抉择的艰难,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作家张炜从经验视域向超验视域转向的端倪。
张炜;身体观;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家园;终极理想
《独药师》主要有三个故事线索,分别是季府与邱琪芝、革命党人、教会医院的纠葛。季府因持有养生“独药”而名震半岛和江北,邱琪芝与季府第五代独药师传人季践有过密切的关系,后来因故分道扬镳。季昨非继任第六代传人后,与邱琪芝重修旧好,在其指点下修习长生之术。由于“宿仇”,他经常怀疑邱有歹念,日久终于冰释前嫌。季践的养子徐竟留学东瀛,参与发起同盟会,为了革命而抛却养生事业,理想笃定以致献出年轻的生命。季府两代暗中资助革命,被称作“革命的钱庄”。季府药局颇有令名,一直视教会西医院为对头,认为中西医水火不容。季昨非患牙疾久治不愈,教会医院轻易解决;季府药局也为教会医院院长解除痼疾,两下和解。在往来过程中,季昨非爱上西医院的基督徒医助陶文贝,辗转追求终成佳偶并追随她与教会医院北迁燕京。
小说涉及的内容是明晰的,有历史秘辛,也有长生奥义,还有个人的情欲纠缠贯穿其中。但与张炜此前的小说相比,《独药师》显得有些特别:主题混沌难明,高潮一再延宕,需要较大的耐心才不至于中途废读。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作者的某种动摇和犹疑。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并不复杂的故事呈现出晦涩情状?可以肯定的是,其涩显然不在文,乃在意。如果说“这是张炜自《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那绝不是因为小说中“半岛养生秘术与革命史料首次披露,历史猛料与叙事陷阱暗合交错”①张炜:《独药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封底。下引该书只在文内注明页码。,而是别有缘故。本文紧扣文本,尝试从字里行间里解开文本的秘密。
一、身与心:三种身体观
小说中无论方士、党魁、庶民、官僚……几乎所有人都对养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于季府有着殷切的期望。这种关注的核心是对身体的重视。由于身份的迥异,对身体的关注也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的身体观;归纳起来,有三种类型,分别以邱琪芝、徐竟、季昨非为代表。小说中包含的三种身体观与张法先生在《身体美学的四个问题》中论及的三种身体本体论暗合,故本文以此为参照进行论述。
邱琪芝一生倾心于长生修炼,面对风雨飘摇的时局,他的一番话令季昨非印象深刻:“凡乱世必有长生术的长进,春秋魏晋莫不如此。我们如今又进入乱世,这样的年头除了养生,不值得做任何事情。只有生命危在旦夕,才更加明白生命的宝贵。”(第12页)深刻的见识加上修养的成果*邱琪芝自称140多岁,却肌肤如婴儿,“没有一道皱纹,脸皮像无鳞鱼那么细滑,银丝绝少”。(第18页)以及季府的愧怍*季昨非之父季践作为独药师第五代传人却只活了74岁,令他赧颜。使得独药师季昨非甘愿拜邱为师。邱琪芝对养生要诀有独到的理解:“吐纳”是气息的周流,“餐饮”是如何用眼睛看取周边的世界,“膳食”是吃喝,“遥思”是意念。他的密室中专门设置了观看星月烟霞的座位和孔洞。他主张废除意念的牵引,而任气流自由运行。“物我一统,往来无碍,无消逝无诞生,也无损益。这就是永生。”(第194页)季昨非的证悟从旁印证了邱琪芝对身体的态度。这种态度近乎道家的任自然和佛家的去执着。对身体的态度既不是放纵,也不是苦行,而是希望在反复的练习中达到主客一体的圆融。不废除主观意志,也不刻意强调;不被外物淹没,也不独立于世。身体、意念、世界互相呼应、协调一致,而不偏废任意一方,如镜照物,物来则应。“身体在世界中,身心是一体的,身动则动心,反之亦然。身心之动是朝向世界的,身心之动则世界亦动,反之亦然。”*张法:《身体美学的四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身心统一、人与世界乃是一体,身体在世界中显现。这种身体美学属于梅洛-庞蒂型,其中的身体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主体间的身体,身体由主客互动所决定。
徐竟本是季府养子,对养生有浓厚兴趣,欲撰写《长生指要》。在日本留学时参与发起同盟会,积极投身革命,以推翻满清为志业,日渐疏远长生大业。小说多处写到他的身体,干瘦、没有水分、有焦糊味儿。与身体的枯槁相对的是他饱满的激情和卓绝的意志。身如槁木,心却在燃烧。在身体与意志(心灵/理性)的关系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意志凌驾于身体之上,规训、压抑甚至无意识中摧残着身体。季昨非伺候徐竟洗澡一节对后者的身体与意志之间的关系有相当精彩的描写:他的裸体活像干瘪的螳螂,毛发均匀而稀薄,下体那儿就像伏了一只死蚕;季昨非为他搓洗,好像“手下的躯体早已经纤维化木质化了,只让人感到韧和艮,体温也不明显”;而一旦谈到“革命”的主题时,“他呼叫着,一手攥拳”,“他呼喊这些话的同时,两腿间的那个僵蚕突然变大了,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地昂扬起来”。(98-100页)在此,意志对身体的绝对优势、身体完全支配于意志非常明显。不同于邱琪芝的身、心、世界一致,徐竟的身体如同一架机器、一个工具,服从意志的支配与调遣,被心灵、理性所塑造与管理,其目的在于用身体改造世界。这种身体美学属于笛卡尔型。“这是客观化的身体、被动的身体,身体是由身体之外的东西决定的。”*张法:《身体美学的四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这种情形在很多革命主题的老电影中尤其常见。当男女主角因情欲而快有身体接触的时候,意志立马强行干扰,将情欲升华、过滤,转换成革命的激情,话题也迅速由私人情感切换为革命事业。此时的身体就是被动的,服从于革命的意志,被强行压制和管理。
与邱琪芝和徐竟相比,季昨非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形。他是第六代独药师传人,本该秉承家学用心修习长生要诀并护持养生独药,然而他却拜家族“宿敌”为师,有背叛家族的嫌疑;更修习邪术、放纵情欲,与长生之旨背道而驰;与革命党人纠缠不清却竭力维护自己的独立。这些都集中表现在他对身体的态度上。邱琪芝美其名曰去其“倔性”以利修持,却让他以身试邪法,放纵肉体、沉沦欲海。他中途有所醒悟,自囚三年以悔其过。出关后本欲好自修行,却被革命裹挟,不得不为之奔走。他敬佩革命者的志向胸襟,却不赞同流血害命——如果革命是杀人,不如闭门养生。他本该清修以证长生、杜门以护秘笈,却偏偏任欲使气;一方面与邱斗法,一方面追情逐爱,还与革命党交厚。他跳脱了家族使命的宰制、对手的阴谋和情欲的牵绊,特立独行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一切的动力都来源于他自身,与同尼采相仿,“把身体作为一切事物的起点,从身体到感性到理性到精神到意志,人用身体和由身体的巨大冲击力而来的激情、理智、精神、意志,去开辟世界,征服世界,获得幸福”*张法:《身体美学的四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这是主动、主观化的身体,身体由其自身决定,这是尼采型身体美学。这一类型的身体美学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把肉体和感性当做一切事物的起点,正如尼采所言——“我整个地是肉体……感觉与精神不过是工具与玩物:它们的后面,‘自己’存在着……它即是你的肉体。”*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尹溟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1-32页。这在季昨非追求陶文贝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首先看中的是对方的身体,并且是用肉体(欲望)以一种猎取的姿态观看,他也承认这是出于他的“怪癖”(第145页)和全身散发出的“小公马的气味”(第151页)。小说多次写到他对医院铁门上花卉图案的注视,他猜测那是“罂粟:邪恶之花”,其实不过是洋蓟,只是欲望的投射让目光所触之人、物都蒙上欲望的幻影。他陷入灾难、从灾难中冲决出来、坠入情网、从爱情中升华,根本的动力全在他自身,他的身体、情欲以及由此生成的激情、意志、精神等所爆发出的动力,让他摆脱困厄、获取幸福。
徐竟把身体当做工具、革命机器的零件;邱琪芝将身体与心灵和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不断放弃意志而使其内外和谐。他们的身体观比较单纯,与之相比,季昨非对待身体的态度却相当暧昧,既没有邱琪芝的纯粹,也不如徐竟斩钉截铁,他在两者之间摆荡。作为一个养生世家的独药师传人,他应该心无旁骛继承养生事业,像邱琪芝一样修行。他虽同情革命,却反对流血,所以不能成为革命的同道。由于他的特殊身份——独药师传人、革命家的兄弟——其犹疑摇摆的姿态背后其实是一个抉择的艰难:身在乱世,究竟该全“身”而退,还是以“身”蹈火。他既不愿如徐竟一样全然交出身体,也不甘像邱琪芝一样抛却意志对身体的搅扰;他要紧紧抓住身体(“自己”),这是他在乱世中惟一的凭借,既不与世界“和解”,也不向任何组织让渡支配权。这个艰难的抉择之实质乃是一个道德问题:身体的个人性与社会性如何平衡?私人权利与家国大计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也是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它如沼泽一般持久地消耗着张炜的大部分注意力,拦阻了他向更高的理想迈进。
二、“独药”:道德理想或终极理想
诚如论者所言,“在启蒙和革命时代,身体话语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它是政治话语需要压抑和消灭的对象”*葛红兵:《身体写作——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之后:“身体”的当下处境》,《南方文坛》2005年第3期。。如果回到20世纪初,基本上用不着大费周章地讨论。而今,一百年过去了,在消费主义语境下,对身体的重视才得以可能。饶是如此,一旦涉及到民族、国家等话题,身体/个人依然不能被单纯而自由地谈论,因此不断有作家去挑战这个话题。2008年柏桦的长诗《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出版,江弱水先生在评论中写道:“这首诗,这本书,想必也会深深冒犯另一些人,因为里头有好多的政治不正确。道德批评家与社会批评家将拉下脸来责问:一种儿女情长的个人叙事,如何对时代变局和社会苦难做一个交代?”*江弱水:《文字的银器,思想的黄金周——读柏桦的〈水绘仙侣〉》,《读书》2008年第3期。
泱泱华夏、礼乐之邦,道德从来高踞神坛。道德本是生命内在的律令,一旦外化成僵死的规条并与权力话语捆绑,则异化为一架戕害人性的无形机器。因此之故,几千年的历史中,常常只见道德而不见个人,身体、个人、个性被压抑与规训到虚伪的地步,以至于鲁迅悲愤地控诉:“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狂人日记》,《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26页。道德背离了自己的主体(人),反过来成为枷锁。在这种情形下,身体不再属乎个人,早已“不由自主”、成为任道德与权力摆布的工具,被剥夺自由支配自己的权利而沦为没有意志和情感的机器。虽有徐竟这类甘愿让渡身体支配权的,更多的是被裹挟被剥夺了身体支配权的,比如那些在炮火中化为灰烬的年轻人。季昨非看到数以千计的鲜活生命以革命的名义被战争宰杀,他因此对革命保持距离,不愿意加入革命组织,更不愿意充当革命的屠刀。*革命组织建议他以拜师仪式为名设局诱杀血债累累的康非,遭到拒绝。为一项正义的事业献身是可敬的,然而死去不易、活着更难。诚如木心先生所言:“最好是‘得道’,其次是‘闻道’,没奈何才是‘殉道’。古人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今我是朝闻道,焉甘夕死——以‘死’殉道易,以‘不死’殉道难。我择难。”*木心:《海峡传声——答台湾〈联合文学〉编者问》,《鱼丽之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页。在大多数人一边倒时,他为何可以保持独立?盖因季昨非已闻生命的大道,所以他坚持乱世独立而不为热血鼓动去殉革命之道。具体而言,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原因。首先,他受邱琪芝的影响很大,对生命本身十分看重。邱琪芝的主张是:乱世除了养生,不值得做任何事情。他的养生秘诀是身心合一、物我同一。季昨非的父亲临终时嘱咐:死亡是荒谬的,长生是可能的,只要不犯错。季昨非继承父业、在邱琪芝指导下修炼长生,他对生命自然有别于革命党的看法。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满清,不过一朝一代的更替;而养生的旨趣则是超越兴废、与时间一同永恒。其次,季昨非在追求基督徒陶文贝的过程中,生命有极大的改变。认识陶之前,他修行邪术、沉迷肉欲;相识之初,他注视陶的目光充满强烈的情欲;随着交往的深入,他的心性与眼光慢慢变得纯净起来,甚至在陶文贝的教导下祷告,最后决定离开家业追随陶文贝与教会医院北迁燕京。基督教的核心教导是爱:以对人的爱完成对神的爱。他在爱的哲学的熏炙下不断从恶习中回转,对个体生命自然而然会更加珍视。有了这双重的超越性视野,他必然能在众人皆醉时独醒。
虽然季昨非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但他身上依然呈现出一种摇摆和犹疑。他虽然尽量保持独立,仍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并大力支持。根本原因在于情分和道义:首先,他父亲与革命党有交谊并有所援助;其次,徐竟是他哥哥,两人情分很深;再次,他所感念的恩师王保鹤也在革命阵营里;最后,他痛恨清廷的腐朽,在道义上支持革命党人。纵然如此,他仍不愿意将自己/身体交与革命,刻意保持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与自由。*维持这种独立相当不容易,连“遗世独立”专修长生的邱琪芝也卷入革命而被火铳重创身亡,可见其难。他的摇摆表面上是个人权利与民族、国家的龃龉,如同冒辟疆所面对的质疑:个人在乱世有没有权利“苟全性命”甚至逸乐而不参与到时局中去?从道德的角度讲,个人需要担当、奉献,必要时,可以让渡甚至放弃包括身体、性命在内的一切权利,但必须以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为前提。然而,一个号称为人谋福利的事业如果是以无数个体的牺牲为基础、完全用血肉筑就的,其合法性也会招致质疑。所以,这一类问题,似乎永远在仁、智之间,不可能完全达成一致。因此,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去讨论季昨非的摇摆与犹疑,意义并不大;其实质是个体生命的社会属性与超越属性、道德理想与终极理想的冲突,只有看到这一点,才可以体察到小说的深刻之处。时移世易,道德标准随之变更,人的社会属性也在变迁,曾经的铁律不乏柔化为尘灰的案例,并且屡见不鲜。与其琐碎纠缠于道德甚而怒目辩驳,不如将目光抬升,仰望那永恒的星空,超越道德而探索更为终极的领域。张炜毕竟是作家而不是政治家,用小说为现实社会与政治谋划不是他的本职,从超越的层面俯察与透视生存的种种烦难与困顿并给人以启示才是他应该做好的。
“道德理想主义”切实地点出了张炜创作的重心所在。张炜的道德理想是将精神家园坐实于此岸世界,无论“融入野地”还是走向“高原”,其基本理路一以贯之。他希望通过故地而融入野地——“故地指向野地的边缘,这儿有一把钥匙。这里是一个入口,一个门”,在野地里,“我可以做一棵树了,扎下根须,化为了故地上的一个器官”。*张炜:《融入野地》,《上海文学》1993年第1期。主体消弭于自然/野地以获得新的“生命”,作为生态、文化隐喻尚可讨论,作为精神归宿却是极为可疑的。以主体的消灭、此在及此世的瓦解来融入野地,殊不可取。精神家园“须与人的精神息息相关,舍此就无所谓人的家园;这一家园并非是某种走向沉寂的终点,而毋宁是精神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走向新生的起点”*丁少伦:《寻找家园——关于〈融入野地〉的哲学思考》,《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融入野地”的问题恰恰在于精神的断灭和家园实体化成为终点,对此邓晓芒先生批评道:“张炜一点也不想触犯传统道德,他那样热烈地赞美了这个道德的温情的一面乃至于残酷的、毁灭人的、把人变成植物的一面。”*邓晓芒:《张炜:野地的迷茫——从〈九月寓言〉看当代文学的主流和实质》,《开放时代》1998年第1期。到了《你在高原》,这部被誉为融汇了张炜前半生文学经验的的“大成之作”*陈晓明:《〈你在高原〉就是高原》,《文艺报》2010年9月15日,第8版。对精神家园的探讨依然没有实质性进步。在小说中,他将精神家园实体化为故地的一座葡萄园,在那里劳动、写作、论道、办杂志。这一设定与“融入野地”的路径并无二致,原本虚灵的精神“高原”被矮化为一个地理坐标,实在是《你在高原》最大的败笔。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张炜的士大夫心结太重,太过焦灼于现实的种种问题,使得他把经验性道德理想当做超验性精神家园的替代物,这是其创作瓶颈和困境。超越性视野的缺乏极大地限制了张炜创作的品质。
《独药师》被出版商噱头般地夸张为“自《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歪打正着地点出了这部小说的特色和重要性——但并不在于“半岛养生秘术与革命史料的首次披露,历史猛料与叙事陷阱暗合交错”,而在于它初露端倪的超越性品格。季昨非在个体与家国大业问题面前的艰难抉择,他在基督教爱的奥义的启示下悔改恶习,都是这一品格的体现。张炜以此为突破口,把目光从道德理想投向终极理想,从经验世界抬头仰望广阔无垠的超验世界,这将是张炜创作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如果这是张炜的自觉,那么其创作品质可望飞跃性的提升。
无论对于小说中的季昨非,还是现实中的张炜,对终极理想的关注超过对道德理想的关注都是至关重要的。就季昨非而言,在风潮一边倒的情形下,对个体生命的张扬和强调至为宝贵,它是一面旗帜,高扬着人道与理性;这一情节对当下的启示也不言而喻:狭隘的民族主义常如暴风雪一般裹挟大众,个人的理性被弃置不用,少数独立的个体反而被目为异类口诛笔伐。惟有个体的理性普遍绽放才是民族的真正福祉。就张炜而言,写作40年之久,终于穿过“野地”、一窥“高原”,自不必说是一大幸事,同时也是读者的美事。
季昨非这个名字令人自然联想到“蘧瑗知非”的典故,小说中他确实不断迁善改过:父亲说只要不犯错就可以长生,他一直在寻找父亲所犯的错误以改进;他与家族“宿敌”邱琪芝、教会医院和好;自囚三年以悔纵欲之过……而最大的一宗“迁善”是在汹汹乱世独善其身,尝试从有限一窥无限的芳容,孜孜寻求终极理想。“附录:管家手记”里写道:“季昨非与兄长徐竟探讨养生与革命,徐竟谓:时下中华民族之‘独药师’即孙文先生。‘救中国者只一味独药:革命。’”(第348页)作为个体生命的“独药师”,他的独药却是从乱世抽身以保全身体/性命,以身、心和世界融合为路径将永恒在身体里收藏,这是人类长久以来的终极理想。
(责任编辑:曾庆江)
A Review of Zhang Wei’s New Work The Independent Pharmacist
YAO Liang
(DepartmentofChinese,GuizhouUniversity,Guiyang550025,China)
There are inTheIndependentPharmacistthree body concepts—the Cartesian type body concept of regarding the body as a machine typified by Xu Jing, the Nietzsche type body concept of considering the body as ontology represented by Ji Zuofei, and the Merleau-Ponty type body concept of taking the body as the unity of body and mind and as being oriented towards the world represented by Qiu Qiya. The swing and hesitation of the protagonist in the body concept is reflective of his difficulty in his choice between his moral ideal and his ultimate ideal, which has shown the writer Zhang Wei’s clue of change from experience domain to transcendentalism realm to a certain extent.
Zhang Wei; the body concept; moral idealism; spiritual home; ultimate ideals
贵州大学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困境探析”(项目编号:GDQN2016014);贵州大学引进人才项目“从‘野地’到‘高原’:张炜诗学理想的困境与出路”(项目编号:贵大人基合字(2015)022号)
2016-07-20
姚亮(1984- ),男,湖北利川人,博士,贵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
I206.7
A
1674-5310(2016)-11-004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