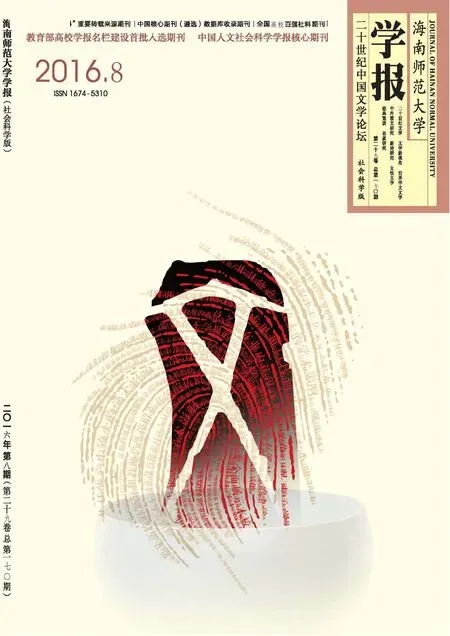历史和现实纠缠中的知青写作
2016-03-16徐勇
徐 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历史和现实纠缠中的知青写作
徐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对于知青写作(作家)而言,历史记忆往往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一存在决定了他们不断徘徊于现实和历史之间,他们一方面想通过肯定现实以走出历史,一方面却发现现实中无法承受之“重”,其结果是他们常常只能通过再造历史以再造自我和现实:历史、自身和未来,也都在这种叙述中得到了有效安置。
知青写作;记忆之“痛”;现实与历史
在柯云路的《新星》三部曲中,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虽然往往被人们忽略,但对理解小说却十分关键:那就是李向南的“红卫兵”身份。对李向南来说,罹患了胃癌固然让人绝望,可真正让他绝望和窒息的还在于他的红卫兵身份。这一身份始终制约着他的前途和命运,即使是他竭力挣脱,它仍像一个幽灵式的存在,显影并回荡于小说叙述的始终。他的政治对手三番五次地抓住这点不放,但他却无能为力;他说服林虹走出“文革”的阴影,他自己却始终笼罩其中,不曾走出自己布下的“迷宫”半步。不论李向南多么地想挣脱历史的束缚,历史却始终是作为一个“缺席”的“在场”,高悬于现实生活的星空,你可能感觉不到它,但它作为绝对的存在,时刻闪耀。实际上,这又何尝不是知青作家的困境的表征呢?即使现在,距离知青岁月的结束已有三十余年,很多作家仍旧沉浸于知青岁月的回忆和想象中,做着几十年前的“旧梦”。可见,要想真正走出这一段历史,并非易事。
事实上,不惟李向南如此,对于1980年代小说中的中青年主人公们来说,“红卫兵”的身份始终都是一个幽灵式的存在,这一身份及与之相关的记忆,总是作为“噩梦”或“疼痛”被烙刻在现实生活之中,任你如何努力总也不能抹去。无论你是玩世不恭,还是愤世嫉俗,抑或破罐子破摔,或者郁郁寡欢,甚至铤而走险,如斯种种,都一再表明,回避或遗忘都并不能解决问题于万一,只有坦然或者正视,才有可能走出。1980年代初,“潘晓来信”引起全国范围内持续的大讨论,正表明这点,而这其实也正是社会、时代对文学提出的要求。
在知青写作中,吴欢的《雪,白色的,红色的……》十分特别。小说开头,主人公郑良珏沉浸在出国的想象中忘乎所以,但这一切却因与多年不见的同学夏芸芸的偶遇而突遭破坏:夏芸芸的出现,使他一下子回到了早已淡忘的知青岁月。而这“过去的经历”曾被他以“荒废”为由早已忘得干干净净。历史既然在他看来毫无价值,过去的人和事、曾经的情感经历,自然就可以如敝屣一样弃之不顾了。但眼前两人截然不同的处境,夏芸芸那虽处逆境但不气馁、仍平和的心态,都深深触动了他,这种触动遂变成一种强力,过去的经历在他的“记忆”之阀下得到“重写”:“生活本来是片段的、零星的,是被连续而来的一个又一个日夜粉碎了的。但是,记忆却把这零星、粉碎的生活连结起来,使它完整了。”原来,“荒废”的历史并非一无是处,过去的经历其实可以悟出许多道理。正是通过这种“记忆”,叙述者“我”(郑良珏)渐渐看清自己原来“是一个极端狭隘的小人”。在这里,“记忆”通过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即“完整”)而对历史进行了重新的“编码”,“记忆不是对过去的事实的简单描述,而是一种对事实的建构以及积极地对世界重构的形式”*[德]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冯亚琳、[德]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而历史同现实之间也在这种讲述中得到某种和解,“我”虽然认识到自己的“小”,但最终释然了,其结果自然就可以安心地出国去了:即为了追求所谓的国家富强而不是个人的一己享乐而出国。在这篇小说中,历史虽然像幽灵一样偶尔出现在记忆之中,但并没有构成现实的债务,相反,现实的优越感反使得历史看起来无足轻重,因此,对叙述者而言,既然将来一片光明,自然就不存在走出历史的阴影这一沉重的问题了,历史也仅仅成为现实欲求的合法性资源。但对大多数知青写作而言,历史似乎并不如此。
一、记忆之“痛”:肯定现实/走出历史
知青一代的记忆之“痛”,是刻骨铭心而又不堪回首的,这里面既包含有年轻时的狂热,也有真诚;既有盲目的自信,也有无尽的迷茫;既有言不由衷的世故,也有发自肺腑的天真。概言之,历史对于知青,显然并不轻松,而毋宁说十分沉重。这种沉重,不仅表现在历史本身的“荒谬”性上,更表现历史往往造成对现实道路的潜在的负面影响上。换言之,历史往往成为一种债务或疼痛式的存在,若不及时清理则可能使人最终走向毁灭。
“文革”的结束,很大程度上是某种“颠倒”:此前的“革命理想”如今看起来显得极其荒谬,而此前的“谬论”现在却被视为天启式的预言。随着这一“颠倒”而来的,是对知青历史的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是历史对知青一代所开的最为荒唐的玩笑。这一否定在知青大返城中表现无遗,随着知青的返城,等待他们的已不再是红花和锣鼓,而是冷漠、怀疑和避之犹恐不及。历史就像垃圾一样,既被社会唾弃,也被知青一代所憎恨,从这个角度看,知青写作在1970年代末表现出对“文革”之“创”的控诉就显得再自然不过了。可以说,很大一部分知青写作都属于此列。
在这些小说中,《伤痕》和《枫》比较特别。这两部小说既不同于一般的伤痕写作,也不同于大多数知青叙述。这两部小说中充满了对“文革”的简单控诉,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主人公对自己的过去深深的忏悔和否定;但问题是,忏悔过后,如何面对现实的生活?而一旦全面否定自己的过去后,又该如何重建自身?实际上,即使是那些全面否定“文革”的知青写作,也并没有完全否定自身,而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具体的否定和抽象的肯定的结合。孔捷生的《大林莽》和《在小河那边》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前者中的“大林莽”是一个可以做多种阐释的意象,其既是“文革”中人们的迷乱和无助,以及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最终的觉醒的象征,也可以被理解为“文革”中的一块“飞地”,是人类的困境的比喻,在这里,人的全部人性,包括丑恶和崇高、自利和他利等等,都得到展示并集中地表现出来,而这其实又是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以及整个当代历史在这短短数天中的浓缩。在这部小说中,虽然无情地批判了“文革”,但对红卫兵一代曾经坚守的理想本身,直至小说最后都没有彻底否定:理想本身并没有错,错只错在理想被人利用,或者其他。后者虽然以离奇夸张的手法表现“文革”的荒诞,但这种荒诞背后却是异常清醒、痛苦的觉醒者。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文革”越是荒诞,越能反衬出他们作为先觉者的孤独和伟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部小说代表了知青写作控诉“文革”的两端,前者代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通过对“文革”的扬弃,达到对理想主义本身的肯定,青春也在这种理想主义的光芒下放射异彩。这一趋势,其后在梁晓声、张承志等人的小说中达到极致。后者则通过对“文革”荒诞和残酷的展示,以表现知青一代中先觉者的成长过程。叶辛的知青写作、张抗抗的《隐形伴侣》、老鬼的《血色黄昏》等等都是这样的典型。不管如何,这两类作品都表现出某种共同的倾向:即对“文革”的批判,其实是与知青一代的自我重建同时并存的。“文革”带来青年的迷狂,也引起他们的思考和反省,而这种反省,反过来又更加导致他们的命运的磨难,这些小说也更具悲壮色彩。
对于这些写作来说,其执著于“文革”历史的倾诉是为了走出历史,但往往事与愿违,他们越是想走出历史,越是被带进历史的胡同不能挣脱,这似乎是一个循环。梁晓声的《雪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小说从知青大返城开始叙述,但对小说中的主人公而言,却似乎是真正开始了生活和人生:现实的极端困顿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琐碎和坚实,这也更加促使这些知青沉浸在对(兵团)历史的想象和回忆中不愿走出,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中的人们纷纷投来的怀疑、警惕和不信任,这也使知青主人公们变得异常敏感而多疑,也变得越来越表现出对现实的抗拒和无端的愤怒。小说中的姚玉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返城使她从一个兵团营指导员,沦落为待业青年,这种处境的逆差让她十分难堪,而这又同她作为一个业已三十的老姑娘的心态缠绕在一起,这些都让她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虽贵为市长千金,姚玉慧不愁工作和去向,但要靠自己的双手在现实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却显得十分艰难;对于她,知青岁月留下的除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似乎再也没有别的,但这种经验在现实生活中却又显得那么荒谬。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政治工作的限制,在姚玉慧的身上形成了理性和感性的分裂式的人格特征;虽然如此,对于她,知青岁月并不一定就是噩梦,与现实生活相比,其至少能给她以更多的认同。虽然并不想回到从前,但凡是涉及到从前和返城知青的人事,总能引起姚玉慧强烈的震动和共鸣,她虽然“身”在现实生活,其实是“活”在历史和对历史的回忆中。
这种走不出的历史,还表现在理想坍塌后对日常欲望的追逐中。对于知青一代,理想主义崩溃的结果,往往使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陈建功的小说《飘逝的花头巾》和《迷乱的天空》就是这样的典型。在《飘逝的花头巾》中,“花头巾”是一个很有象征性的意象,也是一个需要不断被阐释的意象。最开始,“花头巾”是沈萍用来向她妈妈招手的标记或符号,在主人公秦江眼里,迎风飘展的“花头巾”无异于是一面旗帜,使他迷惘的内心突然明亮起来,正是在这符号的象征力量的指引下,他开始并最终完成自我人生的重建。但反讽的是,“花头巾”的主人却一步步“沉沦”下去,变得虚荣而浅薄。究其实,“花头巾”只是一个符号,它的主人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实物,而主人公却非要从中解读出象征意义,这种阐释的错位,是导致他们之间感情悲剧的根源,但问题似乎又不仅于此。在小说中,秦江和沈萍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和记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对于前者,为了逃避这种记忆,甘当水手去做苦力,但他并不能真正从中挣脱出来,所以一旦看到那迎风招展的“花头巾”和不屈的沈萍,有如灵光乍现他感觉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对于后者,“花头巾”只不过是个信物,能够不时唤起她对过去的记忆,因此沈萍要想走出历史,就要改变自己的装束,就要让自己“看不出一个外省姑娘的丝毫痕迹”;在她这里,装束和饰物,显然既表明历史的残留,也是身份的表征,所以改变装束就是告别历史和对庸俗日常的追逐。
二、现实之“重”:从日常出发回到历史
在1980年代初期,日常生活是一个内涵复杂的范畴,其一方面被当作“文革”意识形态的“他者”,在针对“文革”的批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典型的莫过于古华的《芙蓉镇》 以及从维熙的小说;另一方面,日常所具有的平庸的一面,也常常被理想主义或改革意识形态所摈弃和否定,而在另一些时候,对日常的超越,也往往是主人公精神升华的象征,这在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中表现明显。应该说,这种复杂性在知青写作中都有呈现。在1980年代的知青写作中,日常生活叙述并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梁晓声的《雪国》是为数不多的执着于直面日常生活的知青写作,但这种日常生活在他的小说中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一个过渡形态。换言之,日常生活对知青来说,是他们为之疯狂的革命理想主义坍塌后暂时休息的港湾,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迷恋,而毋宁说时时表现出针对日常的超越。在知青小说中,日常叙述往往显得暧昧而游移。虽然一方面日常是作为革命理想主义的“他者”而存在,但日常却并不一定接纳他们这些归来的“逆子”们,或者不如说日常的“门”并不向他们敞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一群被排除在日常和革命理想主义之外的存在,已不可能再回到革命理想主义,奔向日常也显得困难重重,更何况日常往往表现得那样平庸和无助。
返城知青之所以常常怀念过去,很多时候源自于日常生活的困窘。但他们并非真的愿意回到过去或他们曾经呆过的农村、农场或兵团。这里往往有一个奇怪的悖论,在梁晓声的《雪城》里表现尤为明显。在刘大文和姚玉慧的眼里,过去对他(她)们而言,竟十分地相似,即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胜过一切,虽然一个(刘大文)是通过沉溺其中来张扬日常幸福的意义,另一个(营指导员姚玉慧)是以被压抑的方式显示正常欲望不可遏制的力量。但当他(她)们返城后,却要表现出对日常的超越的渴望:刘大文渴望成功,姚玉慧不甘被父母安排。这一悖论表明,当过去在回忆中呈现时,“日常”是作为否定革命意识形态出现的,而当回到现实中时,为了重建一代知青的自我形象——因为在小说中,返城知青无时无刻不受到民众的质疑乃至嘲讽——又表现出针对日常的超越。而实际情况是,大多数返城知青日常生活的困窘是真切而紧迫的问题,他们缺衣少食,没有工作,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想证明自身(一代人)不甘于此、不甘于被生活的洪流淹没,正是这种极端矛盾,在小说中奇怪地缠绕在一起,极富症候性。
梁晓声以《雪城》的写作表征了知青面对日常的四种方向和可能:第一种是现实的困窘,促使他们回到过去。第二种是日常的平庸使他们追怀过去,但并不想回到过去。对于前者,有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铁凝的《村路带我回家》、陆星儿的《冬天的道路》等,而更多的是后者,像梁晓声的小说、陈建功的小说《水流弯弯》和《迷乱的星空》、张抗抗的《北极光》等,都是这样的典型。第三种是现实的困窘使他们怀念过去,但却并不想回到过去而是对现实有所求,这在叶辛《爱的变奏》等小说中有所表现。第四种如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以及《绿夜》、史铁生的知青写作、韩少功的《远方的树》等则表现为,日常的平庸而非困窘,使他们重返故地,但并不是回去。不论如何,这些过去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过去,而是经过“现实”改写了的“过去”,因为这些针对过去的回忆都是在日常的对照下进行的。在这些小说中,过去显然已经不再是噩梦式的存在,而是过去在同日常的平庸和困窘的对照下闪耀出诱人的光芒。现实的困境只是暂时的,返城知青们迟早大都会有工作,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事实上,物质上的困窘和贫乏是整个1980年代的时代特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种知青写作并没有持续多久也并不普遍,而第三种也不可能得到广泛的呼应。知青写作更多的是第二种和第四种,即虚化历史和重返“故地”。
如果第一种和第三种知青写作是日常的困窘使他们对过去充满了想象和温情的话,那么这种“怀旧”之情终究难以持续下去,因为困窘总是暂时的,日常的平庸却是永恒的,这是日常的本质性规定之一。从这点而言,第二种和第四种表现出的对过去的怀念就带有了永恒的意味在内了。此处有一个区别,即对于第二种而言,像梁晓声的部分小说、张抗抗的《北极光》以及陈建功的《流水弯弯》等,日常虽然显得平庸,但他们并没有想要回到过去,其意图还是表现在如何超越日常平庸的层面,因此“历史”在他们这里,只是作为现实的“他者”式的存在,即通过现实来返观历史,其实是预设了一个不同于平庸的现实的“历史”存在,故而历史在他们眼里往往就成了抽空具体内容的、抽象的、理想主义的象征。换言之,为了达到对日常的庸俗的超越,历史的平庸和不堪的一面都在这种预设下被过滤掉了,历史最终变成类似于理想主义的代名词。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就是这样的典型。这篇小说虽然始终都是在回忆性的口吻中呈现,但实际上是在现实和历史的对照下展开叙述的,而且这一充满死亡之气的“鬼沼”就有点像孔捷生的《大林莽》中的“大林莽”,是一个极富象征性的意象;所不同的是,在孔捷生的“大林莽”中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大林莽”就是一个人性丰富性的浓缩和凝聚;而“鬼沼”则不同,这是一块就像题目所显示出的“神奇的土地”,这块土地虽然充满死亡的气息,但这气息在征服自然和艰难困苦的英雄主义气概下,最终烟消云散,而且这也是对历史的寓言式的表达:知青经历中的“文革”,不正是这种“鬼沼”式的存在吗?其虽到处弥漫着死亡之气,但在这死亡气之侧,是一代人甚至更多的人改天换地的雄心和毅力,是改造世界的坚韧和不拔,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如果说在梁晓声的这篇小说中,日常的平庸只是一个潜在的、可能性存在的话,那么在陈建功的《流水弯弯》、《迷乱的天空》以及张抗抗的《北极光》、《淡淡的晨雾》等小说中,日常的平庸却是切实而令人窒息的:
是的,当我紧靠着明伟(小说叙述者“我”的丈夫——引注)那宽宽的肩膀,一起走向高雅的剧场,迎来等待退票的青年男女们羡慕的目光的时候,当我和他坐上公共汽车,听他高谈文艺界趣闻,而乘客中有人认出他就是某剧里的某角色的时候,我心里确实升起一种满足。满足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也许,这就是他所说的“懂得生活”的乐趣?也许,这不过是女性的虚荣?唉,我对幸福的要求也许太苛刻了。因为在一时的满足过后我又觉得,生活是很幸福的,又很无聊。我的生活里好象缺少一点什么更有意思的东西,……缺少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清。
渐渐地、不由自主地,我想起了和钟奇一起的日子,我来到了这静静的小河边。*陈建功:《水流弯弯》,《陈建功小说选》,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179-180页。
显然,现实的平庸使“我”想起了钟奇,而 “和钟奇一起的日子”就是历史,就是过去那些插队的日子,这些日子虽然很苦,但生活得“充实”,那种“青春的活力”,是“多么有魅力”!相比之下,现实却是那样的平庸、沮丧和无聊。在小说中,历史是同“奋斗”、“激情”、“虔诚的热情”和“理想的境界”连在一起的,虽然“奋斗”、“理想”(即组织“红卫兵公社”)显得多么的不切实际。这样一来,在小说中,“文革”和插队生活,就被过滤抽象为对理想主义的坚守和追求了。而且,这种过滤是在回忆的过程中一步步完成的:“生活已经无忧无虑,却并不使人感到满足……越这样,我越忍不住插上回忆的翅膀,回到六年前,回到钟奇身边。渐渐的,我觉得,该恨的也许是我自己,而不是他。他对生活的态度,有一种难能可贵的东西,而我却丢弃了它,今天才明白它的可贵。”*陈建功:《水流弯弯》,《陈建功小说选》,第189页。此处叙述者通过“回忆”最终完成了针对日常的超越和对理想的回归,而这些并不是在实际层面而是在精神层面完成的。
这种日常所表现出的平庸,是与“文革”造成信仰的毁灭和坍塌息息相关的。“唉,我们这代人,生不逢时,历尽沧桑。没有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叫人如何相信生活是美好的呢?理想如同海市蜃楼,又如何叫人相信理想呢?有人说这叫什么虚无主义,我认为也总比五、六十年代青年那种盲目的理想主义好些……”*张抗抗:《塔》,《北极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22页,换言之,是“文革”意识形态的失效导致青年一代理想主义的缺失,以及沉溺于日常的平庸中的倾向。显然“五、六十年代时代”那种“盲目的理想主义”已经失效,但对那些不甘于沉沦的人,像小说中的芩芩和曾储,却并不愿意就此平庸或变得玩世不恭,他们想重新寻找到生活的支点,“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但是我不愿意象现在这样活着,我想得更有意义些”*张抗抗:《塔》,《北极光》,第217页。。在这里,两人的知青身份和经历虽然没有过多涉及,但一直是他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即旧的理想主义破灭后如何重建新的理想。问题在于,这一支点又难以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到,而历史又过于沉重,他们也不想回到过去,所以小说一方面没有过多涉及芩芩和曾储的知青历史,只是偶尔在回忆中闪现,另一方面现实又是那样平庸,这种困境到最后就导向从现实回到历史深处——即不同于“文革”的他们的“幼年”历史。在小说中是芩芩的幼年——去寻找那理想之光(北极光)。“北极光”是一个极好的象征,它与现实的平庸恰好形成对照,可能存在又难以找寻,既能“言说”又难以具形,正是这种既具体又抽象的“无言”的表征,与记忆深处的人类“幼年”状态十分相似。因此,“北极光”这一象征,就是阿甘本所言的人类“幼年与历史”*参见[意]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尹星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51页。的符号表达,是从人类幼年的历史中去寻找精神之源、理想之光。从这个意义上,此后的寻根文学具有回到人类的幼年的倾向*参见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7-74页。,同《北极光》之间,显然有某种内在精神上的一脉相承之处。
三、再造历史以再造自我和现实
类似于张抗抗的《北极光》以及《淡淡的晨雾》等小说,那种否定现实又不愿回到过去的倾向,已经预示了向历史纵深处探询或重新构造历史的可能,正是这种否定现实,也使这些小说忽视了1980年代最大的意识形态实践——现代化的想象和实践。如果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忽视与其说是无意的,不如说是有意为之。因为现代化的实践,虽然承诺了美好的未来,但这一承诺终究是以物质形式——即四个面向表现出来的,对于理想主义的知青写作来说,物质层面正是他们要力求超越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少功、史铁生以及张承志等人的知青写作,正是沿着《北极光》、《流水弯弯》等小说这一脉络发展而来的。
但是韩少功和张承志等人却并非要否定日常现实,而是要通过向历史纵深处的挖掘,试图给现实寻找到另一重根源,以此作为现代化实践的补充或延伸。因为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这些作家的知青写作所呈现出的并非要回到故地,而是在故地和现实之间做来回的穿梭,以及表现出的精神上的回归。换言之,现实仍是他们的“持存”和基础,他们要在精神上寻找一个家园,但只能回到历史或故地去寻找。张承志的《绿夜》很有代表性。这篇小说从叙述者“他”返城八年以后重访草原开始叙述,“这漫无际涯的绿色,一直远伸到天边淡蓝的地平线……一点点的在他心里勾起滋味万千的回忆”,这所谓的“滋味万千”并不矛盾重重,而是现实的平庸琐碎使叙述者产生了回到过去以寻找精神依托的冲动,“生活……淹没了诗”,故而回到故地就是为寻找那被淹没的诗,那“逝去的青春”,就是回应那“遥远的呼唤”。在小说中,小奥云娜无疑就是诗、青春和呼唤的隐喻。但这些都是叙述者一厢情愿式的想象,不仅身边的人不能理解,即使真地回到草原见到分别八年后的奥云娜,实际情况也与想象和回忆中的判若两然:“她没有羊角似的翘小辫,没有两个酒窝。她皮肤粗糙,眼神冷淡。她甚至没有亲热地喊他一声啊哈——哥哥。他慌了。”“这是他的小诗、他干旱心田中的绿洲、他青春往事的象征、他的小奥云娜么?”所谓的“小奥云娜”只是叙述者想象和回忆中构造出来的形象,这一形象之所以显得那么的美好,无非就是因为远离现实而与历史相勾连,因此小奥云娜就是叙述者通过想象和回忆构造出来的“历史”,一旦遭遇现实,霎时便会显露出它的不实来,“生活露出平凡单调的骨架”。这也使叙述者清醒地认识到“在现实中追求梦境就是使梦破灭”,“应当让那种过于纯洁的梦永远萦绕在心头”,相反,生活的严峻“使他将把献给梦的爱情投入现实”。叙述者突然认识到,生活其实是矛盾两分、并行不悖而结合一体的,既可以表现出超越的一面,也显示出平庸的一面,叙述者也大可不妨一面沉溺于生活的平凡,一面去寻找追求那“浩淼的暗绿中亮起的”“奥云娜为他举起的灯”那“明亮的星”,只要他不曾忘记生活中一定会有那颗“明亮的星”就足够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叙述者寻找理想和生活中的诗是为了更好地投入现实生活,这一意图在《北方的河》中同样如此,张承志通过重返去寻找“北方的河”,并不是走向历史的纵深,而是想通过走向历史的深处,重新更好地走回现实人生。这也是一种双重的扬弃,既扬弃了日常现实,也扬弃了历史,其结果是在否定现实的同时,也否定了历史,同时在更高的意义上肯定现实。韩少功在《归去来》中以寓言式的形式表征了这点,其他的作品如《远方的树》、《飞过蓝天》和《西望茅草地》等也都如此。《归去来》这一题名即表明现在和过去间的距离。其曰“归去来”,虽预设了一名知青返乡的故事,但返乡的结果,与其说是回到了过去,毋宁说是现代文明对传统秩序的一次冲击。小说叙述了一个名叫“黄冶先”的男人来到乡下收购香米和鸦片,却被乡民一致认作十年前回城的“马眼镜”,而叙述者“我”(黄冶先)也在恍惚记忆的引导下,冥冥之中重温了一遍历史。在此处名称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一种象征,因为“黄冶先”和“马眼镜”,虽然是属一人,但其实分属不同时代,其间不可能混淆。如果说“马眼镜”代表的是过去和历史的话,那么“黄冶先”则对应着现实和当下,这两个“名称”在叙述者“我”回乡过程中的彼此矛盾,也在意味着现实和历史的不可通约、不可化解乃至不可逾越,而“我”最后逃也似地返回县城,最终表明任何企图填平这一鸿沟的意愿都是那么的无望和不可能。这里与其说是“归去”,不如说是“归来”,“归去来”表明,一旦回到现代文明的大都市,“归去”已不再可能。《飞过蓝天》也一再表明这点,当鸽子晶晶远涉群山千辛万苦回到主人身边,却于意外之中死于主人的枪口。从这个意义上,《远方的树》不仅是一次重访旧地,更是一次精神上的回乡之旅,是现实意义上的超越之路。在《远方的树》中,这棵“树”,既真实也虚幻,真实是因为曾经存在过,后来被砍掉了,虚幻则因为是作为画的形象得以再生,它是“过去”极好的象征。那段知青岁月虽然不可能从记忆中抹去,但无疑早已远去,因而只能以画面或叙述中的形象存在,它的存在因为是在生活现实的对照(现实的庸俗和烦恼)下呈现,已非原来意义上的过去,而是再造后的历史了。因此,叙述者“田家驹”的返乡之旅,就是为他重回现实和都市重建了一精神上的支点,他重访旧地就是一次精神上的返乡。这一逻辑发展到后来,其结果自然是走向历史的纵深:“过去”既然已不可能重回,那么现实中的“我”或叙述者、作者,最好的办法无非就是立足当下,或者走向历史的更深处,而这两者是可以、实际上也是相通的。其后不久的寻根小说证明了这点。
这表明了这样一个趋势,即第四类知青写作有一个成功者返乡的结构*对于第二类而言,虽然也有一个精神返乡的结构,但知青主人公却不是现实中的成功者,也并没有在现实中建立自己的位置,故而他们返乡只是为了重建生活的目标,而对于第四类而言,生活的目标虽没有得以重建,但无疑他们是生活的强者,他们回到过去只是为了给现实提供某种补充,因为现实对于他们而言,是某种缺失,他们需要这种过去来弥补这种缺失。。他们的返乡并不是因为城市的失败经历,而是精神返乡之路,他们是为了寻找曾经丢失的美好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现代大都市里都已经荡然无存或微乎其微了。正是沿着这种路径,他们最终走向边地,走向了文化寻根之路。可见,文化寻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成功者精神返乡的表征,但对现实中失败的知青来说,这是不可想象也不可能做到的。
四、结语:如何过去,怎样未来?
在知青写作中,既有张抗抗那种于焉其中、参与称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分界线》,也有像卢新华和孔捷生的那种立足“现在”、批判和表现知青“历史”经历之“痛”的《伤痕》和《在小河那边》。在这两类写作中,叙述者同叙述内容之间,不是过于“和谐”(前者),就是过于对立(后者),因此在这两类创作中不存在叙述内容和叙述者立场之间对话的可能。知青写作更多的是一种错位,即现实同历史之间的矛盾处境。换言之,知青一代的历史,虽然伤痕累累、沉重并充满血泪,但并非一无是处,现实也并不如当年想着回城时的那样美好或尽如人意,这就造成了某种错位:“将来”并不能从“现实”中得到承诺,相反倒是常常同历史纠缠在一起,结果似乎是“历史”决定了“将来”,最终也就决定了“现在”。这就有点像马尔库塞所说的记忆的治疗作用:“记忆所以具有治疗作用,是因为它具有真理价值。……解放过去,并不是要使过去与现在调和。与发现者自己施加的限制相反,面向过去的结果将是面向未来。追回失去的时间成了未来解放的手段。”*[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3页。从这个角度看,知青写作并不同于那种现代性时间进程中的、从昨天经由今天到明天的主流写作,而更多地表现出时间上的混杂的现代性特征。
对于知青一代(不论是作者还是主人公)来说,直面知青的历史或许不难,难就难在“历史”的阴影无论怎样挣脱,始终不能走出。在1980年代小说写作中,“红卫兵”身份及其知青经历作为一个幽灵式的存在,出现在中青年主人公的生活中,其往往于不经意间流露,便成为不可遏止的“记忆”之“痛”。即使主人公有意回避或遗忘,反而更加被纠缠其中不得解脱。从这个角度看,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被人为或刻意地分为伤痕小说、改革小说、知青小说以及寻根文学,乃至现代主义小说,就似乎显得不很恰当。实际上,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一条若隐若现的脉络,那就是如何从沉重的历史记忆中挣脱出来并重建自身的主体性。这一脉络不仅指向那些复出的“右派”和中老年干部,更是经常萦绕于红卫兵出身的知青一代身上。
这既是现实和历史的纠缠,也是现实和历史之间的对话、冲突、融合乃至和解的过程,因而决定了知青写作整体上的“对话体”的文体特征。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记忆以及对记忆的叙述,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现实的取向及其意图,即现实处境决定了记忆的方式及其向度*这一取向决定了不能仅仅从疗救的作用上去理解记忆。莫里斯·哈布瓦赫虽然对记忆的美化功能表示困惑,“在遥远的世界里,我们遭受了令我们无法忘却的苦难,然而,对某些人来说,这个遥远的世界却仍然散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这些人历经磨难,幸存了下来,他们似乎认为,他们自己最美好岁月都驻留在了那个艰难时世里,他们希望重温这段逝去的时光”([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6页),但他仍从“昨日社会里最痛苦的方面已然被忘却了”这一角度去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沉思冥想的记忆或像梦一样的记忆,可以帮助我们逃离社会。”(第87页)因为显然,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要面对现实,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永远逃离社会。这就决定了“记忆”的疗救功能只是一种缓冲和转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这在晓剑和严亭亭的《一代人的情歌》和梁晓声的《雪城(下)》等小说中有明显表现。。这种记忆的叙述其实就是故事的呈现方式,就像前面分析过的《雪,白色的,红色的……》一样,它提出了通过两个时代之“我”的对话的方式而达到现实同历史和解的问题。在这里,首先需要针对“故事”做必要的解释。本文使用的“故事”是针对“记忆”而言存在的,也就是说,“记忆”通过故事方式呈现的同时,最终达到了现实与历史的和解。用理查德·卡尼的话说就是“众多的故事使我们具备了人的身份。”“有人问你是谁,你得讲自己的故事。也就是说,你会依照对过去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来讲述自己的现状。你根据自己过去的状况和将来的发展来阐述自己现状的境遇。这样,便给自己一个叙事的身份,而这个身份便终身粘着在身上。”*[爱尔兰]理查德·卡尼:《故事离真实有多远》,王广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3页。如果说“故事”确定了何为人及其身份的话,那么“记忆”就不仅仅指向历史,其实也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了:通过“记忆”使我们明白,我们原来是有历史的存在,而这一历史指向今天,我们有了时间感,也就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将要往何处去了。简而言之,通过“记忆”和“记忆”中不同时期的“我”的对话,我们埋葬了历史,也安置了自身,更设定了未来。
(责任编辑:王学振)
Writings of Educated Youths amid Entanglement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XU Yong
(CollegeofHumanities,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As regards writings of educated youths, historical memory has always been a haunted “specter”, thus determining the constant wandering of educated youths between reality and history, because they have wanted to transcend history by affirming reality on the one hand but have discovered the unbearable “burden” in reality on the other hand. As a result of all this, educated youths would often have to remold themselves and reality by reinventing history, i.e. history, the self and the future have also been effectively placed in such a narrative.
writings of educated youths; “pains” in memory; reality and history
2016-05-30
徐勇(1977-),男,江西景德镇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
I206.7
A
1674-5310(2016)-08-0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