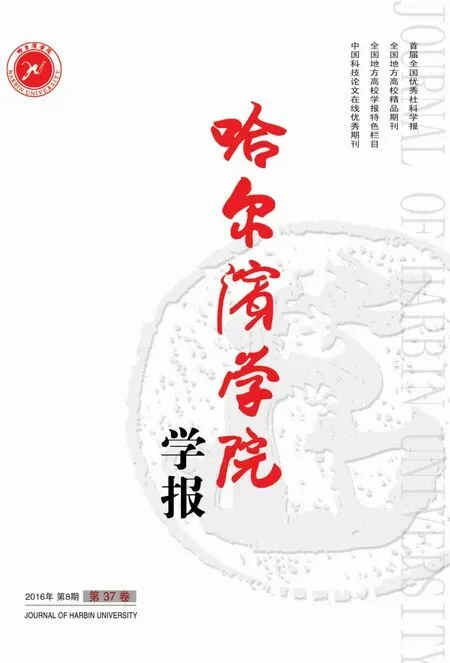“玄武门之变”与贞观雅正诗风的兴起
2016-03-16李巍
李 巍
(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玄武门之变”与贞观雅正诗风的兴起
李巍
(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150028)
[摘要]禁门喋血,李世民杀兄逼父,夺取皇位继承权,内心深处产生畏惧心理。他特别畏惧群臣非议,畏惧史臣秉笔直书,这种畏惧心态使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最终化为励精图治的动力之一,以图扭转乾坤。这种励精图治的心态反映到文学上是一种政教化的文学观,倡导雅正之文学。在其耳濡目染之下,贞观初年雅正之风大兴,诗坛上兴起一股清新劲健的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矫正绮靡诗风的功效。
[关键词]玄武门之变;贞观;雅正诗风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历来聚讼纷纭,议论不断、经久不衰。以“诗言志”“文以载道”为核心的诗教传统,已根深蒂固地将文学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形成我国独特的审美范式。《诗大序》论述得更为详细:“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P8)文学已成为政治的晴雨表,唐初的这场宫廷事件——“玄武门之变”也影响到贞观诗风的形成。
一、“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及唐太宗的畏惧心理
关于“玄武门之变”的性质,历来的史学家们采用“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替李世民开脱,说这场政变是李世民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之举,然事实并非如此。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事件。”[2](P58)“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及其谋士主动发起的一场宫廷夺嫡政变,政变的结果是原太子李建成命丧黄泉,李渊主动逊位,完成政权鼎革,李世民继承大宝,承传李唐神器,天下安定,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治世局面,堪称后世楷模。“玄武门之变”究竟对发动者亦是胜利者李世民内心产生怎样的影响?
据记载,李世民在事后经常梦中惊悸,李建成和李元吉出现在梦中骚扰李世民,长孙皇后想尽各种办法也难以使他安稳入睡。后来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为皇帝站岗,结果李建成和李元吉再也没有进入李世民的梦中,可能是尉迟敬德曾经杀死了李建成的缘故。后来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就被画成了门神,日夜守护着皇帝的大门。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它的真实性我们不必深究,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日诛杀兄弟之事给李世民内心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1900年,敦煌藏经洞里发现一篇古代小说,王国维名之为《唐太宗入冥记》,是《朝野佥载》的继续,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李世民对此事的心理。当崔子玉问六月四日事时,太宗“闷闷不已,如杵中心”,触及了内心的伤痛,也就是说,“玄武门之变”使李世民产生畏惧心理,不敢触碰,成为内心难以抚平的疤痕。
“玄武门之变”使李世民不仅畏惧死者,还畏惧生者,害怕时人的非议与指责。贞观二年,唐太宗即对侍臣说:“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3](P6048)
敬畏皇天乃自古常见现象,冥冥之中对上天敬畏乃人之常理,其实“下惮群臣”方是太宗的真正心声。“玄武门之变”是宫廷事件,波及范围未必广泛,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乱,百姓未必可知,而群臣则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此,李世民“下惮群臣”的指责非议,“下惮群臣”的蜚短流长,也“下惮群臣”将此事如实载入史册。由此,李世民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勤俭执政,以期用自己的实际政绩向群臣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继承者。
《资治通鉴》记载太宗在即位之初对侍臣裴寂讲自己勤勉政事的情况:“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3](P6026)《大唐新语》也载道:“太宗尝临轩,谓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乐当年,而励心苦节、卑宫菲食者,正为苍生耳。’”[4](P4)显然,唐太宗把全部的精力和思绪用在治理国家和百姓苍生上。
由于太宗的励精图治,勤勉执政,采取了“安百姓”“重人才”“强政治”“重法治”“开边境”等措施,特别是安抚百姓、知人善任并能虚心纳谏,使君臣上下戮力同心,形成一种励精图治的政治风气,开创了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就连对唐太宗“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行为给予严厉抨击的范祖禹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创世之功:“畏义而好贤,屈己以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5](P86)“下惮群臣”将此事如实载入史册,对历史怀有敬畏之心,畏惮他的子孙后代以及后人对此事的评价,于是他把视线投向了史书。他一方面设馆修史,由宰相监修国史,另一方面,多次觊觎观览国史,为“当代史”的书写符合自己的意志大开方便之门。
唐太宗曾经多次要求看国史,贞观九年,向朱子奢暗示欲看《起居注》,未遂。贞观十三年,向褚遂良旁敲侧击,打着“以自警戒”的名义暗示想看国史一事,遭到了褚遂良和刘洎直言不讳的拒绝。一年后,贞观十四年,他转向对自己听之任之的房玄龄。《贞观政要》卷七载: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自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6](P223)
此次李世民也是打着“以为鉴戒”“得自修改”的旗号,并没有和房玄龄商量,而是直言“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无奈之下只好略微删改为编年体,让皇上阅览。李世民见玄武门之事“语多微文”,即含混不清,立场不明,其原因可能是史官为了不让李世民知道秉笔直录的真相而进行删改的结果,也可能是大臣对此事的性质也难以界定。李世民看后便对六月四日事的性质进行诠释,此行为乃是行周公、季友之事,其动机是“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至此,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书写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变,由大逆不道变成是大义行为、至公大道。以后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无不众口一词,称此政变性质的合法性,并使这种解释方式固定化和永久化。
二、唐太宗的政治心态促使雅正文学观的确立
“玄武门之变”使李世民内心产生畏惧心理,这种畏惧心理一方面使他励精图治,国家蒸蒸日上,逐渐走向“贞观之治”的康庄大道。另一方面用儒家周公诛管蔡之事来解释“玄武门之变”这一做法,使其帝位继承方式合理化、合法化。并通过翻看并干预国史的编纂将这一解释方式固定化、永久化。这种政治的畏惧心态反映到文学上就是一切为政治服务的政教化的文艺观。
贞观初年,李世民君臣有一场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大讨论。《贞观政要·礼乐》载: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樽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相魏征对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6](P233)
杜淹认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是文艺决定政治,文艺的绮靡淫放能够导致亡国,所谓“亡国之音”。唐太宗则认为,悲欢之情源于人心,哀欢悲悦之情导致乐曲的欢愉与悲苦,与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人心的哀欢悲悦何所致,主要是政治。国家清明康泰,百姓安居乐业,家庭其乐融融,那么哀苦之情由何所生?值此清平治世,即使是重奏《玉树》《伴侣》之曲,由于人心和乐,也会听之不悲。概而言之,唐太宗的观点就是政治决定文艺,政治的兴衰成败决定人心的欢悦悲苦,进而导致乐曲之音。魏征也与李世民的观点相似,“乐在人和”,也即人的内心和乐与否往往决定乐曲本身的特征。其实也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观点如出一辙。
李世民的文艺观是有政治导向性的。在《帝京篇·序》中也说,“朕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6](P3)政治是第一位的,在政治之余方留意文艺。如何涤除前代余弊扫除绮靡文风?李世民在《帝京篇·序》中云:“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6](P3)也即在政治方面,希冀用尧舜清明康健的政风来涤荡秦汉以来积留的弊政;在文艺方面,希望用唐尧帝喾时的盛世乐章改变当时的绮靡烂漫的曲调。概言之,政治要回归古圣先哲之政,文艺要复归清平盛世之音。创作《帝京篇》的目的是“明雅志”,此亦政亦文,政治上要清明雅洁、志向崇高,文学上要典雅庄重,李世民的文学观有益于政教民生的,是政教化的文学观。
《贞观政要》“论文史”第二十八中记载了唐太宗与房玄龄的一段对话,也反映出此种文学观:“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杨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册?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7](P222)这段话体现了李世民的文艺思想,即应重视作品的社会功能,主张反对“浮华”,提倡“词理切直”,有益“劝诫”,可补“政理”,即务必对政教有所裨益的标准,体现了为政治而文艺的政教化的文艺观。
李世民是诗坛首领,他不但倡导雅正之风,而且创作大量的作品引领这种风尚。《帝京篇》是李世民的代表作,《全唐诗》将它置于卷首。序文明言“雅志”,组诗抒发“雅志”。《帝京篇》是一套组诗,首先在《帝京篇·其一》中对帝王雄伟壮阔的宫阙加以渲染描摹: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维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整首诗展示李唐王朝建国初期皇宫之恢弘与壮美,宏伟恢廓的气势中洋溢着昂扬的精神和广阔的胸怀。接下来其二至其九对帝王的宫廷生活场景进行蒙太奇式的描绘:潜心读书、阅赏武功、欣赏乐曲、游赏园囿、荡舟游赏之趣、宴饮之乐、后宫嫔妃之乐。游赏玩乐但不纵乐,虽构思精巧,但皆格调新奇,与前代的“靡靡之音”不可同日而语,诗中还相当强烈地表达作者励精图治的愿望:“对此乃淹留,欹案观坟典”(其二);“得志重寸阴,忘怀轻尺璧”(其八);“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其十)。而且虚心、纳谏、思民、慎行,警戒惊惧之心充溢其中,透露出一代天子君临天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忧惧情怀。
胡震亨云:“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赡精华,最为杰作。……雄才自当驱走一世。”[8](P1729)此评价可谓一语中的。“雄才”即雄才大略,在治国中体现出来眼光境界、胸怀谋略和才华底蕴,这些能驱走靡靡之音,达到“雅音方可悦”之目的,也即作者在序文中津津乐道的“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的“雅志”。
此外,李世民多数诗中无论是写景、纪事、游历还是其他,都不忘励精图治的愿望,在诗中,作者往往喜欢加上一句或几句述怀言志的诗句。例如:《春日玄武门宴群臣》“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出猎》“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元日》“巨川思欲济,终以寄舟航。”《初春登楼即目观作述怀》“弥怀矜乐志,更惧戒盈心。愧制劳居逸,方规十产金。”《冬狩》“禽荒非所乐,抚辔更招忧。”《春日望海》“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执契静三边》“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已知隆至道,共欢区宇一。”《望终南山》“对此恬千虑,无劳访九仙。”《帝京篇》第十首“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过旧宅二首》“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还陕述怀》“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还当葵藿志,倾叶自相依。”《赋尚书》“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入潼关》“弃繻怀远志,封泥负壮情。”等等。
以上诗歌或为咏史述怀之作,或是对往昔战争生活的回忆,或是对古圣先贤的讴歌与赞美,或为写物绘景之作,多在诗尾表达自己的雅志:或明确表达自己要虚己求贤、纳谏慎行、克己积善的美好志愿;或表示要为苍生安乐、天下统一、四海清平的康泰景象的希冀与追求;或忧心国政,抒发自己远志壮情。这些都是李世民日思夜想,汲汲以求的美好政治愿望。
三、唐太宗的文学思想对贞观诗风的影响
《全唐诗》录贞观时代的诗人近五十位,而当时有一定影响的诗人约十八位。[9](P28)这些诗人,除王绩、王梵志等少数隐逸诗人外,基本上都是唐太宗周围的大臣,他们具有政治家兼文学家或史学家等多重身份。唐太宗以其特殊的身份及理论创作方面的引领,理所当然成为文坛领袖,为贞观文臣树立了榜样。这些大臣耳濡目染,也表现出对前朝绮靡文风的批判,对雅正质实文学的倡导。这在贞观初年李世民下诏编纂的史书和类书中有明显的体现。
在《隋书·文学传序》的开篇,魏征站在儒家立场对文学在政教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10](P1729)
将“天文”与“人文”对举,天文之道与人文之道并存,文学乃隶属于人文,文学从根本上应承担教化天下的责任。而后又对梁陈靡靡之音进行批判,认为梁陈之音为“亡国之音”:“梁自大同以后,雅道论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镖,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10](P1729-1730)
五代史的修撰,房玄龄乃名义上的总监,实际上修撰者是魏征。魏征长于史论,“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征多预焉”,[11](P762)“《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12](P2550)《隋书·文学传序》乃魏征所撰,可以说是整个五代史中文学观的总纲,代表着贞观时期史臣的主流思想。
姚思廉的《梁书·帝纪论》《陈书·后主本纪》、李百药的《北齐书·文苑传序》、令狐德棻的《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等都表现出对齐梁以来的绮靡文风异口同声地指斥与批判,称其为“亡国之音”,这主要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上对梁陈及隋不崇教义、丧失雅道的文学给予痛彻批判;在形式上对淫丽辞藻、轻险之风给以严厉斥责,并且站在儒家正统思想“诗歌之道与政合”的立场指斥这不良之风为“亡国之音”。持论虽略显偏激,但切中要害。
既然雅道丧失、繁缛词采能最终导致国覆身亡。那么,为了国祚绵长、政风康健,则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提倡雅音,回归雅道。用雅正质实之内容来改善绮靡艳丽之风,以革新当时风气,于是倡导雅正的文学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在分析南北文风之特点后,主张南北取长补短,形成“文质彬彬”的风貌: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10](P36)
南朝文学过于“清绮”容易导致家国败亡,北朝文学过于“气质”容易流于质木无文。鉴于此,魏征的诗美理想就是取长补短,以雅斥靡、以气补意、以质救文,用丰富的政治内容充斥南方的清绮之风,形成“尽善尽美”的文学风貌。
令狐德棻撰成《周书》,在《庾信王褒传论》中言及梁陈宫体,强调文章要以气为主、文质得宜之时,更强调典雅庄重之风: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途,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8](P744-745)
令狐徳棻从文学之源说起,文学源于“情性”,也就是先秦之“缘情说”。笔锋一转,无论是“诗赋”“奏议”还是“铭诔”“书论”,也就是大文学,都要文气兼备。所谓的“气”,就是要广采儒家和诸子百家的经典来充斥文学的内容;所谓“文”,就是要探究屈原、宋玉、司马相如和杨雄文章的艺术技巧的奥秘,使文章文采斐然。“典”即典雅,雅正。强调文章注重“文”的同时,还要质实典雅。概言之,就是要达到调远、旨深、理贵和辞巧的要求,实现典雅赋丽、文质彬彬的美学理想。
李百药在《北齐书·文苑传序》后的赞语中卒章显志,也表达了对雅正之风的倡导:“赞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宁资刊勒。乃眷淫靡,永言丽则,雅以正邦,哀以亡国。”[13](P628)
要之,贞观史臣在对前代文学的绮靡文风进行批判同时,倡导质朴雅正,以雅正邦,以德兴邦。此时的文学已与政治联姻,文学的倡导走向为政治而服务,一切源于政治,一切为了政治。雅音的倡导正是从政治出发,是为政治而服务的政教化的文学观。
贞观时期纂修过很多类书,如《艺文类聚》《群书治要》《兔园册府》《文思博要》等。其所编纂类书的性质,也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以辅助帝王治国为标的,而文学上则以有益于教化为基准,即使是艺文类的类书也不例外。
《艺文类聚》的编纂始于高祖,完成于唐太宗时期,该书本是文艺类的纂辑,但是题材取向上多将古代贤明的帝王以及圣贤忠孝之士作为教化的典型,以达到文艺为教化服务之目的。
《文思博要》是唐太宗主持编撰的大型文学类书,贞观十五年十月完成。该书的序言中明确表达了政教化的文艺观:“义出六经,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则,极圣贤之训,天地之道备矣。”[14](P1358)类书由于源出六经,兼及百家,因此其作用不但能穷究帝王施政的成败得失,提供借鉴的历史法则,而且能穷极古代圣贤仁人的古训,备尽天地之大道。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与其他类书编纂之目的大同小异。
贞观时期类书编纂的直接目的就是为政治服务,通过编纂类书为帝王提供历史的借鉴,为他们的施政纲领及谋略提供参考的蓝本,即使是文学方面的类书也要服从、服务于政治。
此外,即使是受到前朝绮靡之风熏陶的大臣在进入贞观后也表现出对雅正之风的倡导。虞世南是历陈隋入唐诗人中颇为重要的一位,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籍”五绝,可见对其极其器重。虞世南入唐已经是六十岁高龄了,早年颇受南方六朝文学的影响,以浮艳、绮丽著称。贞观以后,践行李世民所倡导的雅正文学,虽然尚有六朝余续,但是有所改观。甚至一旦发现李世民有非雅正之作就当即谏止。《唐诗纪事》卷一载:
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尔!”[15](P6)
至于李世民是否真的创作艳诗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文献无载,但是据此推测可能是身为皇帝对绮丽之词一时的喜好罢了,后文的“朕试卿耳!”一句也许是李世民对虞世南的一种考验也未可知。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虞世南针对当时雅正之风的态度,对非雅正之风能够马上劝阻,即使是皇上也不例外。正因为皇帝的倡导、大臣们的身体力行,贞观初年才兴起了一种雅正之风,一股革新的风气。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唐太宗的倡导,大臣的践行,君臣之间形成了一股革新的风气,一股雅正的潮流。虽然并未完成清除六朝积弊的绮靡之风,但是也颇多改观。然而,由于贞观初年太宗君臣过于重视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诗歌的教化作用,使得诗歌说教有余,而情感不足,有矫枉过正之嫌。
要之,“玄武门之变”是一场宫廷夺嫡行为,使发动者李世民的内心产生畏惧心理,一方面畏惧时人非议,从而兢兢业业,将其化为励精图治的动力之一,使其皇位继承合理化;另一方面畏惧史臣秉笔直录,借阅史为名篡改历史,使其继承方式合法化。这种政治心态反映到文学上是为政治而服务的政教化文学观。在其耳濡目染之下,贞观初年,诗坛上兴起一种以中和雅正之政风矫正绮艳靡丽之文风的风气,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刘肃.刘德楠,李鼎霞.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范祖禹.唐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吴云,冀宇.唐太宗全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7]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令狐德棻,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9]尚定.走向盛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0]魏征,令狐徳棻,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刘知己.赵吕甫.史通新校注[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2]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4]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计有功.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谷晓红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8—0051—06
[收稿日期]2015-12-1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3E032;2014年黑龙江省教育厅教改项目,项目编号:JG2014010982。
[作者简介]李巍(1982-),女,黑龙江双城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文研究。
[中图分类号]I227.7;K2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8.013
“The Incident at Xuanwu Gate ”and the Rise of Zhenguan Standard Poetic Style
LI Wei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China)
Abstract:At the Forbidden Gate,Li Shimin murdered his elder brother and threatened his father to pass the throne to him,which made himself fear of revenge. He was afraid of being criticized. It is the fear that makes him careful and hardworking. This idea also leads to a standard poetic style. At the beginning of Zhenguan,this style was very popular. To some extent,this corrected the florid style at that time.
Key words:The Incident at Xuanwu Gate;Zhenguan;standard poetic 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