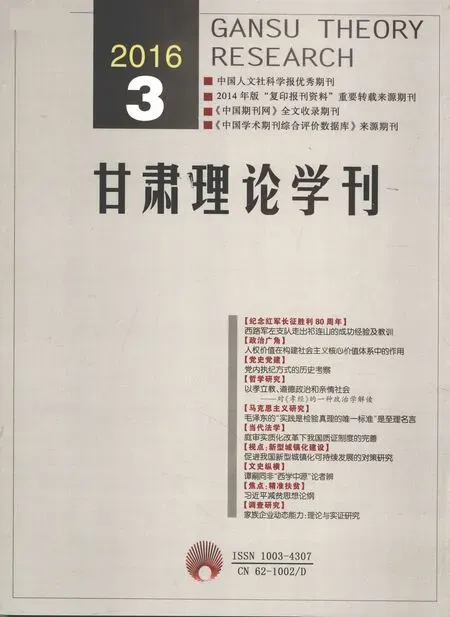马克思文本解读方法探析
——基于对“分析目的论”的反思
2016-03-16刘寒
刘 寒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马克思文本解读方法探析
——基于对“分析目的论”的反思
刘寒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1)
随着马克思文本研究中方法论自觉的提升,“分析目的论”的传统文本解读方法遭到批判。“分析目的论”以目的论预设为理论前提,其理论实质是逻辑优先的唯心主义方法论,理论延伸是“线性进化论”和“圣性焦点模式”,方法表现为成分分析法,理论后果是对马克思文本思想整体性的破坏和对文本的误读。不过,对“分析目的论”的批判需澄清三点认识。基于对“分析目的论”的反思,至少应从四个方面建构新的文本解读方法。此外,文本研究固然重要,但也应与现实研究相结合。
马克思;文本解读;分析目的论;方法
文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对文本的理解和掌握,是我们把握马克思真精神的必经环节。文本研究主要包括文献考证和文本解读,这两项研究自新世纪以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已渐成大势。其中,在文本解读研究中,解读方法是一个重要议题,对于把握马克思文本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空谈“方法论”容易给人“只说不练”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很容易把某种本身就成问题的方法论奉为圭皋,成为非批判观点的附庸,甚至沦为别人的某种方法论的蹩脚模仿者,而对自己的论域、限域等缺乏自知之明。但在马克思文本解读中,方法论自觉却是不可或缺的。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至少包含以下四层意思: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解读模式是“六经注我”(阅读马克思是为了构建自己的理论),还是“我注六经”(想成为马克思研究“专家”)?两者都无可指摘,但如果没有这种“自觉”,甚至有时故意混淆两者,就是不恰当的。[1]91-93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避免阅读的盲目性,审慎选择科学解读方法。再次,要明确自己所使用的方法的边界,意识到任何一种方法都是有限度的,与其他方法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最后,要对原有的方法论予以反思和重构。这是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该学科突破旧的思维结构、创建新的理论框架的重要先导。
随着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日渐兴盛,国内学者的方法论自觉已大有提升,突出表现在对传统解读方法的反思和批判方面。近年来,学界对“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等解读模式的反思,引发“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的强烈呼声,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倡导创立“中国马克思学”。其中,对苏联解读模式的反思和超越成为不少学者的突破口。对“分析目的论”的批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赫然登场。
一、对“分析目的论”的五大批判
“分析目的论”是一些学者对苏联治史模式的概括。由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本质上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延伸出的学术领域,与发展史研究密不可分,因此这一治史方法也浸染到文本研究领域。其基本涵义是:解读者认为马克思生而为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带着这种“马克思必将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将马克思文本(尤其是早期文本)划分成不同的思想成分,找寻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和生长点,并常常以教科书原理体系反注思想史。阿尔都塞曾在《保卫马克思》中以“总问题”为理论武器对“分析目的论”大加批判,借此指责当时学界对青年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现在国内学界则多借用西方“目的论预设”、“预设论”等术语来指称这一方法。从学者们的论述来看,学界对“分析目的论”的批判主要从以下五个维度展开。
1.理论前提:目的论预设
“目的论预设”意指研究者带着“马克思必将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来解读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展现一种“从结束向开始的回溯”。具体表现为:第一,认为马克思天生就是要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作为后人,要做的只不过是梳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从中找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和生长点,进而重现其不断实现的过程。第二,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理论为支点,去回溯马克思思想是怎样一步步向此支点靠拢的。如在传统教科书体系支配下,以唯物论加辩证法为理论支点,随着中国实践语境的转变,又转向以主体性的实践以及人的存在等为理论支点。[2]9-10第三,以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为“历史的秘密法庭”[3]41,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观念作出判决。
2.理论实质:逻辑优先的唯心主义方法论
在不少学者看来,在目的论预设的前提下,这一方法的理论本质只能是以主观意图来绑架真实历史的唯心主义方法论。这一方法用预先制定的理论框架或者概念范畴来主观地演绎马克思主义生成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在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下,研究者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教科书的原理体系来反注思想史,由此将思想史诠释成抽象概念的历史,书写出来的思想史成为了思想如何验证原理与公式,以及一个概念如何向另一个概念推导、演进的过程。因而必定是一种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绝对逻辑主义的研究方法。
3.理论延伸:“线性进化论”和“圣性焦点模式”
这是国内学者张一兵教授的提法,本文沿用这一提法。所谓线性进化论,意指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时,总是试图追求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寻找逻辑上平滑的进展,试图把问题说圆,从而发现出一些所谓“正确”与“合理”的地方。因此,在传统的研究工作中,我们看到的总是一个顺理成章、思想流畅的马克思。在这种解读中,马克思似乎是一粒“马克思主义者”的种子,从其出生时起,至少从其开始哲学思维时起,这粒种子就种下了,以后的发展不过是这粒种子的进一步发芽、开花、结果罢了。[4]29所谓圣性焦点模式,则指在研究马克思的过程中,总是以马克思为绝对中心,不客观地贬斥同时期其他思想家的学术影响,以凸显马克思的思想原创性和深刻性。[5]7
4.方法表现:成分分析法
这是最典型的“分析目的论”的做法,就是把每一文本还原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并对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成分单独进行研究,或者把它与属于另一个体系的另一个类似成分相比较。其突出表现是,首先把某一文本中的思想分为唯物主义成分和唯心主义成分,然后从各自的立场和标准出发,着重强调其中的某一成分,据此对马克思在这一文本中所体现的思想性质予以评价,最后对这一文本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地位进行定位。例如,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指出马克思虽然在阐述中使用了带有费尔巴哈色彩的甚至是黑格尔的表述,但文中显然也包括了一些唯物主义成分,如社会阶级的现实存在,私有制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的存在,甚至唯物辩证法的存在,等等。
5.理论后果:对文本思想整体性的破坏和对文本的误读
在阿尔都塞看来,把同一文本分成不同的成分严重破坏了对文本思想的整体性。他指出: “唯心主义成分就是唯心主义成分,唯物主义成分就是唯物主义成分,把两种成分在一篇文章里结合成一个生动和现实的整体,谁能够去断定它们究竟具有什么意义?”[3]44-45此外,在以往研究中由于“意图先行”,导致了对马克思文本的误解或“误读”,特别是在这种解读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性考量,使马克思思想的阐释随着意识形态的转换成为一种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的政治游戏,损害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恒定性。
二、关于“分析目的论”的三点澄清
以上主要是质疑者对“分析目的论”所做的批判。应当说,在传统解读模式中,“分析目的论”的方法确实是存在的,上述分析和批判是较为恰当的。但是抛弃“分析目的论”不意味着走向极端反面,即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的方法论传统;更不意味着把所有的主义或意义全部抛开,只剩下历史的素材在跳偶然性的舞蹈。因此,在对“分析目的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还需要澄清以下认识。
1.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有其内在逻辑
马克思的文本不是文献素材的偶然排列,而是内在蕴含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马克思文本中,存在着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两种逻辑:一种是主要反映马克思学术理想的“应有的隐性逻辑”,另一种是主要反映马克思实际完成的理论成果的“现有的显性逻辑”。[6]183对第一种逻辑的理解,事实上牵涉对马克思的精神实质的把握。这一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解读者的“前理解”而出现的,不涉及“目的论”。因为,如果没有对马克思精神实质和思想主题的深刻把握,也很难对经典文本作出透彻的理解和合理的评价。但是,第二种逻辑则不应该是解读者在预先设定了诠释模式和理论支点之后,通过回溯的方法得来的,而应该是通过深层的文本解析解读出来的。对第二种逻辑的真实再现必须摆脱“目的论预设”。
2.拒斥“目的论”并不意味着抹杀解读者的主体性
解读者不可能如洛克所说的带着一块“白板”式的心灵去解读文本,必然会有自己的主体认知模式、自己预设的观念系统等“前见”,“嵌入”和参与到具体的解读过程当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样如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在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时,我们总是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以下三种研究视角中的某一种视角的影响:恩格斯的研究视角、卢卡奇的研究视角和马克思本人的研究视角。[7]13-14但是,这些不应当成为我们膨胀自己的先验观念的理由,否则就容易陷入“预设论”困境。事实上,解读者的主体性究竟应限制在什么程度,而不致影响对文本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和注意的问题。
3.马克思早期文本中新旧哲学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并未消解反而彰显了文本魅力
新旧哲学的矛盾在马克思早期文本中处处可见。例如,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论证的内容和使用的方法就多少存在一些不匹配之处。他从经济事实出发,但由于经济知识准备不足,在论证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使用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方法和黑格尔的三段式方法。此外,马克思的主观意识和客观理论趋向也常存在不一致。例如,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虽然客观上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了费尔巴哈,但他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和费尔巴哈的分歧,相反在主观上还认为自己是费尔巴哈的学生,还存在着对费尔巴哈的迷信。正因为如此,为阿尔都塞所诟病的“成分分析法”才会在马克思早期文本研究中极为流行。因此,很大程度上,这一做法并非出于“目的论预设”的理论前提,而恰恰是对文本思想仔细考察后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至于阿尔都塞的批评,我们都知道,“问题式”是他的理论出发点,他所谓“问题式”其实是一种统摄问题域的隐性功能结构,是以结构主义为理论前提的,他的理论本身就带有一种“方法论帝国主义”(阿多诺语)的痕迹。而且,内容和形式、意识和趋向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更加彰显了马克思早期文本的巨大张力和永恒魅力。因此,对于马克思早期文本中新旧哲学的矛盾毋庸讳言,对其作出区分和具体分析不仅无可指摘,而且是一种必要的解读方式。
总之,本文认为学界将传统马克思文本解读方法归结为“分析目的论”并将其作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反思和批判之余,我们也不应走向反面,而要澄清上述三点重要认识。
三、马克思文本解读方法的新建构
对“分析目的论”的反思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超越这一方法,实现马克思文本解读方法的创新。对此,有学者提出“内在性历史发生学的方法”[8]11的主张,本文较为认同这一提法。针对“分析目的论”的弊端,本文认为,在马克思文本解读中至少应坚持以下方法论原则。
1.坚持历史优先的原则,抛弃“目的论预设”
对马克思而言,如何准确把握所处的时代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朝着特定的哲学历史观发展,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新哲学的创立是他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逐渐和自然形成的。因此,文本解读需要坚持历史优先的原则,抛弃“目的论预设”。马克思主义究竟具有怎样的丰富内涵,这本身需要研究来得出结论。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当然,我们知道青年马克思必将成为马克思,但我们不打算代替马克思去生活。”[3]58因此,在文本解读中,不应在研究之前就服从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设定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否则当意识形态需要用另一种观点来作理论支撑的时候,便自然会产生对马克思文本的另一种解读。这种学术景象只会是表面繁荣,其实是理论研究退步的表现。不过,关于这一原则,还需要明确以下两点。
首先,坚持历史优先并不否认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如前所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有其内在逻辑,但这种逻辑不是在历史之前被先验设定,而是在历史过后彰显出来。在文本解读中,坚持历史优先的方法原则,并不是有意遮盖这一内在逻辑,相反,这一方法要求我们把真实呈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作为主要学术工作。强调历史优先,意在矫正逻辑优先的做法。对逻辑的展现应建立在对文本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深度解读基础上,而不是主观臆断,将其撰写为逻辑的历史。在这里应坚持“以文本为本位”,即在阐释马克思思想的时候,从他的文本的特定语境和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而不是从别人提供的解读模式和诠释框架或自己的观点、倾向方面去考虑。
其次,历史优先并不排斥对概念的解读。有学者曾提出“概念式的解读方式”,意指“对构成文本的基本范畴进行解读,通过对基本范畴的研究来把握解读对象的全貌”。[9]6我们并不反对这种对概念的解读,我们所反对的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逻辑演绎和外在推理。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一些基本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市民社会、实践、分工、交往、所有制等等,有些为马克思所独创,有些则是马克思沿用旧哲学术语但赋予其全新内涵。在文本解读中,对某一文本的核心范畴的理解往往关涉到对文本整体思想的理解。例如,“异化劳动”作为《1844年手稿》的核心范畴,“实践”作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核心范畴,“分工”和“交往”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等,对我们理解和把握这些文本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概念式的解读是必要的。另外,对于在马克思早期到晚年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概念的流变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脉络。不过,概念解读的基础不是读者自己的理解或传统教科书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体系对这些概念的设定,而是文本本身。在解读过程中,应忠实于文本,并考察马克思对这些概念的运用同其他思想家的异同以及他本人在不同文本甚至在同一文本中对同一概念所赋予的不同内涵。
2.坚持表层解读和深层解读以及多种阅读方式的统一
表层解读主要是对文本表层结构的解读,即对构成文本的语言、符号、段落、篇章等进行解读;深层解读则涉及到对文本主旨、总体意图、体系观念以及作者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有学者曾概括出阅读马克思的三种方式:朴素式阅读、症候式阅读和互文式阅读。朴素式阅读把阅读仅仅视作一个直观地看和读的过程,似乎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无需任何理论和现实的中介,它不曾考虑过阅读本身,包括阅读者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旨趣,所阅读文本的语言和风格,阅读的场景和节奏,等等。症候式阅读来源于阿尔都塞,它把阅读视作一种生产,关注文本中的空白、沉默和缺漏,认为能够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不是由主体的视觉决定的,而是由问题结构决定的。互文式阅读面向未来,在文本与文本、科学与修辞、写实与象征之间自由跳跃,要求多角度的阅读和阐释,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10]1这一概括较为全面合理,因此本文沿用这一说法。
朴素式阅读大致等同于表层解读。在这种阅读中,读者往往囿于马克思的字面意思,而不去考察其深层所指,忽略了文本和思想之间的复杂情形。在症候式阅读中,解读者不再停留于文本表层,而是考察字里行间的意思,领悟看不到的东西,对文本的主要意旨、总体意图、体系框架形成自己的理解,并努力把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然而,症候式阅读最多也只能使我们对马克思的本真思想有所体悟,但这并非文本解读的最终目的。对理论的发展、对现实的关照才是马克思研究的落脚点。因此,这就需要一种创造性的阅读法,即所谓互文式阅读法。这种阅读不是停留于对马克思概念和思想的一般性把握,特别是不再简单地用(读者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概念术语来把握马克思,而是能够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框架,这些新的概念框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却又不仅仅是马克思的,而是针对当代的社会生活提出的。例如,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葛兰西的“领导权”,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等等。[10]6这种解读已经不仅仅是马克思文本结构的再现,更是一种重构。因此,文本解读需要坚持多种阅读方式的统一。
3.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简单解释框架,对文本思想作“差异分析”
在传统解读方法中,囿于“分析目的论”的解释框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常常被描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抗的历史。尤其是在马克思早期文本研究中,“两个转变论”、“不成熟论”影响深远。但是,“两个转变”作为哲学的党性原则和日丹诺夫式的哲学史解读模式的一种贯彻和体现,至多只能是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一种解释,而不是唯一的解释。更何况,如此一来,青年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都要被归为唯心主义,被指认成“不成熟”的著作。虽然一个深刻的唯心主义者比一个肤浅的唯物主义者更有价值,但是一旦打上唯心主义的标签,很多文本还是难逃被忽视的命运,文本中不少闪光的思想质点就会与读者失之交臂。例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由于被认为置身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框架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和兴趣。而事实上,此时的马克思,虽然“还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者,并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但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论文所体现出来的勇于突破旧说的独创精神。”[11]23但这种独创精神却长期被忽视,马克思与伊壁鸠鲁、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黑格尔的内在差别长期被排斥在研究者视域之外。
因此,在文本解读中需要借助“差异分析法”,而不能仅停留于“本质认同”[7]10。本文所谓“差异分析”与“本质认同”,代表了思维中的两个不同的路向。具体到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则可以分别被视为对文本具体思想的深入分析以及对文本思想性质的简单定性。尽管“本质认同”在人们的运思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如果我们在解读马克思早期文本时,仅仅满足于“本质认同”,即满足于对马克思的思想属于黑格尔唯心主义或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等进行简单判定,只能导致我们对文本本身以及对马克思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关系的模糊认识,并人为降低了马克思早期文本的思想价值。
4.为马克思“祛魅”,防止把马克思“圣化”乃至“神化”。
在传统研究中,马克思常常被塑造为一个“高大全”的形象,有被“圣化”乃至“神化”之嫌。这在对马克思的论战性文本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研究者在解读马克思的论战著作时,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马克思对论战对象的批判是永恒正确的,由此忽视了对论战对象本身的深入研究。例如,在以往对《神圣家族》的研究中,以往国内学界几乎一致认定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酣畅淋漓、深刻到位,因此也就不再仔细阅读鲍威尔本人的作品。而波兰学者兹维·罗森则客观地指出了马克思的不当之处,指出马克思只是抓住了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上的几篇文章,尤其是主要抓住他的精神和群众的理论,而有意忽视了鲍威尔的整体思想,而实际上,这几篇文章只是鲍威尔作品中的沧海一粟。因此他认为马克思甚至有人为设定一个便于批判的敌人的做法。当然,罗森还是站在马克思立场上的,认为鲍威尔确实存在某种“智力的缺陷”,马克思在很多问题的思考和论述上确实比鲍威尔高明。由此可见,即使最后的结论不变,承认马克思确实比同时期其他思想家更为深刻、高明,我们也不应采取一种惰性的研究方法,只知马克思而不知其他,而必须以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为基础。更何况,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未必一定比同时代的蒲鲁东、赫斯和青年恩格斯等更加深刻。对于其他思想家的深刻性,我们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和肯定,才能进而真正发现马克思在高水平的学术资源基础上实现的思想革命,真正发现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一现象近年来已逐渐得到缓解,尤其是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至少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马克思已渐渐走下神坛,恢复其作为思想家而不是作为“神”的本来面目。
此外,文本解读还应结合对马克思个人人生道路和个性特征的解读以及对历史背景的考察等,此外也要尽可能借助国外文献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等等。囿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文本研究尤其是文本解读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有基础性地位,但同时,实现理论发展、服务现实生活也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文本解读研究热潮的兴起是对肤浅的理论宣传和政策解读的反叛,有助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严肃性和学术性,但我们不能由此滑入罔顾现实、埋头故纸堆的另一极端。所谓“回到马克思”也只是要回到马克思的真精神,而不是回到马克思的一切现成结论上,并教条主义地固守这些既成结论。为此,文本研究需要和现实研究相结合,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单纯变为文本和思想史的诠释学,否则就会出现“史料研究和文本解读的理论空缺”[12]5-6。“以马克思为对象的研究”固然重要,是基础,但“像马克思那样研究”[1]86更加必要。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不仅在于他研究了以前以及同时代的各种思想和文本,更在于他凭借这种研究所积累和锻造的理论素养,透视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历史的种种问题。因此,我们也不应把研究限制在文本范围内,而要实现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结合,构建体现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
[1]杨学功.在范式转换的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评论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唐正东.从预设论到内生性历史发生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法反思[J].学术月刊,2005,(10).
[3]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王金福.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学考察[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5]张一兵.何以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史[J].学术月刊,2005,(10).
[6]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俞吾金.差异分析与理论重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1).
[8]唐正东.从预设论到内生性历史发生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法反思[J].学术月刊,2005,(10).
[9]韩立新.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张立波.阅读马克思的三种方式[J].现代哲学,2002,(3).
[11]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2]何萍.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康继尧]
Study on the Method of Marx’s Text Interpretation——Based on the Introspection of the Skopos Theory
LIU Han
(SchoolofMarxism,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ext research in Marxism research,the methodology consciousness is highly promoted.Along with this,the traditional methodology called Skopos Theory is strongly criticized.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Skopos Theory is the teleology thinking mode.Essentially,it is an idealism methodology.Its extensional theory is linear evolution and divine focus pattern.It adopts component analysis as its method.It can lead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the texts as well as the misreading of the texts.However,we should also notice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ought has its internal logic.Second,rejecting Skopos Theory does not mean obliter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readers.Third,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new philosophy and the old ones exists in Marx's early writings,but it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xts instead of eliminating it.Based on the introspection of the Skopos Theory,a new method of text reading can be constructed at least from four aspects.In addition,although the text research is important,i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research so as to establish the new form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Marx; text interpretation; Skopos Theory; method
2016-03-25
刘寒(1988—),山东菏泽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A81
A
1003-4307(2016)03-008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