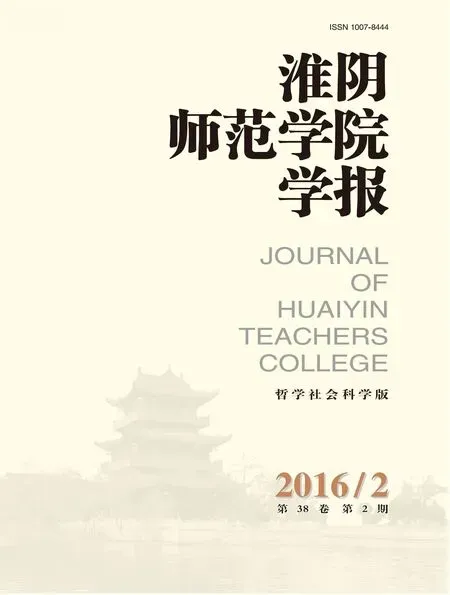“疑古”之外的学术追求——顾颉刚的通史编纂构想与实践
2016-03-16刘永祥
刘永祥
(中国海洋大学 社会科学部, 山东 青岛 266100)
“疑古”之外的学术追求——顾颉刚的通史编纂构想与实践
刘永祥
(中国海洋大学 社会科学部,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抗战期间,发挥史学致用功能越来越受到史家重视,顾颉刚即曾尝试以中国通史编纂唤起民族意识,主张从受众角度探索编纂形式的多样化,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其在编纂理念上,则与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一脉相承,如以中华民族的发展为主干书写社会“全史”;推动由“君史”向“民史”的转型;发扬集体修史的优良传统;将专史视为通史编纂的基础等。顾颉刚这一“疑古”之外的史学追求,不仅折射出抗战时期通史编纂形成继20世纪初“国史重写”运动之后的新高潮,而且提醒人们应当注意“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顾颉刚;通史编纂;通俗史学;民族意识;“新史学”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江苏苏州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留校任图书馆编目,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历任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曾创办朴社、民俗学会、禹贡学会、边疆研究会及中国史地图表编辑社等,主编《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文史杂志》等学术刊物,编著《古史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等。其在历史学、边疆地理学、民俗学等领域皆有突出贡献和影响,尤其是他所领衔的“古史辨”运动,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学者所言:“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派,实际上已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典学界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1]每当人们提及顾颉刚史学时,首先想到的必然是“疑古”,显然已经被符号化。因此,很少有人注意到顾颉刚史学的另一面相,即中国通史编纂,而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更全面地认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而且具有超出这一问题本身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意义。
一、以通史编纂唤起民族意识的努力
近代以来,在作为“他者”的西方国家的不断冲击下,国人开始以此为参照重新认识“自我”,世界文明体系下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意识逐渐萌生并迅速增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由自在阶段步入了自觉阶段。由此,民族主义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因子,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持续侵略则将这股民族主义思潮推向了顶峰,并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取向和学风,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成为包括新历史考证学派在内的诸多史家的共识。其中,一直秉持“只问真不真,不问用不用”治史态度的顾颉刚的转变,就十分典型。他明确指出: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的民族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2]363(《禹贡发刊词》)
年来国势凌夷愈甚,国人皆知非提倡民族主义将无术自存于世,而以史事知识普及于民众,藉先民保存种族之伟绩与其创造文化之光荣唤起其爱国家爱民族之热忱,实为灌输民族主义最有效之方法,于是中国通史之需乃亦亟。[3]203(《拟由本会设立中国编纂处案》)
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以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重建国民自信,并通过历史认同增强民族认同,无疑是极为重要的途径,而兼具叙事性与解释性的通史显然最能承担这一任务,这也是在史学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过程中,通史编纂能够再度异军突起的重要原因。对此,顾颉刚显然有深刻的认识。而且,他认为,以往的通史皆以“汉族的史迹为中心,很容易挑拨各族间的恶感”[3]63(《考察西北后的感想》),极力倡导“不专以汉族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体之活动为中心”[3]87(《考察西北后的感想》)的新的历史书写范式,主张“用平等的眼光记载各族的历史事实,凡是共同享有的光荣和被迫分享的耻辱都应当详细抒写,而摒去一切私愿”[3]63(《考察西北后的感想》)。其落脚点,则在于从历史和文化两个层面论证“中华民族”这一具有近代内涵的新概念的正当性。他说:
从历史上证明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从文化上证明我们中华民族为一个相互融合的大集体,将文化与历史永远打成一片。[4]
当然,要想真正发挥历史在激发民族意识方面的功效,就必须扩大历史知识的传播范围,因此,编纂风格多样的通俗历史读物以满足不同文化程度的受众需求,成为一时风气,而中国通史编纂亦突破原先的研究型写法,呈现出通俗化趋势。顾颉刚正是通俗中国通史编纂的大力倡导者,不仅提出了诸多设想,而且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九一八事变以后,顾颉刚创办了三户书社,出版抗日读物,次年将其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将唤起民族意识、鼓励抵抗精神、激发向上意志以及灌输现代常识作为该社的主旨和目标,而编纂通俗中国通史即为主要途径之一。顾颉刚试图以人物小传为切入点,进而编纂一部类似《三国演义》的通史演义。他的规划是:“打算先由个别人物写起,将来再加工整理,改写通史演义。”[5]376(《中国上古史演义序》)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类小传仅完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几篇。*当时,这项工作主要由其助手郑侃嬨来完成。顾颉刚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又欲作中国通史,而不得一助手。适在《燕大月刊》中见郑侃嬨女士所作《西游记补》,文笔极清利,且有民众气而无学生气,最适于民众教育……此事如能成,必可收救国之效。”(《顾颉刚日记》卷三,《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页)1943年,顾颉刚发起史地通俗丛书编辑社,再次将《中国名人传》的撰写、出版置于首位,并称:“自周迄清得二百余题……期就此数百人之身而表现其各个时代与各个社会之背景,析之为百册,合之为一书,而《中国通史》之雏形于是乎在矣。”[6]23(《编辑中国名人传说明书》)后来,他在担任上海大中国图书公司总编辑期间,主编“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又尝试以历史故事的形式编纂通史,在《编辑旨趣》中说:“先出第一集,计一百六十种。在这一集里,最重要的故事差不多齐备了,顺了次序看去也权当一部中国通史。”[7]尽管上述工作均未能完成,但顾颉刚为通俗中国通史编纂所作出的努力实不应被抹杀。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顾颉刚认为应从受众角度出发探索通史编纂的多样化,主张根据读者阅读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差异分成不同的层次。比如,早在重庆中国史学会成立时,顾颉刚就曾提出针对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等分别编纂不同形式的通史,至1947年,又将这一构想进一步细化,制定了七种通史写法,包括:给小学生及其同程度者看的,用连环图画;给初中生及其同程度者看的,用故事体的叙述;给高中生及其同程度者看的,用演义体的叙述;给大学生及其同程度者看的,用现行的通史体,但不发议论,只在叙述中予以暗示;给专家及高级的大学生看的,用讨论问题并考证材料的通史;给边疆人民看的,用边疆与汉族分量差不很远而足以鼓起其向心力的通史;给世界人士看的,用偏重文化而足以使其认识中国在世界史的地位的通史。[8]164从中不仅可以窥探顾颉刚以现代史学理念普及历史知识、重塑大众历史观念的急切心情,而且更包含着他藉通史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弘扬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刻用意。
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对通史编纂格外关注,尚非仅仅受到日本侵略的影响,而与他早年的学术经历亦密切相关。20世纪初,“新史学思想的输入引起了改编国史的运动。起初最迫切的需要,莫过于学校的课本”[9]。受此风潮影响,顾颉刚也参与到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1922年,在胡适的介绍下,他与好友王钟麒共同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了《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此书共三册,上册于1923年出版,几年内即再版55次,中、下册于1924年出版,亦再版25次。[10]其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后来,他还曾着手编纂《国史讲话》,只是由于其史学研究已转移到上古史领域而未能完成。不过,他曾在《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中说:“在极忙中也乐意接受:只因这件事情原是我自己的,一方面可以逼我增进常识,一方面又可以逼我整理了常识材料而供献于读者。”[11]由此可见,顾颉刚虽然无法分出过多精力从事通史编纂,但对此始终有所挂怀,而日本的入侵则再度激起了他的热情,并对当时通史编纂的现状充满了忧虑,谓:“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12]
二、与“新史学”一脉相承的通史编纂思想
中国传统史学是以历史编纂为主体的,故而梁启超有关“新史学”的理论建构实则服务于一个主要目的——编纂新史,《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皆旨在“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13],并强调“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14]自序。“新史学”在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国史重写”运动,虽以教科书为主要载体,仍令“修史”成为一时风气。受此影响,顾颉刚曾明确表示对这一学风的认可,称:“我总勉力搜集史料备将来的作史。”[15]他的通史编纂思想即主要来源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曾明确说:“(练)为璋带来任公《中国史学研究法讲义》(笔者按:即《中国历史研究法》初稿本),读之如我心中说出,盖即我要说之话,要本这意见预备编书的。快极,拟摘要抄录。”[16]172大致来说,除注重发挥通史编纂的致用功能、以通史编纂激发民族意识外,顾颉刚的通史编纂思想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突破以政治史为主体的通史格局,主张以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主干,书写反映社会整体情状的“全史”。顾颉刚认为,传统的通史“实在只可说为完全的政治史”[5]20(《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而通史的核心任务在于“把进化的迹象指示出来”,“所谓进化的迹象,在大题目上,固是:民族是如何发展的;文化是如何迁流的;各时代中,政治和家庭的组织是如何的,经济力的分配是如何的,道德观念的方式是如何的;文明的主要器械是何时制作的”[5]23(《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1931年,他在致谭惕吾的信中亦说:“我抑不住的野心,总想把中国历史重新排过……倘使我们能够作成一部历史,(1)说明传统文化的来源与演变;(2)说明国内民族的分合的经过;(3)说明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将来的命运;(4)说明民众的生活状况及其改善的途径,吾深信国民的思想将顿然为之一变,将激起其勇往直前的精神,走上向上和合理的道路上。”[17]258-259尤其是,他自觉地对20世纪初的通史编纂加以反思,认为“过去中国通史一类的书籍,差不多都是以日本人的著作为蓝本写的,这是历史学者的奇耻大辱”,并将通史编纂原则凝练为两点:“第一,通史绝不是一姓、一阶级、一种族或一宗教的记载,而应为中国历史的全貌。第二,中国通史应为世界史的一部分,以全国所需要,世界所需为其目的,而绝不能独立的与世界不相联系。”[3]294(《中国之史学》)很显然,顾颉刚试图克服旧史记载范围狭窄的弊端,扩大历史书写范围,而以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主线统摄全史,并突出强调世界视野,则其主旨仍在于重建大众的民族意识和自信。*顾颉刚曾回忆编纂《国史讲话》时的心态,称:“这几年……许多人属望我编成一部中国通史……我的心中一向有一个历史问题,渴望借此得一解决,即把这个问题作为编纂通史的骨干。这个问题是: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这真是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最重大的历史问题。”(《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将上述顾颉刚关于通史编纂的框架和内容的论述与梁启超的观点尤其是《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为“适合于中国人需要之中国史”[14]7所归纳的主要事项加以比照,即可明白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的传承关系。
其次,继续推动通史编纂由“君史”向“民史”的转型。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对旧史编纂展开猛烈攻击,直斥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姓之家谱,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共鸣,时人无不倡写“民史”。顾颉刚亦明确指出:“从前的历史简直是帝王的家谱,无论什么叙述,都是以说明一姓的兴衰为主:战争是为的正帝统,灾异是为的警帝心,以至于一治一乱,一离一合,无非世运使然;他们以为到了相当时候就该有王者应时应运而兴起了。那时的人不是人,是王者的爪牙或工具,因此,从前的历史就只得以帝王为中心而成为一姓的家谱。”[5]1,100-101(《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商榷》)因此,他将目光聚焦于社会基层,注重对社会史料和民俗史料的发掘,认为“应当看谚语比圣贤的经训要紧;看歌谣比名家的诗词要紧;看野史笔记比正史官书要紧”,因为“谣谚野史等出于民众,他们肯说出民众社会的实话,不比正史,官书,贤人,君子的话主于敷衍门面”[5]23(《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他试图转换历史编纂的视角,将书写重心转移到普通大众。1928年,他在《民俗》发刊词中呼吁说:“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18]他还举例加以说明,认为:“与其详载官制的变迁,不如记些科举情形,因为循资升迁无甚可记,而选举科第等事几乎笼罩着读书人的全部思想。我们与其详载国家组织,不如详载家庭组织,因为国家组织及于人民的力量,不如家庭组织的深而且广。至于各代的兴亡,是帝王的家事,远不及民族离合的关系重要了。”[5]20-21(《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他在编纂《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时即践行了上述观念,不再采用朝代更迭的叙述模式,破除正统观念,不用帝王年号,亦不作帝王世系表。客观来讲,顾氏所论自然有失偏颇,但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采用梁启超式的“不破不立”的批判文风,显然有利于推动通史编纂在视野和路径上的转移。
最后,主张发扬集体修史的优良传统,并将专史编纂视为通史编纂的基础。传统官方修史虽因统治者意志的介入而产生诸多弊端,但分工合作的方式的确适用于大规模的修史,也较易取得成绩。顾颉刚认为:“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19]204而现代分科意识的上升促使史学走向专门化,日益细化的专史无疑增加了通史编纂的难度。因此,先专史、后通史的编纂步骤得到越来越多史家的认可。顾颉刚亦将通史编纂分为两步:“第一步为编辑专史,搜集材料而考订之,加以系统之贯。凡十五种,目如下:一、种族史,二、疆域史,三、交通史,四、外交史,五、政治史,六、社会史,七、经济史,八、生活史,九、宗教史,十、教育史,十一、科技史,十二、思想史,十三、艺术史,十四、文学史,十五、语言史。第二步即汇合各种专史。”[3]204(《拟由本会设立中国通史编纂处案》)不过,他并未就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分析。
细加比照,顾颉刚的通史编纂思想基本来源于梁启超的“新史学”。以往学者多将“新史学”限定于五四之前,此后则以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两大主干,这一划分方式过分突出了史学思潮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梁启超所建构的与中国传统史学相区别、与西方现代史学相接轨的“新史学”范式,在五四以后被不少史家完整地继承下来并加以拓展,尤其表现在中国通史编纂领域,而且诸多理念亦对其他两派学者产生不小的影响。*陈其泰先生曾就“新史学”对新历史考证学的影响展开探讨,详见其《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8页。顾颉刚在通史编纂思想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与梁启超“新史学”的一脉相承,即为此增添了一个绝佳的例证*近年来,更有学者认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顾颉刚就此提出“层累说”的“关键性”因素(参见李长银:《“层累说”起源新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结语
顾颉刚的通史编纂理念亦对后来修史者产生直接影响。他曾与白寿彝通信探讨通史编纂问题,其所秉持的注重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书写、突出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发挥通史的教育功能、彰显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等理念得到后者的深度赞同。白寿彝在信中表示,“搜集了他们(边疆)的历史材料放到全国公有的历史书里去”,“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应该是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我们的新的本国史的一个重要观念”[20]162-167。1947年,顾颉刚又给白寿彝写信,提到应编写有利于民众教育的通俗通史、注重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等观点。[8]162-167后
来,白寿彝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对于上述问题尤为重视,当与顾颉刚的影响有一定关联。
参考文献:
[1]王学典.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写在《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N].光明日报,2011-01-11.
[2]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五[M]//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
[3]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二[M]//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
[4]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96.
[5]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三[M]//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
[6]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一[M]//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
[7]顾颉刚,等.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M].上海:中大中国图书店,1949.
[8]顾潮.顾颉刚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9]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J].燕京社会科学,1949(2).
[10]张守智.民国时期总书目[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217.
[11]顾颉刚.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J].孔德旬刊,1925(6).
[1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77.
[1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绪论.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15]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2:127.
[1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M]//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
[17]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二[M]//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
[18]同人.发刊词[J].民俗,1928(1).
[19]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二[M]//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
[20]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四[M]//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
责任编辑:仇海燕
The Academic Pursuit besides the Suspicion about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Gu Jiegang’s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on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Liu Yong-xiang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100,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istorian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utility functions. Gu Jiegang tried to arou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y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He advocated explor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forms of compi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dience in order to enhanc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He followed "the New History" which initiated by Liang Qichao on codification idea, such as writing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history of monarchy" to "the history of people", carrying forward the good tradition of compiling the history collectively, and regarding the special history as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Gu Jiegang’s academic pursuit besides the suspicion about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not only reflected the new upsurge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fter the national history rewritten movemen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ut also reminded peop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new historical textual study.
Key words:Gu Jiegang,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Popular History,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New History
作者简介:刘永祥(1984-),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9AZS001);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S001)。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2-0149-04
收稿日期:2015-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