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矛盾中前行的现当代东方艺术文化
2016-03-15高永
高永
20世纪已经过去十余年,无论是对于西方,还是对于东方而言,过去的那个世纪都是一个复杂的时代。那是一个成就辉煌的世纪,那也是一个饱经浩劫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纪,那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21世纪又将如何?两极格局被多极格局取代,经济全球化已成大势所趋,东西方文化不断融合,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感觉: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纪,将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艺术世界也必将迎来又一个春天。但事实真的会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吗?
面对西方:融合还是排斥

始于近代的东西方大规模的文化冲突,在20世纪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这种冲突不只体现在军事、经济与政治诸方面,也鲜明地体现在艺术世界中。西方现代艺术的传入对东方原有的艺术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对东方而言,这绝不是一个简单地接受冲击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选择过程。其间不乏交流与融合,也因此产生了一大批为东西方都广泛接受的艺术大师和艺术珍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泰戈尔,这位深浸于印度传统文化中的大师,其创作本身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其时的东方文学已然成为“世界的文学”。此外,泰戈尔也是印度现代艺术的推动者。他自创国际大学,开设美术学院,并身体力行地进行美术创作。泰戈尔的绘画创作,强调韵律、平衡与放纵。他那被艺术史家称作“无意识的自动绘画”,不以技艺抑制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现代主义的绘画原则。“他们认为诗人(泰戈尔)以感觉的丰富弥补了训练的缺乏,而过分强调训练会妨碍艺术表现的纯度。”泰戈尔绘画风格的形成,与其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除与弗洛伊德有过交集,并受到其心理学的影响外,早在1917年,泰戈尔可能就注意过《现代评论》上发表的短评《自动的绘画》;大概也留意过1922年在加尔各答举办的包豪斯现代艺术展览。
东南亚艺术的情况同样如此。既被视作印度尼西亚画家,又被视为新加坡画家的李曼峰,在东南亚现代画坛,是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他的成功得益于将“互相融合的东西方元素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硬板油画作品,利用西方的透视技巧和东方的叙事美学,去描绘东南亚的美景”。而其在材料使用方面,更是大胆创新,舍弃精纤维画布,改用平滑的硬木板,“硬木板保留其深褐原木色,形似摊开的中国画轴”,这就又突显了他作为东南亚华人的艺术特性。
与冲击相适应的不是只有接受与融合,同时也会有排斥与变异。对西方世界而言也是新鲜事物的现代主义艺术,在东方世界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文化壁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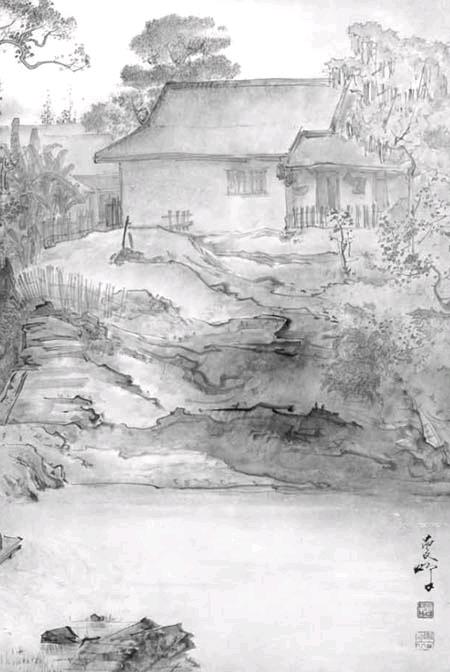
以中国为例:当现代主义撕裂了传统的大幕,给文学艺术世界注入一股新风,并最终成为席卷世界的艺术风暴时,刚刚将一只脚跨进现代大门的中国文学艺术界,却更多地接受了在西方已经成为“过去式”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产生了一大批受西方传统风格影响的作品,且有意无意间排斥新兴的现代主义风格。这与当时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现状的判断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看来,中国仍是一个前现代社会,需要的是传统文学艺术,以适应启蒙的需要。虽然“西方现代主义的基本立场之一就是把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对立起来,作品的目的不在于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经由艺术上的独特形式来‘打击庸俗的现实,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这个口号的背后,也有一种反击现实主义的意义。”但正如李欧梵指出的那样,这种现代主义的艺术却无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中国站住脚,其原因就是在当时很多知识人士(特别是左翼文人)看来,这种现代主义有一种躲进象牙塔的倾向,而中国的那个时代更需要的是执着于现实。虽然包括鲁迅在内,私底下对现代主义艺术并不排斥。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排斥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同时,这也正说明,东方各国(包括中国)开始走向了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对待西方的态度由原来更多地表现为被动接受开始转向主动选择。这是那个启蒙时代——吸收与排斥交错的时代——的必然选择。
审视自身:民族还是世界
当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已成为一句流行语,但事实上,民族的并不必然意味着就是世界的,即使是引起了“别国的注意”,也不等同于拥有了世界价值。现代东方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为此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

不可否认,20世纪是一个东西方艺术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但也不可否认,文化,包括艺术的融合远没有经济的全球化那样明显和容易。反倒是艺术文化的民族性运动时有爆发,冲击着主张文化全球化的“国际主义者们”的神经。20世纪80年代,韩国爆发的“民族艺术运动”,是伴随着其对民族文化的重新审视发生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其文化政策视韩国传统文化为封建、保守、落后的文化,视其民族艺术和民间艺术为落后的、愚昧的艺术形态。其后,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历届政府主推韩国经济的现代化,与之相适应,也主张文化的西方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并且“把韩国的传统文化贬得一文不值,把传统文化视为现代化的一个很大障碍”。但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韩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本民族的历史,重新思考本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试图找到属于本民族的艺术文化。于是他们开始挖掘民间的传统艺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开始意识到艺术是民众的,而不是官方的;艺术与政治、经济共同构成一个文化整体,而不是独立于生活与历史之外的存在。
但问题似乎永远没有那么简单。民族主义的兴起,艺术民族性的自觉,并不能改变东方艺术必须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事实上,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文化艺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正反映了东方兴起的民族主义艺术文化运动本身的偏颇——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就是西方化,国际化也并不意味着以丧失民族性为代价。这并不是一道单项选择题。也许万隆画派的艺术理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一问题。
万隆画派的画家们大都拥有欧洲教育背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这些“积极地拥抱西方现代主义”的画家们,并没有失去民族之根,虽然他们在1965年印度尼西亚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被人民文化协会攻击为“西方的实验室”“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但其创作的理念即是要“通过西方现代主义去发掘自己的民族身份”,并且认为“印尼的艺术有必要同国际发展挂钩”。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富于建设性,又不失操作性的艺术创作理念。极具影响力的万隆派画家波波·依斯干达就曾向民族主义画家古纳宛等学习绘画技巧,其对民族主义的重视可见一斑。但依斯干达等人追求的却是一种具有普世主义意味的文化艺术理想,正如他们在《文化宣言》中表明的那样:“对艺术家而言,文化就是要使人类生活条件更趋向完美的一场斗争。各文化领域对我们来说都一样重要。所有文化领域都应当依循各自的本质,朝向‘理想文化的目标共同奋斗。”这样的文化艺术追求,保证了艺术创作在民族根基之上具有一种世界维度。
事实上,民族主义没有错,现代化也没错,世界性更没错。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文化相对滞后,文化势能较弱的东方各国而言,在面对西方艺术文化大潮时,其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基本立场?其艺术创作的最终指向又该是什么?答案也许不是唯一的,但有一点确是可以肯定的:无论基本立场是什么,也无论其艺术创作的指向是什么,以民族文化中的癣疮作为吸引国际眼光的手段,这既不是民族的,也不是世界的,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吸引眼球,但其价值充其量也不过是奴性文化的新演绎。只有那些用国际的视野,审视本国艺术文化,并用一种批判的精神对待民族文化者,才能真正将民族推向世界。
21世纪:乐观还是悲观
20世纪留给人们的遗产不只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辉煌灿烂的文学艺术,还有生态的严重破坏、多极格局下的多元冲突、消费时代的物化人群。世纪之交,各种末日预言冲击着东西方各国人民的心灵,这样的末日预言与其说是一种可能的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危机感,一种心灵寓言——人类无时无刻不对前途充满质疑、充满焦虑与恐惧。电影 《2012》的成功也许就在于其充分利用了这种心灵寓言,洞悉了人们内心深处最脆弱的东西。如果说,人类精神史上时有发生的末日恐慌主要还是一种宗教情绪的话,那么人们今天对末日的恐惧,与其说是来自人们对世界终点的忧虑,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当下人类现实处境与精神状态的忧虑。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持续升级,以致枉顾人民利益;不同文化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加剧,以致导致局部战争;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淡漠,弱者向更弱者举起屠刀已屡见不鲜;个体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质疑以至否定,于是身陷于无望的苦海无法自拔,这一切无不向人们昭示:21世纪将是一个暗流涌动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上的东西方两大文化阵营间冲击虽将持续但会弱化,这当然得益于上个世经通过多种渠道的相互冲突与融合,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新的矛盾已经形成。
总体看来,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将从原来的表面冲突走向深层次的冲突,即由原来的经济、政治以至军事冲突走向以信仰或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化冲突。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现实战争的时代,那么21世纪可能就是一个文化战争的时代。与东西方文化冲突相伴生的,还有东方世界内部冲突的突显。不可否认,东方世界内部的各种冲突,与上世纪西方列强在东方种下的祸根不无关系:巴以冲突、印巴冲突、朝核问题、阿富汗战争等等,这些地区无一例外都存在强烈的信仰与意识形态冲突,这也是造成冲突的重要原因。

艺术作为现实的反映,艺术活动作为一种现实活动,在东西方文化冲突走向深层次的21世纪,必将使所有的艺术创作者走向身份探寻之路,实现自我认同。自身与生俱来的文化与艺术标签——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在文化冲突中都失效了。它必须重新整合在冲突与融合中接受下来的艺术与文化元素。选择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分歧也是必然的结果。21世纪的前十几年,再清楚不过地向人们表明,东方艺术文化正在走向民族自觉与国际化相融合之路,但其势能仍无法与西方文化相对抗,更何况西方艺术文化并不是僵死的存在,其在体系内部不断进行的调整,以及对东方艺术文化的吸纳,使其在21世纪不会如有些学者估计的那样,成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注脚。西方中心主义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东方中心主义的开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文化势能低弱的东方各民族,不应只将眼光锁定在西方,东方文化内部的相互吸纳同样重要。东方艺术本身具有西方艺术无法通约的一些特性,这本身正是东方艺术存在的合理性,也是东方艺术内部相互借鉴与吸收的理由。
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带来的不只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还有资源的损耗、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恶化。当前生态问题是全球化问题,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是某一国或某几国的责任,而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共同的责任。生态环境的破坏是迅速的,但恢复的过程却是困难而又漫长的。更重要的是,环境问题的解决,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它关系到人类如何看待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些人主张一种生态文化的价值取向,即致力于建构基于互利思维方式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价值取向,一般认为符合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而与西方文化传统上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相反。事实上,无论是强调天人合一,还是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人的地位都必然是主体性的。人类该如何正确使用这种主体地位,才是问题的关键。
艺术归根到底是人的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必然关注三个维度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21世纪的艺术同样如此。20世纪无疑是一个科技理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当人类试图通过科技手段主宰一切外在之物和自身时,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被单一化了。生态文化的启示价值之一就在于使人们重回一种复杂关系。与之相适应的是艺术的话语方式和表达技术将会更趋于复杂。有学者认为这是21世纪艺术的一个核心单元,即对抗的美学和艺术表现主题方面:“只要有各种形式的对个人的压抑和社会性统治的出现,就会有对抗的美学和艺术表现母题。比如电子社会、消费社会、跨国资本主义、大众媒体和少数国家的帝国化,这些统治性结构至少在21世纪上半期,仍然会以惊人的规模和速度扩展其结构力量和统治范围。这些统治的力点依然在于实体权力和技术宰制,而反抗的艺术渠道依然在于视觉美学和叙事的意识形态,在话语方式和表达技术上会更趋于复杂性。”东方艺术因其在文化上的先天优势——如前文如述——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虽然今天仍无法真正预测这种影响到底能有多大,能在多大程度上击溃在当下仍占优势的西方艺术的进攻。

此外,21世纪必将是一个文化的统一化与文化的碎片化共存的时代。所谓文化的统一化,是指世界文化在冲突继续的同时,也必然走向融合,事实上冲突本身就是一种融合,或者说冲突必然带来融合。但人们必须保持清醒,文化的统一化只是“和而不同”中“和”的部分。各民族国家在强调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使之与本国文化相契合,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世界文化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虽然这些碎片可以组成一个看似统一的世界,但其独立性是不容忽视的。21世纪文化的统一性体现在艺术上,则表现为时空观念的消解——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的艺术都可能在同一部作品中得到展示。就此朱其认为,“21世纪的艺术不应该再有时间的概念,只有各种结构之间的交错、重叠和卡位,结构的转向才是导致变革的一个可能途径。”这当然与后现代的消解冲动有关,事实上,正是因为后现代的这种冲动,也导致了艺术的碎片化,21世纪的艺术必然是拼贴的艺术,碎片的拼贴。这样的艺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观照人性与人生,完全取决于创作者本人的内在精神强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无从判断其艺术价值的大小。特别是当下,电脑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艺术创作被大众化裹挟着,其真正的意义何在,是令人怀疑的。尽管如此,艺术是人类的创造物,东方艺术是东方各民族的创造物,其中的文化意蕴必然会随着人类意识的发展,对其进行不断的解读与阐释,而且那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审美之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