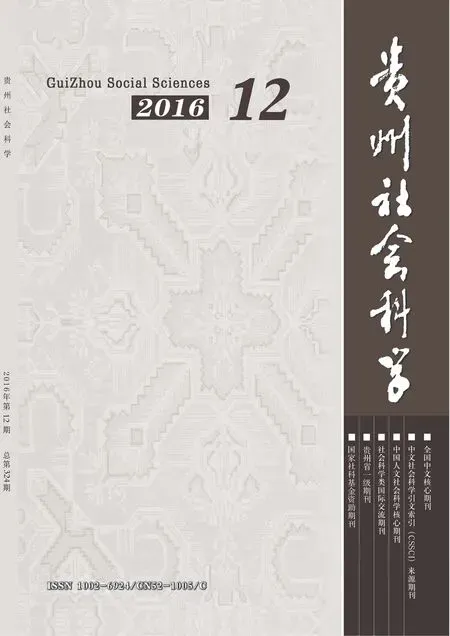美国外交史学的“文化转向”:源起发展、路径领域与学科认同
2016-03-15曲升
曲 升
(1.聊城大学,山东 聊城 252000; 2.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13)
美国外交史学的“文化转向”:源起发展、路径领域与学科认同
曲 升1,2*
(1.聊城大学,山东 聊城 252000; 2.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13)
美国外交史学文化转向的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研究”和新左派史学那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文化转向启动和最初发展的时期,文化根基、跨国文化交流以及全球性意识三类研究取向发展了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文化转向大发展时期,意识形态分析、文化传播领域都在经历着研究的深化和范式的转移。同时,文化人类学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被引入外交史研究。文化转向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激进文化论者与传统主义者关于学科认同的争论,但多元、开放、包容仍将是美国外交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美国外交史学;文化转向;学科认同
一、传统美国外交史学的学科认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外交史学确立了在大学历史学科中相对独立科目的地位。从那时起,随着流派更替,学术兴趣转移,研究领域扩大和方法更新,美国外交史学就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定义自身的过程中。
最初,外交史被定义为“国与国之间通过谈判建立关系的正常行动研究”。以塞缪尔·比米斯为代表的第一代专业美国外交史学家,虽然一开始就把美国外交史研究置于国际视角之下,但利用官方档案、研究外交活动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派和新左派先后兴起,从国际环境和国家内部寻找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成为新的学术关注点,于是“美国外交政策史”取代“美国外交史”,成为通行的提法。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国家间关系研究和外交政策国内根源研究开始结合起来,美国外交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①
1967年“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成立。学会成立过程中,学者们就“外交”、“对外关系”的含义以及专业组织的命名,展开争论,并最终以“对外关系”作为本专业的主要定义。②尽管他们还习惯地称自己为“外交史学家”,但开放、包容和多元化成为学会的发展理念。所以,当1977年学会的旗舰杂志《外交史》创刊时,它这样表述自己的宗旨:“致力于美国国际史和对外关系(研究),宽泛地说,包括大战略、外交,以及与性别、文化、族裔和意识形态相关的重大问题。它从全球和比较的角度考察美国的各种关系;它视野广阔,可满足多学科的兴趣,包括政治科学、国际经济学、美国历史、国家安全研究,以及拉美研究、亚洲研究、非洲研究和欧洲研究等”。③
实际上,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史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科身份认同。根据王立新的总结,美国外交史学传统主要由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两大解释范式主导。现实主义范式包括被称为“民族主义派”的第一代职业外交史学家、战后50年代的“现实主义派”和70年代的“后修正派”。进步主义范式由著名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60年代以威廉·威廉斯代表的“新左派”发扬光大至顶峰。尽管现实主义范式走外向分析的路径,即主要从国际环境因素寻找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进步主义走内向分析的路径,即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动因植根于美国社会之中,但两大传统具有很多共同特征,主要包括:在学科范围上,大致把自己界定在美国国史分支学科,并赋予它很强的政治史色彩和兰克史学风格;在本体论上坚持国家中心论、美国中心论和精英史观;在方法论上,主要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强调外交政策动力中的物质性因素(权力和利益的追求);在认识论上,持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和反映论,坚持档案实证分析的基本分方法,以还原历史、寻求因果关系为目的。④
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这些共同特征,也可视为他们共享的学科认同(特性)。所以,尽管现实主义派和进步主义派在史观上截然对立,他们会为如何评价美国外交的问题论战不止,甚至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却从未对自己的学科特性产生根本分歧。这种局面,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国际化取向,尤其是文化转向的发展,已被完全改观了。目前,传统主义者和激进“文化主义者”就美国外交史学的核心特征、研究路向、研究方法以及认识论等问题,正在进行着针锋相对的论战。如何确认新的学科认同,已成为美国外交史学未来发展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美国外交史学科认同争论的产生,源于学科文化转向及其带来的学科形态巨变。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一文对美国外交史传统和文化转向路径的归纳、对文化转向改造传统史学的分析,清晰而深刻,却未触及当前美国外交史学面临的学科认同问题。本文以王立新的研究为基础,尝试把美国外交史文化转向置于美国国内外广阔的政治、社会和学术背景之下,追溯其渊源,描述其发展轨迹,考察其范畴领域及其引发的学科认同问题。
二、美国外交史学文化转向的源起与发展
美国外交史学文化转向与美国史学文化转向具有共同的史学源头和理论资源。根据詹姆斯·库克和劳伦斯·格里克曼的研究,美国史学“文化转向”并非源于某单一研究领域方法论的发展,而是众多研究领域方法论创新交汇影响的结果,其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史学”,以卡洛琳·威厄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对美国史学文化转向产生重要影响的,是 “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它在英国被称为“文化研究”,在美国称为“美国研究”。⑤“美国研究”与“文化研究”在轴心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上是一致的,均持这样的假设:历史“事件”(events)和历史“情节”(actions)镶嵌于“文化框架”(cultural frameworks)之中,文化界定一切具体的社会运动;文化和意义中隐含着权力关系,不仅言说者的立场,而且宰制性的(dominant)叙述、象征和阐释有权力创造、定位,甚至消灭历史记忆、社会选择和某些人群。⑥
进入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史学成为文化转向的重要源头。库克把某时的劳工史专家赫伯特·古特曼、思想史专家沃伦·萨斯曼、社会史专家那桑·哈金斯、政治史专家劳伦斯·列文、妇女史专家史密斯·罗森堡奉为文化史的五位先驱。⑦不过,外交史学文化转向的源头,却并不在五先驱那里,而在被称为“新左派”旗手的威廉·威廉斯。正如伊雷泽·曼尼拉所言,以威廉斯为代表的“修正派”对美国外交史学的影响“不仅限于对美国外交本质的批判,还在于他们的研究框架和方法”。⑧威廉斯开创的美国外交意识形态分析框架开启了外交史学文化转向之门,对此,笔者曾有专文论列,不复赘述。⑨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威廉斯意识形态分析框架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今在美国外交史学文化转向中具有很大影响的埃米莉·罗森堡和弗兰克·科斯蒂格利奥拉早年均深受威廉斯影响,他们各自的早期文化转向作品《传播美国梦: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扩张,1890至1945》和《棘手的统治:美欧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1919至1933》,都秉承了威廉斯探析美国生活方式扩张的传统,可谓突出文化因素的佳作。⑩意识形态分析是美国外交史学文化转向最早开辟的研究领域或路径,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愈益丰富和深刻,但这一路径一直备受重视,许多重量级学者都是在该路径上实践着文化转向。
美国外交史研究文化转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启动与初步发展,得益于三方面因素的交汇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新事态、国际学术新潮流以及领风气之先思想者的启迪。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以降,美国社会动荡不宁,各种形态的激进运动风起云涌,催生了新思维、新意识,人们对美国历史的看法也为之一新。其中,民权运动引发了对黑人史研究的新兴趣,妇女运动则为妇女史的兴起创造了社会氛围。在此期间,这两个领域的关注点从黑人、妇女遭受压迫转向了“自主”的黑人文化和妇女文化,从而为日后“种族”(race)范畴和“性别”(gender)范畴引入外交史研究铺就了道路。
从国内政治层面看,越南战争的失败、水门事件的发生,打破了美国权力无远弗届、战无不胜的神话和美利坚民族对自己民主制度的自豪感,引起美国社会对政治精英滥用国家权力的怀疑和反感。正如约翰·加迪斯所观察到的,20世纪70年代,即越战前后进入学术界的年轻一代,普遍带有对权力的不信任和忧惧感,在许多院系,权力研究甚至成为“禁区”。于是,转向文化,探寻美国国际失败和国内腐败背后的深层文化根源,成为新一代学者的不二选择。
从国际关系层面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现象、文化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数量和作用日益增加。首先,广泛文化意义上的环境保护和促进人权开始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内容。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之后,防治环境污染和保护野生动物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同时,少数族裔、妇女、儿童、残疾人甚至囚犯等易遭歧视的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问题,也引起国际范围内的讨论和关注。这是卡特政府推出“人权外交”的国际背景。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权威衰落,非政府组织迅速成长,身份认同和文化多元化趋势愈益明显;宗教极端势力兴起,艾滋病传播加速以及毒品走私猖獗等广义文化现象,都与传统外交史概念中的政府间政治、国家战略和经济事务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把这些新发展纳入思考,就不可能对70年代的美国外交展开讨论”。
20世纪70年代也是欧美学术风潮大变,后现代主义席卷艺术、建筑、语言、文学、社会学等领域,并开始侵袭史学的年代。后现代主义挑战了自启蒙时代确立起来的对理性、科学、进步的信仰,表现在历史编纂学上,就是研究重点的转移:从精英转移到普通人;从巨大的非个人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这些研究所包含的新的研究战略,是“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也注意到,这一时期存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中的对与某种社会“科学”的观念相联系的决定论的反叛现象,指出这种反叛“是在文化的旗帜下发生的”。西方史学的文化转向就此发生。
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权力和利益为思考重心的传统美国外交史学,已不能适应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学术的新趋势。在其他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其他分支纷纷进行“文化转向”的反衬下,外交史学日益显得“落伍”,并因之而陷入“危机”之中。查尔斯·梅尔于1980年发表了全面检视国际关系史学科状况的《停顿不前:国际关系史学》一文,指出美国外交史研究及其著作已沦为大学研究和公众阅读的“继子”,缺乏公认的大师,离“学术前沿”渐行渐远。他认为,美国外交史学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热情,研究方法陈旧不堪,“狭窄的研究领域,狭隘的视角,以及对他国语言和资料的陌生仍在束缚着大量的作品”。美国外交史学界对梅尔的“学科诊断书”虽然反应不一,附和者有之,反驳者亦有之,但对于他开出的突破旧研究框架,尝试理论创新的“大处方”,却鲜有异议。在把梅尔的议程具体化和实践化的过程中,入江昭提出的“文化取向”(cultural approach)因应时代变化,脱颖而出,渐成主流。
1979年入江昭在《外交史》杂志发表《文化与权力:作为文化间关系的国际关系》一文,率先对外交史研究的文化取向进行“方法论陈述”。文章断言,国家是一个文化系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文化体系间的互动”,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必须思考“既定文化系统内部的本质特征,并观察它们是如何影响了彼此间的互动”。换言之,应从文化的角度而非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去理解各民族间的互相交融和对立。文章明确提出了把文化维度应用于美国外交史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设想,这在美国外交史学界还是第一次,吹响了美国外交史学文化转向的号角。
在入江昭的呼吁和启发下,20世纪70年代后期及整个80年代成为美国外交史学文化转向启动并初步发展的时期,文化取向的作品明显增多。1990年,入江昭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扫描和检阅,从中总结出外交史文化转向的三种类别。第一类为“文化根基取向”(cultural foundations approach),探究一国对外行为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之根基。第二类取向研究“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包括非正式与正式(informal and formal)或私人与公共的(private and public)两个层次的四个领域:(1)美国人的海外活动;(2)美国的商品、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其他国家社会中的传播及其影响;(3)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包括互派留学生、邀请专家讲学、举办学术会议、艺术展览和文艺演出以及旅游观光活动;(4)由官方推动的、作为其外交努力一部分的文化交流。第三类取向研究“全球性意识”,以超越国家边界或超越民族主义的世界性关切为主题,包括国际和平运动、促进人权、环境保护等。
从入江昭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取向外交史著作的总结中,不难发现这时期的文化转向具备以下特点:第一,作品数量有限,尚未撼动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两大传统的统治地位。第二,跨国层面的“文化交流”和“全球性意识”两个领域的研究还很薄弱,尚未和国际化转向实现对接融合。第三,即便在有较大进展的“文化根基”领域,也还存在着方法论缺陷,“没能深化外交史的概念框架”。上述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时期学者们对“文化”概念的狭隘理解。他们或者从传统意义出发,把文化视为人类活动的产物,简约化为学术性和艺术性产品,主要指高雅文化,同时也包括所谓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或者把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换言之,此时美国外交史学者的文化概念还不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更非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当文化人类学和后现代理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在美国学术界孕育、引入和发展时,许多其时从事文化转向的研究人员在学术上尚处于成长阶段,他们需要时间对新理论加以熟悉和吸收,而后才可能将之运用到美国外交史研究中。
美国外交史学文化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这首先得益于冷战终结的客观现实。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对抗,是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在外交史学各领风骚一时的现实依据。然而,冷战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终结,现有的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因无法对之进行有效预测和解释而备受质疑。学术界期盼新理论、新解释的出现。
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竞争在国家战略考虑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经济、文化竞争,尤其是文化竞争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情形下,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说,指出:在世界变革的情况下,“所有国家,包括美国,要学会通过新的权力资源来实现其目标”,而这种新的权力就是“软权力”;“软权力的新形式正在出现,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的”;软权力常与“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相联系”。
冷战终结的另一后果,是原先被掩盖的族裔冲突的和文化冲突,带着触目惊心的血腥和暴力爆发出来。发生在巴尔干半岛、车臣和阿塞拜疆等地的种族战争,使西方学术界认识到,文化在搅动世界局势、牵动人的神经方面的能量,绝不亚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一时间成为国际学术热点。亨氏认为,未来的冲突将发生在世界上的几个主要文明之间,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至于何谓“文明”,亨氏基本上把它等同于“文化”:“文明是一个文化的实体”,“是民族之间的最高文化组合及最广泛层次的文化认同”。
如果说政治学界和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文化热”为美国外交史学文化转向提供了外部示范和刺激的话,那么,外交史学内部,尤其是《外交史》杂志则为外交史学文化转向提供了难得的“实验室”和“清谈馆”,从而极大地引导和推动了冷战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交史》杂志对新兴文化转向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除继续零散刊发对外交史进行文化分析的文章外,更精心推出了一系列的“专题讨论”、“圆桌会”和“论坛”,集中刊发同一主题的系列研究论文和相关评论。这些专题讨论、圆桌会和论坛涉及了社会性别、社会记忆、宗教、种族等领域以及文化帝国主义、全球美国化等问题。
文化取向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盛,不仅表现在文化取向论文在《外交史》杂志上的爆炸式增长,还表现在相关著作的大量出版。这些文化取向著述,涵盖了美国外交史的全时段和更大问题,就连一向为现实主义研究范式所把持的冷战史研究也不例外。2001年,罗伯特·格里菲思发表文章,明确地把冷战研究的这种变化称为“文化转向”。“文化转向”一词随即被其他一些学者接受,并把它泛用到整个美国外交史学,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取向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兴盛景象。文化转向的实践者们还开始用“文化主义者”(culturalist)称呼自己,以便把自己同那些坚持传统研究的人区别开来,彰显自己的不同。
三、外交史学文化转向的路径、领域和范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外交史学文化主义者对文化概念理解的多元化和深化,更多研究路径(approach)发展了出来,王立新把它们归纳为“三条路径六个方面”。入江昭曾把文化定义为“记忆、意识形态、情感、生活方式、学术和艺术作品以及其它符号象征的制造和传播”。据此,本文将把文化转向分解为四个不同的范畴和研究主题,以便进一步考察之:(1)意识形态分析,研究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大国关系的关系;(2)一般意义范畴文化,研究美国文化的海外传播;(3)文化人类学范畴文化,研究国家认同、种族、性别和阶级等信念、态度如何形塑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权力的运用;(4)后现代主义范畴文化,为文化转向带来了更多的理论视角。
总体上看,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文化转向不仅在意识形态分析路径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分析领域得到了深化和拓展,出现了新的动向,而且更具有创新意义的,是文化人类学和后现代理论、概念、范畴的引入和运用,形成了对传统外交史学的全面挑战。由于后现代理论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运用,笔者已有专文论列,在此主要介绍前三个领域范畴的情况。
(一)意识形态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是美国外交史学文化转向中最早开拓出来的路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路径经历了进一步的深化和转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廉斯的意识形态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其基本假设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维护权力关系的工具,是对现实的颠倒性反映;它模糊甚至扭曲了国家利益认知,导致了美国外交的悲剧性后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外交史学者对文化人类学的理解和运用的娴熟,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逐渐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格尔茨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套完整的、连贯的象征体系、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认为它非但没有模糊社会关系,反而构成和表达着社会现实。所以,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解世界所需的象征体系,这种象征体系在危机来临和快速变化的时代,具有重大意义。
韩德1987年《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标志着意识形态范畴上述转变的开始。韩德认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主要有三种观念构成——国家伟大的希望、种族等级观念和对社会革命的恐惧;这种意识形态把推进国内外自由的宿命、使命感与美国为进步代理人的信念编织在一起,深刻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威廉斯一样,韩德也发现意识形态把美国人引向了歧路。不同之处是,韩德在承认意识形态给美国外交带来麻烦的同时,认为意识形态并非僵固不化,而是能够调整自身以适应现实的变化,这种变化为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创造了可能。
如果说韩德的著作代表了一种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综合分析之尝试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则往往抓住美国意识形态某一核心观念,或聚焦于某一时段,或统揽全局,对美国外交史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罗伯特·史密斯的《维护共和》以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为中心,考察了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早期外交的影响。托尼·史密斯《美国使命》把考察时段限定在20世纪,提出了“自由民主国际主义”是20世纪美国意识形态“发明”的假设,认为正是这一意识形态指导了美国输出民主以平息动乱和冲突的外交活动。安德斯·斯蒂芬森则以“天定命运”意识形态为线索,以“美国例外论”这一神授使命观为中心,通盘分析了开国至冷战终结的美国外交史。
美国外交史意识形态分析的进展,也许最集中地体现在冷战史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冷战史新研究”学术潮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和重新认识。在这股潮流中,两位卓越的现实派史学家、冷战史学领军人约翰·加迪斯和麦尔文·莱夫勒都开始把意识形态纳入到自己的分析框架中,探讨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考量在决策者身上的交叉汇集及其对外交决策和大国关系的影响。加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认为,冷战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制度层面的斗争。在《冷战:一部新的历史》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布尔什维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人对集权体制的不信任感之间的对立,是冷战的根源。与加迪斯把苏联描述为罪恶之源不同,莱夫勒则对美国冷战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深度审查。他指出,对苏联主宰世界的地缘政治担忧影响了华盛顿“优势战略”的形成,进而导致了一种独特冷战意识形态的泛起。这种冷战意识形态涵盖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凝聚性意识形态以及自由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造成了一种判断什么是“与美国人心目中的好社会相容的(外交战略制定)外部环境”。在《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一书中,莱夫勒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在美苏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批判性地分析了意识形态对国家安全和冷战动力的影响。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2005年度主席演说词中,莱夫勒甚至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即“价值和观念的话语”去分析“九一一”后小布什政府反恐战略在美国外交史上的连续性。有学者由此而称莱夫勒“开始了语言学转向”。
(二)文化传播领域的范式变迁。20世纪80年代跨国文化交流研究领域还十分薄弱,90年代以来,该领域则呈现出兴旺繁盛和快速变化的局面。从一般的角度理解,文化即一个民族(国家)特有的价值、观念及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机构、制度和人群。文化传播领域把文化视为“研究对象”而非分析工具,探究美国的文化观念、文化价值、文化产品在地区间、盟友间和敌国间的传播。
文化传播领域横跨了政府、民间或正式、非正式两个层面。正式层面的主要课题是美国的“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文化外交研究视文化为外交政策工具,认为文化外交是一国政府所从事的,有着明确国家政治目的对外文化交流行为。弗兰克·宁科维奇在清晰界定文化外交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文化外交政策在1938—1950年间的源起和发展,开创了文化外交研究的先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期间的美国文化外交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沃尔特·希克森和伊丽莎白·C. 霍夫曼揭示了二战末期至60年代,美国政府利用宣传、和平队等政策工具对苏东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文化渗透战略及活动。肯尼斯·奥斯古德、迈克尔·卡伦恩等则研究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心理战、“原子弹用于和平计划”以及文教交流政策,揭示了这些政策活动背后操纵舆论、争取人心的隐蔽目的。埃尔文·华尔、理查德·奎赛尔、克里斯汀·罗斯研究了美国与法国之间的文化关系。联邦德国—中欧国家与美国之间的文化碰撞也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一些雄心勃勃的著作甚至对美国与整个欧洲间的文化交流进行了广泛的考察。
在非正式领域,学者们则广泛研究了人员、商品、观念在美国与他国之间的双向流动,尤其是美国的海外慈善事业、旅游观光、海外驻兵、教育交流,以及报刊、广播、电影、体育等大众娱乐的海外文化活动及其影响,备受重视,佳作云集。
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目前有两大动向,引人注目:研究范式正在发生转变,即从“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范式向“文化传播”(culturaltransfer)范式的转变;与国际化潮流实现了对接融合,日益突破传统外交史学的国家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甚至走向了跨国史。
“文化帝国主义”范式基于一国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产品及生活方式加在他国身上的前提假设,采取单向度的研究思路,仅仅关注文化输出端的意图、方式、手段,而把接收端视为被动无助的受害者。美国文化外交研究大致是在这一范式内展开的。“文化帝国主义”范式具有明显的批判意识;“文化传播”范式则力图淡化之,主张基于双边甚至全球的立场,打破主动/被动、主宰者/受害者的简单化两分法,在关注文化输出端的同时,更加关注文化接收端的反应,强调接受者对美国文化的抵制、选择、改造和转型。文化传播范畴已经突破了传统外交史研究的美国中心论,具有明显的国际史色彩。
实现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是与文化转向几乎同时出现的一种发展趋势,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过倡议、阐发和实践,其中入江昭提出的“文化国际主义”主张具有代表性,其根本思路就是把国际史视野与文化分析结合起来。最初,国际化和文化转向的结合,尚未突破国家中心论、美国中心论的束缚,这反映在对“美国化”(Americanization)课题的研究上。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美国外交史学界进一步探索全球化对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影响和意义,提出了“全球史”(global history)、“跨国史”和“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的研究框架和议程,呼吁关注那些跨越国家疆域的,与权力有较少关系的超国家的,非国家的力量、现象和主题。这样,文化转向连同国际化一道,深刻改变了美国外交史学的形态,“传统风格的美国外交史正在转变成美国全球史、美国跨国家史和跨文化史”。
(三)文化人类学范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文化概念得到美国外交史学家的青睐和广泛运用。格尔茨把文化定义为“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弗兰克·科斯蒂格利奥拉和托马斯·帕特森把文化解释为“由社会中(逐渐跨越各社会界线)的人们所制造、交换、质疑和变更的共同的意义和价值”。也可以说,文化是埋藏于日常生活中的象征及意义体系,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重要的是,文化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意义之网”这种宽泛的文化理解,而是在实践中进一步解构“意义之网”,抽取其“网丝儿”,把“文化”具体化,于是发展出许多新范畴,开拓出许多新领域。这些新范畴、新领域主要包括语言(language)、情绪(emotion)、种族、性别、宗教(religion)、记忆(memory)等。每一个领域内都云集着一批新锐学者,他们孜孜不倦,辛勤耕耘,极大推动了美国外交史学的转型。例如,杰拉德·霍恩在种族范畴,克里斯汀·霍根森在性别范畴,安德鲁·普雷斯顿、大卫·齐兹马在宗教范畴,皆能推陈出新,成绩斐然,卓然成家。而埃米莉·罗森堡、安德鲁·拉特尔、弗兰克·科斯蒂格利奥拉等人,则自由穿梭于种族、性别、宗教、情感、语言等范畴领域,展示了广泛的学术兴趣和对理论工具的熟稔。
受文化人类学影响,“认同”(identity)成为外交史学家手中的便利工具,一切文化范畴都成了“认同”——“种族”是认同,“性别”是认同,“阶级”是认同,不过,“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他们研究和关注的重点。美国国家认同研究一般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强调国家认同重塑中对邪恶“他者”形象的利用;一条思路考察正面国家使命的肯定在认同重塑中的作用。
在这些研究领域内,学者们把美国人的态度、想象、价值观和偏见与外交政策实践、国家权力运用直接联系起来,取得了累累硕果,揭示了美国对外关系复杂深刻的国内文化背景。以种族范畴为例,学者们开拓出了大致三个方面的研究课题:非洲裔美国人争取种族平权的斗争与美国对外政策间的关系;“白人至上”观念在美国外交史中的建构及其影响;种族因素与美国对外战争和殖民主义的关系。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为重视精英决策、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的传统外交史学所忽视的。
四、学科认同的争论与前瞻
伊雷兹·曼尼拉在最新总结美国外交史学科现状的文章中写道,文化转向带来“(外交史学)领域快速演变的同时,也使得该领域内外的史学家难以确定学科的范围和内容(contours and content)。近年来,学术会议大厅和学术杂志版面,已经见证了大量的、通常是十分激烈的围绕此一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关于学科认同(特性)的争论贯穿于美国外交史学文化转向的全过程,始终未息。这场争论,主要在持后现代主义激进立场的文化论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展开,涉及了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
本体论层面围绕外交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围问题展开。激进文化主义者主张,外交史研究的真正对象,应该是社会而非国家,是文化关系而非权力政治,是话语而非行动。因为,根据后现代理论,传统外交史视域中的国际体系、民族国家、国家利益、安全威胁、外交政策等等,都是文化建构物,文化作为外交史研究的起点乃理所当然。他们认为外交史研究领域是“一片辽阔而空旷的平原,没有既定的边界”,不应该沿袭方法论上的陈规旧习;强调美国外交史家最吸引人们眼球的,不在于他们懂得如何去研究权力和国家,而在于善于把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纳入到自己的学科领域内,研究“公民及其与美国边界之外世界的所有接触”;号召史学家在文化史研究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进一步破除美国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简言之,他们主张把外交史更多地推向社会史、文化史和国际史。
传统主义者对激进文化论者的上述论调,抱持怀疑、“反感”甚至“拒斥”的态度。他们批评文化转向的“文化”概念过于宽泛,缺乏清晰度和严谨性,存在着泛文化论的倾向,回避甚至无力回答国际事务中关键的权力问题。他们担忧文化转向过了头、偏了向,正在使美国外交史学丧失学科特性,“缩小与历史行业其他部分的距离”,放弃了一些使之与众不同却对整个社会具有意义的东西”。他们提醒外交史学家,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吸引力,来自它明确地将这样一些重大而深远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研究领域:战争与和平、美国在世界上应该代表什么、争取什么以及实现什么。他们认为“维持国家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对于高质量的研究乃绝对必要”;把“国际舞台上(美国)权力的研究置于优先地位”,是美国外交史区别于其他美国史学科的“鲜明特征”。还有学者在考察了文化转向的利弊后,建议国际史进行“外交史回归”(diplomatic twitch),更多关注国家、权力、战争、和平以及外交决策等传统研究对象和主题。
在认识论—方法论层面,传统主义者坚守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立场,指责文化转向陷入了文化决定论,把语言、修辞、话语绝对化,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忽视了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模糊了对因果关系的探讨。激进文化论者则在质疑现代知识形式,解构人的理性的基础上,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史料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文本,史料并不是纯客观的,实际上掺杂着记录者的主观因素,并非对历史的真实反映;作为思想和表达工具的语言也并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现实的制造者,但语言(符号)是“延异”的,没有确定的含义。因此,传统史学信奉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及其对历史因果律的追求,都是虚幻的。激进文化论者欣赏诠释“深描”、话语分析等新方法,认为它们“关注的不是标示‘原因’和‘结果’,而是凸显机制和假设(assumptions)之间表面上不存在的具有符号意义的相互关系,其目的是理解‘知识’构成和那些被想当然地认为是‘自然’的事物的边界”。
这场学科认同(特性)争论带有某种争夺“正统性”的色彩,争论双方均声称自己的研究方式是最好的,而对方则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应当取消的。这种刻意贬低对方的态度,在激进文化论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主张从后殖民视角研究美国帝国主义史的埃玛·卡普兰认为,传统范式完全割裂了文化研究与对外关系研究,并把文化因素和文化分析排除在了美国帝国主义历史研究之外。宁科维奇则干脆说:“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思路都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观念,是诞生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历史时期、繁荣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历史背景之下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方式现在已是行将就木了。”难怪托马斯·泽勒感叹:自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成立起就在困扰着美国外交史学家的学科认同问题,而今显得尤为迫切了!
外交史学内部这种排他性的“正统”之争并非特例,而是整个美国史学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学科转型后的普遍现象,但却与“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倡导的多元、开放、包容的精神相悖,更与外交史学科演变的基本趋势背道而驰。牛可指出,由“趋同性”学科变为“趋异性”学科,由“硬学科”变为“软学科”,由“范式型”学科向“非范式型”学科转变,由汇聚的、紧密结合的学科变为发散性的、松散结合的学科,由“学术部落”转变为自由联合、自由进出的学术群落,是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学科演变的基本趋势。由是观之,美国外交史学界在面对学科认同重塑这一问题时,需要的是平和心态——传统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均应多一些开放、少一些封闭,多一些宽容,少一些狭隘,以平和的心态,妥善处理新学旧知间的关系。学界常有新思潮,乃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传统主义者须坦然接受。激进文化主义者也应该懂得新理论要建立在旧理论基础之上,概念的延续是理性推理之根本的道理。他们应该倾听约翰·加迪斯的建议:“任何未来的观念只能来自对以往某种观念的认知,否则的话……没有语言能表达它们。”如此才能营造旧学新知相互竞争,相互借鉴,融会贯通的正常学术生态。
总之,面对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浪潮和学术研究的日益多元化,美国外交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以一种更加客观持平的态度,对旧学新知进行批判、调和,将“作品和观点放入更大的故事框架”,“对美国和全球的历史提供新鲜的综合而全面的描述”。
注 释:
① D. C Watt, Alan Palmer, “What is Diplomatic History,” History Today, vol. 35, no. 7(July 1985), pp. 34, 39.
② David L. Anderson, “SHAFR Fortieth Anniversary Forum,”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1, no. 3(Jun. 2007), p. 435.
③ Diplomatic History, http://shafr.org/publications/diplomatic-history
⑤ James W. Cook, Lawrence B. Glickman, and Michael O’Malley eds., The Cultural Turn in U.S.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p. 5-6; 21-22; 32-33.
⑥ Susan Jeffords, “Commentary: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U.S.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8, no. 1(Winter 1994), p. 92.
⑦ James W. Cook etc, The Cultural Turn in U.S.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p. 16-19.
⑧ Erez Manela,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in Eric Foner and Lisa NcGirr eds., American History Now,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04.
⑨ 曲升:《传统美国外交史学与文化转向》,《聊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⑩ Emily S. Rosenberg,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 1890-1945, Hill and Wang, 1982; Frank Costigliola, Awkward Dominio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Europe, 1919-1933,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责任编辑:翟 宇]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转型研究”(13YJA77002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外交史学史”(13BSS026)。
曲升,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教授,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校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外交史。
K03
A
1002-6924(2016)12-075-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