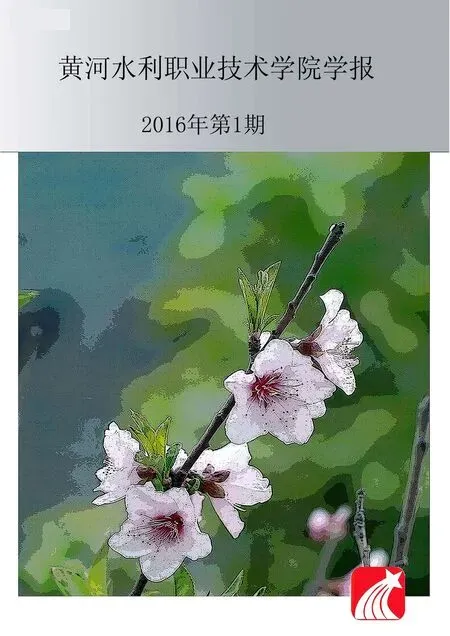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性解释
2016-03-15孙浩文
孙浩文
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性解释
孙浩文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我国学者在对交通肇事“逃逸”问题进行解释时,主要采取了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方法。无论哪种方法都有其天然的缺陷,产生了很多让人难以接受的结论。对“逃逸”应该从它的行为结构入手进行解释,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实属交通肇事罪与遗弃罪的结合犯,这样才能有效解释立法者对其升格法定刑的依据。
交通肇事逃逸;逃避法律追究说;逃避救助义务说;规范目的解释;行为性
0 引言
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以来,关于交通肇事逃逸的问题便成了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关于逃逸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十分丰富,但学者的这种热情,却并没有得到立法上的任何回应。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各种疑难问题也不断出现,主要集中在“逃逸规定的规范保护目的”和“逃逸的行为结构”两方面。最近,有学者通过质疑其规范目的解释的正当性,并试图以“逃逸”的行为性来解释其行为结构,又为上述争论增添了新的话题。如果想在纷杂的争论中找到头绪,使交通肇事罪中关于逃逸的难题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最重要的便是找到加重其法定刑的根据。如果无法合理解释这种根据,对逃逸问题的研究也就无法开展。
我国《刑法》第133条中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将“逃逸”与“其他特别恶劣情节”放在一起,作为交通肇事罪中升格法定刑的条件,并且以“逃逸致死”为由,再次升格法定刑,这又造成了解释上的混乱。我们都知道“交通肇事行为”和事后的“逃逸”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为,在“交通肇事行为”已经构成基本犯罪的前提下,缘何用事后的“逃逸”行为影响前一个行为的刑法评价,单单是因为“逃逸”行为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吗?然而,根据责任主义与合并主义的原理,法定刑升格的根据只能是责任的加重,而不是预防必要性的增大[1]。因此,单纯的主观恶性是不足以作为升格法定刑的依据的。那么,在“逃逸”行为的背后,究竟体现了立法者怎样的初衷?笔者试通过对各种理论深入地挖掘和利弊分析,以明确我国《刑法》第133条中关于“逃逸”概念的内涵,并期对今后的司法实践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1 关于“逃逸”理论学说的评析
“逃逸”是弄清交通肇事罪的关键。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对“逃逸”的解释五花八门,而目前大多数的学者都主张采取目的解释的方法对“逃逸”进行分析。通过这种解释方法,大致得到了“逃避法律追究说”、“逃避救助义务说”、综合说和择一说几种理论学说。其中综合说和择一说并不是主流的观点,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逃避救助义务说”和“逃避法律追究说”的对立上。
1.1“逃避法律追究说”理论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的《解释》中将“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行为界定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这种解释从行为人的主观条件着手,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主体进行了限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解释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响应,例如在“周立杰交通肇事”案中,裁判理由就指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原因有很多种,有的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有的则是因为担心周围群众的殴打而采取的临时躲避行为,还有可能是在前往投案的途中等等,不能一概而论,之所以要把“逃逸”的主观目的限定为逃避法律追究,就是要把上述这些情形加以区分。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解释》带有明显的限缩性,似乎也符合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然而“逃避法律追究说”仍然为大多数学者所诟病。首先,在犯罪后基于对法律追究的逃避而逃跑的行为是人之常情,是没有期待可能性的。也正是因为这样,自首成为我国《刑法》总则中的法定从宽情节。张明楷教授曾指出:“只要刑法分则没有特别规定,刑法总则的规定就必须适用于分则。所以,刑法总则规定的自首制度,应当适用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每一种犯罪。《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并没有排除自首制度的适用”[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刑法》所要求的“不逃逸”与自首之间即使有所竞合,也必然不会完全等同,除却与自首可能竞合的部分之外,这种“不逃逸”必然蕴含着其他的义务。其次,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来说,这种解释方法既有可能不适当地缩小“逃逸”的范围,也极有可能不适当地扩大了“逃逸”的范围。前者比如肇事者在肇事行为发生之后,在案发地没有逃逸,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救助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肇事者的不作为提升了对被害人造成伤亡的危险,体现了他较高的主观恶性。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这种情形适用第二档的法定刑可以说是妥当的。后者肇事者在肇事行为发生之后,及时将被害人送往医院,使其在得到救助之后才逃跑的情形。鉴于其主观恶性以及救助行为,若对其适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加重法定刑,是极为不妥当的。正是因为上述两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频发,使得学者们质疑“逃避法律追究说”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逃避法律追究说”强调的是公诉机关对肇事者的追诉权,却忽略了对被害人生命健康权的重点保护。在救助被害人还是保障公诉权两者之间做选择的时候,持“逃避法律追究说”的学者在利益衡量之下,选择了保障公诉机关的追诉权,这种出发点本身就是不符合常理的。在刑法以保障人权为宗旨的前提下,对被害人的救助应当比公诉机关的追诉权重要得多。
1.2“逃避救助义务说”理论
在交通肇事案件发生后,被害人处于弱势地位,必须依赖他人的救助,而肇事者由于肇事这种先行行为,被认为对受害者有保证人的地位。有学者指出,刑法之所以单单在交通肇事罪中把逃逸情节作为加重法定刑的依据,是因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通常有着需要被救助的被害者,由于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包括交通肇事行为及其他行为)使他人的生命健康处在十分危险的处境,因此便产生了救助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履行这一义务,则必然可以成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换言之,应当以不救助被害人的行为(不作为)为核心界定交通肇事的“逃逸”行为。笔者亦认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有责任和义务救助伤者,而且这已经在社会上达成了共识。“法律应该以追求适合事理的规整为目标,在有存疑时亦应如此假定”[3]。我们不难发现,关于“交通肇事逃逸”的规定,恰恰是这一事理在刑法领域的投射。因此,即使“逃逸”规范目的的外延无法得到确定,但其核心内涵早已显现:肇事者具有救助被害人的义务,使交通事故中被害人受到的损害降到最低。
然而,“逃避救助义务说”也受到了理论界的诸多批评。第一,救助义务只发生在有救助可能的情况下,若在某些不存在救助可能的情形(例如被害人当场死亡或者只有重大的财产损失),是无法定义“逃逸”行为的。第二,救助被害人义务无法涵盖肇事者的全部义务。在张明楷教授的《刑法学》教科书中就提到:“能否认为,刑法将逃逸规定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另一个根据是,行为人在造成该交通事故后因为高度紧张,其驾驶机动车逃离的行为具有造成新的交通事故的危险性。果真如此,则逃逸既包括不救助被害人的不作为,也包括驾驶机动车逃离的作为”[4]。还有学者引用《交通安全法》,通过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相结合的方式,把肇事者的义务确定为:救助被害者的义务、为肇事现场设置警示标志或及时报警的义务、消极不逃跑的义务,由此认为“逃避救助义务说”是不全面且无法进行合理解释的。
2 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性解释路径
2.1对交通肇事“逃逸”文义解释方法的质疑
毋庸置疑,由于立法语言的概括性和简约性,法律需要被解释才能运用到个案当中。正如加达默尔所言:“如果我们每个人对事物都有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因此,解释方法的选择就变得尤为重要。在我国刑法理论界,有学者对解释方法的排列给出了这样的顺序“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而且这种解释方法的选择顺序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适用。因此黄伟明教授指出:在关于交通肇事“逃逸”问题的解释上,文义解释的方法被完全舍弃掉了,现存的各种解释跨越了文义解释而直接选用目的解释或其他解释方法,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做法[5]。然而笔者认为,要证明刑法解释方法本身的正当性,就必须要满足正确解释法律的要求,同时还要兼顾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妥当性。我们在解释法律条文时,确实应当首先考虑语词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然而,“首先考虑”并不代表着“必然采用”,当它的字面含义无法妥当表达立法者的目的时,只能舍弃字面含义,以其他解释方法对语词进行理解和解释。
2.2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规范目的解释方法的质疑
诚然,在研究交通肇事“逃逸”问题时,通过运用规范目的的解释方法,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但对这种解释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不管是从目的主体的选择上来看,还是从目的内容的论述上来看,规范目的解释方法都存在着无法解决的两极化趋势。在法解释学理论中,向来就有客观解释和主观解释两种不同的方法。而在涉及规范目的解释时,主观解释论者强调站在立法者的角度,以立法者的意思去进行解释,但客观解释论者则会根据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其规范目的。在还未进行实质解释之前,规范目的解释方法就已经面临这样一个严重分歧,不能不让人产生对它的质疑。以交通肇事“逃逸”为例,持“逃避法律追究说”的学者主张的目的实为逃逸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持“逃避救助义务说”的学者主张的目的则为立法者的目的。在此,就出现了两种不同主体的目的。由此看来,在用规范目的方式解释交通肇事“逃逸”时,在关于目的主体的选择上就出现了不可调和的错误。此时,关于两种目的的争论是注定不会有结果的。
2.3行为性解释——交通肇事“逃逸”解释的新出路
犯罪由行为引起,刑罚亦由行为产生,因此,坚持行为性解释的方法是正确理解交通肇事“逃逸”的唯一出路。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结构上来看,此种情形包含了肇事和逃逸两个行为:肇事行为是指行为人过失地引起交通事故,并造成了严重的人身财产上损害的行为;而逃逸行为则是因肇事者不履行救助被害人义务,可以评价为不作为犯罪的行为。由于两行为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牵连或是吸收关系,在这种具有多个行为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考虑到的便是成立数罪。虽然我国刑法以类似于结果加重犯或是情节加重犯的方式规定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但笔者仍然主张,在对其进行解释时,按照“交通肇事罪(基本犯)+遗弃罪”的公式会让我们更容易理解立法者的原意。
2.3.1被视为结合犯的“交通肇事后逃逸”。
正如上文所言,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情况实际涉及肇事行为和逃逸行为两个独立的行为。在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已经成立的情况下,由于“逃逸”行为提升了行为人的法定刑,因此对“逃逸”行为有必要进行单独的刑法评价。将“交通肇事后逃逸”解释为交通肇事罪(基本犯)与遗弃罪的结合,不仅合理地解释了法定刑升格的原因,同时也避免了与其他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有学者认为,将这样两种罪名杂糅在一起的做法极为不合理,会导致许多不必要的理论争议,影响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6]。然而笔者认为,虽然在立法上将“逃逸”行为单独成罪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手段,但我国现行刑法选择以结合犯的形式规定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形也未必不合理。如何规定犯罪类型是立法者的权力,这并没有什么可以指摘之处。
2.3.2被视为“结合犯的结果加重犯”的“因逃逸致人死亡”
《刑法》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实际起到了顺接上文的作用,是作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加重结果出现的。由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在我国刑法中并不成立独立的罪名,而是作为以结合犯出现的加重的交通肇事罪,因而,“因逃逸致人死亡”可谓结合犯的结果加重犯[7]。由此,我国刑法中关于交通肇事罪就可以完整地表述为:(1)交通肇事基本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2)交通肇事基本犯+逃逸(不作为的遗弃罪)=结合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3)交通肇事基本犯+逃逸(不作为的遗弃罪)+致死后果=结合犯的结果加重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此外,通过我国刑法各罪中的法定刑配置,也可以印证“因逃逸致人死亡”是“结合犯的结果加重犯”这一推论。我国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法定刑最高为3年,遗弃罪的法定刑最高为5年,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最高为7年。上述三罪的最高法定刑相加,恰好等同于“因逃逸致人死亡”所适用的最高法定刑。因此,从法定刑的角度来看,以上推论是具有合理性的。
3 结语
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在对交通肇事“逃逸”问题进行解释时,主要采取了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方法。但是,无论哪种方法都有其天然的缺陷,都会产生很多让人难以接受的结论。因此,在对交通肇事逃逸问题进行研究时,应当抓住两条线索:一是逃逸规定的规范保护目的;二是交通肇事后逃逸场合涉及的行为结构。通过对上述两条线索的把握,我们可以得出“交通肇事后逃逸”实属交通肇事罪与遗弃罪的结合犯的结论,这也可以有效地解释立法者对其升格法定刑的依据。
[1]张明楷.论升格法定刑的适用根据[J].法学论坛,2015(4):36-44.
[2]张明楷.论交通肇事罪的自首[J].清华法学,2010(3):27-41.
[3]刘淑莲.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作为性质[J].法学杂志,2005(2):53-54.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34.
[5]黄伟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性解释——以质疑规范目的解释为切入点[J].法学,2015(5):151-160.
[6]黄河.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罪名化[J].政治与法律,2005(4):119-124.
[7]劳东燕.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问题研究[J].法学,2013(6):3-14.
[责任编辑冯峰]
Behavior Interpretation of Traffic Accident“hit-and-run”
SUN Hao-wen
(Law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Shandong Jinan,250100)
When scholars interpret Traffic Accident issue,taken the literal interpretation and purpose of interpretation methods.However,whatever method has its natural defects,resulting in a lot of unacceptable conclusion.Therefore,the“hit-and-run”should start from the structure to explain its behavior,saying that“after the Traffic Accident”it is combined with committing traffic crime and abandonment of sin,so as to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basis for the punishment to be upgraded to their legislators.
Traffic hit-and-run;avoid legal action;evade duty relief;specification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behavioral explanation
D924
A
1008-486X(2016)01-0101-04
2015-11-26
孙浩文(1992-),男,山东烟台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学学习与研究,研究方向为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