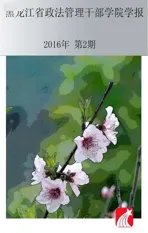中外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路径比较研究
2016-03-15时杜娟
时杜娟
(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西安 710063)
中外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路径比较研究
时杜娟
(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西安 710063)
摘要:我国2014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了修改,提高了惩罚性赔偿金额的比例,并规定最低赔偿限额。与国外的实践相比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适用范围较为局限,并且存在法律条文之间相互矛盾、条款过于原则化等问题。我国应该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立法技术上应掌控惩罚性赔偿金额和社会效果之间的平衡,防止巨额赔偿金额造成负面效应,并考虑将食品安全、产品责任、商品房买卖和部分医疗事故等纳入适用范围。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适用路径;比较分析;完善立法
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国1763年的Huckle v. money一案,后在普通法系国家得到推广。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从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上解释它的含义,可以概括为:“惩罚性赔偿金不是具有赔偿性或者象征性的损害赔偿金,它的授予原因是因为令人不可容忍的行为,需要对此行为进行惩罚并预防该行为人以及其他人将来实施类似的行为”[1]。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出现打破了民法的补偿性赔偿原则,在侵权、合同欺诈、医疗事故、房地产交易、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责任等领域被逐渐适用。
我国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首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较之于西方的判例实践,我国立法晚了两百多年,这囿于我国受大陆法系和中华法系的影响,奉行严格的民事补偿性赔偿原则。2014年,我国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法”),第55条将原来旧法第49条中的1倍赔偿金增加至3倍,另外规定损失不足500元时,最低赔偿金额500元。新消法加大了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力度,体现出我国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现象的严厉制裁和遏制。目前,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适用领域较为局限,适用于产品和商品造成的侵权和部分合同,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进入我国立法时间尚短,因而缺乏实践经验,在适用领域、赔偿金额计算、法律协调、概念界定等方面存在很多漏洞和不足,我们有必要分析和探讨国外判例实践中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推进过程,以及现今国外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领域和实践中的某些要求,以期对我国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立法有所借鉴。
一、国外的判例实践和适用路径
(一)英国
英国合同法排除惩罚性赔偿制度历经了近100年的实践。1964年的Rookes v.Barnard一案*Rookes v. Barnard[1964] AC 1129。,首次明确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规则,上议院认为一审法院对被告作出的惩罚性赔偿判决是不当的,因此否定了一审法院的判决。但是,Lord Devlin法官确定了三种例外适用的情形*原文表述是:(1)Oppressive, arbitrary or unconstitutional actions by the servants of government;(2)Where the defendant's conduct was 'calculated' to make a profit for himself;(3)Where a statute expressly authorises the same。:一是政府公职人员的压迫性或违宪的行为;二是被告的行为是为了自己获得利益;三是如果法律有类似明确的规定。这三种例外没有涵盖违约的情形,因此,在英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原则上不能适用于违约[2]。直到Attorney-General v Blake一案打破了这一原则*Attorney-General v Blake[2001] 1 AC 268。,基本案情如下:
Blake曾供职于英国情报局,1951年到1960年他泄密给苏联,后被判处42年的监禁。1966年,他逃亡到莫斯科。1989年,他在莫斯科写了一部自传,内容涉及情报局的工作内容。他随后授权Jonathan Cape Ltd.出版社独家出版,该出版社承诺签订合同后付给他50 000英镑的报酬,待他交付手稿后再付给他50 000英镑,待书出版以后还要付给他50 000英镑的报酬。当他从出版社获得了60 000英镑后,英国情报局对他提起了私法诉讼,诉由是他违反了雇佣合同中的保密义务,要求赔偿损失,赔偿额包括他从出版社已经获得的报酬和即将获得的报酬。一审法官驳回了原告的起诉,认为一个人没有义务一生都为自己曾经在情报局的工作而保密,而且当保密信息已经超过一定的时间,泄露这些信息不会对国家的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原告提起上诉,这次是基于公法的起诉,诉由是违反1911年的《官方保密法》,要求法院对被告颁发禁令,以阻止他从自己的犯罪行为中获得任何报酬。上诉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求,认为被告违反了保密义务的根本在于违反了雇佣合同,但是原告并不能证明自己受到的损失,因此不得主张名义补偿*原判决中的措辞是:nominal damages。以外的赔偿,并且认为向被告颁发禁令相当于是没收被告的私人财产,而普通法没有没收私人财产的权力。然而,Lord Hobhouse法官不赞同只能进行名义上赔偿,他认为,即使该案中的情报已经不再具有保密价值,但是该案具有涉及国家秘密的特殊性。名义补偿不能弥补此种情况的违约后果,被告的泄密行为应该受到限制和否定,目的在于惩罚和预防此类特殊违约。他认为作为惩戒,赔偿额应该包括被告已经从出版社获得的60 000英镑,以及出版社承诺给付的90 000英镑。
该案首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违约,扩大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国的适用范围,跳出了诱奸、诽谤、诬告、不法侵占、非法拘禁等损害名誉和侵犯人身的限制。这是因为法官认识到此种违约与侵权一样具有严重的后果,并且一般民事补偿不能体现公平正义,此种行为应该打击和遏制。本案中英国情报局并未受到实际损失,惩罚性赔偿金仅仅是对违约行为和泄密行为的遏制和威慑。
(二)美国
美国在1784年的Genay v.Norris一案中首次确认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与英国早期一样,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美国也是适用于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害的赔偿案件。后来,美国将该制度广泛应用于商事领域,特别是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独立侵权行为[3]。例如Formosa Plastics Corp.一案*Formosa Plastics Corp. USA v. Presidio Engineers & Contractors, Inc.,960 S.W.2d 41 (Tex. 1998)。,1989年Formosa公司筹划在德克萨斯州的康福港建设大型基础设施,Presidio接到了投标邀请。投标方案中明确要求:1.Presidio全权负责自己负责部分建筑材料的订购、运送、交付等事项,并且由Presidio为项目公司先行垫付这些材料的费用。2.工程从动工开始应持续不断地完成。3.该部分工程计划于1990年7月16日动工,在随后90天之内完工。Presidio注意到项目公司要求承包方必须为天气等不可预知的延迟负责,所以Presidio向项目公司提交了了一份延长30天的说明,最后以600 000美元的低价中标。但是该工程最终耗时8个月完工,是项目公司计划时间的近3倍,是承包方提议修改时间的2倍,这是Presidio在投标时根本无法预见的。实际上,项目公司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迫使承包者签订合同,利用投标方案中的条件诱导承包者对工程迟延负责,然后私下另有完工计划和交付时间安排,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获得1 500 000美元的利益。陪审团认为项目公司违反了诚信义务,其行为是故意的、放肆的,具有欺诈性。初审法院最终判处项目公司赔偿原告700 000美元的实际损失,另外付给原告10 000 000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
本案是一个典型的合同欺诈,合同中存在欺诈性的诱导陈述,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就可以基于独立于违约的侵权损害请求惩罚性赔偿。而且惩罚性赔偿金高达实际损失的14倍之多,实际损失和惩罚性赔偿金之和超过了项目公司企图的获利数额。
(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较早提出反对英国Rookes v. Barnard案中的三个例外适用规定的国家,在Australian Consolidated Press Ltd v. Uren一案中(该案是一个诽谤案件)*Australian Consolidated Press Ltd v. Uren (1967) 117 CLR 221。,澳大利亚最高法院的法官Taylor J.认为对惩罚性赔偿授予的分类不限于Rookes v.Barnard案中作出的规定,Windeyer J.法官也认为应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定是否给予惩罚性赔偿,而不是拘泥于Rookes v.Barnard的限制,Owen J.和Menzies J.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一开始澳大利亚也不允许惩罚性赔偿适用于违约*Gray v. Motor Accident Commission (1998) 196 CLR 1。,后来才逐渐扩大到违约和更多的领域,比较典型的判例如下:
Harris v. Digital Pulse Pty Ltd一案中*Harris v. Digital Pulse Pty Ltd (2003) 197 ALR 626。, Harris违反与受雇公司Digital的保密合同,在职期间从事与公司具有竞争性的工作。Digital公司起诉Harris违反了雇佣合同,同时违反了《2001年公司法案》中的保密义务,并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请求。Digital公司在一审中获胜,Harris提起了上诉。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不能同时适用于违反合同和违反诚信义务。Heydon JA法官认为法院没有权利以衡平法上的公平为诉由判处惩罚性赔偿。前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席法官Spigelman CJ虽然强调被告的行为属于违约,但他还是认为要避免依据公平的不义行为(equitable wrongs),而是要依据是否侵权作出惩罚性赔偿。Mason P大法官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没有一项原则规定惩罚性赔偿只能适用于普通法上的侵权,而不能适用于破坏公正的违约行为。因此在澳大利亚,如果基于一项合同产生独立的侵权损害,那么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时违反衡平法上的公平原则,而做出错误的行为也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四)新西兰
在新西兰,惩罚性赔偿是在Auckland City Council v. Blundell案中得到确认的*Auckland City Council v Blundell[1986] 1 NZLR 732。。,在Paper Reclaim Ltd v. Aotearoa International一案中*Paper Reclaim Ltd v Aotearoa International Ltd[2006] 3 NZLR 188。,法官认为惩戒性赔偿金不能适用于违反合同的情形,但是法庭认为在违反合同造成侵权的情况下是可以适用的。在Couch v. Attorney-General案中*Couch v Attorney-General[2010] NZSC 27。,新西兰最高法院禁止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最高院的法官认为惩罚性赔偿不能适用于因疏忽导致的行为,除非该行为是被告有意的或者是严重的主观过失。这两个案件中法官的态度明确了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条件,一般的违约不能适用,除非是主观上蓄谋违约,比如欺诈;再者,违约若带来如侵权般的严重后果,则可适用。体现出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主观恶意和某些不良行为遏制的初衷。
二、中外适用路径分析比较
(一)侧重的适用领域
从上述几个判例可以看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美等国的适用领域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诽谤、诱奸、诬告、非法拘禁等逐渐转入合同领域,并且是在侵权案件中适用的3倍[3]。比如违反保密合同、违反诚信义务、合同欺诈、基于合同产生的侵权等,这些案件都强调了一点,即违约造成的损失在某些情况下比侵权和刑事犯罪可能更加严重,此时若仅仅只是弥补损失就无法体现公平正义,也不利于遏制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因此必须给予制裁,而恰好惩罚性赔偿再合适不过,因为它起到制裁违约方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序良俗的作用。
我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的较晚,而且适用领域十分局限,且多在侵权领域。比如《侵权责任法》第47条*《侵权责任法》第47条:“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和《新消法》第55条的第二款*新消法第55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都是基于侵权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我国目前在合同领域也有相应的立法规定,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这两条都规定了因为隐瞒或者其他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或者无效、撤销、解除的,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和《新消法》第55条第一款都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而且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合同法》肯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些变化说明我国也在逐渐将该制度适用在合同领域。
(二)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
在Blake案中,法官最后判处的惩罚性赔偿金是Blake已经从出版社收取的和即将得到的酬金之和,因为本案中情报局没有受到实际损失,无法计算比例。在Norris一案中,法官判处的惩罚性赔偿金高达实际损失的14倍之多。更加令人诧异的是Liebeck v. McDonald's Restaurants一案*Liebeck v. McDonald's Restaurants, P.T.S., Inc., No. D-202 CV-93-02419, 1995 WL 360309(Bernalillo County, N.M. Dist. Ct. August 18,1994)。,Liebeck被麦当劳的热咖啡烫伤后向麦当劳索赔20 000美元的医疗费,Liebeck自己负担20%的过错,因此赔偿金额降至16 000美元。但是陪审团同时判给Liebeck 2 700 000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是实际损失的168倍之多,遭到批评后降至480 000美元,是实际损失的30倍。可以看出,国外对赔偿金额的计算除了法律偶有规定外,大部分是法官和陪审团作出决定,而赔偿金额的多少并没有一定的比例可循,但大多都是巨额赔偿。
我国1993年消法和2014年新修订的消法对惩罪性赔偿金都做出了明确的比例和下限数额要求。笔者认为我国规定比例的出发点在于给予法官有限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因法官个人的决断导致巨额赔偿或者赔偿额太少而不能达到制裁的目的。该赔偿标准究竟是否会达到预期效果,还有待新法进一步的实践。如果我国将来在侵犯人身权利但并未构成犯罪的情形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笔者认为不宜直接规定统一的比例赔偿,而应该考虑到行为人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收入状况。若惩罚性赔偿金超出行为人所能负担的范围,势必会造成判决的执行困难,或者导致行为人陷入危险境地,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在于制裁和遏制,而不在于制造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究竟赔偿额度如何把握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和探讨。
(三)对正当程序的要求
一般看来,惩罚性赔偿的巨额数字已经远远超出了实际损失的数额,但是,根据美国司法部一位法学专家的数据统计,惩罚性赔偿的案件数量只占美国民事诉讼案件的2%,中间水平的赔偿金额一般在38 000美元 到50 000美元之间*Douglas Laycock, Modern American Remedies(Aspen,2002),p.732-736。。为了避免出现法官和陪审团作出巨额赔偿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根据《美国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作出了多个决定来限制惩罚性赔偿。在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案中*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517 U.S.559(1996)。,法庭认为过度的赔偿金额违反了正当程序,赔偿金额必须是合理的,应该根据被告行为导致原告受损的程度,或者考虑惩罚性赔偿金和补偿性赔偿金所占的比例,或者任何与该行为类似的刑事或者民事给予的处罚金额。
我国对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规定较为明确,并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惩罚的效果适时在新法中作出了比例调整和规定了最低限额。相对来说,我国法官在赔偿金额上的自由裁量权较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巨额赔偿金额的产生。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美的适用比较灵活,它可以被法官不断地去实践和斟酌,希望从中提取该制度最正面的社会价值,不断消磨可能被滥用产生的负面效应,这也是该制度备受争议却又一直存在的动力。
三、对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相关立法的评价和建议
(一)科学立法,协调有关法律之间的规定
消法中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何为“欺诈”?我国《民通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而《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显然后者中的“其他不正当手段”包含了前者中的“故意隐瞒”,并且涵盖了其他《民通意见》中没有包含的欺诈情形。所以目前法律对“欺诈”的界定是不统一的,应该对何为“欺诈”有一个统一的解释。笔者认为《民通意见》中的界定很具体,但有局限。而《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中的界定涵盖广泛,但是在实践中对“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判断上则要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
(二)将原则性规定具体化,增加可操作性
我国在《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一条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的实施方法。《侵权责任法》和《产品质量法》中都没有关于产品缺陷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具体规定。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能否适用于产品责任是有待商榷的,在将来的规定中应该区分生产企业是否事先知悉缺陷的存在,如果是有目的的实施欺诈,或者明知产品有缺陷而生产销售的,可以纳入惩罚性赔偿的范围。在赔偿金额的确定上也要兼顾生产者的主观恶性、受害人的损失程度和企业的经营状况,在这三者里面,首先应该注重对人身安全的保护,其次是对企业承担能力的考虑,不能因保全一个企业而不顾一般人权,要掌控处罚金额和惩戒效果之间的限度。
(三)突破适用的局限,适当扩大适用领域
有学者提出应该限制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合同责任中的适用,因为考虑到违约损害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的救济目的的不同等因素,并且担心在合同中适用会影响市场经济的繁荣。笔者认为,我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目前还处于比较谨慎的态度,是否能适用于合同责任不能一概而论,在某些低成本违约、欺诈等破坏公平交易的情形下可以适用,而且不仅不会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反而有利于交易主体之间展开公平有序的合作。所以我国应该不仅限于消法的规定,可以适当扩大适用到食品、药品、房地产和部分医疗事故等领域。
参考文献:
[1][奥]赫尔穆特·考茨欧,瓦内萨·威尔科克斯.惩罚性赔偿金:普通法与大陆法的视角[M].窦海阳,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91.
[2]陈任.英国合同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63.
[3]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
[责任编辑:刘晓慧]
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66(2016)02-0062-04
作者简介:时杜娟(1989-),女,陕西永寿人,2013级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