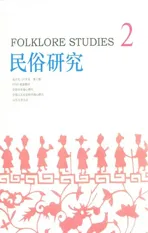御凶、飞天与吞月:中国古代的天狗异兽
2016-03-15刘泰廷
刘泰廷
御凶、飞天与吞月:中国古代的天狗异兽
刘泰廷
摘要:古代文献中,天狗作为异兽常常与星占体系中的天狗星相混淆,了解人们如何接受这个观念并把它合理化是揭示天狗形象意涵的必要条件。天狗食日、月的传说在明代就已广泛流传,对于古人来说并不是一个仅供谈资的故事,警天狗、救日月的民俗行动也未像端午节赛龙舟等民俗活动那样蜕变为游艺性、趣味性十足的游戏。直到民国时期,民间仍然普遍相信天狗是日月食的祸首,每当日月食发生时,人们心中仍会涌起对于天狗的恐惧。
关键词:天狗;异兽;物占;食月
提起天狗,大部分人心中出现的就是食月的恶兽形象。事实上,这种认知的产生时间比我们想象中要晚得多。我国古代的确存在名为天狗的异兽,如果把它置于文化及思想的脉络中来考察,会发现这种形象既不固定也不单一。
本文的讨论重点不是天狗一词的得名,而是由天狗折射的古人的知识、信仰世界。因此,一些虽具“天狗”之名却与此主题无关的寻常动物则被置而不论。如许慎《说文解字》记载了一种名为天狗的水鸟:“,天狗也。”段玉裁云:“按今所在园池有之,谓之鱼狗,亦谓之鱼虎。”这个名称在南朝仍然被记忆。沈约《郊居赋》云:“其水禽则大鸿小雁,天狗泽虞。”①(唐)姚思廉:《梁书》卷十三《沈约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239页。如今无法判断这种鸟被如此命名的缘由,或许如李时珍所说:“狗、虎、师,皆兽之噬物者,此鸟害鱼故得此类命名。”②(明)李时珍:《金陵本〈本草纲目〉新校正》,钱超尘等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1621-1622页。李时珍指出蜀人把一种獾类的动物也称为“天狗”。如此之类,皆无关乎本文论题,故置而不论。
一、物占与误注——从《山海经》说起

天狗在文献中首次出现就带有神秘色彩,它更近于传统文化中的瑞兽,只是它的特性并不是昭示祥瑞,而是去祸免灾。*关于瑞兽文化,参于爱成:《祥瑞动物》,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
同书还记载了天狗原始形象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源头,其寓义恰恰与上述相反。《大荒经·大荒西经》云:“有金门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以一种动物的出现来预兆兵灾,这是古老的物占方术。*参赵沛霖:《先秦神话思想史论》第二编第一章《物占的起源与神话》,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115-134页。因为在天犬与有兵的占兆形式中,人的意志无法贯穿其中,卜者没有任何的能动余地,甚至不需要具备专业的素养技巧,只要能够识别即可。正如梁钊韬在《中国古代巫术》中所指出的“仅限于利用自然的预兆方法,而没有人为的卜筮方法,足以代表中国最原始的占卜形态。”*梁钊韬:《中国古代巫术》,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
这种名为“天犬”的怪兽在形态与象征意义上都与上文所述的天狗迥异,但却因为预示兵灾的祯兆而被注疏家们与天狗星相牵合。已知最早的注释者郭璞注此云:
《周书》云:“天狗所止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十数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其光如电。”吴楚七国反时,吠过梁国者是也。*(晋)郭璞注,毕沅校:《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2页。
郭氏以星注兽固然是有问题的,如清代学者郝懿行案此谓:“赤犬名曰天犬,此自兽名,亦如《西次三经》阴山之兽名曰天狗耳。郭注以天狗星当之,似误也。”*(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596页。但从此可见当时已有以天狗星为一有形神兽的观念。叶舒宪认为郭璞引流星注天犬的“巫术性机理或依据”是“对流星的恐惧与犬崇拜相结合。”*叶舒宪、萧兵、[韩]郑在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75页。这并没有把握住问题的关键。其核心思想是星辰有灵与形象化的观念*《后汉书·天文志》李贤注引张衡《灵宪》云:“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跱,各有逌属。……六扰既畜,而狼蚖鱼鳖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备矣。……庶物蠢蠢,咸得系命。”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216-3217页。,而郭注则是建立在此观念基础上对星占与物占的混淆。这种混淆被后世所传承,并纳入天狗星占体系中。《太平御览》于“天狗”条下引此天犬与星占并列而不引《西次三经》之天狗,即可见编者意同郭氏。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天地类“天狗星”:
元至正六年,时云南玉案山忽生小赤犬无数,群吠于野。占者曰:此天狗坠地,有大军覆境。*(明)郎瑛:《七修类稿》,中华书局,1959年,第67页。
占者明确地将赤犬与天狗星联系起来,但所说较为模糊。与郎瑛同时的潘埙所辑《楮记室》云:
至治元年,玉案山产小赤犬。占曰:天狗堕地为赤犬,其下有大军覆境。*中华书局编:《古今怪异集成》,中华书局,1919年 ,第19页。
点出了天狗与天犬的明确关系:天狗星坠地化为天犬。胡文焕《山海经图》释此更为详细:
天门山,有赤犬,名日天犬。其所现处,主有兵,乃天狗之星光色流注而生,所生之日,或数十。*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590页。
这种说法将异兽天犬纳入到了天狗星占中,成为兵灾的征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谓天犬只是作为天狗星的衍生品,仅在天狗流星坠后才会出现。有研究者认为:“正因为郭璞的错误注释,‘天狗’、‘天犬’才升天为天狗星。”*秦永洲、李云泉:《生肖狗》,齐鲁书社,2005年,第36页。如此论述是不妥的。首先,《山海经》中的异兽天狗从未与天狗星占相混,其次,天犬入占后也没有升天为星。
二、脱胎换骨:从阴山到天宫
作于汉时的《三秦记》*《三秦记》早佚,六朝著作多引,所记皆秦汉而不及魏晋故事。王谟《汉唐地理书钞》有考(中华书局,1961年,第365页)。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21页)亦有论。云:
骊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时有天狗来下,有贼,则狗吠之,故一堡无患。*刘庆柱:《三秦记辑注 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7页。此条出《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略同,详见第99页。
在这个故事中,天狗作为一只具体的动物出现,“狗吠之”说明了这一点。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注此云:“《北齐书·昭帝纪》:时有天狗下,亦其类也。《山海经》有兽,亦名天狗。《西山经》曰:阴山有兽焉,其状如豹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榴榴,可以御凶。”*(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10页。这又是一则混淆天狗星与天狗兽的例子。《北齐书》所记为天狗流星,引此为非。但其引《西山经》则在情理之中。因为“天狗御凶”的特性与“一堡无患”的结果极为相合。《三秦记》直言天狗而未作解释,所指似乎就是《山海经》中的天狗。
由于资料的缺失与记叙的简略。我们无法通过《三秦记》了解天狗的具体特性。“时有天狗来下”似乎暗示它从天而降,但《山海经》对金门山之天犬的描述(“其所下者”)使这种暗示重新模糊起来。考究天狗的来源非常重要,它可以揭示天狗的旧有形象是否在文本中被简单地复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三秦记》就表现了当时对天狗形象的另一种设想,它存在于天空而非大地。这种形象在汉唐是缺少文献佐证的,使人怀疑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对天狗的神话想象并不热衷。
在宋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天狗已脱离于《山海经》里的原始形象。罗愿《尔雅翼》卷十七云:
九头鸟,今谓之鬼车鸟。秦中天阴,有时作声,声如力车鸣。或言是水鸡过。说者曰:此鸟昔有十头,能收人魂气,为天狗啮去其一,至今滴血不止。*(宋)罗愿:《尔雅翼》,中华书局,1985年,第185页。
欧阳修《鬼车》诗云:
射之三发不能中,天遣天狗从空投。自从狗啮一首落,断头至今清血流。*(宋)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7年,第346页。
天狗啮九头鸟的传说可明其在时人观念中的凶猛形象。*天狗之凶猛吞啮的意象直至清代仍为人所使用,侯方域作《悯獐》文,以韩子庐(犬名)友獐而食之喻害友之徒,其下有《卢告》,言韩子庐托梦以鸣不平:“余且三踊三号而湔其颈之血,以上请于帝,化为天狗,而噬夫天下之负涂而载鬼,黑乌而赤狐者,以信余之志,辨余之族类,而洗之于夫子。”侯方域著、朱凤起选注:《侯方域文》,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38页。“天遣天狗从空投”则意味着此时天狗已可飞天,非山野之凡品。辽代王鼎所撰《焚椒录》载:
懿德皇后萧氏为北面官南院枢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梦月坠怀,已复东升,光辉照烂,不可仰视,渐升中天,忽为天狗所食,惊寤而后生,时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母以语惠,惠曰:“此女必大贵而不得令终。”*(辽)王鼎:《焚椒录》,中华书局,1991年,第1页。
萧观音母耶律氏之梦反映了飞天之天狗已进入人们的知识、信仰世界。明时天狗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明人宋懋澄《九籥集》卷十《蟠桃宴》*(明)宋懋澄:《九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20页。与王同轨《耳谈类增》卷四十五《河洛人幻术》*(明)王同轨:《耳谈类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87-388页。记载了幻术表演者上天偷桃而自云为天狗所逐的故事。天狗在两个文本中都承担了看守天门的职责,前一则里咬得童子胫下血淋淋,而后一则更为血腥,偷桃者肢体为之破碎。但它们有一共性特点,即无论是作者亦或是文本中的叙事者(术士、妇)都没有对天狗进行交代,可见天上有天狗为当时一个默认的知识背景。这种背景一直延续下去,如清人林直《壮怀堂诗初稿》卷五《放歌行柬芑川即送其司训甯德》云:“玉皇诏开钧天门,雷公喝道阍者惊,天狗吠我声狺狺。”*(清)林直:《壮怀堂诗初稿》,《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57册,第378页。(清)张际亮《思伯子堂诗集》卷七《思归吟》:“昨梦游戏凌天阊,天狗訚訚向我狂”*(清)张际亮:《思伯子堂诗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26册,第553页。等。天狗甚至被刻在陵墓的华表上,钱泳《履园丛话》卷十六:
苏州宋文恪公墓在沙河口,乾隆中,有坟旁老妪陆姓,月下见一物如狗者从空而下,跃水中攫鱼食之,如是者旬余,不解其故。一日,守墓者遥见华表上少一天狗,过数日天狗如旧,或疑此物为怪,击碎之。*(清)钱泳撰:《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第430页。
天狗从《山海经》中阴山上的异兽到后世天宫中之神兽,这其间的变化轨迹并不清晰,我们无法判断后者的形象是如何出现的,甚至不能断定这个形象脱胎于《山海经》,或许,两者除了名字相同外没有任何关联。郭璞的误注则暗示:即当天狗星形象化后,是否有变成动物类天狗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萤窗异草》卷二云:“人之艰于嗣者,多绘张仙以奉之,以其能卫厥子孙也。其像为美丈夫,锦袍角带,广颐丰髭,左挟弹,右摄丸,飘飘乎有霞举之势。仰视云中,一犬叫嗥而去,盖即俗所谓天狗也。”*(清)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3页。在张仙像中,天狗星已化为有形之天狗*此种形象与第三节所论食月之天狗为一。《历代神仙演义》卷十九第一节《行遁甲枉施匕首 出阳神易折琼花》:“帝昼寝见一美男子粉面五髯,挟弹而前,曰:‘君有天狗守垣,故不得嗣,赖多仁政,予为弹而逐之。’帝请详其说,曰:‘予桂宫张仙也,天狗在天掩日月,下世啖小儿,见予则当避去。’帝顿足而觉,即命图像悬之。” (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71页)关于张仙的考证,以杨荫深《事物掌故丛谈》(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28页)最为详实。亦可参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92-695页。。从“俗所谓天狗”一语推断,上文所论的广泛存在于宋明清文献中的天狗形象其本源可能即是天狗星。当天狗星脱离星占的原始语境,它在人们心中所意味的便不再是昭示凶祸的星辰,而变成了一个具体可感的形象,尽管这个形象仍然是不祥的。
三、吞日啮月
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回忆道:“后求学南京,忆于一黄昏时望月食,俗谓此由天狗食月,故街上群儿皆共击鼓,声闻四野,谓所以驱此天狗,而救此月之光明。”*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59页。天狗食日月的传说流传很广,并一度为人们所坚信。这种想象并不是汉族所独有的,鄂伦春、白、傣、哈尼、藏、苗等民族都有类似的传说。*参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一种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7页。张竹筠、周颖:《中国少数民族日月神话传说述评》,《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第1期。它甚至不限于中国,李谋和姜永仁在《缅甸文化综论》中提到缅甸也有天狗吞月的传说,并把它作为中缅相互影响的实例。*李谋、姜永仁:《缅甸文化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0页。巴比伦、美洲的印第安人亦传此说。*王政:《战国前考古学文化谱系与类型的艺术美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4页。林惠祥《神话论》云:“日月蚀在不明天文学的民族看来,常当作奇异的灾祸,故有许多神话说明他。如南美奇歧托人(Chiquitos)说月蚀是因为月被大狗所咬噬,其红光便是流出的血。人们需大声喊叫、射箭天空,方能赶走大狗。同洲的卡立勃人(Caribs)和秘鲁土人都有相类的神话。”(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8页)仅就中国的天狗日月食的研究现状来看,还有很多问题前人尚未涉及,兹详论如下。
(一)真实的恐惧:以晚清民国的报纸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代,报业传媒迅速发展,这为回望这一时期的社会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史料,其实时性与公众性是后人据以对过去进行真实展现的较好保障,当然,这种保障并不是绝对的,如政治会牵动报纸论调,甚至迫使其参与消息造假。*参李良荣:《李良荣自选集:新闻改革的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9-348页。庆幸的是,在关于天狗民俗的报刊文章上,类似的失真不会发生。由日月食而引起的救日月活动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被视作启迪民智与推广科学必要性的例证而为知识人广泛关注,那些泛黄的记忆提醒我们注意两个容易为人忽略的事实:一、食日月的祸首并不是一只来由不清的天上之犬,而是天狗星化身的天狗,这不待考据学家发现,而是当时民间普遍的共识。二、天狗食日月并不仅仅是传说,人们救日月的各种行动也不是简单的风俗传承,当日月食发生时,他们真切地感到惊慌与恐惧,并坚信鸣锣升炮等行动可以驱赶天狗。
1873年,《申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记月食》的文章:
前夜月食沪地,于九、十点钟时见之。食既所余仅如一指爪痕。各处鸣锣升炮,作救护之举。按俗谓天狗星食月,殊属荒诞可笑。不知月本无光,借日光以为光,中隔地球,有时而地球之影掩月,故月为之食。此盖西人之言,颇为有理,故因而附记之。*《申报》,1873年5月14日,第2版。
这是一个“智者”对民间救月这种有失理性行为的冷眼旁观。从他提到西洋理论时的语气可以推测,他并没有受过专业的西洋教育,“西人之言”也仅是道听途说而已。“荒诞可笑”的“天狗星食月”的俗传印记是随处可见的。如时人所作《冬行春令辨》:“日月之食为天狗星吞而复吐,则尤不改一字,童而习之矣。”*《申报》,1879年12月29日,第2版。
当日月食发生时,民间的救日月行动也随之而生:“一般无知识的人,对于日蚀的解说向来是很神秘的。他们一看见日蚀现象发生,不是说天狗吃日,便是说恶魔在吞食太阳;而且,即刻就要打锣击鼓,希望太阳复原,否则人间便会长期黑暗,永无光明了。”*《申报》,1936年7月12日,第22版。这种行动并不限于民间,地方官吏也会参与到其中:
夫鲁阳、夸父岂真有其事者,况于天狗而能吞日耶?窃谓野人俚谚固不足信,为更不足凭也。西人见中国每于日食之期地方官民军人僧道一齐救护,不觉哑然失笑。*《论救护日食之法最古》,《申报》,1882年5月21日,第1版。澳洲记者莫理循(Morrison G.E.)便亲眼见证了东川知府带领乡绅救日的仪式,这个仪式庄重而又复杂,还搭建了一个10英尺高的木头棚。见[澳]莫理循:《1894年,我在中国看见的》,李琴乐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37-138页。
1921年,竺可桢在《本校急应在北极阁上建筑观象台意见书》中写道:“南京素称文化之邦,而去年10月27日月蚀时,城中各处锣声震地,群讶以为天狗食月,南京如斯,他处更可知。”*高庄:《竺可桢与科学普及》,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筹备组编:《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论文报告集》,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8页。
在知识阶层的眼中,“愚昧的”救月行为反映了民智未开的社会现状,正为我国科学的落后作了注脚。而报纸作为科普宣传重要阵地的作用则被凸显出来。如徐家骥作《辟救月之荒谬》云:
吾国人素多迷信,至今日尚不能革除,良可浩叹。夫月蚀者,地球行于日月之间而使月不能受日光也。月蚀而称之曰天狗吃月亮,曰野月亮吃家月亮。可笑也……则地面爆竹之声欲以驱天狗者约须十三日始逹月球,试问月蚀之时间仅二小时,岂天狗因闻爆竹之声而遁耶?夫生而为二十世纪之人须具有科学的人生观,一切迷信皆应破除,愿学者速以科学常识劝导乡愚,毋再迷信致贻笑中外也。*《申报》,1920年 11月4日,第17版。
邵力子《迷信与发狂》说:“大家想一想,这一夜中所放爆竹的钱,倘使拿到北方去赈饥,要救活同胞多少生命!”*邵力子:《迷信与发狂》,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0月28日“随感录”,今引自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429页。这里提到的北方之灾当指1920年华北五省的旱灾,乃“四十年未有之奇荒”。*关于此灾之具体情况,参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页。而将救月行动放在灾荒背景下考量则从侧面反映出民众参与的广泛程度。
天狗食日月的恐慌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34年的月食报道,当月食发生后,“炮竹声四起”,“结果,眉月复圆,大家额首相庆,说:月亮已经脱难,天狗已经吓走了。训政时期已过五年,而民智如此。”*《晨光》(杭州),1934年第3卷第9期, 第14页。即使到了1941时,这种状况仍没有明显的改善:“重庆在中国之科学家,以其最新式之仪器观察日蚀时,重庆之普通民众,仍依照习俗所传,敲锣鸣砲,高声叫嚣以吓退天狗。”*《电台广播观测情形》,《申报》,1941年9月22日,第3版。
上文所引的报纸、回忆录等材料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存在于人们想象中挥之不去的鬼魅暗影。这个影子很早就盘桓在先民的记忆里,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本文一二章所勾勒的天狗异兽都没有展现出吞日噬月的伟力,那么,天狗食日月的想象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呢?
(二)天狗食日月想象探源
董作宾在《殷历谱》第三卷《交食谱》中按《谷梁传》释春秋隐公三年日食为“有食之者,内于日”一段云:
谷梁氏以初亏为“食”,以复圆为“吐”,以“食之者”为不可知之物,殆犹存神话之背景。民间传说则以日月食皆为天狗所食,故必鸣金击鼓以营救之,此义殷人似已知之。卜辞中有御祭天犬之文……天犬疑即后世民间流传可以吞食日月之天狗,祭之所以祈免日月之灾欤?……又《地官·鼓人》:“救日月,则诏王鼓。”弓矢以射之,鼓以震惊之,则古人果即以为食之者为天犬乎?录之以备一说。*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三《交食谱》,中国书店,1980年,下册第2-3页。
董氏以甲骨犬祭文而参姬周救日月之礼,疑天狗食日月传说在殷商时就已出现。赵容俊承其说,以“商代甲骨文的食字为有盖之食物,使用为吞食某物之意义,并且以食字表示天文日月的蚀象”为佐证,得出“后世天狗食日与月的传说,以及用嘈喧声响以驱逐天狗的迷信,商代可能已存在”的结论。*[韩]赵容俊著:《殷商甲骨卜辞所见之巫术》,中华书局,2011年,第142页。
两位学者的推论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他们提供的史料只可推出商周时有救日月之传统,有日月为“物”所食之观念,然不可证此物即为天狗。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文献可以证明食日月之天狗形象在先秦就已存在。在汉代的传说中,食日者为三足乌,而食月者为虾蟆。
《史记·龟策列传》云:“孔子闻之曰:‘日为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乌。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虾蟆。’”《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高诱注:“踆,犹蹲也,谓三足乌。”又《说林训》云:“月照天下,蚀于詹诸”。*日中乌鸟、月中蟾蜍的形象可见于汉画,参侯良:《尘封的文明:神秘的马王堆汉墓》,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6页。承周言师提醒,东汉画像石有三足乌负日,月中有蟾蜍的图像,象征日月交食。见《南阳汉代画像石墓》,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192-193页。《论衡·说日篇》:“儒者曰:‘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此说至唐宋仍然流行。*见马杰:《食月传说探源》,载《文艺生活》2011第4期。关于蟾蜍食月在唐代的文化意象,可参葛景春:《李白与唐代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3-214,226-227,230页。又古代只有虾蟆食月说,而无食日之说,陈遵妫《日食简说》第三章《古代的日食传说》(正中书局,1941年,第10页)将其混为一谈,实误。袁珂引虾蟆食月之史料,认为“天狗食月盖后起之说”,*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465页。王孺童于《百喻经译注》中亦征释典而言“中印古时皆谓‘虾蟆食月’,而非‘狗食月’”*王孺童:《百喻经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327页。。
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证》“天狗食月”条下云:“昭人言月食曰天狗食月,此古传说之遗也,见《史记·天官书》,惟食月之天狗指月中凶神。”*姜亮夫:《姜亮夫全集》第16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按,“古传说”盖即《史记正义》所谓“太白五芒出,早为月蚀,晚为天矢及彗。其精散为天杵、天柎、伏灵、大败、司奸、天狗、贼星、天残、卒起星,是古历星。”姜氏之论有两点可商,一、太白五芒出为月蚀,非后世所谓“月食”,而是属于月星相犯的范畴。《开元占经》卷十二有“月与五星相犯蚀”一节,即专论此种情况。王童孺亦考云:“‘天狗’犯月或食月,与‘天白’犯月同为星象,非后世所谓之义。”*《百喻经译注》,第327页。二、“月中凶神”为一月之中的凶神,与月亮无关,是择吉术的用语。*见刘道超:《择吉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0页。以“月中凶神”而释天狗食月的学者很多,如李秀娥《中国的月神传说与信仰》,《历史月刊》1999年第140期。王家歆《谈天狗食日、食月的神话》,载《历史月刊》2008年第249期。当然,天狗星犯月的星象也许就是天狗星食月传说的原型,故而“古传说之遗”的说法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值得注意是,辽代王鼎《焚椒录》记述了辽后萧观音母耶律氏梦月坠怀又为天狗所食的故事。有学者将天狗食月的源头追溯于此,认为“宋初天狗食月的信俗已很普遍。”*见吴裕成:《十二生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第172-173页。又可参赵伯陶:《大话十二生肖》,齐鲁书社,2004年,第204页。这个说法还有商榷的必要。目前没有第二条史料提到宋或宋之前有天狗食月的传说,故此为孤证。此外,我们可以思考的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耶律氏梦中的天狗食月并非是当时的“信俗”,而恰好是特殊的个案。上节已经论述到宋时就已经存在天上之狗的形象,而这里为天狗所食的“月”是否和九头鸟之头一样,只作为飞天之天狗的一个注脚,并不能引申为当月食发生时,人们普遍相信食月者为天狗呢?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记述首先给出了天狗食月的意象。
食日月之天狗最迟至明代已经出现。如刘炳《承承堂为洪善初题》云:“天狗蚀月岁靖康,血战于野龙玄黄。”*(清)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九,中华书局,2007年,第2册第622页。虞淳熙《答朱太复》文曰:“谚云天狗蚀月。”*(明)虞淳熙:《虞德园先生集》卷二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3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36页。以上两证皆为天狗食月之例,兹再举明人写日食之佳作。罗洪先《即事》二首其一:
今年三月日食既,愁云黯黯风摧地。稚子悭呼新月生,行旅狂奔暮雨至。父老招予且指示,天狗凶猘恣吞噬。寒精闪闪不受降,欲灭未灭两争势。袒跣堕冠仰天视,残星三四如相避。便欲伐鼓集村市,缴弓注矢快殱殪。天宇沈沈高莫攀,反袂无声掩双涕。*徐儒宗编校:《罗洪先集》卷二十七,凤凰出版社,2007年,下册第1069页。
从“父老招予且指示,天狗凶猘恣吞噬”句可看出当时食日之天狗已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如今论天狗食日月传说者大多引少数民族之口述整理材料,其实自明以后提及此说的文献甚夥。如《雅州府志》卷二芦山县“姜城夜月”条载姜维祠前有“天狗食月”石,“形以伯约中秋遇害邓艾锺会,如天狗之食月。”*(清)曹抡彬、曹抡翰:《雅州府志》卷二,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64页。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二十五《月食词寄徐公三首》其三,诗云:“天狗垂涎时,饼饵视明月”*(清)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二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6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42页。等等,不烦备举。
根据上文的考证,至少在宋之前,虾蟆食月与三足乌食日的传说一直为人们所言说。天狗食月的意象在宋代已经出现,但天狗食日月传说的广泛流传最迟可推至明朝。有很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比如促使传说转变的原因是什么?上文第二节描述了宋以后广泛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天狗异兽,它是九头鸟的克星,在天宫中充当守卫,并被刻到墓地华表上,也许也是作为守卫的象征。它会不会就是吞食日月的天狗,而分开叙述仅仅意味着把同一种异兽的不同内涵加以区分呈现出来?毫无疑问的是,食日月之天狗形象的出现绝非朝夕之事,而是有“天狗”层累的文化内涵作为基础。当古人在月食之夜,指着想像中的天狗奔走号呼,大多数人或许并不会意识到,这背后有如此错综复杂的渊源。
[责任编辑刘宗迪]
Exorcism, Flying, and Eating the Moon: Heavenly Dog as aMonstrous Animal in Ancient China
LIU Taiting
In ancient documents, as amonstrous animal, heavenly dog often mixed up with Sirius. In examining the meaning of heavenly dog,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how people accept and rationalize this idea. Stories that heavenly dog ate sun and moon were already popular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was not just a funny story for amusement. Warning the heavenly dog and saving sun and moon did not develop into an interesting game as the boat racing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t was still generally believed even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that heavenly dog caused the eclipses of sun and moon, leading the feeling of fear.
Key Words:heavenly dog; monstrous animal; object divination; eating the moon
作者简介:刘泰廷,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