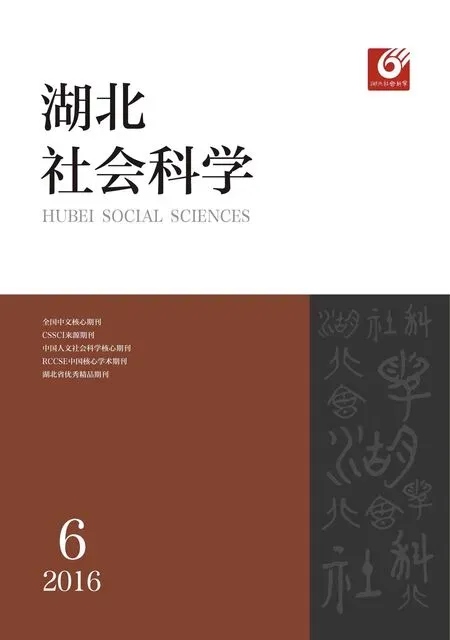对价值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续思
——基于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视角
2016-03-14闫艳
闫 艳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对价值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续思
——基于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视角
闫艳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的逻辑起点,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对价值的界定和理解方式在哲学界早已饱受诟病。从马克思交往实践观这一视角出发,价值不仅是一个表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范畴,也是表明主体与主体关系的范畴,是这两种关系的产物。马克思交往实践观很好地揭示了“客体满足主体需要”、“主客体关系说”的价值内涵对人的拒斥和消解,还价值以“属人性”——价值就是人的价值。依此,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的“术语体系”和“解释框架”都值得商榷,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确切的表述应是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是否有利于价值的开发和提升是评价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的根本标准。
马克思交往实践观;价值;类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
价值问题乃至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搞不清,不仅影响和动摇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更会降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理论品质和学术品位。
一、对学界普遍使用的“价值”概念界定的质疑
价值是一个被广泛使用而又含义非常复杂的范畴,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至今人们也未能给价值下一个全面、简明且没有争议的定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在阐述对价值内涵的理解时往往引用和参考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阐述的观点。“‘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它是“人在把成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进行估价,赋予它们以价值或使它们具有‘价值’属性。”[1](p162)并据此得出结论,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观点表明,价值产生于人与外物的关系。事实上,学者们引用马克思的这两句话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这两句话摘自马克思晚年写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详见下文:
“如果说,‘按照德语的用法’,①正是由于没有特别留意这句马克思对瓦格纳的讽刺,使一些人误读了马克思的原意。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而‘价值’的其他一切形态,如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只不过是这个概念的属概念。一位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自然愿望’是,从某一个‘概念’中得出‘价值’这一经济学范畴,他采取的办法是把政治经济学中俗语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按照德语的用法’改称为‘价值’。”[2](p406-407)
“但是瓦格纳先生想使我们和他自己相信,他并没有给予同样内容的东西以两个名称,而是相反地,从‘财物’的规定上升到与它不同的、更为成熟的‘价值’的规定,而他达到这一点的办法只是用‘或’‘财物’来代替‘外界物’,——可是这个过程又为他用‘或’‘外界物’来代替‘财物’‘弄糊涂’了。他的这种混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迷惑了他的读者。他同样可以采取下列办法把这种‘绝妙’推论颠倒过来:人在把成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作为这种满足需要的资料,而从其他的外界物中区别出来并加以标明时,对这些物进行估价,赋予它们价值或使它们具有‘价值’属性;这同样可以这样来表达:他赋予它们以‘财物’这个属性作为特殊的标志,或者把他们当作‘财物’来评价和估价。因此,‘价值’,或外界物,就被赋予‘财物’的概念。这样,就从‘价值’的概念中‘推论’出‘财物’的一般概念。所有这类推论的目的只是回避作者不能胜任的任务。”[2](p409-410)
对于学者们经常引用的这两句话,只要细心研读,就不难发现这两句话是马克思对瓦格纳错误观点的概括和引述,但却被一些学者误认为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犯了与阿·瓦格纳这类“德国国粹教授”一样的错误,即“把通常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叫做‘价值一般’或‘价值概念’”。[2](p411)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反复强调:“这个德国人的全部蠢话的唯一的明显根据是,价值(Wert)或值(Würde)这两个词最初用于有用物本身,这种有用物在它们成为商品以前早就存在,甚至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但是这同商品‘价值’的科学定义毫无共同之点。”[2](p416)而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中,马克思也讥讽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他们认为“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3](p101)实际上,马克思讲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就商品的二重性而言,所谓商品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一般的无差别的社会劳动,而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指商品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因为学界一直存在对马克思价值内涵的误读,用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概念界定价值,导致到现今为止,教育界(包括德育界)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对价值的概念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价值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1](p162)“价值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与作为需要对象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4](p171)“价值是对主体的效应,或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意义)”[5](p168)等偏狭理解上,亦即仍然从“客体满足主体需要”、“主客体关系”模式来定义价值。抛开“价值不仅是‘满足需要’的问题,而且包含‘衡量需要’的问题”[6]不说,仅就“主客体关系”模式而言,赖金良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当主客体关系理论被普遍化为一种方法论模式,被广泛推广或运用于包括价值论研究在内的哲学各学科领域时,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或后果决不能低估,而其中最为突出、最为严重的,便是它在方法论上对人的拒斥和消解。”[7]他认为,“主客体关系说”只能很好地说明客体的价值,却很难充分说明主体的价值。价值理论的轴心概念应该是“人”,用抽象的“主体”概念取代人,合理性是很难想象的。同时,用“主客体关系说”来界定价值还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将人降格为“客体”的事实。如有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客体关系说“在说明一种手段价值时显得游刃有余,而在说明一种目的价值时就显得力不从心。”[8](p51)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中早就揭露过人被“客体化”、被“物化”,即把人单纯当作“工具”、“手段”的危害,他指出:“工人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来说是没有目的的。”[9](p432)对于这点,我们并不难理解。在现实生活中,想象我们在做一件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或工作)是出自我们的本意,是我们自觉自愿的,哪怕付出再多的辛劳我们不仅不会抱怨,反而会油然而生出一种成就感、满足感。反之,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言行是被迫的,是不自由的,或者充当了被他人(社会)利用的“工具”,那么不仅会产生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精神上和行为上的“颓废堕落”,而且更严重的是激发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从这个方面来讲,“人被客体化”是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和谐乃至社会不和谐的一个显性因子。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文科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中在涉及价值内容的有关论述时,指出“价值是对人而言的”,“价值是事物或现象(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事物或现象)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是其对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好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10](p305)此价值定义虽然成功规避了“人被客体化”的风险,但这里的价值仍然指的是物或现象的“使用价值或效用价值”。所以,该教材在界定人的价值的概念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认为“从根本上说,人的价值是一种创造价值的价值。”[10](p139)“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所规定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或意义,即为人的价值。”[10](p136)
综上,单纯从“客体满足主体需要”、“主客体关系”模式来定义价值面临种种诘难。哲学巨擘张岱年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撰文指出:“人类的价值”是不能用“需要—满足”等于价值的简单公式来说明的,而应从“人贵于物”的意义上,也就是“人类具有其他物类所未有的优越性质与能力”上理解“人的价值”。[6]由是观之,价值是“属人”的,应从人出发来界定价值。“只有通过对人本身包括人的生命存在、活动及其意义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究,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价值的起源、实质、类型、特点以及价值的发展变迁等问题。”[7]
二、马克思交往实践观视角下对价值内涵的解读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殊胜之处恰恰体现在用人的方式来思考人,将人还原为人。这无疑为我们理解并重新界定“价值”内涵提供了最契合的视角和理论依据。在对待人的问题上,马克思既反对历史唯心主义者脱离现实的生活条件,奢谈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也反对抽象的经验论者撇开人的社会特性奢谈人的本性。马克思始终视人为“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p525)是“从事活动的人”。人类的活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9](p540)显然,人改造自然,凸显的是生产力,是生产实践;人改造人则主要是通过交往实践来完成的。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生产实践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他亦肯定了交往实践之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对此他有很多表述,如:“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9](p520)“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9](p724)人们从事的生产运动,“是由于交往的扩大才获得了动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9](p560)“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11](p515)……可以说,正是因为马克思将交往与生产、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将交往的普遍性的空间拓展至整个世界,才为人类找到了一条通向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之路。因此,撇开人的交往实践这个重要的视域,撇开人的“交往的力量”这个重要维度,仅囿于在“主体—客体”生产实践框架中谈价值问题,到头来难免还会遗落了人。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实践展现的是“主体—客体—主体”关系。他指出:“每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作为这另一个人所需要的客体的所有者而出现,这一切表明:每一个人作为人超出了他自己的特殊需要等等,他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12](p195)“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9](p533)此外,马克思认为,交往是一个过程。从个体交往来看,交往的过程是多级主体的肉体和精神的相互作用、相互创造的过程。个体的本质也是在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变化不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交往内容、形式、手段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交往是生产性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而不是复制性的、机械性的、重复性的活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也说明,人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人、虚构的人、静止的人、概念化的人,而是彰显了“交往的力量”的“现实的人”。这种“现实的人”是具体的人、历史的人、始终处在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的动态关系中,因而可以说“人始终是未完成的、未定型的、未达到终点的,或者说,人总是处在一个开放的、充满可能性的、向着未来的过程之中。”[13](p37-38)这个过程也凸显了人的二重性特质,即人既是其所是,亦是其所非。或者说,人自身是“实然存在”与“应然存在”的二重化整合。人作为一种实然存在和应然存在既表现出实然向度(社会的给定性)又表现出应然向度(不断创造新的需要超越自身)。实然性是所有生物的特性,而应然性是独为人所特有。整个人类史就是人不断从“实然存在”向“应然存在”转化的历史,即“人成为人”的历史。赖金良教授认为,人的“实然存在”即“是人”是一个事实,而人的“应然存在”即“成为人”则是不断超越和实现自身的过程,体现出人的价值。因此,价值在“‘人成为人’的自我创造、自我超越、自我实现过程中”。[7]对此观点,笔者颇以为然。人是双重规定,一方面是既定的、给定的,一方面是创造性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必须思维,一方面是为了把那个只用精神、思想才能驯服的肉体控制起来,另一方面,是为了能实现他作为创造者和创造物的反思规定。”[11](p328)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哲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反对用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来界定价值,尝试摆脱“劳动价值论”而从“哲学价值论”视野给价值一个全新的定义:如万俊人教授认为“价值作为一种‘属人的’或‘人为的’、‘合目的性的’意义,体现着人类的崇高理想和永恒追求。”[14]何中华教授认为“所谓价值,既不是有形的、具体的存在所构成的实体,也不是客观对象与主体需要之间的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而是人类所特有的绝对的超越指向。”[15]郁建兴教授认为“所谓价值,就在于人的类特性、社会性,就是人的理想性、超越性。”[16]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虽然对价值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即:价值就是人的价值。寻此思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笔者在此也大胆尝试给价值一个界定:所谓价值,是指基于实践(主要是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基础上人所具有和表现出的超越性和人道性意义。超越性主要指人在各类实践中表现出的目的性、理想性和创造性等特点,人道性则主要指人在交往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人的生命(也包括其他物种的生命)、种族、人格、尊严、自由、权利等的尊重和反思,这种尊重和反思既指向自身,亦指向他人。①这样,即便一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甚至丧失了生活能力的人也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即使他在生产实践中丧失了其价值存在的前提,但是在交往实践中(特别是近亲关系中)他仍被需要,被珍重,有其存在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为人道价值或精神价值。此价值概念界定表明:人即价值本体,人的行为即价值源泉,人的发展即为价值结果;价值包涵人的精神(意识)与生命的双重发展,包涵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发展;实践是价值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实践(尤其是交往实践),就无法形成“主体—客体—主体”关系,也就无法形成价值关系。同时作为“价值一般”,此概念的界定也涵盖了一切价值形态。如按价值主体划分,价值可分为个体价值、社会(群体)价值、②鉴于社会是由具体的、现实的人构成的,且这个集合体的人(群体或团体)有某种同一性或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群体的价值”也可表述为“社会的价值”。人类(类)价值;按价值结果指向不同,价值可分为人的自我价值,即人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超越性和人道性意义或作用的结果主要指向自身;人的社会(群体)价值,即人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超越性和人道性意义或作用的结果主要指向社会(群体);人的类(人类共同体)价值,即人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超越性和人道性意义或作用的结果主要指向全人类。3○在此,人的社会价值和类价值,其结果虽然不指向自身,但这种价值仍是人的固有价值的体现,不能理解为“工具价值”或“使用价值”。价值是“属人”的,“工具价值”、“使用价值”是“属物”的。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漫长的发展时期,人被物化、人的价值沦为“工具价值”或“使用价值”的现象是存在的,并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但存在的并不一定是合理的,这种“实然”最终会被“应然”所代替!○按价值体现的社会领域不同,价值可分为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道德价值、法律价值等,表现出价值的多样性。这些价值的存在正是人在不同领域发展中的规律性本质存在。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划分种类,由于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故不赘言。
需要提及的是,龚群先生在《论价值与价值关系》(2013)一文中认为,价值不仅是一个表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范畴,也是表明主体与主体关系的范畴。在这一点上,笔者和龚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价值问题的本质从来就不是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9](p184)“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9](p247)龚教授在其文章最后也给价值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价值是在主客关系和交互主体关系中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两类关系的产物。”[17]对此界定,笔者不能完全认同,笔者对此概念的主要诘问,龚教授恰恰在对价值界定的引注中已经提及,即此定义“没有解释从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相区分的角度所提出的应然或‘应当’的问题(即从我们的观点看,相对独立于事实领域但与事实领域有联系的‘应当’问题)。”[17]显然,龚教授也觉得这个价值定义略有“缺憾”,因此只好表示:“虽然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发现了价值领域,但主客体关系与交互主体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研究价值的进路。”[17]笔者在此不揣浅陋地认为,本文对价值的界定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龚教授价值定义的“缺憾”,既体现了“关系说”,又体现了事实与价值范畴的区别。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1.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表述的商榷。
令人颇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并未充分反映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研究中来,正像我们上面提及的,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对价值的定义仍然逃不出“主客体关系说”,寻此逻辑,教育价值被界定为“是指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主体的人的需要与作为社会实践客体的教育现象的属性之间的一种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4](p9)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一般被理解为“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和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效益关系。”[18](p29)“是人和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发展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1](p162)“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及其属性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的满足关系。”[19](p72)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鉴于学界对价值的误读在先,所以上述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界定无论表述得如何“完美”,也难逃逻辑上致命的错误。
那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价值呢?依据哲学价值论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笔者对价值的界定,价值就是人的价值,人以外的物或现象并没有价值①没有价值,不等于没有存在的必要和权利,比如自然界(动物、植物、各种微生物等),本没有价值,但自然界本身仍有不依赖人的存在而独立存在的权益。对自然界权益的尊重恰恰彰显出人的价值,即人的生态价值。或无所谓价值,只不过当物或者某种现象与人发生了“关联”,这种物或者现象对于人就有了价值。譬如自然界中的风,本无所谓价值,没有人的存在它依然或“款款而来”或“狰狞而去”,只不过和人发生关联,它产生了“价值”,当然,聪明的读者一望便知,这里的“价值”只是一种使用价值或效用价值。它属于价值一般的局部形态,是指外界物(现象)对价值实现的效力和作用,表示“物为人而存在”。这个效用价值有大小、有正负,全凭它对价值实现程度的“效用性”。人也正是借助于外界物或现象的“效用价值”而实现和彰显自身的价值的。这样一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确切的表述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价值的某(几)方面开发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才显露出它的某(几)方面的效用价值。那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呢?简言之,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对价值开发和提升的效用性。以“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为例,科学的表述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效用价值”,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对人的生态价值开发和提升的效用性。而生态价值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对生态(自然环境)的合理利用和改善所表现出的超越性和人道性意义。由此来看,对价值的澄明“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无疑动摇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的“术语体系”和“解释框架”,但正如本部分开头所讲,价值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含义,在生活中也有被滥用或泛化的情况,譬如人们将价值和“财物”混淆,认为“车子、票子、房子”就是价值;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即“有用性”混淆,认为某种事物或现象有价值是因为其“有用”。这种生活中价值概念被“误读”、“泛化”、“滥用”的现象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学术研究必须有严谨求实的态度和作风,不然,直接的后果是降低自身的学术魅力和理论品质。
2.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的分类。
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的概念是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分类的出发点,此外,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的分类还要结合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属性和活动的特点,并参照前文对价值的分类。正如前文所描述过的,价值有很多分类法,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直接面对的就是人,主要是个体和社会(群体、组织、集团、共同体等的代名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从作用的主体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价值开发和提升的效用性,即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效用价值。其二,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体价值的开发和提升的效用性,即思想政治教育个体效用价值。其中,思想政治教育个体效用价值依据个体价值层次不同又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个体的自我效用价值、个体的社会效用价值和个体的类效用价值。
鉴于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个体的类效用价值”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在此尝试做一些简单、肤浅的阐述。思想政治教育个体的类效用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类价值的开发和提升的效用性。“人的类价值”按照本文之前的界定,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超越性和人道性意义或作用的结果主要指向全人类。它强调人的实践活动要拥有全球视野,超越个人和群体的狭隘视界,关注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发展和全球的利益。因为,人作为“‘超物之物’,他不只是与一切其他之物相区别,更重要的是与一切其他之物还有着普遍同一和本质统一的一体性联系,而这正是人之为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20]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曾强调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指出在共同面对全球性问题和世界政治、经济等复杂形势时,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都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党中央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了“非此即彼、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二元逻辑;体现了个体与他人、群体的共在,民族与世界的共在,人与环境的共在等多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它充分认识到“个人—集团—民族—国家—类存在”之间的彼此递进与相互包含关系。[21]依马克思“社会形态论”观点,从“人的依赖形态”(群体本位)到“物的依赖形态”(个体本位)再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形态”(类本位)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向。所谓“类本位”,“在这里不过是指,这时的每个人都已自觉为人,把个人存在纳入他人本质,也把他人存在纳入自身的本质,即各人都以人为自我主体的人的自为存在状态”,“它体现的就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内在统一的一体性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必须经过彼此分化的过程,而后在更高的基础上才能形成。”[20]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3](p97)由此可见,“类本位”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它是人的类价值不断开发和提升的结果。因此,实现、彰显人的类价值无疑是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最高层次的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也要致力于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不断提高人的觉解程度,使人逐渐从自然境界(求本能的善)、功利境界(求个体的善)、道德境界(求社会的善)跃升到冯友兰先生所倡扬的天地境界(宇宙的善),彼时,即人的类价值将充分彰显,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再是一种乌托邦。
3.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的评价标准。
讲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离不开价值,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价值不断开发和提升的过程。如果不能使价值得到有效开发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也就荡然无存。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是人,人的存在具有实然存在和应然存在双重属性,人的这两种存在样态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使人获得现实的、既定的精神文化属性,使人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适应社会的现存状况。另一方面,也即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更深层含义在于它要承担起赋予人所独有的应然性的使命,即着眼于人的应然性特点,使受教育者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有担当,勇于超越,热衷于意义世界的建构,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要能够不断开发和提升价值,使属人的这种特性生发出来,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因此,是否有利于价值的开发和提升无疑是评价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的最重要标准也是一条总体标准。对此标准,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相对于“授业解惑”、解决“以何为生”的各类知识、技能教育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传道解惑”,更侧重和强调“为何而生”。因此,其效用价值最直接地体现在使人在精神领域或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得到增值,进而在正确的精神理念和精神动力的作用下,间接地使人在其他领域的价值得以增值。故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的评价标准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不断拓展人的精神领域的广度、深度和高度,使人的人格愈发高尚、精神视界愈发敞亮,不断澄明、觉解和跃升,最终成为真、善、美的统一体。
其次,价值在人(类)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总是体现为正价值,如一些战争狂人、恐怖组织或致力于人兽杂交研究的所谓科学达人等,他们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所谓“超越性”恰恰是反人类的。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的评价还要看其能否校正错误价值取向,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价值共识。“价值共识就是对不同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积极合理因素的某种认同。例如在当代,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和谐等观念就是一些价值共识。”[22]这些主流价值和价值共识将有利于人的价值的开发和提升向着不仅对自身而且对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有利、有益的方向发展。
复次,就像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大小不能简单分个“伯仲”一样,在评价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时,也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个体效用价值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效用价值谁优先的原则,这只是出于研究需要的一种分类法而已。因为,“在人类共同体内部,不同个人之间永远是相互依赖的,没有任何人是绝对独立、自主的;人类作为一个类或物种也没有绝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人类依赖于地球的生态健康,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其他物种的生存(如各种农作物、家畜以及各种野生动植物)。”[23]更何况马克思也一向反对“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9](p188)社会就是人的社会。而从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微观层面来讲,评价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既要看其对受教育者的价值增值,也要看其对教育者的价值增值,要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价值增值,实现共同体所有成员心智图式与实践方式的同步优化与精化。
再次,价值的增值一般意义上来讲是人的个体价值、群体(社会)价值和人类价值的辩证统一的增值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人、群体、社会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在实现各自的价值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体、类)、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此时对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的评价就要看其能否平衡和协调诸方面的关系和相互利益,使价值“总和”趋于“最大化”。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实际上主要表现在使人从“是其所是”不断发展为“是其所应是”的过程中,亦即“成人”、“树人”的过程中。因此,判断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的大小需要有过程思维。要将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价值放在个人的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评判。
[1]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王坤庆.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价值论视角的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张澍军.德育哲学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张岱年.论价值的层次[J].中国社会科学,1990,(3).
[7]赖金良.哲学价值论研究的人学基础[J].哲学研究,2004,(5).
[8]兰久富.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美]赫舍尔.人是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14]万俊人.真理与价值及其关系拓论[J].人文杂志,1992,(6).
[15]何中华.论作为哲学概念的价值[J].哲学研究,1993,(9).
[16]郁建兴.关于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商榷[J].哲学研究,1996,(8).
[17]龚群.论价值与价值关系[J].苏州大学学报,2013,(6).
[18]罗洪铁,董娅.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9]周中之,石书臣,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探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高清海.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1).
[21]闫艳.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交往取向之析[J].求实,2014,(11).
[22]陈先达.论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J].哲学研究,2009,(4).
[23]卢风.“内在价值”概念再检讨[J].道德与文明,2012,(5).
责任编辑 张 豫
G41
A
1003-8477(2016)06-0179-07
闫艳(1973—),女,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美国加州克莱蒙研究生大学访问学者,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已出站)。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3M542364);天津市高校创新团队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013-ZXCX1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