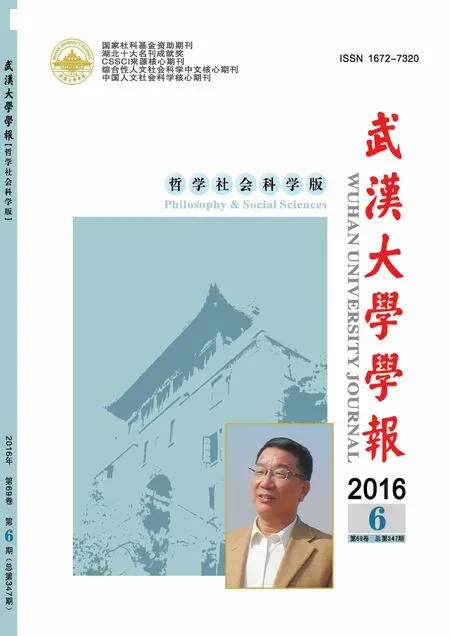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中居民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克服
2016-03-13张莉萍张中华
张莉萍 张中华
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中居民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克服
张莉萍张中华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垃圾围城”现象及其引发的环境、社会问题日益凸显,通过垃圾源头分类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垃圾分类工作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即大量居民出于怕麻烦、费时间等原因,不按照规定进行源头分类投放。只有将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第三方强制执行、选择性激励、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利用社会资本等四个途径有机结合,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政府应切实担负起顶层设计和率先垂范的责任,特别注重推动垃圾分类中社会信任的建立,培育和有效利用社会资本。
生活垃圾源头分类; 集体行动; 社会资本; 城市化
我国大规模、高速度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种种“城市病”。“垃圾围城”现象及其引发的环境、社会问题便是其中之一。通过垃圾源头分类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是解决城市生活垃圾问题的重要途径。垃圾分类涉及每一位城市居民,需要居民的积极参与,形成集体行动。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却面临着居民参与不足的“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垃圾分类行动难以推进。因此,我们从集体行动困境理论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问题,以期为垃圾分类困境寻求解决之道。
一、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面临的困境
全球城市化率的迅速提高,使得城市生活垃圾的产量也快速增长。为了治理城市垃圾,许多国家都将垃圾源头分类作为一项重要措施,我国也不例外。但是,垃圾分类在我国却面临着重重困境。
(一) “垃圾围城”问题与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重要性
生活垃圾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30多年来,随着我国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固体废弃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城市产生并在城郊聚集,导致“垃圾围城”问题日益凸显。城市生活垃圾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管理,不仅会污染环境,降低我国城市和郊区的环境质量,而且还会影响城市的和谐及可持续发展——自2005年以来,由垃圾压缩站、填埋场、焚烧发电厂的建设和污染引发的抗议行动和社会冲突事件几乎每年都有,很多垃圾处理处置设施项目的建设,都陷入了“政府决定建设——居民抗议——项目搁浅”的反应模式,使得城市生活垃圾治理面临更多困难。
城市生活垃圾是固体废弃物的一部分。目前,世界普遍接受的固体废弃物管理原则为“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全过程管理。垃圾源头分类可以有效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也可以为后续的垃圾处理减轻压力、节约成本,因而成为许多国家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重要手段和环节之一。目前,垃圾分类已经写入了世界垃圾治理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之中,如日本的《废弃物处理及清扫法》、德国的《包装条例》、我国台湾地区的《废弃物清理法》、《台北市资源垃圾强制分类回收管理办法》等,并形成了完善的政策体系。在当前我国城市化率不断提高,而“欢迎建设,但不要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情结”使得垃圾处理设施选址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垃圾源头分类实现垃圾减量就更为重要。
(二) 我国垃圾分类试点进展及困境
2000年,我国开始实施垃圾源头分类试点。从2000年至今,尤其是2011年以来,我国的垃圾分类试点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制定和实施了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垃圾分类投放和运输的基础设施设备配置逐步完善,垃圾减量也在上海、杭州等城市取得一定成效。然而,从全国范围内看,我国垃圾分类试点进展并不顺利,收效不明显(孟思奇,2014),有的城市甚至曾中途放弃,或者从源头分类转为末端分类(蓝辉龙等,2014)。“从公众感知判断,垃圾分类似乎每次都声势浩大地发生在身边,却一次次无疾而终。”(陈沙沙,2014:69-71)而导致垃圾分类试点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就是居民未能有效参与。
垃圾分类是一个由多个环节构成的过程,其中,居民的分类投放是第一步,是整个分类过程的基础,而试点的情况表明,居民不按照规定进行分类的情况非常普遍。例如,2010年,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在600个试点社区1.3万多户居民中进行的垃圾分类调查显示,试点社区当年的生活垃圾虽然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但居民投放后由保洁员和垃圾分类绿袖标指导员二次分拣的约占75.6%。两年后进行的回访显示,情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郑磊,2014)。2012年,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对北京6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地调研发现,在检查的240个厨余垃圾桶中,39%的厨余垃圾桶内垃圾完全混合,完全分开的厨余垃圾仅占1%(熊孟清等,2014)。上海市在总结生活垃圾分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4个原因中有两个涉及居民:一是居民意识与工作推动脱节,居民分类习惯尚未养成,二是社区居民主体作用发挥不足*徐志平:《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成绩与不足》,载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网站,http://lhsr.sh.gov.cn/sites/wuzhangai_lhsr/neirong.aspx?ctgid=3a222e8f-e1e5-4737-8697-41de8c789e31&infid=e3d94cfe-345c-4ac7-8177-e6f28f1943db,2015-01-12。。
二、 集体行动理论视角下的垃圾源头分类问题
我国垃圾源头分类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居民参与不足。其中的原因,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垃圾分类是一项集体行动,从集体行动困境理论的视角进行系统观察,将有助于深化对这一困境的理解,进而找到根本的解决途径。
(一)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困境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居民垃圾分类参与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曲英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分析得出了影响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意向的7个主要因素,即感知到的行为障碍、环境态度、主观规范、公共宣传教育、利他的环境价值、利己的环境价值和感知到的行为动力,并指出,利他的环境价值越高、感知到的行为动力越强、居民的环境态度越积极、主观规范越强、公众宣传教育接受的越好,居民越有可能实施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曲英,2011:42-51)。鲁先锋从环境心理学理论出发,将影响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因素分为内在因素(个人习惯、环保意识、“经济人”理性等)和外在因素(法律制度、部门管理、宣传教育等),认为提高城市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需要法律规导、政府管制、经济惩罚等外压机制与思想教育、经济补偿、舆论支持等诱导机制的共同作用(鲁先锋,2013:86-91)。瞿利建等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影响因素分为外部条件和内部动机,其中外部条件包括分类收集点的远近、分类投放设施配置、分类知识的明确指导、宣传教育及参与氛围等;内部动机包括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环境认知、相应的法律规范、主观规范、心理因素和金钱报酬需求等(瞿利建等,2013:25-29)。田凤权则将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分为制约因素和驱动因素两大方面,前者包括行为控制、法规与道德约束、环境知识、环保意识、负面干扰五个部分,后者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宣传导向、行为动机、政策法规五个部分。其中,行为控制、法规与道德约束两个主因子是制约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两个最主要因子。就“行为控制”来看,阻碍着市民积极参与并持之以恒的因素多是市民自身的原因,没有时间和精力、占用过多的家里空间等因素使市民不能坚持对生活垃圾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与投放(田凤权,2014:178-180)。
现有的对于居民参与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诸多因素,颇具启发意义。不过,“垃圾分类及分类处理的基本定性是一种建立在个体行为基础上的社会行为”(熊孟清等,2011),社会行为需要社会成员的集体行动,而目前的研究中,更多地从个人行为、法律规范与制度保障等角度进行了论述,尚缺乏从集体行动的视角进行的系统考察。相关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的集体行动往往会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从集体行动困境的角度来考察我国城市居民垃圾源头分类的问题更有助于从根本上寻求解决之道。
(二) 我国垃圾源头分类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居民集体行动困境
人类在组织集体生活、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会面临“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2014:2)的“集团行动困境”,其核心问题是“搭便车”。很多学者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对这一困境进行了分析,如公用地的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等。这些分析表明,如果每个人能够合作,则人人都会获得利益,但在缺乏协作和可信的相互承诺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选择背叛对方,结果无法达成合作(燕继荣,2015:序言3)。
就垃圾源头分类而言,良好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带来的是更好的城市环境、全社会的资源节约和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因而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共产品;垃圾源头分类,是垃圾管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垃圾源头分类也是一项公共事务,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因此,垃圾源头分类同样面临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例如,在试点小区中,居委会、二次分拣员和部分居民可能会非常认真和积极地进行分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劳动,甚至有的志愿者宁愿自己掏腰包来设置设施为居民的垃圾分类提供方便,但更多的人,却不愿或不能做到分类投放——有的居民可能会认为垃圾源头分类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了个人的方便和利益而不去执行;而其他人为垃圾分类所做出的努力,带来的垃圾减量、资源节约、环境改善的好处,不参与分类的人也能够享受到,致使垃圾源头分类不能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而这一居民集体行动困境,正是当前我国垃圾源头分类面临的最主要阻力。
三、 我国垃圾源头分类居民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四种路径及其适用性
集体行动的困境客观存在,但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等垃圾分类做得很好的国家和地区的事实表明,对于垃圾源头分类的居民集体行动困境,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推动解决,从而形成集体行动的。那么,解决垃圾分类居民集体行动的困境,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对于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已有的研究主要提出了四种途径,即:第三方强制执行、选择性激励、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利用社会资本,这四种分析路径,在我国的垃圾分类中能否适用?
(一) 第三方强制执行及其适用性
作为最早面对集体行动困境的社会理论家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指出,要想维持社会内部和平和进行外部防御,唯一的道路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霍布斯,1985:131-132)。“利维坦”被学界视为强权国家,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公正无私而又强大有力的政府权力或公共权力(燕继荣,2015:序言3)。第三方强制执行,可以理解为由政府公共权力来对公众行为进行强制。
在世界范围内,尽管存在自愿进行垃圾分类的情况,但作为一种社会集体行为,则均为政府强制推行。强制的方式是制定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并严格执行。纵观垃圾治理成就显著的国家和地区,法律的强制力在推行具体政策和居民分类习惯的养成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日本垃圾分类成功的经验首先是制定了近乎“苛责”的法律,民众在长期法律约束和教育宣传影响下,将垃圾分类做到了极致。同时,行政的执行力也是必需的。我国台湾省台北市,1988年制定了《废弃物清理法台北市施行细则》,2001年3月和7月分别出台了《台北市资源垃圾强制分类回收管理办法》、《台北市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费征收自治条例》,实行“垃圾不落地”与“强制分类”政策,垃圾费随袋征收(钱胜、李炜永,2011:44-47);台北垃圾车由环境部门每日定时定点运营,居民错过了垃圾投放时间,需要自己将易腐烂的垃圾存储在冰箱,等待下一次投放。
综观当前我国关于垃圾分类的法律规定,多是宏观性的,责任不明确,操作性不强,对于垃圾必须分类的法律规定还没能起到约束民众的效果,需要进行改进。而相较于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强制执行可能更为困难。从宏观环境上来说,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着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很多事情在争夺着政府和居民的注意力,比如经济发展、公共安全、空气污染,交通拥挤,甚至垃圾焚烧厂的建立等等,与这些似乎“更为重要”的公共事务相比,在我国执法状况本就不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加强对尚在试点的垃圾分类的监督和执法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现实的。正如帕特南所评论的,强制执行方式的“困难之处部分地在于,强制执行成本太高。”“更为关键的是,公正的执行,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品,一样受制于它所致力于解决的基本困境。”(帕特南,2012:214)所以,如果法律法规本身不够完善,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制环境和足够的执法力量,仅靠政府和法律本身的强制力将很难实现对居民垃圾分类的约束。
(二) 选择性激励及其适用性
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只有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奥尔森,2014:34-35)。通过选择性的激励,那些没有为实现集体利益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组织和个人才会有所不同。奥尔森还指出,“这些‘选择性的激励’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就是说,它们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或者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奥尔森,2014:35)选择性激励,在对垃圾分类的管理中也较为常见。
1.负面激励的适用性
政府的强制执行,往往会与“消极的”负面激励相结合。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中,会规定不遵守分类规定的罚则。例如,日本《废弃物处理法》第25条14款规定:胡乱丢弃废弃物者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3万元);如胡乱丢弃废弃物者为企业或社团法人,将重罚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500万元)。法律还要求公民如发现胡乱丢弃废弃物者请立即举报(谢德良,2013:30-31)。在台北,如果居民不对垃圾进行分类,不但垃圾车会在收运时拒收,而且依据《废弃物清理法》第50条规定,要被处罚1200-600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000-30000元)。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负面激励法律规定和惩罚力度都不足,试点推行以来各地所规定的处罚措施几乎都是不了了之,难以对居民形成激励。2015年,广州和杭州等一些城市出台的关于垃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中,设置了具体的罚则,意在加强处罚的落实。不过,加强惩罚固然能起一定的作用,但可能带来的问题和存在的困难也不少,包括:容易形成对立情绪,尤其是在关于分类的指导不够,没有详细的操作指南的情况下,很难获得居民的认可;投放垃圾有时十分隐蔽,对于违规行为取证困难;执法力量有限,加上传统的“法不责众”的心态,难以形成现实的威慑力等。因此,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负面激励的效果并不乐观。
2.积极激励的适用性
通过积极激励方式来推进垃圾分类,往往会在垃圾分类推广初期被广泛采用,在成熟的垃圾分类制度中,也还会有诸如饮料瓶押金返还等激励措施。我国一些城市在利用垃圾分类激励机制上,更是结合最新的信息、网络技术,进行了很多的创新,例如上海的“绿色账户”、北京的垃圾智慧分类模式等。主要的做法都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居民信息与垃圾分类建立对应关系,对垃圾分类行为进行积分,居民用积分可以兑换各种奖励,如购物卡、手机充值卡甚至现金。
积极激励对于宣传垃圾分类、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分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资金支持的可能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在政府和企业的财力有限的城市,积极激励的空间比较小。其次是激励措施的可持续和连贯性问题,例如上海的绿色账户就存在条形码的及时补给问题和积分兑现很难的问题,消耗了居民的积极性*参见王玉华、林嘉:《垃圾分类推进,难点在哪里?——来自垃圾分类先行小区的报告》,载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网站,http://lhsr.sh.gov.cn/sites/wuzhangai_lhsr/neirong.aspx?ctgid=3a222e8f-e1e5-4737-8697-41de8c789e31&infid=9e713deb-9a70-4f51-92f4-5b34dba1cc68,2015-01-15。。第三是老年人对新科技的掌握困难。在家中负责垃圾分类的很多是老年人,但是像扫二维码这样的智慧分类方式,很多老年人掌握起来并不容易(贺勇,2015)。同时,积极激励措施只会对对激励措施有兴趣的人才起作用,很多居民会对这些措施无动于衷。
因此,在运用选择性激励时,应当完善激励的前提条件,如完善的分类设施、充分的分类指导等,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激励措施和奖惩力度——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选择性激励对个人偏好的价值要大于个人承担集体物品成本的份额,价值较小的制裁或奖励不足以动员一个潜在集团(奥尔森,2014:50)。
(三) 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及其适用性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之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摒弃了用国家控制和私有化解决“公地悲剧”的方法,提出了通过公众内部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通过对公共池塘资源情境中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制度方法的研究,奥斯特罗姆指出,要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集体行动问题,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即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相互监督问题(奥斯特罗姆,2012:49);她还从大量成功案例中归纳出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所共有的八项设计原则:清晰界定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和嵌套式企业(奥斯特罗姆,2012:208)。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理论,也蕴含了“多中心治理”的理念。
虽然垃圾分类一般都是政府强制推行的,但是,在推广分类和执行分类政策的过程中,各种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参与和自我组织却十分重要。在垃圾分类先进国家和地区,这些组织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德国,包装协会为解决厂家各自回收废弃包装的困难,建立了“绿点系统”,对减少包装垃圾、实现包装材料的分类回收和重复利用发挥了关键作用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纺织服装工业联合会等80多个行业协会、商会组织都不同程度地成为落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力量(陈秀珍,2012:69-72)。环保志愿者和环保团体在垃圾分类回收的舆论宣传、推动立法、监督监管等方面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台北的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就是台湾环保组织“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影响市议员的成果;在台北,仅慈济功德会就动员了6.2万多志愿者进行垃圾回收分类;居民小区的管委会作为对小区垃圾分类的直接管理者,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万建刚,2014)。
在我国的垃圾分类推广和实践中,也有许多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参与。例如,上海的“绿色账户”工程,就是由孔令韬和他的上海大学伙伴们共同发起的;达尔问环境研究所、中国零废弃联盟、绿色和平组织、宜居广州等非政府组织,在垃圾分类的宣传、实施方案设计、具体实施指导、调查研究和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着积极的行动;一些企业(如银行)加入了对垃圾分类的宣传和资助的行列;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等社区新兴营利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也为社区垃圾分类提供了服务和管理。但是总体而言,我国自组织的社会基础尚不充分,自主治理能力未能充分发挥,活动范围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在垃圾分类的自主组织和自我管理方面,我国还有赖于社会自治的推进和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
(四) 利用社会资本及其适用性
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以“社会资本”为基础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法,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帕特南认为,“集体行动的困境,可以通过利用外部的社会资本来加以克服”(帕特南,2012:218)。他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2012:216)。在帕特南看来,在所有社会中,集体行动困境都阻碍了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的尝试(帕特南,2012:228)。第三方强制执行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自愿性合作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存在。而人们之所以选择合作,原因首先在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稳定的信任关系使自发的合作成为可能。这一巩固的社会信任“能够从这样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帕特南,2012:221)。也就是说,由于社会成员之间关系密切,相互信任,从而形成了公民参与网络,而社会网络又使得信任得到传递和扩散;为了维护参与网络,人们培育出了参与过程中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和信任。并且,社会信任、规范、公民参与网络和成功的合作,是互相支持、互相强化的(帕特南,2012:232)。
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合作和社会信任的角度寻求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新途径,而纵观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垃圾分类历史,社会资本也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信任方面,政府不遗余力、持之以恒地宣传并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使社会公众能够感受到政府在垃圾分类中的决心和诚意,由此对政府产生信任。同时,政府还清晰、明确地公布每年生活垃圾具体的削减数量,使公众知晓自己所做事情的贡献,了解到政府和他人也在做,由此增加彼此的信任感。其次,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较完整的纵向和横向的参与网络。纵向上,建立了政府和社会构成的纵向参与网络,政府从分类知识的宣传、法律法规的完善、政策设计、制度建设到硬件设施等方面都竭力做好,以获得社会成员的配合。横向上,由居民、志愿者组织、企业组成的横向网络形成了合力,一起发挥作用。第三,在规范方面,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措施之外,这些地方还形成了无形的道德规范的压力,如果不按规定分类,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因而,社会资本的存在,不仅提高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垃圾分类社会民众的参与程度、合作程度,而且增强了法律执行效果,降低了法律、制度实施的成本,从而提高了垃圾分类的成效。
四、 结论与建议
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重要手段和环节。我们认为,垃圾分类是一种建立在个体行为基础上的社会行为,垃圾分类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因而会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从垃圾分类集体行动困境克服的视角进行系统的考察十分为必要。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垃圾源头分类的集体行动中,克服居民集体行动困境的四种途径在共同发挥作用。其中,强制、选择性激励、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更容易观察,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也更为显性,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分别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而丰富的社会资本是其他方案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其作用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但正是由于社会资本的作用不像其他方案那样显性和直接,容易被我们忽略。
因此,笔者建议:第一,政府应切实担负责任,加强垃圾分类政策的顶层设计。将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四种路径结合起来,全面改进我国垃圾源头分类的法律规范和政策设计,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垃圾分类相关的法律、制度,推动和鼓励社会的全面参与。同时,可以考虑在符合条件的城市适时结束试点,全面推行垃圾分类,从而为垃圾分类及相关激励措施的实施奠定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第二,政府应率先垂范,培育社会资本。正如马格丽特·勒维(Margaret Levi)指出的,应该重视政府在创造和积累社会资本方面的作用,“政府也可以是社会资本的来源,政策绩效能够成为信任的来源”(Levi,1996:45-55)。事实上,垃圾分类先进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固然有社会原有的因素(如日本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传统文化、德国人的严谨精神等)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对垃圾分类政策认真推行的结果。我们也应以增强政策绩效、建立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为突破口,创造和积累社会资本,为我国居民垃圾分类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而言,政府要严格执行垃圾分类相关制度,切实履行好自己在基础设施、分类运输和处理的管理等方面的职责,增加公众对垃圾分类的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个体、社区、社会组织、企业等共同参与的横向网络,各主体各尽其责,合力推进垃圾分类。一旦垃圾分类取得切实可见的效果,又会增进公众彼此之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反过来推动合作,从而形成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最终克服我国垃圾分类居民集体行动的困境。
[1]曼瑟尔·奥尔森(2014).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12).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3]陈沙沙(2014).14年,北京只多了几个垃圾桶.民生周刊,16.
[4]陈秀珍(2012).德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经验及借鉴.特区实践与理论,4.
[5]贺勇(2015).垃圾贴上二维码,分类能换购物卡.人民日报,2015-12-14.
[6]托马斯·霍布斯(1985).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7]蓝辉龙等(2014).破解垃圾分类:欲从源头分类转为末端分类.南方都市报,2014-06-10.
[8]鲁先锋(2013).垃圾分类管理中的外压机制与诱导机制.城市问题,1.
[9]孟思奇(2014).试点14年,效果不明显,垃圾分类为何难推广.人民日报,2014-06-11.
[10] 罗伯特·帕特南(2012).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 钱胜、李炜永(2011).垃圾处理:台北的成功实践——基于上海世博会台北城市案例馆的分析.环境教育,3.
[12] 瞿利建等(2013).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研究现状.中国资源综合利用,12.
[13] 曲英(2011).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数理统计与管理,1.
[14] 田凤权(2014).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意向影响因素分析.科技管理研究,18.
[15] 万建刚(2014).台北垃圾分类离我们有多远.现代金报,2014-07-07.
[16] 谢德良(2013).日本:乱扔垃圾可判刑5年.环境与生活,6.
[17] 熊孟清(2014).垃圾分类缘何止步不前.中国建设报,2014-09-16.
[18] 熊孟清等(2011).应推广垃圾干湿分类.广州日报,2011-03-07.
[19] 燕继荣(2015).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 郑磊(2014).居民嫌麻烦垃圾不分类,北京七成以上垃圾需二次分拣.京华时报,2014-11-17.
[21] Margaret Levi(1996).Social and Unsocial Capital:A Review Essay of Robert Putnam’s Making Democracy Work.Politics&Society,24(1).
■责任编辑:叶娟丽
◆
Source Classification of Municipal Domestic Waste: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of Residents and Its Overcoming
ZhangLipi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angZhonghua
(Shandong University)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of China,the “garbage siege” phenomenon is leading to more and mor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roblems.Source classification of municipal domestic waste is helpful in waste reduction, innocent treatment, and resource recovery.It is also essential for the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aste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is facing a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that is,large numbers of people do not release waste in accordance to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for not disturbing themselves, for not wasting time or for some other reasons.Third-party enforcement,selective excitation,autonomous organization and self-governance are four possible ways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A hybrid strategy has been discussed based on system analysis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Meanwhile,the government should really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y and lead by example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confidence in classification,and should pay large attention on nurturing and effective use of social capital.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capital; urbanization
10.14086/j.cnki.wujss.2016.06.0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ZZ03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662015QD038)
■作者地址:张莉萍,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Email:zhangliping@mail.hzau.edu.cn。
张中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