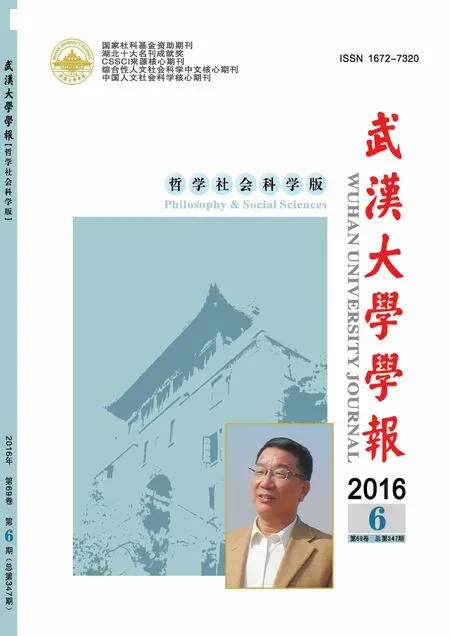现代预算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十大关系——基于文献的审视
2016-03-13曹堂哲
曹堂哲
现代预算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十大关系
——基于文献的审视
曹堂哲
现代预算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前提基础”和“有效支柱”。两者的关系是全方位的,它们是整体共生性、具体相关性、制度同构性的有机统一。整体共生性表现在价值诉求、体系构成、形态特质和功能实现四个方面。具体相关性表现在预算模式、预算权力、预算过程、预算机构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和功效上。制度同构性意味着现代预算和现代国家治理都以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作为共同的制度基础。上述三个维度一共包括十大关系。
现代预算;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设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首次将财政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中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是核心。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要重点推进预算管理制度等三个方面的改革。2014年8月31日,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2015年1月1日实施。2014年9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已经成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的重大议题。
现代预算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是一种与传统预算相对的预算形态,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逐步确立和完善起来的预算权力、预算过程、预算模式和预算机构系统。现代国家治理是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市场与社会以特定的结构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统治形态与管理形态。现代国家治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亦经历了结构性的演化。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现代预算与现代国家治理形成了整体共生、具体相关和制度同构的关系。整体共生即系统之间在系统层面上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撑的关系。具体相关指系统之间在基本构成要素层面上具有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制度同构指两个或多个系统作为子系统共同构成更高层次的制度系统。
总之,如果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那么现代预算是国家治理的“前提基础”,“前提基础”强调现代预算制度在规范政府财政行为方面的基础作用,现代预算通过规范政府的财政行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基础。如果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支柱,那么现代预算则是国家治理的“有效支柱”,“有效支柱”表明现代预算制度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为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工具。
一、 现代预算与现代国家治理的整体共生性
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现代预算与现代国家治理在价值诉求、体系构成、形态特质和功能实现方面具有整体共生性。
(一) 共享价值诉求
从历史发展、空间比较和思想流变的角度来看,“现代性”是现代预算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共同价值追求。理性化、民主化、透明化、法治化和可问责是两者建立和发展的共享价值诉求。
现代(modern)普遍被定义为约开始于16世纪,中世纪(medieval)之后的历史时期。现代意味着以人为中心,关心人和他的潜能、他的命运;而不是像中世纪那样,是以神、宗教或超越界作为其文化的核心(沈清松,1993:4-25)。现代化是现代社会不断演进的过程。欧美等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基本完成了现代化,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后现代社会。现代化的研究最初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当代的现代化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孙若彦,2003:31)现代性(modernity)是指现代社会的性质或特征(夏光,2005:4-5)。
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预算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既与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致,同时也在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被塑造和拓展。就西方国家而言,以现代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方式的差异为标准,可以将现代国家治理和现代预算制度划分为议会主权式治理阶段、行政国家与大政府治理时代、小政府与新公共管理治理时代、善治时代。从“国家统治”到“自由市场”再到“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协调,进而走向“善治”是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线索。亚非拉等地的发展转型国家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转型道路,在国家治理上大体也各自经历了“全能主义”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双方面教训。在全球化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这些发展转型国家也将既强调“国家统治”又强调“社会与市场”的“善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参照。抛开现代化的路径、时代和国别差异,现代预算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作为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它们拥有一些共同的现代性特征,这些特征在漫长的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成为塑造现代预算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的规范性标准。这些规范性标准贯穿在现代预算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演化的始终。以至于“预算一词就像社会正义……等词一样,成为政治的常用语。”(卡恩,2008:126)
具体地说,理性化、民主化、透明化、法治化、可问责是现代预算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在几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中不断完善、一以贯之的价值原则,充分体现了“现代性”的基本规范。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存在差异,但是在既强调“国家”的领航作用,又强调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新一轮现代化价值观下,这些基本价值原则得到了再次确认和整合。
(二) 共联体系构成
共联体系构成意味着系统之间通过共同的场所联系起来。现代预算体系作为社会子系统和社会行动主体的联系纽带,恰好构成了现代国家治理行动者的重要舞台,两者共联,共同推动社会体系的演化。“国家治理”是一个既主张国家“领航”又强调市场与社会共同“治理”,从而体现了协同思想的概念。国家治理体系强调国家、社会、市场和公民通过伙伴关系实现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公共事务的合理解决。现代预算系统作为社会各个子系统的联系纽带,作为国家治理行动者的重要舞台,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催化剂和维持剂。
其一,现代预算系统是社会子系统的联系纽带。预算系统本身同时具有经济属性、政治行政属性和社会属性。预算行为将经济、社会和政治同时呈现在一个平台上,能够生动地展示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的枢纽。正如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所言:“整个社会是由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三个子系统构成的,而财政是连接这三个子系统的关键环节,或者说,三大子系统以财政为媒介构成了整个社会。”(李炜光,2014:55)“财政制度是把经济基础转化为政治结构的转换器。”(Braun,1975:243-327)预算作为财政的核心内容和具体体现,更加现实而直接地体现了社会各个子系统的综合状况和发展趋势。
其二,现代预算系统是治理主体行动的重要舞台。按照治理理论的阐释,治理过程是多向度的、网络式的、柔性的,治理的优劣根据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和互动的结果进行判断。预算系统既是治理主体行动的政策议定场所,也是治理主体之间联合行动实现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纽带。现代预算决策的议定场所是多元的,不同的预算议定场所容纳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行动主体,预算议定场所和治理行动主体的变化,往往意味着政策的变迁。比如:目前我国大力推动的公私伙伴关系(PPP)制度,就能充分地展示这一点。诸如确定哪些PPP项目,PPP项目如何定价,PPP项目合同如何签订,如何顺利地完成PPP项目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与政府PPP预算编制、预算审批、预算执行和预算绩效评价紧密相关,PPP预算为多元治理主体的联合治理提供了行动舞台。
其三,现代预算系统是持续繁荣的催化剂。现代社会结构是市场与政府、国家与社会各司其职,各自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共同推动国家迈向持续繁荣的良性结构。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的目标是二元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诺思,1994:24)财政和预算在协调国家二元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直接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能够根据历史的发展,有效地划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有效地协调国家的二元目标,从而实现持续的繁荣。如果预算系统被官僚和利益集团俘获,财政资源在分配过程中无法引导其走向“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方向,就会直接导致经济的停滞和社会的不公正(奥尔森,2005:序3)。如果按照现代预算系统改革传统的预算系统,使得财政资源的配置符合良善治理和强化市场型政府的需求,那么预算系统就成了维持现代社会结构的稳定剂和促进社会走向持续繁荣的催化剂。
(三) 共定形态特质
共定形态特质意味着一个系统的形态特质由另一个系统的形态特质所决定。现代预算在财政汲取方式、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形态和治理能力。这一观点是财政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在财政社会学看来,国家的财政汲取来源、结构与方式,反映了一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对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国家政治、行政和法律制度的建构,进而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和国家治理现代性程度。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家财政汲取方式决定国家治理形态。财政社会学者认为财政收入来源的差异,形成不同形态的财政国家类型,不同形态的财政国家类型形成不同形式的国家与社会的契约关系,从而导致国家治理体系、过程和绩效的差异。早在1917年,戈登希德(Rudolf Goldschid)就关注到财产收入和税收的变化对国家政治的影响。1918年熊彼特发表了《税收国家的危机》,他在区分“领地国家”和“税收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税收塑造现代国家的观点。财政社会学者们进一步将20世纪以来的财政国家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税收国家、自产国家和租金国家。连接财政国家类型与国家治理的中间变量被概括为社会与国家的契约关系(Moore,2004:297-319)。存在三种常见的契约关系模式:“征税—代议制模型”、“租金—国家自主性模型”和“税收讨价还价—政治民主模型”(马骏,2011:19)。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契约在国家自主性与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其中税收国家更有利于推动代议制民主的发展,具有更高的国家治理绩效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撑(Moore,2004:297-319;Moore,2008:34-63;马骏,2011:18-30;马骏、温明月,2012:86-108)。预算集中地反映了财政收支情况,可以认为,预算是透视财政与国家治理关系的多棱镜,它一体多面地展示了社会经济结构、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预算的变革必然带来国家治理的变革。
其二,预算国家这一制度结构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必经之路。财政社会学者不仅仅研究国家汲取对国家治理的决定作用,还关注国家支出结构、原则、制度、方式和工具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正如希克所言,“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预算能力。”(Schick,1990:1)一些学者认为:在西方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上,发生了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再向“预算国家”的两次转型(王绍光,2007:3)。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两次财政制度转型,现代国家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王绍光、马骏,2008:1-37)。只有拥有现代预算制度的国家,才能称为“预算国家”。那些有预算,但是没有按照现代预算原则建立了现代预算制度的国家不能称之为预算国家。现代预算制度萌芽于17世纪后期英国税收国家形成之后,直到19世纪最终成型,并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预算国家体现了现代国家在资源分配和利用方面的两个基本特征,即财政上的集中统一和代议机构能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王绍光,2007:4-5)。预算国家的成长历史表明:拥有现代预算的预算国家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必经之路。
其三,财政收支的制度安排决定国家治理的行为和绩效。制度安排是在相对稳定的制度结构下形成的具体规范。财政收支的制度安排是约束和规范社会财政资源汲取和支出的行为规范。财政收支的制度安排广泛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形成了社会行为的重要激励约束结构,从而影响到国家治理的行为和绩效。财政收支的制度安排影响到官员的理性选择行为、制度的变迁甚至王朝的命运与兴衰。熊彼特认为,“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像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财政有助于现代国家的产生,也是现代国家发展的推动力量。国家对私人部门征税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将塑造一种特定的现代经济,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与价值。在塑造了一个本身能够逐渐发展的公共官僚体制的同时,征税也塑造了人民,塑造了一种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Schurnpter,1958:17-19)熊彼特之后的研究者进一步阐述了税收国家推动国家建设的因果机制(杜赞奇,1996:序1-2;黄冬娅,2008:38-63;王绍光、马骏,2008:1-37;刘守刚,2008:169-182;黄仁宇,2001:1-416)。
(四) 共致功能实现
共致功能实现意味着一个系统作为另一个系统的工具,实现另一个系统的功能。国家治理的过程亦是国家职能的实现过程,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职能的实现程度。正如亨廷顿所言:“各国之间最大的政治分野,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效能。”(亨廷顿,1989:7)现代预算作为基本的财政工具和国家治理工具,同时具备资源分配、收入规划、经济稳定、行政责任、支出控制、资金移转、经济发展、行政效率等功能,对于有效的履行国家职能、实现公共政策目标、提升政府效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徐仁辉,2002:28)。
国家职能的实现需要以财政资金作为基础。预算收入和支出的规模、投向和方式直接体现了国家职能,国家职能的差异可以用国家对社会资金投入的范围、方向和强度等方面来衡量。“预算说到底是一种制度,它是通过一些复杂的技术或者精确的数据来形象地告诉人们,他们的政府打算做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做了些什么。预算改革的实质就是要界定政府活动的合法范围,确定政府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确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进而划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叶娟丽,2009:194)总之,预算作为核心的财政工具,“财政工具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其目标的制定则有赖于人们对理想社会以及该社会之内国家职能的设想。”(马斯格雷夫,1995:15-21)
国家职能的实现过程需要一定的执行工具作为保障,执行工具将国家意志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其中现代官僚制度和现代预算制度分别从人事和财政两个方面构成现代国家职能实施的有效工具。作为执行工具的现代预算制度,将宏大抽象的国家意志转化为可以用数目字加以衡量和管理的体系,将国家职能转化为实际的国家行为。“预算过程中做出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利的分配。实际上,在政治与政策中,无论政治家的目的是什么,预算过程都是一个政治工具。如果政治家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那么,预算就成为经济增长的手段。如果政治家的目标是收入分配,那么,预算就成为收入分配的发动机。”(Wildavsky,1997:2-8)现代预算制度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控制、计划、政策、管理与责任多重功能的国家治理工具,这些治理工具深刻而广泛地塑造着国家与社会关系,影响到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方式,影响到每个人的行为和决策。
二、 现代预算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具体相关性
现代预算系统的四大基本要素(即预算模式、预算权力、预算过程和预算机构)与现代国家治理都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具体如下:
(一) 现代预算模式直接塑造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规范
预算模式是预算系统基本构成要素之间的稳定联系,以及预算行为变迁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阶段性特征。预算模式包括预算功能、预算原则和预算取向三个基本要素。预算功能是预算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预算原则是为了与特定预算功能相匹配,预算行为应该遵循的法则和规范。预算取向是不同历史时期,预算功能和预算原则的方向性和倾向性。预算模式镶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直接塑造了国家治理的基本规范。
其一,预算功能是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和保障。预算系统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其功能的发挥是由国家治理体系的总要求决定的。预算功能的调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国家治理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治理变迁的基础。在君主专制鼎盛的年代,君主专制权力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调,国家治理紧紧围绕君主的权力展开,财政和预算为君主服务,从而成为“宫廷财政”和“家计财政”。随着现代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国王的权力不断地被压缩和限制,在英国《大宪章》和《权利法案》之后,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则得以确立,“议会主权”的国家治理体系得以确立,议会掌握国家的财政预算权力,行政机关仅仅是预算的执行者。在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对预算功能的要求主要是发挥预算的控制功能,确保公共财政资源使用过程中的合规性与依从性(Schick,1966:243-258)。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形势的改变,国家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行政权的作用和地位逐渐上升,“行政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行政国家增加了对预算功能的要求,预算不仅仅要履行控制功能,还要发挥政策、计划与管理功能。政策、计划功能强调预算决策过程中的政策制定与选择,强调问题解决方案的分析、评估与选择。管理功能则强调预算项目管理过程中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实现项目的经济与效率。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行政权力过度膨胀,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的弊端日渐暴露,环境、贫困、社会福利、公正问题凸显,公平行政、民主行政的呼声高涨,公民权利运动勃兴的环境下,代议机构再次加强了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和约束。美国在1974年通过了《国会预算及截留控制法案》,该法案加强了国会预算的政策功能、控制功能和问责任功能。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轫于英国,并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重新塑造了政府治理体系,在新公共管理市场化、社会化和民营化的大旗下,最小化政府的古典原则重新回归到历史舞台,社会和公民的力量得到了彰显,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得以确立。在此背景下,预算的功能进一步拓宽出了绩效问责和民主参与等功能。20世纪90年代,进入治理理论主导的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治理作为融合国家和市场的第三种选择,融合了历史上预算的各项功能,形成了同时兼具控制、政策、管理、民主、问责等多项功能的复合体。总之,现代预算功能伴随着现代国家治理的发展而不断丰富,预算功能的多样性一方面满足了国家治理的复杂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预算制度设计的复杂性。
其二,预算原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规范。预算原则是为了实现特定预算功能的预算制度、机制、流程、行为所依据的法则和标准。虽然预算原则主要是针对预算系统本身,但是预算过程同时贯穿在政治过程、政策过程、行政过程的始终,并且是政治过程、政策过程和行政过程的最终落脚点,这决定了预算原则同样深刻地影响到政治原则、政策原则和行政原则,从而构成国家治理的基础规范。比如现代预算的控制和民主功能,衍生出来的诸如公开原则、明确原则、事前决定原则、严密原则、限定原则、单一原则、完全原则、不相属原则(张则尧,2001:285-289),同时也是强调控制和民主功能的国家治理应该遵循的原则。现代预算原则与现代国家治理原则的一致性,可以使用结构功能理论加以解释。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会系统由不同的制度安排发挥不同的功能构成,同一种功能的发挥,可由不同的结构加以体现,虽然结构不同,但是结构设计的原则是相同的。比如现代税收和现代预算都反映的是现代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因此现代税收和现代预算都遵循法定、公平、效率、统一、规范和层级原则(陈志勇,2015:13-15)。
其三,预算取向是判断国家治理取向的重要依据。预算取向是预算意图实现的目标,以及围绕这一目标形成的相关预算制度、机制、程序和方法。比如:以亨利为代表的学者将美国现代公共预算划分为七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取向、范围、个人能力、重要内容、决策方式、计划部门的角色、预算部门的角色存在差异。第一阶段分项排列预算(1921-1939)。基本取向是控制,只告诉我们政府将钱用到哪里去?却不一定能通过它了解政府花钱的目的。第二阶段绩效预算(1940-1964)。其核心是效率的改进,具有明显的管理取向。绩效预算选定工作衡量的单位,估计活动成本,建立定额标准,并将绩效与预算额度联系起来。第三阶段计划项目预算制度(1965-1971)。计划项目预算制度使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将长期目标、方案分析与选择、预算资金连接起来,尝试形成一种计划、政策与有效的资源配置相融合的机制。第四阶段目标管理预算(1972-1977)。目标管理强调目标和成果,也是一种管理取向的预算,与计划项目预算制度相比,简化了备选方案的比较分析。第五阶段零基预算(1977-1980),零基预算属于决策导向的预算。预算编制不受往年预算的制约,一切从当年的计划和业务开始。第六阶段由上而下的预算(1980-1992)。先设定联邦各机关的施政目标及支出上限,再由各机关根据默认的目标自行规划运用预算,并对目标实现率有进展的联邦机关提供预算激励。第七阶段企业化预算(1993迄今)。企业化预算是重塑政府运动的产物,强调预算的结果导向,根据结果的测量与评估确定预算资源的分配和问责,同时主张弹性自主的预算执行方式(亨利,2002:208)。事实上,上述七个阶段的每种取向也并非泾渭分明,比如:企业化预算虽然强调结果取向,但是传统预算积累的绩效测量与评估方法也为结果的测量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结果取向的预算与目标预算、计划项目预算制度也有很多重合的地方。事实上,预算的取向与国家治理的取向是一致,预算取向是判断国家治理取向的重要依据。国家治理的理念和目标决定了预算的理念和目标,而预算技术为国家治理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比如:分项排列预算反映了加强资金控制的治理理念。绩效预算、计划项目预算则反映了传统公共管理以效率、系统优化为核心的理念。零基预算则反映了最小化政府的努力。企业化预算反映了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取向。
(二) 现代预算权力是联系国家权力分支的重要纽带和舞台
预算权力是指决定、支配国家预算的权力,是国家预算的编制、审查、批准、执行、调整、监督等权力的总称。按照分权学说,横向分权以国家职能—机构—人员的分离为标准,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纵向的分权侧重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职能、边界、关系、结构和人员的划分。无论是横向分权还是纵向分权,预算权力都是联系国家权力分支的重要纽带和舞台。
其一,预算权力是国家横向权力的纽带和舞台。现代预算权力的确立过程经历了漫长过程,从13世纪到17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在与国王的斗争中,将财政预算权力逐渐从国王手中完全转移到议会。1215年英国贵族与国王签订的《大宪章》确立了“非同意勿纳税”原则。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正式确立了议会是英国最高的立法机关以及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并再次否定国王的征税权,规定必须定期召开议会会议。该法案申明财政权永远属于议会;君主、王室和政府机关的开支都有一定的数额,不得随意使用。政府机关和官员在处理国家的财政收支上,都规定有其责任和权限,必须遵守一定的法令和规章*卫东:《从英国预算制度的产生看预算与议会的不解之缘》,载中国人大网(2014-11-02),http://www.npc.gov.cn/npc/xinwen/rdlt/wysd/2014-11/02/content_1884648.htm,2015-07-10。。之后,英国议会通过了系列法案奠定了议会主导的现代预算制度框架和传统。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职能空前拓展,“行政国家”逐渐兴起,行政权逐渐发展成为国家权力中的主导力量。与此相一致,国会预算权和行政机关的预算权,以及行政机关内部的预算权也不断地改革和调整,形成了立法机关的预算权和行政机关预算权之间的分立与制衡。这种分立与制衡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预算权力结构从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国会主导,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行政主导,再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国会与行政均势的演变过程就充分体现了预算权力在国家横向权力结构中的纽带作用(章伟,2005:31;威尔达夫斯基,2006:34-35;朱大旗、何遐祥,2009:128-135;Schick,1980;Kahn,1997;马骏、赵早早,2011:90-121)。正如杰克·瑞宾与托马斯·林奇所言“有关国会预算权力争论的主要焦点大致是围绕着立法部门是否确实把握着真正的权力而展开的”(杰克瑞宾等,1990:77-88)。
其二,预算权力是国家纵向权力的纽带和舞台。国家纵向权力结构主要涉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配置。无论是单一制、联邦制,也无论是内阁制、总统制、委员会制,中央向地方分权是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普遍选择,他们的区别仅仅是集权和分权的种类、程度和方向不同而已。最常见的分权包括三种类型,即“政治分权、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政治分权涉及机制创新,亦即在制定那些影响到地方居民的决策时,允许他们有发言的权利。行政分权主要集中在官僚机构内部决策制定权的分配。财政分权主要是提供给次级中央政府以支出和征税的权力,一般是与行政决策制定权的授权联系的”(Schroeder&Aoki,2009:1-16)。预算通过收支计划的形式,以规范化和数字化的形式反映了财政分权的状态;同时预算过程同时具有政治、行政、财政等多重属性。这一特性使得预算分权成为国家纵向分权的纽带和舞台。“纽带”是指纵向预算权力将国家纵向权力不同类型的分权有机地联系起来。“舞台”指预算权力及其运作生动地体现了国家纵向权力运行的真实情况。预算权力纵向配置反映了中央与地方政权、事权、财权的划分,从而奠定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基调,是国家纵向治理的基础和支撑。
总之,尽管世界各国的预算权力结构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存在现实和历史的差异,但是预算权力作为连接国家横向权力和纵向权力的纽带和舞台,实际上成为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塑造了国家的治理模式,并对国家治理能力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 现代预算过程是贯穿公共政策过程的纲目
国家治理水准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水准的高低。在国家治理中,公共政策一般经历了政策议程设定、政策方案选择、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政策纠错和新的政策议程设定的往复循环的过程。政策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涉及资源和价值的配置和利用,比如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自然资源等等。其中财政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在整个政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财政资源通过预算过程和预算工具,将政策目标与实现目标的财政资源结合起来,从而将政策转化为行动。“预算是政府的血液,是政府行动倾向和政府行动的财政反应。”(Wildavsky,1964:128)。
预算过程一般包括预算编制、审议、执行及决算等环节。预算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政治过程、政策过程和技术过程的统一。良好的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标志是预算过程与政策过程的匹配和融合,预算以数字化的形式,为政策和国家意图编制出一张数字“纲目”,形成“数目字管理”的现代国家能力:第一,预算的收支计划、预算项目、预算额度等预算内容能够有效地支撑政策意图的实现。第二,预算编制、审议、执行、决算等各个环节既是政策议定的场所,也是将既定的政策方案转换为收支计划的技术过程。第三,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意志的实施工具,能够有效地实现总量控制、资源配置、运营效率、受托责任的功能,从而成为与政策有机统一的国家治理工具。
预算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工具和管理管理,贯穿在政策过程的始终:在政策制定阶段,政策的引导和预算约束相互作用,形成既体现公共需求,又符合财政资源约束的预算方案。在政策执行阶段预算以基本支出、项目、补贴、奖励等形式将政策规划转化为影响社会的产品和服务。在政策评估和终结阶段,对预算的绩效进行评估和审计,从而确保了政策执行结果的经济、效率、效益和公正。
总之,在现代国家治理中,预算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与政策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保持高度一致性,预算过程从财政资源总量、配置、运营和问责的角度展示了政策过程的一个侧面,政策过程和预算过程的协同作用,推动了国家治理的实现。
(四) 现代预算机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预算能力是实现预算控制、计划、政策、监督、问责等功能的能力。预算能力取决于预算系统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系统之间相互调适,以及预算系统本身结构的优化。实践中,预算机构的增加、调整和整合所形成预算机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部分。
其一,战略机构与预算机构的协同能力。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实现国家战略与预算一致性的能力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治理能力。很多国家都设置了专门的战略、预测与规划部门,这些部门与财政部门的相关机构相互协调,共同实现规划与预算的协同一致。比如:在法国“现代化委员会”作为战略计划部门与经济财政部的协同,以及经济财政部内部计划局、统计与经济研究所、预测局之间的协同保证了法国经济发展计划与预算的一致性。澳大利亚内阁中也设置了四个有关预算战略制定的机构:联合经济预测小组、预算官员委员会、支出审查委员会、税收委员会,这些机构在预算过程中的协同,保障了战略与预算的一致性。日本内阁设置的“财政制度委员会”是预测和战略规划部门,财政部的主计局则主要负责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和决算(吕旺实,2002:45-54)。总之,战略机构与预算机构之间的协同保障了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执行。
其二,行政机构内部核心预算机构的统和能力。20世纪以来,随着行政国家进程的加快,无论议会内阁制国家还是总统制国家,行政权力在国家权力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渐上升,与此相一致,行政部门预算统和能力也得到了加强。行政部门的预算统和能力集中地体现在核心预算部分的设置和运行上,核心预算部门在行使行政机关的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权力的时候拥有统一性、唯一性和一致性。核心预算机构的预算能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在预算审查过程中能够合理地审查部门的预算申请,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能够改进运作效率(马骏、於莉,2007:23)。比如:美国是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国家,1921年之前,总统并不拥有统和行政部门预算的权力。1921年《美国预算和会计法》通过后,总统拥有了统和行政机构预算的权力和向国会报告的责任。为强化总统的预算统和能力,在财政部设立了直接对总统负责的预算局。1939年,预算局划归为总统直属机构。1970年7月,预算局合并到新成立的管理和预算局。该局被认为是供美国总统使用的一个最有权威的协调机构,它既管预算,又管支出、管采购与决算,财政部的职能和权限则相对萎缩。在议会内阁制国家,内阁各个部的部长是议会各党派的头目,预算是各个部门和内阁意见的综合和均衡的结果,为了便于协调,绝大多数国家的预算司设置在财政部之内。这些预算机构拥有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的统一职责和权限,拥有强大的预算统和能力(吕旺实,2002:45-54)。在许多国家,在政府内部通常只有一个核心预算机构。也就是说,预算分配权是高度集中的。在另外一些国家,预算分配权则不是这样集中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名义上的核心预算机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机构承担着核心预算机构的作用,即所谓的双轨模式。核心预算机构(例如财政部)主要负责经常性预算的分配,而资本预算通常是由一个计划部或者发展部来分配的(Potter & Diamond,1999:16)。在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预算核心机构“零碎化”的局面(马骏、侯一麟,2005:64-72)。提高核心预算机构的统和能力将是未来改革的重要方向。
其三,代议机构内部的预算机构能力。现代预算制度建立之初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议会主权原则,行政机构仅仅是国会预算的执行机构。20世纪行政国家兴起后,行政预算权与国会预算权逐渐形成均势,双方在互动博弈中形成了完整的国家预算过程。西方国家的国会拥有预算创制、审议和监督的广泛权力,为了将这些权力变成现实,强大的国会预算机构是基本保障。比如: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各有一套审核联邦预算编制的庞大机构,包括国会拨款委员、国会筹款委员会、国会预算委员会、国会预算办公室、国会审计署(2004年更名为政府责任办公室)等,上述专业机构共同构筑了美国国会强大的预算编制、审议、评估和监督的能力*财政部:《美国政府预算管理情况介绍》,载财政部网站,http://gjs.mof.gov.cn/pindaoliebiao/cjgj/201304/t20130409_813495.html,2015-07-10。。英国的财政部专司预算的编制、执行等工作,国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预算的审议和预算执行后的审计。英国国会下议院拥有预算的实际权力。下议院院会直接审议行政机关的预算。下议院还设置了部门选任委员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国家审计署共同监督行政部门预算的执行和绩效。德国、法国、日本等国都在代议机构内部设置了预算机构,保障了代议机构的预算能力。
三、 现代预算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同构性
现代预算和现代国家治理都建立在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基础之上,预算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构成部分,丰富了国家治理的形式。预算法治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
(一) 预算民主是民主政治的构成部分
民主政治是政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民主作为核心价值和运行规则以及评价标准的政治形态。预算与选举、立法、司法等活动一样,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预算民主是民主价值、民主规则、民主标准在预算权力运行过程中的体现,是预算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人民对政府预算权力的制约。预算参与和协商、预算公开与透明、预算监督与问责集中体现了多数被管理者对少数管理者的权力制约关系。
其一,预算参与和协商。预算参与和协商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对话行政的典型形式。有效的预算参与和协商总有一套公正、透明的预算制度和预算程序加以规范,这些制度包括代表产生的办法、议事规则、决策规则、问责机制等内容。预算参与和协商体现了公民的参与与国家制度化的均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比如中国温岭和盐津等地在实践中形成了抽样选取参与者、志愿参与、人大代表为主体的参与、按照领域的名额分配、问卷调查、现场表决、议事会议、群众议事员等多种公民预算参与和协商的形式。从预算参与和协商的主体来看,可以分为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两种形式。公民个人可以根据相关的程序和制度被选为公民代表,并在参与过程中发挥信息咨询、意见表达、意见综合和决策决议等作用。社会组织则以第三方的形式,发挥第三方组织专业性、中立性、民间性的特点,参与到预算过程中。比如在预算执行和预算评估阶段,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参与到预算过程中,有助于诊断预算中的问题,为绩效问责提供专业基础和信息基础。预算参与和协商是非常广泛的参与行动,其本质是对财政资金的配置,确定资金分配的优先事项。在美国地方政府,公民都可以参与到预算决策过程中。在中国温岭的参与预算模式中,公民广泛地参与到日常支出预算和建设项目预算的决策、审议、执行和评估过程中。预算参与和协商贯穿在预算编制、审议、执行、审计与评估各个阶段,体现在日常支出预算和资本预算的各项内容中。比如:在预算编制阶段。巴西阿里格雷港市,公众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整合偏好、选择优先项目,并通过全体会议选举的代表与相关机构对政府预算决策施加影响。偏好表达主要按照“区域性”和“主题性”逻辑进行,邻里会议、区域会议、市级会议是主要的组织机构(苟燕楠、王逸帅,2009:267)。在预算审议阶段,印度古吉拉特社会人类行为发展创始组织(DISHA)通过预算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公开,为公众、利益相关者团体和立法部门提供预算审议的专业信息支持(Shan,2007:74)。在预算执行阶段,乌干达建立了教育服务公共支出跟踪机制。在预算评估阶段,1994年印度班加罗尔市(Bangalore)实施了公众报告卡制度,通过收集公众关于城市服务提供者绩效的意见,促进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效率的全面提升(苟燕楠、王逸帅,2009:268-269)。
其二,预算公开与透明。预算公开透明是确保公民拥有预算信息知情权的前提,是预算参与的必要条件,是预算监督的前提,是提高预算决策、审议、执行和评估质量的基础,也是建设一个政治清明、政府清廉的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早在1916年,著名公共预算学者克里夫兰就指出,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不可能是负责的政府。只有将“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人民以及人民的代表才有可能对它进行监督(Cleverland,1916:50-84;王绍光,2002:4;林慕华、马骏,2012:73-90)。通过立法确保预算信息公开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做法。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日本、巴西等国家都建立了较为完善预算公开透明的法律体系。实现全口径和预算全过程的信息公开,已经成为预算公开透明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些国家在信息的可读性、可接近性等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努力,使得预算信息真正能为民所懂,为民所用。
其三,预算监督与问责。预算监督是指国家通过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对国民经济各项活动进行的监督,预算监督在国家监督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预算问责是相关主体部门对政府及其官员是否认真履行职责,是否明智和可靠使用委托给他们管理和控制的政府预算资金,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系列责任追究以及绩效奖励的过程。预算监督与问责都基于人民主权和预算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基本政治原则。预算监督确保整个预算过程能够体现合规、效率、公正、效益的基本原则,预算问责则进一步对预算行为造成的结果予以强制性的惩处或奖励。预算监督与问责首先要发挥权力机关的作用。预算监督与问责权力都是最重要的立法机构监督政府的工具,立法机构的预算监督也因此成为建立对人民负责政府的关键手段。在各种监督中,预算监督是最有效的手段(穆勒,2007:155)。预算监督与问责需要建构全方位的预算监督网络,建立公民、社会组织、新闻舆论、审计协同作用的监督网络。其中审计机关能够独立充分完全地行使预算监督和问责的权力是预算监督与问责的关键环节。比如:根据2004年美国审计总署人力资源改革法案修正案,自2004年7月7日,美国审计总署(Gener Accounting Offiec)正式更名为政府责任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该机构作为美国国会的下属的独立机构,负责调查、监督联邦政府的规划和支出,政府问责办公室的职责范围几乎涵盖了联邦政府的所用活动。国会建立强大的政府问责机构和问责制度保证了国家治理的受托责任。
(二) 预算法治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预算法治是预算权力、预算过程和预算行为依法治理的状态。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预算法治是现代预算的重要标志,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预算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预算立法奠定了现代预算的制度基础。现代预算制度成长的历史既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也是现代法治国家发展的历史。英国的《大宪章》、《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主权的预算原则。随后英国议会颁布的《联合王国统一基金法》(1789)、《公共收入统一基金支用法》(1854)、《国库与审计部法》(1866)等法案奠定了英国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则。在美国建立现代预算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包括宪法、制定法到管理规则,包含预算体系和预算程序的完整法律体系。预算法律体系为预算权力、预算过程和预算行为的运行奠定了制度框架(陈立奇,2008:46)。其他建立了现代预算制度的国家,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预算法律体系。预算法治不但可以实现对权力的制约,还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而防止预算权力的腐化,让预算权力服务于现代国家治理的总目标。
其二,有效执行是预算法治的关键。预算法律的执行是将预算法律规范转换为实际预算行为的过程。法律有效执行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立法的重要性,“事实上,策略被成功的执行的之比例只有十分之一。”(Kaplan & Norton,2001:33)在预算法的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多预算法律规范都难以做到完全有效的执行,有的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法律不能有效执行还得不到纠正,法治秩序就会混乱,一部法律最终就会变成纸上谈兵。提高执行有效性需要强化行政机关预算核心机构的权威和能力,使其能够按照现代预算统一性、公开性、完整性、真实性、年度性等原则的要求,统筹和协调预算的编制、执行和绩效评估;同时还需要强化日常监督机构和人员的作用,构筑全方位的综合监管网络;强化预算绩效的全过程管理,通过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模式,推动政策、管理、控制和监督的统一。
其三,及时纠错是预算法治的保障。有效执行和及时纠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现代预算制度成熟的国家都建立了全方位的、有效的预算纠错机制,这种机制以立法机构审议、监督和问责为核心,以向预算执行主体问责为指向,以社会和公众广泛参与为依托,共同构筑起了强大的监督和纠错网络。立法机关常用的机制包括强化设置专门的预算委员会,建立全口径、全过程预算审议与监督机制,强化审计机关的作用等等。预算执行机关需要加强预算内控管理,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检查,提高预算执行的全过程监控能力,及时纠正预算执行中的偏差。信息就是权力,监督权力的有效行使与预算信息的获取紧密相关,增强预算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让预算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社会和公众的参与提供便利有效的路径,是确保预算执行问责和纠错的前提。
四、 结 论
现代预算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关系是全方位的,它们是整体共生性、具体相关性和制度同构性的有机统一。这种关系决定了现代预算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前提基础”和“有效支柱”。这一结论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理论上,人们在对现代预算展开研究的时候,往往在技术、政治、管理、经济等视角单兵突进的时候,忽视了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综合性地审视现代预算对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和支柱性作用。即便人们已经对“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预算这一财政的核心制度如何构成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并没有进行系统而充分的阐释。本文在文献整合的基础上,全面阐释了现代预算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关系,论证了现代预算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前提基础”和“有效支柱”这一观点。
在实践中,我国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下,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和全面小康建设,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呈现出多点突破、协同推进的局面。新《预算法》的颁布和财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预算改革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预算改革已经成为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综合性、统领性的突破口。本文对现代预算与现代国家治理关系和作用机制的阐释,有助于统筹预算与国家治理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奥尔森(2005).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陈立奇(2008).美国联邦预算法发展简析.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
[3]陈志勇(2015).现代税收与政府预算:内在逻辑和制度契合.税务研究,2.
[4]杜赞奇(1996).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5]苟燕楠、王逸帅(2009).参与式预算: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复旦公共行政评论,1.
[6]亨利(2002).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第七版).张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亨廷顿(1989).变化社会中的秩序.王冠华译.北京:三联书店.
[8]黄冬娅(2008).财政供给与国家政权建设:广州市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研究(1949-1978).公共行政评论,2.
[9]黄仁宇(2001).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0] 杰克瑞宾、托马斯、林奇(1990).国家预算与财政管理.丁学东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1] 卡恩(2008).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与公民权(1890-1928).叶娟丽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12] 李炜光(2014).财政何以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法学评论,2.
[13] 林慕华、马骏(2012).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6.
[14] 刘守刚(2008).财政类型与现代国家构建:一项基于文献的研究.公共行政评论,1.
[15] 吕旺实(2002).各国财政机构设置的比较及借鉴.中国财经信息资料,13.
[16] 马骏(2011).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研究:走向税收国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
[17] 马骏、侯一麟(2005).中国省级预算中的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5.
[18] 马骏、温明月(2012).税收、租金与治理:理论与检验.社会学研究,2.
[19] 马骏、於莉(2007).中国的核心预算机构研究———以中部某省会城市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20] 马骏、赵早早(2011).公共预算: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
[21] 马斯格雷夫(1995).财政理论中的国家职能.财政研究,11.
[22] 穆勒(2007).代议制政府.段小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3] 诺思(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4] 萨托利(1993).民主新论.冯克力、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5] 沈清松(1993).从现代到后现代.哲学杂志,4.
[26] 孙若彦(2003).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及拉美现代化道路研究的主要问题.拉丁美洲研究,2.
[27] 王绍光(2002).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8] 王绍光(2007).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读书,10.
[29] 王绍光、马骏(2008).走向“预算国家”: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公共行政评论,1.
[30] 威尔达夫斯基(2006).预算过程中的新政治学(第四版).邓淑莲、魏陆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1] 夏光(2005).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
[32] 徐仁辉(2002).公共财务管理.台北:智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33] 叶娟丽(2009).一个关于预算的故事:评《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公共行政评论,3.[34] 章伟(2005).预算、权力与民主:美国预算史中的权力结构变迁.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5] 张则尧(2001).预算存稿.台北:自印.
[36] 朱大旗、何遐祥(2009).预算权力配置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4.
[37] Rodolf Braun(1975).“Taxation,Sociopolitical Structure,and State-Building:Great Britain and BranderburgPreussia”.in Charles Tilly(ed.).TheFormationofNationalStatesinWesternEurop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8] Frederick A.Cleverland(1916).Budget Making and the Increased Cost of Government.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6(1).
[39] J.Kahn(1997).BudgetingDemocracy:StateBuildingandCitizenshipinAmerica1890-1928.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40] Robert S Kaplan & P.Norton David(2001).策略核心组织:以平衡计分卡有效执行企业策略.台北:城邦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41] Mick Moore(2004).Revenues,State Formation,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in Development Countries.InternationalPoliticalScienceReview,25(3).
[42] Mick Moore(2008).Between Coercion and Contract:Competing Narratives on Taxation and Governance.In Deborah A.Braytigam,ODD-Helge Fjeldstad & Mick Moore (eds.).TaxationandStateBuildinginDevelopingCountri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3] Barry H Potter & Jack Diamond(1999).GuidelinesforPublicExpenditureManagement.Washington,D.C.:IMF.
[44] A.Schick(1966).The Road to PPB:The Stages of Budget Reform.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26(4).
[45] A.Schick(1980).CongressandMoney:Budgeting,Spending,andTaxing.Washington,D.C:The Urban Press.
[46] A.Schick(1990).CapacitytoBudget.Washington: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
[47] Larry Schroeder & Naomi Aoki(2009).测量分权的挑战.熊美娟译.公共行政评论,2.
[48] Joseph A.Schurnpter(1958).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InInternationalEconomicPapers.New York: Macmillan.[49] Aawar Shan(2007).ParticipatoryBudgeting.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50] Aaron Wildavsky(1964).ThePoliticsofBudgetaryProcess.New York:Little,Brown and Company.
[51] Arron Wildavsky(1997).Budgeting:AComparativeTheoryofBudgetaryProcess.New York:Transaction Publishers.
■责任编辑:叶娟丽
◆
Ten Type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dern Budget and Modern State Governance:Review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s
CaoTangz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of China)
Modern budget is the premise foundation and effective pillar of the modern state governance.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dern budget and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involve three properties:global symbiosis,specific corre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Global symbiosis is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value demand,system constitution,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realization.Specific correlation is reflected in budgeting model, budget power, budget cycle and the impacts of the modern budget on the state governance.The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means that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rule of law are the basis of modern budget and modern state governance.These three dimensions include ten types of relastionships.
modern budget;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ment capacity
10.14086/j.cnki.wujss.2016.06.0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ZD02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GLB033);中央财经大学重大科研课题培育项目(2014)
■作者地址:曹堂哲,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Email:caotangzh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