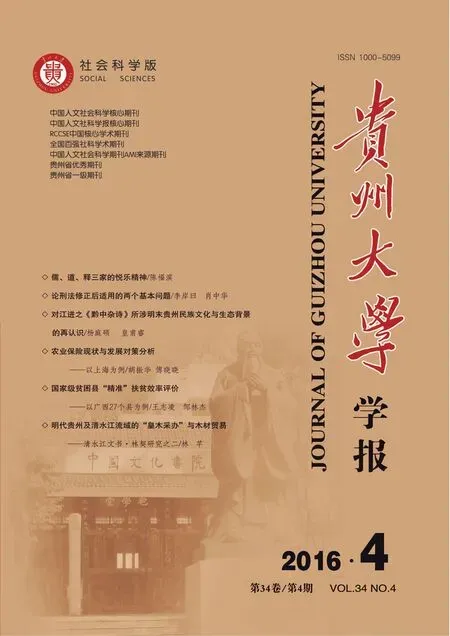红娘:从文学人物到社会角色
2016-03-09李占鹏
李占鹏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红娘:从文学人物到社会角色
李占鹏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红娘既是喜闻乐见的文学人物,又是家喻户晓的社会角色,这已是世所共知且无可争辩的事实。像她这样集文学人物与社会角色于一身的跨行兼任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甚至世界史上都独一无二。作为一个出现于唐代传奇里的婢女,却在近现代产生了新的意义与新的功能,这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深思的文化现象。红娘是在唐代以来的各种艺术样式里聚集和蓄积了足够的人气之后,才被作为社会职业的媒人或媒婆的代称,这个转型既十分独特,又非常成功。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红娘作为社会角色的媒人的称谓使用便渐渐增多了。1921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红娘形象演变迎来了新机遇。新时期以来,由于改革开放,政府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出现了以红娘命名的职业婚姻介绍所,将红娘作招牌,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上征婚成为时尚和潮流,“红娘”一词是当今婚爱流行语。作为备受世人喜爱的社会角色,红娘已不限于婚姻、女性和中国,她越来越多地出入于当代各种社交应酬场合,成为人们进行沟通、交际、联谊活动的重要介质。我们坚信,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红娘作为社会角色必将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红娘;文学人物;社会角色;接受;传播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4.023
一
文学人物脱胎于社会角色,社会角色的来源却殊少是文学人物。自有文明以来,文学人物灿若繁星,数不胜数。然而,真正能够融入现实、被赋予某种社会角色的文学人物却寥寥无几。从整个文学史看,把三五个社会角色糅合成一个文学人物已屡见不鲜,但三五十或者三五百甚至更多个文学人物却没有一个社会角色脱颖而出也非咄咄怪事。社会角色对文学人物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人物对社会角色的意义。读者只在乎文学人物的肌体到底吮吸了多少社会角色的乳汁,至于社会角色的行列是否加入了文学人物这样的新成员,仿佛还没有引起格外关注。实际上,社会角色并没有峻拒文学人物,文学人物一直都呈现于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期待视野”,是一种“当代的存在”[1],都在接受社会角色的考察和选择,只不过这种考察和选择的成功率非常低罢了。尽管文学人物演化为社会角色十分罕见,却不是一个都没有,还是有令人惊喜的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最早出现在我国唐元稹文言小说《莺莺传》,后经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王实甫《西厢记》杂剧以及明清以来各种艺术样式不断增改和润饰,荣膺“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2]盛誉的崔莺莺的婢女——红娘。她既若“文字之起承转合”,“有此许多起承转合,便令题目透出文字,文字透入题目”,又像“药之炮制”,“有此许多炮制,便令药往就病,病来就药”[3],起着莫能替代的联络、调剂、传导、合成作用,具有左右时势、掌控局面的特殊本领[4]。红娘既是喜闻乐见的文学人物,又是家喻户晓的社会角色。这已是世所共知且无可争辩的事实。像红娘这样集文学人物与社会角色于一身的跨行兼任的文化现象,可以说在中国甚至世界史上都独一无二。
红娘确实是一个例外,像她这样,既是终于超过崔莺莺从配角变为主角的成功的文学人物,又是越来越被公众喜欢、现实生活离不开的社会角色,这种跨行兼任的现象,在中外文化史上无疑属于绝无仅有的孤例。中国文学描写的比她早的有名有姓的女性并不多,像秦罗敷、刘兰芝、花木兰,应该说名气都不小,尤其花木兰更是无人不知,可是,她们充其量只是一个个文学人物,没有演变为具有一定职业的社会角色。中国文学描写的与她同时和比她晚的有名有姓的女性,多得简直犹如盛开的百花和耀眼的群星,像霍小玉、李娃、红拂(张出尘)、红线、聂隐娘、刘无双、璩秀秀、窦娥、赵盼儿、谭记儿、杜蕊娘、谢天香、王瑞兰、燕燕、崔莺莺、李千金、张倩女、赵五娘、杜十娘、莘瑶琴、陈妙常、杜丽娘、李慧娘以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祥林嫂、蘩漪、陈白露……,她们都是作者呕心沥血塑造的女主角,都具有高度的典型性,然而,却没有一个能像红娘这样迈出文学的大门,成为一种特定行业的社会角色。即使红娘侍奉的小姐崔莺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不能抵挡红娘跨行兼任的强劲风头,当今知道红娘的人却不一定知道崔莺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女性名流也不少,像娥皇、女英、西施、孟姜女、貂蝉、王昭君、杨玉环、穆桂英、李清照、梁红玉、红娘子、李香君、柳如是,乃至武则天、慈禧,她们都曾红极一时,是社会焦点和舆论中心,然而,却没有像红娘这样在近现代仍有市场。外国文学作品里的女性更是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像朱丽叶、绿蒂、爱斯美拉达、简·爱、爱玛、玛格丽特、卡门、海丝特·白兰、安娜卡列尼娜、玛丝洛娃、纳斯塔西娅、娜拉、郝思嘉、阿克西尼娅……她们内心世界丰富,感情细腻真挚,深受世人喜爱,却没有一个能像红娘这样穿古越今,进入非文学领域。即使外国历史上那些不属于文学人物、未受封建礼教桎梏的丽姝、名媛、女王、女首相们,也没有一个像红娘这样走运。还有,曾经和正在活跃的古今中外许许多多光彩照人的艺术女明星们,也没有一个像红娘这样有福气。是的,这样走运、这样有福气的女性委实少得可怜,但毕竟还有红娘。而从男性文学人物演变为男性社会角色者,资料显示,迄今全世界连一位都没有*西方文化里的罗马神话人物小爱神丘比特,与红娘倒有相似之处,但始终是一个神话人物,没有演化和转变。况且,他的意义仅在于强调爱情当事人因一见钟情与彼此吸引而获得的婚姻幸福,跟红娘通过积极奔走和努力争取换来的爱情当事人的婚姻幸福截然不同。。唐代以来,以王实甫为代表的谱写崔莺莺故事的文学艺术家们,贡献给世界和未来的不是崔莺莺,而是红娘。像崔莺莺这样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在古今中外并不鲜见,像红娘这样活泼伶俐的婢女在古今中外也不乏其人,但像红娘这样能在生前身后赢得社会各阶层共同接受、全面认可的独特的婢女,千百年来却只有这样一位。
当今,红娘已成为媒人或媒婆的代名词,不仅在广大城乡的日常生活,即使公共媒体与政府新闻都把红娘作为媒人或媒婆的最佳称谓。历史上曾有过的别称,诸如执柯、媒妁、冰人、月老、保山之类,除月老还被继续沿用外,其他都因为过于陈腐或失之浮泛而退出了时代舞台,它们由于本身运用的狭窄已不适应当今社会公众的认知习惯。如果把它们作为媒人的代称,那么,肯定会使绝大多数社会公众莫名其妙。而红娘却不同,它没有时代的烙印和历史的局限性,从时间上说可以纵贯古今,从空间上说可以横跨中外,不论从语义学还是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称谓的优势都是其他称谓无法比拟的。在迄今为止的所有关于媒人或媒婆的称谓里,惟独红娘这个称谓是现实、普世并充满喜庆色彩的,它不含父母之命,虽有媒妁之言,却完全是从当事人的意愿出发的,更不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它既有对婚姻的严肃审慎,又蕴蓄着对当事人爱情的担当奉献,更有期待这种爱情之花能结出婚姻之果的成功和喜悦。正如今人所说“当用红娘指代媒妁时,多指那些乐为他人做嫁衣而又不计任何得失的良媒”[5],它特别符合近现代人对理想爱情婚姻想通过媒人来完成来满足的感情期待与心理需求。而执柯、媒妁只是一种行动,侧重对婚姻双方的介绍和联系,冰人、月老虽凸显了爱情的晶莹纯洁,甚至有一种带着神话传说的浪漫,却不免有些寒意,且不说喜庆,即使必要的温暖都不能保障;保山则过于强调结果,缺失了当事人的爱情,又兼寓了其他行业经纪和担保的公证人的意义;媒人或媒婆更是该行业的概括称谓,过于笼统,没有特色,不能引人注目。没有一个婚姻介绍所或征婚广告,愿意用执柯、媒妁、冰人、保山之类的字眼来招徕生意,月老虽未舍弃,但用得不多。红娘是一个出现于唐代的婢女的名字,却在近现代产生了新的意义与新的功能,这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深思的文化现象*媒人别称,除本文提到者,还有蹇修、红叶等。“蹇修”出自《离骚》,后世几乎未用过。“红叶”出自唐代“红叶题诗”,后世也不多用。这些别称,贯穿着从《诗经》到《红楼梦》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始终。红娘虽出现较晚,却后来居上。。
二
我们说过,作为文学人物的红娘最早出现于唐代诗人元稹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小说所写情节的年代是唐代贞元十六年(800年)*关于《莺莺传》的写作年代,迄今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唐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以陈寅恪、王季思、卞孝萱为代表;一种是唐贞元十八年(802年)九月,以孙望、吴伟斌为代表。参见程国赋《〈莺莺传〉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2年第12期;李丹、尚永亮《元稹百年研究综述》,《学术交流》2004年第4期;胥洪泉《〈莺莺传〉研究百年回顾》,《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我认为,此小说的写作年代虽存争议,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它所写情节的年代却很明确,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可以说,元稹所写情节的年代就是此故事作为素材开始进入构思并被传播的起点。。这篇小说是元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关于这一点,自宋王铚、明胡应麟、瞿佑至近现代鲁迅、陈寅恪以及研究此作的部分学者通过细致考证给予了充分肯定*关于《莺莺传》创作是否是元稹自寓的问题,迄今也仍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参见上注。我认为它就是元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是元稹自寓。因为在唐代,传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还没有脱离纪实进入虚构,多多少少都留有纪实的痕迹,而《莺莺传》这一点则更明显。。我们也赞同此说。既如此,那么,可以推断,他笔下这个红娘的原型,当然就是他见过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婢女,即小说女主人公崔莺莺原型的贴身丫鬟。我们无法考证元稹写的红娘的原型是否也叫红娘的名字,我们以为不叫红娘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元稹把自己都改成了张生,违心地为“始乱终弃”辩护,他想去污撇清,不愿让后世洞悉崔莺莺的原型跟他有丝毫关系。在他看来,改得越面目全非、越不露蛛丝马迹,越让他放心。但他又不得不把它写出来。不写出来,如骨鲠在喉,浑身难受,灵魂不得安宁;照原样写出来,又害怕斯文扫地,毁弃前程。因为这一年元稹22岁,这年秋,守选期满,将入长安参加冬集,仕途刚刚开启*参见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贞元十六年庚辰(800),二十二岁”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所以,连婢女的名字也不能跟现实生活的原型相同。惟此,他才不会授人以柄,既能不至于陷入当时受社会舆论谴责的漩涡,又能掩耳盗铃般地在身后保持贞节清誉。这是做了亏心事的作家,为了保护自我惯用的一种写作的曲笔和障眼法。然而,他终究还是写了出来,这说明他还有良知,还有底线。如果自寓说成立的话,那么,元稹这样做纯属庸人自扰,自欺欺人。
即使红娘的原型不叫红娘,而小说里把这个看似普通却很重要的婢女称为红娘,也绝不是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举。“红”字除了作为颜色和姓氏的意义外,还有喜庆、顺利、成功以及受人重视和欢迎等意义,这些意义与恋爱、婚姻的热烈、神圣、幸福、美满和令人羡慕等意义具有本质的同一性。“红”字简直可以说是中国婚恋或中国色彩的热词、关键词。如果要找一个词来概括中国人对婚恋理想状态的比拟和描述的话,那么,首选的也是最合适的词应该是“红”字。中国民俗学里就把嫁娶、丧葬仪式称为红白事,红被用来指代婚姻,已经约定俗成。中国人特别崇尚红色,它象征着光明和进步,代表着正义和希望,是充满朝气的新生力量和革命队伍。以鲜艳的五星红旗作为新中国的国旗,就具有这样的寓意。它已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感情和生命里了。另外,“红”字也有让人受惠、获得利益的意思,如今很流行的经济学术语红利的“红”就是这个意思。值得强调的是,它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而是被借用到各个领域,凡是共同参与经营取得成功的事业都会有可观的红利。红娘的“红”字与此意义也甚为吻合。红既是一种福利和公益,又是一种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如果再稍作延伸,我们就会发现,与“红”字相连组成的一些词语,也具有爱情和婚姻的意义,像红豆、红丝、红线、红鸾、红庚、红绿帖,或象征爱情,或代称媒妁,或主宰婚配吉兆,或专指婚约凭证,“红”字都是起关键作用的定语。而“红叶题诗”故事在唐代玄宗、德宗、宣宗、僖宗时期都出现过,真正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题红”文化现象*参见孟棨《本事诗·情感》、王铚《补侍儿小名录·贞元中进士贾全虚者》、范摅《云溪友议·题红怨》、刘斧《青琐高议·流红记》。。元杂剧《题红怨》、明传奇《题红记》、现代地方戏《红叶诗》都是由这一题材改编来的。
而“娘”字有一种含义指的是年轻的女孩子,与大娘的“娘”所指年长或长一辈的妇女具有不同的意义。它象征着年轻,代表着青春,还蕴含着圣洁、希望,是一种潜力股和能够带来预期效益的价值观。年轻的女孩子为未婚男女青年牵线搭桥,与婚恋的神圣性、纯洁性又取得了根本的一致。她们不像那些走街串巷的年纪大的媒婆,贪财嗜利,靠说媒谋生,根本不关心当事人的想法和愿望,使婚恋蒙上十分功利的世俗色彩。红娘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搭桥,完全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是出于想促成他们终身大事的热心、诚心、善心,不含任何企图,没有丝毫私欲杂念。这些意义,也使“娘”字增加了取名用字容易被选择的机率。
“红”与“娘”的联缀真可谓姓名的黄金搭配,都突出了生命、爱情、婚姻、事业的元气和底色,写法简易,音节响亮,寓意成功,象征希望,正因为如此,红娘就成了一个越来越受人喜欢、特别吉祥、能带来好运的名字。不仅如此,早在唐代,就有以红娘命名的流行歌曲。可见在唐代,红娘就是已不限于专指文学人物的固定名称了*参元稹《狂醉》诗有“舞引红娘乱打人”句,崔令钦《教坊记·曲名》有“红娘子”目,还有以“红娘子”命名的中药。另,发行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今存孤品邮票也称《绿衣红娘》,这都是因为元稹小说《莺莺传》里红娘的缘故。。无论怎样说,把这个婢女叫作红娘,是元稹对中国文学的一个巨大贡献。元稹之后,红娘能如此走运,也是他生前不曾预料过的。
再说,红娘能到崔宰相家做丫鬟,肯定经历了一番介绍、引荐和挑选。当时想获得丫鬟这个差事的女孩子也绝不只是红娘。她无疑是从至少三五个待选女孩子里挑出来的。她的出身、体质、相貌、性格、品行、能力,方方面面,都得符合崔宰相,尤其是崔老夫人、崔莺莺的要求和标准,虽不像当今需要政审或体检,但基本的考察、审查,诸如多方打听、了解与初次见面的问话、感觉以及此后的反复比较、思量,必须中意称心才行。像崔莺莺这样的大家闺秀,需要的并不是只知端茶送水、抹桌擦椅的很机械的使唤,而是在思想和精神上能与自己交流、有呼应有共鸣的心有灵犀的闺蜜。如果从这个意义来说,红娘角色的重要实在不亚于同床共枕的夫君。出身过于贫寒,体质显得羸弱,相貌平平常常,性格孤僻,品行欠端正,能力平庸,有些呆头呆脑、笨手笨脚的女孩子是不能入选的。从《莺莺传》及后来的文艺作品描写看,红娘很符合崔宰相家丫鬟的资质和条件。红娘入选本身就是她非常出色的一个有力证明,而且在一定程度代表了以唐代为中心的我国古代主流社会普遍的审美习尚与观念取向。她也不是出身于贵族的上等人家,上等人家的女孩子不会做丫鬟。即使中等人家的女孩子,也未必非要做丫鬟。这样看来,红娘极可能是当时下等人家的女孩子,像《红楼梦》里的鸳鸯、袭人、晴雯一样。崔宰相家与红娘,选择与被选择说到底仍是一件如同恋爱婚姻一样属于两厢情愿的事,恋爱婚姻要般配,小姐丫鬟也要般配,所谓红花要绿叶来陪衬,正是这个道理。但也有区别,下等人家的女孩子有誓死不愿嫁入豪门的,却很少有不愿去豪门做丫鬟的。因为嫁入豪门关系爱情和终生托付,讲究门当户对,而去豪门做丫鬟,只不过三五年的工夫,不会妨碍自身姻缘,根本用不着煞有介事。
红娘是一个让近现代人很愿意接受的指称媒人或媒婆的名字。正因为这个名字的独特性,作为文学人物的红娘一些不符合媒人或媒婆的特征,诸如十四五岁的年龄与做婢女的身份,竟被完全忽略了*王实甫《西厢记》说红娘“自幼伏侍”崔莺莺,据此推断,红娘到崔家的最小年龄当在五六岁,她伏侍崔莺莺十年左右,也就十四五岁了。王季思曾认为红娘是崔家家生婢女。我以为非。如果是,谱写莺莺故事的作品应该有所透露。另,《西厢记诸宫调》卷三有“一托头的侍婢,尽是十五六女孩儿家”的话,可见中国古代女孩子最大到十六岁后,一般就不适宜再做丫鬟了。。现实社会里的媒人或媒婆,年龄极少是十四五岁的,这种年龄的女孩子还不能胜任促成美满姻缘的职责,谁愿意让一个黄毛小丫头来决定终身大事呢?这多少有些轻率,说得严重点,岂不是儿戏吗?即使年龄再大些的未婚女青年,一般也不愿主动去做媒人,因为自己还待字闺中,哪有闲心思去为别人说亲呢?何况未婚女青年去说媒,不论怎么说,都对个人声誉没有裨益。尽管当今婢女已消失了,但新中国成立前,生长在豪门高第里的金枝玉叶,又有哪个没有婢女呢?然而,却都没有成为媒人或媒婆。那是因为婚姻何等神圣,低微的婢女还没有为主家小姐或公子说媒的资格。婢女没见过什么世面,不具备主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深广的社会关系,她们的地位决定了她们不可能做媒人。因此,文学人物红娘与社会角色红娘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就年龄和身份而言,文学人物红娘做媒说亲在现实社会里很难见到。在文艺作品里,红娘的做媒说亲是在特定环境下进行的,虽是十四五岁的婢女,却是促成崔莺莺婚姻大事的惟一人选。在现实社会里,做媒说亲的,几乎没有十四五岁的婢女,即使有也不是完全靠在她们身上。社会角色红娘不是文学人物红娘的简单照搬和机械挪移,虽都是红娘,但内涵和外延已发生了变化。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社会角色红娘是从文学人物红娘演变而来的,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至少说明文学人物红娘委实具备了成为社会角色红娘的基本潜质和必要条件。
红娘经历了唐宋以来各种文艺作品的反复传播才走进了公众视野,唐宋以来各种文艺作品在不断翻新、改编崔莺莺故事的同时,也把红娘呈现在读者和观众眼前。没有这些文艺作品漫长而不惮其烦的传播,红娘不可能成为作为媒人或媒婆的社会角色。如果从艺术样式的角度看,红娘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文言小说、说唱文艺戏曲、电影电视等样式来完成的,其中说唱文艺和戏曲的贡献最大。新的艺术样式的产生为红娘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和载体。而唐代以后正是新的艺术样式越来越繁盛的时期。红娘所以能走出文学,进入社会,与随时代发展产生的越来越繁盛的新的艺术样式有密切关系。如果只是一种样式,像最早描写红娘的《莺莺传》,没有别的样式,红娘的名字传不出去。即使有别的样式,却没有选择红娘,那么,红娘也不会大幅度地进入社会舆论中心,成为公众人物。尤为重要的是,越往后产生的艺术样式越具有大众化特征,传播时间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久,突破了文字的局限,利用除了阅读还通过凝视、聆听就可接受对象的认知本能,使占大多数的不识字的文盲和识字较少的半文盲以及文化程度偏低的普通百姓、群众成为接受主体。这样一来,中国故事普及率空前飙升,红娘传播范围成倍猛增。各种艺术样式为红娘走进千家万户做出了巨大贡献。红娘是在唐代以来的各种艺术样式里聚集和蓄积了足够的人气之后,才被作为社会职业的媒人或媒婆的代称,这个转型既十分独特,又非常成功*这些文艺作品主要指《莺莺传》《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南西厢记》《金圣叹评西厢记》、京剧《红娘》、电影与电视剧《西厢记》《红娘》等。。
三
红娘自唐德宗贞元十六年进入文献著录视野以来,迄今已1200多年了。这期间,她一直都在演变、传播,未曾消歇、停滞,但主体是文学艺术形象,并非社会角色。她是从何时起变成社会角色的呢?也就是说,社会上把“红娘”一词用来指称媒人有具体的时间、事件和语境史料吗?对此,风俗史、民俗史、婚姻史著作要么置若罔闻,要么笼统地说王实甫《西厢记》后就被用来指称媒人了*自张亮采著《中国风俗史》至钟敬文主编《中国民俗史》以及迄今出版的多种中国婚姻史著作,都很少提到红娘,即使偶尔提到了,也没有做进一步考证和阐释,遂使红娘何时从文学人物变为社会角色这一问题一直模糊不清,未能获得圆满解决。。实际上,情形并非如此。我们说,唐代红娘自然不是媒人或媒婆的代称,即使宋元明清提到红娘的很多文献,像《唐诗纪事》在第三、六、七卷,《南村辍耕录》在第十四、十七卷,《醒世恒言》在第十六、二十三卷,《金瓶梅》在第八、七十一、八十三回,《红楼梦》在第一、五、四十、五十八回,都不止一次提到红娘,而一次提到红娘的明清笔记、世情小说也不在少数。但从文本看,这些文献提到红娘,一部分是因叙述莺莺故事,所说红娘就是《西厢记》人物;另一部分是把红娘比作传递消息的信使,所说红娘则是《西厢记》人物的借用或引申,都还没有把她用来专指社会角色的媒人。清代官方和民间婚书在落款媒人姓名前写的称谓都是“媒人”,像《台湾私法人事编》第三章《婚姻》所收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婚书落款,在指称媒人时都写作“配婚媒人”“婚配媒人”“为媒人”“为媒者”等,婚书正文写的也是“月老”“冰人”之类,没有一处写红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启蒙。这次改革和启蒙,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作为领导者都先后提出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等进步主张,开启了婚姻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变的新风气,因为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遭遇冷落甚至被抛弃,红娘作为社会角色的媒人的机会自然就减少了。二十六年(1900年),蔡元培在提出再娶五原则后与黄仲玉订婚,虽是自主婚姻,但声明聘请叶祖芳做“媒介”。二十八年(1902年),天津《大公报》刊登了我国第一份征婚广告,《中外日报》刊登了《世界最文明之征婚广告》,都未聘请媒人。二十九年(1903年),章太炎在提出丧妻征婚四标准后与汤国梨订婚,婚仪当场所作《谢媒诗》有“于今有斧柯”句,媒人称谓仍是“斧柯”。此后八九年至中华民国建立,出现在舆论媒体和公众视野的各种婚姻(包括涉外),除了这些传统称谓,“绍介人”或“介绍人”成为媒人的一种新称谓开始引领潮流,红娘作为社会角色的媒人的称谓还没有被使用。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可以说是红娘形象演变的一个分水岭。自此往后,红娘作为社会角色的媒人的称谓使用便渐渐增多了。始于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被誉为“民国第一红娘”,在赴台湾前曾主持过150多场婚礼,许多名流像赵元任与杨步伟、陈西滢与凌淑华、冰心与吴文藻、沈从文与张兆和、李方桂与徐樱、蒋硕杰与马熙静,他都是介绍人或证婚人,真可谓盛况空前,破了主持婚礼次数的纪录。胡适虽戴着“民国第一红娘”的桂冠,但凡与他有关的婚姻文献还未发现有使用“红娘”字样的史料。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红娘形象演变迎来了新机遇。毛泽东在繁忙公务之余,也很乐于当红娘。1923年就为刘少奇和何宝珍牵线搭桥,这是他第一次做红娘,但还未使用“红娘”二字。后又为堂妹毛泽建与陈芬、夏明翰与郑家钧、和尚乐能与贫女月秀、王稼祥与朱仲丽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子女、晚辈当过红娘。其中,他为堂妹毛泽建与陈芬做媒的时间是1925年,对堂妹毛泽建说的“我知道,是要三哥为你当红娘哟”的话,是迄今所见有确凿文献记载的较早把红娘作为社会角色的媒人称谓的珍贵史料。1941年,在西柏坡简易的俱乐部里,毛泽东看了京剧《红娘》,对在场的王震说:“那是出好戏,那个红娘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去就是演红娘,在那里唱主角,去给新疆各族人民做好事。”1956年,建军节前夕,对王震又说:“你不但是屯兵边陲的大将军,也是一位最伟大的红娘。”受毛泽东影响,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贺龙、陈赓、王震、邓发等中共领导人都做过红娘。红娘进入了中共领导层的话语表述系统,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很有意义的变化*法国当代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认为,人们“这样说”而不“那样说”,受话语结构和话语权力制约。我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红娘从文学人物变为社会角色所起的话语作用,与福柯的话语理论颇有相通之处。参见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2、190页。。红娘的品格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红色政权的追求颇有犀通契合之处。鉴于此,红娘作为社会角色的媒人,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出现在世人面前,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努力提倡、积极推介具有直接的关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话语里的红娘,仍是一个被喜欢使用的概念,还不是一种职业。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大陆改革开放,政府鼓励发展个体经济,以红娘命名的职业婚姻介绍所出现了,将红娘作招牌,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上征婚才成为时尚和潮流,“红娘”一词是当今婚爱流行语[6]。而各种文学、文艺作品在描写婚恋故事时也常常把红娘作为媒人的代称。至此,可以说红娘从文学人物到社会角色的漫长转型才算真正完成。
自中华民国建立到新中国诞生尤其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不同时期的婚姻法都还没有使用过“红娘”一词,但红娘作为社会角色的媒人已是毫无争议的事实。这个时代的红娘,作为社会角色的意义第一次超过了作为文学人物的意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大凡提到红娘,所指几乎都是作为社会角色的媒人,而不再是文艺作品里的人物了,即使是文艺作品里的人物,也是作为社会角色的媒人的引子或铺垫,归根到底要表达的还是作为社会角色的媒人。这真是一个具有质的飞跃性的巨大转变。当然,红娘作为文艺作品里的人物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她继续活跃在电影、电视、网络等现当代媒体,只是名气、人脉以及被社会所需要的实用功能已远远不能跟作为社会角色的媒人的红娘相比了。作为文艺作品里的红娘,观赏她可以陶冶性情,但不观赏她也不妨碍生活,而作为社会角色的媒人的红娘,虽说不是必不可少,但没有她则肯定会显得不太圆满甚至是一种缺憾。她已融入现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作为媒人的“红娘”二字,只要是稍有社会阅历的中国人或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外国人一听都能明白它的意思。这种频繁被社会所需要的吃香态势也远非作为文学人物的红娘所能比。作为文学人物的红娘,到现在已走过了1200多年;而作为社会角色的红娘,如果把她进入社会舆论与公众视野的上限定在中华民国建立的1912年,到现在她才走过了100年多一点。就时间看,前者约12个世纪,后者约1个世纪。从中华民国建立到现在的1个多一点的世纪,红娘作为文学人物和社会角色可以说是共生同行,但普及面、知名度却判若云泥;前者时间是后者12倍,但社会接受、认可度却不及后者千万分之一。从现在到以后很长时期,红娘作为文学人物和社会角色仍能共生同行,但它们的地位会越来越悬殊,作为文学人物的红娘越来越落寞,而作为社会角色的红娘则越来越忙活。我们认为,将来有一天,后者会完全取代前者,在人们的观念里,红娘就专指社会角色,不再兼任文学人物了。这或许就是社会角色不同于文学人物的奥妙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红娘不仅仅是社会角色的媒人,而且被广泛运用于其他行业,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界,都出现了穿梭、往来于个人或团体之间起牵线搭桥作用的红娘的身影*比如,王学梅《党的南湖红娘王会悟》,就从政治角度来阐释红娘。参见《党史纵横》,2015年第6期。。红娘的职能不限于婚姻,性别不只是女性,地域也不囿于中国*据考证,《西厢记》早在清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五年(1872-1880)间就有了法语译本,随后英、德、俄、日、西班牙等语译本也相继出现。。近年来,受中国文化影响,一些外国人把婚姻介绍人或事业联络人称作红娘的新闻也常见诸报端*《京华时报》2010年12月6日第5版刊发了配图新闻《外国红娘传授经验》,报道了一名“美国红娘”指导男士如何给女士献花的消息。。作为备受世人喜爱的社会角色,红娘越来越多地出入于当代各种社交应酬场合,成为当代人进行沟通、交际、联谊活动的重要介质。我们坚信,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作为社会角色的红娘必将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1]〔德〕尧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C]//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6.
[2]汤显祖.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C]//徐朔方.汤显祖全集编年笺校(第四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
[3]金圣叹.读第六才子〈西厢记〉法(第四十八、四十九)[C]//金圣叹评〈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蒋星煜.红娘的膨化、越位、回归与变奏[C]//〈西厢记〉研究与欣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5]任清.八面玲珑话媒人·圣洁的红娘[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4.
[6]刘新平.百年时尚(1900—2000):婚姻中国[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钟昭会)
2016-03-15
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曲学史研究”(10XZW021)。
李占鹏(1965—),男,甘肃正宁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戏曲史。
I207
A
1000-5099(2016)04-013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