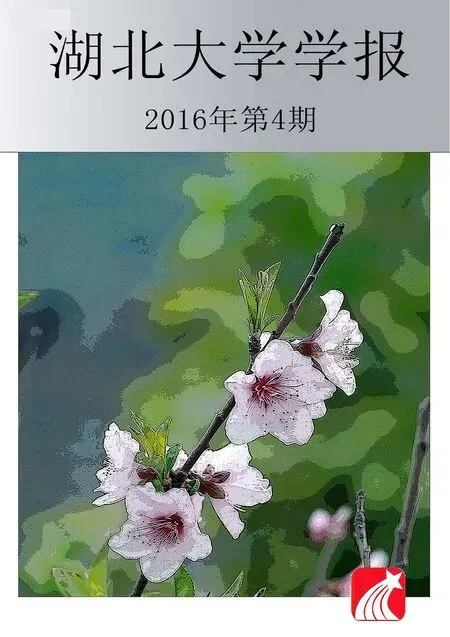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学生日常管理探析
2016-03-08赵厚勰
赵厚勰,陆 佳
(1.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62;2.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200234)
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学生日常管理探析
赵厚勰1,陆佳2
(1.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62;2.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200234)
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的学生日常管理主要包括对学生学习活动的管理、对学生日常生活的管理和对学生宗教活动的管理。从教育活动史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和分析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的学生日常管理活动,可以发现其具有积极的影响:严格的学生学习活动管理保证了较高的教育质量,教会学校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名望,其学术成就和影响之能被社会承认,应该说与这种严格的学习活动管理有很大关系;家庭化的日常生活管理造就了学生爱校如家的情怀,许多教会学校的校友在数十年之后,内心仍然具有一种浓厚的母校情结和对母校强烈的精神认同,应该说与他们当年在母校所接受的家庭化的教育密不可分;持续的宗教活动管理影响了学生的品格养成,教会学校举办的一些宗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学生找到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基督教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学生良好品格的形成。
民国;教会学校;学生日常管理
教会学校自清末创办,发展到民国时期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了从教会中小学到教会大学的较为成熟的体系,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近年来对于教会学校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从教育活动史的视角切入,探讨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学生日常管理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教育活动史研究是近年来在教育史学界逐渐兴起的一种研究范式。它“打破了此前教育史学仅关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窠臼,主要以历史上教育活动主体微观的、具体的和实在的日常教育活动的发展及演变为研究对象”[1]。本文拟从教育活动史视野出发,深入探讨和分析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的学生日常管理活动。
一、教会学校的学生日常管理
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的学生日常管理主要包括对学生学习活动的管理、对学生日常生活的管理和对学生宗教活动的管理。
(一)对学生学习活动的管理
在学生的学习方面,教会学校一般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如福建的一些教会中学有着严格的出勤、考试和升留级制度。考试分为平时考、月考、学期考,平时考试成绩占月考成绩的2/3;学期成绩有两门主科不及格者留级;其他不及格者准予补考,补考后仍有一科不及格者准予“积欠”升级;但初二升初三和高二升高三要全部“清欠”,不得带不及格学科升入毕业班,所以被称为“鬼门关”。一年级或二年级连续留级两次者退学[2]135。天津工商大学附中规定,学生上课如迟到,进校后要先到训育科填写一张红色的迟到上课证,持证才能进教室听课。每位教师都持有班级的学生座次表,违反纪律者,或当面告诫,或作个记号,扣操行分[3]126~127。
教会大学对学生的考试管理也非常严格。如震旦大学仿效法国学校的考试制度,不论预科或本科,都实行周考制度,每星期六轮流考试一门功课。此外,每学期举行两次月考和学期结束考试,到年终举行年考。周考有时笔试,有时口试,月考、学期考和年考,既有笔试,又有口试。考试制度非常严格,预科学生毕业后能升学的约2/3,留级的约1/3。评分采用20分制,11分以上为及格,18分的已属凤毛麟角,19分的更少,20分的一般没有。笔试时监考很严,大考多在大礼堂举行,本科、预科混在一起,共有几百人,试卷用五色彩纸,同年级同学座位分散,前后左右都是不同班级的学生相互穿插,以防联络舞弊。震旦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如此回忆当时的毕业考试:
法学院毕业考试范围广泛,四年的功课全部要考。首先,用法文做论文,时间大约半年多,最后几个月是笔试。好在同学们平时考惯了,还不觉得怎么吃力。最不易应付的是口试,主考人不是本科教授,而是从外面邀请来的,多数是法院官员,加上几个教授和老教友。先是中文毕业考试的口试,主考先在教室里商量好,然后分科坐定,每科主考对面留一个座位让考生坐。这样的座位有十多个,也就是说要考十几门功课,考生先后坐上这十几个位子去应付口试,口试完毕,再集合在教室外等候发榜。接着是法文毕业考试,主考大多是法国官员。笔者参加毕业考的那一年,主考人是法租界公董局督办、法领事等。考试范围很广泛,评分也很严。最后的考试是口述论文大意,由主考人提出问题,必须立即答复,而且不能被主考人驳倒,否则就不能毕业。考生全部考完后出场,等候发榜。宣布及格名单后,学生鱼贯入室,领取文凭,主考人当场在文凭上签名,并向及格学生握手祝贺,学生则向主考人道谢。接着,教务长又把文凭收回去,留在举行毕业典礼时重行发给。[4]29~30
为了培养学生的品格,有不少教会学校还实行无人监考制度。如湘雅医学院就曾实行过“Honor System”(无人监考制)。根据学生回忆,在每次考试时,学校不安排监考人,老师出完试题就离开了,让最后一位交卷的考生,将全部试卷收齐送交老师。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学生舞弊的。万一发现有人舞弊,处罚将非常严厉,直至开除学籍[5]605。通过这种举措,学生养成了自治、自尊、以诚实为无上光荣的观念,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一般来说,教会学校对学生的课外活动不会多加干涉。学校往往鼓励学生开展课外活动,这些活动多以学生自主进行,同时教师开展必要的指导工作。但是如果学生在课外活动方面花费时间过多,以至于影响到他们学业及正常生活的时候,学校就可能会采取一些必要的举措。金陵女子大学就是如此。1924 到1925学年的第一学期,学校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有很多学生在课外活动方面花了大量的时间。过多的社会活动、近乎过度的礼品消费,以及完全不必要的接物待客耗费了学生太多精力和金钱。许多学生觉得力不从心。因此学校决定实行“积点制”(point system)管理。这一制度规定,任何学生在一学期内从事课余活动的时间都不容许超过20“点”。与此同时,积点制也提高了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如果某门课程仅得60分的话,只能算及格,但得不到积点。积点的标准是根据各门课的学分及考试分数的多少而定。学生毕业时,除学分达到规定标准外,积点也必须达到要求。包括聚会、表演、班级活动在内的所有活动都必须接受检查,以核定所需要的时间和经费。学生不容许私自给教师送礼物,集体赠送的礼物及其所要花费的资金数量须经委员会审核通过。结果,学生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被用到了更加有价值的方面[6]56~57。
(二)对学生日常生活的管理
对学生日常生活的管理主要指对学生衣食住行的管理。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因学生多来自官商家庭,在衣食住行方面颇有些讲究,学校的管理也较为严格。
在穿衣方面,大多数教会中小学都定制有各自的校服,显得较为整齐划一,社会人士一看便知其身份。如上海启明女校的制服因其式样别致,据说受到教育局局长和首席督学称赞,而通令其他女中仿行[7]292。教会大学则一般不像中学那样要求穿着统一的校服,穿着打扮因人而异,但学校的要求同样严格。如金陵女子大学不许学生穿着不符合学校规定的服装和饰品。据校友孔宝定回忆:“有一次我和自文外出采购,我这个痴迷大红色的女孩,发现有红色袜子出售,喜出望外,于是就兴高采烈的选购一双返校,第二天得意洋洋的穿上这双红袜就去上课了。后来吴校长看到了,婉转地告诫我,一个女大学生穿着要以庄重得体为宜,一个人的服饰往往会影响她的仪表,希望加以注意。我马上体会到校长的关怀,十分感动,从此不再穿红袜。”[8]124
在饮食管理方面,教会学校一般要求学生遵守作息时间,按时进餐厅吃饭。据金陵女子大学校友回忆,“记得早晨7:00打钟用早餐,7:30玻璃门挂上‘不入内’的牌子,就不准进餐厅了”,“三餐之间不吃零食;谁要吃零食,请你在用餐时吃”[9]117~118。有的学校将学生的膳食交给学生管理。如华中大学成立后不久,在学生膳食管理工作上,一开始是由公寓管理员承担,但从1930年起,学校将伙食管理的具体事务交给一个由几名男女学生组成的伙食管理委员会管理,校评议会委派一名教员作为该委员会的顾问。伙食委员会负责厨师的雇佣、辞退以及食品的购买,还负责转达学生对伙食所提出的意见。由于这种管理方式运作良好,华中大学在膳食管理方面一直沿用这一模式。它非常成功地使华大校方避免了因伙食供应不好而遭受责难[10]56~57。
教会学校在学生宿舍管理方面较为严格。震旦大学的每一个学生宿舍都有一名外国人担任舍监管理。舍监直接受校长指挥,职权比教授和学院院长大得多。每晚9时,舍监要查房间,经常在宿舍门外小窗口向内窥视学生是否都在室内,如果不在室内,就要追问。尤其是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特别注意,不是本宿舍的学生,不准逗留在内,必须回各自宿舍[4]34。
在日常出行方面,教会学校也有着严格的规定。以武昌文学书院为例。据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该校的校友回忆,当时武汉地区的教会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比中国其他公私立学校要严格,而文学书院比一般教会学校又更严格:
开学以后,学生一律不准自由外出。门房设在大门口,凡因事外出者必须有校监或院监批准的条子,否则门房不仅不准外出,还可给予严厉的批评,甚至把学生带至校监或院监办公室,请予处分。凡是家在武汉的高年级同学,每逢星期六下午五时起,可以自由离校回家,但星期天下午五时以前必须返校,过时如无家庭证明函件,不准进校门。凡是一年级新生,特别是中学部新生,家在武汉者,到星期六下午四时以后,须家庭有人到校相接,方准离校回家,否则,一律不准自由离校回家。星期天返校时间与高年级的同学一样。文学书院学生的上下课和自习以及吃饭、就寝等一切活动,完全以书院天主教堂的钟声为标准行事。当下晚间自习约一刻钟,所有的自习室就都灯熄门关了,如果行动不快,就会被关在里面,我初上学时,就吃过这样的苦头。[11]144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很多教会学校纷纷明确地提出实行“家庭化”宿舍管理。如福州协和中学的教职员在学校与学生同食宿,即使是外国教员也如此,并经常在课余指导学生。福建格致中学各班除了有班主任外,学生还可自选一名教师作为班级的顾问或导师,公私问题皆可请教之,师生感情亲密,亲如父母[12]556。为了更好地实行“家庭化”管理,一些女子学校,如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以及上海中西女中、北京慕贞女校、湖南福湘女中等学校创立了“姐妹班”制度。所谓“姐妹班”,就是为了促进同学之间的交流,尤其让入校的新同学更好及更快地适应新生活,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同学结成姐妹班。同学之间亲如姐妹,关系融洽。此外,教会学校对于已毕业的校友也很注重联络。如燕京大学将每年5月的第一个礼拜天设为“返校节”,这一天外地校友集中返校,和在校师生一起共同会餐、活动,热闹非凡。
(三)对学生宗教活动的管理
教会学校既然是由传教士们创办的,当然很注重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这几乎是所有教会学校的共同特点,各校在这方面也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并严格实行。早期的教会学校,一般都强制要求全体学生读圣经及参加宗教仪式活动,无论信教不信教的学生都是如此。震旦大学1940届毕业生黄渊回忆说:
在震旦,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学生分别居住,前者住四舍大楼,后者住七舍大楼。两类学生都是每日早6时起床,8时上课,上午最迟的课11时半结束;下午1时半上课,最迟的课5时结束;晚7时在宿舍或图书馆自修,9时结束;9时半熄灯。……这是一般的规则。至于对教友学生(即信教的学生)则另有教则:晨6时半,由领班的同学(即热心教友)带领列队在楼房门前的走廊里念早祷经文(包括起身经文、圣母经文、天主圣三经文和早祷经文),7时进伯多禄教堂做早课(即拜天主之意),晚自修后9时10分再由领班同学带领念晚祷经文(包括天主经文、圣母经文,有时加玫瑰经文和晚祷睡前经文)。每逢复活节、圣体降临节、圣灰节和圣诞节等较大的宗教节日,则一起进教堂望弥撒,时间多在早6时至8时左右,由宗教指导神父在他们的房间内大揿电铃,召集全体教友同学齐进教堂。如果无故不去参加这宗教仪式,就被认为不是“热心教友”、“对宗教冷淡”,会影响到升级和毕业。评定学生的“好”与“坏”,此亦为标准之一。逢主日(即星期日)早晨也要进教堂望弥撒,主祭的神父多系自己的师长神父或这个伯多禄教堂的本堂神父。晚6时降福,热心教友还在主日进堂时“告解”。所谓告解,就是向神父忏悔,忏悔在一周中犯了哪些天主教十诫以及灵魂上(即思想上)犯了哪
些罪,求神父降福宽恕;有时神父要罚他诵经或拜若路等才能免罪。按教规每一教徒每年至少须告解一次。每逢星期五为小斋,在那天只许吃半饱,不许吃大牲畜的肉,只许吃鱼、禽肉类,据说可以避免肉体冲动而不犯罪,同时有纪念耶稣受难之意。[13]269~270
虽然早期的教会学校强迫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宗教活动,但其实信仰是无法强迫的,黄渊就是如此。虽然他是基督徒学生,但在他看来,震旦大学的“种种清规戒律遇到像我这样的不虔诚的教友,往往忘记小斋,一年不告解一次,到主日不去望弥撒,甚至和‘异教徒’(指非天主教徒)结婚,亦不禀告神父,几乎完全脱离了宗教生活,这是神父所极不满意的,但亦无可奈何”[13]270。
20世纪20年代,教会学校在经历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绝大多数学校相继取消了对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的强制性要求。燕京大学在1922年首先宣布废除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主日仪式和教堂礼拜的旧习,并缩减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的时间。这一举动遭到一些教会人士的反对。但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认为,由于教会学校实行《圣经》必修和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已经多年,人们习惯于用教堂中拥挤的人群和《圣经》课良好的出勤率来衡量宗教教育的成绩。然而,人们常常忽视了这种强迫所产生的恶果。事实上,很多教会学校的学生由于这种强迫产生了对基督教的反感,而他们的反叛,进一步刺激了其他人对基督教的攻击。司徒雷登的这种观点为许多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和中国基督教的革新人物所赞同。一些人干脆提出废弃“宗教教育”的名词,而以“人格教育”代之[14]232。尽管如此,教会学校的宗教活动以及对学生宗教活动的管理仍然持续开展,这也是教会学校与其他学校的重要区别之一。只不过,后期的教会学校更重视引导学生参与宗教活动,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强制性要求。
二、教会学校学生日常管理的积极影响
(一)严格的学生学习活动管理保证了较高的教育质量
教会学校对学生的日常管理,其严格程度是超过一般非教会学校的。客观而言,为了保证学校的教育质量,这种严格的管理是无可厚非的。虽然有些学生觉得这种管理似乎是严格得有点过分,而奋起反抗,乃至罢课。如齐鲁大学前身之一的广文大学就曾在1915年爆发过一次学潮。学潮的起因是学生认为学校的规章制度过于严苛且不合理,于是全体罢课,要求取消这些繁苛的规则。“校方不让步,双方僵持很久。后来传教士把学生代表关到楼上一个教室里,不准随便出入,勾结了潍县县长,派兵把学生强行解散。学生代表中的积极分子,有的被开除学籍,有的受停学一年或二年的处分。一九一六年学校重开,以往的一些为学生所反对的严苛的规则,都取消了。学生的斗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5]83当然,像这种因学校的严格管理而导致学生罢课的例子毕竟是极少数。
教会学校这种十分严格的学生日常管理,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对学生的高淘汰率。教会大学的淘汰率一般都在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如湘雅医学院第三班学生预科人数为36人,到毕业时只剩下4人,淘汰率为88.9%(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档案馆:《私立湘雅医学院概况》,1932(民国二十一年),编号:M W-73,第20页)。1920年2月27日,齐鲁大学文理学院教务会议决定:有9名学生因3门功课不及格而退学;有2人因2门功课不及格一人重考,一人降级并重新进行入学考试;另有9人因有2门课不及格而留级(齐鲁大学档案:《ARTS FACULTY M INUTES》,编号:J109-01-421,第14页)。燕京大学在1937年有43名学生因成绩欠佳而被劝退[16]200~201。又如1936年圣约翰大学的文、理、工学院学生的总人数,一年级为170人,二年级171人,三年级86人,四年级69人,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从二年级到三年级学生人数缩减了一半的情形。其中原因,有的是学生出国留学,但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学生学习跟不上而被淘汰。虽然毕业班有69人,但实际上到毕业时,毕业生人数还要减少[17]420。天津工商大学也是如此。其首批学生入学时是48人,毕业时只有工科8人,商科4人,共12人参加毕业典礼。第二批毕业学生更少,工科3人,商科5人,共8人。第三批学生为工科8人,商科3人,共11人。以后也是常有一些学生未能完成学业,中途离校。这在历年毕业纪念刊中都有所反映[18]166。像这样的例子在教会学校里真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客观来讲,教会学校这种严格管理和要求学生,并不断淘汰一部分学生的做法,虽然引起不少人的批评,但它毕竟保证了毕业生的高质量。由于学校极高的淘汰率,对在校学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迫使学生不得不重视学习以及在校的表现,从而有力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水平,也有利于良好的学风和校风的形成,保证了学校的教育质量。教会学校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名望,其学术成就和影响之能被社会承认,应该说与这种严格的日常管理是有很大关系的。
(二)家庭化的日常生活管理造就了学生爱校如家的情怀
实施“家庭化”管理,让学校成为一个“大家庭”,这是民国时期许多教会学校管理者提出的目标。这种目标意味着一种温馨、平和的校园氛围和平等的人际关系。
教会学校的学生之间虽然也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客观地讲,由于学校管理制度较为严格,并且实行民主、自治的学生自我管理,学生干部如班长、寝室长等一般由学生民主选举产生,这种管理模式大大增强了学生的自治能力,一般的纠纷都能自行解决。学生即便有矛盾和冲突,一般也不至于太过激烈。总体看来,学生之间还是较为和谐的,同学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不少同学关系至为亲密,犹如兄弟姐妹一般。
值得肯定的是,为了让学生尽快适应学校生活,使他们在一种和谐融洽的环境中更好地学习与成长,教会学校很注意在制度上加以良好的引导。一般说来,新生入学时往往有很多不适应之处,许多学校则采取各种措施,比如迎新会、文艺演出等方式,努力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熟悉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这其中既有教师的引导和参与,也有高年级学生的积极参与。一些学校的“姐妹班”制度更是被校友广为称道。在金女大,每年开学典礼上,高年级的“姐姐”就会拿着抽签得到的名字认领各自的“妹妹”。“新生住的房间里一定有一个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姐姐’同住,便于在各方面照顾她们,使这些新来乍到的‘妹妹’能很快习惯新的生活,也使当了‘姐姐’的高班学生学会关心照顾别人,培养了学生间互助友爱的精神”[19]111。学生对“姐妹班”制度极为认同,很多姐妹班学生毕业几十年后仍然保持着好友关系甚至延续到下一代。平时,由学校组织的同学之间的联谊性活动也非常丰富。对于毕业班同学,学校也会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欢送。这些做法形成了教会学校的优良传统,一代代流传下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学校不仅有着较为严格的纪律,同时还有一种家庭般的温情。教会学校这种“学校生活家庭化”的管理,使得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具有一种浓厚的人情味和家庭氛围,也使得师生具有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家的归属感。经过时间的积淀,这种感情愈发珍贵,成为他们生命中永远也无法忘怀的记忆。即使经历无数的风风雨雨,这种记忆仍然是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许多教会学校的校友在数十年之后,内心仍然具有一种浓厚的母校情结和对母校强烈的精神认同,应该说与他们当年在母校所接受的家庭化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三)持续的宗教活动管理影响了学生的品格养成
毋庸讳言,教会学校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传教士,特别是近代早期入华的传教士来说,他们之所以从事教育,既不是由于教会愿意对发展中国教育承担专门职责,也不是传教士对从事教育活动怀有特殊兴趣,而是为了争取教徒,完成传教使命;是为了征服中国,使西方可以自由地扩展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20]5。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受到了一定的抵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尽管教会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步走上世俗化、本土化的进程,但始终没有放弃宗教上的追求。然而,这种试图在精神上和价值观念上影响乃至改变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努力,最终并未能成功。
但是,实事求是地看,教会学校所开展的宗教教育,对学生的品格培养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首先,教会学校举办的一些宗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学生找到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如震旦大学学生熊斗寅所言,虽然他并不真心信教,但他“喜欢教堂那种神圣的氛围。每次当我心情烦躁时,一走进教堂就有一种清新的感觉。特别是望弥撒,那悠扬的管风琴伴随着唱诗班的颂歌和那阵阵飘香,你会暂时忘却一切烦恼。我想此时此刻我接近宗教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家的巨变给我带来的沮丧和迷惘。我从宗教活动中多少得到一丝慰藉和渺茫的希望,但这并没有构成我的信仰”[21]72~73。其次,基督教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对学生良好品格的形成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基督教教义有要求信徒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主张“奉献”、“牺牲”、“服务”等内容,它们在客观上有利于塑造人的良好品性,同时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是有利的。
20世纪20年代末,教会学校纷纷立案以后,不再将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也不再强迫学生进教堂、参加宗教仪式活动,但对学生品格的教育并没有放松,转而以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来影响学生的品德。如为了学生操行的评定,金陵女子大学确定了十条标准,要求教师从以下十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考查和评定:一、举止仪容;二、银钱使用;三、消遣方法;四、言行诚实;五、工作认真不懈;六、爱护公共用物,尊重他人利益;七、慎言择行;八、合作精神;九、任事负责可靠;十、富于同情,乐助他人。[22]189~190这些规定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基督教价值观的反映,也表明教会学校在学生培养方面非常重视学生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培养。因此,教会学校所培养的学生,其个人品格基本都不差,甚至很多人受到基督教“博爱”、“奉献”、“牺牲”和“服务”等观念影响,日后作出了非凡的成就与贡献。
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主要由欧美的传教士们创办,其办学的初衷,是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并由此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由于种种原因,教会学校最终未能实现这个目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教会学校彻底退出中国大陆,其所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也随之终止。虽然如此,教会学校在教育事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影响仍然值得肯定,表现在学生日常管理当中即是如此。教会学校对学生学习活动的严格管理,使其教育质量得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准。教会学校所实行的家庭化的日常生活管理,造就了学生浓厚的爱校情结,使母校成为万千学子心中永远的精神家园。而教会学校对学生持续不断的宗教活动管理,客观上对学生品格培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对我们今日的学校教育有着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1]周洪宇,李艳莉.论教育活动史多维视野的实现途径[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2]薛来弻.八闽之光——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志(1881-2001)[M].福州: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01.
[3]于学蕴,刘琳.天津老教堂[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4]刘麦生.回忆震旦大学[M]//陆坚心,完颜绍元.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8).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5]凌敏猷.从湘雅到湖南医学院[M]//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17):文化教育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6]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M].杨天宏,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7]胡午峰.启明女校校史[M]//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9):教科文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孔宝定.吴校长对我的教育和关怀使我终生难忘[M]//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金陵女儿(续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2000.
[9]吴柳琪.怀念吴贻芳校长和母校[M]//金女大南京校友会《金陵女儿》(续集)编写组.金陵女儿(续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2000.
[10]柯约翰.华中大学[M].马敏,叶桦,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1]段继李.武昌文学书院的回忆[M]//湖北文史资料:一九九○年第三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
[12]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基督教天主教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3]黄渊.我所了解的上海震旦大学[M]//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4):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14]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15]张士新.我所知道的齐鲁大学[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山东文史资料选辑(16).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16]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17]郑朝强.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M]//《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精选(5).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18]侯杰,范丽珠.津门历史名校——天津工商大学[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19]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M]//吴贻芳纪念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20]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21]熊斗寅.冲浪人生[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
[22]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黄文红]
G40-09
A
1001-4799(2016)04-0148-06
2015-09-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BOA130117
赵厚勰(1971-),男,湖北潜江人,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史学研究;陆佳(1992-),女,江苏连云港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