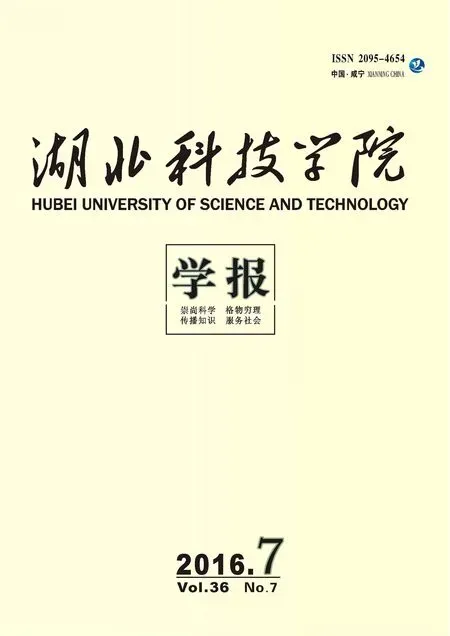苏芬战争与芬兰对苏政策演变
2016-03-07王鹏辉
王鹏辉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苏芬战争与芬兰对苏政策演变
王鹏辉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芬兰和前苏联是邻国,双方有一千多公里的边界线。历史上,芬兰曾经被沙俄帝国统治,成为其公国;独立之后则处于比较矛盾的状态,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靠拢西方,但是由于自身的位置而又不得不采取与前苏联和平相处的政策。其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芬兰一直秉承中立政策。在1939年底曾因维护国家主权和前苏联爆发了冬季战争;然后在1941年夏又因想复仇而跟随纳粹德国入侵前苏联(续战),最终失败收场。在芬兰对苏政策的演变过程中,苏芬战争(包括1939—1940年的冬季战争和1941—1944的续战)占有重要地位,对于芬兰对苏政策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苏芬战争 ;东方战线 ;和平中立政策
芬兰和前苏联同是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国家,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芬兰的对苏政策多次变化:从19世纪初开始,芬兰被俄国统治,成为俄国控制下的公国;独立后则处于比较矛盾的状态,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靠拢西方,但是由于自身的位置而又不得不采取与前苏联和平相处的政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奉行;后来又因国家利益的关系爆发了战争,分别是1939年底—1940年初的冬战和1941—1944年的续战,双方兵戎相见;而到了苏芬战争结束后,芬兰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从现实角度出发,采取了对苏友好的和平中立政策,这其中的变化耐人寻味。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对芬兰而言,前苏联这个邻国实在是特殊,两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不可能成为盟友,但是地理位置又决定两国不可能相互隔绝。因此,对苏的中立外交政策成为其外交政策中的指导思想。在上述变化中,苏芬战争起了很大的转折作用。本文以苏芬战争为立足点,阐述了这场战争对于芬兰对苏政策演变的影响,所叙述的历史主要集中在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
一、芬兰独立后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对苏政策
经过独立初期的混乱之后,芬兰的对苏政策很快得到确定,即采取中立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前苏联保持和平往来,同时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深化与西方的经济往来,以此来平衡前苏联的影响。
艰苦的国内战争,使得苏俄国力凋敝,与邻国关系紧张。为缓和周边局势,进行经济建设,苏俄与芬兰都想结束两国敌对状态,遂于1920年10月签订了《多尔帕特和约》,确定了两国的边界,“前苏联将贝柴摩省划归芬兰作为对芬 兰1884年把卡累利阿地峡一块地方割让给沙俄的补偿。”[1]
经过了艰苦的战争时期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的相继失败,列宁实际上放弃了“国际革命”的设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学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相处,因此,此时的苏俄(1922年底开始称苏联)的重心放在了恢复国民经济建设上面,外交政策趋向缓和,注重与邻国的和平相处。但由于芬兰与苏俄相邻,芬兰政府及欧洲国家担心芬兰被赤化,发生苏俄式的革命,所以在外交政策上对苏俄保持了很高的警惕(在1923年,芬兰共产党被取消了合法的地位,转入地下)。不过,芬兰对苏的和平中立政策并未改变,仍然在执行。由此两国关系趋于平稳,而且经贸往来也得到发展,在前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芬兰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二、20世纪30年代(冬战前)芬兰的对苏政策
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针对前苏联的消极变化,给平稳的苏芬关系蒙上阴影。芬兰苦心维持的对苏和平中立政策并没有持续下去,因为国力日益强大的前苏联不满足于现状,双方关系面临着新的问题。
(一)苏芬关系在国际形势影响下的变化
到了20世纪30年代,苏芬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不利的变化。引发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从2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前苏联的态度就开始发生转变。1927年5月27日,英国悍然宣布断绝同前苏联的外交关系,废除1921年英苏贸易协定。而且,1928年的《非战公约》一开始也把前苏联排除在外。芬兰不可避免地受到消极的影响,1930年到1932年期间,芬兰在拉普阿地区出现了农民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而且,在1932年还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暴力干涉。
到了30年代,西方大国继续敌视前苏联,试图祸水东引,纵容法西斯的侵略。这使得自认为处于“资本主义包围圈”的前苏联感到极大的不安,也把芬兰推到了风口浪尖的位置。为改善自身的处境,前苏联多次与芬兰秘密谈判,调整两国边界但未取得任何结果。于是,前苏联开始与纳粹德国接近,1939年8月,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附有的“秘密附加议定书”对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界线作了规定:“当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属前苏联势力范围,德国和前苏联在波兰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一线为界。”[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前苏联为防止战火东延,巩固西部边境的安全,从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间,用各种方法把国境线向西推进,构筑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谓“东方战线”的防御带。而与芬兰的领土交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芬兰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危机。
第二,1929年,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芬兰受到严重影响。芬兰在经济上经历了严重的危机,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激化了政治上的矛盾:一方面,是由于前苏联的迅速发展和在经济危机期间的良好表现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左翼思潮涌动;另一方面,芬兰比较担心共产主义的扩张,因为前苏联一向自诩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积极对外输出革命;虽然两国之间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但是芬兰还是担心前苏联的扩张会影响到本国的中立地位及国家利益。
(二)苏芬战争战前的芬兰对苏政策
尽管两国的关系在30年代出现了消极的变化,但是芬兰的对苏政策却依然是中立的和平外交政策,甚至用条约固定下来。因此也可以说,30年代的芬兰对苏政策是20年代对苏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不过,30年代的前苏联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国力大为增强,其外交政策变得比较强硬。在两国和平相处的背后,危机也随之而来。
在国际形势相对平静的1932年,苏芬两国调整了相互之间的关系,签订《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互不侵犯现有边界,避免任何指向对方侵略行动。条约还宣布:双方“将始终致力于以公正的精神解决它们之间的任何性质或任何根源的争端”。这项条约一度缓和了两国之间的矛盾。1934年又进一步确定此协定为十年有效。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对“侵略”的任意解释,该条约还对“侵略”作了规定:“侵略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或政治独立的任何暴力行为,即使未经宣战并避免战争征象者,应被视为侵略行为。”[3]
然而,芬兰政府努力维持的芬苏和平相处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羽翼丰满的前苏联政府并不满足于芬兰的中立,想谋求更大的利益。早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前,前苏联领导人就担心,“芬兰有可能轻易地成为德国或英法这两个主要帝国主义集团中的任何一个采取反苏行动时的进攻基地。”[4]因此,前苏联一直想改变芬兰政府的立场。从1938年4月起,前苏联就以加强北方防务需要为由,多次向芬兰政府提出获得租借汉科半岛和芬兰湾的某些芬兰所属的岛上设防的权利,但都遭到坚守中立政策的芬兰政府的拒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前苏联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于是便通过外交途径向芬兰施压。在1939年10—11月的莫斯科苏芬外交谈判中,前苏联坚持租借汉科半岛,移动两国边界,把靠近列宁格勒的芬兰边界向北推后20—30公里,并想用东卡累利阿地区交换芬兰卡累利阿地峡南部等地区。芬兰认为汉科半岛涉及自身的防御,不肯租借,但同意调整两国边界。前苏联坚持原有要求,谈判破裂。至此,芬兰苦心维持的与前苏联中立的和平外交政策宣告破产,双方最终兵戎相见。
三、苏芬战争时期的芬兰对苏政策
20世纪30年代末,前苏联为改善自己的周边环境,对芬兰提出过分的领土要求。芬兰政府坚守中立,拒绝前苏联的要求,招致战争。在战败后受复仇情绪影响,跟随德国进攻前苏联,最终以失败收场。经过战争的教训,芬兰找回了自己的道路。
(一)冬战时期的对苏政策
1939年11月28日,前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废除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第二天,宣布断绝两国外交关系。11月30日,前苏联列宁格勒军区的军队越过了边境,发动了直接入侵芬兰的战争。前苏联的侵略行为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处境十分孤立。国联于12月14日将前苏联除名,英法向芬兰提供飞机和武器,瑞典、挪威和丹麦则向芬兰派出了大约1万人的志愿军,此时全世界只有希特勒支持前苏联的侵略行为。而芬兰在12月初仍希望恢复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争端,但遭到前苏联的拒绝。在前苏联大军压境的危急情况下,芬兰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的想法,开始全力抵抗前苏联的侵略。
前苏联原计划12天就结束对芬兰的战争,结果,由于芬兰人的顽强抵抗和红军战斗力的差强人意,不得不一再增兵,时间也越拖越长。苏军对芬兰“曼纳海姆防线”的进攻屡屡受挫,伤亡惨重,“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的防御工事和部署得很有效的大炮阵地。‘曼纳海姆防线’是难以攻陷的。”[5]一直到1940年2月,苏军才突破“曼纳海姆防线”,取得主动权。3月,前苏联终于取得对芬兰战争的胜利。据统计,“在105天的苏芬战争中,苏军动用了96万军队,11 266门大炮,2 998辆坦克,3 253架飞机,付出了289 510人的损失。”[6]1940年3月12日,前苏联和芬兰在莫斯科签订和约,和约中“前苏联除了得到连同维堡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地区外,将苏芬边境向北移动了150公里,并租得汉科半岛及其附近岛屿,为期30年。”[6]在和约之中并没有提到领土补偿的问题。在3月底,前苏联在从芬兰取得的地区成立了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
战争时期的芬兰对苏政策有了复杂的变化,战争爆发初期,芬兰还是希望对前苏联对话,和平解决争端;在遭到拒绝后,芬兰抛弃幻想、奋起抵抗侵略;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为保全国家和人民,芬兰求和,满足前苏联的要求。虽然芬兰暂时屈服于前苏联的武力,但是前苏联对芬兰的侵略使得芬兰人对前苏联怀有强烈的复仇情绪,这又让芬兰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跟随德国进攻前苏联;而苏军在这场战争中所暴露出的弱点,又为希特勒后来进攻前苏联下定了决心。
(二)续战时期的对苏政策
芬兰和前苏联的关系在冬战结束后暂时恢复了和平,但双方存在严重的敌对情绪。而芬兰对于前苏联的这种敌对情绪(主要是复仇思想)被纳粹德国利用,德国为了谋取在对苏战争中的优势,诱导芬兰站在德国一边;因此,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芬苏两国又一次处于战争状态。
冬战结束后,芬兰总想找机会复仇,和德国的关系迅速接近。1940年初,德军攻占丹麦和挪威,芬兰与西方国家的联系通道被切断。芬兰指望从德国获得国内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商品,而德国为了进攻前苏联,也想取得在芬兰的过境权。于是,芬兰和德国越走越近。1941年春季,德军在芬兰的土库港登陆,5月份,德国还与芬兰制定名为“蓝色北极狐”的作战计划,胁迫芬兰站在德国一边,以便在对前苏联作战时从北方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德军在芬兰北部大量聚集,磨刀霍霍。
1941年6月22日,德军发动对前苏联的闪击突袭,名为“巴巴罗萨计划”。驻芬兰的德军属于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战争一爆发,德军就从芬兰境内向前苏联的北部发起进攻,其空军也从芬兰的机场起飞,轰炸列宁格勒。而此时,芬兰却表示,自己处于中立;前苏联空军于6月25日轰炸了芬兰南部一些驻扎有德军的城镇,以此作为反应。当晚,芬兰议会对前苏联宣战,就这样,苏芬两国在冬战结束后15个月又一次处于战争状态,芬兰称之为“续战”。为此,芬兰动员了50万军队,占全国人口的16%,并且还协助德国人包围列宁格勒。
不过,战争中的芬兰人并没有在仇恨中迷失。他们不愿随德军全面进攻前苏联,只是收回了在冬战中失去的土地而已。因为他们很清楚,不管战争结果怎样,前苏联(或俄国)始终都是芬兰的邻国,与前苏联彻底的敌对不符合芬兰的国家利益。虽然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但是芬兰却怀念起二三十年代中立的和平外交政策。
随着战局的发展,德国败象已露,胜利已经成为不可能,芬兰国内的中立和平思想进一步得到加强。由于国内资源贫乏,所以芬兰对德国的依赖愈加严重,处处仰承德国政府的鼻息,而国内物价飞涨,粮食紧缺,人民强烈要求早日结束战争。从1943年年初开始,芬兰就开始探索和平的可能性,它通过瑞典作为中间人,试探与前苏联议和的可能性,但由于前苏联提出以1940年的边界作为谈判的基础,芬兰认为太过苛刻,难以接受,议和未能成功。在之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苏芬之间多次提出议和的意向,但都因纳粹德国的压力而作罢。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打击纳粹德国的第二战场。作为回应与支持,苏军在卡累利阿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芬军难以抵挡,整个卡累利阿地区重新为前苏联占领。芬兰政府走投无路,只得于1944年9月19日与前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以及临时和约。苏芬临时和约的内容很多,“芬兰除承认1940年苏芬边界外,还把贝柴摩省割让给前苏联,将赫尔辛基附近的波卡拉半岛以五十年期限租借给前苏联,作为收回汉科半岛的代价,芬兰还要付出三亿美元的赔款。除了这些之外,芬兰尚负有把驻在芬兰的德军全部驱逐出境的义务。”[7]虽然完成和约的这些要求比较困难,负担很重,但是芬兰还是在这场中全身而退,保全了国家的独立。
四、苏芬战争对于芬兰对苏政策演变的影响
经过苏芬战争的教训,芬兰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立政策的重要性。芬兰政府根据本国的国情,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平中立政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对苏政策——对苏友好的和平中立政策,并一直奉行。
(一)苏芬战争结束后的芬兰对苏政策
战后初期,芬兰根据本国的实际国情和国家利益,调整了对苏政策,使芬兰的外交政策步入正轨。1947年2月6日,前苏联等同盟国在巴黎同芬兰签订了正式和约,肯定了1944年9月签订的临时和约。根据这个《巴黎和约》,战后芬兰解散了一切法西斯组织,对前苏联的赔款一直赔偿到1952年。从本国的中立政策出发,1948年,芬兰拒绝了以美国为主的、从经济上对抗前苏联的马歇尔计划,与前苏联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规定,“芬兰承担维护前苏联西北国界的安全和不得参加反前苏联盟的义务,在军事上,‘如有必要,得由前苏联予以援助或同前苏联共同行动’。”[1]战后的芬兰新一届政府秉承务实、中立的外交政策,“宣布奉行对苏和睦友好、同其他北欧国家保持保持传统合作、与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不介入大国纠纷的和平中立政策。”[1]
战后的前苏联一跃成为能和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芬兰夹在美苏之间,如履薄冰。但由于芬兰奉行了和平中立政策,使得它既得到了前苏联的尊重,也得到了美国的帮助。
(二)苏芬战争对于芬兰对苏政策演变的影响
从前文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芬兰对苏政策的变化,从独立之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中立政策;到了30年代末,双方又因国家利益的冲突而爆发了战争,一直持续到40年代中期;最终,芬兰在经过战火的洗礼之后,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对苏政策——对苏友好的和平中立政策。苏芬战争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苏芬战争打断了芬兰中立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芬兰在经过独立初期的迷茫及与苏俄之间的不友好冲突之后,认识到苏俄(前苏联)是自己不可忽视的邻居。由于自身的位置与前苏联相邻,而西方国家相对较远,所以,芬兰认识到投靠前苏联或与前苏联敌对都不符合本国利益,中立的外交政策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中立外交政策成为了芬兰外交政策中的指导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这个政策都得到有效地执行,尽管面临着诸多的不稳定因素。不过,羽翼丰满的前苏联不满足于芬兰的中立,不惜动用武力来改变现状,芬兰苦心维持的中立政策宣告结束。
第二,苏芬战争提高了芬兰的地位,使得前苏联不敢在轻视芬兰的作用。根据1944年签订的芬临时和约,前苏联要租借波卡拉半岛50年,但在1955年到1956年之交就从芬兰波卡拉半岛撤军了,以此来向西方世界释放缓和的信息。这就体现了芬兰在前苏联外交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加。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在1989年初公布了自己在欧洲部署的武装力量,据它统计,“华约总兵力357万,这里不包括内务部军队和边防军,前线飞机7 876架,59 000辆坦克。”[8]这庞大的军力全部部署在欧洲与北约对峙,没有在苏芬边境。这也体现了前苏联对芬兰中立地位的尊重,有利于芬兰保持对苏友好的和平中立政策。
第三,战争之后双方恢复了和平,芬兰的中立外交政策上了一个新台阶。在经过苏芬战争的教训后,芬兰人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立政策的重要性。为消除前苏联的疑虑,战争结束后的芬兰将对苏友好作为本国中立外交政策的立足点,同时加强与其他大国的友好关系。这样既消除了前苏联对芬兰的顾虑,又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支持,真正实现了国家的中立。相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立外交政策,这实在是个巨大的进步。二战后的芬兰所执行的和平中立政策,与二三十年代的芬兰所执行的中立政策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二者的实质不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芬兰中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表面上的空壳,意识形态方面靠拢西方,对前苏联相当警惕。而二战后芬兰对苏友好的和平中立政策,是出于芬兰所处位置及其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已经不是主要影响因素。第二,从结果来看,差别也很大。二三十年代的芬兰中立政策,不仅没让芬兰实现真正的中立,反而多次将芬兰拖入战争。二战后的芬兰和平中立政策,使芬兰真正实现了中立,得到国际认可,在美苏之间维护了国家主权。
五、结语
1991年底,前苏联解体,芬兰的外交空间变得空前宽广。前苏联的继承者是俄罗斯,芬俄关系基本上继承了芬苏关系的稳定,但是芬兰的对俄政策受美国影响较大。美国对俄罗斯是很不放心的,“对美国来说,俄罗斯实在是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果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罗斯又太强壮了。”[9]
总的来说,芬兰的对苏政策经过较大的变化,从独立之初的混乱、矛盾;再到认清现实,采取了中立的外交政策;然后签订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维持表面上的和平相处;再来就是因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前苏联爆发了冬战以及受复仇心态的驱使,在二战中依附于德国,与前苏联展开续战,两次均失败收场;最后“幡然醒悟”,基于国家利益,务实、理智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周旋于两大阵营之间,尽可能地维护国家利益。可以看出,1939年与1940之交的冬季战争和1941—1944年的续战在这个变化中具有重大的转折作用。
经过苏芬战争的教训和自己国家所面临的现实,芬兰最终选择了最符合本国利益的对苏政策——对苏友好的和平中立政策。可以看出,在芬兰对苏政策的转变之中,国家利益是个核心的因素;不管是采取中立政策还是对苏作战,都是国家利益在发挥影响。这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
[1]王祖茂.当代各国政治体制——北欧诸国[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97~98.
[2]周尚文,叶书宗.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52.
[3]石磊,鲁毅.现代国际关系史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293.
[4][俄]爱德华·拉津斯基(Edvard Radzinsky).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M].李惠生,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511.
[5][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M]. 张岱云,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224.
[6]陈之骅,吴恩远.苏联兴亡史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65.
[7]敬东.北欧五国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80.
[8]沈志华.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0.
[9][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1.
2095-4654(2016)07-0022-05
2016-04-16
K5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