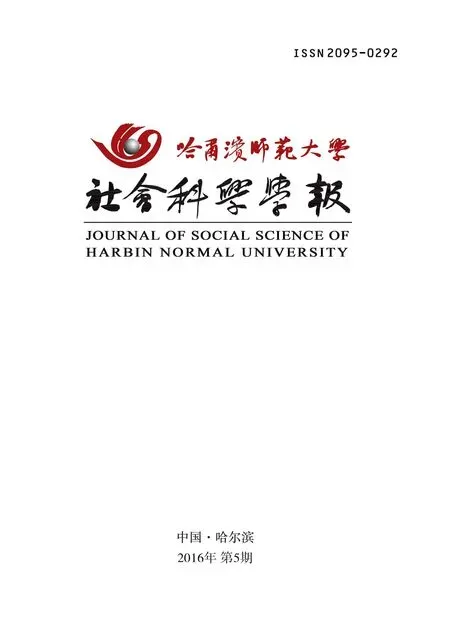重新仲裁制度的立法审视及实践困境
2016-03-07李海涛
李海涛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北京 100088)
重新仲裁制度的立法审视及实践困境
李海涛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北京 100088)
仲裁作为与诉讼并驾齐驱的争议解决方式,在民商事争议的解决,尤其是跨境民商始终争议的解决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经历司法对仲裁过度监督、不监督的极端实践后,晚近国际仲裁的理论与实践均认可,司法对于仲裁的监督应当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良性、先进的仲裁制度表现之一就是司法对仲裁的最大支持和适度监督。重新仲裁制度并非独立的仲裁监督制度,而是作为仲裁裁决撤销制度中的替代性方案而存在。重新仲裁制度的存在,给予仲裁庭纠正错误的机会,可以有效地减少仲裁裁决被撤销的频率,减少资源的浪费,符合仲裁制度的效益价值追求,有利于争议的解决。然而,中国关于重新仲裁制度的立法显示出与国际先进国家立法既不相称又与国内实践脱节的严重弊端。从比较法的角度审视立法,从实践的角度审视制度运营,对于完善重新仲裁制度大有裨益。
重新仲裁;司法监督;制度完善;效率
相比较于法院诉讼程序的僵硬及效率的相对低下,效率无疑是仲裁能够成为与诉讼并驾齐驱的最为成功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当事人意思自治一样,仲裁的高效性应当贯穿于仲裁制度的始终,包括仲裁裁决撤销制度。而重新仲裁制度作为辅助仲裁裁决纠正的程序,兼具效率和公正的价值,应当被赋予比其目前在中国仲裁制度中所处地位更为重要的重视。
一、重新仲裁的内涵及外延
重新仲裁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指的是,在仲裁裁决被撤销后,当事人之间根据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或者原仲裁协议重新提起仲裁。此处涉及仲裁裁决撤销后原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各个国家的规定有所不同,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持肯定说,即裁决撤销后,原仲裁协议依然有效。当然,也有些国家持否定态度,比如荷兰、意大利及中国等。第二种情形指的是,设置于仲裁撤销制度之中,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一种替代方式而存在的重新仲裁制度。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后,法院经受理,如认为仲裁裁决的确存在瑕疵或错误,且这些瑕疵或错误能够由仲裁庭自身进行纠正,则法院会裁定中止撤销仲裁裁决,并通知相关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1](P78)。本文中所称的重新仲裁系指上述第二种情形。
二、重新仲裁的立法实践
重新仲裁制度最先确立于英国。早在1889年的英国仲裁法中,就有关于重新仲裁的规定。但这种规定背后所蕴含的理念与晚近重新仲裁制度所追求的价值大相径庭。此时的重新仲裁与上诉法院以发回重审的方式否定下级法院判决类似,这种规定源于当时的英国司法对仲裁采取的敌视态度[2](P56)。除了英国之外,印度、美国等其他英美法系国家也有关于重新仲裁的规定。但彼时,大陆法系以及国际性法律文件中均极少提到重新仲裁这一概念。
重新仲裁制度在国际性法律文件中的首次引入,是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1980年颁布实施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之中*《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34条第(4)款规定:“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时,如果适当而且一方当事人也提出请求,法院可以在其确定的一段时间内暂时停止进行撤销程序,以便仲裁庭有机会重新进行仲裁程序或采取仲裁庭认为能够消除撤销裁决理由的其他行动。”,并在2006年修订中保留下来。《示范法》第34条第4款规定的重新仲裁制度是立即撤销仲裁裁决的替代性方式[3](P232)。《示范法》对重新仲裁制度的引入,并非对传统英美法国家重新仲裁机制的照搬,而是从理念上第一次赋予重新仲裁完全不同的理念,如果说肇始于英美法的重新仲裁系司法对仲裁的不信任的表现,那么此时的重新仲裁则完全是法院支持仲裁的表现,充分体现法院对仲裁的友善。由于《示范法》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及支持仲裁理念的传播和普及,越来越多的国家或通过直接采纳《示范法》的方法或通过修订仲裁法的方式采纳重新仲裁制度,比如,德国、瑞典、俄罗斯、中国等。《示范法》引领下的重新仲裁制度体现司法对仲裁的最小监督和最大支持,体现追求效率、合理分配并避免社会资源浪费的现代纠纷解决理念[4](P46)。
三、我国关于重新仲裁的立法演进
(一)重新仲裁制度在我国的正式引入
1990年,《江苏省小额消费纠纷仲裁办法》从文字上已经提出重新裁决的概念。当然,在性质上,该办法所谓的仲裁是与以自愿性、民间性及终局性等原则为特征的商事仲裁大相径庭的,因此,虽有重合之处,却不能称其为《仲裁法》中重新仲裁制度的肇始[5](P325)。
重新仲裁在我国的首次确立是在1995年9月1日实施的《仲裁法》*《仲裁法》 第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撤销程序。”中,但该条规定极为简单,对于什么是属于“可以认为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情形并未加以明确。在实践中,这种规定的不明确必然会出现两种情形:一是法院不敢或者不愿触及重新仲裁,那么该条的规定形同虚设;二是法院根据自己的理解形成自由裁量权,自行判断什么是“可以认为由仲裁庭重新仲裁”。这种自由裁量权难免出现裁定不一,甚至相冲突的后果。
(二)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文件中关于重新仲裁的规定
由于《仲裁法》第六十一条关于重新仲裁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可操作性极差,导致在实践中法院适用重新仲裁的情形并不多见。
在执行仲裁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法院纷纷根据自身司法实践,就重新仲裁进行补充规定。其中,2001年1月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及实践指导价值。该意见第九条对可以重新仲裁的事由、通知重新仲裁的程序、当事人对重新仲裁做出的裁决不服如何处理等三个主要问题进行细致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仲裁法》的漏洞。
《仲裁法》关于重新仲裁的规定位于第五章,而在第七章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中并无关于重新仲裁的规定。那么,在涉外仲裁中,是否能够适用重新仲裁?无论是在实务界还是在理论界均存在不同的声音。笔者认为,重新仲裁系依附于仲裁裁决撤销制度的一项旨在体现法院对仲裁提供支持的制度,而仲裁撤销制度不仅包括国内裁决的撤销,还包括涉外裁决的撤销,那么,无论是从制度构建的一致性上,还是从友善仲裁的角度,重新仲裁制度均应当适用于涉外裁决。1998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从侧面确定涉外仲裁的重新仲裁,并且确定涉外仲裁中重新仲裁必须履行与撤销仲裁裁决一样的层报程序。而2005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第二次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9条则直接对涉外仲裁司法审查中的重新仲裁进行规定。
2006年8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法司法解释》)对《仲裁法》实施十年以来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规定。第二十一条对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中的重新仲裁问题进行简要规定,其中,通过列举式方式规定可以重新仲裁的事由。
(三)关于我国重新仲裁制度立法的评析
1.立法体系混乱
我国关于重新仲裁的立法散见于《仲裁法》、《仲裁法司法解释》、最高院的会议纪要以及地方法院的适用意见中。而真正可以作为正式法源可以被法院在裁定书中引用的只有《仲裁法》和《仲裁法司法解释》。《仲裁法》仅仅在原则上规定国内仲裁中的重新仲裁制度,缺乏对涉外仲裁中重新仲裁制度的直接规定,更没有对重新仲裁的事由、重新仲裁的程序等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的问题进行规定。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的突出之处在于其对重新仲裁的事由以及法院通知重新仲裁的程序进行细致的规定。且不论其规定是否合理,至少在司法实践中,该意见对于当地法院对于重新仲裁制度的理解和适用,显然比《仲裁法》更有价值。
《仲裁法司法解释》的出台的确解决《仲裁法》生效十年多以来实践中产生的许多问题,总结并纠正以往在批复中所表达的意见和观点。但令人遗憾的是,针对重新仲裁的问题,《仲裁法司法解释》在第二十一条对国内仲裁中的重新仲裁事由进行无兜底式的列举,在实践中已经证明并不明智、合适。《仲裁法司法解释》对于《第二次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涉外仲裁中重新仲裁制度的意见,以及地方法院根据司法实践制定的颇具合理性的处理意见,尤其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并没有在立法中予以体现。
2.涉外仲裁中重新仲裁制度立法缺失
《仲裁法》及其司法解释缺乏对涉外仲裁中重新仲裁问题的规定。而《第二次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则不具有正式法源的意义。在实践中,对于涉外仲裁中的重新仲裁问题一般都是参照《仲裁法》第二十一条以及《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进行。
《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所规定的重新仲裁事由系国内裁决撤销事由中的两种,采纳的是实体标准,然而,我国涉外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的标准则是程序标准,不涉及实体问题。这种冲突必然意味着《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在实质应用上根本无法适用于涉外仲裁中的司法审查。
这种无法可依的局面也直接导致当司法审查中某项仲裁裁决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法院更愿意直接撤销,而不会过多考虑给予仲裁庭重新仲裁的机会[2](P57)。
3.关于重新仲裁具体规定的微观审视
(1)关于重新仲裁的事由。《仲裁法》第六十一条完全将决定是否重新仲裁的裁量权赋予法院。而法官的个人知识构成及经验的不同将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自由裁量权的应用,并最终导致司法实践中矛盾现象的增多。《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以肯定式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法院可以裁定重新仲裁的事由。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重新仲裁条款的可操作性,但是该条规定的事由过于狭窄。如果仅仅将重新仲裁的事由局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两种情形,那就意味着仲裁程序中如果出现其他问题则只有通过撤销仲裁裁决的形式来解决,迫使案件当事人回到纠纷发生的原点[6](P56)。显然,这种设计既不符合重新仲裁制度设置的价值追求,也违背当事人对仲裁高效、快速解决纠纷的期望。
一般认为,这种肯定式的列举并不是穷尽的。无论是基于对各国立法考察,还是基于对我国司法实践的考察,答案都是如此。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68条第3款*该条第3款规定:“如存在影响仲裁庭、仲裁程序或裁决的严重不规范行为,法院可以:(1)将裁决全部或部分发回重审;(2)全部或部分撤销裁决,(3)宣布裁决全部或部分无效。除非法院认为将争议事项发回重审是不合适的,法院不得行使全部或部分撤销裁决或宣布裁决无效的权利。”对可以重新仲裁的事由进行最为详细的规定。该款所指的严重不规范行为进行多达九条的列举。而在国内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仲裁法司法解释》规定的事由之外裁定重新仲裁的案例也并不罕见。
国内学者对重新仲裁事由的讨论和研究也如火如荼。有学者认为,应依据以下标准审查确定重新仲裁的事由:一是管辖权标准;二是程序瑕疵的可弥补性标准;三是公共利益标准;四是实体上得到可弥补标准[7](P248-249)。在这些标准之下,可重新仲裁的事由远远超过《仲裁法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事由。与司法实践、先进国家立法一样,学者的研究和讨论也反映目前《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落后性及其与司法实践的极不协调性。
(2)关于提出重新仲裁的主体。重新仲裁可以由法院单独决定,还是必须由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才可以做出决定,抑或必须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各个国家的立场也存在差异。俄罗斯《联邦仲裁法》第34条规定,重新仲裁必须满足当事人申请及仲裁庭认为适当这两个条件。瑞典《仲裁法》第3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申请且法院认为合适的情况下以及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的情况下法院均可以决定重新仲裁。《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34条第4款规定,一方当事人申请且法院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决定重新仲裁。而我国《仲裁法》则规定,是否重新仲裁的决定权完全由法院享有,从而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把重新仲裁规定为一种强制性程序虽然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8](P172),但排除当事人自治显然并不符合仲裁本身的性质。
四、司法实践中重新仲裁制度的具体应用
(一)国内案件中的重新仲裁实践
有学者对北京仲裁委员会2000-2012年12年间北京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被法院裁定重新仲裁的案件进行统计和分析。根据该学者的统计,12年间,北京仲裁委员会共计28件案件被法院裁定重新仲裁,其中,以超裁为由的案件数量为5件、以仲裁庭组成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的案件数量为2件、以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的案件数量为6件、以隐瞒证据为由的案件数量为4件、未明确事由的案件数量为11件[9](P46-49)。而在每项事由项下,个案的具体事由仍然有所不同。
由此可见,在实践中,法院据以认定重新仲裁的事由并不仅仅局限于《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并不仅仅限于实体上的标准。基于重新仲裁制度所蕴含的支持仲裁、提高争议解决效率的理念,甚至可以认为,除了不存在仲裁协议、不具备可仲裁性、仲裁员收受贿赂以及违反公共利益之外,其他任何撤销事由,法院均应当优先考虑适用重新仲裁制度。
(二)涉外案件中的重新仲裁的相关实践
正如有学者所言,由于立法缺失、程序障碍以及观念模糊等原因,在拟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中,重新仲裁鲜有适用[2](P56)。德国五矿诉英国菲儿柯公司案[10]被认为是涉外仲裁中适用重新仲裁的典型案例,该案充分体现重新仲裁的制度价值,同时也以实践的方式确定重新仲裁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重新仲裁的审理范围问题。在此问题上,英国法院认为重新仲裁并不是全面重审,重新仲裁也不是原诉程序,重新仲裁是弥补原程序中程序缺陷,并不进行实体审理。
(2013)民四他字第8号王国林申请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2012)中国贸仲深裁字第3号仲裁裁决案是笔者所能查询到的最近的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而最终裁定重新仲裁的案件。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查明仲裁庭在未向当事人释明合同无效的后果以及未给予当事人变更仲裁请求机会的情况下,直接对合同无效后的返还以及赔偿责任做出裁决,确实超出了当事人的请求,属于超裁。但认定仲裁庭有能力纠正上述错误,并因此认为本案应当裁定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该案件的意义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涉外案件的重新仲裁事由进行了认定和确定。
五、结论
重新仲裁制度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诉累,有利于案件的快速、高效解决,有利于社会矛盾及时化解。但是,我国重新仲裁制度在规则层面太过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层面则过于混乱,缺乏统一性。完善我国仲裁制度,不应当忽视重新仲裁这一制度的构建。
[1]赵庆.关于重新仲裁及其中新证据问题的思考[C]//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研究:第3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朱萍.涉外仲裁司法审查中重新仲裁之实践检讨与立法完善[J].法律适用,2011(4).
[3]Stefan Riegler. The Award and the courts: Remission of the Case from the State Court to the Arbitral Tribunal[M]. in Christian Klauseger, Peter Klein, et al.(eds.), Austria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Manz’ssche Verlags-und Universitatsbuchhandlung,2012.
[4]李虎.裁决的撤销与发回重审[C]//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2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5]林一飞.仲裁裁决抗辩的法律与实务[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6]王小莉.我国重新仲裁制度若干问题探析[C]//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研究:第20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7] 林一飞.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务[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8]王吉文.我国重新仲裁制度的重构——以重新仲裁的根据为视角[J].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4).
[9]张霁爽.重新仲裁制度运行的实证分析—以北京仲裁委员会重新仲裁的27个案例为样本[C]//广州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第85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10]刘文仲,译.德国五矿诉菲儿柯公司判决书MINMEALS GERMANY CMBH V. FERCO[J].仲裁与法律通讯,1999(4).
[责任编辑 刘馨元]
2016-07-25
李海涛,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商事仲裁与国际私法研究。
D925
A
2095-0292(2016)05-005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