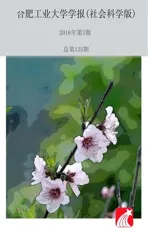格哈德·里希特的单色画实践及其历史关联
2016-03-07熊言钧
熊言钧
(安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格哈德·里希特的单色画实践及其历史关联
熊言钧
(安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在格哈德·里希特形式多样的绘画创作中,单色画具有视觉表现上的特殊性并与西方现当代绘画史有密切的关联。文章从里希特单色画创作实践的展开过程与成果的视觉风格分析入手,揭示这类绘画通过对色彩和幻觉形象的“零度化”处理而获得的物性特征,并将其与西方现当代绘画史上的单色画家及其作品的创作动机和艺术观念进行比较,论证里希特绘画中的反形而上学倾向、物质主义的独特性与美学的历史相关性。最后,文章就“绘画终结论”与单色画关系的讨论,分析了里希特单色画创作中所具有的超越现代主义艺术叙事的开放性。
格哈德·里希特;单色画;历史关联;绘画终结论
德国画家格哈德·里希特的绘画一直为艺术批评家与艺术史家所高度重视,最近的一系列大型艺术回顾展又继续凸显了他的历史地位。里希特一生坚持并推进绘画传统,创作丰厚、风格多变,几乎将自己的画室变成了一个视觉形式的博物馆。从早期的类现实主义作品到其后的波普艺术阶段,再到摄影式绘画、灰色绘画、色彩图标绘画,直至晚期的色彩斑斓的抽象作品,里希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清理了西方绘画文化的形而上学,重新审视了绘画的物质性基础并刷新了绘画美学,也超越了个人风格的传统格局,以一种明朗的物性化特征重建了绘画艺术与现实时空之间的深刻联系,再次恢复了人们对绘画的信心。
关于里希特绘画的研究,评论界显然更热衷于讨论其绘画与摄影的关系,特别将他某一时期的人物(肖像)绘画与德国历史、政治联系在一起。这些有所侧重的研究和解读深化了对于里希特某类风格作品的认识,但也有把里希特带入到类型化视野中去的危险,这将割断他不同时期绘画中所隐藏的内外线索,也将其复杂的创作活动简单化,从而造成对真实的绘画实践和思想的遮蔽。目前来看,人们对里希特抽象绘画的研究仍未得到深入展开,而除了美国艺评家罗伯特·斯托尔在《里希特四十年绘画批评》中有过精要论述之外,里希特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所创作的(灰色)单色画,更鲜有人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因此这些创作的重要性还未被充分认识[1]122。从里希特的访谈和笔记中可以看出,单色画是他极为看重的一类创作,通过这些创作,里希特与另一些重要画家形成了超越时空的深度关联,使他进入了一个包括卡西米尔·马列维奇、伊夫·克莱因、马克·罗斯科、罗伯特·莱曼、阿兰·查尔顿等在内的不同时期画家的单色画家族。同时,里希特的单色画也以明晰、极简的面貌及创作方式的极致性铸成其个人艺术生涯的里程碑,他在此将绘画归为零度,重启并构建起后期复杂、灿烂的色彩空间。本文因此以单色画为线索,从一个独特的维度探讨这位杰出画家的绘画美学实践与历史性成就。
一、走向物性的单色画
里希特的单色画实践不仅显示了个人绘画风格的演进,也清楚地表明他所接收的时代性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某种特定绘画文化的质疑和回应。通过对绘画幻觉、内容及情绪化的否定和技术手段上的多样化操作,里希特赋予绘画以明朗、多变的“物性化”特征,也同时将绘画行为及其艺术存在带向了哲学的“拷问”。
里希特在东德时期(包括在学生时期)的艺术经历已经显示出他不会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物,所以,当他得知柏林墙另一边的艺术世界正发生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便难以拒绝这种时代的召唤。里希特于六十年代初进入西柏林,再辗转至杜塞尔多夫,西方前卫艺术对他早期艺术观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他早期的创作依然残留着东德意识形态为上的、实用的艺术教育影响,但是已明显地表现出来自杜布菲、丰塔纳及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影响,其中有对画面的破坏、缝补以及表现性的涂抹。之后,激浪派运动的兴起更是将里希特带入到西方前卫艺术运动的中心地带。尽管以里希特的个性,他可能与所有这些潮流都保持了适度的距离,但不可否认他对这类达达主义的、否定性的艺术活动保持了开放的心态,并接受了其中某些新的观点。他与西格玛·波尔克一起举办的展览,可以视为对美国波普艺术及安迪·沃霍尔等人物化的、消费的美学的响应。得益于前期的实践,里希特后来转入使他赢得广泛声名的摄影绘画,这些绘画是对摄影图像和绘画本身的双重思考。从最初对快照的任意选择到之后刻意选取新闻和社会热点照片,里希特的这些绘画,通过对形象的模糊化处理及对画面表层的物质感的强调,目的并不在于从社会学意义上考验人们对真实的观点,而是聚焦于视觉的实验,即在不抛弃形象的情况下,尝试把绘画的实体性予以展示。六十年代末,里希特开始了抽象风格的创作,然后又过渡到一个画面以灰色为主的单色画时期。表面看上去,这种变化是突然的,但是在里希特的画室中,两种形式的创作并行不悖,因为单色画对于绘画实体性的呈现与前者对摄影图像的绘画改造并不矛盾,前期的艺术吸收和实践把里希特带入到绘画自身的反省当中,对传统绘画文化的扬弃、对绘画内容和文学性的否定、追求现成品和日常趣味以及反审美的绘画态度,这些直接导致了他的绘画步伐与美国艺术的趋近。
里希特的单色绘画时期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不仅作品数量庞大,而且统一使用了看上去异常单调的灰色。如果我们对单色绘画的范围不做严格限制的话,里希特这一时期的创作与摄影绘画的界限其实并不明显。六十年代后期,他的摄影绘画已经出现了抽象化的延伸,比如大量表现窗户、门、格子与阴影的绘画,也同样使用了灰色,这类作品从表现规整的物象直到一些简单的、几何化的图形,延续了摄影绘画的那种模糊效果,但已越来越显示出对形象的简化甚至排斥。而后,灰色绘画变得更加纯粹,不再有具体物象,只有灰色和被覆盖的画面,这些画真正可以被称为专有名词意义上的“单色画”(monochrome painting),也正是阿瑟·丹托所确认的——“不仅仅是单一色彩,而且是色彩均匀的绘画”[2]181。里希特尝试了以各种方法处理这些灰色的画面,既采用了常规的绘画工具与“绘画性”的技巧进行涂抹覆盖,也大量使用非常规器具,比如使用橡皮滚筒及一些自制工具将颜料滚压、刮擦在画布上。从完成的肌理效果来看,画面有的光滑、柔和,有的稀薄并突出各种规则或不规则的笔痕,也有的布满大大小小毛刺和颗粒感,显得或斑驳、粗砺或均匀、精致。从灰色的使用上,这些单色作品其实并不像乍看去的那样单调,里希特尝试调配各种倾向的灰色,青色的、偏紫的、土色系的,还有完全没有色彩倾向的“死灰”,光泽度与干湿效果也都有很大差别,如果把众多同类画作放到一起观察,可以发现里希特对于灰色这一色域进行了极大限度的开发,色调运用丰富、微妙,变化万千。关于灰色,里希特说,“它什么都没说,既唤不起情感,也没有联想;它既可见,又不可见,任何其他色彩都没有这种能力,使‘无’可见”[1]145。由此看来,虽然里希特使用灰色时保留了、甚至在后期强化了其间的差异,但勿庸置疑,他的一个关键意图就是弱化色彩在一幅画中通常意义上的影响力,使绘画变得单纯而直接,以另一种方式触及感官。他曾就自己的单色画解释说:“我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哪幅绘画作品比其他绘画作品更美丽,亦或要不同于其他作品,亦或要像其他作品……我的目的在于要使它们看起来相同又不是真正的相同,我想使这些特征形象化。”[3]如果把里希特的有关谈话与作品的绘制过程及最后效果联系起来,我们能很容易发现,色彩的减法正是为了突出另一种存在,也就是绘画的物质性存在。色彩上的微弱差别或者相似趋向于零度状态,画面也完全放弃了对任何形象的再现与描摹。最后,这些绘画仅在一种纯物质性的操作中强调了自身的实体形象。每幅画的独立性不是因为鲜明的形象和色彩的差异而构成,它们是用相似的色彩和不同的方法画出的不同面貌。在极端的状况下,它们在色彩和绘制手法上几乎一样,但是它们仍旧是不同的个体存在。当然,里希特没有刻意地追求画与画之间的相似,这终归不是目的,相似仅作为一种策略,是为了强调画与画之间的物质性差异和视觉的丰富性。
可以说,里希特的单色画体现了明确的物性化特征,它们既非建立在幻觉再现基础上的客观性上,也克服了体现世界观、自我意识和情绪的主观性,而是突出了一种新的客观性——不再是绝对理念与自然的具象或抽象表达,相反,绘画本身就是构成一种自然,而不是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惟此,绘画活动变成一种更加纯粹的物质生产,成为自然进程的一部分,产生出我们称之为“绘画”的东西。这种 “唯物主义”的绘画实践带给绘画以鲜明的日常化和新感性,既标志了里希特对西方绘画文化的个体突破,也显示了他与一个 “单色画”历史谱系的深刻联系。
二、单色画的历史关联
里希特的摄影绘画表现出绘画与图像,特别是摄影图像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他的单色画创作则更多地与现代艺术史密切相关。单色画作为“关于绘画的绘画”,它的重要性将里希特的创作深深地嵌入到单色画历史的风格矩阵当中,使我们对其绘画实践的美学分析有了更精确的参照系和理论纬度。
摄影绘画以方法和视觉上的陌生感和独特性为里希特赢来了广泛的国际声名,而他在绘画上所取得的艺术史上的进展可以在单色画这个标本切片上获得更鲜明的揭示。单色画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阶段的终结,倒更像是个开始,但整个实践过程又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一个从A到B的过渡。单色画有着自身的复杂性和价值,也有着未被整理的历史谱系,我们当以此入手,在更广阔的绘画时空里寻找一些显而易见的联系,以确认里希特的绘画在何种程度上区别于他人,成为绘画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进展。事实上,绘制单色画绝非孤立的事件,从1913年马列维奇展出他的《白底上的黑色方块》开始,单色画视觉上的极致性已经初露端倪。几年后,《白色上的白色》则完全可以视为典型的单色画了。此后,伊夫·克莱因于1957年在米兰展示了他首批蓝色单色画,画面完全被他自己掌握配方并以“国际克莱因蓝” (International Klein Blue)命名的宝蓝色颜料覆盖,单纯强烈,神秘迷人。六十年代末,纽约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罗斯科为休斯顿的一个教堂创作了一系列深紫色、深栗色等幽暗、晦涩的单色画作品,它们与教堂的气氛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他之后,另一位通常被归类为极简主义者的美国画家罗伯特·莱曼则几乎终其一生地创作白色绘画,他最为代表性的画作上除了白色一无所有。与他同时,画家布里斯·马登使用蜡一类的特殊材料创作了大量灰色的、精致的、充满物质感的单色画或单色联画。在极简主义的鼎盛期,一些欧洲艺术家也以各种方法推出了他们的单色画作品,伦敦有阿兰·查尔顿的组装单色画和彼得·约瑟夫的单色方块;在法国,画家苏拉热逐渐远离了突出动势并充满抒情性的“非形式主义”,开始将黑色颜料均匀、规整地厚涂在画面上,建立了新的单色画风格;瑞士画家雷米佐格、更迟的德国画家根特·弗格和格哈德·梅尔兹都有成批量的单色画创作。除此之外,里希特英年早逝的朋友布吉林·帕勒莫不仅自己是一位单色画的积极实践者,还帮助里希特与美国绘画之间建立了联系。
单色画作品多呈现出统一、相似的外观,这是明显的,但是创作这些画的动机则大有区别。里希特的单色画与经典的现代主义类似创作之间的确有密切联系,只是这种联系主要存在于纯视觉方面,而不在于精神层面。里希特艺术生涯的早期就表露出对形而上学和绘画的叙事内容、象征性及文学性的拒斥,这也可以从他对同时代德国画家安塞尔姆·基弗尔的负面评价中看出。在与艺术史家本雅明·H·D·布赫罗等人的访谈中,他特别谈到了早期对丰塔纳、福特利埃等人绘画物质性的关注以及蒙德里安的兴趣,却对马列维奇这位单色画鼻祖反应冷淡,乃至于直斥整个欧洲早期抽象艺术为“教堂的手艺”,这显示了他与欧洲沉溺于精神理念的现代主义者的分野。无论是马列维奇还是克莱因,支撑他们创作的总有一套背后的玄学观念:我们从马列维奇于1915年12月发表的至上主义宣言中可以清楚的发现存在于他的艺术观里的主客观二元论,在这篇宣言中,他声称“在创造艺术中,感觉至上”,“除感觉之外,没有真实的东西”[4],而他的单色画恰恰将自我、理念与宇宙的关系清晰地、图式化地呈现出来;而克莱因的东方经历与新现实主义背景则提示了他的艺术与禅宗及其他神秘主义者如杜尚的联系,他的单色画是需要沉思默想的绘画,而他的空无观念所包含的燃烧的激情和意念与里希特的趣味大相径庭。里希特自始至终致力于“观看的绘画”,他欣赏克莱因,也喜欢纽曼和罗斯科,认同他们在自己时代中的重要性,但不等于说他认同他们的艺术观,而是更多的被他们开拓绘画的勇气及绘画的视觉极致性所吸引。里希特在创作中不愿意有一个先在的主题,他眼中的绘画创作如同“自然界”一样,盲目,绝望,尽其所能。他对于人类理性、理想主义和崇高有着自己的判断,努力在创作中不坠入神学表达的陷阱,也不喜欢绘画从属于任何智力的或者观念的游戏。他直接否定了人们把他的绘画归类为“观念绘画”的看法,对于他来说,绘画就是绘画,不负责传达观念,就像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所以,尽管里希特对杜尚评价很高,却仍然宣称,“杜桑的有些东西不适合我……都是些神秘的制作”[1]97。
里希特开始创作单色画时,极简主义在美国已大行其道。与欧洲的单色画先驱者不同,美国极简主义者对张扬的主观精神性的清除,使里希特颇感亲近,他毫不讳言自己接受过极简主义的影响。里希特不止一次地表示出对莱曼作品的倾心,这自然是因为莱曼有相近的对绘画的物质性的理解,他们的一部分单色画除了颜色上的“灰”与“白”的差异,在表层物感和肌理的处理上确实有很大的相似性。有一点可以确定,里希特至少在某个时候、某些作品中与极简主义者的追求取得了一致性。但是,和莱曼这样极端节制的、习惯于阵地战的画家终究不同,里希特和极简主义最核心的美学观的交会是短暂的。无论如何,像最为专一的极简主义者如唐纳德·贾德的作品中表现出那种虽然物质化、却犹如数学般精确的冷漠的视觉风格,还有其中所强调的单元重复与整体同构性,这显然都不是里希特变动不居的艺术性格所能接受的,也与他对绘画物性化追求的感性、多元和开放性不可协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除了东亚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单色画家外,大多数的单色画家都有“后极简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们的创作虽然在表面上延续着极简的、几何化的外观,但与格林伯格眼中的纯绘画及形式主义要求已相差甚远。比如英国单色画家阿兰·查尔顿对作品采用严格数据控制的“标准化”处理方式,包括绘画的制作尺寸、涂绘、包装和运输要求、展览的悬挂高度与间隔、作品宣传图录的印制等等,一切都依公式进行。这样,他的单色画创作过程直接将自身形象与当代社会规则以及复制景观重叠,表现出对日常世界的美学观照和介入态度。其他画家的单色画作品也多已完成对现代主义和抽象理念的祛魅,返回现实、生活和绘画的感性层面。在这个方向上,可以包括前面提到的苏拉热,他对厚涂黑色颜料的物质感及绘画表面与光之关系的强调和里希特也有相近的地方,不过苏拉热的单色画更显现出法国传统的优雅、享乐主义和音乐性,不像里希特的灰色画面给人带来空洞和虚无感。比较而言,里希特的单色画创作在通向未知的途中更为决绝,总是行动先于思考,“存在先于本质”[5],正像他自己所言,“我的画比我聪明”,这些灰色的画作把里希特带向绘画创作的绝境,也为他打开了希望的出口。
我们把里希特的单色画创作纳入到西方现当代绘画脉络里纵横考察,由此清楚地看出,单色画既是里希特延续一生的个人艺术实践,也因这类创作的特殊性而与“外部”形成了复杂的美学关联。这种存在于历史情境中的关联性,一方面可以准确描画出里希特在二十世纪西方绘画中所处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可以建立起一个比较的视野,以便确证里希特的绘画实践如何趟过了现代主义艺术叙事的泥河,进入当代绘画的新时空。
三、超越现代叙事的绘画
视觉因素极端简化的单色画的出现,一度给西方艺术界带来了一种绘画已然没落的氛围,助长了渲染“艺术(绘画)终结论”的历史想象。里希特的绘画突破了跨越世纪的现代主义艺术叙事,而他的单色画实践因其历史上的关联性和美学上的差异性,更成为观察当代绘画转型的一个完美标本。
按照格林伯格关于艺术必须实现形式纯粹性的逻辑,各门类艺术都要完全地忠于自身媒介的本质特征,那么绘画到极简主义那里就应该终结,因为作为二维平面上的物质呈现已到了极致。但是艺术史并不能捻成一条单一的线索,也不会忠实于进步论的宏大叙事。所以,当格拉斯·克里姆普等人面对如莱曼的单色画作品,声称“绘画内部已经耗尽”后,绘画的终结没有如约到来,到来的反倒是一种关于艺术史叙事的终结。阿瑟·丹托在谈到“艺术的终结”与单色画的关系时,认为正是 “整个领域的突出的艺术活动的选择性”导致“格林伯格式叙事已经终结,表明艺术已经进入可称之为的后叙事阶段”,以此而论,“一个人是否把莱曼的作品看做现代主义叙事的最后阶段,或者把它看成是一种开始在后叙事时代形成的绘画形式”,则莱曼的作品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在《单色画历史博物馆》一文中,丹托写道,“自己关于艺术的终结的声明必须坚决地与有关绘画死亡的声明区分开来,确实,艺术终结之后的绘画极其重要,但是无论怎样,我都不喜欢宣布在单色画基础上的绘画的死亡……除非我自己支持现代主义叙事”。为此,在充分考虑个体差异的基础上,他设想了一个单色画历史的“风格矩阵”,以这个模式来论证单色画始终存在于其他作品的背景中,“只有通过历史化才能产生它们的美学差异”,如此才能解释所有看上去相似的单色画的真实产生机制,并且反映出谱系上的亲疏关系。[2]186在这样一种突破单一历史叙事的视野里,艺术的选择菜单已经开放,多元主义不可避免地到来了——绘画不再遵守禁令并纯洁自身,而是开始拥抱一切可能性。所以,即使如罗伯特·莱曼的白色绘画也不能证明绘画已经无路可走,因为它不但不代表趋向艺术纯粹性的进步论的发展,反而体现了个性的封闭,充满了自足性。而与莱曼相比,里希特更是一个典型的背离艺术纯粹性的画家。在现代主义叙事的高潮也是其最后时段之时,里希特的单色画创作也同样笼罩在这一叙事的阴霾之下,至少在表面上也显现出西方文艺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所弥漫的那种历史性的“虚无”。在里斯特的创作中,绘画的终结论者当然可以找到某种“死亡”信号,不过这只能出于一个理论上搜集证据的需要,而没有触及里希特艺术的特质。因为里希特在与艺术潮流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保留了自由、开阔的创作空间,他面对的只是自己的问题,这恰恰是绘画新希望的出口。里希特关注过格林伯格视野中的画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他们的影响,但他比这些美国画家更加难以自觉规范于一个明确、单一的创作目标——他的出现总是让艺术评论疲于应付,也让艺术界的历史决定论者捉襟见肘。如前所论,里希特否定了绘画文化中的形而上学,也拒绝和极简主义者一起走一条冰冷、僵化的概念主义道路,他的单色画实践把行动置于观念之上,努力在一个“零度化”的平面上重塑绘画的物质性存在,开发被平庸的视觉和说教的理论所遮蔽的感性潜力。里希特凭借这些创作,顺利打通了他个人艺术实践中具象/抽象之间的“隔墙”,进入了一个更加自由和富于包容性的绘画空间,这使他明显地超越了同时代大多数画家——或固守形式、或囿于观念的创作——实现了对现代主义艺术叙事所描述和不断强化的现实困境的突围。里希特的这种超前性,在美国只有菲利普·古斯顿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因此,与后者一样,他也成为当代绘画“后现代”转向时期的关键人物,并随着绘画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复兴”而声誉日隆。
可以说,正是由于里希特等人坚定的、开创性的实践,才改变了后来的批评界和艺术史学者的现实和理论视野,给予他们重新思考当代绘画乃至艺术真实处境的启示。在这种背景下,新的理论摆脱了长期以来进步的意识形态的纠缠,重估整个二十世纪乃至此前所有的艺术历史中发生的一切。就单色画而言,曾经被描述和定位的那些单色画家得以挣脱现代主义叙事的历史链条,开始获得开放性的评价:他们的创作尽管在事实上形成了一幅历史谱系图,但是从个体创作轨迹和迥异的思路来看,却需要新的艺术史笔法对他们进行独立的描述。里希特后来放弃了大规模的单色画创作,然而在有些时候,他又利用一些灰色玻璃等“现成品”材料来延续他在这方面兴趣,这都是极其自然的,也再次证实单色画的实践无论在动机的促发、过程的展开还是在意义的阐释上,都是变动和开放的,难以作为一个整体为某种叙事或结论提供证据。里希特一贯的“对理论的抛弃和他对作品意义的飘忽不定的感觉”,使他的作品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6],在他的单色画及之后的绘画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由,揭示了现代叙事终结之后的“无不可为”的真实状态:一种关于绘画朝向正确目标发展的逻辑被瓦解了,绘画抛弃了建造巴别塔的无望努力,回归到无序的丛林和真实生活当中。在创作单色画的后期,里希特在持续实验绘画物质表面的多样性的同时,开始主动容纳并处理灰色的各种变化。到七十年代末,他直接转向了更繁复、多变的绘画风格,富于冲击力的鲜艳色彩和强烈的动势、笔触的出现像是对前期的反拨,其一贯的超越“形式主义”的物质性表达仍在延续,但更强化了感官体验及其丰富性。及至八十年代,里希特绘制了引起广泛争议的以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红色旅)被屠杀为题材的《1977年10月18日》系列组画,以自己开创的摄影风格的绘画对现实政治作出了有力回应。实际上,目前已年逾八旬的里希特仍旧显示出活跃的创作状态,最新的创作甚至涉及了数码绘画的领域。
概而观之,格哈德·里希特的单色画创作在其个人艺术实践史上形成了一个浓缩的视觉与意义交汇点,对于这个交汇点的分析使我们拥有了新的维度,以解读里希特绘画在创作历程中存在的机缘和必然,重新评价其绘画作品的美学价值;也因其与单色画复杂的历史关联性衔接了现代与当代、美国与欧洲的绘画,从而构成一枚透镜,使我们得以管窥西方绘画和艺术史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1]朱其.形象的模糊——里希特艺术笔记和访谈[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
[2]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M].王春辰,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3]布莱顿·泰勒.当代艺术[M].王升才,译.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71.
[4]爱德华·路希·史密斯.二十世纪视觉艺术[M]. 彭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3.
[5]让-保罗·萨特.存在先于本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5.
[6]乔纳森·费恩伯格.一九四零年以来的艺术[M]. 王春辰、丁亚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81.
(责任编辑刘翠)
Gerhard Richter's Practice of Monochrome Painting and Its Historical Connection
XIONG Yan-jun
(School of Fine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In a variety of painting creation by Gerhard Richter, the monochrome painting has a special nature of visual performance an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stern modern painting history. In view of Richter's practice of monochrome painting creation and the visual style of the painting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paintings generated by the “zero” processing of the color and illusive image, and compares them with the monochromatic painters and the creative motivation and artistic concept of their works in wester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ainting history,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 anti-metaphysics trend, uniqueness of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dependence in Richter's painting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the end of painting” and monochrome painting, and analyzes the openness of Richter's monochromatic painting creation.
Gerhard Richter; monochrome painting; historical connection; theory of the end of painting
2015-10-26
熊言钧(1976-),男,安徽六安人,讲师。
J204
A
1008-3634(2016)03-007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