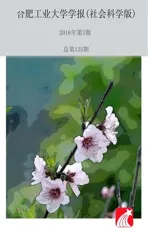汤亭亭《第五和平书》中的创伤书写
2016-03-07王蓉蓉石洪生
王蓉蓉, 石洪生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汤亭亭《第五和平书》中的创伤书写
王蓉蓉,石洪生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230601)
华裔作家汤亭亭晚年将笔触由原先所关注的亚裔女性身份、亚裔男性身份转向对全人类的关怀,其作品《第五和平书》通过对作家自身、虚构人物以及越战退伍老兵等的心灵创伤的书写,体现出她以文学为载体来表征创伤、见证历史、传达作家人文情怀的努力。文章旨在运用创伤理论,将《第五和平书》看成写作治疗文本,从文体、内容和主题等诸方面对作品中的创伤书写进行解读,以期在探索汤亭亭晚年思想和写作轨迹变化的同时,加深对后创伤时代文学治疗功能价值的认识。
汤亭亭;《第五和平书》;创伤叙事;写作治疗
一、引 言
创伤(trauma)源于古希腊词汇“traumatikos”,本意为伤口或者外部的身体受伤。后来弗洛伊德把创伤的概念引入精神分析领域,将其意思延伸为心理创伤。在20世纪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频繁的人道灾难事件:两次世界大战、诸多内战、大屠杀、种族迫害、地区冲突等,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沉重的压力和创伤。创伤体验也从原先少数人的病理特征扩散开来,上升为一种社会症候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创伤研究迅速发展,从原先的医学和心理学渗透到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诸多领域,成为当下人文社科备受关注的跨学科议题。20世纪行之不远,直面和反思这些灾难事件是后灾难时期人类走出创伤阴影、获得精神重生的必由之路。在文学创作领域,关于人道灾难事件的作品也不胜枚举,具体体现在近年来大量涌现的有关创伤叙事的自传、回忆录、传记等见证文学里。英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家卢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认为回忆录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后层出不穷,当下已经形成“回忆录繁荣”的文学景观[1]。著名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于2003年完成的《第五和平书》就是其中一例。
汤亭亭的早期作品《女勇士》、《金山勇士》、《孙行者》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将处于边缘地位的华裔美国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目前读者群和学界对汤亭亭的认识多停留在这些早期作品中,而其新世纪力作《第五和平书》却没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和研究。这与汤亭亭早期轰动美国文坛的作品形成了较大反差。和平书最初的创作灵感源于传说中的古代中国的三卷本和平书。它们讲述如何缔造和平以及与邻邦和睦相处之策,后来这三本书被焚烧了。汤亭亭曾亲自七次来访大陆地区、台湾和香港寻找和平书,但都以失败告终。为了达成心愿,她就以虚构的方式创作《第四和平书》。不幸的是,已经完成156页的书稿连同作家的房屋、所有财物都在1991年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十二年后,一本与《第四和平书》截然不同的《第五和平书》问世,新书从内容到主题也都带有明显的创伤痕迹。目前国内对《第五和平书》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叙事技巧、和平主题和文化解读上。本文拟以创伤理论来观照该作品,着力探讨汤亭亭如何用书写将创伤体验表征为创伤叙事并实现创伤治疗,以期对作家晚年写作风格和思想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同时审视文学在表征和见证创伤历史事件这方面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二、个人创伤叙事
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在其创伤理论代表作《无法言说的经历:创伤、叙事、历史》中将创伤定义为:“对某一突发性意外事件或灾难性事件难以及时应对的体验,当事人对该体验会出现延迟性的回应,并伴随着难以控制的幻觉以及其他破坏性症状。”[2]11也就是说创伤事件的“突发”性和“意外”性超出了当事人的认知范围,并会在之后的时间里以破坏性的方式重复出现在主体意识中,并导致其对现下生活的无所适从。由于创伤体验难以被主体已有的经验意识所接受,因而主体会对其做出混乱和不知所措的反应。对于这样无法被意识接受的记忆,主体往往会采取压抑和遗忘的防御策略,从而导致主体在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叙事的过程中缺乏逻辑性和“断裂”化叙事的现象[2]6-8。观照《第五和平书》,不难发现全书从文体风格到具体内容叙述都呈现出这种“断裂”化的书写形式。
全书由“火”“纸”“水”“土”四个部分和简短的“后记”构成。然而各部分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上的关联,写作风格也各不相同。具体来说,小说主干叙事由不同的叙事视角呈现,并且在不同的场景中展开。“火”是通过汤亭亭的视角追溯奥克兰大火烧毁其房屋、财物以及和平书手稿等一连串创伤事件;“纸”跳转到大火之前作家来中国探寻和平书的经历;“水”又非常突兀地启用虚构人物阿辛的视角讲述其为躲避服兵役,和家人前往夏威夷寻求避难所的事迹;“土”则又跳回现实世界中,通过汤亭亭和诸多越战退伍老兵的视角呈现集体写作疗伤的过程,并穿插了诸多老兵所著的诗歌、散文、日记、随笔等多种文本形式。由此可见,作品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和叙事场景等多个方面都没有连贯性,各部分之间甚至有各自为政的嫌疑,不免给读者带来一种突兀和混乱的感觉。
该书问世不久,纽约时报评论家舒尔曼(Polly Shulman)就指出汤亭亭“没能将各部分融合到一起,这让读者始料未及,因为她在以往的作品中出色地将虚构和记忆交织。”因此,这部小说是“怪异的,充满伤痕的,像是由碎片拼凑而成”,并且充满“大火灼烧后的极度痛苦的气息”[3]。 在受邀水桥书评(WaterBridge Review)访谈时,汤亭亭本人也坦言从未见过这样的作品,也不清楚读者该怎样处理这个复杂的文本。用她自己的话说,《第五和平书》是“非虚构-虚构-非虚构的三明治”[4]。这表明作家自身也意识到该书中松散的故事情节和混杂不清的文体类别将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
除却文章结构所造成的含混感和破碎感外,文中还大量充斥着细节化的个人创伤书写。开篇就将读者带到了火灾和死亡的现场:大火“摧毁了我的房屋,吞噬了我所有的财物,毁坏了邻社和森林”,“带走了25条人命”。 而让汤亭亭近乎绝望的是,仅有的《第四和平书》手稿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5]2。此处她用简短急促的语句一方面再现大火来势汹汹,让人措手不及,另一方面也表明自身在短时间内经历父亲去世、财物摧毁和手稿遗失等多重创伤而难以应对的局面。重创之下汤亭亭患上了大火后遗症,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进行阅读,甚至无法写作[5]21。在水桥书评采访过程中,她回忆“大火之后,我失去了写虚构作品的力量,失去了想象的力量。我无法关照故事中人物的想法和行为。我只想为自己写作,就像孩童时候那样。大火之后,我只想照顾我自己。”[4]可见此时汤亭亭的写作单纯是为了舒缓个人情绪,“就像写日记一样,没有形似,没有艺术性,也没有好的措辞”, “全书都是自私的第一人称‘我,我,我……’。”[5]62作家这样私密化、个人化的写作状态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卡鲁斯指出创伤在第一次发生时无法被主体充分理解,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期后,可能在叙事中体现[2]7。汤亭亭的住所离火源中心有十条高速公路之远,但仍没能幸免于难。汤亭亭用“不可能”(impossible)表明这种现象的不合理性,表明她对该事件的难以理解以及对现状的无法接受,她毫无理由地认定这是亡父对其没有在祭祀礼上提供足够烧祭品的惩罚[5]14。直到母亲安慰她,正是父亲的在天之灵才保佑其幸免于难,作家这才释怀。大火给汤亭亭带来严重的创伤体验,就像她自己说的:“如果一个女人要写一本和平书,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毁灭。”[5]1
由于创伤事件在发生当时没能被主体充分地认识,因而创伤体验“只有在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时间的联系中才能完全显现”[2]17。当创伤事件转化为创伤叙事时,后者对前者有着极强的暗示性和指涉性。第三部分“水”是通过虚构人物阿辛的视角将战争呈现给读者,字里行间显露出战争给汤亭亭带来的创伤。汤亭亭在2006年一次有关《第五和平书》的采访中曾被问及阿辛为什么对她如此重要,她如是说:“阿辛就是我自己。”[6]早在《孙行者》里,读者就可以在阿辛身上看到汤亭亭本人的影子:他们都是华裔美国人,又都是作家,因此汤亭亭本人就是阿辛这个虚构人物的原型。汤亭亭出生于二战期间,频繁的战争体验给她带来无法磨灭的伤痛。她在童年时代就曾多次目睹堂兄弟远赴欧洲和太平洋参战,“虽然没有亲自上过战场,但是战争却夺走了我的青春岁月,它影响了我的一生。”[7]因此战争无疑给汤亭亭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记忆。“水”中展现了阿辛曾想通过剧本创作来建构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然而战争的频繁爆发让他认识到以艺术创建和平的不可操作性。为了抗议战争,躲避服兵役,阿辛和家人逃往夏威夷,却发现战火无处不在。当他们经过飞机场时,看到从战场上运回来的士兵尸体,阿辛的儿子马里奥受到惊吓。这也是对汤亭亭自身的战争创伤经历的真实写照。作家曾在其另一部作品《夏威夷一夏》中追忆全家为逃避战火,迁往夏威夷生活的过程。抱着远离战争目的离开的汤亭亭,却发现“战争无处可逃”。她看到坦克、装备和士兵被送往夏威夷,听到士兵演练的炮击声。一家人一起登山徒步时,“看到弹道炸开草坪露出红色的土地,就像是流着的鲜红的血。”[8]46-47汤亭亭的经历表明,有些人虽然没有亲历战争,但战争却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入侵处于战争时代的每一个人,给他们留下无法抹去的创伤体验。
《第五和平书》充斥着汤亭亭个人的创伤书写:父亲去世的家庭创伤、大火引发的自然灾害创伤以及人为的战争创伤相互交织,汇集成一本伤痕累累的书。可见作家没能写出完整、平稳的叙事文本是对其本人碎片化的心理再现的结果,这也从反面说明创伤事件无法像人类正常经验那样被逻辑性地再现。
三、集体写作治疗
文学和健康之间的实证研究虽然到20世纪才出现,但它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之初: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掌管诗歌和健康二职于一身,可以说是最早暗示文学与健康微妙关系的隐喻。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弗洛伊德在临床研究中发现,治愈心理创伤的重点在于当事人能够口头言说自身的创伤经历,并将创伤事件转化为创伤叙事,于是发明颇有成效的“谈心治疗”(talking cure)方法。卡鲁斯延承弗洛伊德的创伤研究思路,将“谈心治疗”和文学的再现功能等同起来。她认为由于创伤的起点和终点都无迹可寻,因此“任何创伤经验都应该以文学的形式加以表征,而不能够以其他直接的言说形式”[2]5。因为在写作再现创伤的过程中,主体能以一种回顾性的旁观者身份再现创伤事件,因而更容易与其保持一定距离。这意味着主体无法直接言说的创伤体验,往往可以通过写作的方式加以表征。
汤亭亭生来就是一个善于运用写作治疗的实践者。在2007年和莫耶斯(Bill Moyers)的一次采访中作家透露文字总能赋予自己“安全感”,从小时候起每当遇到不开心的事,她都会用写作的方式加以排遣:“我会写下字句,看它们会把我带向何方。当然它们总能将我带到某处,而此时我已经完成了一首诗,一个故事,之后便是一个不同的人了。”[9]当莫耶斯好奇故事怎么会有治愈力量时,汤亭亭感慨:“故事是一种能够带来次序的表征形式,一个形式完好的故事有着和性和生命本身一样的能量……在故事中,我们能够和别人及其心灵沟通。同样,我们也能和自己交流。”[9]作家自身的经历表明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访谈过程中,汤亭亭也提及:“大火让我痛苦不已、深受创伤”,为了远离人群,“我像孩童时期写作那样,一个人秘密蜷缩在角落里。”[9]当问及是如何走出角落时,汤亭亭说是“社群”的力量,是在和经历过残酷战争的退伍军人一起写作、彼此倾听的过程中走出了绝望和毁灭:“在团体写作中——来自同伴的压力和支持,集体的能量和倾听——给了我很大的灵感。”[9]在此之前汤亭亭一直是独自创作,大火烧毁了供她一人写作之地的阁楼,这让她联想到自己很可能和阁楼一道被火海湮没。因此她将阁楼的烧毁看成“一种迹象”,一种走出个人写作天地,回归团体的启示:“和平书的重书需要一个集体。”[5]62
越战结束之后,许多士兵对现下的生活感到无所适从。生活在被战争创伤撕裂的两个世界里,他们失去存在的完整性,甚至有不少退伍士兵选择自杀来结束无法承受的创伤,如何治愈幸存者的心灵创伤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汤亭亭在这方面可谓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和平书烧毁后,作家意识到用艺术缔造和平是虚妄无力的,于是转而关注幸存者的故事。自1991年起,汤亭亭致力于组织和帮助美国退伍老兵以创意写作治疗战争创伤,重新找到精神回家之路。
安·卡普兰(E. Ann Kaplan)曾指出,个人创伤和集体创伤往往相互交织,难以剥离。据此他将创伤受害者归为两类:第一类是亲历创伤者,包括死者和幸存者;第二类是间接受到创伤影响者,比如直接受害者的家庭成员或亲友、救护人员、目击者,甚至包括创伤事件的听众和读者[10]。汤亭亭的写作团体不仅有越南退伍士兵,还有参加过二战、朝鲜战争和海湾战争的士兵以及他们的家人、战地医护人员和一些通过其他途径参与战争的人。这些成员从美国各地赶来,虽然背景各异,但却都曾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亲历过战争。虽然此时战争已经过去数十载,但战争的“影响和后果仍然残留在我们的身体里。”[5]260汤亭亭在第一次组织退伍士兵见面时,有意识地让每个成员用作家的身份介绍自己,以此让他们与士兵的角色拉开距离,重新定义自我。写作团体的一些成员透露自己选择遗忘和压抑的方式,但战争的梦魇始终潜藏在意识背后,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影响他们当下的抉择和对未来的期待,使得生活本身成为一种危机。汤亭亭希望通过写作让每个成员“意识觉醒”,将“碎片叙述成故事。通过语言和文字再现战争,用艺术的方式让过去重新变得有意义”[5]260。
卡鲁斯认为拥有类似创伤经历的人更容易产生移情效应,感怀彼此的情绪。写作团体中的成员拥有共同的创伤经历,使得他们更易进入对方的知觉意识,让彼此成为最合适的听众,同时也为他们言说各自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更具理解和尊重的氛围。越战士兵布朗说道:“写作团体很不一样,我只需要倾听而不需要主动加入其中。我可以什么也不说却不感到尴尬,因为我知道他人能够体会我的感受。加入这个团体后,我更加认真地对待自我治愈这件事了。”另一位老兵写道:“我写日记。记录我的痛苦。我在写作过程中自我疗愈……诗歌和日记都是我自身疗愈的途径。”[7]写作既能让退伍士兵直面战争带给他们的恐惧和死亡, 又有助于摆脱孤独和失语的生活现状,从而修补他们被战争创伤撕裂的灵魂。
汤亭亭创办写作团体的宗旨是帮助退伍士兵“重返家园”,找回精神归宿。因而有意将自己的写作团体称为“sangha”, 此为源自佛教中“和谐共生”的社群之意,作家想借此寓意和退伍士兵共同构建一个彼此分享故事的安全之地。她认为:“在sangha中,人们可以相互交流情感和思想。”在这里大家一起写作,一起冥想,一起饮食。这和汤亭亭小时候同家人团聚在一起讲故事的情形一样,“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5]364。对汤亭亭来说,“sangha”是一个更大的“讲故事”(talk-story)团体,让更多的人发声。她表示:“只有身处愿意倾听我们故事的群体中时,人们才会愿意讲述他们的故事。”[9]通过集体写作的方式,退伍老兵讲述自己的故事,倾听他人的故事,逐渐从旧的故事中蜕变出新的自我。
在这样一个充满尊重和关怀的氛围中,汤亭亭引导写作成员口头讲述和字面书写个人故事。在整个过程中,作家并非被动地接受每个人的故事,而是给予关注,并时不时地对他人的故事加以总结,并穿插自己的感悟,以此来激励更多的人说出自己的故事。在分享故事和倾听故事的过程中,写作成员能够真正直面创伤,重返回家之路。《第五和平书》也由原先有关汤亭亭一人的写作治疗文本延伸为五百多位越战退伍老兵集体写作的疗愈之书。
四、作家的人文情怀
从汤亭亭的创作历程来看,其早期一系列备受赞誉的作品《女勇士》、《金山勇士》、《孙行者》都是对华裔美国人创伤经历的书写——《女勇士》是对沉默、失语的华裔女性的发声,《金山勇士》是对在非人道的种族移民政策压制下的早期华裔美国移民集体创伤的表征,《孙行者》则从文化创伤的角度揭露了新一代华裔美国人的文化和身份焦虑。这些作品虽然形式多变,但始终都是对华裔族群故事的不同演绎。此外它们大都融合虚构、历史、神话和传说等多重文体于一身,并且掺杂作家自己在美国的切身经历,因而又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与作家前期的作品相比,《第五和平书》从内容到风格都有很大的转变。它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传或回忆录,也不是纯粹的虚构作品,因而难以被贴上一个确定的文体标签。汤亭亭于2006来中国访学期间曾谈论到《第五和平书》的创作,表示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应该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她将“《第五和平书》视为一位愿意承担责任的老年作家的作品”[6]168-169。汤亭亭表示大火烧毁的《第四和平书》是虚构的,“在虚构的作品中,我可以想象我们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可以虚构主人公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大火之后,我不再写虚构的作品:虚构作品是一种怜悯的写作形式,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自私的写作方式。”[5]62从汤亭亭话语间透露的信息可以断定被烧毁的《第四和平书》沿袭其早期的作品风格,而《第五和平书》的创作动力就是超越虚构,用文学践行母亲一贯教导她的“教育美国,教育全世界”的使命[5]239。作品中的叙事声音由亚裔族群转向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退伍战争士兵,原先一个人的自传变成一个集体的自传,这体现了汤亭亭晚年试图通过写作参与治疗、见证历史以及传达人文关怀的努力。
文字产生之初就成为人类经验最重要的存储模式。作为人类记忆的特殊载体,创伤记忆可以通过文学实现代际传递功能。“历史不仅是危机的传承,也是幸存者的延续。它只能是大于个体和单代人的历史。”[2]71创伤经历往往是局部人群的体验,但是文学能够将个体或者一个集体的创伤记忆记录下来,转化为全人类的普遍记忆。创伤的社会意义在于分享创伤记忆,见证不仅要求当事人言说自己的创伤经历,还要有听众参与进来,从而形成一个言说创伤经历、分享创伤记忆和建构创伤历史的过程。汤亭亭一再强调“当人们在分享故事的同时也在分享自己的苦难,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听众。我们会分担他的负担”[6]。所以见证不是当事人的个人独白,而是一个需要听众加入的对话模式。通过对创伤故事的倾听,写作团体一方面帮助退伍老兵走出失语状态,满足了他们言说创伤、走出创伤阴影的心理需求;同时也为我们广大读者提供了解战争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的可能。读者可能没有经历创伤,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我们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了解人类自身的罪恶和苦难。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唯一能留给后人的就是有关我们自身的故事。基于此,汤亭亭将老兵们的创伤书写汇集成书——《战争的老兵,和平的老兵》,并在2006年出版。此时她将自己的作家身份隐去,以编者的身份在引言中写到:“我们说故事和听故事是为了生存,是为了保持清醒,为了与他人相关联,为了弄清事件的后果,为了记录历史,为了重建文明。”[12]1这意味着退伍士兵不再局限于故事的讲述者,我们读者也超越了听众的角色。大家在倾听和见证的互动过程中共同致力于创伤历史的重建任务。因此创伤书写不仅能够帮助创伤者开启心理重建之门,也能让后创伤时代的人们反思创伤历史背后的深层次意义。
被大火肆虐过后的奥克兰让汤亭亭联想到战后越南的千疮百孔和被原子弹夷为平地的日本广岛。作家将这场大火看做上帝对人类无视自身罪恶的惩罚和启示:“上帝显现给我们的是(战后的)伊拉克。杀人是邪恶的。”[5]14然而同年,美国政府宣布再次发动对伊战争,这使长期致力于和平事业的汤亭亭大失所望,也迫使她认识到“在虚构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加以解决。”[5]241于是作家投身于反对战争、用实际行动营造全人类的和平事业中。为抗议美国政府宣布对伊战争的举动,汤亭亭亲自参加游行示威团体,到白宫门前抗议,和人群一起诵读历史和诗歌等方式反战,但却被警察逮捕入狱。值得一提的是,和她一同被捕的还有著名非裔美国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5]402。虽然艺术和非暴力的方式无法阻止美国政府发动战争,但汤亭亭的英勇行为重新定位了作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作家不仅能在象牙塔里用文字书写想象的和平,也能以实际行动反对战争、缔造和平。
团体写作的经历也让汤亭亭思想更加开阔、更具同情心。作家开始将人类看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每个人都是跨种族和跨文化的存在。在她眼中“没有所谓的本土的故事,无论是源于亚洲、非洲、美洲还是澳洲的生命。万物彼此关联。”[5]92写作团体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关注。当BBC试图将其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时,汤亭亭坚持展示给世人的必须是“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的美国。每次对外开战,美国自身都出于一种分裂的痛苦之中。无论敌人是谁,他都和我们息息相关。”[5]361汤亭亭的言论透露了她对美国对外文化和外交政策的不满和谴责,因为在她看来,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胜者,更多的是无法磨灭的创伤和丧失人性的代价。当下,汤亭亭和退伍老兵继续着写作团体活动,试图向世人推广这个和谐共生、充满友爱的社群。这也是汤亭亭在《第五和平书》之后继续用写作为后创伤社会的人们撒播关怀之心、传递作家人文情怀之举。
五、结束语
刚刚过去的20世纪被不少创伤学者称为创伤的世纪,其余震仍然冲击着当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在《第五和平书》中,汤亭亭反思当人类在参与非人性化的事件后,如何再次变得人性化、如何重获新生等问题。此时作家写作已不再为了建构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而是改造社会的手段。这表明汤亭亭晚年已经超出近年来华裔作家所关注的种族和文化等问题,转而投身于反对战争,营造全人类和平事业的努力。书中汤亭亭用文学纪念过往历史事件、填补当下创伤记忆空白、憧憬人类和谐共存的未来。同时她也向我们指出,创伤事件有着广泛的社会性,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倾听,创伤体验才不再是一种孤独的体验。这也是汤亭亭用文学来抵御后灾难时代人们对创伤历史的忘却。创伤者终会离世,但却能在社会关怀氛围之下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创伤叙事,将创伤历史传递下去,为后人生存所警醒。
[1]Roger Luckhurst. The Trauma Question [M]. London: Routledge , 2008:117.
[2]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96:6-8, 11.
[3]Polly Shulman.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Out of Ashes.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EB/OL].(2003-09-28)[2015-10-20].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q=Polly+Shulman%2C+The+Fifth+Book+of+Peace%2C+Out+of+Ashes.&btnG=&hl=zh-CN&as_sdt=0%2C5.
[4]Conversations Maxine Hong Kingston. WaterBridge Review [EB/OL].(2004-05-09)[2015-10-11].May 9 2004. Oct. 11, 2015. [5]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3. [6]Miel Alegre. Dave Weich. Maxine Hong Kingston after the Fire. Powells's Author Interviews [EB/OL].(2006-10-23)[2015-09-23].http:www.powells.com/blog/interviews/maxine-hong-kingston-after-the-fire-by-dave/. [7]Justin Berton. Veterans group, Maxine Hong Kingston together Use Writing to Heal. Interview [EB/OL]. (2008-01-07)[2015-11-06].http://www.sfgate.com/health/article/Veterans-group-Maxine-Hong-Kingston-together-use-3298689.php. [8]Maxine Hong Kingston. Hawai'i One Summer[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46-47. [9]Bill Moyers. Author Maxine Hong Kingston on Working With Veterans, Interview [EB/OL].(2007-05-25)[2015-11-06].http://billmoyers.com/content/author-maxine-hong-kingston/. [10]E Ann Kaplan. Trauma Culture: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M].New Yor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5. [11]方红.和平·沉默·叙事技巧——《第五和平书》创作谈[J]. 当代外国文学2008,(1):168-169. [12]Kingston, Maxine Hong, Veterans of War, Veterans of Peace [M].Kihei:Koa Books, 2006:1. (责任编辑蒋涛涌) Traumatic Writing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WANG Rong-rong,SHI Hong-sh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In her later years,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Maxine Hong Kingston has shifted her attention from Asian American identity to universal mankind. In her new workTheFifthBookofPeace, Kingston examines her personal trauma, fictional characters' trauma and veterans' collective trauma,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writing in transferring traumatic experience to traumatic narrative, in bearing witness to history, and in extending a writer's humanistic caring to manki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re, content and theme ofTheFifthBookofPeacefrom traumatic theory and perceives it as a text inscribes writing therapy, so as to get a better picture of Kingston's thoughts in her later years as well as the healing func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post-traumatic era. Maxine Hong Kingston;TheFifthBookofPeace; traumatic narrative; writing therapy 2015-11-13 王蓉蓉(1991-),女,安徽芜湖人,硕士生。 I106.4 A 1008-3634(2016)03-005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