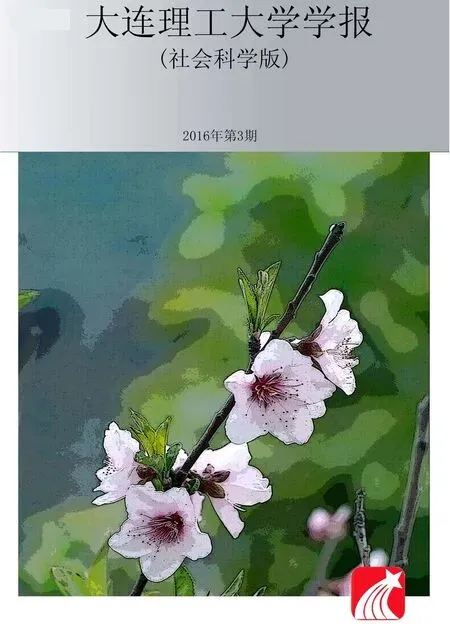截点视域下“诗”学发展的会通与新变
——以《易林》说诗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比较为中心
2016-03-07田胜利
田 胜 利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截点视域下“诗”学发展的会通与新变
——以《易林》说诗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比较为中心
田 胜 利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易林》说诗是西汉末年诗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新出土的《孔子诗论》是关于孔子论诗的文献资料,代表的是先秦时期解诗的观点。汉代《易林》说诗和《孔子诗论》解诗具有一致性,有的案例的相似度明显高于其他诸家诗说,彰显的是《易林》说诗与《孔子诗论》解诗的会际和赓续;《孔子诗论》解诗简约、公允;《易林》说诗具体、灵活,二者又有不少分际存在,相异之处标示的是西汉末年诗学发展的新变。
关键词:诗学;孔子诗论;易林说诗;演变
《焦氏易林》(以下简称《易林》)说诗折射的是西汉末年诗学发展的面貌,上博简《孔子诗论》是新出土的解诗文献,学术界基本认定其是先秦时期儒家的诗学文献,并且在西汉时期或还有版本流传于世。《孔子诗论》属先秦解诗的典范,《易林》是西汉的说诗代表,本文选取诗学史上这两个截点,采用对读的视角,将《易林》说诗与《孔子诗论》解诗予以比较,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同异,有利于厘清周汉诗学发展的演变走势。
一、《易林》说诗与《孔子诗论》的会际及赓续
《易林》说诗建立在用诗基础上,是《诗》的繇辞化,《易林》说诗既有对《诗经》原诗的征引,也有对《诗经》诗歌主旨的蕴藉,落实到具体案例,有的指向和《孔子诗论》解诗具有一致性,存在着会通之处。
《诗经》描写的爱情婚嫁类诗歌引人神往,《邶风·燕燕》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诗的写作缘由,《毛诗序》记载:“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1](p298)毛诗认为是卫庄姜送归妾时所作的诗篇。关于《燕燕》,韩诗未详,今存鲁诗说见于刘向《列女传·母仪》,曰:“卫姑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毕三年之丧,定姜归其妇,自送之至于野,恩爱哀思,悲以感恸,立而望之,挥泣垂涕,乃赋诗曰:‘燕燕于飞……。”[2]鲁诗也认为是定姜送媳归之作。毛序、鲁诗的说解虽已揭示出作诗见志的原委,但并没有指明“己志”为何?对此,《易林》说诗提供了答案:
萃之贲:泣涕长诀,我心不悦。远送卫野,归宁无咎。[3](p1668)
恒之坤:燕雀衰老,悲鸣入海。忧在不饰,差池其羽,颉颃上下,寡位独处。[3](p1190)
《易林》对《燕燕》的说解,彰显的是西汉末期诗学观点,《萃》之《贲》末两句提及卫野,揭示的是庄姜送别陈女的地点。归宁无咎,宁指宁立,毛传:“宁立,久立也。”宁与原诗中“伫立”相应。咎,学津本、四部本、士礼本作子,句谓庄姜对陈女“失去爱子而归国”的感伤。《恒》之《坤》末句“寡位独处”,抒发的是孤零零的悲苦情境,既指陈女,也暗指庄姜自己,正是“己志”之所指。
《易林》说诗对女主人翁因悲苦心境而作《燕燕》的见解,在《孔子诗论》中能找寻到渊源和契合点。
第十简:燕燕之情,……曷?[4](p139)
第十六简:燕燕之情,以其蜀也。[4](p145)
孔子认为《燕燕》一诗言情,蜀,马承源云:“下句读为‘以其独也’,‘蜀’在此不能解释为字的本义,当读作‘独’”[4](p145),马先生的释读是可信的。《燕燕》之情缘于“以其独”,独,指孤独、独处之义,和《易林》说诗可以相互印证,《恒》之《坤》末句“寡位独处”,正是此义,《易林》说诗和《孔子诗论》具有一致性。
《易林》说诗和《孔子诗论》解诗在政论美刺类诗中也存在会通之处,二者的相互印证,有利于正确地对《诗经》予以释读和还原。
《诗经·召南·甘棠》,《易林》写道:
师之蛊:精洁渊塞,为馋所言。证讯诘问,系于枳温。甘棠听断,怡然蒙恩。[3](p276)
复之巽:闭塞复通,与善相逢。甘棠之人,解我忧凶。[3](p932)
小过之坤:谨慎重言,不幸遭患。周召述职,脱免牢门。[3](p2232)
既济之观:结衿流粥,遭馋桎梏。周召述职,身受大福。[3](p2270)
《易林》化用《甘棠》诗而得,后两则中的周召述职,指周公旦和召公奭。召公,《甘棠》原诗中称作召伯,如“召伯所茇”、“召伯所憩”、“召伯所说”。《甘棠》诗位列《召南》第五首,召,朱熹注:“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5](p9)召伯当指成王时期的召公奭,而非周宣王时期的召虎。《召南·甘棠》诗是召公奭采邑之地的民众创作,本事记载见于《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歌咏之,作《甘棠》之诗。”[6](p1246)《易林》说诗既是对《甘棠》歌咏召公奭的认同,也是对其故实的化用,甘棠之人解我忧凶,使我脱免于牢关、桎梏之患是引申发挥。《毛诗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1](p287)鲁诗文献《说苑·贵德篇》曰:“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7](p94)类似的记载也见于《韩诗外传·卷一》第二十八章。三家诗认为《甘棠》一诗歌咏的是召公奭,而非召虎,和《易林》说诗具有一致性。
《孔子诗论》解《甘棠》诗又是怎样的呢,相关简文如次:
第十简:《甘棠》之报,……曷?[4](p139)
第十五简:(思)及其人,敬爱其树,其报厚矣,《甘棠》之爱,以邵公……[4](p144)
第十六简:(甘棠之爱,思)邵公也。[4](p145)
第二十四简: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4](p153)
孔子解《甘棠》诗,分别见于四支简。报谓报恩,交代的是该诗的写作意图。敬爱其树的本事,《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6](p1246)又《韩诗外传》:“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美而歌之。”[8]百姓爱其树是对召公爱之深切的显现。第十五简、十六简中的“邵公”称之谓公即指召公奭,第二十四简是孔子据诗意而作的阐发。孔子认为《甘棠》是民众赞美、报答召公奭的诗篇,这和《易林》说诗于歌咏对象和主旨上是十分吻合的。从先秦至西汉末年《易林》说诗,对于《甘棠》一诗的歌咏对象,各家诗说是没有分歧的。
《鹿鸣》,《易林》有这样的文字:
益之恒:鹿得美草,鸣呼其友。九族和睦,不忧饥乏。[3](p1569)
升之乾:白鹿鸣呦,呼其老小。喜彼茂草,乐我君子。[3](p1691)
《易林》化用鹿鸣意象,配以君子当之,是对君子乐享嘉朋的赞美,也是对《鹿鸣》主旨的揭示。针对《小雅·鹿鸣》主旨,今存的鲁诗主讽刺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载:“鲁说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9](p551)鲁说之语出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6](p357)。《毛诗序》曰:“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1](p405)《鹿鸣》借写宴享欢庆,歌咏君臣之间的和谐之美。类似的说法,还见于韩诗,如《后汉书·明帝纪》:“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壎篪和之,以娱嘉宾。”[10]明帝习韩诗[9](p551),是知韩与毛义合。毛诗、韩诗的说法大体是可信的,但仅和君臣这一政治背景相系,于义理层面则略显模糊,对此,《孔子诗论》有更为详细的论断:“《鹿鸣》以乐词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傚,终乎不厌人。”首句突出主人与宾客宴饮在于乐,后几句交待乐之实质在于以道义相交,向善者学习,不厌人而与人同乐的美德。《易林》说诗不如《孔子诗论》解诗之深刻,但着眼于对君子乐宴宾客的赞美则是一致的。
《周南·葛覃》一诗,林辞《兑》之《谦》曰:“葛生衍曼,絺绤为愿。家道笃厚,父兄悦喜。”尚秉和先生注:“《诗经·周南·葛覃篇》为絺为绤,服之无斁。”[11](p463)无斁指不厌,林辞首两句以葛生漫衍起兴,末两句设想的是女子归娘家后的快乐场景,合乎原诗主旨。《毛诗序》:“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漧濯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1](p276)毛诗附会为后妃之说,显然是对原诗主旨的偏离。韩诗于此诗的解释未详,鲁诗遗说为“葛覃恐失其时”,见于《古文苑·蔡邕·协和婚赋》,甚是简略。《孔子诗论》曰:
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而必欲反一本。夫葛之见歌也,则……[4](p145)
氏,廖名春先生释为“祗”[12],指敬。首句黄怀信先生注:“祗初之志,当直释为敬本的思想”[13],黄先生的见解是可信的,人之本在于父母,敬本、反本正是《葛覃》女主人翁回归娘家最贴切的说解,和《易林》说诗契合。
《诗经》中诗篇并非都是赞美歌颂,还有大量篇目是对世事、权贵的讽刺和揭露,《易林》说诗和《孔子诗论》解诗于此端也有不少会通。
《邶风·柏舟》,林辞《屯》之《乾》曰:“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逢时,退隐穷居。”抒发的是生不逢时的感叹。针对《柏舟》的写作缘由,韩诗未详,鲁诗为“卫宣夫人明志之作”,见于《列女传·贞顺篇》,与《易林》说诗不合。《毛诗序》曰:“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1](p296)毛诗标示的主旨可供参考,以卫顷公时期的故实将诗歌予以坐实则略显背离,《柏舟》诗旨,《孔子诗论》写道:“《邶·柏舟》,闷。”《邶风·柏舟》也确实表达的是一种怨懑之情,如首章:“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遊。”主人公怀才而不得遇,故生发出多重感伤。这和《易林》说诗于情感指向是契合的。
《周南·卷耳》,《易林》多次称引:
乾之革:玄黄虺隤,行者劳疲。役夫憔悴,踰时不归。[3](p35)
贲之小过:玄黄瘣隤,行者劳疲。役夫憔悴,处子畏哀。[3](p866)
鼎之乾:倾筐卷耳,忧不能伤。心思古人,悲慕失母。[3](p1837)
《易林》说诗之义,首则叙写役夫在外劳苦奔波的窘境;次则处子畏哀指未婚妻子会心情悲伤;第三则称忧愁而不能悲伤,古人指故人,末两句谓长思亲人,悲恋慈母。针对这首诗歌的主旨,韩诗未详,《毛诗序》:“后妃之志也。”[1](p277)今存鲁诗遗说见于《淮南·俶真训》高诱注“《诗·周南·卷耳》篇也,……言我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14](p75),均与《易林》说诗不合。《孔子诗论》写道:“《卷耳》不知人。”不知人,谓不知道心中怀念的那个人现在情况怎么样。《易林》征引该诗,指的亦是役夫不知亲人和未婚妻子的生活情况。
《祈父》,林辞《谦》之《归妹》写道:“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转忧于己,伤不及母。”首两句中爪牙指一般的卫士,祈父指司马,职掌兵甲,语出《祈父》前两章。“伤不及母”句出自《祈父》末章。整则繇辞再现的是对祈父的尖锐讽刺。与之相应,《孔子诗论》说道:“《祈父》之责,亦有以也。”[4](p137)孔子认为责备祈父是理所应当、有根有据的,这和《易林》说诗具有相似性。
总之,《易林》说诗情感指向分明,说诗建立在用诗基础上,对诗具体而细腻的理解和《孔子诗论》解诗存在相同或相似之处。对此,刘银昌先生指出:“焦赣之接受《孔子诗论》极有可能……《易林》这种对情感的重视,和《孔子诗论》所谓的‘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是否有关,是值得思考的问题。”[15]刘先生的推测是有道理的。《易林》说诗往往具体入微,《孔子诗论》解诗则以概括的准确到位与之相得益彰,如《邶风·北风》诗,《毛诗序》称刺虐也,《易林》和《孔子诗论》观点一致与毛诗均不同,《孔子诗论》曰:“《北风》不绝人之怨。”周凤五先生论述道:
不绝人之怨,则虽朋友一时交恶,然而彼此无怨,终能言归于好也。……《易林·晋之否》:北风寒凉,雨雪益冰。忧思不乐,哀思伤心。写二人交恶;《易林·否之损》(《易林·噬嗑之乾》同)“北风牵手,相从笑语。伯歌仲舞,燕乐以喜”,则写二人言归于好,与简文“不绝人之怨”相应,而与《毛传》:“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立论迥异,《易林》在三家《诗》为齐《诗》,其说同于简文,盖前有所承者也。”[16]
周先生的“盖前有所承者”,是对《易林》说诗和《孔子诗论》可能成在渊源关系的推测,陈桐生先生也说:“从以上材料可知,《齐诗》之说在不少地方接近《孔子诗论》”[17](p238),陈先生的看法是可信的,他罗列的具体的齐诗语料大抵都采自《焦氏易林》。“《孔子诗论》在汉代或有传本”,陈先生以之为章节标题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17](p218-223)。《易林》说诗和《孔子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读,有时已几无区别,如《易林》说“湛露之欢,三诀毕恩”,《孔子诗论》则曰:“湛露之嗌,其犹酡也”。《易林》说“墙茨之言,三世不安”,《孔子诗论》则曰:“慎密而不知言”。在比较的视域中,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易林》说诗与《孔子诗论》的会通不是偶然的,而是客观存在的。《易林》说诗来源广泛,与《孔子诗论》解诗的相似度有的明显高于其他诗说,具有承继渊源是极有可能的。
二、《易林》说诗与《孔子诗论》的分际及新变
《易林》说诗和《孔子诗论》解诗存在相通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差异,二者的差异是诗学流变过程中的变化与发展。风格上,《孔子诗论》解诗平允公正,《易林》说诗则显得相对灵活,不束限于对一首诗歌的准确揭示。目的上,《孔子诗论》解诗是孔子儒家学说的有机构成部分,而《易林》说诗,《诗》是一种附带的工具,仅是占繇辞的取用对象。
《关雎》是一首耳熟能详的诗篇,韩诗称“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韩诗以之为刺诗。毛诗、《易林》说诗与之不同,《毛诗序》曰:“后妃之德也。”[1](p269)《毛诗序》注重淑女之德,然毛诗以后妃之德坐实,则有欠妥之处,《易林》说诗亦重淑女之德,并且对这种德有形象化的发挥,《易林》写道:
小畜之小过:关雎淑女,配我君子。少姜在门,君子嘉喜。[3](p390)
履之颐:雎鸠淑女,贤圣配偶。宜家受福,吉庆长久。[3](p408)
晋之同人:贞鸟雎鸠,执一无尤。寝门治理,君子悦喜。[3](p1313)
姤之无妄:关雎淑女,贤妃圣耦。宜家寿母,福禄长久。[3](p1632)
《易林》用《关雎》之诗,每则繇辞均以雎鸠起兴,雎鸠在爱情上专一不二,喻指淑女贞节贤美,吉善长久等语皆盛赞贞淑之女是贤圣君子的佳偶,占筮时取其阴阳和谐的吉利象征含义。着眼于雌雄阴阳和合的这种解读在其他典籍中也能找到,陆贾《新语·道基篇》:“关雎以义鸣其雄。”[18]又《淮南子·泰族训》:“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谓其雌雄不乖居也。”[14](p639)对此,《孔子诗论》解诗是怎样的呢?相关上博简有这样的文字:
第十简,关雎之改……曷?曰:童(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4](p139)
第十一简: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
[4](p141)
第十二简: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4](p142)
第十四简:其四章则愉矣。以琴瑟之悦,嬉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4](p143)
《孔子诗论》对《关雎》一诗的解读重点在于以色喻礼,强调一个“改”字,改而合乎礼,注重的是男主人公的表现。称赞男子的举动契合孔子对于君子的界定和要求,是儒家礼学思想的外显。如此一来,《易林》说诗和《孔子诗论》在解读取向上依据不同的目的而呈现不同样态,《易林》引《关雎》,重点在于淑女,占筮取其阴阳和谐的象征意义;《孔子诗论》重点在于君子,取其改而知礼之义。《易林》说《关雎》诗,“既不同于毛诗,又不同于三家诗”[19]而是一种较为独特的说解。
《小雅·黄鸟》一诗,林辞《乾》之《坎》曰:“黄鸟采菉,既嫁不答。念我父母,思复邦国。”采菉,学津本作来集。焦赣对于《黄鸟》一诗予以引申,叙写成一位女子出嫁后思念故国父母诗作,此种说诗已经和原来的诗歌主旨有所背离,占筮时则取其阴阳隔塞的象征义。针对《黄鸟》的主旨,《毛诗序》曰:“刺宣王也。”[1](p434)郑玄笺:“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聊兄弟之不固。”[1](p434)毛诗和郑玄笺着眼于诗歌的现实讽刺意义,坐实性解读也未必合乎诗歌原意,相比之下,《孔子诗论》有这样的论断:“《黄鸟》则困而欲反其故也,多耻者其病之乎?”针对孔子的言辞,徐正英先生有如下辨析:
所谓“欲返其故”,自然是指身处困境中的作者渴望返回故国故乡。所以,孔子对《黄鸟》诗旨的概括,大意是说:《黄鸟》一诗抒发了作者困厄异国而渴望返回故乡的思想感情。值得重视的是,孔子对《黄鸟》一诗的解读至此并未结束。其又云:“多耻者其病之乎?”……意思是说:多蒙耻辱的人,会担忧此类事情发生吧。细玩孔子论《黄鸟》全部言论,他确实是前句概括诗旨,后句则由诗旨诱发联想,发表了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看法[20](p80-81)。
徐先生的辨析是可信的,《黄鸟》的作者遭受困厄渴望返回故国故乡,如《小雅·黄鸟》原诗首章写道:“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归,复我邦族。”诗歌以黄鸟起兴,喻指作者在外遭受困厄而思念归邦返家心绪。诗歌没有指明讽刺对象是宣王,对此朱熹在《诗集传》中有这样的判断:“今按诗文,未见其为宣王之世。”[5](p129)也没交代作者的女性身份,毛诗、《易林》说诗都是对其的发挥,《孔子诗论》则较为公允。
和《黄鸟》具有相似情形的还有《鹊巢》一诗。《毛诗序》以为“刺宣王”系不确之论。《鹊巢》出自《召南》,是一首述写女子出嫁的诗作,林辞《节》之《贲》曰:“喜乐踊跃,来迎名家。鹊巢百两,以成嘉福。”鹊巢点名篇题,以成嘉福是对这段婚姻的美好期待和评价,百两出自《鹊巢》诗的最末一句“之子于归,百两成之。”[1](p283-284)百两形容出嫁时的队伍之浩大,孔颖达疏:“笺以御为迎夫人,将之谓送夫人,成之谓成夫人,故易以百两之礼送迎成之。”百两之礼,暗含出嫁女孩的身份和家世之高贵。针对这首诗的主旨,《易林》说诗秉持的是赞扬的态度。
《鹊巢》诗歌主旨,在后代的流传中却生发出多种不同的解读取向,郭晋稀先生认为是抢婚诗,黄怀信先生认为这是一首诸侯废掉原配夫人,另取新欢的诗,诗意充满怨恨,两位先生皆依据的是《召南·鹊巢》首两句:“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鹊巢鸠占,这种现象自是受到人谴责的,《易林》说诗对此已经有了关注,《节》之《需》写道:“鹊巢鸠成,上下不亲。外内乖畔,子走失愿。”尚秉和先生注:“鹊巢鸠成者,言鹊营巢成,为鸠居也。”[11](p476)鹊巢为鸠所侵占,繇旨凶险,后面的繇辞是在此基础上的引申发挥。针对这首诗,《孔子诗论》有这样的解读:
第十简:《鹊巢》之归,……曷?[4](p139)
第十一简:《鹊巢》之归,则离者……[4](p141)
第十三简:《鹊巢》出以百两,不亦又离乎?[4](p142)
在这三支简中,前两只简标示的一个重要字眼是归,归指的是女子出嫁。第十三简中的“不亦又离乎”,离指离开父母家而嫁入夫家之义。《孔子诗论》的记载均很简约,没有明显的情感标示,较为平正、公允,《易林》对鹊巢鸠占现象的揭示和批判,则是《孔子诗论》未曾提及的。
《易林》说诗建立在用诗基础上,《诗经》篇目以动物物象起兴者如《关雎》、《黄鸟》、《鹊巢》等往往受到林辞编撰的青睐,《易林》化用的目的是将《诗》繇辞化,借用诗之物象和事象,取其象征含义而便于占筮;《孔子诗论》是专门的解诗之作,是孔子向弟子传授的诗学理念,承载的是孔子之儒家思想,二者在侧重点上有所区别。除了上述以动物名篇的篇目外,《易林》说诗和《孔子诗论》的分际在其他篇目中也是同样存在的。
《东方未明》一诗的主旨,《毛诗序》写道:“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毛诗是从讽刺角度对诗歌予以的阐发。今存鲁诗遗说见于《说苑·奉使篇》:“文侯於是遣仓唐赐太子衣一袭,敕仓唐以鸡鸣时至。太子发籄视之,尽颠倒……诗曰:东方未明……。遂西至谒文侯,大喜。”[7](p297-298)鲁诗提及该诗属于称引,未对诗旨予以揭示,但态度是正面肯定的。《易林》说诗与毛诗异,态度上与鲁诗同,然具体所指较之有很大差异,更显详尽,《同人》之《中孚》曰:“衣裳颠倒,为王来呼。成就东周,邦国大休。”繇辞以颠倒衣裳起兴发端,标示的是吉利之象。《升》之《鼎》也写道:“衣裳颠倒,为王来呼。成就东周,封受大侯。”末两句揭示的亦是吉利之象。尚秉和先生于《同人》之《中孚》下注曰:“毛诗叙谓朝廷兴居无节,焦意似指太公佐周,与毛异。”[11](p112)尚先生的判断是从《易林》提及的“成就东周”而得,颇有参考价值。《东方未明》的主旨,历来有不同的见解,《孔子诗论》曰:“《东方未明》,有利词。”利词指的是“锋利尖锐的批判性言辞。”[20](p51)如此一来,《易林》说诗和《孔子诗论》就存在很大差异,《易林》化用《东方未明》始终以吉利示之,然而《孔子诗论》却是持否定态度,这也是后代解释该诗的主流意见。
《周南·汉广》,《易林》有这样的文字:
萃之渐:乔木无息,汉女难得。橘柚请佩,反手难悔。[3](p1683)
颐之既济:黄昏白日,照我四国,元首昭明,民赖恩福。汉有游女,人不可得。[3](p1044)
噬嗑之困:二女宝珠,误郑大夫。交父无礼,自为作笑。[3](p819)
难悔,汲古阁本作离汝。《易林》中的汉女、游女代指一位难以接近的姑娘,君父无礼等句是对追求者的漫画式讽刺。《易林》中的游女本事,见于韩诗。郭璞《江赋》曰“感交甫之丧珮”,李善注引《韩诗内传》写道:“交甫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珮。’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趋然而去十余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不见。”[21]《易林》化用入占辞,叙写的是男子追求汉水游女,并乞请游女之珮,却终究求而不得之情景。《孔子诗论》对《汉广》一诗的评析是这样的:
第十简:《汉广》之智,……曷?[4](p139)
第十一简:《汉广》之智,则智(知)不可得也。[4](p141)
第十三简:(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恒乎?[4](p142)
《汉广》,孔子评析为“不可得”的用语也见于林辞《颐》之《既济》,不同的是孔子认为知道不可得,不攻不可能是一种智慧,而《易林》说诗却借用《韩诗内传》的记载,将其和郑大夫与汉水神女相系,是漫画式讽刺。
《易林》说诗和《孔子诗论》出发点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易林》说诗往往关注诗句中物象或事象,取其象征含义予以编撰,而《孔子诗论》的重点则往往在于对诗歌的评介论析;《易林》用“诗”暗含对诗歌的理解和态度,情感与吉凶相系,指向性明显,《孔子诗论》则是真正的解诗,平正而公允,如《十月之交》,林辞《萃》之《蒙》曰:“家伯为政,病我下土。”《渐》之《井》曰:“家伯妄施,乱其五官。”引诗取阴盛犯阳的象征义;相比之下,《孔子诗论》曰:“《十月》,善諀言”,諀,《尔雅》“訾也”,指善于揭露和批判的特征,是对诗歌整体风格的客观说解。《孔子诗论》解诗是简约的,情感指向偏于中性,《易林》说诗则丰富多彩,显得更为明晰,如《孔子诗论》“《北风》,不绝人之怨”,《易林》则分见于《晋》之《否》,《否》之《损》,前者“北风寒凉,忧思不乐”言哀悲伤心,后者“北风牵手,相从笑语”言燕乐以喜,合观之是《易林》对《北风》的完整解读。
三、结语
《易林》是西汉末年成书的文献,它的说诗和用《诗》捆绑在一起,《诗》是一门被借用入繇辞的工具。《孔子诗论》是先秦时期孔门诗教的教学文本,具有完整的诗学体系和特征,如《孔子诗论》在第一简最后写道:“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4](p123)诗以言志,这一主张正是华夏诗学发展的主脉。落实到具体篇目,《易林》说诗和《孔子诗论》既有会通之处,也有相异点存在,从上博简《孔子诗论》解诗到《易林》说诗,彰显的是先秦至西汉末年诗学发展的演变走势。
参考文献:
[1] 阮元校刻,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张涛. 列女传译注[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17.
[3] 徐传武,胡真. 易林汇校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 马承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 朱熹. 诗集传[M]. 北京:中国书店,1994.
[6] 司马迁. 史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 向宗鲁. 说苑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8] 许维遹. 韩诗外传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0.30.
[9] 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7.29.
[11] 尚秉和. 焦氏易林注[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12] 廖名春. 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札记[A]. 朱渊清,廖名春.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C].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264.
[13] 黄怀信. 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4.
[14]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
[15] 刘银昌. 焦氏易林之诗学探微[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11.
[16]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64.
[17] 陈桐生. 孔子诗论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18] 王利器. 新语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6.30.
[19] 张启成. 诗经研究史论稿[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59.
[20] 徐正英. 上博简孔子诗论研究[R]. 中山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6.
[21] 萧统编,李善注. 文选[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89-190.
收稿日期:2015-09-18;修回日期:2016-01-25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7批一等资助科研项目:“汉代易学类诗辞研究”(2015M570423);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两汉占丹辞研究”(2016T0438)
作者简介:田胜利(1982-),男,湖南常德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E-mail:wyy860316@126.com。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7X(2016)03-0113-06
Thorough Comprehension and New Change of the Song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Vision of Section ——Comparison betweenJiaoShiyilinandConfuciusPoetics
TIAN Shengli
( School of Chinese Liter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
Abstract:JiaoShiyilin is a miniature of poetic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years of Han-Dynasty, Confucius Poetics is a new document literature related to opinions on songs of Kong, which stands for the view of explaining song-made method of the Pre-Qin period. Comparing JiaoShiyilin to Confucius Poetics we can find the consistency. Similarity in some cas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poetry, showing the integration and consistency of JiaoShiyilin and Confucius Poetics. Confucius Poetics is brief and evenhanded, and JiaoShiyilin is specific and flexible . There exist divergences at the same time, which means a new change of poetics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years of Han-Dynasty.
Key words:poetics; Confucius Poetics; JiaoShiyilin; 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