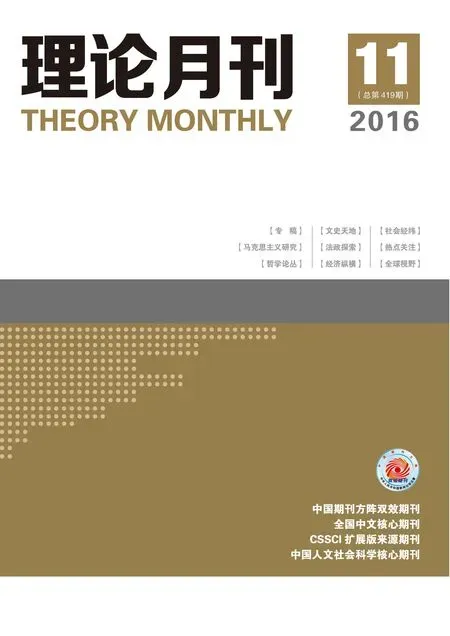“怨”的兵学解诠与文史演绎
2016-03-06袁劲
□袁劲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怨”的兵学解诠与文史演绎
□袁劲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情感体验,“怨”在轴心期便受到先秦诸子的广泛关注。相较于儒道墨法诸家聚焦治国与修身层面的经典言说,兵家在胜败考量和攻守研习之际另辟蹊径,有效拓展了“怨”的认知维度。通观以《武经七书》《孙膑兵法》为代表的兵学元典,可知兵家论“怨”不惟佐证了古文字形“从令从心”解诠的历史语境,还创造性地标举出“兴怨”战术,从而揭橥“怨”所内涵的自然情感与观念建构之双重性。在兵家视域中,“怨”本是左右战局的诸种要素之一,而《史记》《战国策》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史作品的同题演绎,却强化了“怨”在胜败因果及叙事效果中的作用。这种“版本”间的差异亦折射出文史作品对兵家论“怨”思想的接续与转换。
兵家;怨;文史演绎
相较于儒道墨法诸家聚焦治国与修身层面的经典言说,兵家放眼国与国之间的武力攻守,视野宏大却也不失对个体心理的关注。正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所言:“精神要素与战争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决不能从战争艺术理论中省略。”[1](P137)这种“无形战场上的心理交锋”内涵丰富,涉及双方的感觉、知觉、潜意识、情感、意志、需要、性情等诸多精神要素。[2]不过稍显遗憾的是,现有古典兵学研究多围绕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军队建制、军事地理以及日常演练等论题展开,其中涉及精神要素者亦多囿于《孙子兵法》一书中的心理战思想解读,①如丁雪枫将《孙子兵法》的心理战思想归纳为:战略震慑与“死地”战术、凝聚军心与夺敌士气的二元结构,以及倡导“爱、赏、教”与警戒“三患”“五危”(《〈孙子兵法〉心理战思想评析》载《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在此基础上,吕正韬还比较了《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心理战思想(《〈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心理战思想比析及启示》,《理论月刊》2007年第10期)。即便是少数通观先秦兵书的综合研究,也只是大致勾勒出军事心理学思想的基本框架,而尚未深入特定的心理现象来具体分析。②如史志华《先秦兵家军事激励思想探析》一文指出关怀和信任可用于情感激励(《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1年第1期)。解文超在博士论文《先秦兵书研究》中综合考察《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尉缭子》的心理学思想,由此提炼出“诡道”、“用间”、“励士”等战术运用以及对恐惧畏战等不良心理的调控与化解。其实,与“智信仁勇严”(《孙子·计》)代表的将领理想人格以及“怒”、“惧”、“疑”等战场心理学关键词一样,“怨”亦是兵家武库中尤其值得关注的精神要素。大致说来,在兵家论“怨”视域中,战争多起于敌我上下的“争私结怨”以致“怨结难起”(《尉缭子·攻权》),而交战双方常是“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黄石公三略·上略》)。那么,于治军而言,便须留意君、将、兵、民之“和”以求“三军无怨”(《孙子·谋攻》陈皞注)和“令行而无怨”(《黄石公三略·下略》),而绝不可“使怨治怨”(《黄石公三略·下略》)或因赏罚不明以致兵卒“怨而难使”(《孙子·地形》梅尧臣注);至于攻敌,则更要利用对方“百姓怨怒”(《吴子·料敌》)或“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吴子·论将》)式的可乘之机。“怨”之一字,实已关涉选将、励兵、施令、赏罚、行间等多个环节,其用亦可谓大矣。
1 “令”与“心”:“跪跽受命”说的兵学解诠
“怨”之于“兵”因何而生?若要回答这一追问,便需从“怨”的字义解诠入手。“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把语词及其对象联结起来的纽带,我们就必须追溯到语词的起源,我们必须从衍生词追溯到根词,必须去发现词根,发现每个词的真正的和最初的形式。”[3](P155)如卡西尔所言,寻获那“真正的和最初的形式”是审视与解诠“怨”字的基础。一般认为,《说文解字》综合小篆“夕”“卩”“心”的“怨”字释读,已还原出一幅“辗转反侧”的诗意图景。不过在兵学语境中,古文“怨”字还以“令”之于“心”的压抑直指君将兵民与敌我主客之间力的紧张,从而为字义解诠提供了另一种历史语境的支撑。
历代对于“怨”字的解释,以《说文解字》中“怨,恚也,从心夗声”[4](P221)的形声说为主。不过,段玉裁、朱骏声、王筠等学者已注意到“怨”字“古文从令从心”与小篆字体之间的裂隙,故有“此篆体盖有误”[5](P511)式的推测和“古文从心从令,未详”[6](P710)式的暂付阙如。按段玉裁的举证,“怨”字古文异体还有(《集韵》《类篇》)、(《班马字类》《韵会》引《史记·封禅书》)。朱骏声亦认为《礼记·大学》“举而不能先,命也”中的“命”或为“怨”字古文之误。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小篆与古文字体之间的悬殊差异呢?历来文字学家多持字体形变的观点。如王筠认为乃“夕字在上”,之写法亦因“卩字盖夕之上误断为死耳”。[7](P33)现代学者商承祚亦指出与《说文》所列古文写法略异,而又为之讹变。[8](P1024)不惟如此,《说文解字》中“从令从心”之古文,还可找到(《字汇补·心部》)、(《玉篇·心部》)、(《正字通·心部》)、(《集韵·愿韵》)等多种变形。“令”与“心”正是这组一词多形中多个形体皆有的构字元素,“怨”之古文“从令从心”亦可谓渊源有自。
“怨”字的形声与会意两种说解,源自关注点的不同。如果说“从心夗声”的形声说侧重以“转卧”时的形体弯曲来示意“辗转反侧”式的心生委屈,[9]那么“从令从心”的要义便蕴藏于“令”字的进一步拆解之中。许慎释“令”为“发号也,从亼卩”,[4](P187)并认为参与构字的“亼”乃“三合也,从人一,象三合之形”,[4](P108)而象征“瑞信”的“卩”亦“象相合之形”。[4](P186-187)这一串解说中的“发号”、“集合”、“瑞信”三要素皆带有浓郁的军事色彩。由《说文解字》中的小篆追溯至甲骨文,现代学者多将“卩”视作人形而非许慎所言之“瑞信”,同时还在落实“亼”所指之物究竟为何的推进中提出不同见解:李孝定先生认为“亼”像倒“口”,“下从卩乃一人跽而受命,上口发号者也”;方述鑫先生指出“上面像省去铃舌的铃形,下面像执铎施令的人形,是一个会意字,乃人的动作加上人为之事以表达人的意志”;洪家义先生则推测“亼”乃“舍”之省文可表庐舍,即“像人危坐于屋中,会意发号施令。大概当时君长发号施令时是危坐于屋中的”。[10](P365)综合上述三说不难看出,“令”之会意情境大致为上级发令与下级受命的合二为一,只不过“亼”之具像与“卩”在施受双方中的归属还存有争议。诸说之中,为后人征引较多的是徐中舒先生的“古人振铎以发号令,从卩乃以跪跽之人表受命之意”。[11](P1000)“跪跽受命”说兼采方述鑫的“亼”字推测和李孝定的“卩”字释读,修正并补充了许慎对“令”字的拆解。结合“怨”字而言,“跪跽受命”说的优长还在于,既保留了《说文》释“令”的军事色彩,又着眼于“跪跽”者的屈服与压抑,而后者正与“从令从心”之古文字形密切相关。黄锡全先生曾指出,《侯马盟书》之“惌”与《说文》古文及三体石经《无逸》之,皆从冖而小异。[12](P282)此“冖”与“亼”皆象征自上而下的压抑与束缚,可视作“令”之于“心”的效果,其理据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言:“怨之言冤也,谓有屈在中不得申也。凡抱屈不申则怨。”[13](P55)
“从令从心”以表“怨”的造字理据,还能在兵家元典的相关论述中寻获佐证。几乎所有的兵书都会强调“令”的重要性,如《孙子·军争》点明“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黄石公三略》强调“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孙膑兵法·将失》亦提醒“令不行,众不壹”和“令数变,众偷”可导致失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还于虚实之中辨明“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六韬·龙韬》甚至提出常备“伏旗鼓三人”以“谬号令”;而《吴子·治兵》更是直接反问:“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军纪严明,需有保障,故《武经七书》中屡有“不从令者诛”(《吴子·应变》),“有敢不从令者诛”(《尉缭子·将令》),“不听金鼓铃旗而动者有诛”(《尉缭子·勒卒令》)式的申诫。《尉缭子·武议》中的一则情景对话还表明,即便是违令者立下战功,也难以抵消军纪的严惩不贷:
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矣,非吾令也。”斩之。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孙子·九地》中“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之类的描述。所谓“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黄石公三略·下略》),为保证“令行而无怨”与“政行而无怨”,便需要顾及奉行者的接受心理。《孙子》所谓“令民与上同意”(《计》)、“上下同欲者胜”(《谋攻》)与《孙膑兵法》“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月战》)及“内得其民之心”(《八阵》)都将视线收回而关注人心向背。为达到“令行如留(流)”(《孙膑兵法·奇正》)的理想状态,将领常需借助“愚兵”策略与赏罚机制。《孙子·九地》要求将领“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与“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正是为了实现何氏所注“士之往来,唯将之令,如羊之从牧者”[14](P318)的效果。“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司马法·天子之义》),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可保军令畅通,但奖惩尺度的把握也不容忽视。《孙子·地形》言“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孟氏所注“唯务行恩,恩势已成,刑之必怨;唯务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14](P285)即着眼于此。可以说,作为情感的战场之“怨”正萌蘖于令行禁止的另一面。
兵家常持主将视角而主张令行禁止,又在推行之际发觉“心”之于“令”的反作用力。与其他语境相比,军旅无疑增强了“怨”的情感浓度,因为这种施令与受命情境要求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由此实现集体对个人的最大塑形。在这种意义上讲,“从令从心”也是造字者对如此这般生存境遇的一则精彩隐喻。钱钟书先生曾言:“人类最初把自己沁透了世界,把心钻进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硬变定,失掉了本来的人形,仿佛鱼化了石。”[15](P131)通行“怨”字虽没有失掉人形,但与同源字“冤”之“兔在冂下不得走”[5](P472)相参照,也可以说是部分丢失了原初的释义情景。兵学元典之于“怨”字解诠的意义,正在于为古文“从令从心”提供了“跪跽受命”隐喻的语境佐证。
2 “守气”与“攻心”:兵家论“怨”的双向展开
既然“令”之于“心”会滋生负面的“怨”,那么兵家又是如何防备与疏导的呢?这便涉及兵家理念中的“人和”诉求、君将兵民与敌我主客的通观审视,以及围绕着“气”与“心”的精神竞逐。所谓“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六韬·龙韬》)。着眼于“人和”的兵家论“怨”,一面致力于内省以消除己方“怨”之隐患,一面又不忘谋求“兴怨”而胜敌于无形。
对兵家论“怨”的考察可从《孙子》入手。明人茅元仪在《武备志》中曾言:“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此论恰切,于“怨”亦然。虽然《孙子》并未直接使用“怨”字,但十一家注解却屡屡为之呼出。可以说,是书对“和”思想的标举,对“君—将—兵”层层制驭下的情绪掌控,以及主客视角下的“守气”与“攻心”策略,已基本搭设起兵家论“怨”的思维框架。具体说来,《孙子·计》所列“经之五事”以“道”为先,旨在“令民与上同意”。这一总论之下还分设了《谋攻》中的君主不可“縻军”,《火攻》中的“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地形》中的主将不可致“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以及《行军》和《地形》中的将领不可使士卒“刑怨已深”[14](P285)或“怨而难使”。[14](P257)种种“不可”,皆为防备指挥者的不理智,从而尽可能地化解下级的负面抵触情绪。至于《军争》所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已被《武经七书》奉为共识,并在这一序列之末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扩展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云云。主客之“怨”皆生于“心”而形于“气”,兵家论“怨”即在“守气”与“攻心”的命题下双向展开。
“守气”寄托了于己“止怨”以求“和”的诉求。“气”是中国古典兵学的重要范畴,《孙子·军争》之夺气、治气,《孙膑兵法·延气》之激气、利气、励气、断气、延气,《吴子·论将》之气机,以及《司马法·严位》“凡战,以力久,以气胜”等皆可为证。所谓“守气”其实包括守持“和气”,化解“怨气”,而最终形成战斗之“锐气”。前述《孙子》已分别强调君主、将领与士卒之间的凝聚力,《孙膑兵法》又将其整合为克敌制胜的战斗力。是书《兵情》举弩矢之法为例,纳“矢,卒也。弩,将也。发,主也”为一体,以喻上下和同方可胜敌。按照张震泽先生的注解,孙膑所谓“弩之中彀,合于四”涵盖“矢前后轻重得,一也;弩棅正,二也;两洋送矢壹,三也;发者是,四也。四者是以弩射比喻治卒得法,上下和同,可以胜敌有功”[16](P87)。如同弩射中彀一般,兵家认为只有上下“止怨”一心才能凝聚成和同之力,而“弩之中彀,合于四”之喻不惟关注系统性,还凸显了由“和气”而生“锐气”的转换。有鉴于此,《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等皆点明将士同甘共苦的功效。如《孙子·地形》号召“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又如《六韬·龙韬》所论:“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白刃始合,士争先赴。”两军交锋,击鼓进军而鸣金收兵,这里的“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与前述“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孙子·九地》)对比鲜明。士卒斗志由低沉而至高涨,其间玄机正在凝聚“锐气”:“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攻心”彰显了对敌“兴怨”的智慧。“凡战,三军一人,胜”(《司马法·严位》),此道理于攻守双方皆然。以《吴子》为例,战前料敌以定迎击抑或暂避时,如果对方“百姓怨怒,祅祥数起,上不能止”便可“不卜而与之战”,倘若其“上爱其下,惠施流布”则应“不占而避之”(《料敌》);临阵交锋时,将领需要捕捉乃至创造敌方“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的战机,而所谓“事机”之要义亦在“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论将》)。离间“兴怨”可破坏对方的上下一心,从而实现彼消此长,故《孙子》钻研“用间”,《孙膑兵法·篡卒》点明“不用间,不胜”,《黄石公三略·上略》强调“敌睦携之”,《六韬·文韬》更是断言“收其内,间其外,才臣外相,敌国内侵,国鲜不亡”。如果说离间着眼于破坏敌方团结,那么,煽动对敌之怨恨同样是兵行杀戮的有效举措。《逸周书·大明武解》总结的“大武十艺”便将“兴怨”与“间书”并列。对于“兴怨”,潘振云注解为“兴举敌国怨望之人,如吴用伍员是也”,[17](P137)朱右曾则举例“如晋侯退舍,致曲于楚,使众怨之”。[18](P19)前者注重利用怨怒以提升战斗力,此点与《孙子·作战》“故杀敌者,怒也”和《六韬·犬韬》“有死将之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聚为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心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等论述相通。朱右曾的“致曲”说将不义归于对方,这种思维在《黄石公三略·上略》体现为“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的认识,在《尉缭子·攻权》中则凝练成“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贵以不得已;怨结难起,待之贵后”应对之策。“不得已”与“贵后”乃是为了将“争私忿”而引起“众怨”的不义之罪归于对方[19](P856)。所谓“杀戮,所以除怨也”(《郭店楚简·尊德义》),在兵家的诠释与改造下,“怨”便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情感现象,而是彰显出作为观念的建构性——无论是寻隙煽动,还是诱导归咎,皆可使本出于自然的“怨”从无到有、积少成多、由此及彼,而最终为我所用。兵家触动怨心、集聚怨气的心理攻势,展现了“怨”所内涵的自然情感与观念建构之双重性。这种探索与发现为各领域的竞争者所沿用,遂演化为一幕幕瓦解对方、舆论动员与夺取正义的攻心战。
兵家常以兵器论兵情,前述《孙膑兵法·兵情》即以弩矢之法类比和同胜敌。于文本层面的兵器譬喻之外,兵书中还闪烁着思维层面矛盾之喻的光芒,其对“止怨”与“兴怨”的论说便兼备主客视角着眼攻防两端。诸如《六韬·龙韬》对外设立“游士”“以为间谍”,向内又安排“通材”来“消患解结”之例表明,兵家在“止怨”尤其是“兴怨”的同时还一直警惕着对方反施于我的可能。由此不妨说,围绕着“守气”与“攻心”双向展开的兵家论“怨”,已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隐忧转化为自省后的全备。面对“怨”这一负面情绪,先秦诸子在“止怨”的同时还注重引导与利用。与儒家的“诗可以怨”命题相似,兵家标举“兴怨”战术亦彰显了在被动“止怨”之外另辟蹊径的智慧。
3 提炼因果与渲染效果:兵家论“怨”的文史演绎
兵家较早揭示了“怨”所内涵的自然情感与观念建构之双重性,不过“怨”之于胜败存亡作用的进一步显现,还要依靠文史作品的踵事增华。由前文不难看出,尽管“止怨”是治军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环节,“兴怨”亦是出奇制胜的有效策略,但“怨”还只是左右战局的诸种要素之一,并不具有决定性。对读田单坚守即墨、孙膑庞涓马陵之战以及伍员借兵攻楚等战例分析与文史叙述的两类版本,可发现“怨”在后者中的因果性与效果性明显增强。
田单坚守即墨是兵家津津乐道的经典战例。《六韬·虎韬》提醒攻伐者:“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冢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则天下和服。”这种自攻方而言的分化策略显然汲取了即墨之战的经验,将矛头直指敌方领袖,通过安抚士卒和民众来缩小对立面。“冢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等申诫,意在尽量减小对方同仇敌忾凝心聚力的可能性。当然,兵家总结即墨之战的经验还是多从守方立论。《孙子·作战》有言:“故杀敌者,怒也。”杜牧为之注解:“万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势使然也。田单守即墨,使燕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坟墓之类是也。”[14](P46)何氏所注也举此例,与杜牧皆强调归咎于敌而“兴怨”的战术价值。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这一战例还被总结为“田单托神怪而破燕”:“田单为燕所围,单命一人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诡道,天官时日亦犹此也。”那么,历史上的田单坚守即墨一役又是如何记载的呢?据《史记·田单列传》所载,司马迁眼中的即墨防御战分为四个阶段:先是田单施行反间计,使敌将骑劫取代乐毅;又利用燕兵的忿怒情绪,托神师之口诱使其劓降者,并派反间诓骗燕军挖掘城外的齐人坟墓;当齐国军民望见城外坟墓被挖后,本方士气已由望见燕劓降者时的“皆怒,坚守,唯恐见得”积聚至“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与此同时,田单还故意示弱于敌懈其心气,并最终以火牛计出奇制胜。与杜何二注的史实节选和《问对》凸显“诡道”相较,《史记》更为全面地呈现了即墨之战的进程,并反复申说“离间”与“兴怨”。“诡道”固然重要,可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之《运筹纲目》提要所云“兵机万变,转瞬势移,田单火牛,再用则败,是固不可以成法拘耳”,[20](P844)从更普遍意义上讲,即墨之战的借鉴价值在于“兴怨”的蓄势而非“托神怪”的突击。与兵家聚焦技战术的运用不同,史家在通观比较之中强化了“怨”的作用。对于田单赢取即墨之战的关键,《战国策·齐策》还借鲁仲子之口评述道:“将军之在即墨,坐而织蒉,立则丈插,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庙亡矣,魂魄丧矣,归于何党矣!’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闻若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在此例中,史家显然提升了精神要素“怨”在战争胜败中的权重。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兵家的经典战例分析与史家的大事记常有吻合之处。兵书论及的战例(如《孙膑兵法》之《擒庞涓》、《吴子》之《图国》、《六韬》之《发启》等等)再加上后世注家的援引与诠释,与《史记》《战国策》《吴越春秋》等史书形成了多重互文关系。一方面,诸如《史记》中的《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等记载为兵书中的理论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战例补充和富有历史眼光的评述;另一方面,史家还从人与事的参稽比照中总结出诸多规律与镜鉴,如《伍子胥列传》中“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的认识和《战国策·中山策》中因“怨”致战而亡国的警示。“怨”的重要性在史书的战争评述中逐渐显现,这一转变体现在武经与史书同题演绎的不同侧重。比如《孙子》多言战法而不谈战例,而《史记·伍子胥列传》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却有孙武建议吴王利用“唐蔡怨之”伐楚而大获成功的记载。又如,《孙膑兵法·擒庞涓》提到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示之疑”“示之败”而击溃魏军,俘获庞涓。《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则称孙膑利用“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退兵减灶,并于马陵伏击庞涓,逼其自刎而俘虏魏太子申。《战国策·魏策》还在马陵之战齐军杀太子申后有一补笔,记录魏王的反应:“夫齐,寡人之仇也,怨之至死也不忘。”在史家看来,攻伐杀戮往往因“怨”而生且极易冤冤相报。《战国策·中山策》载中山君飨都士而不及司马子期,后者怒走入楚,说楚王兴兵而灭中山。中山君“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之喟叹也寄托了史家的褒贬。所谓“怨毒”伤人害己,司马迁注意到伍子胥率吴入郢而鞭尸平王,实乃报父仇“怨望”所致,后来吴太宰嚭正是利用“怨望恐为深祸”的口实离间了吴王与伍子胥的关系。由是之故,在《伍子胥列传》篇末,太史公还留有“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的感慨以为镜鉴。
由秉笔直书而入文学演绎,“怨”更多地承担起渲染叙事效果的作用。“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文心雕龙·程器》)。于文人墨客而言,兵书中的思想与文辞皆可借鉴。故谈恺《孙子集注序》有言:“今观诸家所注,或本隐以之显,或由粗而识精,或援史而证之以事,或因言而实之以人,于是《孙子》之微词奥义彰明矣。故曰《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抛开奇正、虚实等文武相通的技法不谈,战争叙事及其牵涉的人情物理已成为小说家的题材武库,并孕育出中国古典战争小说的一大流派。《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古代战争经典小说在情感取向、人物塑造和战争描写等方面,对兵家思想成功地进行了艺术化的演绎。[21]以《三国演义》①毛宗岗《三国演义》三十回评曰;“三国一书,直可作‘武经七篇’读。”又,杨义称《三国演义》为“审美的兵书”,见《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对“怨”的讲述为例,若说吕布“听妻妾言,不听将计”结怨部下与张飞复仇心切而为部将所杀等情节,还尚未脱离兵书倡导“和以止怨”的思想且带有以史为鉴的色彩,那么,王司徒巧设连环计、曹操借仓官之头以解士卒缺粮之怨、周瑜打黄盖之苦肉计以及吴魏两国在关羽之死上的互相“归怨”,便多半是为了情节的跌宕起伏。至于《水浒传》中的林冲、阮氏三雄、石秀等“怨毒”之人,以及因“怨”而火烧草料场、火并梁山泊、血溅鸳鸯楼等情节更是“杀戮,所以除怨也”的精彩演绎。在《水浒传》第十八回“林冲水寨大并火晁盖梁山小夺泊”回首,金圣叹援引司马迁“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的评论:“当林冲弭首庑下,坐第四,志岂能须臾忘王伦耶?徒以势孤援绝,惧事不成,为世僇笑,故隐忍而止……夫自雪天三限以至今日,林冲渴刀已久与王伦颈血相吸,虽无吴用之舌,又岂遂得不杀哉?”[22](P383)以此为例不难看出,小说情节蓄势(“晁盖梁山小夺泊”)与人物(林冲)之“怨”的郁积常常保持同步,而后者的爆发正是前者张弛起伏的关键。
金圣叹曾言:“此回(第十八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22](P382)文史演绎中对“怨”的提炼与渲染,除去以史为鉴、以文运事及因文生事诸因外,还会打上文史家个人的情感烙印,而兵书中种种战略与战术思想,也正是借助文史演绎才进一步贴近普通的读者。与兵家论“怨”相较,以《史记》《战国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文史演绎,强化了“怨”在胜败因果及叙事效果中的作用。这种“版本”间的差异折射出文史作品对兵家论“怨”思想的接续与转换,而“怨”所内涵的自然情感与观念建构之双重性亦可谓萌蘖于兵书而绽放于文史演绎之中。
[1]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张蕾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2]解文超.先秦兵书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5.
[3]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武汉:武汉古籍书店,1983.
[7]王筠.说文句读(三)[M].北京:北京市古籍书店,1983.
[8]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古文字诂林(八)[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9]袁劲.“诗可以怨”梳理:字义根柢、阐释分歧与方法启思[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
[10]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1]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12]黄锡全.汗简注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13]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中[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14]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5]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6]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8]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9]刘寅.武经七书直解//中国兵书集成(11)[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2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1]陈颖.中国古代战争经典小说的兵学意义[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5,(2).
[22]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
责任编辑 文嵘
10.14180/j.cnki.1004-0544.2016.11.016
I206.2
A
1004-0544(2016)11-0089-0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15111010201)。
袁劲(1989—),男,山东枣庄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