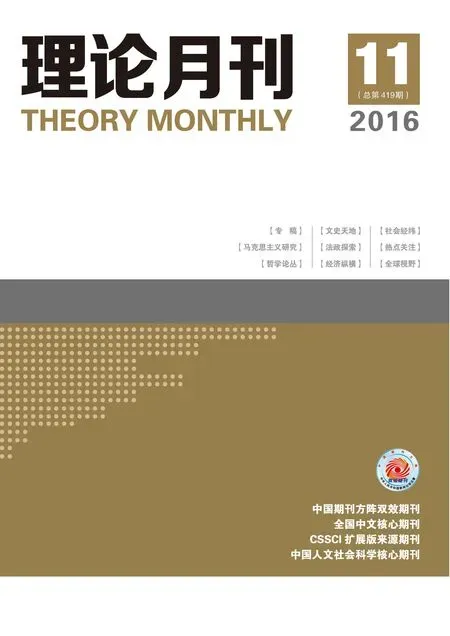文化的返璞归真
——谈废名小说的语言艺术
2016-03-06陈淑梅
□陈淑梅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冈 438000)
文化的返璞归真
——谈废名小说的语言艺术
□陈淑梅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冈 438000)
文学小说中语言的返璞归真作为一种贯穿于中国文学始终的表现形式,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研究文学小说中返璞归真的语言,一方面可以透视着文学小说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文学作品折射出来的文化特征。本文对废名小说中的语言艺术进行分析,以此来透视废名小说中文化的返璞归真。文章分四部分来讨论:第一,返璞归真与简朴自然;第二,返璞归真与原生态方言;第三,返璞归真与乡土情结;第四,返璞归真与禅意天成。
返璞归真;废名小说;语言艺术;原生态方言;文化特征
“返璞归真”是文学的生命,也是文学语言的生命。同时还是作家语言风格的显著标志之一。废名是中国现代第一个田园派小说作家,其小说语言朴质平淡,具有返璞归真的田园风格。他的这种语言风格不但美,而且充满着禅意,为文学铺垫了深厚的文化底色。
1 返璞归真与简朴自然
废名被称为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创造达到了极高的成就,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语言表达的路径——返璞归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作品中用简朴自然的语言。
1.1 简练的对话
废名小说语言通俗简练,尤其是对话中口语化。例如:
(1)阿毛心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想,只晓得她是病。
“阿毛,不说话一睡就睡着了。”
王老大就闭了眼睛去睡。但还要一句——
“要什么东西吃明天我上街去买。”
“桃子好吃”(《桃园》)。[1]
(2)“我姥姥叫我今天不上学。”
“小姑娘,我看你也搽了点儿粉,打扮得很好。”
远望青山一座,近瞧姊妹两个,不容分说——嘴巴两个。
“你这唱的是什么歌儿呢?”
“谜儿,我姥姥告诉我的,——你瞧”(《莫须有先生传》)。[2]
(3)“七月初八那一日,我大早起来望鸦鹊,果然有一只集在桑树……”
“羽毛蓬乱些不呢?”
“就是看这哩。倒不见得。”
“银姐!……”
“乍么?”
“我——我们两个咂嘴…”
“呸!下流!”
我差到没有地方躲藏了(《初恋》)。[3]
例(1)通过桃园主人王老大和他十三岁的生着病的女儿阿毛的平实的对话,来描述人物的心理、感觉、情状;例(2)通过儿童率真的对话,可以解读出废名独特的儿童观;例(3)选自《初恋》,这篇小说呈现的是两位长者追述初恋的故事,自然的对话读来令人回味无穷。让人们体验到人类虽然在不断地变化,但永远不变的是那些原初的情感。总的说来,这些对话十分简洁、自然,就是生活中原生态的语言,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但又不乏深意,这是本真性的生活体现,它不承载更多的理念或历史意向。而是质朴和淡泊,这正是它返璞归真的可贵之处。还如《去乡》可作范例:
(4)“萍姑娘!——回家?——几时来的?月半?——啊,中元上坟。”有谁在问她似的,她回向舱里,咕嗫着。
“一个人吗?”我问。
“不,我的弟弟。”
“上船好久了罢?”
“口茶的工夫。”[4]
这些对话冲口而出,完全是生活化了的口语,没有一点渲染和铺垫,极其简省。
1.2 通俗的比喻
废名的小说中使用了很多鲜活的比喻。使语言生动有趣、形象而富有感染力。例如:
(5)我慢慢地伸手接着,银姐的手缓缓地离开我,那手腕简直同塘里挖起来的嫩藕一般(《初恋》)。[5]
将银姐的手比喻为“嫩藕”,在“我”看来似乎是最好的比拟了。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交接过程,“我”却用“慢慢”和“缓缓”的特写镜头将这个过程无限放慢,细细体会其中的美好感觉,就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能造成一种鲜明的具象化的效果。还如:
(6)姑娘呵,不怪我好哭,高秋冷月,那里有这样一声笛呢?——你的清脆的咳嗽!(《去乡》)。[6]
(7)洗衣在她们是一种游戏,好像久在樊笼,突然飞进树林的雀子(《浣衣母》)。[7]
例(6)将姑娘清脆的咳嗽比喻成笛声,作者借助于听觉认知的相似性催生了一个喻体“笛声”,新颖别致。例(7)将姑娘们到河里洗衣服比喻为“好像久在樊笼,突然飞进树林的雀子”,这些清丽脱俗的比喻,形象生动。使人感到小说中那种圣洁而沉重的人性美,又能使文章的叙事环节延宕推进。
1.3 平淡而有奇
废名小说中的语言看似一个个平淡无奇的词语,排列组合在一起却产生一种特别的韵味和意蕴。平淡而有奇,简练并不简单。例如:
(8)金喜的磕睡飞跑了,盛气的窜到灶门口(《火神庙的和尚》)。[8]
(9)本来低洼的泥地,潮湿得被盐卤了一般(《半年》)。[9]
(10)二十年前,正是这样一个晚上,还添了一轮月亮,不过没有小宝(《火神庙的和尚》)。[10]
(11)现在这一座村庄,几十步之外,望见白垛青墙,三面是大树包围,树叶子那么一层一层的绿,疑心有无限的故事藏在里面,露出来的高枝,更如对了鹞鹰的脚爪,阴森得攫人。瓦,墨一般酌黑,仰对碧蓝深空(《桥·史家庄》)。[11]
(12)太阳已经下了山,是我牧童歌牛背的时候了(《小五放牛》)。[12]
以上例句中的词,在汉语中是很常见的词语,但在废名的笔下却超尘脱俗、极富神韵。给人留下隽永的记忆和韵味,创出了一种新奇的语言表达效果。在《菱荡》中[13](1988)一个个平淡词语的组合,能让读者感受到人物此时的心境和情景相映成趣的意象,自然妥帖令人赞叹:“菱叶遮蔽了水面,约半荡,余则是白水。太阳当顶时,林茂无鸟声,过路人不见水的过去。如果是熟客,绕到进口的地方进去玩,一眼要上下闪,天与水。停了脚,水里唧唧响,———水仿佛是这一个一个的声音填的!偏头,或者看见一人钓鱼,钓鱼的只看他的一根线。一声不响的你又走出来了。好比是进城去,到了街上你还是菱荡的过客”。
2 返璞归真与原生态方言
“返璞归真”还表现在废名小说运用了大量的原生态方言,使他的小说极富地方文化色彩。
废名是湖北黄梅县县城人,他的作品内容大多是反映黄梅的社会世俗风貌,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因此乡音难改,他所用的语言是地道的黄梅话。正如王瑶[14](1951)所说的那样,废名“写的是湖北小乡村,地方性很强,文字也有明显的地方口语。”黄梅话属于江淮官话的黄孝片方言,具有古楚语的特征。例如:
(13)有一回陈大爷要骑我的牛玩,我却赶得牛飞跑,跌了陈大爷一跤(《小五放牛》)。[15]
(14)是呀,妇人家总要这么贤快才好(《毛儿的爸爸》)。[16]
(15)结果,在城南鸡鸣寺里打扫一间小小的一间屋子,我个人读书(《半年》)。[17]
(16)三哑叔,今天你就在我家过夜好不好呢?我上街买好东西你吃。你喝酒不呢?(《桥·落日》)。[18]
(17)洋洋湖水渐渐成了一片绿,不消说,是芦柴(《去乡》)。[19]
(16)倘若在暗淡所在,那便熨贴极了,好像暑天远行,偶然走近一株大树,阵阵凉风吹来(《半年》)。[20]
(17)就是看这哩。倒冇见得(《初恋》)。[21]
(18)这个太阳把我讨厌死了(《莫须有先生传》)。[22]
(19)巴不得月光一下照得它干!(《桃园》)。[23]
(20)赶得到那头的午饭不呢?(《去乡》)。[24]
(21)柚子与两位表兄所穿戴的,同我们弟兄又没有什么分别,在外祖母家也是一样的欢喜不过(《柚子》)。[25]
(22)“粉”者,是黄梅县的方言,是一个形容词,凡说芋,说甘薯,说栗子等物,如果淀粉成分多,便说它“粉得很”(《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之后》)。[26]
在黄梅方言里,“飞跑”是“跑得很快”的意思;“贤快”是“贤惠”的意思。“个人”是“自己”的意思。“过夜”是“吃晚饭”的意思。“熨贴”是“舒服”的意思。“冇见得”是形容词短语,在黄梅方言中可以表示多种意思。在此句中表示“还可以,勉强过得去”的意思;“这个太阳把我讨厌死了”是表示“这个太阳让我讨厌死了”的意思。“巴不得月光一下照得它干!”是个处置句式,是“巴不得月光把它一下子照干!”;“赶得到那头的午饭不呢?”是疑问句式,翻译成普通话是“赶得上那边的午饭吗?”黄梅方言的疑问句都在句末加上一个“不”表示正反问;“欢喜不过”是“很喜欢”的意思,“不过”用在表示心理动词后边做补语,表示词义程度的加深,相当于普通话的“很”。陈淑梅认为:[27](2007)“用‘不过’表示‘很’的意思,这是江淮官话黄孝片用得较为普遍的语法特点。”“粉”形容芋、甘薯、栗子等物淀粉成分多,这种说法在江淮官话黄孝片也普遍存在。
用故乡的语言,写故乡的人和事,表现故乡的文化精神,这在很多作家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会带来一方语言文化,选择了故乡原生态的方言就选择了故乡的淳朴,就选择了故乡的文化。废名小说原生态语言是对美学追求,对传统的叛逆,凸显了废名小说语言独特的文化内涵,从这种与自然交融的语言中,可以看出从城市化的人为的复杂符号中逃脱,转向质朴的原生态的自然,负载着某种更加深层的文化根源。这给同时代与当代小说创作者极大的启发和深远的影响,给生活在当今喧嚣社会中的人们一个净化心灵的艺术空间。
3 返璞归真与乡土情结
“返璞归真”还表现在废名作品的语言负载着浓厚的乡土情结。汪曾祺[28](1998)曾说:“一个作家对传统文化和某一特定地区的文化了解得愈深切,他的语言便愈有特点。”一般而言,童年生活对一个人后天的性格、爱好、价值取向都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种影响会体现在创作的风格或特点上,特别是对于像废名这样具有乡土情结的作家来说,这种影响更加深远。废名在故乡黄梅生活了17年,外出读书和谋生期间又断断续续住在家里。他的小说语言返璞归真源于他沉醉于童年时故乡的美好去编织梦的理想世界,寻找心灵得以归宿的精神殿堂和艺术表现方式。
刘宝昌[29](2012)说:“废名小说的背景,是典型的黄梅风景,那些已为读者所广为熟悉,宛若废名小说经典意象的小溪河、破庙、竹林、桃园、佛塔等,绝不会被误读为江浙小镇或北方的乡村,已经成为废名乡土小说专用的‘符号’”。废名迷恋一种安于自然、悠闲恬适和宁静淡远的乡土田园之中,写下了一曲曲乡村牧歌,最突出的表现是黄梅的语言符号深深濡染着他的乡情,读来让人们能记住乡音,留住乡愁。例如:
(23)一到八月,枣渐惭的熟了。树顶的顶上,夜人不服及,夜半大风,一阵阵落地声响,我枕在枕头上喜欢极了(《枣》)。[30]
(24)这时洗衣的渐渐的都回去了。小林在那河边站了一会,忽然他在桥上了,一两响捣衣的声响轻轻地送他到对岸坝上树林里去了(《桥·金银花》)。[31]
(25)大家一齐送出门,好些个孩子跑拢来看,从坂里朝门口走是一个放牛的、骑在牛上(《落日》)。[32]
(26)好一匹黄牛,它的背上集着一只八哥儿(《金银花》)。[33]
渐渐成熟的枣儿、一簇一簇的竹林、骑在牛上的小孩、集在黄牛上的八哥儿都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能唤起我们儿时的记忆。
废名的乡土情结还表现在他追求一种真实而淳朴的人性自然。这种人性自然不外乎率直、热情、诚实、朴素、善良,而最重要的是要求顺乎天然良知、仁厚等一类品质的真实,要求一种人类的“童心”。在他的小说中将故乡的人物性情之美与田园山水之美写得相得益彰、浑然天成。陈边城[34](2009)“《桥》中的史家庄,和平宁静,男耕女织,知足长乐,人性淳美。程小林、史琴子与细竹之间没有什么情愁打斗之类,一切都是那么和谐、平静、美丽、自然。三个人看山赏塔,采花折柳,各个一颗返朴归真恬淡自然的心。小说以精细而富有风情之笔,给史家庄染上了层层古朴、优雅,并有几分神秘的色彩,宛然一片桃园仙境,化为乐土。其中的农家碧玉、歌呤欢笑、斯文儒雅、怡情养性、澄心净虑,具有不计利害得失,吐纳万物的情怀。在他们的身上,真正洋溢出一派田园牧歌式的青春气息。”在《菱荡》中[35](1988),“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与卞之琳[36](2000)《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是何其相似!
再看下面几段话:
(27)王老大只有一个女孩儿,一十三岁,病了差不多半个月了(《桃园》)。[37]
(28)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竹林的故事》)。[38]
(29)陶家村在菱荡圩的坝上,离城不过半里,下坝过桥,走一个沙洲,到城西门(《菱荡》)。[39]
在《初恋》的结尾有一段明白晓畅的话,极显废名幼年的生活环境和自己初恋的情结:
(30)这已经是十年的间隔了:我结婚后第一次回乡,会见的祖母,只有设在堂屋里的灵位;“奶奶病愈勿”,乃是家人对于千里外的爱孙的瞒词。妻告诉我,一位五十岁的婆婆,比姑妈还要哭得利害,哭完了又来看新娘,跟着的是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拿了放在几上的我的相片,“这是焱哥哥吗?”[40]
故乡的桥、故乡的河、故乡的城、故乡的竹林乃至故乡的人,都是以自然的口语和方言土语的形式倾泻在笔下,这是一个以田园牧歌的风味和意境构成的美丽图画。沈从文[41](2002)对这个文学世界有如下描述:“作者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从我们读废名的第一部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开始,“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的活到那片土地上。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的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
4 返璞归真与禅意天成
“返璞归真”还体现在废名小说的语言中渗透着禅宗意蕴。他的禅意的形成与他从小接触的佛教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废名的故乡黄梅是佛教兴盛之地,有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的故事在黄梅家喻户晓。废名出生在这样一个浓厚的禅宗文化氛围之中,从小对黄梅的禅宗圣地向往之至:他[42](1985)在《冯文炳选集·五祖寺》中说:“五祖寺是我小时候所想去的地方,在大人从四祖、五祖带了喇叭、木鱼给我们的时候,幼稚的心灵,四祖寺、五祖寺真是心向往之。”废名“心向往之”的禅意主要表现为对“观心看净”的虚静境界的凝视与憧憬。具体体现在他的小说语言中就是“禅意天成”。
4.1 心象
所谓“心象”,“搜求于象,心入于境。”从表意上看,“心象”接近“意象”的概念,但它和“意象”在内涵上各有偏重。废名在十年造《桥》的同时又精研佛经,所以《桥》是一个更有效的“心象小说”。他从“心象”出发,将每一个没入心灵的深处“心象”凝成一个个结晶的句子。可以说,在废名的笔下,通过特殊的语言将心象化的途径转换为文字,从而营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
(31)话虽如此,但实在是仿佛见过一只老虎上到树顶上去了。
观念这么的联在一起。因为是意象,所以这一只老虎爬上了绿叶深处,全不有声响,只是好颜色(《桥·树》)。[43]
“因为是意象,所以这一只老虎爬上了绿叶深处”。老虎上树的情景现实中没有人能见到,但在废名的笔下意象凭借观念联系在一起,在观念和想象中,老虎却完全可以爬到树上去。
小说中具体的意象往往倾向于与抽象与观念世界相对应。例如:
(32)竹林上微动一阵风,三个人都听得清响,而依傍琴子一竹之影,别是一枝的生动,小林倏然如见游鱼,——这里真是动静无殊,好风披入画灵了。是的,世间的音声落为形相,摇得此幽姿(《荷叶》)。[44]
“画灵”与“幽姿”虽然是抽象的。但“音声”“动静”“形相”这些都是具象的。现实与虚幻之间在废名的笔下却是无阻隔的,凭借的就是意念化的途径。
4.2 意境
废名的“禅意”体现在空诸一切,让想象与“自心”一致,从而使创作中不写故事,只写带有解除心中盘郁的自娱的意境。他是以诗歌取境之法来造小说之意境,正如李健吾[45](1984)所说:“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意境本身,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美化境界”。例如《桥·菱荡》中的陶家村一年四季总是那样的宁静,它深藏在茂密的树林之中,一个水洲,一道河水使它远离县城的喧嚣与热闹。《桥·碑》营造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意境:夕阳斜射荒原,一条白道把绿野分成两半。幽邃青天下有莽莽苍苍的山影。山顶一块巨石,直指天穹。一只鹞鹰翱翔在天与石之间,盘旋起舞。这些对事物不一般的描写,跳跃的联系,同时又是些极其优美的语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奇朦胧、引人入胜的意境。像这样美妙的意境,在《桥》中俯仰皆是,举不胜举:
(35)抬头,本是想透过树顶望,而两边只管摆,那光又正照住了他的眼睛。摆也摆不脱,大家好笑。等到他再低头,一丛草分成了两半圆,一半是荫的,现得分外绿(《桥·狮子的影子》)。[46]
(36)两人摇步的背影,好像在他的梦里走路,一面走一面还在那里耳语,空野更度细竹的笑声,一直转过一个灌木之丛了(《桥·钥匙》)。[47]
废名写《桥》是用满怀的诗情,在恬淡的心境下用恬淡的语言不紧不慢地勾勒着,在这部全书是一种风景画簿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丛草分成了两半圆”“现得分外绿”“在梦里走路的摇步背影”……这一幅幅绚丽的画卷,把一个个也许无头无尾的故事拼凑起来,成为一个个整体意境。将无穷意味寓于有限的词语之中,构建了太多朴素而诗化的情境、画境与禅境。
4.3 空灵
废名的小说在语言运用方面尤其呈现出一种清空灵动之美。空灵而幽远;似山间的小溪,安详而活泼,在丛林间忽隐忽现,你找不到它的来路,也看不清它的去路,呈现在眼前只是淡淡的色调,静静的喧响。他曾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谈到莫须有先生的思想:“心如一棵树,果便是树上结出来的道理,道理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了”。从这里可以见出,作为废名自己化身的莫须有先生对于惠能的“空灵”是心领神会了。例如:
(37)我的灵魂还永远是站在这一个地方,——看你们过桥。是忽然超度到那一岸去了(《桥·桥》)。[48]
废名的《桥》是在虚幻和现实之间搭起了一座“桥”:一个非常普通的过桥的情景,在废名笔下却化为一个空灵的意境,有一种出世般的彼岸色彩。赋予《桥》一个镜花水月的空灵的世界。还如:
(38)这虽然平平的,差不多一眼望不见尽头,地位却最高,他是走上了那斜坡才不意的收不住眼睛,而且暂时的立定了,——倘若从那一头来,也是一样,要上一个坡。一条白路长长而直,一个大原分成了两半,小林自然而然的走在中间,草上微风吹(《桥·碑》)。[49]
以短句结构的语言,描写小林在荒野中的梦游,没有故事的叙事,缺乏互动的独白。茫茫的一片空。路将平原分野成两半,人在当中,方才凸显出一种“空”来。大自然的空,叫他明白了空的自然:超出一切意识界限的真空,正是世间万物的缘起。因缘的生起,所以本性是空。因为本性是空,所以句与句间也留下长长的空白,颇耐人寻味。
[1][2][7][12][18][23][31][32][33][44][46][47][48][49]废名.废名小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66,293,13,213,94,64,87,93,88,224,106,212,177,124.
[3][4][5][6][8][9][10][11][13][15][16][17][19][20][21][22][24][25][26][30][35][37][38][39][40][43]废名.废名选集:一卷本[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65,105,62,115,84,42,81,218,156,160,169,40,107,40,65,367,106,12,621,204,154,145,93,154,65,337.
[14]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M].上海:开明书店,1951.
[27]陈淑梅.语法问题探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360.
[28]汪曾祺.林斤谰的矮凳桥[A].汪曾祺全集:第4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06.
[29]刘宝昌.大块噫气:废名小说“传统”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9(4):69.
[34]陈边城.废名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简评[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2):45.
[36]卞之琳.卞之琳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73.
[41]沈从文.沫沫集·论冯文炳[A].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46.
[42]冯文炳.冯文炳选集·五祖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5]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45.
责任编辑 文嵘
10.14180/j.cnki.1004-0544.2016.11.011
I207.4
A
1004-0544(2016)11-0061-0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YY034)。
陈淑梅(1955—),女,湖北英山人,语言学博士,黄冈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