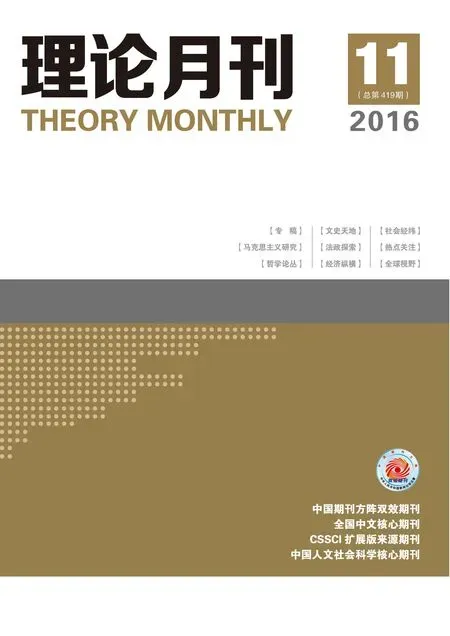论康德伦理神学的双重向度及其意义与反思
2016-03-06白文君
□白文君
(汕头大学社科部,广东汕头 515063)
论康德伦理神学的双重向度及其意义与反思
□白文君
(汕头大学社科部,广东汕头 515063)
康德的伦理神学是以道德为基础的神学,体现出伦理学与神学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的关系,也呈现出德性神圣化和神性德性化的双重向度。德性神圣化拔高了德性,拓广了伦理学的视阈,也助长其形式性;神性德性化为神学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也矮化了神学。康德的伦理神学的得与失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德;伦理神学;德性神圣化;神性德性化
提起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知晓者甚多,但对他在神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知晓者甚少。康德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与神学的关系,建构了自己的伦理神学,对后世影响深远。相较于知识论与道德形而上学,人们对康德的伦理学神学缺乏足够的关注,这将影响对康德的整体思想的把握。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康德伦理神学中道德与神学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的关系,揭示出康德伦理神学所呈现的双重向度:即德性神圣化和神性德性,并以此阐明对伦理学和神学所产生的正反方面的影响,以期丰富对康德伦理神学的理解与把握。
1 康德的伦理神学
康德的理论主旨是捍卫人的自由和尊严,彰显人的自主性。在他看来,最能体现人的自主性是实践领域,为此康德建立了以“自律就是自由”为基石,以尊崇理性,贬斥感性为特色的伦理学。但其理论的综合性、思维上的二元性和非辩证性,致使康德的伦理学在自身范围内难以解决实践领域的“二律背反”,为了解决德福不一致的问题,不得不悬设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这就是康德的“道德导致宗教”的命题。对此康德的解释是:道德为了自身起见,绝对不需要宗教;相反,借助于纯粹的实践理性,道德是自给自足的。但为了至善的缘故,必须悬设定一个最高的存在者,这样道德不可避免地导致宗教。[1](P1-4)
仅止步于此,神学似乎是康德的“权宜之计”,然实则非也。康德的伦理学与神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互为前提。首先,对神学的建构贯穿康德的三大批判及其他的著作中,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以“正义模式”建构神学。《实践理性批判》中则以“义务模式”建构神学,在《判断力批判》以“自由模式”建构神学。[2]这些论证细致而严谨,与康德的整个理论体系严丝合缝,是深思熟虑而为,而非权宜之计。上帝存在也是康德最诚挚的信念,这种信念影响康德的理论建构,如海德格尔所言,“上帝存在”这个问题乃是一种隐蔽的刺激,它驱使着《纯粹理性批判》的全部思想,并且推动康德此后的主要著作。[3](P534)其次,康德的伦理学与神学互为前提,内容相互嵌入。一方面,康德的伦理学具有神学维度。康德的伦理学既具有神学指向,又具有隐秘的神学前提,对道德法则的坚守离不开对上帝的信仰,神学是理解康德伦理学的必要语境,神学也是其伦理学的逻辑必然。[4]另一方面,康德的神学是建立在伦理学的基础之上的。在康德看来,神学和宗教只有出自道德意图才有必要和可能,上帝是一个道德概念,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只能由道德予以“说明”,上帝的属性,诸如全知、全能、全善且公正等只能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道德法则更是康德理性宗教建构的基石和判断的标准。因此康德看来,没有道德,就没有神学;没有神学,道德也是不完整的。康德的伦理神学就展现了伦理学与神学的这种紧密不可分的关系。
2 康德伦理神学的双重向度
康德的伦理神学是神学,是以道德出发点和归宿的神学:伦理赋予神学以“人性”,上帝不再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而是与人相关的、人在成就德性之路上的“指路明灯”和“信念保障”。康德的伦理神学也是伦理学,是信仰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伦理学,神学信仰的“牵引”致使康德的伦理学具有形而上的超拔,使其获得“品性高远”、“超凡脱俗”的品性。因此,本文认为康德的伦理神学明显具有双重向度,即德性神圣化和神性德性化。
所谓德性神圣化,是指意志意向圣洁化。康德认为道德不是体现在符合法则的行为,而是体现在意志意向法则的行为。芭芭拉·赫尔蔓说得更为清楚:“康德式的伦理学是以意向或意愿为基础的道德理论。道德评价的对象不是事件和事态,而是意志活动。所发生的事情本身并无道德善恶、对错之分,只有意志活动才有。”[5](P146)意志意向法则的行为是善的,否则是非善的。对于德性的理解也是如此,康德认为德性就是意志意向法则的状态,人的意志越是自觉地意向法则而行动,则越有德性。正如亨利·E·阿利森所言,康德认为的德性,即是一个人的义务与其形式法则相一致的这种单纯思想。[6](P242)但人有自然偏好和感性欲望,人的意志也容易受到诱惑而背离法则而行动,因而,德性对人来说是一种强制,是“一种依据一个内在自由原则,因而通过义务的纯然表现依据义务的形式法则的强制”。[7](P407)就实然而论,人对法则的遵守是偶然的。康德显然不满足这种偶然的遵守,而是把意志与道德法则的完全符合当作一种道德理想来追求。这种“完全符合”是一种纯粹意志,神圣意志,这只能在上帝或神那里才能达到。康德这是站在神性的角度要求人的德性。难怪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说,“德性首先要求对自己本身的控制”,“德性必然以不动情为前提”。[7](P421)如果说“控制”意味容许感性欲望的激发但意志不受其影响,那么“不动情”则意味着感性欲望都不能激发。这肯定是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于是康德构筑了这样一幅图景:“真正德性之人,即能够真正进行自我控制的人,……他们首先是极少甚或完全不受诱惑,而不是忙于与诱惑进行英勇的持续不断的斗争。”[6](P243)
但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是无法剔除感性成分,意志也无法免受感性欲望的影响,因而人的修德之路是一条“漫漫之旅”,这意味着:(1)德性是在经历艰难的“痛苦斗争”才取得,而非随心所欲就能获得;(2)已有德性并非一成不变,时常会被各种感性欲望所“败坏”,这要求人必须时刻自律克己,不能倦态松懈,否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7](P420-422)这说明康德是在神性的角度上要求德性,拔高德性的标准,以彰显人性的高贵和德性的崇高。
所谓神性德性化,是以德性“说明”神性。首先,上帝是一个道德概念。康德认为上帝属于本体界,是理论理性无法认知的物自体,自在的上帝是什么,人一无所知,只能通过实践理性去“接近”上帝、指望上帝,别无他途。上帝存在对人是必要的,仅仅是因为解决实践理性之“二律背反”,即“德福不一致”的需要的缘故;人关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信念,仅仅是为了信守道德法则的必要,因为“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我们便会要么变成恶棍,要么变成为空想家”,[8](P110)除非我相信上帝存在,否则我会把道德法则当作根本无法实施的法则来抛弃。由此观之,道德是康德“言说”上帝的唯一“语言”,也是上帝“启示”自身的唯一方式。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属于康德的“道德世界观”的一部分,“所以上帝概念是一个从起源上就不是属于物理学的概念,亦不是对思辨理性而言的概念,而是一个属于道德学的概念。”[9](P192)其次,上帝的属性只能从道德上去理解。上帝被设想为全知的,以便知晓行为者最隐蔽的动机;被设想为全能的,以便保证德福的统一;被设想是善且公正的,以便为道德行为分配适当的幸福等等。上帝的神性,就是意志的纯粹性,是与道德法则的一致性。上帝不是罪人获救的保证,仅仅是给予人德福一致信念的保证。基督耶稣,是一个道德圣洁的人、人类道德的导师、可供效仿的道德榜样。可见,康德对上帝和耶稣作了祛魅化的处理,祛除笼罩在他们身上的神秘光环,赋予道德的形象。再次,建构道德神学和理性宗教。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出于实践的意图,为了至善之可能,康德悬设了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从而建立了道德神学。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同样是为了至善的缘故,建立了理性宗教。悬设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仅仅满足至善在逻辑上的可能,至善要在现实中可能,则必需宗教。单纯个体向善,不足摆脱恶的侵袭,只有建立促进善和防止恶的联合体,才能真正向善,最终实现至善。这样的联合体,就是伦理共同体。而伦理共和体必需两个要素:公共的立法者和造就上帝子民的团体,也就是上帝和教会。这就是康德的“道德导致宗教”的实质内容。这意味着康德把宗教奠基在道德上,正如有人指出,“对他(康德)来说,宗教的而恰当的根源,不是纯理性的,而是伦理的。”[10](P372)不仅如此,康德的理性宗教是以道德为目的的。康德虽然不满现存的基督宗教,但还是将之视为最契合他心意的宗教形态。为此,康德以理性为判断标准,以道德为目的对基督宗教进行改造。“人在道德上的归正,构成所有理性宗教的真正目的”,宗教中的一些概念、宗教的仪式以及教会的教义必须经过理性的筛选,凡不利道德归正的,均被剔除。对《圣经》也作了道德阐释,康德认为,不是以《圣经》来阐释道德,而是以道德来阐释《圣经》。这样,康德完成了神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不是神学决定道德,而是道德决定神学),并建构自己的伦理神学。
3 意义与反思
康德的伦理神学的双重向度以精致的形式对道德与神学之间的关系作了新的阐释,对伦理学和神学产生了非凡的影响。阐发康德的伦理神学对伦理学和神学的意义并对之进行反思,对全面、深入理解康德的伦理神学将大有裨益。
3.1 对伦理学的意义
康德将神学“引入”伦理学,对其伦理学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它严格了对德性的要求,德性必须是经过一番“艰难”努力而非在随心所欲的状态下获得,捍卫人的自由与尊严,更为重要的是它拓展了伦理学的广度与深度。
首先,康德的伦理学以自律原则和义务论为特色,单纯强调为了义务而义务,忽视义务的结果对人的行为选择的影响,人为地“斩断”行为结果对行为的“刺激”作用,这显然不符合实际。神学的引入,才使得“我应该怎么行动”与“我可以期待什么”联系在一起,行为的动机与效果才不“截然分裂”。通过神学,在义务论中被拒斥的感性欲求(幸福)又重归康德的伦理学;“遵守法则而行动”与“信仰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伦理神学的建立,一方面改变了康德伦理学重义务,轻希望;有理性要求而无感性满足、有形式而无内容的干瘪刻板形象。另一方面拓广了伦理学的范围,使得康德的伦理学不仅仅局限在道德形而上学,还包括了道德神学和理性宗教。
其次,神学拓展了伦理学的深度。康德的伦理神学充分展示了伦理学的超越面向。人们习惯于将伦理学的任务局限于规范人的行为,以及对之作为善恶与是非判断这一点上。如果伦理学仅止于此,那它与风俗习惯、法律又有多大的区别呢?康德高举实践理性所具有而理论理性所不能有的“优越性”,亦即它能够“通达”本体界,认为人意向道德法则而行动时,必然会“体验”对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和自由的信仰。也就是说,人在遵守道德法则而行动中,会被道德法则“牵引”至“本体的高度”,去关注和思考形而上的问题,从而使人获得精神上的净化和澄明,产生了对凡俗的超越。所以说,康德的伦理神学展示了伦理学所具有的超越性。这种超越,对伦理学本身而言,使其避免陷于因“纠缠”于行为善恶是非的判断而产生的“琐碎凡俗”之中,从而获得精神的灵性。孔汉思曾指出,宗教不能化约为伦理,唯有我们愿意有时忘记伦理,并集中一些“更高”的事上,我们才能真正讨论宗教伦理。[11](P5)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只有目光集中于“更高”的事物,才会使我们获得对伦理问题的探讨的新高度。对个人而言,这种“超越”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本体”作为“理念”对于“理念”所囊括的有限东西具有根本的价值“范导”作用,把有限的事物“范导”到它的理念,就是让有限的事物成为其自身,实现其终极目标和价值。[12]因此,向本体界的超越就是对自身极致世界的开辟和实现,也是人的自我提升和更新。
再次,康德的伦理神学还展示了伦理学“建构”信仰功能。康德在实践理性的立场表明,作为道德法则的必然要求、实践理性的客体的至善要成为可能,则必信仰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因此,康德的伦理神学一方面阐明了对上帝的信仰是实践理性的先决条件,是人信守道德法则的隐性前提,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之信仰的“确证”。前者意味着道德需要信仰,后者表明道德本身可以“建构”信仰。这种“建构”实质上是理性在实践意图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之必要性的主观认同,是一种主观上充分、客观上不充分的“认其为真”。这种信仰不同于依靠各种超验的启示和神迹“建构”的信仰,它是一种世俗的信仰,信奉的是人类理性在“此世”中依靠“自由律”创造至善世界的能力。这种信仰也可以为人提供信念支撑和希望指引。
康德伦理神学的德性神圣化向度虽然赋予伦理学“超凡脱俗”的品性和精神的灵性,但也招致不少的批判。批评之一就是对神学“介入”伦理学表达不满,尤其是无此信仰的人。他们认为“只有在经历无穷无尽的时间后,才能获得道德完美。这简直等于说根本不可能获得道德完美。”[13](P115)统一于彼岸世界的至善被看成是一种虚妄、一种“精神麻醉”,更是在现实世界的软弱的表现。批评之二则聚焦于康德为了追求德性的纯洁和神圣而抑制、排除感性。当然神学对于康德对感性的排除只是促进性因素。在这方面的批评者众多,他们有的批评康德此举是“自相矛盾”,如C.D.布劳德指出:“事实上,当康德在研究纯伦理学的问题时,他把人的本性是理性与感性的混杂当成真实;当康德试图给这些形而上后果提供一种理性理论时,他又把人的本性是理性与情感的混杂当成妄想了。”[13](P113)还有的人认为,康德为了高举德性而不遗余力隔离感性对人行为选择的影响,把人变成纯粹的理性存在,这种做法是不现实也不客观。人是有情感的存在,人的行为选择更多时是关乎人的情感、具体处境的。康德拒绝人个人情感对伦理的影响,但问题是人是否可以放下情感作伦理选择呢?此外,当以此方式高举道德,会有一种担心:一个排除情感和具体处境的人在面对他人时,很容易失去对人处境之同情,因为个人的独特性被否定了。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同情,会不会产生道德冷漠呢?因而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说康德伦理神学的德性神圣化部分地“助长”了康德伦理学的形式性。
3.2 对神学的意义
康德在神学领域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因而被认为是除了施莱尔马赫,没有一个人比康德对近代宗教的影响更大。康德对近代神学和宗教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观点意义深远和对这些观点的运用,而不在于他自己观点的内在价值。[14](P155)康德伦理神学的神性德性化,对近代神学及宗教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康德把上帝从知识领域驱除,限定在价值领域,并在道德意图上“证立”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为近代神学和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神学的“地盘”不断被“蚕食”,影响力日渐式微。康德的举动可看作是为了挽救神学并让其继续发挥作用的一种主动的尝试。把信仰与知识分开,致使信仰与知识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理性的两个重要的方面,从而缓解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神学造成的冲击。就这点而言,对近代神学的发展尤为关键:它使神学摆脱了古典经验主义的腐蚀,同时又维护了宗教信念的合理性。[14](P129)在康德之后,如下两个观点得到了强化并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宗教主要被理解为是人的实践上的事情,对于宗教信念,决定性的是对知识的独立性。还有一些人沿着康德开辟的“道德证立上帝”道路继续前进,如费希特、利奇尔和哈那克、饶申布什,后三者所属的利奇尔学派,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影响了十九世纪前半叶的新教思想。
其次,康德通过道德“证立”上帝的方式向后人启示:人谈论上帝的方式影响着人的上帝观。受此影响,施莱尔马赫以“对宇宙的直观”或“绝对依赖感”来谈论上帝,从而开启了近代多元的基督宗教。康德“悬置”自在的上帝,以道德方式“启示”上帝,这种上帝实质上是与人“相遇”、“人化”的上帝。康德这种作为,“可以理解为把启蒙运动以有神论的方式论证的形而上学溶解和转换为对经验意识的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描述。”[15](P229)康德身后的诸多神学家,尽管不满康德的道德化上帝,但依然沿着“人化”的道路前进,在施莱尔马赫、利奇尔刺激和推动下,形成蔚为大观的自由主义神学。此外,康德对传统神学的批判、对教会的批评,以及对实践理性之优越性的强调,都影响不小。特别是康德对上帝之国的伦理解释,“在神学中的效应远远超出了通常受过康德影响的神学家圈子。特别是施莱尔马赫,虽然批判过康德命令式伦理学,但却接受了他与至善的目标思想结合而对上帝之国概念的伦理解释,而且作为他的神学的一个核心概念”。[15](P249)康德对近代神学与宗教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所以毫不夸张的说,康德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
尽管康德对近代神学和宗教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康德的理性主义、道德主义、非历史主义的宗教解释招致诸多来自神学和宗教内部的批评,这种批判引发了人们对康德伦理神学进一步的认识。首先,这种批评认为康德的伦理神学“矮化”了神学和上帝。这种“矮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将上帝工具化。自笛卡尔以来,上帝逐渐被工具化,康德尤甚。康德认为上帝存在的必要仅仅因为上帝是德福一致的保证,仅仅具有主观必要性的。这对于确信上帝实存的人来说,上帝是本源性、本体性的,是自在的存在,不是道德来“说明”上帝,而是上帝决定道德。康德的立场是一种“退步”,褫夺了上帝的至尊的地位,这是不可接受的。“矮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导致了神学“凡俗化”。康德仅仅从伦理的角度来理解宗教,这会将使宗教自然化,神圣凡俗化。[11](P11)宗教要求人做到本体性圣洁,做一个上帝喜悦的义人,这关乎一种与上帝的关系,而不受个人道德素质的影响。伦理学则要求做一个善人,亦即伦理性成圣。这二者有关联更有区别。一个本应是在本体性圣洁的人只是做到伦理性成圣,仍很肤浅。[11](P5)康德的伦理神学只要求人做到伦理性成圣,而忽视了本体性圣洁,限制了人因与神相遇而产生的自我超越和提升。因而是一种“矮化”。此外,康德的伦理学排除了感性和日常经验,以此来理解宗教,宗教也会变得“干瘪”而缺少灵性。宗教包含个人对生命的体验和对世界的情感,它不是始于命令,而是始于恩典,不是始于思辨,而是始于宗教经验。[11](P13)因此,宗教不能化约为伦理,否则就是对宗教的“矮化”。
再次,另一种来自当代神学家卡尔·巴特间接的批评,他对现代神学的批判也可视作对康德的伦理神学的批判。巴特认为包括康德在内的近代神学偏离了真正的上帝之道,缺乏对神学根基和问题的坚守,从而沦为时代意识形态彻头彻尾的俘虏。[16](P27)对于康德以道德来“证立”上帝,巴特认为,除了上帝在耶稣基督中独一的自我启示外,必死的人绝无可能认识不朽的上帝,也不能达到神的高度,人的理智和概念更不能以实定的方式把握隐秘的上帝。世上不存在一条从人通往上帝的道路,站在人类某条道路终点上的上帝不是真正的上帝。[16](P49)真正的上帝是与人的世界和历史“全然相异者”。康德的上帝本质是人的一种投射,是人的宗教的偶像。针对康德的伦理神学为挽救神学所作的在神学与科学之间的调和,巴特认为,包括康德伦理神学在内的现代神学,还有自由主义神学,其本质是哲学人类学,或者是人类中心主义神学。整个现代神学积极谋求适应现代性,自以为勇于接收现代哲学的洗礼,其实是憎恶自己的出身和谱系,在现代哲学面前步步退让,屈膝辩护,其结果是神学失去自己的根基和问题,神学从根本上被掏空。[16](P60-62)这必然会导致“上帝之死”、“神学危机”。不过,巴特这种“纯粹”神学立场也招致了“对现实没有任何作用”的指责。
[1]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邓晓芒.康德对道德神学的论证[J].哲学研究,2008,(9).
[3]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白文君.论康德伦理学的神学维度[J].学术论坛,2015,(5).
[5]芭芭拉·赫尔蔓.道德判断的实践[M].陈虎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6]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M].陈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7]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Kant.Lectureonphilosophicaltheology[M],Translated by Allen W.Wood and Gertrude M.Clark.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
[9]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胡斯都·L·冈察雷斯.基督教思想史:第3卷[M].陈泽民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11]龚立人.纠缠的灵性:伦理、社会与宗教[M].香港基督徒学会,2006.
[12]邓安庆.伦理神学与现代道德信念的确证[J].文史哲,2007,(6).
[13]C·D·布劳德.五种伦理学理论[M].田永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4]詹姆斯·C·列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M].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15]潘能伯格.神学与哲学[M].李秋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6]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刘宏兰
10.14180/j.cnki.1004-0544.2016.11.007
B516.31
A
1004-0544(2016)11-0038-05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项目(10YJC720002);汕头大学国家项目培育基金(NFC13010)。
白文君(1976-),男,湖南宜章人,哲学博士,汕头大学社科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