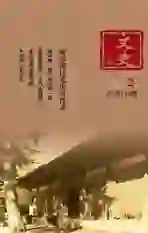李用清与晋阳书院
2016-03-04董剑云
董剑云
李用清(1829—1899),字澄斋,号菊圃,平定州乐平乡(今山西昔阳县)杜庄村人,是清末著名的“居敬行简”的理学家、“表率群伦”的教育家、“清绝一尘”的廉吏。他早年在山西最高学府晋阳书院学习七年。同治四年(1865年)考取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广东惠州府知府、贵州贵西兵备道道台、贵州布政使、署理贵州巡抚、陕西布政使。为官三十年,所到之处地方大治,政绩斐然,并以至清极俭的形象在晚清官场上树起了一座道德丰碑。他晚年辞官归里,又回到晋阳书院,主讲十年,培养出了在民国山西史上开一代风气的赵戴文、张籁、狄楼海、徐一清、冯济川等知名人物,为清末山西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负笈求学
李用清出身书香世家,七岁入私塾读书。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参加平定州生员考试,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被平定州选送到晋阳书院学习。
晋阳书院的前身为三立祠(俗称三立书院),明代时位于今太原市迎泽区西海子靠东。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山西巡抚白汝梅鉴于祠院颓废不堪,在太原府城东南的侯家巷(今太原市公安局院内)购地另建三立祠。这是山西在清代最早恢复重建的一所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在全国22个省会城市各赐帑金一千两,资助建立一所省府书院。山西巡抚借此重新修葺三立祠,添建屋宇,并正式恢复“书院”名称,更名为晋阳书院。以后,经过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八年(1753年)、二十九年(1764年)连续三次大规模扩建,晋阳书院发展到鼎盛。历任山长中出现了王珻、李熔经等许多著名理学家,晋阳书院也因此成为山西理学思想研究和传播的重地。李用清在此接受了严谨而系统的程朱理学训练,数年如一日,刻苦自励,为以后成为理学名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晋阳书院每月都要进行两次课试:一次由学政主持,并出题、阅卷、给奖,称为官课(又称“大课”);一次由山长主持,并出题、阅卷、给奖,称为师课(又称“堂课”)。这两次月考都以八股文章为主、策论诗赋为辅。八股试题以四子书为主,立言又以程朱理学为主。李用清与两位乐平同乡李希莲、李鸣凤在月考中每每独占前三,声名大噪,被当时山西学界称为“乐平三李”。
清代规定,各省学政每三年要对全省生员进行一次考试,选拔出数位学行卓异者贡入国子监学习,称为优贡。在咸丰八年(1858年)的考试中,李用清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当年秋天,又参加了山西省乡试,考中举人,被称为“优贡举人”。
同治四年(1865年),李用清到北京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同榜进士有崇绮(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唐景崧(末代台湾巡抚)、胡聘之(山西巡抚)、王先谦(晚清巨儒)、汪鸣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英才济济,为清代历届进士考试中所少见。同年,李用清被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
李用清进入翰林院后,执弟子之礼进见翰林院掌院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倭仁为著名的理学大师,在同治年间被政界、学界尊为“人伦表率”“群流归仰”。他推崇程朱之学,认为“辨学术当恪守程朱,以外皆旁蹊小径,不可学也。”并对李用清有所指导,使其识见大进。李用清也把师从倭仁视为一生的大幸,从此专宗程朱理学,孜孜矻矻,死而后已。
宦海浮沉
李用清在翰林院时,正值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一部分翰林学士和御史言官奉军机大臣李鸿藻、光绪帝师翁同龢为领袖,打着“经世匡时”的旗号,标榜风节,“严义利之分”。他们反对洋务运动,希望内用程朱理学以定人心,外用除弊、惩贪、固本以利民生,被称为清流派。李用清所在的翰林院是清流派的主阵地,他与李鸿藻、翁同龢、阎敬铭等清流派领袖人物同气相求,交往密切,其学问、品行受到他们的敬重与赏识。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李用清加记名御史衔,随钦差大臣阎敬铭回山西襄办赈荒。他在赈荒实践中认识到,“致荒之道,在不种五谷而种罂粟”“必改花田(罂粟)而种五谷,然后生聚有期,元气可复”,于是垂涕写下著名的《大荒记》,并上书山西巡抚曾国荃,力主禁烟还粮。但曾国荃“疑晋新荒,禁烟效缓,且全国未禁,徒敛怨”(《清史稿·李用清传》),没有采行。
光绪七年(1881年),李用清任广东惠州府知府。次年调任贵州贵西兵备道道台。第二年又破格直升为贵州布政使、署理巡抚。李用清认同清流派“改革弊政”“整肃纲纪”和“兴修水利”的施政理念,他在广东、广西任上大力惩贪肃弊,禁止种吸鸦片,兴修水利,充实粮储,地方风气大变。李用清受到历任长官的高度评价,两广总督张之洞称他“坚确勤苦,不为习俗所夺,可以挽回风气”,四川总督丁宝祯称他“公忠自矢,力崇俭朴,办事实心,实为黔省历任抚臣所罕见。”但由于禁烟措施触动了地方官绅利益,李用清最终被以“操之过急”为由撤职。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在军机大臣阎敬铭、吏部尚书崇绮等奏保下,李用清被起用为署理陕西布政使。他不计沉浮,以国本民食为要义,节流开源,栽桑种棉,兴办纺织,修筑三原龙渠,还用自己的养廉银买谷万石充仓备荒。署政两年,陕藩库帑增加30万两,翻了一番。光绪十四年(1888年)郑州河堤决口,他又慷慨捐银两万两,并为故乡杜庄村捐款筑堤、购田生息以作村中公用之需。岂料他的狷介耿直为督抚所不容,被考评为“人地不宜”而罢官。张之洞、翁同龢等都为李用清打抱不平,而阎敬铭更是直接上疏称赞李用清“为近时藩司(布政使)之最”,并直指该督抚“淆乱黑白,颠倒是非”,恳请朝廷收回成命。阎敬铭为此受到朝廷严厉申斥,遂愤而辞职。
当时朝野对李用清的评价截然两端。赞成者,称他是“藩司之最”(阎敬铭语)、“黔省历任抚臣所罕见”(丁宝祯语)、“蔼然仁人哉”(翁同龢语)、“白璧斯完”(崇绮语)。反对者,则不仅对他的政绩视若无睹,而且还对他的克勤克俭竭尽诋毁之能事,甚至人身攻击。当时,李用清在官场上有个绰号叫“天下俭”。他虽然动辄慷慨解囊捐万两银、万石粮以助赈济困,而自己和家人却过得异常节俭,吃糠咽菜,穿乡下人衣履,住祖传老屋,始终保持了农家本色。他认为如果不刻意提倡节俭,就不足以养民教士。但他这种克勤克俭的作派,却被同朝的浙江名士李慈铭讥讽为“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受也。”御史汪鉴更是诬指他“清操不可取,犹之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为笑柄。”评价判若霄壤,或多或少都掺合了个人好恶,折射出清流派、洋务派的党派之争。李用清的两起两落,不能不说也是光绪中期清流派、洋务派在朝廷中势力消长的一个反映。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对李用清有过一段评论:“他如果生在康熙年间,必获大用,且亦必如汤斌、于成龙之成为理学名臣;而在末世,不能不移疾以去”,不无道理。
十年主讲
自古以来,书院就是致仕官员理想的托身之所。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用清被免职的第二年,回到曾经就读的晋阳书院,担任主讲,而且一干就是十年,直到在书院去世。他在晋阳书院的主要作为有:
一是整顿士习。李用清认为:“国家人材之坏在书院,而士习心田之坏在读书。”书院今日养贤是为了他日养民,学生如果未科举入仕就先染上许多坏的习气,不在身心上切己反求,将来登科入仕也不会是一个清官好官。所以,现在就必须严加约束。他还多次重申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并且规定院内严禁喧哗,进入讲堂必须行列整齐、衣冠肃敬。他严以律己,甚至对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绳以先正,不少假借”。经过整顿,“学者得识行书立身之要,士风为之大变”(王廷相:《李菊圃中丞墓表》)。
二是科举造士。据其弟子回忆:李用清每日凌晨四点就起床盥洗,然后就击梆将学生聚集一堂开始授课。他身材高大,仪容峻伟,目光灼灼,端坐讲席,雍容如泰山磐石,可亲而不可犯。讲课的内容主要是《小学》《大学》,他连讲十年,毫无倦意。李用清去世后,弟子们将他的讲话偶记、治学格言及试卷批语等整理为《课士语录》。洋洋七万言,包括修身、教学、为学、读书、为政、体验、作文、做人、理财、释经、交友等11章30节,主要为修身明伦之理、为师为学之道。但“科举”“为官”等语也俯拾皆是。如,“古来名臣名儒,不从科甲出身者几人哉?试思之。”“专学举业者,则专在语言文字上用功,而身心置之度外。今日但将平日所读之书,反求诸身心,则得矣。而举业功夫,亦从此益进矣。”此外,李用清还在讲学中传授为官之道,如:“将来做官,有两件事:一为教,一为养。养则务本、节用(自古真经济),教则明五伦(自古真教化)便是。诸生好生记下,将来做官,止有这两件事情。”
三是笃守理学。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洋务派陆续开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受此影响,书院内部也开始吹起一股改革之风。山西有两位洋务干将张之洞、胡聘之先后主政,洋务活动蔚为壮观,为全国所瞩目。光绪十年(1884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在明代晋藩宝贤堂故址(今太原市解放北路西侧山西省实验中学初中部所在地)创办了有近代意义的令德堂(又称令德书院),后聘请既精通程朱理学又习知天文算学的著名学者屠仁守任山长。令德堂既保留了传统儒学的正统地位,也设置了算学、格致等众多新课程,屠仁守亲自执教算学,并广购外国书籍,开阔学生眼界,开了山西教育改革的先河。胡聘之主政期间,在全国率先聘请硕学之士到令德堂任教,并亲自邀请著名数学家华衡芳等科学家前来讲学。他还规定,在学堂增设算术、化学、天文、地理、农事、军事等课程,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
令德堂与晋阳书院相去不远。虽然有记载称李用清曾允许学生向屠仁守请教算学知识(李衡云:《方伯李菊圃先生事略》),但从《课士语录》看,李用清作为程朱理学的忠实捍卫者,对于洋务运动以来人们“侈谈经济之宏论,性命之高见”,而避谈“修身齐家之道,诚意正心之说”的情况强烈不满。他告诫同僚和弟子:“近日异学充塞,正道几于不明,吾党其力持之。”他曾说:“修身齐家,便是绝大本领,绝大经济。今人……弃而不治,专去治平上讲究,此最是莫救坏证。”“有谓诗书道理不宜于今者,不知此乃正是迷惑也。诸生试思之。是照书上道理才对,否便不对。”“今之学校,直是全无规矩,放僻邪侈,自诩才子名士,尚不如释道两门尚有清规。”
四是执着禁烟。李用清认定鸦片为国之大患、民之大害,无论早年在山西办赈还是在黔陕任职,无不以禁烟为首务。可以说,其成也禁烟,败也禁烟。晚年到书院后,仍不改初衷。除了在课堂上对学生大讲鸦片之害外,只要有达官贵人来访,他总是痛心苦口地劝诫官民莫种鸦片。“客有谓‘罂粟当禁,方法须要研究’,公则许之;若谓‘罂粟不当禁’,公则蓦地送客,不与多言。其立论之坚,可见一斑。”直至弥留之际,还喃喃:“去就争之,生死以之”(李玉玺:《清李菊圃先生用清年谱》)。
五是忧心时事。李用清在书院主讲时,正逢洋务运动高潮和戊戌变法前夜,政局纷繁扰攘。每逢朝廷有重大人事变动或改革举措出台,李用清总是“中夜起立,彷徨不已”。有弟子安慰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答道:“天下事须痛痒相关。吾自当官后,自觉习与性成,不能忘也。”光绪十八、十九年(1892—1893),山西北部大旱,李用清核计全省储粮不足应付赈济,又夜不成寐,神形顿摧。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更是忧愤交迫,终于导致其自光绪三年办赈时落下的痢疾旧病复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二月初二日,李用清在晋阳书院赍志以殁。
结 语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李用清去世两月后,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又过了两月,山西巡抚胡聘之连续两次上折,请求改省内书院为中西兼习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也就是李用清去世四年后,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前身)宣告成立,晋阳书院最后一任山长谷如墉被任命为大学堂总教习兼中学专斋总理,书院在读学生全部转入山西大学堂。晋阳书院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李用清作为程朱理学的服膺者,倘若健在,对这些新变化新气象也未必乐见其成。正如清代杨颐《贵州巡抚李公(用清)神道碑铭》所言:“呜呼!公殁才数月耳,而变法之说兴,此其公之所及料,又深幸公之不及见也。”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时期李用清等理学家特别强调伦理纲常,矢志守护程朱理学,既包含着对正统思想的不可或缺性和超越功利性的深沉思考,也有着对洋务运动激荡下国人的传统精神家园日渐崩塌的忧虑。如此之立意高远,如此之用心良苦,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斥之为“顽固”“保守”,而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给予充分同情与理解。他们着眼于“常”,与洋务派的着眼于“变”,无论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光大,还是对于今天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价值。正如昔阳籍著名作家二月河所言:“在当今社会,李用清这个典型极具现实意义,他为人为官的道德品质依然是今天人们学习的榜样,他为学为教的认真精神更应该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