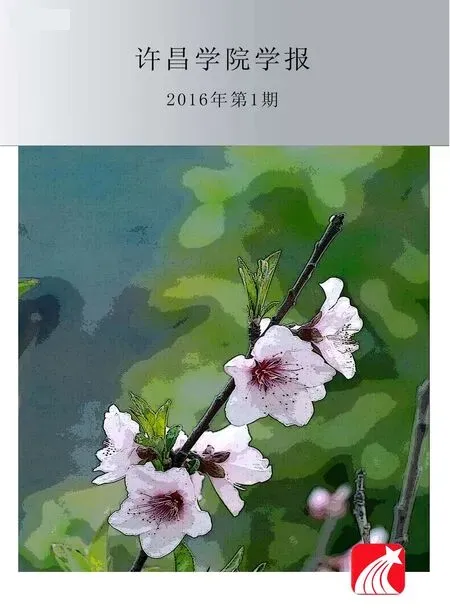犯罪预备问题探究
2016-03-03袁祥境
袁 祥 境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犯罪预备问题探究
袁 祥 境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我国《刑法》第22条规定了犯罪预备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这种普遍处罚的原则引起了实务与理论界的广泛争议。关于犯罪预备的可罚性问题争议最为突出,普遍处罚原则在法理根据与实践可操作性等方面存在着问题。各国的立法实践关于犯罪预备的规定主要有普遍处罚、例外处罚、不处罚三种类型。其中,解决犯罪预备问题的真正方式是立法上进行重构,确立例外处罚的原则;正确区分犯罪预备与预备犯等相似概念是厘清犯罪预备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分析完善犯罪预备的构成要件是正确处理犯罪预备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犯罪预备;可罚性;预备犯;普遍处罚;例外处罚
我国《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实际上是确立了对于预备犯普遍进行处罚的原则。但是普遍处罚原则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理论与实务界对于其可罚性根据争议较大。很多学者都认为对于预备犯普遍进行处罚的立法模式在法理根据的正当性和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方面存在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通说认为犯罪的可罚性根据是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本质上来说具有社会危害性。对于犯罪预备的可罚性分析是探索犯罪预备理论的前提,预备犯与犯罪预备等概念的区分则是探索犯罪预备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预备犯的构成要件则是合理研究及实践犯罪预备理论的关键。以上几个方面是现今犯罪预备理论领域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拟对此类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可罚性问题
(一) 犯罪预备的可罚性问题
1.犯罪预备具有可罚性
我国刑法理论认为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其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而犯罪预备之所以要承担刑事责任,具备可罚性,是因为其行为也具备犯罪构成。但这种犯罪构成不是普通类型的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而是修正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是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前提,适应行为犯罪形态的变化或者共同犯罪各类形式的需要而对基本的犯罪构成加以修改、变更的犯罪构成。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和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的犯罪构成,就是两类不同的、修正的犯罪构成。由于修正的犯罪构成规定在刑法总则性的规范之中,而它又要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在确定这类犯罪构成时,要把分则规范和总则规范结合起来加以认定。”[1]62-63犯罪预备符合这种修正的犯罪构成,所以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受到刑罚处罚。
根据通说,承担刑事责任实质上是因为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犯罪预备行为,是为犯罪准备条件制造工具的行为。虽然尚且没有直接地侵犯犯罪客体,但是其行为在主观上已经表现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在客观上这种为了实施某种犯罪准备条件制造工具的行为对于相应的受刑法保护的法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或者说从一定程度上间接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有学者认为,犯罪预备行为往往按照其自身的行为惯性极有可能引起接下来的犯罪实行行为,如果不加以处罚,必然会放纵接下来的犯罪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带来难以抑制的侵害。“它在不同程度上便于犯罪的完成,因而它包含着对社会关系的实际威胁,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2]171这就决定了犯罪预备是具备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问题在于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否等于一定具有可罚性,换句话说,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否就一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答案是否定的,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有很多,行政违法、治安拘留、社会危害性较小不认为是犯罪等行为就不应受到刑罚处罚。只有在社会危害性程度上比较严重的,才应受到刑罚的处罚。这也是犯罪预备普遍处罚原则受到理论与实务界质疑的重要一点。
2.犯罪预备可罚性的争议
下面笔者主要针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简要分析。梁根林教授认为犯罪预备是不具备可罚性的。第一,在中国刑法理论体系不断地由粗放趋向精致、由平面四要件转向递进阶层式,特别是结果无价值、行为无价值的不法论逐渐取代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知识转型语境下,一般性地赋予预备犯以刑事可罚性并普遍处罚预备犯则陷入了严重的正当性危机。因而他主张从结果无价值角度出发来界定不法。“能够现实地引起法益侵害结果或者法益侵害危险的,只能是实施了作为不法行为类型的构成要件行为即实行行为,预备行为虽然是为了实行犯罪即便利构成要件行为的实行,但毕竟尚未着手实行构成要件行为,因而对构成要件行为这一不法行为类型预定予以保护的法益尚不可能造成实际侵害结果,甚至亦不能现实地造成法益侵害危险。”第二,普遍处罚预备犯没有刑事政策上的必要性。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意味着立法上要求将刑罚干预的触须前置到所有预备行为,对所有法定犯罪的预备犯原则上均得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论预备实行的犯罪侵害的法益性质如何,预备行为的情节、手段、进展如何,预备行为是否接近着手实行犯罪,行为人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原因如何。如此可能会导致刑事处罚范围极度扩张。[3]但是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理论现阶段仍然是以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为通说,其不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仅从结果无价值理论出发来否定犯罪预备可罚性显然是片面的,此外从刑事政策角度来解读犯罪预备的处罚效果,并不一定会导致刑罚处罚范围的无限制扩张,因为我国关于犯罪应受刑法处罚的认定不是单一的机械的,而是在以犯罪构成、社会危害性程度分析(例如刑法十三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坦白自首立功等刑法裁量制度方面对行为人是否进行刑法处罚加以综合立体化的评价考量。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犯罪预备处罚进行限缩而不是全盘否定。
对于以梁根林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的犯罪预备不具备可罚性是因为犯罪预备行为的终点,即“着手行为”难以界定,犯罪预备的构成要件难以厘清,笔者认为这些只是犯罪构成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并不能构成否定其可罚性的根据。因为如果“着手行为”难以界定就全盘否认犯罪预备的话,那犯罪未遂也要被否定,因为“着手”是犯罪预备的终点,但同时也是犯罪未遂的起点。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再者,如果因为犯罪预备行为的要件难以厘清我们就将其否定,那么试问在遇到其他问题难以厘清时我们又当作何选择?另有学者指出,预备行为不被处罚作为一项原则,其理由有三:缺乏犯罪的内容;犯罪的意思证明困难;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4]315这确实需要我们在分析完善犯罪预备理论的时候加以探讨,但并不能全盘否认预备犯的可罚性。
(二) 当前关于犯罪预备的立法模式类型
当前理论界关于犯罪预备的立法模式,或者说是关于犯罪预备处罚范围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不处罚、普遍处罚、例外处罚。
1.不处罚
犯罪预备不处罚原则是指无论是刑法总则还是刑法分则,对于犯罪预备行为都不做处罚规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从形式古典学派倡导的客观主义出发的。他们认为,刑法处罚的行为应当是客观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具有社会现实危害的行为,或者切实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行为。而犯罪预备行为只是为了犯罪创造便利条件的行为,这种行为一方面不具有对刑法保护的法益现实的直接的侵害,不能引起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结果;另一方面准备行为本身也不符合刑法对某一犯罪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因为犯罪预备行为不具备可罚性与要件相统一的要求,对于尚不明确的行为不应给予处罚。1810年《法国刑法典》对犯罪预备行为采取的就是不予处罚的立法例,还有1940年《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典》,1954年《格陵兰刑法典》,1968年《意大利刑法典》以及1973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等。[5]19笔者认为对于犯罪预备行为一律不予处罚显然容易放纵犯罪,虽然预备行为没有直接侵害到法益,但是并不排除个别犯罪的预备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险性和主观恶性,如果不予处罚的话,则往往会按照其自身的行为惯性,紧接着就发生严重的犯罪行为,因而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2.普遍处罚
犯罪预备的普遍处罚原则即法律规定犯罪预备都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例如我国刑法第二十二条对于预备犯应到受到刑罚处罚的规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从主观主义的角度出发,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再犯可能性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行为只是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征表,行为自身并不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本依据。犯罪预备行为完全能够表现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那么犯罪预备行为就与犯罪行为或者说是犯罪既遂行为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采取这种处罚模式的立法例主要有苏俄、我国以及蒙古、朝鲜等国。例如 1924年《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基本原则》与1960年《苏俄刑法典》都规定,无论是犯罪的预备行为还是未遂行为都要负担刑事责任。1958年《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预备犯罪均应受到惩罚。1960年《苏俄刑法典》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于预备犯罪和犯罪未遂的行为,应依照本法典分则规定这种犯罪责任的条款处罚。”1950年《朝鲜刑法典》也做出了类似规定。[6]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模式虽然承认了犯罪预备性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危害性或法益侵犯的危险性,但是对于预备行为不加区分的全部认为是具有刑法可罚性的无疑会引发诸多问题。例如前文所列举的,在证明行为人主观意图上的困难性,假设行为实际上是为了杀人而购买毒鼠强、农药或者菜刀,但是单纯的购买行为如何体现出其杀人的意图呢?难道要只凭借行为人自身的口供?全盘肯定犯罪预备的可罚性未免会造成刑罚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严重影响刑法保护自由与人权的目的实现。
3.例外处罚
例外处罚的原则是指原则上对犯罪预备行为不予处罚,只对法律明确规定的、严重的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处罚。这种类似于折中对待犯罪预备的理论无疑既满足了保护法益实现刑法目的需要,同时又不会不当地扩大刑罚的处罚范围。而在立法实践中,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就是此种立法例。例如日本就规定了内乱预备罪、外患预备罪、私战预备罪、防火预备罪、准备伪造货币罪、杀人预备罪、勒索赎金目的的绑架等预备罪、抢劫预备罪等犯罪类型。[7]2721953年《韩国刑法典》规定:“犯罪的阴谋或者预备行为未达到着手实行阶段,不予处罚。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不在此限。”随后在分则中对三十三种犯罪规定了其预备行为应当处罚。德国刑法典规定处罚预备行为的犯罪仅有第83条第1款规定针对联邦的叛乱罪等5种。[8]74笔者是支持此种观点的,因为“法律不规定和处理过于轻微的事项,相反,只是规定和处理较为重大的事项。”[9]98普遍处罚原则会扩大犯罪预备的处罚范围,对于那些实行可能性不大,侵犯法益危险不直接的行为来说无疑过于严苛。而不处罚原则对于那些危害性相对较大的预备行为无疑是一种放纵。综合分析考量,还是在拿捏一个度的问题。当然这里就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什么样的危险程度的预备行为应当处罚?哪些犯罪的哪些预备行为应当处罚?如何在纷繁复杂、浩如烟海的各种不同罪名中判定出哪些危害严重?有学者提出行为对应法定刑在十年及十年以上的犯罪的预备行为应当受刑罚处罚,具体标准有待商榷。
二、预备犯与犯罪预备等相似概念的区分
犯罪预备理论领域内的几个相似概念,主要有:犯罪预备阶段、犯罪预备行为、犯罪预备、犯罪预备状态、预备犯。这几个概念名词看起来非常具有相似性和迷惑性,似乎是具有同样的意思,但其实不然。对于这几个概念的界定区分是研究探讨犯罪预备理论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可忽视。笔者仅谈谈自己的理解,以期对犯罪预备理论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犯罪预备阶段与犯罪预备行为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犯罪预备阶段,这是探讨犯罪预备理论具体含义的前提性概念,它是与犯罪实行阶段相对应的同一位阶概念。起点是开始为犯罪创造便利条件,重点是着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符合犯罪构成具体要件的实行行为。而犯罪预备行为与犯罪预备则一般被认为是相同的概念,其强调的都是为了犯罪创造便利条件的行为本身。就像我国刑法规定的那样,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当然也可以说是犯罪预备行为。我国刑法对于犯罪预备行为的界定属于举例解释,其实质就是为实施犯罪创造便利条件,而至于准备工具等都是为实施犯罪创造便利条件的具体表现形式。
(二)犯罪预备形态与预备犯
犯罪预备状态与预备犯的概念是相同的,犯罪预备状态是作为犯罪停止形态的一种类型而存在的。它与犯罪未遂状态、犯罪中止状态、犯罪既遂状态属于同一位阶的概念,有时候也会简略地称之为犯罪预备,当然这个时候具体指的是犯罪预备行为还是犯罪预备状态就要结合前后语境进行判断区分了。预备犯就是指的犯罪预备状态、或者称之为犯罪预备形态,是犯罪预备行为在犯罪预备的阶段因为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停止下来,固定下来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就像我国刑法规定的: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预备犯的意思主要倾向于经过分析认定,确定实施犯罪预备行为的行为人应当承担的具体刑事责任,即要使人对某种犯罪的预备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确实地查明犯罪构成的客体、主体、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我们可以将预备犯具体地定义为:出于实现某种犯罪的目的,为完成犯罪创造便利条件,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至于着手实行犯罪的行为。我们这里打一个通俗浅显的比方来区分上述概念:假设犯罪是一个速冻食品的生产过程,那么首先它分为三个阶段:原材料的配备、食品的加工烹饪制作、成品的速冻包装。这三个阶段对应的就是犯罪预备阶段、实行阶段、完成阶段,是一个阶段性过程。而犯罪预备或者犯罪预备行为着重指的是在为此种食品准备原材料的行为,例如购买原材料、清洗切割承重等行为,此时预备行为并没有确定会停止下来,不出意外的话还会按照既定的方向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及包装成型。而犯罪预备形态或预备犯指的是因为某些原因,例如工厂停电、被查封、倒闭等,致使在准备原材料阶段停了下来,不再继续生产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查找原因进行追责了,换句话说就是预备犯要承担刑事责任了。
三、犯罪预备的要件
(一)犯罪预备构成要件的简述
构成犯罪预备有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第一,必须是出于实现某种犯罪的目的。所以预备犯只能是故意犯,而且其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如果出于间接故意或过失,则不可能构成预备犯。第二,实施了为完成犯罪创造便利条件的行为,即犯罪的准备行为。至于准备行为的具体方式则是各种各样的,但它们都是实现犯罪意图的积极活动,我国立法主要规定了两类:准备工具与创造条件。所谓犯罪工具,是指犯罪分子进行犯罪活动所用的一切器械物品。其中包括:用以杀伤被害人或者排除被害人反抗的器械物品,如枪弹、刀棒、毒药、绳索等;用以破坏、分离犯罪对象物品或者破坏、排除犯罪障碍物的器械物品,如钳剪、刀斧、锯锉、爆炸物等;用以掩护犯罪实施或者湮灭罪证的物品,如作案时戴的面罩、作案后灭迹用的化学药品等。此外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犯罪工具本身的危害性和复杂性可以反映出预备行为的危害程度。准备犯罪工具,是指制造犯罪工具、寻求犯罪工具及加工犯罪工具使之适合于犯罪的需要。为实施犯罪制造条件,如为实施犯罪事先调查犯罪场所、时机和被害人行踪。还有准备实施犯罪的手段,例如为实施入户盗窃而事先练习爬楼入窗技术;追踪被害人、守候被害人的到来或者进行其他接近被害人、接近犯罪对象物品的行为等等。第三,未至于着手实行犯罪,即行为停留于犯罪预备的阶段。如果行为人经过犯罪预备转入着手实行,随后或者未遂或者既遂,犯罪预备即被后者所吸收,就不存在预备犯的问题。第四,未着手实施犯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即由于不以行为人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原因如经告发被逮捕,而未至于着手实行,才可构成预备犯。如果由于行为人自动停止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而未至于着手实行,在我国刑法看来,构成犯罪中止,不成立预备犯。
(二)犯罪预备构成要件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必须是出于实现某种具体的犯罪目的,也即“为了犯罪”。为了犯罪一方面表明行为人具有实施某种具体犯罪的直接故意。假如行为人在街上闲逛看到有一摊位卖的三棱刮刀不错,非常锋利,想着自己将来干个啥“大事”可能会用得到,就买下来。这就不是犯罪预备行为,因为没有具体的犯罪故意。其次行为人认识到其准备行为是为了直接服务于自己意图实施的犯罪实行行为的。例如行为人感情受挫想要自杀,就买了剧毒农药,但是回来后经过考虑又放弃了自杀的打算,认为对方甩了自己才该死,于是去对方家里投毒。那么这个买农药的行为就不属于犯罪预备。其中还强调预备行为为实行行为服务的直接性,例如某甲为了将来购买枪械炸药杀人努力打工积攒金钱,努力打工的行为就不能说是杀人这一实行行为的预备行为。张明楷教授认为“为了犯罪”应当理解为“为了实行犯罪”。 他认为这样理解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处理犯罪预备,正确认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正确认定犯罪预备行为的范围。[10]我们这里谈到的两个问题可以概括为具体性和直接性,即具体的犯罪故意和直接为犯罪实行行为服务。注意这两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限制犯罪预备的处罚范围,防止其不当扩大。
四、立法模式建议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犯罪预备的规定是普遍处罚原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面对大量的犯罪预备行为,如果完全按照法律规定一一甄别认定的话无疑给本就有限的司法资源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在进行认定中发现其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又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与其规定普遍处罚原则而实践中不能完全彻底执行,导致刑法权威受到侵蚀,还不如从实际出发确立原则上不处罚,只对例外情况进行处罚的模式。具体的操作方法有很多,但是笔者提倡参考过失犯罪的立法模式,在总则与分则中共同对犯罪预备加以规定。在刑法总则中规定犯罪预备行为的定义,例如现行的“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然后参考刑法第十五条对于过失犯罪的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将犯罪预备规定为“犯罪预备行为,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然后在分则中甄别具体的罪名,在具体的罪名中规定其预备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或者像日本那样将某种犯罪的预备行为单独规定成一个罪名,例如抢劫预备罪等。
结语
通过对于犯罪预备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探析,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犯罪预备行为均具有可罚性,只有那些严重的犯罪预备行为才具有可罚性。我国现存的关于犯罪预备普遍处罚原则存在诸多问题,其根本的解决办法应当是进行立法的重构,分别从刑法总则与分则综合规定犯罪预备的例外处罚原则。而犯罪预备阶段是犯罪预备行为存在的前提性概念,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犯罪预备形态或预备犯则是符合犯罪构成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是在犯罪预备阶段因为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停止下来的犯罪停止形态。认定预备犯需要注意其在主观上应当具有实施某种具体犯罪目的的主观故意以及其行为直接为犯罪实行行为服务的特性。
参考文献:
[1] 肖扬.中国刑法学 [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7.
[2] 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3] 梁根林.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的困境与突围——《刑法》第 22 条的解读与重构[J].中国法学,2011(2):156-176.
[4] 马克昌.刑法理论探索[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5] 朱华荣.各国刑法比较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6] 王志祥,郭健.论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J].政治与法律,2005(2):83-87.
[7] 大谷实.刑法总论[M]. 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8]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9]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 张明楷.犯罪预备中的“为了犯罪”[J].法学杂志,1998(1):7-8.
责任编辑:师连枝
An Inquiry into Problems under a Crime in Preparation
YUAN Xiang-jing
(Criminal Justice Colleg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Article 22 in China’s “criminal law” stipulates a crime in preparation should be punished. This principle of universal punishment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troversy in the field of practice and theor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punishment needs improvement in the legal basi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Legislative practice of States on crime prepared has three types: the universal punishment, punishment exception and no punishment. The real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 crime in preparation is to reconstruct preparatory legislation, establishing exceptions to the principle of punishment, correctly distinguish similar concepts about a crime in preparation, clarifying criminal preliminary issues and investigate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criminal preparation in depth, properly handling the issue of criminal preparation.
Key words:crime preparation; punishable; universal punishment; exception punishment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16)01-0135-05
作者简介:袁祥境(1994—),男,新疆阿克苏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收稿日期:2015-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