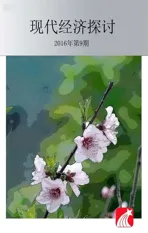论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之关系
2016-02-28张旋
张旋
论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之关系
张旋
内容提要:资本逻辑以“增殖”为唯一目的,强制推动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不断地解构与其密切相关的生态逻辑。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资本逻辑从时间和空间上造成生态逻辑的断裂,决定了恶劣的生产环境。在社会生活过程中,资本增殖逻辑对市场空间的构建导致了异化的消费生活方式和贫乏的生活环境。此外,经济危机和军事生活造成生态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只有正确理解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以社会主义的力量掌控资本,才能跳出“资本增殖”的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健康发展。
资本逻辑 生态逻辑 人与自然 社会主义
一、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以凝结在物之上的“人-人”的关系出现,这种“人-人”的关系表现为“资本家拥有作为物化劳动结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通过这个所有权拥有了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从而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最大化地转化为资本,作为客观的力量支配工人,由此形成了正反馈循环圈,形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化劳动的“资本逻辑”(鲁品越,2015)。资本逻辑一旦形成,便成为主导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刚性规律。
生态逻辑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维持能量流动的平衡和稳定的逻辑。生态系统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的有机物和无机物,每一个个体都在既定的位置上发挥着自身的作用。为了更好地适应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再生产,有机体之间通过不断地竞争和演变达到这一目的。因此,生态逻辑可以归纳为“人-自然”系统追求生存和发展的逻辑。
在西方主流的生态思潮中,对人的研究属于社会问题范畴,对自然的研究属于生态问题范畴,两者相互分离,最终导致“人”成为生态危机的指责对象。纵观历史长河,生态危机并非伴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产生。究其原因,西方学者普遍继承了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将人与自然简单地通约成抽象的人与纯粹的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忽视了现实的社会基础,使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相脱离,进一步使自身的理论脱离现实成为遥不可及的道德幻象。
正确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将“人-自然”的关系理解成为“‘人-人’-‘人-自然’”的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物化劳动是理解两者关系的关键。劳动包括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一方面,物化劳动中的具体劳动形成了“人-自然”的物质变换,通过“感性对象性活动”,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然事物之上,构成了改造后“第二自然”,创造了作为使用价值的物质载体;另一方面,在抽象劳动过程中形成“人-人”的关系即资本的生产关系,这一关系通过物的承载体现出来,从而形成支配生产的强大力量,以交换价值的积累为目的推动社会生产。因此,代表“人-人”的资本逻辑与代表“人-自然”的生态逻辑不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逻辑,在紧密关联中对抗。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像它以前的所有生产过程一样,也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但是,这些物质条件同时也是各个个人在他们的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承担者”。
由此来看,生态问题并非由静止的“人”对“自然”的对抗所造成,而是特定的生产关系中生成的结果,资本家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生态逻辑的不断解构,“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不可持续的特征,世界被降格成资本逻辑,并且世界的每一寸角落都成为为未来积累过程服务的资料”(福斯特,2010)。
二、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
马克思曾引用威廉·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说明劳动和自然作为创造财富的两个重要因素。但是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中,资本增殖是生产活动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抽象劳动往往被视为创造财富的唯一因素,自然则被作为外部因素所忽视。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格格不入,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生态逻辑进行解构,并以此作为自我成长的基础,形成强大的主宰力量和生产的正反馈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了生态逻辑的分崩离析。
1.资本逻辑对生态逻辑的空间解构
资本的生产方式具有地域化的集聚性,从而造成了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生态断裂,破坏了生态空间的水平和垂直结构。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以维持生计,大量的农业人口流入城市。“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近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乡村人口向城市单向输入造成两者之间物质变换断裂:在城市中,拥挤的人口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成为城市生活环境最大污染源;在乡村中,反复耕种的农业用地营养奇缺,天然肥料的流失只能靠化工肥料来补偿。化工肥料的生产既满足了工业资本积累的需求,又弥补了农业土地的营养,但这种方式并不能完美地解决生态系统天然水平结构的破坏,更进一步地破坏相互依赖的垂直生存结构。
密集的生产方式使资本积累的效率最大化,但生产的集聚性和资本积累的无限度与生态资源分布的广泛性和有限性相矛盾。马不停蹄的生产方式既需要大量生态资源源源不断供给,毫无节制的大量集中开采造成生态资源的耗竭,又不断地制造着严重的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使生态系统不堪重负。这种极具危害性的污染进一步随着生态系统的循环性入侵世界各个角落,对生物和人的健康和生存造成了极大威胁。
“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伴随着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工农和城乡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扩大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断裂。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发达国家找到了一石二鸟的妙策——将生态危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输出既满足了利用廉价劳动力达到更多的资本积累的目的,又保护了本国的生态环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国际话语权树立“绿色壁垒”,其严格并繁琐的检测和评估等环节不仅增加了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经济成本,更造成无端的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面对生存和发展的重重压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不得不通过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另一方面作为巨大生产国而遭受着严重的生态苦难。
2.资本逻辑对生态逻辑的时间解构
资本积累的爆发性不容小觑,仅仅是空间上的集聚并不能满足无限积累的要求,资本积累的短期效益性打破生态平衡的长期稳定性,以“黑洞”的方式通过对未来利益和资源的透支实现资本积聚的最大化。
为实现最高效率的资本积累,资本的生产方式不仅透支未来的剩余价值,从而透支人的自然力,并且将目光牢牢锁定“效用”之上,不断透支生态系统的生命力。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披露:“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资本的生产方式始终以“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作为目的,而为了达到这种短期性积累对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所造成的影响则完全被无视,导致了自然资源的快速耗竭和污染的大量积聚。
与资本积累的短期性相对,整个生态系统资源的再生产具有长期性,两者之间的对立使生态资源丧失再生的可能。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包含比较短的劳动时间),从而其漫长的资本周转期间,使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资本的正反馈式的扩张打破了生态系统的负反馈式常态,使整个生态系统陷入正反馈的“恶”的积累模式当中,沦落为资本自我实现的垫脚石。资本的“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五百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福斯特,2006)。如果这种生产模式长期得以进行,最终“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大卫·格里芬,2004)。
3.资本逻辑中的生产环境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生产的外部环境的非可持续性,同样也决定了恶劣的内部生产环境,拥挤不堪和简陋的环境对工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了更直接的伤害。
从资本的生产条件来看,资本逻辑仅仅追逐增殖的唯一目的,将自然资源视为可以任意索取和处理的外部因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不费分文的自然资源由于产权的不明晰,导致了人们的争相开发和对治理的无视,带来了“公地悲剧”的结局。对于这种现象,经济学家们提出产权明晰化的方法,试图根据资源的稀缺性收费缓解资源面临耗竭的问题,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地加速了生态系统的崩溃。究其原因,自然资源的价值并非取决于资源的稀缺性,而是取决于人类的劳动。产权明晰化成为资源拥有者分割剩余价值的尚方宝剑,越是昂贵的资源越能满足资本积累的欲望。这些资源对于拥有者来说,始终“不费分文”,而真正为资源“买单”的是需要更加卖力劳动的消费者,为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而成为资本的奴仆,进一步地破坏整个生态系统。
就资本的生产环境而言,为实现最大化扩张,要求剩余价值积累的“高效性”,这必然需要奉行“禁欲主义”精神,根据“物”的要求创造生产环境,以最“朴素”的条件创造具有巨大价值的“奢华”产品。为最大程度地节约不变资本和提高生产效率,大量的工人被关在狭小的“生产盒子”里,在“朴素”的环境中挥汗如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像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来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社会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难道不对吗?”
资本所履行的“节约”原则和不完备的设施使工人们用生命作赌注,换取微薄的酬劳,缺少安全设备的生产过程随时可能造成群体的生产事故,防护措施的匮乏使“职业病”成为高频现象。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资本逻辑主导的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
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无限资本积累如永动机般不停地生产,生产所创造的交换价值则需要相应的市场空间去实现。数不胜数的产品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刺激消费完成“社会的物质变换”,异化劳动进一步产生了异化消费,构成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特殊生活方式。
1.异化消费
面对资本积累最大化的要求,资本逻辑需要不断地创造基本需求以外的新的市场空间。各种标新立异的产品以差异性贴合人们的需要,但资本逻辑并不满足于被动地迎合消费者的需要,而是以异化的力量不断地创造和更新消费者的需要。
在各种广告和促销手段的渲染下,人们的需求不再基于人的生存需要本身,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基于资本增殖的“虚假需求”。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连同自身的需求一起被物化,“身体不是封闭的未知实体,而是一个相对的‘物’,在多重过程的时空之流被创造出来,被限制、维持并最终消融在其中”(大卫·哈维,2006)。铺天盖地的广告以声色俱佳的手法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手段不断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需要”和“共鸣”,商品在其“物”性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景观”的幻象,人们对这一“景观”趋之若鹜,陷入资本逻辑的魔网中。
资本逻辑从生产领域到生活领域的扩张实现了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双重统治,它所利用的不仅是人们对“需求”的满足,更是对“权力”的追求。人们通过消费生活寻求在生产过程中丧失的自我,“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的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它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马尔库塞,2008),人们试图通过消费的方式追逐权力,最终又为了这一权力而陷入被支配的怪圈,成为资本逻辑解构生态逻辑的刽子手。
2.生活环境
遵从资本逻辑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始终以“资本增殖”为发展的唯一目标,由此导致贫富悬殊的现实生活,体现为劳动者的“贫”和资本家的“富”、发展中国家的“贫”和发达国家的“富”、生态环境的“贫”和资本积累的“富”的鲜明对比。
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为维持生存而出卖劳动力,在资本机器的压榨下不仅处于恶劣的生产环境中,同样因为贫困而生活于脏乱的生活环境中。恩格斯曾描述工人们的生活状况:“他们住的房子都是在最破落最肮脏的大杂院和街道里,通常总是在地下室中”,这样的生活状态仍然维持至今。除居住条件之外,低廉的食品、服装、生活资料等等往往为了降低成本而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其产品都对健康存在一定的危害,而价格高昂的有机产品只能使普通人望而却步。
随着全球化经济和生态危机的转移,贫与富之间生活环境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生态差距。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产品的生产基地,厂房林立、马不停蹄地生产和简陋的生产条件造成了大量自然资源的快速减少和严重的环境污染。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于2016年5月发布了一系列的报告,指出全球死亡人数的1/4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占有极大的比例。其中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发展中国家占61%,因饮水不洁和缺乏卫生设施而导致死亡的人数占97%。在追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资本逻辑所引导的发展方式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生存的两难选择。
资本逻辑所宰割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生态问题并不仅仅是“自然”承担的结果。“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当生态逻辑遭受资本逻辑的非难,人的生存和发展本身也随着这一“无机身体”的受创而悲歌四起。
3.经济危机与生态环境
资本追求扩张最大化的逻辑,要求极尽所能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积累,从而产生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悖论。一方面,资本逻辑要求生产最大化,并需要相对应的消费最大化以实现资本的循环;另一方面,为最大可能地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断压低工人的工资,并极力使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形成生产的无限性与购买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当生产超过市场的承受力,无力购买的产品大量堆积引起资本积累链条的断裂,从而引发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对社会各方面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生产过剩和销售停滞极大地浪费了社会财富和生态资源。在资本增殖的逻辑中,人并非发展的目的,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大量贫困失业人口面临最基本的生存危机,资本家却将大量的产品和生产基地无情地销毁。20世纪70年代的一场经济危机中,美国加州的垄断组织于两天内倾倒了38000多加仑的牛奶,该行为在经济危机中数不胜数,使经济危机进一步发展成为人与自然的生存危机。
面对紧张的资金和财政,环境治理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希腊学者克里斯特·乌拉克斯指出,经济危机期间,经济拮据的欧洲人民无法支付昂贵的供暖系统,靠非法砍伐树木度过寒冷的冬天,而政府对此行为熟视无睹。资金的紧缩使用于环境保护的那部分成为妄谈,所有的环境法都面临实施困难的境地,生产领域不再参与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并中断各项控制污染的措施。
为缓解经济危机,不断向外扩张并寻求市场成为发达国家的选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更加深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世界秩序的建立成为权力争夺的舞台,甚至因此引起战争而造成人与自然更沉重的灾难。
4.军事生活与生态环境
资本作为物化的社会关系,掌握资本便掌握了支配他人的权力,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经济资源瓜分世界,建立起发达国家掌握话语权的世界经济体系。为维护这一霸权体系并追求更多的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命脉成为关键所在,欲达到这一目的,军事战争往往是强有力的手段。恩格斯曾指出“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
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所制造的武器,能够在短时间内对敌方造成致命的伤害,但它摧毁的不仅是敌方力量,同时也是人类的家园。生态环境在战争中所受的伤害不只是肉眼可见的残垣断壁,空袭、生化武器和各类爆炸物的使用造成地表的严重受损,化工厂的破坏而引起的污染以及武器使用之后的放射性物质对水、空气、土壤等等造成长期的危害。战争过程中大量的伤亡极易引发瘟疫,对战后重建和人的生存与健康极为有害。以海湾战争为例,由于贫铀弹的使用,其残留物的辐射长期存在于环境当中,造成战后伊拉克白血病的患病率和婴儿先天缺陷率的大幅度上升。此外,大量的化工和炼油厂的摧毁造成化学污染物和石油的泄漏,引发了世界上最严重的海洋污染事件,破坏大幅海域和海洋生态系统。
为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先进武器的研究和掌握尤为重要,各国对核武器的研究和应用趋之若鹜。核武器对大范围的生物产生短期、长期和遗传性的核辐射效应,实验过程以及核废料的泄露对整个生态系统同样具有致命的威胁。自《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来,一些国家将核试验转移到地下,导致了水源和土壤的污染,引发地表塌陷甚至地震,其“冒顶”事件对地上和周边的环境产生巨大的危害。
资本逻辑不仅主导非暴力的行为,同时也引发暴力行为,为达到资本增殖和扩大权力的目的,不择手段的实践方式不断违背生态逻辑,使整个生态系统以千疮百孔的姿态成为资本圣殿中的祭奠品。
四、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统一
生态危机的根源始于资本逻辑的刚性力量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宰制,使人对自然的关系被人支配人的社会关系所决定。因此,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各种生态学改良方式并非解决生态危机的良方,正如“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力”,这种“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性转变”,将生态逻辑从资本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实现资本逻辑和生态逻辑的统一并非使任何一方独占鳌头,人与人的关系的翻转并不意味着对资本进行简单否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绝不是真正的占有”。必须利用更强大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力量管制和约束资本的无序扩张,达到使资本为人、自然、社会的发展服务的目的。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突破资本逻辑解构生态逻辑之希望所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根本区别,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政府机构,“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资本家”,它的目的始终围绕“资本”。与之相反,社会主义以“人”为出发点,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它的主体地位决定了资本发展的有偿性和有序性,能够跳出资本逻辑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再生产。因此,在社会主义力量这一强大的优势下,应当摒弃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旧的发展模式,持之以人民福祉的目标,辅之以先进的绿色科技和文化,明确“资本”与“生态”发展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将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结合起来,使两者为彼此不断地开拓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利用公共力量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合理调整和监督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最终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统一。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马克思著:《资本论》第1卷、第2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7.鲁品越著:《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8.[美]大卫·格里芬著,马季芳译:《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9.[英]大卫·哈维著,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德]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11.[美]约翰·福斯特著,耿建新等译:《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12.[美]布雷特·克拉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孙要良译:《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吴群]
F032
A
1009-2382(2016)09-0045-05
张旋,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系博士生(上海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