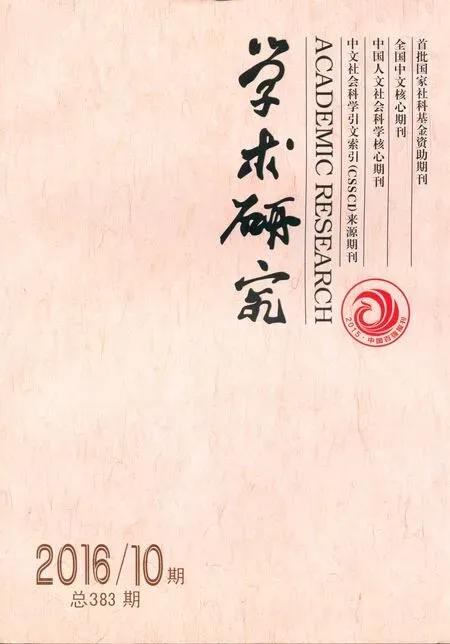论黄遵宪的孔学观——兼与康有为相比较
2016-02-27宋德华
宋德华
论黄遵宪的孔学观——兼与康有为相比较
宋德华
黄遵宪的孔学观既深受康有为孔子改制说的影响,又具有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其对革新孔学极表赞成,力求使之发扬光大;在重新“演孔”的基础上,以“时中”作为孔学的根本特征,彰显其变通性和包容性。与此同时,又抱持审慎的学术态度,注重证据,尊重历史,反对一切将孔学宗教化的做法,坚守孔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并主张仿效西方,分离政教政学,以期学之盛和政之善。这些主张与康有为之说差异甚多,鲜明呈现了维新思潮平实而深刻的另一面。
黄遵宪孔学观康有为孔子改制“圣在时中”
在活跃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家中,康有为的孔学论最为著名。受康及其弟子梁启超的影响,黄遵宪对孔学的许多问题也做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孔学观。对于了解黄遵宪政治文化思想的特质,及区分维新思想不同流派的差别,其孔学观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在此方面,学界似关注甚少,值得加以探究。①关于黄遵宪研究的成果,可参见郑海麟:《黄遵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左鹏军:《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论丛》(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及其他相关论文。这些论著对黄遵宪的生平事迹、政治和文化思想、与日本的交往、对文学的贡献等专题,皆有较为系统深入的阐述,但对其孔学观尚少涉及,留下了一个有待发掘和拓展的重要课题。
一、对孔子改制说的信服与质疑
孔子改制本为今文经学的基本观念之一,意谓孔子在创立儒学的过程中,并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按照自己的理想,重建了损益三代、因时而变的礼仪制度。[1]对此改制之义,康有为根据维新变法的需要,作了极大的发挥,将其由一个经学的学术观点,变成了一个重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政治思想主题。经过康的改造,改制在孔学中占据了最核心的地位,全部孔学都以改制为宗旨,孔子也因而成为改制最权威的宗师。更重要的是,以改制的名义,康有为完全使自己的变革思想与孔学融为一体,所谓孔子改制成为康学得以独树一帜的标志语,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康有为变法论的代名词。②为了论证孔子改制,康有为专门撰写了《孔子改制考》,在其他许多著述中,孔子改制也是康极力宣扬的思想主张。关于康有为孔子改制说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参见拙著:《岭南维新思想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3-241页。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提出后,在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的反响非常强烈。除了康门弟子与其师保持一致,并大力加以宣扬外,其他赞同者甚少。守旧派固然对改制说大肆抨击,而赞成变法之人也多持反对态度,如俞樾、孙诒让、翁同龢、陈宝箴等都是如此。他们之所以也不认可改制说,主要原因在于康有为对孔学的解读走得太远,思想过新过激,学术过偏过异,超出了一般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底线。
黄遵宪是康门弟子外,对孔子改制说少有的赞同者之一。他这样写道:“吾年十六七始从事于学,谓宋人之义理、汉人之考据,均非孔门之学。……而其时于孔子之道,实望而未之见,茫乎未有知也。及闻陋宋学、斥歆学、鄙荀学之论,则大服,然其中亦略有异同。”[2]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在求学之始,黄遵宪对占统治地位的宋学、汉学就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并非孔门之学,这可视为他能够很快接受康有为孔子改制说的思想基础。不过对究竟什么是孔子之道,他当时还无从知晓,直到听闻康梁等人对宋学、歆学和荀学的批驳,才恍然大悟,深感信服。但他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也不是完全赞同,而是有同有异。这种既“大服”而又“略有异同”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对“孔教复原”的论析之上。
所谓“孔教复原”,名义上是要恢复孔教的原貌,其实质则是重新解释和革新孔学。①“孔教复原”是梁启超的提法,康有为则称之为“发明孔子之学”。参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7页;康有为:《答朱蓉生书》(1891年),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5页。这一点,可说是孔子改制说的真正价值所在。黄遵宪对此看得很清楚,明确表示“吾所心佩者,在孔教复原,耶之路得,释之龙树,鼎足而三矣。儒教不灭,此说终大明于世,断可知也”。[3]黄遵宪将“孔教复原”比之为马丁·路德对基督教的改革,龙树对佛教的创新,断言只要儒教还在,“复原”之说就终将为世人所公认。可见对于改制说的根本精神,黄遵宪一开始就把握得很准,并在他人满怀疑惧之时,以长远的眼光对其抱有坚定的信心。“复原”后的孔学,亦即康有为“发明孔子之道”的“大纲”,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总括为六条,即进步而非保守、兼爱而非独善、世界而非国别、平等而非督制、强立而非巽懦、重魂而非爱身等六大“主义”。[4]这既可视为梁启超对康有为所传授的孔教的转述,也可以说其中亦包括了他对今日应有之孔教的解读。在此六大主义的基础上,黄遵宪又增加了两条“曰博大主义,非高尚主义;变动主义,非执一主义”。[5]黄遵宪所作的增补,应该说相当重要。梁提出的六条,都还只是孔学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而增补的两条,则体现了孔学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特征。“博大”就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而不是一枝独秀、孤芳自赏;“变动”就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而不是一成不变、万世独尊。这是黄遵宪多年出使在外,具有了世界文化的眼界之后,所获得的真切感受。②在稍晚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黄遵宪对“以保国粹为主义”的主张有所商榷,认为:“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距,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国力之弱,至于此极,吾非不虑他人之搀而夺之也。吾有所恃,恃四千年之历史,恃四百兆人之语言风俗,恃一圣人及十数名达之学识也。”参见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9月),《黄遵宪全集》上册,第433页。这些看法可视为对“博大”和“变动”两主义的注脚。
黄遵宪还表示,在六大主义中,他对“强立主义,非巽懦主义”这条最为在意,“向读此条,深为敬服。意谓孔子没后二千馀年,所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者,惟此足以当之。但所恨引证尚少,其重魂主义一条尤鲜依据,能张皇其说否”?[6]也就是说,对于孔子那些业已失传的学说的发掘,只有“强立”一条才最为名副其实。黄遵宪如此重视“强立主义”,与他长期作为外交官同列强打交道有密切关系,这一经历使他对中国国力的衰落和民族精神的柔弱有着切肤之痛。他之所以力主维新变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强国家、强民族,这是其维新思想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尽管心仪孔教“复原”,黄遵宪还是抱持审慎的学者态度(这与康有为大不相同)。他深感“强立主义”“引证尚少”,而“重魂主义”“尤鲜依据”,其他各条如何,他没有评论,想来也会存在能否确证的问题。①从梁启超“复原”孔教的六大主义,到黄遵宪增补的两大主义,都是后人借孔教之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与原来的孔教并不是一回事,或者只有某些形式上的、作为思想资源的联系。因此,要想充分证明这些主义的确古已有之,本来就属于不可能做到的事。梁启超在写完《南海康先生传》之后,也逐渐跳出孔子改制说的窠臼,不再谈孔教“复原”。事实上,康有为为了宣扬孔子改制说,在学术上有很多不顾史实、只凭主观的“武断”之处。梁启超对此作过直截了当的批评,这也是学界公认的看法。他希望梁启超能担当起“张皇其说”的任务,也就是要梁找到更多的历史“依据”,对“强立”、“重魂”等孔教的主义作出详尽的证明和阐释(此时的梁启超正在摆脱对孔教的依附,当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不仅如此,黄遵宪还对改制说直接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质疑,这就是不相信六经皆孔子自己所创。他认为,其他各教皆由旧创新,其新教完全脱离旧教而自立 ,“耶稣出而变摩西之说,释迦兴而变婆罗门之说,摩诃末兴而变摩尼之说,皆从旧说中创新学,自立为教”,但孔子对前圣之说则多有传承,“于伏羲、文周之卦,尧舜之典,禹汤之谟诰,未尝废之也”。他直言:“此与改制之说不甚符。虽然,《公羊》改制之说吾信之,谓六经皆孔子自作,尧舜之圣为孔子托辞,吾不敢信也。”[7]
在经学史上,所谓“《公羊》改制之说”,只限于《春秋》一经,从公羊高到董仲舒、何休、刘逢禄等人一脉相承,皆宣称在《春秋》表面的文字中,隐含着需要特别解释的孔子的“微言大义”,至于“微言大义”究竟为何,每个人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康有为沿袭和利用了这一旧说,并添加了很多新论。即便如此,康有为也承认《春秋》仍有鲁史原本,至少从文本看,孔子所做的只是删改工作。《春秋》已然如此,如果要确证六经皆为孔子“自作”,尧舜等等皆为孔子“托辞”,揆诸史实,恐怕更难立论,②这大概是尊重历史、注重“证据”的黄遵宪“不敢信”的重要原因。
二、以“时中”作为孔学根本特征
黄遵宪虽然赞同康、梁以改制精神论孔,但并不满足于他们对孔学所作的“发明”或“复原”。为了“光大”孔学,他自己还有一个独特的“演孔”即重新阐释孔学的计划。在先后两封写给梁启超的信中,黄遵宪都谈到了这一点。前封信这样写道:“吾胸中有一孔子,其圣在时中。所以时中,在能用权;所以能权,在无适无莫,勿固勿我。无论何教,欲挟彼教之长以隘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正之拒之;无论何人,欲抉孔子之短以疑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解之驳之。吾欲著一书,曰《演孔》,以明此义,他日当再与公论定也。”③《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第20号,第51页。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1-292页。后封信又说:“吾所谓不喜旧学,范围太广,公纠正之,是也。实则所指者,为道咸以来二三巨子所称考据之学、义理之学、词章之学耳。六月中复公书中,有时中孔子,故欲取旧学而光大之也。……近方拟《演孔》一书,书凡十六篇,约万数千言,其包含甚广,未遂成书者,因其中有见之未真、审之未确者,尚待考求耳。今年尚能脱稿,必先驰乞公教,再布于世。”[8]
黄遵宪不仅拟定了《演孔》的书名,而且对将写的篇数、字数及大致脱稿的时间,均作了具体的预计,只因有“尚待考求”者,所以还“未遂成书”,可见他对如何“演孔”已思之甚熟。以黄的思想素养和学术功底,加上力求见之真、审之确的严谨态度,该书若能撰成,想必会成为极有价值和代表性的著作。可惜后来并无该书撰写情况的消息,不知因何故而中止。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尽管未见成书,从上述信中却能见到黄遵宪对孔子和孔学总体思想特征的高度概括,这就是“时中”二字。④“时中”是中国文化中非常古老的概念,基本的含义为合乎时宜、不偏不倚等等。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时中”的用意会有所不同。黄遵宪没有直接解释“时中”的含义,而是对何以能够“时中”,作了一个因果链接的说明。这就是要善于变通(“能用权”),才能达至“时中”,而善变的前提,又是要接人待物不分厚薄(“无适无莫”),论事言理不墨守成规、自以为是(“勿固勿我”);孔子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些,所以孔学既可包容其他一切教义的长处,自身又不存在任何不能澄清的疑点。这是黄遵宪对孔子和孔学所作的一个相当特殊的评价,可称之为“时中”新论。
对此“时中”新论所凸显的变通性和包容性,黄遵宪以先秦学术史的演变为据,围绕孔子与周公及儒教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述。在他看来,中国的强君权、弱民气,是从周朝开始的,“自周以后,尊崇君权,调柔民气,多设仪文阶级,以保一家之封建,致贻累世之文弱,召异族之欺凌者,实周公之过也。至周末而文胜之弊尽见矣。”为了纠正周朝的弊端过失,先秦诸子们纷纷而起,各自创立与“周道”、“周制”背道而驰的学说,却都有明显的缺陷,“于学术首唱反对者为老子,然老子有破坏而无建设。(黄遵宪原注:其所企慕者,乃在太古无为之治耳。)至墨子而尚同、尚贤,乃尽反周道,别立一宗矣。于政治首立异说者为管子,然管子多补苴而少更革。……至商鞅而教战教耕,乃尽废周制,而一扫刮绝矣”,他们“皆指周公为敌而迭攻之”,但都未处理好革新与继承的关系。只有孔子,对老子等四人取长补短(“介乎四子之间”),主张“通三统”、“张三世”,“于文献也有征,杞征宋(此处标点似应改为:于文献也,有征杞征宋——引者注)之言;于理之损益也,有继周之想;其于周公不必尽反,亦不必尽从……盖一协于时中而已。”[9]这就是说,孔子非常善于处理前代的文化遗产,既不全盘接纳,也不一概排斥,而是将继承与革新完美地结合起来,以“时中”的态度求得二者的统一。
在此基础上,黄遵宪对世人(包括康有为)将“儒术”等同于孔子道术的误解进行了考释,指出:“自周以后,始有儒称,实成周时庠序中教师之名耳。……其道在优柔和顺,以教民服从为主义,是周公创垂之教也。……若我孔子,则综九流、冠百家,不得以儒术限。(黄遵宪原注:儒乃孔子之履历,非孔子之道术,汉儒亦多未明白。……闻南海有儒为孔子所建国号之语。是亦见释迦之创佛教,[此逗号似应改为顿号——引者注]耶稣之创天主教、摩诃末之创回教,误以为儒教亦孔子所创也。)世以周孔并称,误矣!误矣!”[10]在此,黄遵宪提出了两个核心的论点:一是周公所创儒术局限于“优柔和顺”和“教民服从”,而孔子能取“九流”、“百家”之长,已超出儒术的范围,两者不是一回事;二是孔子并未另创儒教,只是继承和发展儒教,不能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创立相比附。这两个论点,分别说明孔子与前人的区别和联系,再次解读了“圣在时中”的内在涵义。
将黄遵宪的“演孔”与康有为的“发明孔子之学”相比,可看出两者既有共同之点,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同者在于他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阐释孔学的要义,以清除历代以来对孔学所作的种种曲解。为此,他们都具有对旧儒学的批判精神,都力图将自身的新学问新思想灌注融汇于孔学之中,也都在借助儒术独尊地位的同时,尽量使孔学变得理想化。在表达若干重要思想时,他们都同样借用着一些非常古老的概念(如“改制”、“三统三世”、“大同”等)。这种相同性,是他们得以同属维新思想家的重要基础。他们之间的不同,似乎表现得更加明显。首先,重构孔学的计划有大小之别。康有为“发明孔子之学”的设想是:“先辟伪经,以著孔子之真面目;次明孔子之改制,以见生民未有……以礼学、字学附之,以成一统;以七十子后学记续之,以见大宗。辑西汉以前之说为‘五经’之注,以存旧说,而为之经;然后发孔子微言大义,以为之纬。”[11]显然易见,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写作计划。①这一计划将政治与学术、孔子之旧与康有为之新紧密交织在一起,于庞大之外,更增添了复杂繁难性。康有为自己也承认这一计划“体裁洪博,义例渊微”,恐怕“汗青无日”,难以完成,抱着“成不成则天也” 的态度。参见康有为:《答朱蓉生书》(1891年),《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5页。相形之下,黄遵宪准备“演孔”的“万数千言”,就篇幅极为有限。其次,重构孔学的方式有宽窄之别。在康有为的计划中,不仅有辟伪经、明改制、阐发微言大义等凸显思想性的内容,还有汇编礼学、字学、七十子后学记及五经之注等学术性极强的工作,大有涵盖一切、包罗万象的气势,而黄遵宪的计划,似只偏重于对孔子思想学说精义的阐发,尽管他同时也非常注重进行学术上的考证。再次,重构孔学的结果有成与不成之别。按照计划,康有为陆续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及其他一系列“发明”孔子之道的著作,虽未完全实现初衷,亦已堪称宏富,蔚为大观,而黄遵宪出于某种原因,“演孔”终未成书。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构孔学的态度有偏激与审慎之别。康有为对“发明”孔学极为自信和自负,将其认知视为绝对化的真理,因此在以“改制”论孔之时,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往往不顾一切地颠覆旧说,别为新论,虽大获思想震动之效应,亦多有主观武断、牵强附会之弊。比较而言,黄遵宪的“演孔”要严谨得多。他虽然也对自己“胸中”之孔充满自信,却力求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尽量将新孔学建立在可靠可信的论证之上。正因如此,他以“时中”作为孔学的根本特征,这是一个既能变通又能包容、既有创新又有继承的孔子,与康有为因“改制”而独尊的孔子有很大的不同。①黄遵宪对梁启超提出要求说,如果将其论孔子“时中”之义的信函公开发表,须将“演孔”二字“藏起”, 因为这只是说给梁听,“非对普天下人语”,参见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9月),《黄遵宪全集》上册,第433页,可见黄遵宪对“演孔”之事非常小心谨慎。
之所以有这些不同,根源还在于康、黄二人重构孔学的目的存在着巨大差异。康有为早在1888年上清帝第一书前就已形成自己的新思想体系,为了使之能够公开宣扬、为人信从,他有意借助孔学的巨大声望和丰厚资源,力图通过论证“改制”的途径,将“康学”与孔学联为一体,既为维新变法锻造有力的思想武器,又使自己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领袖。为此,他慨然以孔学的真正传人自居,奋力承担起重释孔学的繁重任务,并断然否定人们对“改制”之说的一切质疑,主观独断性表现得格外明显。与之相比,黄遵宪则重在探求和弘扬孔学的真义,以改变历代的曲解和误读,从而传承这份宝贵的遗产,并为其增添时代的精神。尽管他实际上也在革新或改造着孔学,其态度却要客观平实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孔学“时中”论虽不像康有为“改制”说具有那样大的思想震撼力,但可能更加接近或有利于揭示孔学的历史真实。
三、反对将孔学宗教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孔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就一直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到戊戌维新时期,其冲击的力度更加强烈,并尤以基督教的强势传布对孔学的破坏性最大。面对这一形势,康有为采用的对策是赋予孔学以宗教的性质,提升孔子至教主的地位,同时举起“保教”的旗帜,以与西方宗教相抗衡。对此,黄遵宪非常明确地表示反对。他依据自己对孔学的理解和对基督教、佛教及西方政教关系的认识,着重从中西比较入手做了多方面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相当深刻的思想。
其一,辨析孔学②除了使用“孔学”一词之外,黄遵宪也会采用孔“教”的提法以与各教相比。这一用法的含义应为“教义”“教说”“教化”之“教”,而并非将孔学视为宗教。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在引证黄遵宪之说时,统一以“孔学”称之。与基督教、佛教性质的同异,极力赞颂和彰显孔学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以此断言孔学绝不会被他教所灭。戊戌年间,“保教之说盛行”,对孔学之外的其他各教具有很大的排斥性。时为湖南维新运动中坚人物的黄遵宪,担心“素主排外”的湘人受此说鼓动而攻击西教,因而在南学会的演说中,特意指出孔学与基督教、佛教并非彼此截然对立的宗教,“世界各教宗旨虽不同,而敬天爱人之说则无不同然”。[12]既然有此重要的同一性,当然也就不应彼此相攻。
但相同之外,也有诸多相异,其最大的不同就是孔学最为重视“人道”。黄遵宪列举了各教论“天”的一些代表性说法,认为“孔子之天,异于佛而近于耶。佛之天多,故以己为尊,而以天为从。耶之天独,故尊天为父,而以己从之”,而相比之下,还是孔子的“参赞”之说③“参赞”之说见《礼记·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转引自朱熹:《四书集注》,陈戍国标点,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46-47页)黄遵宪引述此说时这样写道:“惟孔子独曰:‘可与天地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我不过参赞云尔。’”参见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5月),《黄遵宪全集》上册,第426页。意谓孔子既不像佛教那样使“人”凌驾于“天”之上,也不像基督教那样以“人”为“天”之附属,而是将“人”与“天地”并列,并界定“人”只是对“天地”生生不息的演化起赞助作用。更胜一筹,因为此说“兼三才(即天地人——引者注)而一之,真乃立人道之极,非各教之托空言者可比之”。所谓“立极”,就是讲出了最透彻的道理,而托之“空言”,就是并无事实根据。孔学因紧贴“人道”而能与人类相始终,“人类不灭,吾教永存,他教断不得搀而夺也”。基于天、地、人三者统一的观念,他对“以元统天”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今尊孔子而剿用佛说,曰以元统天,于理殊未安也。”[13]“以元统天”之说是康有为孔学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命题,黄遵宪却认为其不过是“剿用佛说”,于理不合,这对于康论具有很大的颠覆性。
关于孔学更加符合“人道”,黄遵宪以“天堂、地狱”说为例,从学理上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一是指出各教均言天堂、地狱,惟独孔子不言。这是因为天堂、地狱是否“确有可凭”,以人天生的“秉赋”而言,无论过去还是将来,皆属于“不可知”之事。二是从人类认识发展的趋势看,天堂、地狱之说的影响必然越来越小。起初,“古之人愚,非天堂不足以劝,非地狱不足以诫”,天堂、地狱不过是各教用于“劝诫”的工具,并非宇宙间实有的场所,孔子不言天堂、地狱,也并不能证明其视野狭隘,“不知天道”;接着,“后之人智,知天堂之不可求,于耶稣冉冉升天之说,今既不之信,(黄遵宪原注:西人以距离之远近求天,谓耶稣即如炮弹之速率,至今犹不及半也。)何况于后来”,也就是随着智慧的开启,人们势必越来越不相信天堂、地狱之说;最后,“……格致日精,教化日进,人人知吾为人身,当尽人道于一息尚存之时,犹未敢存君子止息之念,上不必问天堂,下不必畏地狱,人人而自尽人道,真足以参赞天地”,自然科学(“格致”)和人文教育(“教化”)的发展,将使人类不再在乎天堂与地狱,而是自觉立足于自身而尽力发挥其能动作用(“人人而自尽人道”)。三是预言在各教的较量中,孔学终将取胜。其表现,就是等到未来“人理大行,势必舍一切虚无元妙之谈,专言日用饮食之事,而孔子之说胜也(黄遵宪原注:佛言佛法有尽。尝为之反复推求,惟此时为佛法灭时也)”。[14]黄遵宪以“人身”、“人道”、“人理”等组成了一个孔子人本说的系列,认定属人性是世界的本质,以此对抗宗教神话,甚至敢于“推求”佛法之灭,堪称富有近代启蒙精神。可惜这些精彩的思想还只是一些提纲似的论点,未能以专文作更充分的阐释。黄遵宪在孔学与基督教和佛教之间的这种价值取向,与康有为也有显著的差别。他以为人类越到将来,就越少宗教的“虚无元妙之谈”,而康有为在展望人类大同远景之时,则向往充满宗教气息的“天游”境界。对于康有为来说,孔教与佛法是天理的两极,缺一不可,相比之下,佛法还更为广大深远玄妙,只有高智之人才能领会。应该说,这两种取向都有自己的道理(人文与宗教本来就分属于现实和信仰两个不同的领域),为后人的思考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不过,就对孔学本身的界定而言,黄遵宪的结论似理由更加充足。
其二,考察孔学与他教施教方式的区别,明确否定孔子为“教主”及“保教”的必要性。黄遵宪认为,各教教主传教皆具强制性,只有孔子不然:“孔子为人极,为师表,而非教主。凡世界教主,无论大小,必嚣嚣然树一帜以告之人曰:‘从我则吉,否则凶。’释迦令人出家,而从之入极乐国;耶稣教人去其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之乐,而从之生于天国。……摩诃末操一经、一剑,以责人曰:‘从我则升天堂,不从则入地狱。’此皆教主之言。而孔子第因人施教,未尝强人以必从也。”[15]将宗教信仰的专一服从性与孔子的“因人施教”相比较,可比性似并不强,但黄遵宪断言孔子并非“教主”,而只是“人极”和“师表”,从不强人以必从,这个结论是非常中肯的,由此亦可见其反对一切宗教的强制性,坚持给人以思想自主选择权的人文态度。这种宽容而非强制、包容而非排他的特点,进一步延伸成为黄遵宪主张不必“保教”的理由:“古之儒者言卫道,今之儒者言保教。夫必有仇敌之攻我,而后乃从而保卫。耶稣禁设一切偶像之禁(前一“禁”字似为衍文——引者注),佛斥九十六外道之说,回回于异道如希腊、如波斯,拒之尤力,故他教皆有魔鬼。大哉孔子,包综万流,有党无仇,无所谓保卫也。且所谓保卫者,又必有科仪礼节独异于他教,乃从而保之卫之,俾不坠于地。赞美和华,千人唱和,耶之礼仪也;宝象庄严,香花绕拜,释之礼仪也;牛娄礼拜,豚犬不食,回之礼仪也。大哉孔子,修道得教,无所成名,又何从而保卫之?既无教敌,又不设教规,保之卫之,于何下手?至孔子所言之理,具在千秋万世、人人之心。人类不灭,吾道必昌,何藉于保卫?今忧教之灭而唱保教,犹之忧天之堕、地之陷,而欲维持之,亦贤知之过矣。”[16]在此大段论述中,黄遵宪谈了三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孔学有极强的包容性,它没有敌人,无需保卫,从古之“卫道”到今之“保教”,其实皆无必要;第二,孔学不设严划宗教界限的独门“教规”“礼仪”,只重内心的“修道得教”,并不需要外在的顶礼膜拜,无从保卫;第三,孔学之理具有永恒的价值,与人类同存,不必保卫,所谓“保教”实与杞人忧天无异。孔学是否真的如此,当然还很有讨论的余地。黄遵宪所说,除了很多确为事实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了对其心中的孔学,或者说对中华文化的理想化期待。
其三,主张学西方应学其“政”与“学”,尤其应学其政与教、政与学的分离。关于这一点,黄遵宪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且泰西诸国,政与教分,彼政之善,由于学之盛。我国则政与教合。分则可借教以补政之所不及,合则舍政学以外无所谓教。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不必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较短长也。”[17]学西方不应限于其器物和技艺,而要抓住其作为根本的政治和学术,这是当时许多维新派人士的共识,而明确提出政教、政学的分合问题,则显现出黄遵宪相当独特的眼光。他的观点是,西方由于政教分离,才会出现“学之盛”的局面,从而对“政”起补救作用,使之成为善政,若像中国那样,合政“教”为一体,则只会使“政”独大,使“教”丧失其独立的地位。时至今日,中国应吸取西方政学之优长,以挽回中国政学之衰败,而不要再度强化“吾教”之声势,与人一争高下。这里有两点需要略加辨析。一是从上引史料看,政、教、学本应并立为三,其中“教”为宗教,“学”为学术。但实际上,黄遵宪往往将教、学二者混用,言中国之“学”时,几乎皆称之为“教”。因此,所谓“政与教分”、“政与教合”,应该包括政与宗教的分合、政与学术的分合两方面的含意。二是“合则舍政学以外无所谓教”,根据上下文之意,笔者以为应作“合则舍政以外无所谓教”,“学”字很可能为一衍文。2000年来“独尊儒术”,其实真正独尊的是君主的权力,而“学”则被权势者任意利用,在科举考试中,更是变成了莘莘学子的“敲门砖”。黄遵宪的这个论断,可以说揭示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严重痼疾,有很强的思想力度。
其四,指出在康有为的孔学论中,存在着对欧洲历史的很大误解。对此,黄遵宪说得非常直截了当:(康有为)“其尊孔子为教主,谓以元统天,兼辖将来地球及无数星球,则未敢附和也。往在湘中,曾举以语公(指梁启超——引者注),谓南海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不知崇教之说久成糟粕,近日欧洲……于教徒侵政之权,皆力加裁抑。居今日而袭人之唾馀以张吾教,此实误矣!”[18]黄遵宪用他所了解的西学知识和亲眼所见的西方现实,直言“崇教之说”早已成为被人遗弃的“糟粕”,毫不客气地批评康有为的尊孔主张不过是拾人唾余,言词相当尖锐,再次清楚地显现了其坚持将孔学视为人学而非神学的文化立场。
总之,黄遵宪的孔学观既深受康有为孔子改制说的影响,又具有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他对革新孔学极表赞成,力求使之发扬光大;在重新“演孔”的基础上,以“时中”作为孔学的根本特征,彰显其变通性和包容性。与此同时,他抱持审慎的学术态度,注重证据,尊重历史,反对一切将孔学宗教化的做法,坚守孔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并主张仿照西方,分离政教政学,以期学之盛和政之善。这些观念与康有为之说差异甚多,鲜明呈现了维新思潮平实而深刻的另一面。
[1]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76页。
[2][3][5][6][7][12][13][14][15][16][17][18]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5月),陈铮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黄遵宪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26、426、426、426、427、426、426-427、427、427、427-428、427、427页。
[4]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第67页。
[8]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9月),《黄遵宪全集》上册,第433页。
[9][10]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4年8月14日),《黄遵宪全集》上册,第454、454-455页。
[11]康有为:《答朱蓉生书》(1891年),《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5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K203
A
1000-7326(2016)10-0120-07
宋德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