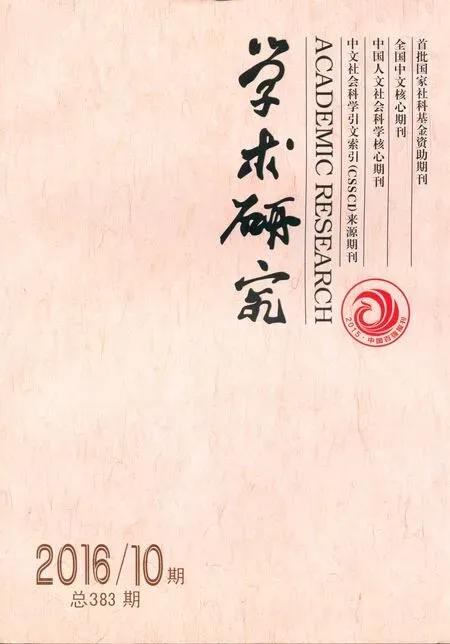汉人的“风水”观念与汉赋的文学表现*
2016-02-27姚圣良
姚圣良
汉人的“风水”观念与汉赋的文学表现*
姚圣良
两汉时期尚未出现“风水”之名,“堪舆”亦非用以指代风水,但实际上宫宅与墓地风水信仰皆已开始盛行于世。汉赋的宫宅风水描写,主要体现在以京都、宫苑为题材的作品中。张衡的《冢赋》,则集中反映了汉人的墓地风水观念。汉代的风水信仰,是形成汉赋题材内容及意蕴表现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考察汉人风水观念对汉赋创作的影响,会让我们对汉赋的认知变得更为全面,也更加符合实际。
汉代风水汉赋文学表现
“风水”亦称“堪舆”,它是一种通过观测住宅或墓地的地势、方向等,借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的民间信仰。两汉时期尽管尚未出现“风水”之名,但是已经有了风水之实。“堪舆”一词产生于汉代,不过此时的“堪舆”还不是风水的代名词。汉代的风水术,属于相术之一种。汉人既相阳宅,又相阴宅,而这两个方面在汉赋中都有所表现。汉人的风水信仰已经成为影响汉赋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目前学者对此却关注甚少。鉴于此,笔者拟就汉人的风水观念与汉赋创作之关系做一初步探讨。
一、汉赋的宫宅风水描写
(一)汉人的宫宅风水观念
中国的风水信仰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风水术就已经萌芽了,起初它与预测吉凶祸福的迷信思想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甚至可以说其中还存在一定的科学成分。古人在选择定居点时,根据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逐渐意识到了什么样的地方才最适合自己部族今后的生存与发展,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相地术”。如《诗经·大雅·公刘》记载:“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1]诗人所描述的,就是周人祖先公刘率领民众到达豳地后,通过观察山形地貌以及水源流向等,最终决定在此建立城郭的情景。先民在定居生活中总结出的这种简单的相地术,便是最初的风水术。
两汉时期,风水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已经出现了专门的风水文献。《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著录有“形法”六家,其中一家就是“《宫宅地形》二十卷”。[2]汉代的形法,即今人通常所说的相术,属于《汉志》所录数术文献之一种。李零曾指出:“古代相术是以目验的方法为特点。它所注意的是观察对象的外部特征(形势、位置、结构、气度等),所以也叫‘形法’。”[3]《汉志》云:“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4]班固认为形法根据城郭屋舍之地势、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等,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并非鬼神迷信,乃是自然之数也。很明显,在《汉志》所录形法六家之中,《宫宅地形》就是一部通过观察城郭屋舍之地形来预测人事吉凶祸福的风水书。
汉代虽已出现“堪舆”一词,但此时的堪舆并非专指风水,二者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如《史记·日者列传》记载:“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5]汉代的堪舆家,与五行、建除、丛辰等家一样,亦属于当时能够帮助人们择日的众多占家之一,还不是专门负责相阴阳二宅的风水师。再如《论衡·讥日》云:“堪舆历,历上诸神非一,圣人不言,诸子不传,殆无其实。天道难知,假令有之,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讳何祸?”[6]所谓的“堪舆历”,就是用以趋吉避凶的择日历书。《风俗通义·佚文》又曰:“《堪舆书》云:‘上朔会客,必斗争。’”[7]可见,汉代的堪舆,应该与择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除了择日之外,堪舆还被汉代学者解释为“天道与地道”。《汉志》所录“五行”文献中有“《堪舆金匮》十四卷”,颜师古注曰:“许慎云‘堪,天道;舆,地道也’。”[8]三国时期,曹魏人孟康在为堪舆作注时,最早将其与图宅书联系在一起。扬雄《甘泉赋》云:“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孟康注曰:“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9]此后,堪舆进一步发展演变,最终成为风水的代名词。显然,汉代的堪舆,并不是专门用来指代风水的。
孟康称堪舆为“造图宅书”之神,这一注解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是,两汉时期确实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图宅术。如《论衡·诘术》云:“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遭祸。’”[10]又云:“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11]王充作《诘术》,其责问、驳斥的对象就是时人所迷信的图宅术。汉代的图宅术,是以五行相生、相克理论为基础。汉人先是将五行与五方(东南西北中)、五音(宫商角徵羽)等结合在一起,然后再把住宅主人的姓氏按照五声分别归属于五音。他们根据五行相生、相克原理来进行推演、预测,认为住宅主人姓氏所属的五音,应该与住宅方位之五方相适宜,进而指出“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12]王符《潜夫论·卜列》亦论及图宅术:“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门。’……又曰:‘宅有宫商之第,直符之岁。’”[13]从王充与王符的这些记载来看,东汉时期图宅术就已经比较流行了。
不管是《汉志》著录的《宫宅地形》,还是《论衡》、《潜夫论》所提到的图宅术,汉代所有的相宅文献如今都已经失传了。实际上,相宅术产生的时间相当早,目前已出土的楚简和秦简中皆有关于相宅术的记载。如湖北江陵九店楚简《日书》称:“北方高,三方下,居之安寿,宜人民,土田骤得。……西方高,三方下,其中不寿,宜人民、六扰。”[14]再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称:“宇四旁高,中央下,富。宇四旁下,中央高,贫。宇北方高,南方下,毋(无)宠。”[15]可见,汉代之前,人们已经将屋舍之地形与其主人的吉凶祸福相关联,初步形成了早期的住宅风水观念。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两汉时期尽管尚未出现风水之名,而堪舆也还不是专门用以指代风水,但是宫宅风水信仰实际上已经开始盛行于世。汉代的宫宅风水观念涉及甚广,大到城郭之地势,小到屋舍之地形,甚至于住宅之门的朝向与其主人姓氏之五声是否相适合等,所有这些在汉人看来皆与人们的吉凶祸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二)汉赋的宫宅风水描写
汉赋的宫宅风水描写,主要出现于京都赋之中。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就发生过定都长安还是洛阳的争议。如《汉书·娄敬传》记载:“敬说曰:‘陛下都雒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则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驾西都关中。”[16]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之时,又有不少人主张迁都长安。如杜笃曾经“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17]两汉时期的建都之争,直接影响到了汉人的京都赋创作。汉代京都赋的环境描写,皆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不管是赋中的假托人物,还是赋作家本人,他们对于自己所偏爱的都城,一般都会极力突出、渲染其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的自然环境,有时甚至于还有意识地将它描绘成所谓的风水宝地。如张衡《东京赋》中安处先生对于东京洛阳自然环境的一段描述:
昔先王之经邑也,掩观九隩,靡地不营。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审曲面势: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回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轘辕。大室作镇,揭以熊耳。底柱辍流,镡以大岯。温液汤泉,黑丹石缁。王鲔岫居,能鳖三趾。宓妃攸馆,神用挺纪。龙图授羲,龟书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绳则直。苌弘魏舒,是廓是极。经途九轨,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视。汉初弗之宅,故宗绪中圮。[18]
“先王”,指周成王。汉家尧后、大汉继周是两汉朝野上下颇为流行的思想意识。《汉书·律历志》称汉高祖“伐秦继周”,[19]《汉书·礼乐志》又称“今大汉继周”。[20]《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21]又《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22]安处先生首先声称洛阳是周代先王经过反复观察、精心测量而最终选定的王城,它正好处于“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的“天地之中”。接下来,则具体描写了洛阳城所特有的“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大室作镇,揭以熊耳”这一山水环绕、无比优越的自然环境。紧接着,又借用“王鲔岫居,能鳖三趾”、“宓妃攸馆,神用挺纪”、“龙图授羲,龟书畀姒”等传说故事,来进一步证明古都洛阳的神奇与灵异。然后,再次强调洛阳乃是召公、周公二人通过相宅、卜宅而为后世帝王创建的最佳都城。以上四个方面的描述结束后,安处先生明确指出:“汉初弗之宅,故宗绪中圮。”意思是说,汉家王朝之所以国运中衰,原因就在于没有选择洛阳做都城。之后,又称:“我世祖忿之,乃龙飞白水,凤翔参墟。授钺四七,共工是除。欃枪旬始,群凶靡馀。区宇乂宁,思和求中。睿哲玄览,都兹洛宫。曰止曰时,昭明有融。”[23]“曰止曰时,昭明有融”,吕向注曰:“言光武当止是洛邑,必有昭明长久之福。”[24]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最终导致王莽篡位、汉祚中衰。东汉建立后,光武帝思阴阳之和、求天地之中,于是决定放弃长安,改以洛阳为都城。光武帝还都洛阳之举措,必将会使汉家王朝从此国运昌明而又长久。安处先生的这番言论,正是源自于汉人的宫宅风水信仰。
张衡《南都赋》亦表现出一定的宫宅风水理念。赋云:“尔其地势,则武阙关其西,桐柏揭其东。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汤谷涌其后,淯水荡其胸。”[25]张衡不仅刻意描写了南阳城山环水绕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而且还着重指出:“夫南阳者,真所谓汉之旧都者也。……近则考侯思故,匪居匪宁。秽长沙之无乐,历江湘而北征。曜朱光于白水,会九世而飞荣。察兹邦之神伟,启天心而寤灵。”[26]李善注曰:“言考侯既察此都之神伟,且启上天之心,又寤先灵之意,使之而王也。”[27]《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云:“(节侯)买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从弟钜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28]考侯正是因为“察此都之神伟”、“启上天之心”而又“寤先灵之意”,才与从弟刘回等迁居南阳。又《后汉书·光武帝纪》云:“(节侯)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29]当年随考侯迁往南阳的刘回,就是光武帝的祖父。可见,张衡已把光武帝的兴起与南阳的风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扬雄《蜀都赋》对于风水信仰亦有所反映。赋云:“蜀都之地,古曰梁州。……上稽乾度,则井络储精;下按地纪,则巛宫奠位。”[30]“乾度”,指天之分野;“巛宫”,即地之坤宫。左思《蜀都赋》称:“远则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天帝运期而会昌,景福肹蠁而兴作。”[31]刘渊林注云:“《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上为天井。’言岷山之地,上为东井维;岷山之精,上为天之井星也。”[32]在扬雄看来,蜀都上应天之井星分野,下居地之西南坤宫,乃是含日月精华、获神明福佑的风水宝地。
汉代的宫宅风水信仰对于汉赋创作的影响,并非仅仅体现于京都赋之中,在那些直接以帝王宫苑为题材的作品里也有所反映。如刘歆《甘泉宫赋》云:“迴天门而凤举,蹑黄帝之明庭。冠高山而为居,乘昆仑而为宫。按轩辕之旧处,居北辰之闳中。”[33]秦始皇曾经“作甘泉前殿”,[34]后来汉武帝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35]甘泉乃是传说中轩辕黄帝之“明廷”,《史记·封禅书》记载:“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36]甘泉宫坐落在黄帝明廷的旧址之上,不少古代帝王亦都于此,在汉人眼中这里肯定具有好的风水。刘歆在赋中有意识地强调甘泉宫“蹑黄帝之明庭”、“按轩辕之旧处”,正是受到了汉代宫宅风水观念的影响。再如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其序云:“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意者岂非神明依凭支持,以保汉室者也。然其规矩制度,上应星宿,亦所以永安也。”[37]在赋中,作者又云:“据坤灵之宝势,承苍昊之纯殷。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烟煴。……神灵扶其栋宇,历千载而弥坚。永安宁以祉福,长与大汉而久存。”[38]王延寿认为鲁灵光殿之所以能够“永安”,原因就在于其“规矩制度,上应星宿”,占据了好的地势,吸纳了天地之间的“元气”,并得到了神灵的保佑。赋作家的这种思想意识,亦是来自于汉人的宫宅风水信仰。可见,不管是两汉时期的京都赋,还是那些直接以帝王宫苑为题材的赋作,对于汉人的宫宅风水观念都有所表现。
二、汉赋的墓地风水描写
(一)汉人的墓地风水观念
众所周知,风水信仰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阳宅,即活人的住所;二是阴宅,即死者的墓地。汉人既重视阳宅,也重视阴宅。汉人认为死者墓地的好坏将会对其子孙后代的吉凶祸福产生直接的影响。
古人最初的丧葬行为,并不具备风水意识。唐代吕才《叙葬书》称:“《礼》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见之。’然《孝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顾复事毕,长为感慕之所;窀穸礼终,永作魂神之宅。朝市迁变,不得豫测于将来;泉石交侵,不可先知于地下。是以谋及龟筮,庶无后艰,斯乃备于慎终之礼,曾无吉凶之义。”[39]可见,古之丧葬,原本只是为了“长为感慕之所”、“永作魂神之宅”,并无“吉凶之义”。
远古时期人们就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观察山形地貌来为逝者选择合适的墓地。《吕氏春秋·节丧》称:“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抇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40]古人常常选择山陵或高丘来安葬逝者,以避免死者遗体浅埋被野兽刨食、深埋被水泉浸泡。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与爱护而已,与后世的墓地风水信仰有着本质的不同。西周时期人们已将死者墓地的选择与预知未来的神秘思维相结合,初步形成了墓地风水信仰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载:“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41]樗里子正是因为可以准确预测到自己墓地百年之后的情形,才被后世的堪舆家所推崇。樗里子这一预言确实非常神奇,但它与樗里子后世子孙的吉凶祸福并没有什么关系。
到了汉代,墓地风水信仰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死者墓地的好坏已经与其后人的吉凶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后汉书·袁安传》记载:“初,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42]袁安“当世为上公”,其子孙后代亦“累世隆盛”。在时人看来,袁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兴盛几代,原因就在于袁安父亲的墓地风水好。再如《后汉书·郭镇传》记载:“(吴)雄少时家贫,丧母,营人所不封土者,择葬其中。丧事趣辨,不问时日,巫皆言当族灭,而雄不顾。及子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43]吴雄的母亲去世后,他不仅“营人所不封土者,择葬其中”,而且“丧事趣辨,不问时日”,所以巫师都预言吴雄“当族灭”。然而,吴雄并没有因此而“族灭”,吴雄再加上其子、其孙恭,吴氏家族“三世廷尉,为法名家”。《后汉书》所载袁安与吴雄的事例,一正一反,足以说明两汉时期墓地风水信仰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两汉时期还出现了墓地风水文献。如《后汉书·王景传》记载:“初,景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错糅,吉凶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云。”[44]王景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冢宅禁忌”、“堪舆日相”等进行筛选,取其“适于事用”者,集合在一起,编成了《大衍玄基》一书。可见,“冢宅禁忌”亦是汉代颇为盛行的“众家数术文书”中的一类。在汉代著名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对汉人的墓地风水信仰已有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如《太平经·葬宅诀》云:“葬者,本先人之丘陵居处也,名为初置根种。宅,地也,魂神复当得还,养其子孙,善地则魂神还养也,恶地则魂神还为害也。五祖气终,复反为人。天道法气,周复反其始也。”[45“]魂神复当得还”是《葬宅诀》的理论基础。《葬宅诀》认为死者的墓地若选择的是“善地”,死者的“魂神”自然就会“养其子孙”;相反,若选择的是“恶地”,死者的“魂神”非但不能“养其子孙”,而且还会对其子孙后代造成危害。可见,《葬宅诀》已初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墓地风水理论。
(二)汉赋的墓地风水描写
汉人的墓地风水观念,在汉赋创作中同样也有所反映。张衡的《冢赋》可以称得上是汉赋在墓地风水描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冢赋》篇幅不长,兹录全文如下:
载舆载步,地势是观。降此平土,陟彼景山。一升一降,乃心斯安。尔乃隳巍山,平险陆,刊藂林,凿盘石,起峻垄,构大椁。高冈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坛,罗竹藩其域。系以脩隧,洽以沟渎。曲折相连,迤靡相属。乃树灵木,灵木戎戎。繁霜峨峨,匪雕匪琢。周旋顾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绳,正之以日。有觉其材,以构玄室。奕奕将将,崇栋广宇。在冬不凉,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处。修隧之际,亦有掖门。掖门之西,十一余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车之道,交通旧馆。塞渊虑弘,存不忘亡。恢厥广坛,祭我兮子孙。宅兆之形,规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丽,践而行之巧以广。幽墓既美,鬼神既宁,降之以福,于以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46]
《冢赋》被收录于《古文苑》,章樵注曰:“古者不预凶事冢圹,卜葬而后穿筑。至春秋时,晋文公有功于周,请隧,弗许。曰:‘王章也。’释者云:‘阙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礼也。’晋文以此为请,则预为冢圹矣。汉之人主多预为陵庙,则士大夫必有预为冢兆者。详观此赋,其平子预为筑之冢邪?”[47]章樵推测《冢赋》所描述的,应当是张衡生前特意为自己选择墓地并预筑冢圹的情形。《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48]李贤注曰:“西鄂,县,故城在今邓州向城县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49]章樵所谓《冢赋》乃“平子预为筑之冢”这一推论,还是比较可信的。当然,《冢赋》也有可能与《归田赋》一样,完全就是张衡的想象之辞。
《冢赋》开篇即云:“载舆载步,地势是观。降此平土,陟彼景山。一升一降,乃心斯安。”费振刚《全汉赋校注》注曰:“舆:指堪舆。迷信术数的一种,俗称‘风水’,应用于勘察住宅基地或坟地的形势。”[50]两汉时期堪舆并不是用以指代风水,因此将“舆”直接解释为“堪舆”似乎不妥,极有可能违背了张衡的原意。此处的“舆”,应该指的是车子。开头的这几句话,是在叙述作者察看地形、确定墓地的过程:时而乘坐车子,时而徒步行走;先是下到了平地,后又登上了高山。经过反复观察,最终选定了自己满意的墓地。作者仔细勘察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寻找所谓的风水宝地。
接下来,《冢赋》对于墓地周边环境的描写,则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风水意识。古代的坟茔,亦称之为“垄”;而“椁”则是古人套在内棺外的大棺,或以木材为之,或由砖石砌成。在中国传统的风水信仰中,人们一直将山与水视为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相信有山有水的地方,才能够积聚天地之灵气,成为风水宝地。赋作家通过“隳巍山”、“凿盘石”来“起峻垄”、“构大椁”,其坟墓肯定是依山而建的。尽管作者在赋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水,但是从“下有直渠”、“舟车之道”等语来看,坟墓附近应该会有水源存在。可见,张衡所选的墓地,依山傍水,这与古人的风水理念是一致的。
“高冈冠其南,平原承其北”,章樵注曰:“枕南而向北”。[51]在作者的心目中,墓穴的南面是隆起的高冈,北面则是开阔的平原,葬于此处,枕南而向北,南面高高的山冈恰好就像自己戴在头顶上的冠一样。汉人认为地势高而又宽敞的墓地,才会具有好的风水。如《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52]韩信尚为布衣之时,其母亲去世,尽管家贫无以为葬,但是韩信还是特意选择了一处“其旁可置万家”的“高敞地”来安葬自己的母亲。再如《后汉书·冯衍传》记载,冯衍的《显志赋》,其正文前面还有一段相当于序文的“自论”。冯衍在“自论”中说:“先将军葬渭陵,哀帝之崩也,营之以为园。于是以新丰之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地势高敞,四通广大,南望郦山,北属泾渭,东瞰河华,龙门之阳,三晋之路,西顾酆鄗,周秦之丘,宫观之墟,通视千里,览见旧都,遂定茔焉。”[53]李贤注曰:“奉世为右将军,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将军’。渭陵,元帝陵,在长安北五十里。哀帝义陵在长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义陵茔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别求也。”[54]可见,与韩信一样,冯衍亦是把“地势高敞”作为选择墓地的重要标准。又《汉书·陈汤传》记载,汉成帝原本已建初陵,后来又听从陈汤的建议而另起昌陵,结果数年未成。群臣反对营造昌陵,主张还复初陵,他们声称:“故陵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绪,宜还复故陵,勿徙民。”[55]显然,大臣们在劝说汉成帝时,同样也是将“处势高敞”作为“还复故陵”的一个重要理由。张衡所选中的这一墓地,南枕高冈,北临平原,地势高敞,视野开阔,完全符合汉人的墓地风水观念。
“乃树灵木,灵木戎戎”,章樵注曰:“树之灵木,所以识荫。戎戎,盛貌。灵,善也。”[56]此处的“灵木”,应该是指种植在坟墓四周的青松翠柏。“繁霜峨峨,匪雕匪琢”,意思是说,到了冬季,墓园中的松柏披着一层厚厚的白霜,显得格外庄严肃穆,这种景象可不是人工雕琢出来的。“周旋顾盼,亦各有行”,意思是说,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看,墓园里的树木都排列有序、整齐成行。《太平经·葬宅诀》云:“欲知地效,投小微贱种于地,而后生日兴大善者,大生地也;置大善种于地,而后生日恶者,是逆地也;日衰少者,是消地也。”[57]可见,汉人认为墓地周边的草木长得是否茂盛,乃是衡量其风水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上,在汉代的风水信仰中,不管是死者的墓地,还是活人的住所,人们对于其地表植被的生长状况都极为重视。在汉人看来,只有那些地表植物长势良好的所谓“生地”,才有可能成为风水宝地。后世的堪舆家将“郁草茂林”作为判定一个地方风水好坏的重要标准,便是源自于汉人的这种风水理念。汉人的这一风水理念,在汉代京都赋中也有所体现。如扬雄《蜀都赋》云:“禹治其江,渟皋弥望,郁乎青葱,沃壄千里。”[58]再如杜笃《论都赋》云:“《禹贡》所载,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弥望。保殖五谷,桑麻条暢。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59]张衡《西京赋》又云:“尔乃广衍沃野,厥田上上,寔为地之奥区神皋。”[60]《冢赋》关于“灵木”的这段描写,其所反映的正是汉人这种风水观念。
“宅兆之形,规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丽,践而行之巧以广”,意思是说,墓地的地形、陵墓的建筑都完全符合规矩,从远处望去,整个墓园显得方正而又华丽;走到近旁再看,则发现它巧妙而又广阔。“幽墓既美,鬼神既宁,降之以福,于以之平”,意思是说,陵墓那么幽美,鬼神安居在这里,一定会降福于子孙,让他们永享和平。张衡的这种思想意识,与《太平经·葬宅诀》所称“善地则魂神还养”这一墓地风水观念显然也是一致的。
《冢赋》的结尾,是作者如诗如画般的深情赞美:“如春之卉,如日之升。”在张衡的眼中,墓园如此美好,就像那春天的花卉,又像那初升的朝阳,蕴含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乐生而恶死,本是人类的天性。坟墓则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是与死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留给世人的印象总是阴森、可怖、痛苦和绝望。但是,《冢赋》却让读者耳目一新,我们从中感受到的并不是恐惧与忧伤,而是作者的惊喜、欣慰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张衡竟然能够产生这样的慰藉与希望,其心理支撑正是汉人的墓地风水信仰。
总之,汉代尽管尚未出现风水之名,此时的堪舆亦非用以指代风水,但是风水信仰实际上已经开始盛行于世。两汉时期的宫宅及墓地风水信仰,在汉赋中皆有所反映。汉赋被视为“一代文学之代表”,而汉代又是风水信仰发生发展的关键时期。汉代的风水信仰,已是形成汉赋题材内容及意蕴表现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考察汉人风水观念对汉赋创作的影响,将会让我们对汉赋的认知变得更为全面,也更加符合实际。
[1] 程俊英:《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28页。
[2][4][8][9][16][19][20][55]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74、1775、1769、3523、2119-2121、1023、1075、3024页。
[3] 李零:《中国方术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5][22][34][35][36][41][52]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22、133、241、458、1402、2310、2629-2630页。
[6][10][11][12] 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65、1417、1428、1428页。
[7]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63页。
[13] 彭铎:《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8页。
[1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0-51页。
[1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10页。
[17][28][29][42][43][44][48][49][53][54]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95、560、1、1522、1546、2466、1897、1897、986、987页。
[18][23][25][26][30][33][37][38][46][50][58][59][60] 费振刚:《全汉赋校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78、678、726、728、212、326-327、850、852、749、750、212、387、629页。
[21] 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15-721页。
[24][27][31][32] 李善等:《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7、88、98、98页。
[39] 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23页。
[40] 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970-971页。
[45][57]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82、182页。
[47][51][56] 章樵:《古文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33、133、133页。
责任编辑:王法敏
I206.2
A
1000-7326(2016)10-0170-07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先秦两汉民间信仰与文学研究”(14BZW042)的阶段性成果。
姚圣良,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淮河文明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河南 信阳,46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