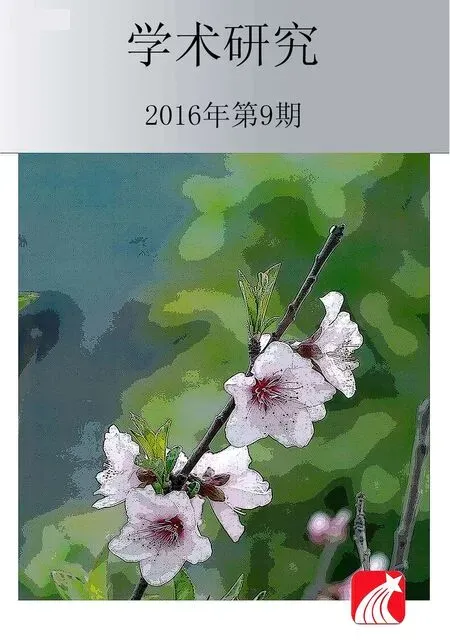论强制阐释的预设维度与征用疆界*
2016-02-27韩伟
韩 伟
学术聚焦
论强制阐释的预设维度与征用疆界*
韩 伟
强制阐释论是当下文学理论领域中最被关注的话题之一。强制阐释中的主观预设总体上应包含三个维度,即话语导向维度、体系建构维度、现实解释维度。在征用场外理论方面,应合理地圈定出征用疆界,人文性是确定一种理论是否合适的主要划界标准。在具体方法层面,应吸取“失语症”及古代文论现代转化讨论无疾而终的教训,将研究落到实处,并尽量探索避免强制阐释的具体规则或标准。
强制阐释预设维度征用疆界
强制阐释的主要特征是主观预设和场外征用,前者用张江的话说就是“论者主观意向在前,前置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1]事实上,除了理论与文本之间存在主观预设之外,尚存在理论与理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多重预设维度。总观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这方面的主观预设似乎较之从理论到文本的主观预设更普遍一些。对于场外征用,我们亦应辩证地看待,确定合理的征用疆界和征用标准将是避免理论形而上学的必要手段。下面围绕预设维度、征用疆界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做一梳理。
一、理论预设之话语导向维度
理论之间主观预设的第一个维度是话语导向维度。就中国文学的理论土壤来讲,文学与话语、理论与话语似乎一直都保持着某种联系,只不过在某些时段会以潜在的方式存在,某些时段则会以显性的方式展示而已。对于话语,在中国古代集中体现为政治导向因素,当代更倾向于某种主流的文化导向或文化潮流。因此,我们在讨论主观预设的时候理应对这种由外在内化为主体认知的预设维度予以关注。
中国古人在理论内部也经常进行这种先入为主的预设。不妨以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有重要奠基意义的第一篇专论文章《诗大序》为例,对其作者目前虽然众说纷纭,但基本上认为是经过汉人整理而成。在笔者看来,这种整理严格意义上应该说是“杂缀”,汉人是在先秦文献的基础上人为地对众多材料进行裁剪,最终组合成一篇符合自己主观意愿以及时代要求的理论文字,以此来保持与时代文艺政策的高度一致。《诗大序》带有鲜明的因袭先秦乐论的痕迹,其远祖当为先秦乐论。比如《诗大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同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文字的源头可追溯到《乐记•乐施》篇。另一段较明显的例证是“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这段文字见于《乐记•乐本》篇。除此之外,《诗大序》言:“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在《周礼•春官•大师》中存在与之相类的记载:“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此处所讲的“六诗”即是《毛诗序》所言之“六义”,虽然两者的称呼不尽相同,但所指内容是完全一致的,甚至顺序都并未调整。大师在周代属于重要乐官,归大司乐统领,主管音律校订、典礼音乐的指挥,并协助大司乐进行音乐方面的教育,统领瞽矇,因此“六诗”很有可能就是大师的基本传授技艺。《诗大序》除了在文字层面体现出明显的因袭、拼接痕迹之外,在义理层面也同样如此。比如其“谲谏”观的提出,《毛诗序》称之为“主文而谲谏”,在“谲谏”前用“主文”加以限定,“文”此处当有文饰、修饰的含义,《毛传》言:“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2]孔颖达亦言:“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3]就是说劝谏君主除了在主题层面要委婉含蓄之外,同时也要兼顾形式层面的可接受性,配合音乐将主题以歌咏之,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那么,《诗大序》搬用先秦乐论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当与汉代的文化环境有关,汉代的帝王对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异常重视,为统一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而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都是在皇帝的授意甚至亲自参与下召开的,学术的政治化是汉代学术的总体特征。《诗大序》对先秦乐论进行裁剪,最终是要将风、雅、颂从政治层面进行重新定义,并将“诗言志”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学价值论相嫁接。事实上,这种在理论层面以政治为出发点的主观预设在汉代以后一直未曾中断过。那么,这一类型的强制阐释在当下的理论界也普遍存在着。耶鲁批评学派的哈罗德•布鲁姆坦言:“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4]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当下的理论界几乎被各种各样所谓的“后”理论裹挟着,而这些后现代理论用周宪的话说实际上可以总称为“政治实用主义”,即“把文学作为文化政治的理论阐释素材……坚信文本的意义是在话语活动中经由阐释而产生的”,[5]这也就是伊格尔顿所指出的一切文学都具有政治倾向性的应有之义。文学成了文化政治的阐释素材,而理论又何尝不是呢?文化政治潜在地规约着理论可达到的区域,这种先入为主的立场构成了一种潜在的预设维度,在重视文本为理论服务的强制阐释之外,我们亦应对理论为立场服务的深层主观预设加以反思。
二、理论预设之体系建构维度
理论预设的第二个维度是体系建构维度。体系建构维度相较于话语导向维度更具学理性,这种主观预设与单纯以阐释某个单一理论为目的预设不同,它更接近一种宏观的体系性搬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当代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小到具体理论的运用、具体思潮的推行,大到整个学科合法性的建构都带有这种影子。以作为大学中文系学生必修课的“文学理论”为例,对文学理论具有重要奠基意义的教材是童庆炳的版本体系,其所呈现的问题域、范畴系统、言说方式都潜移默化地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者的集体无意识。童庆炳据以构筑其教材体系的框架来自M. H.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说,其早期版本中引入的再现说、表现说、客观说、实用说等文学观念也成了后来文学理论的关注对象。除此之外,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也对新时期的教材体系甚至研究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一点在童庆炳的教材体系中亦有十分明显的体现。因此,可以说当下我们据以安身立命的整个知识体系,某种程度上都带有理论层面主观预设的痕迹。只不过,对其优劣得失,我们不能单纯按照张江所说的“文本为理论服务”的主观预设的含义去理解,这需要以辩证思维去抽丝剥茧。
另一个需要重点申说的话题是中国美学学科的建构。美学是德国学者鲍姆加登在18世纪后期主张建立的一门以理性的方式研究感性的学问,对于这门学问,日本学者以“美学”二字翻译之,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又将这个词从日本引入国内,自此这一新兴学科才在中国理论界正式落户。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学科在西方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学科建制,但面对中国崭新的文化环境,则必须寻找其能够赖以扎根的文化土壤,因此对中国本土资源的重新反思和审视便是其必须选择的途径。在经历过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以及80年代的方法论热潮之后,中国美学的学科体系逐渐形成。这里有必要谈一谈80年代美学热中与方法论热潮并行的另一种趋势,即对中国古典资源的再发掘。“中国古典美学”或“中国美学”,这一概念或学科成立的前提是,先有西方美学的输入,然后研究者才致力于重新挖掘本土的艺术资源,从而彰显美学的民族特色,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国美学实际上是也是对西方美学的再度阐释。古典美学研究是美学学科在中国学科化的结果,研究者为了增强学科意识而自觉地寻找中国古典资源,这种尝试在80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朱光潜在1961发表于《文艺报》上的《整理我们的美学遗产,应该做些什么》一文中说:“认为美学是一种新科学,我们自己仿佛还没有,必须由外国搬过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认为我们自己没有美学未免是‘数典忘祖’了。”[6]另一位美学大家宗白华亦与朱光潜类似,他从中国艺术的总体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论、画论、乐论里,有丰富的美学思想资料,一些文人笔记和艺人的心得,虽则片言只语,也偶然可以发现精深的美学见解”。[7]进入80年代以后,众多美学研究者如李泽厚、刘纲纪、叶朗、于民、敏泽、皮朝纲等人都试图将这一问题推向更为纵深的层面,即不再追问美学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这个已经形成共识的问题,而是在美学的基本框架下,努力探索中国美学的特殊性。为了使这一学科获得充分的合法性,此时开始广泛地撰写中国美学史,李泽厚和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1984—1987)、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1987—1989)等在后来颇具影响的美学史专著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些早期的美学史著作一定程度上构成了90年代以后同类写作的基本范型,也为美学的学科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王国维、宗白华被重新发现,人们将二人的思想以“美学思想”视之,进而以对二人的研究为中介,开始逐步探索古典美学的资源以及合理的研究方法。这一类型的主观预设也是需要我们辩证看待的。中国文论、中国美学虽然在体系建构维度表现出明显的预设痕迹,但可贵的是其体系内部有非常顽强的自身生长性,比如中国美学实际上将西方的哲学美学逐渐转化成了艺术美学,这是需要肯定的。
三、理论预设之虚拟现实维度
理论层面的第三种主观预设维度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只不过这种现实是一种人为建构起来的虚拟现实,因此权称之为“虚拟现实维度”,即为了某种主张或某种理论的合理性存在,而将现实情况进行人为的选择、渲染,进而在这一层面上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笔者想到几年前由文化研究热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都市文化研究。对于这一多少带有人为建构的研究热潮来讲,其理论资源无疑带有鲜明的舶来品特征,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对当时的理论来源进行了梳理,总体上包括三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城市社会学理论、后现代空间理论。[8]今天看来,以本雅明、詹姆逊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其他两种来源则有一定的问题,征引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属于过度诠释层面,而借鉴城市社会学理论则属于强制阐释的范畴了。因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建构者是德国的西美尔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的人物帕克(R. Park)、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西美尔对城市文化心理的分析集中在货币这一范畴上,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已经打破了前现代社会田园牧歌式的生存状态,代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其巨著《货币哲学》的整个目的就是通过分析货币这一(后)现代社会最普遍的交往媒介,“以表现最表层的、最实际的、最偶然的现象与存在最理想的潜力之间的关联,表现个体生命与历史的最深刻的潮流之间的关联”。[9]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具体分析了货币经济中分工、交换、生产、消费机制如何影响现代拜金人格的形成,正是因为城市已经被这种非人化的关系所统治,所以现代都市人便产生消极逃避的心理状态,顺应、倦怠和逃避成了都市人生活的主要方式。受其影响,芝加哥学派在理论上也相当关注人的生存状态问题,广泛运用实证主义方法,同时以一种整体性的眼光来看待城市。以帕克和沃斯这对师徒为代表,基本上都主张“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它是生态、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过程的综合产物,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10]他们致力于使现代社会的结构失衡性、涣散性得到弥合,重新恢复由于社会不断运动而造成的结构性失调,进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以便维持人与自然、社会的正常关系。
西美尔、帕克和沃斯的理论在社会学层面是深刻的,但将之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则有强制阐释的嫌疑。当时中国的都市文化以及以之为载体的都市文学还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的对象较多是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主的个案研究,因此在都市以及都市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在现代与后现代景观并存的大背景下,理论的引入便带有某种一厢情愿的性质。当时研究者常用的方式往往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主观地看成是全国的普遍性模版,从而使理论的言说有据可依。虚拟化的现实成了理论进行驰骋的训练场,为理论虚拟注释性的文本与为理论虚拟现实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虚拟现实是文学疆界扩容后的极端表现,也是伴随近年来文化研究热潮而产生的副产品,甚至较之虚拟文本,这种行为在当下更具普遍性。
除此之外,近年来对超文本理论的建构以及对现实的虚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在西方,广义层面的超文本文学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形成创作高潮,当时的经典之作有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品钦的《V》、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巴思的《迷失在开心馆》等。所谓“超文本”,纳尔逊在《文学机器》一书中这样定义:“非连续性著述,即分叉的、允许读者做出选择、最好在交互屏幕上阅读的文本。”[11]目前,被国内学术界广泛征引的超文本文学作品包括乔伊斯的《下午:一个故事》、莫尔斯洛普的《维克托花园》以及台湾“歧路花园”网站相继推出的《烟花告别》、《西雅图漂流》等小说和诗作,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解构了传统的阅读模式,伴随不同的链接可以生成若干种故事情节,或者实现了文字与图像、视频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超文本文学最大程度地打破了时间因素对于文学的固有束缚,将空间因素引入文学领域。不妨以“歧路花园”网站苏默默《抹黑李白》组诗中的《诗•尸》为例,全诗仅四句:“漂泊的诗/一具不安的尸/漂泊的尸/一句不安的诗”。全诗仅是将“诗”与“尸”两个关键词互换,将李白的诗意(失意)人生表达得恰到好处。另外作者将全诗的最后一句的六个字设计成红、绿、蓝、白、粉六种颜色,而且在频繁地上下跳动,这种设计更加深了读者对于“漂泊”与“不安”的实际体验,更有利于读者理解略带悲情化的李白。这种带有实验性质的文学创新是值得肯定的,但事实上,就大陆目前的文学现状而言,超文本在本土尚未形成自觉。这样,国内的学者对所谓超文本理论的建构便带有鲜明的虚拟特点,即将超文本文学视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从而构筑所谓的研究性理论。这种研究模式就其本质而言着眼点并非是现实或研究对象本身,被虚拟出来的现实仅仅是理论的注脚而已。“为现实”与“为理论”便成了正常阐释与强制阐释最为明显的差异所在。
四、征用的疆界
强制阐释论中与主观预设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场外征用。按照张江的理解,这种强制地将其他领域的理论嫁接到文学领域的现象是当下文学理论界的普遍现象,这也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下面要讨论的问题是,对场外征用的摒弃是否意味着文学研究最终要走向自我封闭的死胡同呢?若不是这样,那么在文学研究中征用的疆界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征用疆界的确立是使文学研究避免故步自封,并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的关键。中国古人就有“征用”理论的做法,事实上很多现在大家熟知的古代文论的概念、术语,其肇始点都并非文学领域。比如“韵”是从秦汉间音乐领域产生的概念,之后在魏晋乐论中才逐渐上升到美学领域,继而才波及到人物品评(如《世说新语》“风韵”)、画论(《古画品录》“气韵”)、文论(《文心雕龙•声律》“韵气”)等领域,最终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美学范畴。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味”也同样如此,其最早的源头当是老庄哲学,到了魏晋时期则变成了一个普适性的美学范畴,朱自清曾经这样写道:“魏、晋以来,老、庄之学大盛,特别是庄学,士大夫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欣赏与批评也在长足的发展。清谈家也就是雅人要求的正是那‘妙’。后来又加上佛教哲学,更强调了那‘虚无’的风气。于是乎众妙层出不穷。”[12]到了唐代,“妙”首先被运用到书法和绘画理论中,并成了划分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正是由于“韵”与“味”在美学史上的长期积淀,到了司空图这里才产生了著名的“韵味说”,并将之推广到文学批评之中,用于对文学意境的体认。
确定可征用的问题域,这其实也就是如何自我认知的问题。就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而言,其属于艺术领域,因此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等方面的理论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对象,但若将纯粹社会学、伦理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东西引入,恐怕就走得太远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各种理论浪潮频繁登场,但多是各领风骚三五年,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往往为理论而理论、为标新立异而理论。今天之所以有关于强制阐释的反思,就在于这些所谓的思潮退却之后,还是要回到真正的研究对象这里。对于理论的场外征用问题,张江曾专文对之进行解释和论辩,在讨论中为了充分阐释场外理论的范围和有效性,他又进一步提到了“场外理论的文学化”问题,认为在文学研究中适当地引入场外理论是必要的,只是要充分注意这些理论的边界,在他看来,“其一,理论的应用指向文学并归属于文学。其二,理论的成果落脚于文学并为文学服务。其三,理论的方式是文学的方式”。[13]这些认识固然不错,但在我看来仍然有些不够准确,就中国文学理论而言,笔者认为用场外理论的人文性来取代文学化似乎要更准确一些,所谓人文性是与工具性相对立存在的概念,较之后者它更加强调理论的艺术性、人本性和无功利性。以人文性取代文学化绝不是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因为衡量理论有效性的途径应该是能否与文学实践相结合,能否最大限度地接近文学的本性,化用王国维的术语便是“隔”与“不隔”的区别,前者属于一种没有文学指向的征用,比如硬性地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或者以先在立场进行的文本贴合,后者则是一种自然合理的征用,比如借鉴一些艺术学、音乐学甚至哲学、美学的理论深化对作品的认知。不妨以马克思《巴黎手稿》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例,前者对全面异化的分析以及后者对社会物化状态的探索,某种意义上都是以人作为最终的关注主题的,这就与同是人学的文学存在天然的同质性,因此它们的理论适用于文学批评领域,便是“不隔”。
不仅对西方理论的征用如此,中国古代这种现象似乎更为明显。中国艺术的特性使得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往往是胶合在一起的,乐论中包含文论,哲学中涉及文学,等等。笔者认为,人文性与文学化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人文性的所指范围较之文学化更宽泛一些,哲学、艺术、历史、美学等与文学具有相通性的观点、理论都可以成为文学理论征用的对象,而文学化似乎有将文学研究重新象牙塔化的嫌疑。这些领域的观点并不一定非要如张江所言具备文学化的特征,只要存在契合点(即“不隔”),哪怕是有限有效的,不妨拿来,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这里笔者赞成周宪的观点:“就强制阐释而言,问题的核心好像不是种种理论的‘出身’,而是在于其阐释文学的相关性和有效性。”[14]而张江所说的“场外理论的文学化”,其理论预设是可以理解的,即是说只有这些理论为真实的实践服务而不是相反,才承认这种征用是有效的,合理的,而实际情况往往是,我们如何判定某种具体的理论征用是自为的还是他为的呢?当面对形形色色的场外征用理论的时候,如何对理论的真正目的和实践效果进行判定?我们是更看重理论的文学潜能,还是更介意它们偶尔被强制阐释?我想,张江的初衷是好的,其观点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性的,只不过还要将强制阐释、场外征用等问题做具体分析。在承认强制阐释的大背景下,如何将其波及的范围科学地圈定出来,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应该逐步展开对当下文学研究领域中具体理论、具体流派的客观分析。惟其如此,才会使有关强制阐释的讨论落到实处,避免以抽象的方法论做指导(事实上这也会导致理论先行的新的强制阐释),并对真正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提供警醒和借鉴。
五、中国文论重建
讨论强制阐释以及与之相关的预设维度、征用疆界,最终目的是在探索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此次对强制阐释的讨论与十多年前对“失语症”以及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讨论是不同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已经倡导多年,事实证明结果不尽如人意,而强制阐释的逻辑起点是基于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文学批评实践往往将西方理论搬来,进行带有自恋性质的理论言说,或者脱离文学实践经验,或者单纯进行理论演绎,文本充当了理论建构的注脚之事实,从而呼吁合理的场内阐释、场内征用,避免牵强。新世纪之前对“失语症”问题的讨论,某种程度也的确抓住了当时理论界的共性现象。笔者认为其对现象的描述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其所采取的方法则有些极端,完全建立在民粹主义之上的掩耳盗铃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从“失语症”的提出到现在已经接近20年的时间了,事实证明单纯而绝对的否定西方有价值的理论形态是极端的,这也就注定了这种尝试仅是一种理论愿景,而绝难变成现实。真正要将口号、观点落实到实处,关键是要拿出真正具有现代性和生长性的古典理论或概念进行真正的文学批评。此次强制阐释问题的提出,也应如此,在适当的理论层面的探讨之后,真正地进行场外理论和场内理论的鉴别,甚至在此基础上试图寻找到可行的鉴别标准,这些恐怕是未来我们应努力的方向。惟其如此,才能使这一讨论不至中途夭折。
我们既没必要完全臣服于外来文论,也没必要极端地抬高本土的古代资源,前者往往会产生过度诠释甚至强制阐释,最终使理论变成凌空蹈虚脱离文学实践的概念演绎,变成为理论而理论;一味强调后者也容易使阐释变得僵化,脱离实践而无实用价值。总观近年来的文学理论建设,表面上风光无限、异彩纷呈,甚至弄得很“高大上”,追求与国际接轨,实际则是带有理论和批评上双重不自信,理论上自说自话,批评上削足适履,将批评实践与文学理论弄成了不相干的两回事,且乐此不疲。笔者认为,改变这种状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分析中国古典文论中是否还有阐释当下问题的潜能,其中包括具体概念、创作思想以及创作方法,并做具体分析;其次,对百年来西方理论的征用,进行个案梳理,期望通过以史为鉴的方式发现一些判定甚至避免强制阐释的规则或标准。
[1]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1、271页。
[4][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文版序言,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页。
[5]周宪:《也说“强制阐释”——一个延伸性的回应,并答张江先生》,《文艺研究》2015年第1期。
[6]朱光潜:《整理我们的美学遗产,应该做些什么》,《文艺报》1961年7月第7期。
[7]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4卷,林同华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75页。
[8]韩伟:《国内都市文化研究潜存的三种模式及其理论构建》,《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9][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页。
[10][美]帕克:《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6页。
[11] Quoted from George P. Landow. Hypertext2.0: the Convergence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p.3.
[12]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1页。
[13]张江:《场外理论的文学化问题》,《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期。
[14]周宪:《文学理论的来源与用法——关于“场外征用”概念的一个讨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I02
A
1000-7326(2016)09-0001-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美学史”(12&ZD11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乐论与文论的关系谱系研究”(14CZW001)、黑龙江省普通高校青年学术骨干项目“中国古代乐统重建与文统分化的关系谱系”(1254G031)、黑龙江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辽金元音乐文学及其理论形态研究”(UNPYSCT-2015055)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韩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黑龙江 哈尔滨,1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