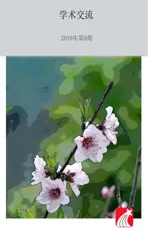政治·个人·性别——“十七年”女性文学的多元话语现象
2016-02-27李海燕
李海燕
(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政治·个人·性别
——“十七年”女性文学的多元话语现象
李海燕
(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十七年”文学中女作家在文学政治化体制的强制规训下普遍倾向于政治话语的阐述与表达,“十七年”女性文学因此呈现出强烈的政治化倾向。但女作家们的知识分子情结驱使她们选取知识分子题材、书写人情人性、传达批判精神,五四个人话语在她们的文本中不时闪现。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则驱使她们不自觉地选择日常题材、关注女性命运、聚焦情欲叙事,她们的文本因此呈现出相当的女性话语特征。于“十七年”女性文学而言,国家政治话语无疑处于叙述的中心,但个人话语、女性话语也在叙述的边缘发出自己的声音,“十七年”女性文学表现出多重话语纠缠的复杂矛盾特征。
“十七年”文学;女性文学;多元话语
从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十七年”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受市场机制和战争形态影响的现代文学多元格局被国家权力整合为高度政治化的“一体化”文学,“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形态、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等各方面均表现出“政治一体化”特征。“十七年”女性文学同样处于这一政治化体制模式中,在国家权力显性或隐性的规约下,女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普遍倾向于政治话语的阐述与表达。但“十七年”女性文学在表面的“一体化”之下,仍潜隐着多种文学形态和话语的存在,“它既是高度‘一体化’的, 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的复杂缠结”[1]。“十七年”女性文学的异质话语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与女性话语。作为被专政与改造的对象,“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五四的启蒙、个体意识被此时的原罪和救赎意识所取代,知识分子们处于身份如何归属的焦虑与不安中。但权力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本身存在“他者”与“自主者”的矛盾,而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精英意识和“独善其身”的高洁品格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随着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知识者个体差异表现出或隐或显的特征,传达知识分子自主意识的个人话语也就不自觉地呈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与男性创作相比,“十七年”女性文学的异质因素还表现为女性的性别意识和独特的审美体验。“十七年”女作家在顺应文艺政策、主动追随政治话语表现宏大叙事的同时,属于女性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审美传达及被压抑的女性意识始终存留在女作家的内心深处,并借助她们的笔墨在政治与革命的话语间隐秘地表现出来。
一、国家权力规训下的政治话语
“权力”“话语”是福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这两者也被福柯紧密联系在一起。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在某种条件下,它甚至转化为权力。不同的话语主体按照各自的模式行使话语权力,获得其他行为主体的权力须受相应的话语控制。不同时期的话语形态是多元的,但话语权的争夺决定了特定时期某一特定话语常常占主导地位,其他话语方式则处于边缘或压抑的状态。对于“十七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而言,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支配和控制着一切,国家话语是为国家意识形态认可和承认的主要话语,它遮蔽并压制了其他话语方式,这种近乎一体化的话语模式是在国家权力的强制规范和驯化中完成的,而权力的规训主要表现为改造和净化创作主体的思想认识、建立严格统一的文学生产机制和批评机制。对于“十七年”的女性作家们来说,她们同样面临着净化思想、规范文学创作的要求。
从创作主体的身份来看,“十七年”的女作家大多参加过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她们对革命和政治均满怀热情与忠诚。她们自觉遵守新生政权的要求,努力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国家主流话语的规范下进行文学创作。有些女作家因为身处政治高位,主动承担了文学一体化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她们宣扬文艺政策、传播政治话语,她们的文艺批评常常成为文艺思想批判和斗争的工具。如丁玲在经过了延安时期的思想改造后,主动向文学新体制靠拢,新中国成立后则熟练地运用政治话语,成为体制的中坚力量。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丁玲要求“文艺工作者也还须要将已经丢弃过或准备丢弃、必须丢弃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属于个人主义的肮脏东西,丢得更干净更彻底”[2]。主编《文艺报》时期,丁玲对所谓“文艺界的错误”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话语批评,如指责萧也牧的小说表现出反对“人民的文艺”的倾向,批评陈学昭、卢耀武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小资产阶级”面貌,等等。
丁玲对政治话语的主动追随与她高昂的政治热情、女性知识分子渴望身份认同的强烈愿望关系密切。这种自觉依附权力话语的文学创作行为在刘真、茹志鹃、杨沫、陈学昭、草明等作家身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从创作题材上看,革命历史题材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是国家权力话语规定的创作方向,它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但对于亲身经历过革命或生产建设,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女作家们来说,重大题材的选取又来源于她们内心深处的强烈意愿。如杨沫在《青春之歌·后记》中提到为逝去的战友们写一部小说是她的夙愿,“这些人长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来渴望有机会能够表现他们”[3]。自小便参加革命,有着“少共”情结的刘真更是将表现革命、讴歌革命人民视为自己的使命。从创作主题来看,女作家们对革命和建设的热情驱使她们将颂扬革命斗争精神、表现社会主义新貌、讴歌时代英雄视为首要任务,而这一主题的选择也是女作家迎合国家主流话语,为女性争取一定的社会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对于此时的女性作家而言,她们并不希望自己被冠以“女”字,“革命青年”“战士”是她们更为渴望认同的身份。这种模糊女性性别、以社会身份归顺国家政治话语的策略使女性作家们在文学一体化的时代中避免了被“清算”的厄运,留下了属于女性的声音。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堪称“十七年”女性文学的经典,作品在出版后颇受欢迎,“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售出了130万册,成为在这时期长篇小说仅次于《林海雪原》的‘畅销书’”[4]。茹志鹃的《百合花》则得到了茅盾的大力称赞,“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5]。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它前后印制了14版,发行量20余万册。草明的《火车头》首次开拓了工业建设题材,而草明也被誉为“中国工业文学的拓荒者”。“十七年”女作家们成绩的取得与她们主动迎合国家政治话语,以中性甚至男性的声音发话,将女性意识遮掩在革命话语和宏大叙事中的行为密切相关。这也正如苏珊·兰瑟所说:“任何一位女性作家都会对权威机构和意识形态持有双重态度,就如写小说并寻求出版社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话语权威的追求:这是一种为了获得群众、赢得尊敬和赞同,建立影响的企求。”[6]
“十七年”女性文学在创作题材、主题、人物塑造等方面表现出的政治话语特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女作家们试图获取话语权、争取社会身份的愿望分不开,但国家权力的强制约束与暴力规范更是女作家们不得不采取政治话语的重要原因。对于女作家尤其那些带有浓厚知识分子情结和女性意识的女作家们而言,权力话语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等问题上的强迫性限定经常使她们陷入生活体验与政策规范的两难选择。如丁玲在创作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时曾向家人致信表示自己的作品进展缓慢,感觉很难,“我不能把人的理想写得太高,高到不像一个农民。可是我又不能写低他们,否则凭什么去鼓舞人呢?”[7]杨沫《青春之歌》的最初构思是适应时代要求塑造革命英雄人物,但对人物的陌生和疏离使她始终处于矛盾与焦虑中,“总想写些东西,心头酝酿着那些我认识的英雄人物的生与死。但是,总又拖拉着没有写”[8]109。杨沫最终将革命英雄的讴歌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结合起来,写出了英雄指引下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史,从而达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规范要求。其他如茹志鹃的《百合花》着重书写战争后方的军民关系,刘真的革命历史小说多从儿童视角切入,李纳的作品也主要侧重部队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十七年”女作家们大多试图在国家权力的制约下寻找自我与规范的融合,并由此成就了一部部出色的著作。但女作家们的这种平衡因其文本隐约表现出的个人话语与女性话语受到了国家权力话语的严厉批评。宗璞的《红豆》因书写知识分子在面对革命与爱情抉择时的痛苦心情而备受批判,杨沫的《青春之歌》因表现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和思想而招致批评,柳溪因发表指斥时弊的《爬在旗杆上的人》被打成右派,茹志鹃的《百合花》被认为感情阴暗,刘真的《英雄的乐章》等作品则被评价为歪曲革命战争,等等。在招致了一系列的严厉批判后,女性作家们或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力,或陷入了写作的迷惘与焦虑中,有的时候她们甚至因自卑或赎罪意识而自觉中断创作。国家权力对文学一体化的严格限制迫使“十七年”女作家们不得不放弃个性话语的传达,转向符合主流话语的宏大叙事,在体制内尝试着她们的政治化写作。
二、知识分子情结影响下的个人话语
作为被国家权力话语改造和批判的贬斥对象,“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国家主流意识的询唤,努力摒弃自己的小资思想向工农靠拢。他们的创作也表现出抵制个人话语、顺应政治潮流的特征,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似乎已完全被整合进国家权力话语中。但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个体自我意识、精英意识以及承传五四的启蒙批判意识决定了他们在思想改造和身份认同中的矛盾和焦虑,而文艺工作者对艺术自主自律的执著认知及文艺创作的独特性又驱使他们徘徊于工农大众与知识者形象的塑造抉择中,知识分子的沉思及其独特的个人话语始终潜隐在宏大的主流叙事中,从而突破了国家政治话语一统文坛的单一局面,给“十七年”文坛带来了异彩。
对于“十七年”女性作家而言,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首先是通过题材的选取表现出来的。自延安整风后,知识分子题材选取便面临严峻的考验,但“十七年”女作家的知识者身份决定了她们在表现工农题材时的陌生与艰难,作家们试图以政治话语与个人话语相结合的方式解决这一瓶颈,从自我体验出发展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史与成长史。如杨沫在创作《青春之歌》时本能地倾向于书写以“自我”为主体的小说,“常常在构思我那篇传记式的小说。如此篇能写成,我感觉一定不会太坏”[8]109。而《青春之歌》亦如她的构思一般展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奋斗史。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的最初意愿是书写知识女性的人生之旅,后来的她虽因权力规范将小说叙述成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史,但小说仍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宗璞一直生活在校园,知识分子情结促使她选取知识分子作为主要题材,虽然这些作品大多侧重自我意识的革命改造,但小说中属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不时闪现,个人话语在她的《红豆》《后门》等作品中表现明显。而宗璞本人因“写作不能自由,怎样改造也是跟不上”等原因,“决不愿写虚假、奉命的文字,乃下决心不再写作”的行为更显其高洁的人格,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反抗意识在她的个体行为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9]
个人话语的典型表现是对人情人性的书写。“十七年”女作家惯于从情感层面表现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她们的作品充满了人情人性的书写,而爱情叙事无疑是她们个人话语的最好表达。如杨沫的《青春之歌》以林道静的三段爱情展现其革命成长史,宗璞的《红豆》以江玫的爱情演变写出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剧变时的艰难,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叙写了战争年代的爱情,柳溪的《我的爱人》则以“我”的情感发展来达到讴歌时代英雄的目的。虽然这些爱情叙事因意识形态的要求均裹上了政治和革命的外壳,但女作家们在爱情的发展和具体情感的表达上常常流露出个人主义倾向。如《红豆》中,宗璞用大量的笔墨表现了江玫与齐虹间浪漫而真挚的爱情,而江玫在个人情感与革命理想间的痛苦调和与抉择、失去爱情后的悲恸与感伤更是作家的着力之处。刘真《英雄的乐章》则敷衍了一段浪漫而忧伤的爱情故事,但也因此被定性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修正主义文学。
人伦温情在“十七年”政治规范的影响下被人们冠以“小资产阶级情调”而排除在国家意识形态之外,女作家们却常以曲折的方式将之潜隐到阶级情、同志爱中加以表现。她们深入主人公的感情世界,细腻地描写充盈于笔下人物间的亲情、友情及革命情谊。其中茹志鹃、刘真在展示人伦温情上用力颇多,《百合花》以几处细小的场景、几个细微的情节,将军民之间、战友之间的情感表现得纯真而温馨;《长长的流水》《好大娘》《高高的白杨树》《关大妈》等作品则将“大姐”或“大妈”与小八路之间的母女之情体现得曲折有致。其他如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王晓燕之间的姐妹情感,宗璞的《红豆》里江玫与母亲的相依为命,柳溪的《春》中秋波对公公既尊重、关爱又无奈、埋怨的复杂情绪,李纳《撒尼大爹》里撒尼大爹与“我”之间近似父女的深情,均被女作家们书写得真挚生动、自然而随性,人情人性的美好温馨在她们的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传达。
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五四启蒙精神一直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使他们试图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以清醒而犀利的眼光剖析社会和人性深处的痼疾。“十七年”女作家亦深受时代的影响,在“干预生活”的大讨论中相继诞生了《爬在旗杆上的人》《我的爱人》《假日》等揭露与批判社会黑暗面的作品。在《爬在旗杆上的人》中,柳溪以细腻清新的笔触将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中的官僚者朱光与形式主义者李震刻画得栩栩如生,对合作社时期讲究形式和宣传、注重名誉和权力而不关心民生疾苦的官僚作风进行了细致而有力的批判,从而实现了作者大胆地直面现实、批判现实的目的。在《我的爱人》中,柳溪借英雄之口喊出了人们的心声,“他们不能允许一个不关心别人疾苦只追求数字目标的官僚主义管理工厂!”陈布文的《假日》对机关的形式作风有所揭露。小说以大量的笔墨渲染新婚妻子因丈夫会议过多而孤独寂寞的情绪,既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又流露出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小说虽然不是创作于同一时期,但知识分子启蒙精神的潜存仍然使她们的作品充满浓厚的批判意识。如宗璞的《后门》对当时的“走后门”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则塑造了一个颇有个人意识的英雄形象张玉克,在张玉克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对音乐的迷恋、对个人幸福的向往、对死亡的慨叹,其中对战争杀戮的厌倦彰显了张玉克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在一个知识分子被规约和边缘化的时代,宗璞、刘真等女作家们敢于直面现实、剖析人性,这无疑是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曲折传达。
三、性别体验指引下的女性话语
“十七年”期间,女性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国家政权赋予了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享有与男性同等地位的权利。一方面,“十七年”的性别解放给数量众多的女作家们提供了“一间自己的屋子”,而社会地位的变化促使女性对人格独立有了更多的要求,女作家们证明自我、表达自己的欲望也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十七年”女作家虽然竭力削弱自己的性别特征,但女性的性别身份决定了她们大多选取女性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而女性独特的生理特征和生命体验又驱使她们在“写什么”及“怎么写”上呈现出与男性作家较大的差异。与男作家相比,“十七年”女作家对日常生活题材、女性生存书写等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而女性情欲叙事更是女性话语的有力表现。
伍尔夫认为,女性在历史上幽闭的境遇造成了女作家们的写作常常局限于家庭。“十七年”女作家虽然走向了社会,但仍然承担着繁重的家庭劳务。历史文化与现实环境影响着女作家们普遍倾向以日常生活题材敷衍宏大叙事,女性写作由此表现出对主流话语的疏离感。张爱玲的《十八春》《小艾》是新中国成立后她为适应主流意识形态写就的作品,小说虽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化倾向,但作品对日常生活空间的观照仍延续了她以往的创作风格。《十八春》是日常生活中的爱情悲剧,整个故事均围绕着家庭而发生:曼桢与世钧的爱情在一次次家庭拜访中升温,但也因双方家庭尤其是曼桢姐姐的介入而以悲剧告终。《小艾》则详尽地描写了旧式家庭和平民百姓的日常家庭生活,从而构成了一幅旧上海的日常风俗画。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展现了知识女性李珊裳的思想成长史,但拙于政治修辞的陈学昭主要以政治家庭化的方式展现李珊裳告别“旧我”走向革命的人生旅程,她的文本因此呈现出疏离政治话语的性别意味。以战争和斗争题材为创作重心是“十七年”女作家融入主流的主要方式,但女性身体特征决定了她们无法亲历和直击战争,只得以旁观者的身份在日常生活中书写革命和斗争,正是这种选择使她们的文本体现出性别话语的特征。茹志鹃的《百合花》以赶路、借被子、缝衣服等几个日常情境刻画了一个可亲可爱的平民英雄形象。刘真的《英雄的乐章》《长长的流水》等小说也都充斥着日常生活话语。李纳的《撒尼大爹》和《婚礼》均属于革命题材,但斗争在她那里依然以背景和日常的面貌出现。另外,与男性作家对战争持乐观和礼赞态度不同的是,女作家将关注的目光大多投放到战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破坏与使之中断上,“十七年”女作家的战争文本因此散发出一股难以抚平的感伤气息。
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是“十七年”女作家传达女性意识的一个有力途径。“十七年”女性走出家庭,承担相应的社会任务,但以男性为主导的话语结构又要求女性继续在家庭中做好“贤内助”,社会给女人们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韦君宜的《女人》主要叙写了新时代女性为争取人格独立而反抗家庭男权的故事,《阿姨的心事》则讲述了家庭妇女李玉琴在走向社会过程中迷惘彷徨乃至坚定自我价值的故事。诚然有人会说这两个作品是典型的女性实现“男女一样”国家政治话语的文本,但我们更多地看到了韦君宜对女性个体的尊重,对男权话语的反抗。“十七年”女作家对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悲苦命运也颇为关注,《十八春》无疑是这方面的出色之作。有着现代女性意识的曼桢因不见容于传统文化和周围环境而陷入爱情悲剧,为家庭生计所迫堕入风月场所的曼璐上演了一出由社会的受虐者转化成施虐者的命运悲剧,封建家庭中的石翠芝则经历了梦醒后却无力冲出家庭、追求自我的人生悲剧。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注使《十八春》明显成为裹着政治外壳张扬女性话语的文本。《青春之歌》的女性苦难也十分突出。透过林道静的个人成长史,我们能清楚地找寻到传统家庭中的性别压迫和性别冲突。出身于旧式封建家庭的林道静一直遭受着父母亲的性别歧视,和余永泽结合后的小家庭同样存在着性别拘束和压迫,林道静在与命运抗争过程中最终成长为革命战士。作为“十七年”时期的女作家,杨沫等人的创作不能不冠以显性的革命或政治话语,但她们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关注、对男女性别冲突的书写却使她们的文本透露出明显的性别话语。
情欲叙事对排斥一切小资情调的“十七年”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禁忌,可仔细审视“十七年”的女性文本,我们依然能发现情欲这一异质元素的存在。这一存在极大地拓展了女性自我的表达空间,是“十七年”女性文学中性别话语的强力展现。柳溪在情欲叙事上的表现颇为突出,她的《鸭倌陆文俊》将女性的情欲追求书写得大胆而热烈。年轻丧夫的田寡妇爱上了英俊高大的陆文俊,她带着女性的羞涩以整理葡萄架为借口接近了他。约会前的一刻,她精心打扮;一起劳动时,她心慌意乱;鸭倌拥抱时,她则沉浸于两人的甜美性爱中而毫无畏惧。在田寡妇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反抗伦理违逆道德、精心大胆而又些微羞涩地追求自我情欲的现代女性形象。杨沫的《青春之歌》在国家政治话语的掩盖下也隐藏着热烈而大胆的情欲叙事。作为一个单纯热情爱幻想的现代女性,林道静内心深处一直渴求着肉灵一致的爱情,而卢嘉川则是她情欲的理想对象。文中对林道静有一大段充满情欲的梦境描写,它隐晦地传达出林道静对卢嘉川一直以来的强烈欲望和冲动。其他如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宗璞的《红豆》、柳溪的《我的爱人》等作品均隐晦地对男女主人公的欲望作了较为曲折的表达,“十七年”女作家们的情欲叙事让我们明显感受到女性话语的存在,“十七年”女性的性别主体意识在她们的情欲追求与释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与管理的一体化文学,“十七年”女作家们在自我身份认同和国家权力的强迫性约束下或主动或被动地采取政治话语传达她们的文学诉求。但“十七年”女作家亦有作为知识分子和女性两者的身份体验。知识分子情结影响着她们经常以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人情人性的书写、批判精神的继承更使“十七年”女性文学的个人话语得以传达。女性独特的身体特征与生命体验则驱使她们不自觉地选择日常题材、关注女性命运、聚焦情欲叙事,她们的文本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女性话语特征。“十七年”女性文学矛盾而多元,充满了异质话语的存在。在政治话语的主导下,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女性话语以曲折隐晦的方式顽强地生存着,“十七年”女性文学因此表现出多重话语纠缠的复杂特征。
[1]吴秀明.论“十七年文学”的矛盾性特征——兼谈整体研究的几点思考[J].文艺研究,2008,(8):15.
[2]丁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M]//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08.
[3]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533.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8.
[5]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M]//茹志鹃研究专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251.
[6][美]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
[7]丁玲.致陈明[M]//丁玲全集(第1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0.
[8]杨沫.自白——我的日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9]宗璞.宗璞文集(第4卷)[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336.
〔责任编辑:曹金钟孙琦〕
2015-12-14
李海燕(1975-),女,湖北钟祥人,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7
A
1000-8284(2016)09-0178-05